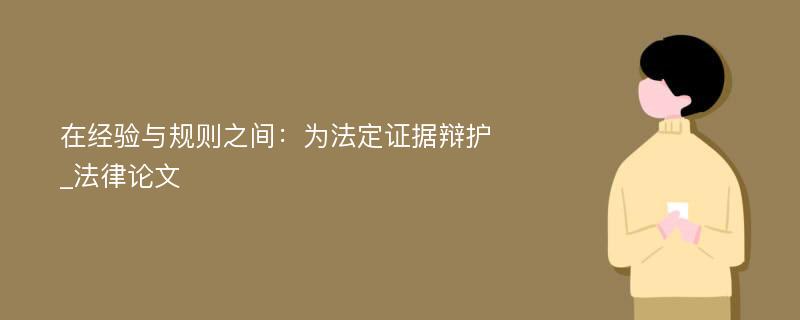
经验与规则之间:为法定证据辩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证据论文,规则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证据证明力的评价,是采自由心证,抑或采法定证据,目前学界已渐趋达成共识,认为自由心证取代法定证据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实务界对法定证据却天然地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认为在没有一定规则可遵循的情况下,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无所适从,因此纷纷呼吁立法来予以规制。为适应这一需求,2002年出台的民事和行政证据规定以及四川省公、检、法新近公布的刑事证据意见等,都用专条对证据的证明力作了规定。这里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在理论界普遍认为法定证据该寿终正寝的时候,而实务部门对之却难舍难分,是实践违背了理论,还是理论本身出了问题?
一、对法定证据的误读
法定证据一般是指“一切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以及对证据的取舍和运用,都由法律预先明文加以规定,法官不得擅自评断和取舍。”(注:崔敏著:《刑事证据理论研究综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不难看出,这里的法定证据,是建立在和自由心证比较基础之上的,其主要渊源于1790年杜波尔在法国制宪会议上一段经典表述,但是杜氏在论辩时对法定证据进行的剪裁性描述,并不能反映法定证据的全貌,而据之对法定证据作出的判断就难免会出现以下两个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之一:没有区分形式的法定证据和实质的法定证据,把法定证据片面地理解为形式的法定证据,即认为法定证据只规定证据的证明力,而不涉及其证据能力。的确,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定量分析”确实是法定证据的一大特色之处。但是,规定证据的证明力只是法定证据的内容之一,对证据能力的规范也是其应有之意。陈朴生先生将前者称为形式的法定证据,而把后者视为实质的法定证据:“在法兰西革命前,在采纠问制度之裁判,为防止裁判官之专断,乃以法律规定其证据之价值,具有一定证据者,不问裁判者之心证与否,均得为一定事实之认定,称之为形式的法定证据主义;英美法为利于当事人诉讼之进行,并适应陪审裁判之要求,就证据能力,即证据之许容性严加限制,以拘束当事人辩论之范围与方法,寻求合理之证据,或称之为实质的法定证据主义。”(注:[台]陈朴生著:《刑事证据法》,台湾三民书局1970年版,第66页。)尽管是在两种不同语境下的使用,但应肯定,法定证据并不排斥对证据能力的规范,即便是在法兰西革命前也是如此,在刑讯逼供已成为当时主要之侦讯手段时,法定证据一般要求对拷问的要件、程序、程度以及口供的记录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如法国1670年王令规定,拷问必须在满足:1.可判死刑的重罪案件;2.犯罪本身确实发生;3.至少存在半证据这三项要件才能进行。如有违反,则发生两方面的法律效果:一是口供失权,不能据之认定案情;另一是拷讯者被追究相应责任。(注:王亚新:“刑事诉讼中发现案件真相与抑制主观随意性的问题”,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2期。)
误区之二:没有区分积极的法定证据和消极的法定证据,把法定证据简单地等同于积极的法定证据,即认为裁判者在审查运用证据过程中,必须听命于法律,是法律的“自动售货机”。然而,随着认识的深化,人们逐渐转采向消极的法定证据。一方面,“在欠缺法律所预定的必要的证据的时候,不许论罪,即便其已形成心证。”(注:王亚新:“刑事诉讼中发现案件真相与抑制主观随意性的问题”,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2期。)“在有些案件中,法官不能宣布事实已被证明,尽管法官自己认为某一事实是真实的。因此,可以把这种消极的作用比作广泛的补强证据规则。”(注:[美]达玛斯卡著:《漂移的证据法》,李学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另一方面,在证据达到法定要件时仍允许法官保留怀疑的态度,进一步搜集证据乃至对被告人作其他处分。也就是说,在要求严格遵循证据规则的同时,还需要裁判者形成内心确信,否则不能定罪量刑。例如,对于被告人之自白,加洛林纳法典后来允许法官继续调查取证,1670年王令要求要有其他半证据来排除怀疑。
到了后期,这种消极理论的趋势更加明显。如1853年《奥地利刑事诉讼法》对被告人自白的要求之一就是“必须与重要各点和有关犯罪行为的现有资料相符合。”1857年《俄罗斯帝国法规全书》对口供要求最重要的一条是:“所陈述的行为情况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不能使人有所怀疑。”(注:See A.Esmein,"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Procedure,"TheLaw Book Exchange,Ltd,2000.)正如乔纳森·科恩教授所说:“在旧制度下,法律同样具有这种要求的含义,即一名正直的法官在作出有罪判决之前也应该对充分证据的存在达到确信的程度。”(注:何家弘:“为‘自由心证”正名”,载《法学杂志》1997年第6期。)因此,把法定证据等同于积极的法定证据,“是建立在对法律历史的普遍误解之上的,无论就宗旨还是适用而言,罗马教会证据法都很少强迫法官做出违背其判断或‘良知’的裁决。”(注:[美]达玛斯卡著:《漂移的证据法》,李学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二、对法定证据批驳理由的质疑
正是缘于以上对法定证据的误读,各个教科书和论著在论及证明模式时,一反上个世纪80年代前意识形态领域对自由心证的口诛笔伐之常态,几乎一致认为法定证据已丧失其存在的价值,最终为自由心证所取代是历史的必然。抛开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等原因,单就制度本身来说,其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第一,经验法则的无限性决定了建立有限规则的不可能性。“法定证据制度对证据证明力的规定过于刻板,过分注重证据及证明活动的一般情形,而忽略了不同案件中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形,忽略了个案证明中的特殊情形。”“其将审理某些案件中运用证据的局部经验,当作一切案件收集、判断证据的普遍规律。”这种用普遍判断代替个别判断,“用法律预先规定的僵死标准来判断证据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在证据制度中的典型表现。”(注:王国枢著:《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因此,“在涉及论据和证人之可靠性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制定出真正确定的规则。”(注:Baldus de Ubaldis,Codicem Commentaria.See Mirjan Damaska:"The Death of Legal Torture,"87Yale L.J.860(1987).)
第二,经验法则的灵活性决定了建立确定规则的不可靠性。法定证据制度“使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只充任着‘账房先生’的角色,只能根据法律上僵化死板的规定,对每一案件中的证据的证明力加以相加计算,按照计算结果认定案件事实,依这种刻板的断案方式是难以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的。”(注:刘金友著:《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法定证据原则往往是牺牲发现真实的诉讼目的来保障抑制法官主观随意性的理念,换言之,是在某种程度上以牺牲诉讼的可靠性来确保诉讼的可信赖性。”(注:参见王亚新:“刑事诉讼中发现案件真相与抑制主观随意性的问题”,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2期,第121页。)
第三,法定证据的形式性决定了其与刑讯逼供的天然联系性。“法定证据制度另一个弊病就是与刑讯拷问的内在联系。”(注:参见王亚新:“刑事诉讼中发现案件真相与抑制主观随意性的问题”,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2期,第121页。)因为“形式的和理性的两方面证据的刻板僵硬,经常使得在刑事案件中确定定罪依据变得十分困难。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其他什么原因,最终导致了广泛地使用刑讯手段获取证据,尤其是获取‘证据之王’——口供……最有资格对思想状态作出证明的莫过于被告人自己,而能够保证被告人供认他的思想处于犯罪状态的有效方式又莫过于刑讯。”(注:[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贺卫方、高鸿钧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313页。)
对此,笔者分别做以下回答:
关于第一个理由,不可否认,社会现象是千差万别的,我们很难对社会科学进行“量化”或是“数字化”管理,对证据的证明力的大小、强弱,我们不可能设计出万能公式对之“一网打尽”,要依凭人们的经验、常识等进行灵活判断,经验法则的无限性和盖然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的经验上升为规则。但是,一方面,在我们常说的经验或逻辑的背后,有没有基本的、一般性的规律可循,这种经验或逻辑本身是否也隐含着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如果有的话,那么,随着经验的积累和人们认识的深化,立法者是否可以将这种经验或逻辑背后的不成文的“潜规则”进行归纳、整理,使之成为一个能看得见的、可触摸的“显规则”呢?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对于证据证明力的认定是“像雾像雨又像风”,从而使之成了一门“玄学”的话,不仅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同时,陷入“刑不可知而威不可测”的臼窟,证明也会因缺乏可预测性和可操作性而丧失其应有之功能。
另一方面,这里的规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具有开放性和可反驳性。因此,在经验的无限性和盖然性决定了所有经验上升为规则不可能的同时,规则的一般性、开放性和可反驳性又决定了部分经验上升为规则的可能性。事实上,德国学者卡塞尔就把经验分为“生活性经验法则”和“实验性经验法则”,并认为对后者可直接检验和予以规制。(注:W·Kasser;Wahrheister forsschung in Strafprozess,D.T.Uerlag,1974.S.91.)
我们知道,在人类之初,是没有成文法律的,只是随着认识的深化才逐步将以经验为主的习惯法上升为以规则为主的成文法的,在这种转化过程中,也存在着社会现象的多样性和法律条文僵硬性的矛盾和冲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习惯渐变为成文法律。证据也不能例外,证据立法就是一个不断从经验法则到证据规则的过程,对证明力规范尤为如此。事实上,“从本质上讲,证据规则也是一种经验……我们制定证据规则,主要就是要将经过司法实践检验的,能够正确指导法官判断证据的经验上升为规则。”(注:江伟、徐继军:“经验与规则之间的民事证据立法”,载《法学》2004年第8期。)当然,这个过程首先是一个价值选择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技术过程。对此,亚里士多德说得最明白不过:“从经验所得许多要点使人产生对一类事物的普遍判断,而技术就由此兴起”(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页。)。
关于第二个理由,一方面,从法定证据的具体设置来看,虽然其无法保证每一案件的真实发现,但对于大多数案件是没有问题的,至少法定证据的普遍认知性可以强化认定结果的可接受性。例如,加洛林纳法典规定两名典型证人证言是完全证据,法官可据此定罪量刑。虽看似刻板,实不无道理。因为所谓的典型证人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两人彼此无关;二是品信良好;三是陈述一致。再如《俄罗斯帝国法规全书》规定构成坦白的要件是:1.自动的坦白;2.在审判机关里在法官面前进行;3.坦白与已经过去的行为完全符合;4.所陈述的行为情况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不能使人有所怀疑。试问在这种证言、坦白面前,即便法律不做规定,我们还能“心证”出别的“事实”吗?
另一方面,从证明目的看,法定证据也并不排斥对客观事实的追求。的确,积极的法定证据确因僵化而不利于发现真实。但是,对于消极的法定证据,如果证据没有满足法定的要件,即便法官已形成心证,仍不能定罪量刑。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枉纵犯罪,但从另一角度,也最大限度地防止了冤假错案的发生;而对于那些已满足了法定条件,但法官尚不能形成确信的案件,仍要求继续调查取证,相对于自由心证,无疑更有利于案件事实的发现。正如学者所言:“消极理论不同于积极理论的,是大大减轻了刑事证据理论的畸形弊害。”(注:[前苏联]安·扬·维辛斯基著:《苏维埃法律上的诉讼证据理论》,王之相等译,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90页。)同时,囿于认识能力的限制,为了达到对案件真实的认识,法定证据对于不同的案件,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影响等设定了不同的证明标准。例如法定证据萌芽时期的《格尔蒂法典》规定:“若有成年的证人作证,法官根据证言判决。涉及一百或以上斯塔特的案件,要有三人作证;涉及十斯塔特的案件要有二人作证;涉及更小额的案件,要一人作证。”(注:由嵘等主编著:《外国法制史参考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法律之所以有不同要求,是在当时认识条件下,难以对所有案件都达到客观真实不得已而为的办法,由此其对案件真实的追求也可见一斑。
关于最后一个理由,法定证据是否与刑讯逼供存在必然联系?换句话说,刑讯逼供是否是法定证据的产物?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且不说刑讯逼供是诉讼模式、刑事政策、科技水平和人权观念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恐非是法定证据独能承受之轻。单就以下三个问题,就是此说所难以解答的:第一,在我国古代社会,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定证据制度,可为什么也普遍地存在着刑讯逼供呢?第二,在法定证据制度产生之前和如今践行自由心证的国家,是不是就不存在刑讯逼供呢?第三,法定证据制度对刑讯条件和拷问手段等的规范,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刑讯的滥用起到了抑制或缓解作用呢?诚然,法定证据制度认为口供是证据之王,这在客观上确是助长了刑讯逼供之风。但是,撇开这是当时人们认识手段不足,不得已而付出的合理代价外,“口供至上”只是法定证据制度大厦的内容之一,即便其再“恶”,也不能轻率的得出整个法定证据皆“恶”,法中也有“恶法”,我们是否也会因“恶法”中的“恶”而抛弃整个法律制度呢?
事实上,法定证据制度在功能目的上是为防止司法官吏任情枉法、滥用酷刑而出台的,只是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在一定程度上对刑讯逼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仅仅是在操作层面上的技术问题,不能因之而否定整个制度。“证据充足率……本来是启蒙运动与封建专制长期斗争中确立起来的人权屏障,现在,却被当作旧制度的恶瘤加以铲除了。”(注:朱学勤著:《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95页。)殊不知,在国家允许刑讯逼供的大背景下,正是法定证据对被告人口供的获取和运用设置了严密的规则。
三、从经验到规则——为法定证据辩护(注:这里是为“法定证据”辩护,而不是为“法定证据制度”辩护,后者是指一定语境下的具体制度,而前者则是一种证明模式或方法。同时,鉴于学界对规范证据能力已无争议,故在此仅对规范证明力进行论证。)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化为我们规范证据证明力创造了条件。一方面现代工业革命对传统的认知方式提出了挑战,特别是21世纪以来,对于案件事实可以通过精密的设备和仪器予以揭示,更是让传统的凭直觉和“五听”等断狱方法显出了几分窘迫。与此同时,现代科技中的数字化革命,如对生命基因的编码等却又为我们化解这一矛盾提供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正处于从定性分析向定量管理的过渡时代。“科学将作为优势资源继续发展,精密复杂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将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注:这里是为“法定证据”辩护,而不是为“法定证据制度”辩护,后者是指一定语境下的具体制度,而前者则是一种证明模式或方法。同时,鉴于学界对规范证据能力已无争议,故在此仅对规范证明力进行论证。第205页。)具体到法学,精密司法、技术司法也越来越为学界所重视。对此,林山田认为:“对于科学业已证实之事实证据,法官惟有采信,而不能以其自由心证而拒绝之。换言之,即一个已经科学研究而证实之事实,尽管法官个人怀疑其真实性,或其本人因欠缺此等专业知识,而无法自己证实者,亦应采信而认定具有证明力。”(注:[台]林山田:“论刑事程序原则”,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8卷第2期。)因此,“‘当用自然科学的知识可确定一事实时,此时法官的心证即无适用之余地。’……法院必须拥有一可能性,即其应可运用‘一虽在经验科学上尚存争议性,但是终究是已通过良好的证实,并且为该学术领域中相当多数学者所公认的一般法则’”。(注:BGHST10.211;Puppe,1994.参见Claus Roxin著:《德国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可见,和经验法则不同,科学证据作为“形而下”的东西,为我们制定证明力规则创造了条件。“这些规则,就象多伯特案中所解释的那样,涉及到必须以某种方式得自于科学本身的一些准则。”(注:[美]肯尼斯·R·福斯特等著:《对科学证据的认定》,王增森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26页。)而且,“在使用科学这一工具解决司法争端的过程中,法庭必须给之以必要的尊重。”(注:Edward Cheng;Thomas S.Kuhn and Courtroom Treatment of Science Evidence,Temp.Envtl.L.& Tech.J,1996.Fall.195.)“只有在证据涉及专家方法或程序可靠性,而非专家的结论或行为的时候,法官才考虑其可信性。一旦证言可采,陪审团必须确认该证言的证明力。”(注:Developments in the Law-Confronting the New Challenges of Scientific Evidence.Harvard Law Review,1995.108.1523.)
可见,在物证技术中,在一定的程序保障下所得出的数据,再经进一步数理逻辑分析所得结论,自然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如对DNA的同一认定等甚至可以视为法定证据制度下的“完全证据”。“这种量化的标准有利于证据采信的统一规范,也便于司法实践中操作。”(注:何家弘:“对法定证据制度的再认识与证据采信标准的规范化”,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至于人证领域,在现有的科技条件下对之进行数字化管理尚有难度,但随着心理学、生理学和测谎仪等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应用,相信在不远将来,至少我们可以建立一些“灰色模型”对之进行大体的描述。
其次,我国的司法现状决定了我们规范证据证明力的必要性。法的最基本功能之一是其规范和预测作用,法定证据中的有关证据能力的规则自不待言,对证明力的规范同样不可或缺,尤其是在我国法官素质不是很高的特殊国情下,更是显示出某种程度需要的迫切性。“无论法官怎么样,他们总是人……立法者由于是通过一般法律处理事物,而不是通过个别判决处理人,因而不会怀抱偏见。他应当用明确的和固定的规则指导负责对人和私人利益作出判决的法官。”(注:[法]罗伯斯庇尔著:《革命法制与审判》,赵涵舆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0-31页。)而且“法官的理性基础和人格因素并非一成不变、永远可靠,将统一的司法裁判要求委任于并不统一的人格条件,就好像把一座高楼大厦建造在松软的沙滩之上,必将面临随时坍塌的危险。”(注:[日]庭山英雄著:《自由心证主义》,学阳书房1983年版,第23页。)
同时在实践中,一方面对证据的证明力由于缺乏最基本的评价规则,时常会出现举证、质证时“赢得了法庭”,可在认证时却出乎意料地“输掉了官司”。而证据采信、采纳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让当事人也只能是“有苦说不出”,这种对诉讼结果的可预测性的匮乏,会深深地挫伤当事人对“证据裁判”的信赖,痛定思痛而转向对证据以外的诸如“打点”、“勾兑”等非法律手段的追求。另一方面,由于在证据评价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规范,因此采取了事前预防、事中保障和事后救济等措施。不可否认,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对心证的制约作用,但也各有其局限性。如责任追究制度,往往会使裁判者因害怕受到追究,而“自由”得让一些在普通人可以形成“心证”的案子,只因为缺少“必要的印证”而不敢定案。这种“不敢定案”也从另一侧面彰显了在我国现阶段法官素质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法官自身对法定证据的“路径依赖”和制定一些基本的评价证明力规则的必要性。实践中“印证证明模式”(注:参见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的出现,就是这种对证明力规则需求旺盛,而供给却又相对不足的矛盾下的特殊产物。
最后,法定证据和自由心证区分的相对性,为规范证据证明力进一步提供了空间。一般认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方法或手段一是常识,二是科学。一般常识我们可以根据经验、情理自由心证;对于那些具有普遍规律性的常识,我们可以将之上升到规则的高度实行法定证明;至于科学,由于不能为普通公众所认知,在具备一定可靠性保障而可采的情况下,实践中也都别无选择地赋予了其法定的证明力。同时,“常识与科学在刑事司法中的运用不是绝对分离的,常识性认知中有时包含有科学的原理;而当一种科学知识在司法证明中反复使用并得到普遍的认同时,它往往就转化成了一种常识。”(注:参见熊秋红:“从‘科学的证明方法’谈起”,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因此,自由心证和法定证明的区分是相对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可以交融的“亦此亦彼”的关系。
事实上,两种类型划分只是为了便于研究,而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证据制度典型特征进行的模型化描述,在现实生活中纯粹的法定模式或自由模式都不存在,即便是在各自产生之初,法定证据并不绝对排斥法官的心证,自由心证也或多或少地要接受某种规则的约束。再将这种区分绝对化,认为自由心证就可以不要任何法定的证据规则,或者法定证据就完全排除了法官对证据的自由判断,并不符合各国的历史和现实。如在自由心证发源地法国,在经济与税收犯罪案件中,除非提出相关笔录属于伪造的证据,否则笔录具有证明力(海关法典第336条);在违警罪犯罪案件中,某些技术装置所作的记录,除非行为人举证证明其运转不良,否则都具有法定的证明力。(注:[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71-772页。)德国也有学者认为:“书证是对过去事件的最保险的证据”(民事诉讼法第415条及相关条款)。反之,“人证是最经常的证据并且——除了询问当事人外——是最差的证据。”(注:[德]奥特马·尧尔尼希著:《民事诉讼法》,周翠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287页。)
因此,“司法中的证明活动……不可避免地会渗入审理者对证据的分析判断,即心证的因素。另一方面,审理者运用和判断证据必然会带上法定的因素,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心证。”(注:李浩:“民事证据立法和证据制度的选择”,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这也可从自由心证的倡导者之一——罗伯斯庇尔前后的思想转变窥见一斑。罗氏曾比较激进地认为:“审判所需要的证据……只要能够得到所有正义和有责任心的精神上的自然确证即可,审判规则就是陪审员那颗经过爱国主义启蒙的良心。”(注:[美]哈罗德·布罗姆著:《卢梭和道德共和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5-256页。)可是到了后期,罗氏对此却不无顾虑:“法律应当要求这一点来制止任意摆布,在这方面法律所定的规则,是明智和无私的结果,因为这种规则是一般性的。”但与此同时“这些规则在实践中往往被特殊情况所推翻,这种特殊情况是立法者预见不到的,不能做详细规定的,而是只有法官才能知道的。因此,必须用法官的知识和个人信念来补充法律一般预见所不能包括的东西。”最后罗氏得出结论说:“要把法定证据所具有的信任同法官的内心确信所获得的信任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法定的证据,陪审员不能宣布犯人被证明有罪;如果陪审员的知识和他们的个人信念同这种证据有矛盾,他们就可以而且应该宣布犯人未被证明有罪。”(注:[法]罗伯斯庇尔著:《革命法制与审判》,赵涵舆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33页)类似的情况,在德国著名法学家弗兰杰瑞的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注:Flangiere,System der Gasetzgebung.参见陈浩然著:《证据学原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177页。)
四、法定证据语境下的证明力评价
在分析了对证据证明力规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接下来就是具体规范的问题了,这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非一时一己力量所能胜任,在此仅提供路径分析。对于证据证明力的评价,抛开刑事政策、人权保障等因素,单就规则本身,应坚持以下几个标准:
第一,普遍认知性。制定证明力规则的过程就是从经验到规则的过程,那么这一规则就必须为人们所普遍认知,包括从一般经验到证据规则的社会公众认知和从特殊技能到数理模型的专家同行认知。但与此同时,由于受主客观等因素的制约,可能存在偏离事实的情况,允许偏离多大或者说在多大范围内偏离,这就涉及到我们普通公众能够接受的程度,制定评价证据证明力的上限不能突破我们的道德所能容忍的底线。换句话说,在底线范围内的不可避免的偏离,应限于我们在从经验到规则过程中所能承受的合理代价。
第二,开放性。经验法则的无限性和个体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制定一个普遍适用的万能规则,因此,从经验到规则的过程只能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成熟一个,制定一个,不能一蹴而就,而且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力求最大限度地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认识能力的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进入人们的认识视野,同时有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证明力很强的证据,也会因人们获得了新的认识而丧失其效力,神明裁判就是典型例证。因此,对于证据证明力规则,应保持一开放的体系,不断积累、完善、刷新。
第三,可反驳性。就确定性程度而言,规则包括强制性规则和指导性规则两类,对于证据证明力规则无疑也应分属于两种情况,但仔细分析,除了“口供补强”等少数否定的强制性规则外,其他绝大多数证明力规则都应是指导性的,也就是说,即便符合了证据规则要件,但如还不足以让裁判者形成确信,或者其内心尚存疑问时,并不当然确认其效力,即属前文所说的消极法定证据之一种,这是由经验法则的盖然性决定了的。因此,法定证据应当允许裁判者内心的疑问对之进行“反驳”,当事人也可以提出有效“异议”,而且,法律应在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对这种“反驳”和“异议”提供保障。
基于上述特点,落实到证明力的具体评价,一般应从单个证据的证明力强弱判断和多个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判断两方面考虑。
对于单个证据的判断,通常存在两种情况:一是从否定的角度,法律强制规定某些证据不具有证明力或不具有完全的证明力,前者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4-415条规定的品格证据规则、习惯证据规则、事后补救规则、和解证据规则等等,因缺乏相关性而不具证明力被排除;后者如补强证据,最为经典的例子是关于单凭口供不能定案的规定,同时,我国民事证据规定和行政证据规定还规定了另外五种(第69条)和七种(第57条)需要补强的情况。二是从肯定的角度,在特定条件下法律赋予某些证据以完全的证明力。与前文的“口供补强”正好相反,在美国等实行‘辩诉交易’的国家,犯罪嫌疑人的有罪答辩,可以视为其典型代表。这里也存在着两种情况:其一,法律明确规定对某些证据裁判者应确认其证明力,如我国民事证据规定第70、71条列举的五种法院应当或可以认定其证明力的情形,德国刑法第190条规定的侮辱罪成立的几种情况等;其二,法律并不明确规定某些证据的证明力,而是隐含于诸如推定、自认等认定案件事实的规则之中。透过概念语言的表象,这实际上是对特定证据的证明力的一种间接规定。
至于多个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判断,比起单个证据来更需要一些智慧和勇气,实践当中也非议颇多。但还是有一些脉络可以大体遵循,这一点就连强调自由心证的陈朴生先生也不否认:“此类证据,其证明力从一般情形言,本可以下列标准定之:1.直接证据较间接证据为强;……9.无疑义证据较有疑义证据为强。”(注:[台]陈朴生著:《刑事证据法》,台湾三民书局1970年版,第577-578页。)这在我国民事证据规定第77条、行政证据规定第63条和刑事证据意见第33条也有类似规定。当然,受种种条件的限制,以上规定并非无懈可击,甚至有相互矛盾之处。如行政证据一方面规定:“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同时又规定:“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这是需要不断完善的技术问题,也是我们今后研究所应着力之处。
目前,证据法学的研究多集中在证据上,对证明的研究似显不够,且主要分布于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两部分,前者由于研究方法的擎肘,在理论上已经“山穷水尽”了;后者也陷于认识论上的臼窟,最终演变成了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争论。而与当事人利益攸关的证据评价,也都扔给了“经验法则”而殊少论证。这一点,已为学者所警觉:“‘证明的科学’是先于证据的审判规则的,也是比证据规则更重要的。可是,在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中,‘证明的科学’被忽略了”。(注:[美]约翰·W·斯特龙等著:《麦考密克论证》,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因此,加强证明法学的研究,对心证的形成和证明力进行规范和评价,无疑将是未来证据学研究的一个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