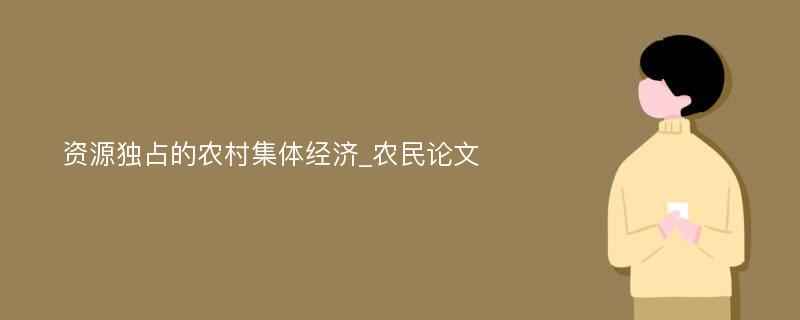
资源独享的村庄集体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体经济论文,独享论文,村庄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农村改革打破了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中体制,在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户重新成为独立的生产者。伴随着集体耕地的分户承包和集体资产的分配,村庄集体在经济发展上的作用大大降低。农民人均收入中从集体统一经营中得到的部分,1981年为116.20元,占全部收入的50%强,而到1989年则只有56.62元,不足10%; 家庭经营的纯收入则从84.53元上升到494.22元,由1/3强上升到80%以上。(注: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529页。)但是,在普遍的分散化趋势下, 也有一些村庄的集体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村庄集体经济。这些村庄都有比较发达的非农产业,村庄的集体经济实力很强,村级组织在村中有很高的权威,并执行社会再分配的职能。
这种现象已经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但研究成果尚嫌不足。(注:参见本课题报告之一——王晓毅:“国家、市场与村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与制度研究室:《大变革中的乡土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版。)研究者们更多地强调这种现象产生的合理性,而对其产生的特殊背景则关注不够。事实上,村庄集体经济并不完全是农民自我选择的结果,也不是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易言之,村庄集体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有其特定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条件,是村庄集体对非农产业发展资源的独享。本文拟就此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不妥之处,尚祈教正。
一
就全国而言,每个村庄集体经济的产生都有不同的背景。这种不同主要表现为发生时间不同、产业结构不同以及所有制形式不同。综合来看,村庄集体经济的产生主要有下面几种类型:
原有人民公社社队企业的遗产。
在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非农产业已有所发展。到1971年,全国社队企业产值达到102亿元。(注:陈吉元、陈家骥、 杨勋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545页。)在一些条件比较好的村庄,农村工业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部分农民已经在企业就业,其村民的收入较没有农村工业的村庄的农民高出许多。这些村庄在80年代初实施土地承包过程中,集体的非农产业并没有被简单地分掉,依然保留了集体经营的形式,并在80—90年代得到了快速发展。
典型的如江苏省华西村。早在1969年,华西村就开始发展“小五金厂”。(注:陆银初等:“一个相当发达的现代农村社区”,陆学艺主编:《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 页。)到1978年,华西大队的工业产值已达69万元,占农副工总收入的64%。(注:冯治:《吴仁宝评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再如河南省刘庄村,在1978年时, 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只占劳动力总数的40%,在工业企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已经达到53%,而且全部都在本社区集体企业就业。到1980年,工业产值已经占到了全部产值的66%,人均收入已经达到470元。 (注:陆银初等:“一个相当发达的现代农村社区”,陆学艺主编:《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又如河北省半壁店村, 在1971年开始发展副业,1978年依靠临近唐山钢铁公司的便利条件,开始发展钢铁工业。到1981年时, 村庄的工农业收入已接近100 万元。 在1983年落实生产责任制之前,工副业劳动力已经占到全部劳动力的70%,农业生产劳动主要由妇女承担。此时, 农民分配收入已经达到日工3元的水平。(注:作者1997年在半壁店村所作的调查。)
这类村庄在农村改革全面展开的时候,都不曾按照当时流行的做法实行承包,而是保留了集体经济的形式。在华西村,农业由华西村农工商总公司经营,由农业专业队集体承包,负责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农户只承担插秧、除草、收割等环节的田间劳动;工业企业则采取层层承包的方式,把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注:陆银初等:“一个相当发达的现代农村社区”,陆学艺主编:《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32页。 )刘庄则成立了农工商联合社,下设7个专业、36个生产经营承包单位,实行集体经营、 共同致富和全面发展的原则。(注:陆银初等:“一个相当发达的现代农村社区”,陆学艺主编:《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半壁店村也没有把土地分包到户, 而是根据经营农业的劳动力减少的具体情况,将原有的3个生产队合并为2个,以后又成立了作为村庄集体之下的一个独立核算单位的农场;工业企业也一直保留着集体经营的形式,并在80—9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壮大。
这些村庄集体经济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延续。尽管它们的多数资产是在改革以后形成的,但他们往往仍然以人民公社的理想为口号,在经济方面则借用了国营企业的许多管理模式,如工资制度、福利制度等等。
新集体经济。
在农村改革过程中,一些村庄先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农民分户经营,经过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回到集体的村庄经济。这种模式,被一些学者称为“新集体经济”(注:参见王颖:《新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此种形式的村庄集体经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最为普遍。
典型的如深圳万丰村。该村在1979年就已经将集体的耕地承包给各个农户,农村经济发展很快。但是,1984年以后,在工业化过程中,通过农民入股的方式,村庄再次形成了强大的集体经济,并运用股份制的方式,将集体经济量化到不同的单位。在万丰村股份总公司的总股份中,万丰村营经济发展公司的股份占35%,下属5个经济合作社占10%, 其他法人企业占5%,个人(主要是村民)共占50%。 (注:折晓叶:“农民再合作的制度体系和社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夏季号,总第15期。)类似的例子,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还有许多。如作者所调查的东莞市雁田管理区,在农村改革之前,农民收入很低,许多农民逃到香港地区谋生。农村改革之初,这里也像全国各地一样,将土地平分到户。但在80年代,随着整个东南亚经济的结构变动,大量“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生产和补偿贸易)企业在珠江三角洲建立,雁田管理区的集体收入大幅度增加。到1994年我们调查的时候,村庄所收到的“工缴费”(即“三来一补”企业向村庄集体支付的加工费用,由外商以港元支付)已超过亿元,95%以上的村民在企业中就业,耕地则由村庄集体收回,转交给农业办公室,承包给外来的农民耕种。(注:王晓毅、张军、姚梅:《中国村庄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转型》,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表面看来,这种类型的集体经济,通过股份制的方式将资产量化到个人,与原有的集体经济有着重大区别,但就其实质而言,两者具有共同性。因为村民取得股份并不是因为他们购买了股份,而是因为他们是这个村庄集体的成员,他们别无选择地成为股份的持有者,正像当年别无选择地成为公社社员一样。村民手中的股份是不可转让的,股份只不过是集体福利的另一种体现。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类型。如河南省南街村,在改革之初也同全国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将耕地和村办企业都承包给了个人。但到1984年,为了解决承包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又将企业和耕地收回,重新实行集体经营,并取得很好的效益。(注:邓英淘等:《南街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与珠江三角洲的新集体经济不同的是,这种类型的集体经济,其工业化是在农村改革以前起步的,村庄的主要收入依靠村办企业,村庄公共资产的所有权并没有通过股份制被明确。
另外,在城市郊区,也产生出许多集体经济强大的村庄。这大多是因为随着城市的迅速扩张,城郊村庄的土地被大量占用,使它们获得了发展非农产业的初始资金,从而形成了规模较大的村庄集体经济。这类例子有许多。如坐落在陕西省渭南市城区的五里铺,就是依靠国家1984年付给的430万元征地款发展起来的。西安市临潼区的西街村, 则依靠地处骊山脚下的优良地理条件,集体开发旅游资源,建立了许多旅游设施。(注:张建功主编:《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304、146—156页。)下表收录了一些村庄集体经济发生的简单情况,可参看:
村庄名称所在省市发生日期发生原因主要产业
雁田广东1986年 三资企业加工业
万丰村广东深圳 1985年 三资企业加工业
刘庄河南 1978年以前村办企业
造纸和制药
华西村 江苏 1978年以前村办企业 编织及金属加工
南街村 河南1986-1990年 村办企业
农副产品加工
福安村 辽宁 1978年以前村办企业 金属加工
东陌堂村山东1980年 村办企业
加工业
窦店村 北京 1978年以前村办企业农业及畜牧业
岐星村 陕西 1978年以前村办企业 建材及建筑
半壁店 河北80年代初村办企业 钢铁
村庄名称
资料来源
雁田注11
万丰村 (1)
刘庄
注4
华西村 同上
南街村 (2)
福安村 (3)
东陌堂村(4)
窦店村 (5)
岐星村 注13
半壁店
作者调查
(1)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邓英淘等:《南街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版。
(3)苑鹏:《福安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4)张泉欣等:《东陌堂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年版。
(5)张泉欣等:《窦店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二
关于村庄集体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已有的解释往往强调这是农民选择的结果,因而较多地分析其合理性。但是,如果我们更深入地进入村民的生活世界,就会发现,与人民公社制度一样,村庄集体经济也很难说是全体村民自动选择的结果。因为集体经济的社区属性,每一个村民,不管其是否愿意,只要他被认定是属于这个村庄的成员,就会被纳入到这个体系之中。因而,如果非要说这是农民自己的选择,那也是在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情况下的选择。
尽管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非常发达的村庄集体经济,但尚不能断言这种经济模式是高效率的。首先,这些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得力于许多特定的条件,如特定的资源和机会,如果缺乏和失去了这些机会和资源,集体经济往往会归于失败。90年代初,就有许多村办企业倒闭,它们给村庄留下的惟一遗产就是债务。就全国而言,固然存在大量成功的村庄集体经济,但失败的村庄集体经济更是不胜枚举。如果仅以发达村庄为例来证明村庄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其次,即使这些发达的村庄,其集体经济的发达也主要不是来源于经济组织的高效率,而更多的是因为村庄具备比较特殊的发展条件。如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村庄,许多收入是外来企业上缴的;北方的村办企业则往往得益于其特殊的发展机会。如在我们调查过的半壁店村,主要行业是钢铁业,在90年代初期的经济过热中,村办企业的投资曾得到很高的回报。但是,企业的收入主要被用于提高村庄居民的福利和扩大投资规模,技术水平仍然保持在较低水平上。
这些村庄集体经济之所以没有解决好效率问题,主要是因为村庄经济的高福利政策难以鼓励村庄成员的工作精神;相反,在经济发达以后,村庄成员越来越成为村庄集体经济的享受者。如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量外来企业以及外来劳动力支撑了村庄经济的发展,从外来企业收到的厂租和“工缴费”构成村庄集体收入的大部分。依靠这些收入,村庄可以维持一个较高的收入分配水平。但是,本村的多数劳动力依靠其村民的身份获得高收入以后,其能力却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反而因为收入的容易获得,逐渐演变成一个准食利者阶层。如在东莞市雁田管理区,多数本村农民在外资企业中担任厂长和报关员的职务,而企业中的一般劳动者、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几乎全部来自村庄之外。在北方的许多村庄,情况也基本相同,艰苦工作和技术工作几乎全部由外来劳动力承担,本村人员多从事办公室工作。在村庄集体经济中,本村成员往往具有就业的优先权,在这种非平等竞争的就业机制下,村庄成员的竞争意识十分薄弱。
村庄集体在经济发展以后,往往要维持一个高福利的村庄经济政策。如在半壁店村,教育、医疗和日常的食物消费几乎全部由村庄集体提供,全部村民都住进了由集体统一建筑的别墅式楼房。在雁田,自村庄收回耕地以后,全村人就自然获得了村庄集体的股份,每年按照人口分配红利,在1994年,每个村庄成员集体分配收入就已经达到4000元。就全国而言,福利式分配在发达的村庄集体经济中都占有很大份额。此外,许多村庄的本村职工的工资报酬还是模仿国营企业制定的,特别是那些从人民公社时期发展而来的村庄集体经济,更是如此。在人民公社时期,能够有稳定的工资收入是农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他们渴望摆脱农民的身份,希望像城市企业职工一样挣取工资。当村庄企业发展起来以后,他们有了将理想变为现实的条件,许多村庄便依照国营企业建立起工资标准制度。如在半壁店村,对改革前进入劳动年龄的人,按照其农业劳动的每日工分额,折算出其相应工资级别;对改革以后进入劳动年龄的劳动力,则按其学历制定不同的工资级别。这种企业工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集体时期大锅饭的一种回归,不利于提高职工的劳动积极性。
尽管村庄集体经济通过福利制度和就业制度在村庄内部基本上消灭了最贫困的阶层,但并没有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在不少村庄,权力在分配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随着公共财产的高度集中,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日益普遍,村庄主要领袖的作用有被神化的倾向,而管理的制度化却一直在较低水平上徘徊。在这些村庄中,由于经济实力的强大,村庄本身往往按照公司模式建立管理机构,一般村民很难参与公司的决策过程。而且,村庄的党支部或党委书记大多兼任公司董事长,成为村庄的主要决策者,而经过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则作用较弱。权力占有的不平衡很容易在收入分配中体现出来。多数村民的经济来源是工资和集体分配的收入,但也有一些权力持有者通过承包等形式,发展出了规模较大的自有产业。这种不平等几乎在每一个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都或多或少地可以发现,村庄主要干部往往成为收入较高的阶层。
尽管村庄集体经济带有很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如万丰村的共有制,被广为报道的南街村的政治氛围,等等),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一个村庄通过理想主义被整合在一起。因为一个村庄的人口是由其出生和户口关系所决定的,并不是如同一个党派一样是为了某一个共同目标而被聚集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使村民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先天的,而并非共同的理想,当然共同的理想也发挥着整合作用。在村庄集体经济中,往往存在着一些理想主义的口号,如共同富裕、热爱集体等等,但这种理想主义往往被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而不是日常生活的准则。村民关注的是村庄为他们所提供的各种利益,村庄所提供的利益越多,则村民与村庄认同的程度越高。因此,为了维持和加强村民的认同,村庄只能不断提高公共福利水平,而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村庄经济的低效率。
一些学者把降低风险视为村庄集体经济形成的原因。他们认为,农民在进入市场以后,发现市场是他们所不熟悉的,充满了风险,而村庄集体可以降低他们的风险。从表面上看,村庄集体经济的确降低了每一个农户的风险度,因为任何风险都要由集体承担,通过集体这一中介,风险被分散到所有成员身上,因而每一个成员所承担的风险就会相应减少;但是,这只是风险的分散,而不是风险的减少。在村庄集体经济中,权力高度集中,因决策失误所带来的风险可能会大大增加。在发展村庄集体经济过程中,有许多村庄因企业破产而负债累累,说明村庄集体经济并不能有效地降低风险。即使许多就目前状况来看发展还比较好的村庄经济,其经营中也往往潜藏着重大风险。这种风险首先来自决策的随意性,因为村庄集体往往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决策缺少民主程序,而在农村经济越来越受市场影响的今天,决策的风险将越来越大。其次,以村办企业为主的村庄集体经济多是负债经营的,在过去的20年中,因为集体企业容易得到贷款,所以许多村庄集体都背负了大量的债务,这也蕴含着很大的风险。
尤为重要的是,在村庄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村庄的公共资产不断增加,与之相伴随的是村庄干部、特别是主要干部的权威不断提高,而一般村民在村庄决策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小,农民的自主选择权被严重削弱。再者,当村庄越来越向企业集团发展、决策越来越专业化的时候,一般村民的参与权自然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应当看到,村庄集体并不同于合作制,因为村庄集体包括了村庄的所有成员,他们无须申请加入村庄集体,也不可能从村庄集体中退出。如果说,在合作制中,成员可以通过退出从而实现“用脚投票”,那么,村庄集体中的成员却恰恰缺乏这种权力,或者说,因为代价太大,他们不敢行使这种权力。到目前为止,村庄集体的资产还是不可分割和转移的。
三
既然村庄集体经济并不是农民自我选择的结果,村庄集体并没有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和公平问题,也不能帮助农民减少实际风险,为何村庄集体经济会在不少地方发展起来呢?我们认为,村庄集体经济能够得到发展,主要是因为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实现了对发展资源和发展机会的垄断。
人民公社时期,通过彻底的集体化,村庄已经成为一个社区性的经济实体,控制了所在地域上的全部资源。农村改革以后,尽管许多村庄的耕地承包给农户,而且承包期有不断延长的趋势,农户可以从事个体和私营的非农业经营活动,但是村庄仍然是一级经济组织,仍然保留了从事经济活动的职能,在一定条件下,村庄集体的经济职能还可能被特别加以强调。可以说,至少在名义上,村庄仍保留着一定程度的经济垄断地位。而在条件适宜、机遇来临时,名义上的垄断就会变为事实上的垄断。
在农村改革之初,尽管全国普遍实行了以土地承包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责任制,但对于那些村办企业已有相当发展的村庄来说,如何有效地落实生产责任制,却成为一个不易解决的大问题,因为企业很难像土地那样被简单地加以分割。事实上,在80年代之初,刚刚脱离人民公社体制的农民还没有形成产权概念,有些地方的农机具被简单地拆开分掉,有些村办企业简单地承包给个人经营。但是,用对待耕地的办法来落实企业的责任制,是很难行得通的。如果说土地的承包是农民所熟悉的,但他们的经验却无法告诉他们如何对待已经发展起来的企业。因此,在80年代初,也有许多村办企业保留了村庄集体经营的方式。这种方式一旦存留下来,就会具有排他性,因为村庄集体企业雇用了村内的多数劳动力,并成为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这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他经济形式的发展。村办企业越强大,越能吸引社区内的资金、劳动力等资源。相应地,其他经济形式的发展机会也就越少,往往只能在缝隙中生长,从事一些简单的商业和服务业。
与传统的手工业和加工业不同,发展现代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需要较大面积的土地,而土地是全部属于村庄集体所有的,因此,发展农村集体的非农产业,在使用土地上要比个体具有更大的优势。这一点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那里,至少在80年代农村工业化之初,“三来一补”企业所交纳的“工缴费”和厂房租用费是村庄集体的主要收入,这实际上都是间接的土地收入。土地归村庄集体所有,因而也只有村庄才可能进行大面积的土地开发。尽管有些农民家庭也建设了一些厂房,但大量外资企业的进入所需要的大面积的开发,却只有通过村庄集体才能实现。因此,在迅速的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成为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在缺少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的情况下,农村集体在土地使用上具有很大的垄断权,集体所有的土地不仅提供了工业化所需要的建设用地,在很多时候,从土地上所得到的收入也是农村工业化的初始资金。
在中国农村工业化过程中,资金是一项短缺的资源,而且多数资金为农村集体所垄断。中国农村主要的融资渠道是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在农村改革以前和以后的许多年中,这些机构不为非集体的农村非农产业提供贷款服务,而农村集体则可以相对比较容易地得到贷款支持。因此,在占有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方面,村庄集体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许多农村集体经济,特别是依靠发展村办企业兴旺起来的村庄集体经济,往往都是负债经营。如我们所调查的一个村庄,当时有将近3 亿元的银行贷款,超过其资产的50%。可以设想,在多数农村地区,只有集体企业才有可能得到如此多的贷款支持。
农村集体正是通过对土地和资金的独占,实现了对农村工业化机会的独占。
非农产业发展的初始规模,对村庄集体垄断资源的程度有很大影响。大体说来,非农产业的规模越小,越接近农民社区所熟悉的传统手工业,其受到的资金限制和土地限制也就越小,也就不容易被纳入村庄集体经济中。典型的如温州的个体私营经济,它们在发展之初主要生产一些小的轻工业产品,对资金和土地的需求不大,所需资金依靠民间金融调剂即可以得到解决。(注:参见王晓毅:“农村工业化中的民间金融”,《中国农村观察》(北京)1999年第1期。)在河北省的一些农村地区,也有许多金属加工工业,它们规模很小,所需资金很少,大多分散到农户中进行加工。这样的非农产业,一般都能维持其私营地位。相反,如果发展规模较大的重工业,需要很大的资金和土地,就必然对村庄所占有的资源产生较深程度的依赖性,因而就较易被纳入到村庄集体经济之中。
非农产业发展的起始时间,对村庄集体经济的垄断程度也有重要影响。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村庄集体对非农产业发展所需资金和土地的独占,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发展机会的独占,正在逐渐减弱。其次,随着各种非国有金融组织的建立和国有银行的改革,农村各种非集体企业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获得贷款支持,村庄集体对金融服务独享程度亦逐渐降低。第三,随着土地政策的调整和变化,非集体企业有了比过去更公平的土地使用机会。此外,随着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的展开,农民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到村庄以外寻找发展资源,这对村庄集体也会产生一定的瓦解作用。因此,可以设想,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村庄集体经济所赖以产生的特殊条件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事实上,在一个村庄范围内,发展的机会是有限的。当村庄集体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村庄内非集体经济的发展机会就受到抑制,甚至在一个村庄的集体经济发展到较大规模后,周围村庄的发展机会也会被吸纳到这个村庄中来。我们在广东调查时,就曾发现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有一个村庄,我们1995年前去调查时,还远不如镇政府所在地繁华,但这个村庄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当我们1998年再去调查的时候,镇政府所在地已经随着这个村庄的发展严重衰落了。
概括地说,由于上述一些特定因素的影响,村庄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在许多地方采取了集体经济的形式。这种形式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也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但是,也应看到,村庄集体经济在形成自己的发展惯性以后,会在很长的时间内按照既有的道路走下去,并对其他的发展方式产生排挤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各种问题会不断积累。事实上,村庄集体经济在目前已经暴露出一些问题,如高福利、低效率、大锅饭、制度化水平低、个人权威高等等。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是当前亟待研究的课题。
最后,必须指出,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是多样化的,由此形成的未来的村庄格局,也将会是多种多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越来越像是一个都市,很可能会形成一种新的农村城市化模式。而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加深,资源独享的格局亦有可能会被冲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用另外一篇文章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