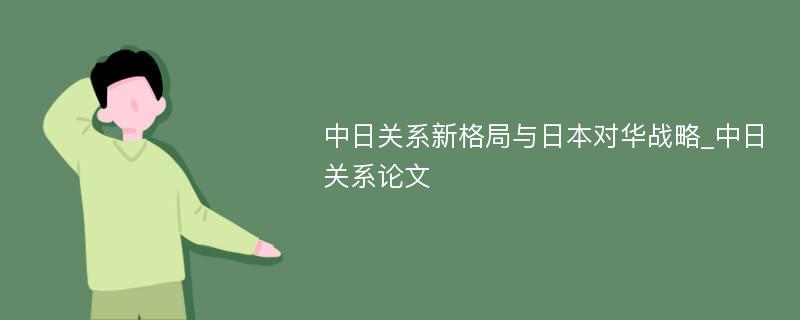
中日关系新格局与日本对华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日本论文,新格局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日本政治大国目标的追求与中国的日益崛起
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向政治大国迈进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孜孜以求的国家战略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很快得到恢复与发展,在60年代末,日本经济规模已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70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在世界各地扩张,其经济利益几乎遍及各大洲。在这种背景下,日本要求参与世界事务的欲望与日俱增。经过70年代的彷徨、争论和探索,大平正芳首相的智囊机构于1980年提出了著名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报告。该报告主张,日本不能继续做“经济大国—政治小国”式的“跛足国家”。这份报告为日本的对外战略转折提供了理论基础。
进入80年代后,随着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日本明确减出了要做“政治大国”的口号。1983年7月, 中曾根康弘首相便提出日本要做“国际国家”,“应发挥与经济大国相适应的国际作用”,其着眼点就是“要加强日本在自由世界和世界政治上的发言权。不仅做经济大国,而且要增加做政治大国的分量”。(《中曾根首相主张做政治大国》,载[日]《每日新闻》,1983—07—31。)
90年代,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剧烈的历史转折给日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日本加大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政策的调整幅度,加快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步伐。目前,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已进入全面实施并竭力推进的阶段。面对挟经济、科技和金融大国实力不断向世界发出挑战的日本,同为东亚大国的中国如何应对,怎样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中日关系,这的确是一个新课题。
在日本以超级经济大国实力为后盾,加速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同时,中国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全力发展经济,加快走向经济大国的步伐。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 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截至199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76万亿元人民币,提前5 年完成了翻两番的目标。1996年,中国又制定了2010年远景目标。今后三四十年中国经济将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实现腾飞。中国的发展也引来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世界银行在《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研究报告中惊叹:“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总和的国家,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发展。”还有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提高到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经济实体的地位,并因此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提出怀疑。现在,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强国的看法已为舆论的主流。然而,外部世界在赞扬或评论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崛起存在着种种忧虑与猜测,国际舆论中出现了所谓“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论”甚至“中国危机论”等不谐和音。某些外国人甚至将西方传统观点简单地套用来分析中国的未来走向,认为中国强大了也必然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
日本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这一论调在日本相当盛行。这是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是日本所始料不及的,它不仅使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也在心理上给日本人以很大冲击。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也是日本经济实力进一步膨胀的时期,尤其到了8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进入泡沫经济阶段。这一时期的日本,财大气粗,不可一视。它非但不像以往那般任由美国摆布,还视美国为头号竞争对手,在诸多方面向美国发起挑战,从而导致日美摩擦激化。一时间,“日本威胁论”和“嫌(厌)美论”充斥美日两国报端。在此背景下,日本就更不把亚洲邻国和中国放在眼里了。日本认为,中国即使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也要在半个世纪或百年之后。进入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日本意识到无法同美国一争高低,回过头来想稳做亚洲“老大”,可又发现身旁的中国正在崛起。于是,日本有了一种“危机感”。作为百余年来亚洲惟一的世界强国并曾独霸过一方的日本,心理上的不平衡以至畏惧情绪,反映在舆论上就是日中友好的提法有所减少,“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在增加。如今,日本逐渐不再视中国为发展中国家,而开始把中国看成自己潜在乃至现实的竞争对手。1995年底日美联合舆论调查显示,三分之一以上的日本人认为中国是其今后最强大的经济对手,这一比例超过了对美国的看法。在某些日本人看来,正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日本与经济上日渐强大的中国难以保持像以往那种友好关系,认为“中国增强了经济实力之后,对渴望在国际社会增加发言权的日本来说,无疑会成为一个超出纯友好对象范畴的存在。到那时,日中两国就将立即进入摩擦的时代”。(志村规矩夫:《中国的经济大国化与日本》,载[日]《时事解说》,1993—06—05。)
世纪之交,日本由超级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而中国则快步向经济大国迈进,中日两国正在进入“强强型”关系的新阶段。可以说,中日之间日趋明显的两强并立局面,正从根本上改变两千多年来以一强一弱为基本格局的两国关系史。
从历史上看,中日关系呈现三种形态。在19世纪日本崛起之前,东亚国际体系的政治和文明中心一直是中国,日本处于这个中心的“边缘”。在这种体系下,中日关系的特点是中国强日本弱。而从日本明治维新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中日关系则是中国弱日本强。在冷战时代的前半期,中日两国意识形态各异,分属不同阵营,日本追随美国敌视中国,中日两国处于对抗地位,中日关系表现为冷对峙形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不断扩大,双边关系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然而,在冷战结束之前,从相对地位来看,日强中弱的格局仍未得到根本改变。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基调是友好与合作,并伴有一些摩擦。冷战后,和平与发展进一步成为国际社会的主题,时代为中日两国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世纪之交,中日两国的实力都处在上升期,国际上的影响日益增强。中日之间两强并立或“强强型”关系的新格局正在出现。这种新格局,对中国和日本以及中日关系的影响将是重大而深远的,并且这两个大国如何做邻居,则直接关系到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新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
冷战结束后,面对日趋明显的两强并立的局面,日本为适应新形势,在争当政治大国目标的驱动下,已开始对其外交战略进行一系列调整。当然,作为日本外交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华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
冷战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中日复交。在这一时期,日本追随美国,实行亲台反共的对华政策,遏制新生的中国,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极力阻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日之间虽保持民间往来,但仍处于敌对状态。第二阶段是从1972年至冷战结束。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历届内阁对中日关系均相当重视,即使在中日关系因一些摩擦而处于某种低潮时,其维持“长期稳定的日中友好关系”的基本方针也始终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
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出于深谋远虑的战略选择,而非权宜之计。日本著名中国问题专家、80年代日本的对华政策的重要智囊冈部达味教授在他为外务省撰写的《8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咨询报告中,明确道出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思路和目标,即:(1)日中关系友好稳定, 对日本的对外关系及内政两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因而应在不损害日本利益的范围内,加强日中友好关系;(2)中国的稳定对日本有利, 日本对华行动应以有助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为目标,必须避免对中国稳定起副作用;(3)中日友好关系的加强, 不得改变迄今的日本对外政策路线的性质,损害和其他国家的关系;(4 )必须尽量提前采取措施,防止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中国成为军事及经济威胁; (5)排除日本国内情绪性的中国观、日中关系观,根据双方共同利益发展友好关系;(6)克服日中之间的误解,增进相互理解, 开展各种文化交流。 (参见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编:《80 年代日本外交的方向》,292—317页,东京,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1980。)回顾冷战结束前的中日关系史,我们看到,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基本上遵循了这样一种方针。而基于上述指导思想制定的8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特点是:(1)以经济合作为发展日中关系的基础, 试图通过经济合作实现某些战略意图;(2)借重中国,抗衡苏联;(3)对华政策受美、苏因素制约很大。总之,中日复交后日本与中国因共同战略需要和经济利益驱动以及彼此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终于使两国关系在80年代进入了所谓“蜜月期”。
冷战后,经过几年的酝酿与调整,新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构想已初步形成。那就是在建立“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总体思路下,继续加强同中国的合作与协调,借重中国为其政治大国目标服务,同时视中国为战略对手,对中国进行牵制与防范。
1.建立“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这一概念,是1991年8月海部俊树首相访华时首次提出的, 其要义就是日本政府要从世界局势和自身外交战略角度处理日中关系,而中国也必须向世界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协调行动,成为国际上的“稳定力量”,进而使日中关系成为对世界有贡献的、新型的、有利的关系。由此可见,日本对华政策经过曲折的调整,已充实了新的内涵。海部之后的日本政府都肯定和继承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这一基本方针,将其作为发展日中关系的总体框架。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时,小渊惠三首相明确表示:“今后,日中作为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负有责任的国家,不能仅仅考虑两国间关系,而应面向国际社会,进一步发展对话与交流”。可以说,进入90年代,日本政府已经结束了仅从双边角度考虑对华政策的时代。“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考虑中日关系着眼点的扩大,即从以前的双边关系扩大到着眼于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在目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政府将在这一总体思路下处理对华关系。
2.继续加强同中国的合作与协调。日本在1992年举行的“日本的安全政策与中国”的讨论会上,与会著名专家一致指出,“中国对日本来说是一个特殊国家,不能简单地用两个国家的关系来形容日中关系”,“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日本更多地在中国经济中发挥作用,是日本的对华长期战略方针。1995年1月, 由学者和财界人士构成的以研究日本外交政策著称的“日本国际论坛”,在向村山富市首相提出的关于日中关系的建议中,也强调日本应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日本政府认为,一个保持改革开放发展势头的中国,符合日本的战略利益;相反,如果中国经济改革失败,因失去协调和维持秩序的能力而陷于混乱,社会动荡,难民涌出,则将直接危及日本,并冲击世界的经济与稳定。因此它希望中国继续沿着市场经济道路走下去,从而为日本提供广阔市场和带来巨大经济利益。
基于以上认识,面对正在向经济大国迈进的中国,日本政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表现了比较友好的姿态。例如,在“中国1989年政治风波”后,海部首相率先访华,推动了西方解除对中国制裁的进程。在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及后来的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日本政府一贯态度积极。在经济方面,加大对华经贸合作力度,继续把经济合作作为对华外交的主旋律,中日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在安全方面,积极加强对华安全对话与合作。此外,还在解决诸如朝鲜半岛、印巴核试验等地区性争端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协调。
3.借重中国,实现政治大国目标。日本争当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立足亚太,成为左右亚太局势的地区性政治大国,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向世界性大国迈进;二是争取早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日本这两个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中国的支持,保持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是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重要条件。
冷战后,面对欧美在国际舞台上的挤压,日本进一步“脱美入亚”,将整个外交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放在亚太地区。1992年底,宫泽喜一就任首相之初就强调,“今后日本外交的关键是亚洲外交”。1995年,日本外相河野洋平也公开发表文章,强调把日本外交的重点放在亚洲,并首次提出日本已不是“单纯的西方一员”的见解。(河野洋平:《日本外交前进的方向》,载[日]《外交论坛》,1995(1)。 )河野这一思想的出笼,是日本进一步面向亚太展开全方位外交的重要标志。1997年日本《外交蓝皮书》更是公开提出,日本要在亚太地区“发挥真正的中心作用”。然而,日本深知,没有中国这个重要亚太国家的理解与合作,要实现上述目标是困难的。正如宫泽喜一首相所说,“日中关系在日本的亚洲外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在国际问题上离不开美国,在亚洲问题上离不开中国”,“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同等重要”。前外务次官小和田恒也曾告诫日本政府,“不能忘记中国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出于这些考虑,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在推行亚洲外交时积极争取中国的支持与配合。
日本视开展“联合国中心主义外交”为跻身世界政治大国的重要台阶。一般认为,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日,也就是其争当政治大国目标实现之时。目前,日本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许多有利条件:(1)冷战后,改革联合国体制已成为现实必要与可能;(2)日本是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也是联合国财政负担大国;(3 )日本在联合国中影响日益扩大,并握有一些重要机构的领导权。由此观之,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可能性愈来愈大。然而,日本在推行其联合国外交的过程中,也不能不视中国为“关键”因素之一。这是因为:中国是联合国现任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也是亚洲地区惟一的代表;日本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需要得到中国的谅解和支持。并且,中国坚决主张安理会改革必须照顾发展中国家占联合国多数这一事实。
4.视中国为战略对手,牵制和防范中国。首先,借重美国对付中国。从1996年4月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 次年签署《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到1999年5月日本众参两院正式批准指针的相关法案, 日美最终完成了冷战后其同盟体制的重新定位。与冷战时期相比,新同盟体制由过去主要防范苏联进攻转为主要对付亚太地区的所谓“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即所谓的“周边事态”。日本政府虽然百般解释“周边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事态性质的概念”,但其含糊的说辞,足以暴露出其制约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的企图。在日本决策层的一些人看来,“亚太地区当前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当然是无法预测其行动的北朝鲜,但从中长期来说,正在向超级大国迈进的中国的动向是日美两国决策者最关心的事情”。(富山泰:《周边事态与“台湾有事”的暖昧性》,载[日]《世界周报》,1997—09—02。)日美新指针“相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从大国关系处于转折期的国际体系的力量对比中产生的;它是在日本无法单独与中国在同一层次上展开政治权力斗争的现实上成立的”。因此,它将“具有双重作用。一是明示作用,即防备出现朝鲜半岛发生不测之类的地区纠纷;二是默契作用,即在国际体系中使变化中的大国关系稳定”。(添谷芳秀:《日美中关系的结构与日本外交战略》,载[日]《外交论坛》,1997年秋季增刊号。)当然,新同盟体制也是日美相互利用、相互借重的产物,也符合美国的战略需要。美国也不愿看到中国强大,成为其未来的竞争对手,从而动摇其霸主地位。可以说,在遏制中国的问题上,日美一拍即合。另外,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日本还大力发展自身军事力量,调整防卫态势,企图加强防范中国的实力基础。第二,对华经济援助政治化。以日元贷款为主体的日本对中国的 ODA(政府开发援助)确实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冷战后,日本对华经援中加重了政治色彩,将日元贷款与中国的人权、军备、核试验等问题挂钩,企图打日元“贷款牌”,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并掌握中日关系的主导权。第三,通过多边机构“规范”中国的行为。为了避免因中国崛起而使自己在日中双边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日本政府采取了既将中国纳入国际协调体系又力图制约中国影响力的双重方针。例如,在亚太地区事务问题上,日本积极倡议建立东亚多边安全框架,着力推进中、日、美、俄大国安全对话;推动以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为中心的地区多边政治对话等。即使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问题上,日本也主张应该探索日中两国在地区安全保障、多边合作框架内开展合作的可能性。日本认为,如果上述努力得以实现“将会带动日中关系出现质的发展”,“建立在这种实践基础上的新型日中关系,将作为内在的多边合作的构成要素,对两国间的友好合作以及整个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日本国际论坛政策委员会政策建议书:《日本与美中俄关系的展望及其构想》,载[日]《世界周报》,1999—06—08。)由此可见,日本极力拉中国参加多边协调机制,是有其明显的政策意图的。这样做,日本既能制约中国,又能避免与中国单独对抗,并可促使中日关系有限度的发展,可谓是一石三鸟。日本今后会继续沿此方向走下去。第四,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90年代以来,日本不断发展与台湾的关系,日台关系呈现出一些新趋势:由基本上局限于经济关系开始向政治关系发展;政治上的接触,由隐蔽转向公开、由低层转向高层。今后,随着日本政界朝野亲台派势力的上升和扩大,日本会进一步介入和干预台湾事务。日本认为,一旦台湾“有事”,日本是不能袖手旁观的。日美新同盟体制把台湾包括在内的主要目的就是,阻止中国统一台湾,长期维持台湾的现状。日本企图通过打“台湾牌”牵制中国。第五,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尤其是那些与中国尚有一定矛盾的国家的关系,借用它们的力量抵制中国。其中,东南亚国家是日本争取和联合的主要对象。日本著名国际问题学者北冈伸一毫不讳言地提出:“就东亚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政治来看,只有东盟和澳新这些中小国家能够成为日本的盟国,它们和日本具有共同的利益”。此外,日本还积极开展对俄、对韩甚至对中亚国家的外交,加强与印度之间的战略对话,谋求利用它们来制衡中国。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世纪之交,随着中国和日本日趋明显的两强并立格局的出现,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正在重新审视中国和中日关系,并对以往推行的对华政策进行了调整。而走向经济大国的中国当然也必须重新看待日本和中日关系,采取妥善对策。中日关系是我国整个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处理好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对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至关重要。笔者认为,我国在开展对日外交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明确中日经济关系是中日友好关系的重点和基础;(2)在警惕和预防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前提下,承认并支持日本在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中起积极作用;(3)注意保持中国与美、欧、日、 俄等大国间关系的平衡;(4)近年来, 日本社会舆论总体上朝着不利于中日友好的方向演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媒误导和一些日本人不了解事实真相造成的。因此,还必须加强中日民间外交,增信释疑。
从理论上分析,未来的中日关系可能出现三种局面:(1 )中日友好(友好关系);(2)中日并立(非敌非友关系);(3)中日对抗(敌对关系)。现在看来,今后10—20年的中日关系将基本上呈现一种并立状态(或者说是并立关系的形成期)。在这种并立状态之下,中日关系的基调中摩擦与协调、竞争与合作并存。这种“强强型”的中日关系是摆在中日两国面前的一个新课题。为此,中日双方必须从长远战略角度和两国共同根本利益出发处理双边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标签:中日关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中日文化论文; 外交争端论文; 世界现代史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