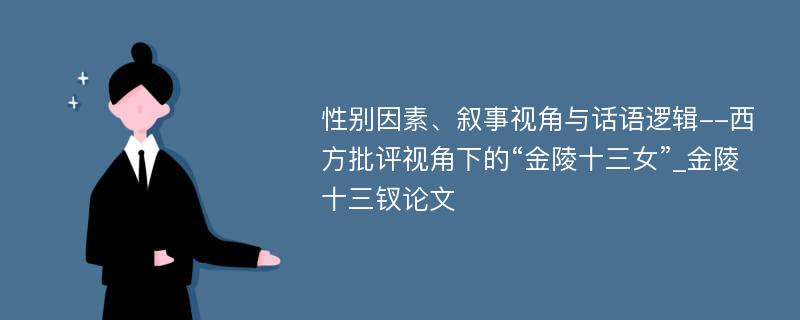
性别元素、叙事视角与话语逻辑——西方批评视野中的《金陵十三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陵论文,视角论文,视野论文,话语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2)02-138-06
大屠杀一旦进入叙事,也就是说“历史事实”一旦被转换为“叙事话语”,引起的争议是复杂且广泛的。从本质上讲,大屠杀真相是对人类叙述能力与现有审美陈规的挑战,本雅明就悲观地认为,惨无人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作为一个文类、一种话语模式的“讲述故事”艺术(storytelling)衰落了……面对满目疮痍的世界,人们已经无话可说[1](P25)。但是不去回忆,就无法清算罪行与审判凶手;不去叙述与呈现,就面临遗忘与虚无。英国政治学家奥克肖特就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的经验。历史不是别人而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办法。”[2](P36)因此,大屠杀不仅在人类的记忆中存在,也需在历史叙事中不断出现,而无论是关于大屠杀的叙述话语,还是关于大屠杀的解释与分析,甚至是关于大屠杀叙述的批评话语,都构成了一个相当庞大而独特的历史话语景观,在这个庞杂的景观中,中心与边缘、共谋与排异、历史真相与当代政治微妙地相互勾连又相互指涉,或许正像齐格蒙特·鲍曼说的,“大屠杀是最富有戏剧性道德意义的事件。”[3](P229)
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2011)也深嵌在大屠杀的话语景观中,重复着某种戏剧性的命运。这部讲述南京大屠杀的影片特征明显,一面是不可避免地回溯民族历史的创伤,希冀通过影像穿过历史的暮霭,重现事实本身;另一面又延续了近年来国内电影在呈现南京大屠杀影像时的“世界化”倾向(如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合拍片《拉贝日记》),努力突破证据的罗列、情绪的宣泄,希望把历史真相融入到普适性更高的影像修辞中,在更广阔的平台上让世界听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回响。或许,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在这点上做得更为极致,该片投资近六亿人民币,邀请了好莱坞战争特效团队和一线影星克里斯蒂安·贝尔加盟就是例证。但是从收到的效果看,《金陵十三钗》在跨国传播中却遇到了诸多问题,不断地与国际电影节的诸多奖项(美国金球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等等)失之交臂,同时也遭遇西方文化精英一面倒、粉碎性的批评,国内有媒体将之概括为“西方媒体恶评如潮”。而本文的目的在于回到电影本身,对此进行实事求是地评价与回应,或者从某个角度说,正是针对批评的“批评”。
一、《金陵十三钗》中的性别话语
在古希腊神话中,历史之神克莉奥(Kleio)是位女神,她是希腊神话中九个缪斯女神之一,终日拿着羊皮纸,司掌历史和英雄诗。从神话开始,我们就能读出历史、诗性叙事与性别之间微妙而含混的联系。对于《金陵十三钗》中显而易见的女性中心形象,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直面关于大屠杀叙事中性的元素。在西方批评者眼里,“最愚蠢的好莱坞制片人才会做的事——将色情噱头注入如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大惨剧中”[4]。
在大屠杀叙事中,性的存在并不能必然构成伦理的压力,只要叙事者能运用“手头的材料”给予其合理的“解释内核”,就往往能在影像中成为人性的镜像。欧文·豪说,精明的作家在处理大屠杀这个题材时,采用了珀尔修斯对付美杜莎的办法,即用光亮的盾牌作镜子找出美杜莎并砍下了她的首级,从而避免正面看见她变成石头的命运。[5](P288)在屠杀叙事中,性往往是一面特殊的镜子或者一座浮桥,电影《朗读者》中的性代表着一个女纳粹帮凶正常的人性,而《苏菲的选择》中的性隐含着一个母亲的屈辱与大屠杀幸存者的心灵炼狱。在《金陵十三钗》中,在日军令人发指的集体兽行前,女主角与约翰的纠葛是慷慨赴死前的情感宣泄与爱意表达,并不能算西方男性眼中东方女性身体的奇观展示,玉墨们原是社会的边缘人、卑贱者,但当她们易装赴约时,走出教堂时光彩耀目,宛若南京城最漂亮的女学生。低贱与高贵、神圣与卑微、纯洁与不纯、献祭与自我牺牲这诸多矛盾话语互相指涉又相互置换,如冰炭相逢,分外冷艳凄厉。
第二个问题在于影片是否以一种简单化的方式征用性别话语。《纽约时报》的影评也是攻击其对女性形象的使用,“她们以慢镜头摇曳着穿越教堂院落,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不以为然”。值得批评人注意的是,《金陵十三钗》写的不是一个女性,而是一群女性,从单方组成元素看,无论是女学生还是妓女,她们与战争叙事都发生过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在叙事中常被征用的性别符号。在战争片中女学生的遭际往往遵循“无辜者叙事”的模式,日本导演今井正的《姬百合之塔》(1953、1982年)就是一例,影片中文弱的女学生是战争的炮灰,是纯洁无辜的象征。至于战争叙事中的妓女或舞女形象,往往作为国家与社会群体中的“他者”被直接征用,成为某种特定的影像修辞逻辑。在战争语境中,她们或是通过献祭的方式再次回归国家主流话语,或是通过献身来拯救良家妇女来洗白自己,她们虽然也是战争的牺牲品,但在影像的深层意指中,她们是作为“证物”而不是“证人”存在的,“因为‘她’在心照不宣的权力与文化的‘规定’中,已先在地被书写为一具尸体,一个死者”。[6]
实事求是地说,《金陵十三钗》试图努力摆脱这种简单处理的窠臼,张艺谋虽然抽掉了“伤兵”的元素,但聪明地保留了些许原著中结实、饱满的女性互动,带来了两个女性群体间错综的“看与被看”。女性之间的“凝视”也代表着一种靠近。因此在电影的前半段,我们看到了当教堂作为孤岛在血雨腥风的南京城里矗立时,教堂内的这两个群体之间也发生着一场场女人之间的小战争。教会学校里长大的少女和在欢场摸爬滚打的歌女放置于同一个空间,两类女性群体微妙的对抗磨合,充满了抗拒排斥,却又带有说不清的向往,歌女们羡慕女学生的文化身份,而书娟则从成熟歌女身上感受到女性性别意识的萌芽。女性之间的互动带来了女性话语丰富的层次感。张艺谋想让歌女们摆脱物的存在,作为有血肉的“见证人”重新出场,去见证那段屈辱和苦难,最为直接也是最为适切的方式就是通过女性身体,通过被蹂躏的身体,通过冲突和战争中女性特有的身体恐怖和惊悚,让“她们”浮出民族历史记忆的海面,重新呈现在镜头前。
可惜的是,这种女性话语的丰富层次感并没有延续到后半场,玉墨们代女学生慨然赴宴的过程被“小蚊子找猫”、“女学生情急之下要跳楼”等偶发事件牵引,玉墨们的心理历程也仅仅被交代为“别人都说商女不知亡国恨,我偏要做一件有情有义的大事”所轻轻带过。日军设计侵犯唱诗班少女,歌女却甘愿以身相代,这种历史细节的重现没有问题。但正如柯林武德所提倡的“富有理解力的想象”,对历史的想象应建构在真正的理解基础上。这一具体的历史细节所指向的核心话语与终极动机不应仅是一种“仗义”,也不仅仅是编剧刘恒所说的“以人性之善战胜人性之恶”,更不应是对纯洁女孩与堕落女人之间个体社会价值的冷静权衡,而应是女性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向死求生、对抗侵略。这一对抗的深层动机完全应当用女性之间的互动点染,用充分的女性友谊升华。在神性与人性一同沉默的无边黑暗里,无论歌女还是女学生都是被“抛弃”的畸零人,在日军的性暴力面前,作为女性的她们自然成为“命运共同体”。侵略是一种广义上的强奸,在暴行面前,女性友谊也是一种抵抗策略。这样,她就变成她们,她的身体就变成她们的身体,她的主体性觉醒就成为一个群体的主体性觉醒。女性之间在血腥屠杀中友谊、互助与自我牺牲,构成了一幅霍尔所说的“他者联盟”。[7](P128)。如果真的能把这点做扎实,做到底,贯穿整个文本,也许这一核心情节在电影文本中的呈现会更有说服力,玉墨们的铿锵会显的更有血有肉。
二、叙事视角中的历史呈现与电影美学
抛开细枝末节的纠缠,我们面对《金陵十三钗》会有一个最根本性的要求——那就是作为一部叙述大屠杀的影片,它是否把“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清晰地“呈现”出来。严歌苓的同名原著无疑是电影《金陵十三钗》对历史的取景框,张艺谋承袭了原著中的核心事实与叙事视角。原著的“历史内核”来自于作者翻阅魏特琳日记时看到一段关于日军在难民营骚扰百姓,有风尘女子挺身而出代替良家女子的记载。电影还承袭了原著的叙述角度,摒弃了南京大屠杀影片既有模式(在全景描绘的格局下形成品字形结构:抗战官兵、中国平民、日本侵略者三条线索),独独从女学生书娟的视点出发,选取教堂一隅,带领观众重回历史现场,教堂宛如当年南京的一个缩印,见证着死亡与兽行。但正是这种视角带来了响亮的质疑声音,进而对核心事实产生怀疑,批评者(特别是部分西方影评人)认为“女学生的视角罗曼蒂克且是选择性的”,“张先生与大屠杀故事大格局之间的距离体现在他决定将影片的大部分场景局限在一个虚构的欧式教堂区里面……人物与现实世界的南京隔绝开来。”“一群女学生躲在文切斯特教堂中,教堂的厚墙似乎将她们与滥施奸淫的战胜者日本军隔离开了”[8]。这些批评聚焦于书娟的视角是否遮蔽甚至隔绝了南京大屠杀的清晰呈现?
这些责难的背后涉及大屠杀叙事的深层问题——如何再现大屠杀?从某种程度上看,大屠杀不可再现,人们只有依靠话语的想象性言说去接近作为历史事实的大屠杀,就像历史学家卡尔所说,“历史事实的确并不像鱼贩子案板上摆着的鱼。事实是像游泳在广阔的、有时是深不可及的海洋里的鱼。历史学家能钓到什么,这一部分要靠机会,而主要地要靠他到海洋的哪一部分地区去钓,他用的钓具是什么。”[9](P65)同理,对于大屠杀影像来说,历史的呈现取决于叙述者所在的“位置”与“钓具”。在大屠杀影像中,接近历史事实的方式可以是《夜与雾》(阿兰·雷乃,1956)中来自社会学解释,如历史纪念碑般雄伟的画面与剪辑;可以是《浩劫》(克洛德·朗兹曼,1985)中受害人与访谈者在反思、追忆和否认中组构的诗性对话;也可以是《美丽人生》(罗伯托·贝尼尼,1997)中对抗屠杀的父爱,《苏菲的选择》(艾伦·J·帕库拉,1982)中修辞性叙事,最近的《朗读者》(史蒂芬·戴德利,2008)则以成年女子与一个少年的情爱纠葛对大屠杀进行间接性叙述,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部电影以大屠杀为反思对象,却没有一个镜头正面描述大屠杀。
因此,要落实对《金陵十三钗》的批评,视角本身并不构成问题,关键是书娟的视角是否能“见证”南京大屠杀,它带观众重回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现场后究竟要完成哪些任务,这是需要仔细探究的。在严歌苓的原著中,《金陵十三钗》是在牺牲与救赎的主题下一曲边缘者、飘零者的悲歌,原著中的戴涛上校是求助者与受害者的混合体,以不抵抗的方式被日军残忍杀死,以此换取女人的安全,这个话语是悲怆的。但张艺谋将其改为了悲壮,李教官是拯救者与受难者的混合体,他的舍生取义最大限度地填补了神父被炸身亡后“精神之父”的空缺。他的牺牲是无条件的,用海明威的话来说,这样的人你可以消灭他,却不能打败他。两相对比,严歌苓执意走在家国之外回望这段民族悲情,而张艺谋更多的是在家国之内接近历史,电影中的李教官对原著中戴涛上校的改写强化了文本中的民族主体性。
但是改动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克里斯蒂安·贝尔所扮演的米勒这一角色的功能问题。值得深思的是,这个几乎是为克里斯蒂安·贝尔度身定做、希冀沟通东西方受众的角色成为西方影评人开足火力的批评目标。《好莱坞报道者》用了整整一段倾泻对该角色塑造的不满:“留着小胡子,活像六十岁的嬉皮士,说话的方式愚蠢且年代错误,出于某种特定动机把一个白人刻画成一个贪婪积财,愚蠢和粗俗的人物”[10]。《金陵十三钗》中的米勒与《辛德勒的名单》中的辛德勒都从一个较低的道德起点开始,但沿着情节发展,辛德勒成长为一个悲天悯人且无所不能的英雄,他最终站在了工厂中心高高的平台上向犹太工人和看守的德国士兵进行演讲时,斯皮尔伯格在构图上给了他一个上帝般的存在位置。而在《金陵十三钗》中,米勒披上黑袍,以仰视的角度出现在教堂的平台上,为救女学生向日本兵进行布道般演讲时,他下一秒就被日本兵拉下神坛,打晕了过去。在整部影片中,米勒更多的是见证者的功能,而没有“救世主”的光环。
因此,从本质上看,米勒是一个表面上的男主角,虽然克里斯蒂安·贝尔的奥斯卡影帝光环与天价片酬都赋予这个人物绝对的主角地位,但是一旦深入文本,观众就会发现米勒绝不是文本的精神核心,李教官与玉墨们才是,他们的牺牲夺人心魄。在电影中,米勒形象设计是为了一种商业或传播上的考虑——突破南京大屠杀题材的自言自语,让本民族的苦难在好莱坞的平台甚至广泛的国际平台上流传开来。但是这种表里不一的“伪好莱坞”式人物刻画很快被“火眼金睛”的西方批评者发现并大加鞭挞,同时他们还不忘对其中李教官——这一彼时中国抗日军人形象定性为“张艺谋对国家至上主义的让步”[11],其中的症结或许正如特里·伊格尔顿反复向我们强调的,审美也是一种意识形态[12](P43)。
此外,视角也带来了电影美学方面的争议,西方批评者认为“该片是对一个过度戏剧化的历史事件的别出心裁而又没有说服力的演绎”,其斑斓的电影色彩正是“一种奢华的、受好莱坞启发的情节剧的背景,没有能够实现宏伟、历史背景、真正的悲怆。”。[8](P13)正如本雅明在其绝笔之作中所说,“过去只能在一次性的、突然闪现的意象中加以把握。”在我看来,书娟的视角正是一种引导性的目光,在混乱与混沌中开启历史之门的瞬间,连接着当代的观众与彼时的受难者,在重回历史现场的瞬间,我们得以“凝视”那些反抗的士兵、勇敢的少男少女、无私的歌女,那些抗争过的、为别人牺牲过自己的人,带着一种对历史中死难者生命价值的敬意,我们确定了他们或她们生存的价值。这也确保了大屠杀中死难者在艺术空间里生命的价值,从而避免出现齐泽克所说的“符号性死亡”,死难者不是单纯地像牲口一样被虐杀,而是作为主体在死亡面前牺牲与给予,以此防止生命符号意义的消失,也帮助他们从历史的必然毁灭中赎回。
在匀速的电影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处是有意放慢了叙事节奏,进行隆重地“凝视”,一处是开篇中国军人排队炸坦克的长镜头,另一处是逃生的书娟在记忆中回眸玉墨们走进教堂时的绝代风华。在悲哀与诗意凝结的某一瞬间上,时间化为审美式的空间。其实,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在美学上更靠近中国传统的抒情小品,从整部电影看,它提供的不是在西方大屠杀电影中常见的史诗性宏大结构,也不是某种在异质的、多声部的话语思辨中提供切入历史腹地的尝试,它只是提供一个塞尔日·达内所说的“默哀仪式”:“生者需要电影的默哀仪式去释放因失去珍贵事物而聚集的恐惧和悲痛,电影成为克服恐惧和悲痛的生存仪式”[13]。这也是大屠杀电影通常的用途。
三、跨国批评背后的深层逻辑
我们都知道,由于语言及艺术形式自身的局限,要想通过艺术手段来再现创伤性历史事件是相当艰难的,正如一名犹太教哈西德派拉比所说:“有些真相由言语就可以传达,有些更深层的真相却只能由沉默来传递;而在另一层面上,则有一些真相连沉默都无法去表达。”[14]我们始终面临诸多悖论:如何由活着的人去叙述那些由逝去的死难者才握有的秘密?如何用虚拟的叙事去编织那些确实发生的悲剧与人们难以言说的痛苦体验?如何超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语逻辑,无私无畏地照亮历史暗夜中血腥、蒙昧的特定时刻?这是人类叙述大屠杀永恒的难题。正因如此,叙述与扭曲,揭露与遮蔽,成了大屠杀叙事中如影相随的孪生姊妹。面对大屠杀,任何个人或群体都无法在某个具体时段创造出全然真实的艺术作品和话语体系。
有了这个总体性的思想背景,反观《金陵十三钗》,也许可以得出中肯的评价:作为中国人叙述南京大屠杀话语谱系中的一个文本,虽未必是大屠杀影像中的杰作,但至少应该是合格的叙事作品,导演汲取先行者在大屠杀叙事中引起争议的经验,老练地设计了大屠杀中的反抗者、受害者、加害者与见证者这四种角色类型,严格地控制各种戏份,将种族、阶层、性别等多重冲突讨巧地编织在一个关于反抗与拯救的故事当中。当然,《金陵十三钗》也是妥协的产物,它努力在商业与艺术,普适话语与民族话语之间寻求平衡,有时显得捉襟见肘;同时在叙事节奏与制作水准上也有显而易见的短处,特别是如果将之放在世界大屠杀电影经典叙述的水平上要求,它确实有许多地方有待提高。
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于《金陵十三钗》的影片批评本不应构成问题,只要批评话语是常态的、健康的,不仅有助于提高中国艺术家叙述南京大屠杀的讲述能力与艺术水平,而且也能更有效地促进南京大屠杀作为历史话语的国际传播。再退一步说,在跨国批评中即使存在文化上的“误读”,也没有太大关系,或许正如乐黛云所说的,“两种文化相处时很容易有误解,‘误解’不一定符合被看的一方的本来面目,但能开拓人的思想”[15]。在西方批评者对《金陵十三钗》高分贝的批评声中,对影片文本的核心元素、叙事视角与电影美学的批评都不是问题,历史事实的彰显或许正是可以通过双方的对话与交锋而完成。但令人深思的是,西方“恶评”的话语逻辑不是基于彼时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而是现今刻板印象中的“中国想象”,所谓“中国资助”、“丑化日本、为国家发声”这种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新闻框架(newsframe)成为西方精英读解《金陵十三钗》唯一入口。这种靠流言蜚语的想象力拼接构成的解释框架不仅出现在一些不入流的小报上,也出现在如美国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英国《卫报》(The Guardian)这些公信力较强的大报上。如《纽约时报》的影评人说“《金陵十三钗》像是一场中国对外树立形象的战役”[8]。《好莱坞报告》的评论文章称“如果在1942年导演这样一部电影,也许可以成为有效的反日宣传片,而且博得好效益,但今天它扮演的只不过是低级噱头而已。”[11]。
英国《卫报》署名为乔森纳·沃茨(Joathan Watts)的作者用“中国指望用血腥大片赢得朋友和奥斯卡奖”(China banks on bloody blockbuster to win friends…and Oscars)为题,首段就开宗明义:中国政府已加大了对媒体和文化产业的投资……但该片情节乏味、表演僵硬,带有宣传意味。接下来沃茨强调“这部电影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过后几天就开始公映,看来中国过去遭受的苦难和如今文化产业的雄心壮志都将借助该片激发出人民的民族热情。”仔细读来,《卫报》这篇评论文章的结构十分“特别”,它用了三分之一谈及“南京大屠杀”的政治意义:“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什么事件比‘南京大屠杀’更加敏感……自从毛泽东执政时期开始拍摄黑白宣传史诗作品起,这场屠杀在中国经常被改编制作成电影。而这部高预算的新片加入了更有挑逗性的对话、形象造型和高科技元素。”接下来三分之一,聚焦中国政府打算振兴文化产业、提高软实力;而在最后的三分之一,则谈了日本观众对该类影片的观感,它使用了两个被采访人的话,一个是生活在东京的影评人马克·席林,他说:“想想中国在过去几年中拍摄的所有反日题材的电影,再多一部不会有什么大的区别。”另一个是日本右翼学者(Rightwing academics)Hirohito Moteki,他把承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看作”历史受虐狂”(historical masochism)的症候。[12]。
不难发现,持此类话语的西方批评者有一个概念上的偷换,那就是“如何讲述南京大屠杀,如何进行历史的问责”,变成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此时此刻要说南京大屠杀?”这个概念偷换是耐人寻味的,它指向过去,也指向现在,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混淆了过去与现在,它不是着眼于彼时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而是富有意味地聚焦现今西方精英刻板印象中的“中国想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概念偷换的逻辑不是第一次作用于在南京大屠杀身上,也不仅仅发生在欧美学者身上。2003年日本右翼学者富泽繁信在《南京事件の心》一书中就宣称“南京事件是因为中国政府嫉妒日本的经济成就而采取的政治手段。为了提高中国人的向心力、实现他们的外交目标,中国政府就利用南京事件谴责日本,达到其宣传目的”[15]。这是如出一辙的逻辑。
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大屠杀带来了深刻的话语资源。而这种作为历史的话语资源又最大限度地为当代的各种需求所利用,对于南京大屠杀来说,政治偏见与西方话语中心的规则成为了操纵性环节。这种充满意识形态的偏见,这种具有后冷战意味的对峙,暗示了大屠杀叙事是如此紧密地镶嵌在政治秩序框架中,也正是后冷战政治秩序的西方知识话语环境造成了南京大屠杀边缘性地位。如此显在而强大的因素使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叙事无法真正发挥作用,所有回溯过去的努力都被无谓地引向当下。在针对《金陵十三钗》的评论中,这些跨国批评话语是很有问题的,这不仅是苛刻的双重标准、胡搅蛮缠的逻辑,充满优越感却罔顾历史事实的指手画脚,恰如桑德拉·哈丁所指出的“整个优势群体往往在这种框架内思考自然界和社会关系,并且往往用这种框架为他人建立社会关系。”[16](P202)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以艺术批评的名义掩埋事实、歪曲真理,公然蔑视大屠杀中的死难者与活着的人的情感。这些批评话语溢出艺术之外、直指当代政治,以艺术之名却不行艺术之实。同时,它们也提供了一个话语症候,这症候既指向单部影像文本的际遇,也揭示了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在西方视野中被搁置与边缘化的命运与深层原因。
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艺术界的事实——南京大屠杀与犹太大屠杀影响力的不对等性,全世界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电影至今不过十几部,而叙述犹太大屠杀的电影已成百上千部;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学术界的事实,“不像在中国,海外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一直是个充满争议并且相当敏感的历史议题。它在各种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政治势力和民族主义立场的干扰和影响。”[15]。但是,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意味着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里惨绝人寰的具体事件,而且已经构成中国人感情记忆中一个最突出的象征符号,象征着二战中日本军队在中国国土犯下的骇人罪行。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南京大屠杀从不需要被刻意宣传,然而它有权利被中国艺术家或世界艺术家讲述,正如阿多诺所说:“有必要让苦难发出声音,这是一切真理的条件。”[17](P17)
标签:金陵十三钗论文; 南京大屠杀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张艺谋论文; 克里斯蒂安·贝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