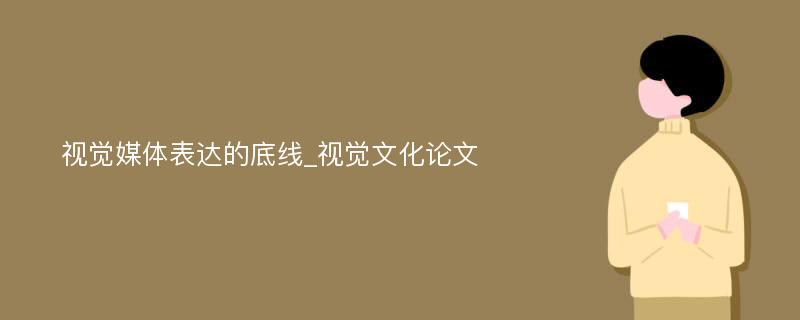
视觉媒介的表述底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底线论文,视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0)05-0124-(06)
如果我们承认当今正处于一个视觉文化的时代,那么,我们过去以文字为基准而建立的传播策略和社会伦理,现在都面临着一次历史性的检验与重构,最起码我们应当思考的是:所有适于文字表述的内容都适于用影像来表述吗?进而言之,即便我们对传播内容的判定具有某种合理的依据,那么在影像化的社会语境中,这种文化标准又是否能够真正执行呢?不过,我们在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之前,有一个事实是可以确认的,那就是视觉时代的社会问题肯定比印刷时代更为普遍、也更为尖锐,这是因为视觉的力量从来都比文字的力量更为直接、更广泛、也更强烈。
不论是虚构性的故事影片,还是专题性的纪录影片,凡是由影像组成的视觉媒介,对它们的内容和形式都有必要进行文化分析、甚至是思想的检查。人类自从有了电影不久就有了对于电影的审查,这不是因为电影伟大,而是因为这种通过逼真的影像来表现生活的艺术,不仅能够给人造成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而且还极易引起人们模仿的欲望。我们可以举出太多的恶性事件都和影像媒介有关,从刺杀在任总统,到校园枪击案,从在闹市里飙车,到9·11的恐怖袭击,几乎都可以找到它们和影像媒介千丝万缕的勾连。所以,影像媒介的表述问题,并不单是一个艺术的命题,它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问题。
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开辟了一条通往现实生活的捷径,它比文字更直接、比绘画更真实、比舞台更丰富,遗憾的是在这条路径上最令人们兴奋的往往是那些灾难性的事件。这可能与早期电影的新闻属性有关。所以,早期电影频繁地涉及到死亡与毁灭的事件。托马斯·爱迪生在其早期影片《大象受电刑》(1903)里面就详细地展现了一头大象被电刑处死时的可怕景象,直至拍摄到大象脚底都冒出了白烟。与此相似的还有《在加尔维斯敦的大马路废墟中搜寻尸体》(1900),片中展现的是德克萨斯的一场飓风所造成的惨痛现场。还有《宣读死刑判决》和《执行绞刑》(1905),记录的是对一位女犯人行刑的真实情景。也许观众对电影的这些内容会感到厌恶(小说里面描述的此类事件不会让人们产生如此强烈的反感)。但是,对这些令人恐怖事件的表现却在世界电影史上形成了独特的电影类型:恐怖、惊悚、灾难片。所以,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现在被激进的批评家指控,它终结了已延续了两百多年的精英文化。[1](P118)
如果灾难、恐怖类型是电影望而却步的禁地,电影恐怕就不会有今天的情景了。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历史灾难都是适合用影像来表现,即便就是要表现,也存在着一种在什么语境、用什么方式来表现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带着巨大心理创痛的不幸事件,并不能够因为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就可以随意地被搬上银幕。
美国在9·11后并没有立即拍摄以这个恐怖事件为题材的影片。是好莱坞没有这种制作能力吗?是美国人把这个世纪的灾难忘却了吗?显然不是。事隔5年之后,美国环球影业公司才拍摄了直接表现9·11事件的影片《93号航班》。①在这部93分钟的影片里,导演表现了在93号航班里所有陌生的乘客及机组成员在危急时刻团结一致、共同粉碎恐怖分子劫机阴谋的故事。尽管所有人员无一生还,但是机上自发的反抗行动粉碎了恐怖分子计划撞击白宫的阴谋,为被恐怖主义笼罩的纽约上空带来了胜利的希望。导演保罗·格林戈拉斯并没有刻意再现9·11空难的惨状,而是以指挥塔台上的蓝色荧光屏的消失取代了飞机遇难场面,包括丧心病狂的劫机犯把飞机撞向地面,导演是用静场、黑幕来表现飞机坠毁的最后瞬间。影片没有一个直接表现飞机坠毁的镜头(世贸中心的撞击镜头是通过在指挥塔台里的工作人员目击现场的方式间接表现的),这种淡化灾难场面的修辞方式,使观众在心理上铭记那场世纪性灾难的同时,在情绪上远离它所带来的痛苦和恐怖。还有同样以9·11事件为题材的影片《华氏9·11》,同样是以黑屏(带画外音)的形式来表现飞机撞上世贸中心的情景。是没有记录当时现场情况的影像素材吗?是缺乏制造空难情景的技术手段吗?显然都不是。美国人是不愿意再现那个让所有人都撕心裂肺的悲恸景象,不愿意利用摄影机去揭开人们内心还在流血的伤口——这也许就是视觉媒介表现的底线。
自从5·12汶川大地震以来,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通过某一种方式把我们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能把我们对这样一个震撼世界的事件的内心感受表达出来。可是,对于这样一个指涉到巨大民族创痛的历史灾难,对于一个关乎到数万人生死的“带血的题材”,我们并不应当去轻易地触碰它。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过后不久,以这场灾难为题材的影视作品纷纷诞生,有些作品仅仅是从一个行业如何参与抗震救灾的角度出发,把在这样一个以重大历史灾难为题材的作品所应当表述的人道主题置于行业的作为之下,这样难免会失去这种作品的深度和高度。另外,灾难片本身的情节设置不可能回避逼真的灾难情景,观众对灾难片的观看过程中也潜藏着对“影像奇观”的观赏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对灾难现场的表现更应该坚守必要的心理底线,不能够把地震造成的灾害作为招揽观众的“视觉奇观”来展示。包括“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事件,在中国电影中已经多次出现:罗冠群导演的《屠城血证》(1987)、牟敦佩导演的《黑太阳南京大屠杀》(1995)、吴子牛导演的《南京1937》(1995)、郑方南导演的《栖霞寺1937》(2004)、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2009)。我们可以说,当看见一个走在街上孑然独行的老人,突然间被冷枪打死,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滥杀无辜;一个被日本鬼子轮奸了的中国女人,经受不住身心的摧残精神失常后,被日寇随手枪杀,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惨无人道;成千上万的平民在江边被日寇集体屠杀,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杀人如麻;特别是我们看到一名不满10岁的女孩被日寇毫不犹豫地从窗户里扔出去的时候,我们感悟到了什么叫人性丧尽……可是在以上这些影片中,我们还看到了更为残酷的屠杀场面,比如在《黑太阳南京大屠杀》中,日寇把中国孕妇腹中的孩子挑出来挂在刺刀上的镜头,还有中国妇女遭到群体奸污的场面。这些惨不忍睹的影像对人的接受底线是一种挑战。影片《风声》设计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酷刑,有许多观众由于无法忍受血淋淋的残酷场面而中途退场,在现场无法面对这种阴森恐怖的情景而捂住眼睛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我们不能够因为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就可以毫无修饰地表现血腥屠杀一样,我们也不能够因为讲述的是一个革命者的斗争故事就可以任意地展示种种酷刑。我们知道,用文字表现的内容并不一定就适合于用影像来表现,况且残忍的杀戮难道必须要用残忍的方式来表现才真实吗?
影片《甘地》也有一场表现血腥杀戮的场面,那是英国军队对1,000多名手无寸铁的集会者的屠杀。导演在近两分钟的时间内为我们提供的观看角度是一个客观的、记录性的、具有历史感的视点,那是一个拒绝与英国人的视点相同一的空间视点,大部分使用了远景和中景镜头,这种叙事主体与视觉主体的分离使观众能够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位置观看这场血腥屠杀,避免了观众与英国殖民者的同化。应当说,这种对暴力情境的表现本身就具有非暴力的影像特点。导演不仅在表现内容上“忠实”了甘地的非暴力主义的文化精神,而且也在表现形式上同样“忠实”了甘地的人道主义理想。希区柯克的《精神变态者》(1960)不仅是这位悬念大师的代表作,而且也是世界惊险恐怖电影的经典之作。在阴森惨烈的气氛中,他创造了恐怖影片的经典段落——浴室谋杀(时至今日它不知道被后人“复制”过多少次)。在2分47秒的时间内,希区柯克用54个跳切镜头,可是其中没有一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人场面,却造成了世界电影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恐怖情景!由此可见,恐怖的场面未必要用恐怖的方式来表现,血腥的情景也未必就一定要用血腥的镜头来渲染。
《英雄》在中国武侠电影的历史序列中无疑是一部带有暴力(刺秦)内容的影片,可是在这样一部长达2个小时的武侠动作电影中,没有一场真正的以杀戮为目的、以生死较量为旨意的武打。影片中所有的武打场面都是非对抗性的武舞表演。它们不是假定的,就是意念化的,不是想象的,就是虚拟的。尽管影片的故事内容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可是全片仅出现了三处滴血的镜头:残剑在无名的故事中被飞雪刺中后淌出的血,飞雪与如月对阵时剁在树上的剑锋上滴下的血与秦王被残剑划破脖子流出的血。与那种血光四溅、尸横遍野的武侠电影相比,《英雄》这种“消解暴力”的叙事策略,表现出它的作者对武侠电影经典叙事方式的把握和对电影观影心理的洞悉。同样的还有成龙。他是一位真正地用生命书写电影的“电影作者”,为拍电影数次受伤,流血,住院。据报道说有些保险公司都不敢让他买保险。他说“什么都不怕……能为电影而死”。为此,他的生命、他的行为本文与他所创造的电影叙事本文共同构成了成龙在电影史上的双重意义。所以,看成龙的电影,实际上是在看一个电影明星惊心动魄的历险记。可是,成龙的电影里几乎看不见鲜血。他曾经说,在他的电影里会有许多喜剧,但是不下流;会有许多动作,但是不血腥。
也许,对于历史大屠杀这类的历史灾难最好的影像方式是用纪录片来表现它,因为纪录片在电影中是最逼近真实的片种,除此之外,在商业化的电影体制中在这样一个用人的生命来表现的题材中,任何商业的诉求都是不合适的,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事件,我们宁愿用集体募捐的方式来筹集拍摄资金,也不愿意让这种题材的影片有任何经济的负担,否则,一旦被商业的逻辑所控制,影片的市场回报必然牵动影片的表述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就难免会对历史事件的客观性有所取舍,如果不能够把握这类影片的真实度,那么损失的就不仅仅是金钱,更重要的它可能还会扭曲人们的历史记忆,使在地下的数十万魂灵永远不能安宁。
克劳德·朗兹曼1994年在《无法再现的大屠杀》这篇富有影响力的文章里严厉地批判了斯皮尔伯格将奥斯威辛“无法再现的”事件改成电影故事片的做法。作为一部揭露纳粹德国种族屠杀的政治片,《辛德勒的名单》中布满了许多令人惊悚的屠杀场面:纳粹法西斯凶残暴戾,任意杀戮无辜的犹太平民,以杀人取乐,把犹太人作为靶子随便枪杀!纳粹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像人类历史上一场阴森惨烈的噩梦,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多世纪了。但是至今人们仍然不能忘却那600万被屠杀的犹太儿女。在朗兹曼看来,《辛德勒的名单》犯了歪曲历史事实之罪,因为在这个犹太大屠杀的历史故事中,每个人都和其他人交流,甚至受害的犹太人跟他们的迫害者也会交流。事实上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朗兹曼谴责的不是斯皮尔伯格对“历史细节”的改变,也不是原著作者托马斯·基尼利对历史事件的表现,他指责的是塑造这些细节和事实的叙事方式,是用一种故事化的娱乐形式来再现这个人类历史的悲剧。对于我们来说,《辛德勒的名单》是一部描述法西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巨片,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在阴森的长夜里奔向黎明的生死进军,人们不再把牢狱作为永久的黑暗之地,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粉碎的牢笼。这也许正体现了当代人对这个人间地狱的深切的痛恨。当年,《辛德勒的名单》在欧洲国家首映之时,人们为斯皮尔伯格铺上了红地毯,他先后受到法国总统密特朗、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波兰总统瓦文萨的接见。而对朗兹曼来说,《辛德勒的名单》是个“庸俗的传奇式戏剧”,犹太人的大屠杀在这里显得平凡而琐碎。包括如《美丽人生》和《午夜守门人》(一部将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关系塑造成施虐受虐狂的心理剧),有人认为它们表明了将历史浩劫作为娱乐奇观来再现的普遍倾向,[2](P90~92)这些都是克劳德·朗兹最不能够接受的伦理底线。如果我们接受克劳德·朗兹的观点,那么我们是否也应当设定一个让娱乐媒介止步的文化禁地呢?最起码我们在涉及到某些特殊题材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它在表现灾难时的视觉禁忌,这种禁忌也许就是视觉媒介的表述底线。
在以经济利益为主要驱动力的时代,媒体的经济利益与社会的公共道德经常会发生某种冲撞和抵触。媒体应当在坚持基本的职业操守的前提下,去获得其自身的发展诉求,而不是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才考虑其职业道德的坚守问题。这里就涉及到了媒介表述内容的道德底线问题。
如今追求收视率是媒体普遍信奉的商业策略,在这种制片取向驱使下,影视节目传统的分类边界不仅正在逐渐消失,为了吸引观众的视线,有些节目甚至开始踩踏媒介最基本的道德底线,直至把人类的恐怖灾难事件作为有奖竞猜的素材。2004年9月6日晚,我国一家电视台在转播俄罗斯北奥塞梯学校人质事件时,屏幕下端的滚动字幕竟然是:“有奖竞猜:俄罗斯人质危机目前共造成多少人死亡?下列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A 402人;B 338人;C 322人;D 302人。移动用户发答案至××××××;联通用户发答案至××××××。”同年,在阿富汗的恐怖袭击事件中,11名中国工人遇难,4人受伤,该事件牵动了党和政府与亿万同胞的心。可是某电视台在节目播出中却打出了滚动字幕:“发短信到×××选择中国工人遇害的袭击者:A基地组织;B东突分子;C当地势力。猜对可获美国十日游奖励,每天1名幸运者!”[3]这种以杀人事件为竞猜内容来吸引观众的伎俩,以历数屠杀自己同胞的人数来刺激收视率,媒介的道德底线已经被践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还有比这种道德的“缺席”更带有颠覆性的问题是,我们正处在一个虚拟美学盛行的时代。正像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在1983年宣称的那样,“景观社会”已告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拟像”(simulacrum)时代的到来,所谓“拟像”就是没有原物作为摹本的图像,它“与任何一种现实都没有关系:它只是自身的纯粹的拟像”。鲍德里亚认为掩藏在这种“拟像”背后的是“图像的谋杀能力,它是谋杀真实的凶手”。[1](P31)换句话说,它已经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真实现实相去甚远。所以,现在关于视觉媒介的道德底线与修辞策略都应当重新修订,传统的判断标准已经很难应对复杂的现实问题了。
不论是在传播学的视野上,还是在美学的领域中,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共识,那就是现在并没有一个能够和客观世界相互对应的真实的影像世界,影像世界的真实只是一种表述方式的真实性,一种叙事立场的真实性,这种真实都是以人的主观取向为前提的。谁说摄影机不会说谎?如果对于A的选择就是对B的回避,那么,从摄影机开机的时刻起,也就是它开始“说谎”的时刻,因为它选择了此时此地、没有选彼时彼地,前者的真实承诺其实就是对后者的欺瞒,况且摄影机的取景框更是遮蔽了摄影机之外的所有世界,那些没有进入摄影机的世界难道就不真实吗?我们能够说那些没有出现在影像表述话语体系中的客观现实就根本不存在吗?显然不能。这说明摄影机的记录属性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摄影机的客观属性。
在现代电影理念的视野下,叙事的策略不是强调影像的客观性,而是强调摄影机的视点、观众的视点与银幕角色的视点的一致性,这种以“三点合一”为叙事形态的影像体系,总是利用大量的正/反打镜头和完整、均衡的画面构图来消除观众的客观立场,使观众脱离现实的客观存在,进入到影像为其提供的观影情境(剧情)之中,使他们成为内在于银幕的一部分,成为本文意指系统的被编码物。这如今已经成为主流电影普遍采用的一种修辞策略。
主流电影的修辞策略始终是以对观众心理的同化为目的,而艺术电影则往往采取不尽相同的表述方式,使观众与银幕保持相对的间离,使其具有相对客观、独立的审视角度(立场),把观众从以情绪介入为主要方式的电影观赏惯例中解脱出来,进而能够真正地按照自我的立场、而不是剧中人的立场来审视影片。长镜头通常被认为是艺术电影的“拿手戏”。它不仅能够保持银幕空间的完整性和时间的连续性,而且还能够使观众的观察视点客观化。众所周知,暴力是常规电影的基本母题,不论是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同样都在表现暴力,但问题的关键是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主流电影大都以快节奏的正/反打镜头来展现暴力的情景,在快速的镜头切换中把观众带入到紧张、激烈的暴力剧情中,而艺术电影一般都采用长镜头来表现暴力的场面。
侯孝贤导演的影片《风柜来的人》在表现澎湖地区青少年打架的场面就是以固定的机位和长镜头把事件的全过程客观地展现给观众;台湾新电影的代表作《小毕的故事》中,小毕和同学在街上与流氓打架(包括有人被刺、小毕疾跑),导演采用的也是中远景距离的景别和不加任何剪辑的长镜头;《油麻菜籽》中丈夫与妻子的厮打,《悲情城市》中在乡野中的争斗,都是以长镜头作冷静、客观的凝视。包括表现人物的对话,也经常以长镜头、单视点来表现,使银幕宛如是一扇打开的窗子。最有说明性的是,在《我这样过了一生》这样一部长达117分钟的故事片中,竟然没有一个正/反打镜头出现。
对这种以长镜头见长的新电影的评价,以往人们总爱把它的意义引入艺术的风格论范畴,认为这样是完整地体现了巴赞所崇尚的所谓“纪实美学”的风格,其实如果是从观众心理的意义上看,这种叙述方式最重要意义在于,它阻止了观众的潜意识进入影片的本文/阅读系统,使观众在观赏常规电影中时常出现的本我的欲望受到扼制:观众既没有在女性温情的注视下渐渐陶醉;也没有以男性正义者的身份使潜意识中的暴力欲望得以宣泄。可见,不同的美学理念,不同的创作主旨,会遵循不同的视觉修辞策略。不论因为电影艺术的历史发展,还是由于电影导演观念的转变,电影的修辞策略并非一成不变,“世界上不仅没有一种可以统一运作的电影理论,能放诸四海皆准的一套电影分析方法也不存在。”[4](P12)
以视觉影像为载体的电视节目同样也涉及到如何利用有效的修辞策略来引导观众的问题。2004年北京电视台《法制进行时》节目跟踪拍摄了北京市公安局解救被绑架的电影演员吴若甫的过程。当时摄制团队分成了两个组,一组跟随公安局刑警队到现场拍摄营救的情景,另一组在公安局拍摄指挥整个行动的局领导办公现场。跟踪拍摄这个破案的行动无可非议,对这种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人质事件”曝光也未尝不可,可是我们从电视媒体视觉表述策略来看,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是:在这样一种极具纪实性的新闻报道中,本应最大限度地“抵近现实”,保持一种电视观众与所报道的事件之间“零距离”的心理感受,同时最大限度地隐藏摄影机的存在,包括隐藏相关电视摄制人员的存在。整个报道过程中的主角始终应当是在场的公安人员和当事人,而不应当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换句话说,这个节目的特定内容决定了它应以一种现场报道的节目形态出现,主持人在这个报道中是以幕后的方式出现,不应当、也不可能成为这一事件的主角。特别是在一场关乎人质生死的解救行动中,不应当表露出任何媒体在进行“自我炒作”的意图,整个报道应当是给观众造成一种“目击现场”的真实感觉。
真实是所有艺术形式和大众传媒都竭尽全力所要实现的目标,但是真正能够到达真实心理效果的作品并不很多。包括以真实电影而出名的法国电影导演布莱松——他之所以受到人们的膜拜正是因为他的影片创造了一种与好莱坞主流电影截然不同的真实的空间形态,因为与其他类型的影片相比,他的电影更逼近现实,更具有现场感。但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布莱松精心营造的真实感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在当代视觉文化研究的视野内,布莱松的镜头语言并不是最为真实的修辞策略。在他的影片中我们多次看到主人公开门/进门的系列镜头,这些镜头的排列方式是:前面的镜头(在屋外)拍摄的是主人公在门外准备开门进来的场面,后面的镜头(在屋内)拍摄的是门被打开,主人公走进屋内的情景。后面的镜头等于告诉观众,摄影机已经先于影片中的人物进到房间里,并在等待着主人公到来。摄影机的这种调度方式无疑破坏了观众对影片的真实感受,因为在现实的意义上讲,摄影机并不可能在那里等着人走进来,在真实电影的代表人物(在西方电影史学界布莱松和雷诺阿都被认为是真正的“作者”的范例),[5]那里都会出现这种修辞策略上的问题,更何况我们平时看到的电影了。记得前些年笔者曾经参加《东方时空》节目的评奖,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那时即便是最崇尚影像真实性的导演,在他们拍的节目中依然也会出现这种“先入为主”的镜头,所以影视作品的创作归根结底在于你要在一部作品中实现什么样的意图。而你要达到这种意图所采取的途径,是否与你的目标相一致,影像的修辞策略在此便具有极其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我们现在已经陷于一种视觉化的生活环境中,在公共汽车和超级商场里,在高速公路和机场登机口上,以及在银行的自动取款机旁,摄像镜头一刻不停地监视着我们。同时,我们的工作和休闲也越来越依赖于电视、电脑和各种视像媒体。人们的经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需要视觉图像的支持,从浩瀚的天宇中传来的卫星照片到人体内部微循环血管的医学摄像,视觉影像几乎垄断了我们对世界的全部感觉。但是,这一切究竟只标志着我们的文化境遇,还是在改变着我们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呢?这是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
注释:
①据当时的新闻报道称:“美国联合航空公司93次航班9月11日上午遭劫持后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的一片树林坠毁,机上45人全部遇难。据报道是由于乘客反抗,恐怖分子利用该机攻击华盛顿重要目标的战略企图才告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