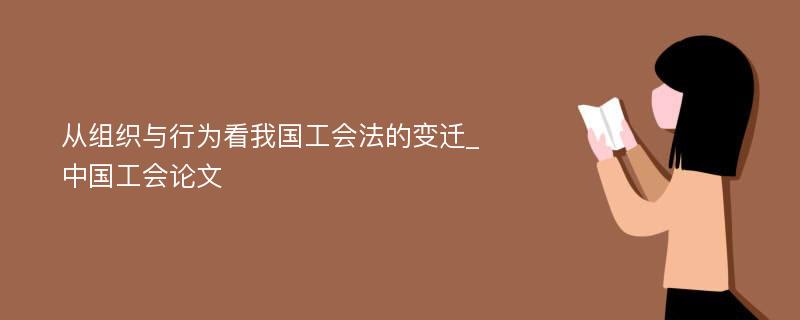
组织与行为视阈下我国工会法变迁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会法论文,组织论文,我国论文,历史论文,视阈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6)05-0082-04 一、工会法发展的三个时期 综观世界各国工会法的历史发展,政府刚开始一般都禁止工会的组织以及行为,随后认可工会的组织,但对其行为又给予限制,发展至最后,法律对工会则采取积极保护的态度[1](P60-61)。禁止时期的工会组织被视为非法组织,其活动和行为往往被视为犯罪。然而,随着工业时代工人数量的增加以及资本家压迫的严重性,工会组织作为事实上的存在成为无法遏制的趋势,法律的态度只能由禁止转向认可。随着工会组织的日渐强大,开始逐渐掌握立法上的话语权,工会法亦走向积极保护时期,法律开始赋予工会以相应的权利,包括劳动团结权、团体交涉权以及争议权[2](P254)。 我国工会法也经历了前述三个时期,但稍有不同,而且最终找到了契合自己国家历史与国情的道路。总体而言,清末及北京政府初期对待劳工组织及其活动采禁止态度,属于反劳工立法。到20世纪20年代,北京政府的三部草案让工会法进至承认但限制时期。同时期,在南方的广州政府则率先立法,并创建了近代中国最为先进的工会法,此属于积极保护时期。但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会立法又返回到承认但限制时期[3](P37)。新中国成立后,工会法所确立的工会职能更为全面,而且将西方工会与企业的对立状态转变为合作共赢的状态。直至今日,工会组织在维权的同时,也积极投入到国家和社会建设中,构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工会法和工会运行模式。 二、组织视阈:我国工会法的三次历史转变 (一)从禁止到有限承认:北京政府工会立法的转变 清末法律禁止工会组织的存在,更不允许罢工的存在,罢工行为被视为刑事犯罪[4](P152)。到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了《治安警察条例》,同样对工会组织采取禁止态度,其中即规定警察和官吏可以对劳工聚集进行禁止,而且对劳动聚集过程的煽动行为给予处罚,最高可处五个月徒刑和五十元的罚金[5](P7-12)。此为工会组织在中国的禁止时期。 但自1923年开始到1925年,北京政府先后起草了三部工会法草案,分别是《工人协会法草案》、农商部《工会条例草案》和交通部《工会条例草案》[6](P243-251)。通过对三部草案内容的考察,尽管它们都对工会组织进行了种种限制,如农商部《工会条例草案》就禁止地方各业工会的联合,联合组织不但要遭到解散,而且也要对发起者处以刑罚[7](P1077),但我们仍然要看到其进步的一面,中央政府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开始认可工会组织的存在。之所以此时开始认可工会组织,根本原因在于工会组织自身的发展和实力的增加。如在广东出现了一些地方性工会和较大的工商联合组织,较为著名的广东总工会就有7个支会,国民党员谢英伯创办的互助总社有23个团体会员,计有人数约2万多人[8](p69-75)。正是因为工会组织的发展,才掀起了随后全国范围内的罢工高潮,在罢工过程中又成立了更多的工会,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而此时的北京政府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形势,只能对已出现的工会组织予以认可和拉拢。 (二)从积极保护到限制:国民党政权工会立法的转变 1922年广州军政府颁布的《暂行工会条例》以及随后在1924年以此为基础修正而来的《工会条例》[9]将中国的工会法推至积极保护时期。其中,《暂行工会条例》[10]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得以实施的工会法。从内容上来看,《暂行工会条例》对工会的设立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对工会的运行采取保护的态度,赋予工会全面的职能[3](P62-63)。《工会条例》更是赋予了工会以同盟罢工权、团体交涉权、团体协约权以及国际联合权,成为国民党政权最为先进的一部工会法[3](P68-69)。 之所以此时能够积极保护工会,与国民党此时所处的革命党地位有关。作为革命党,其首要问题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推翻现行政权而建立新政权。此时期的工人力量正以空前的速度发展,不论是孙中山还是国民党其他的领导人,都无法忽视此种力量。戴季陶强调“制定工会法及工场法,尤为必要而不可缓之事业”[11]。孙中山同时期也提出了保护劳动、谋进工人生计、提倡工会的施政方针[12](P433)。可以说,两部法律的出台与孙中山提出的施政方针密切相关。 在此种方针和法律的影响下,中国的工会组织和工会会员显著增长,工会运动也开始兴盛。据统计,在该条例颁布后的1925至1926年,两年中的罢工次数达到853次,参加人数达到1324406人,而从1918年中国工人运动开始到1926年这九年中共计罢工次数才有1232次,参加人数1613291人[13](P147-148)。只可惜此部法律实施的时间过于短暂,实施的范围也仅限于南方少数省份。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国民党政权对工人政权实施了铁血政策,其工会法也出现了历史性退步。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工会立法方面的成果可谓丰富,然此时国民党的工会立法渗透着限制与控制的主导精神,中国的工会法又退至承认但限制时期。以1929年《工会法》为例,无论是对工会的组织还是对工会行为都有不同程度的限制甚至控制。就组织而言,该法对发起人数、发起和组织主体、发起程序、工会联合都有法律上的限制[3](P102-106)。就行为而言,该法对工会的团体交涉权进行了限制,工会缔结、修订和废止团体契约须经主管官署的认可[14]。同时,对罢工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该法明确规定,因劳资纠纷而需要罢工必须得首先通过调解仲裁程序,同时还需经过全体工会会员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14]。 之所以控制与限制的精神主导此时的工会法,与国民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变化密切有关。在大革命时期,改组后的国民党尚能代表工农阶级利益,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也曾以扶助农工为己任。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国民党蜕变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其代表的利益甚为狭隘。为了维护自身阶级的利益,即开始打压劳工组织,劳工阶级利益让位于所谓的国家利益。此外,也与国民党解决劳工问题的改良态度有关。孙中山认为工业的发展不仅能够带来资本的繁荣,也同样能够带来工人工资的提高,所以他强调劳资要互助,农工应合作[15](P115)。此时的劳资协调政策实际上被国民党政府演化成为实际的限制和控制。此种情形下,中国的工会组织、工会会员人数显著减少。在1927年5月在汉口召开泛太平洋劳动大会时,中国代表报告全国有组织的劳工达到3065000人,而到1930年4月,全国主要省份和城市的工会组织仅剩771个,会员人数仅为576250人[16](P13-17)。再以浙江省为例,从1927到1932年,工会组织和工会会员几乎都减少了十分之九[17](P1)。此时是中国工会的衰落时期,也是工会法的退步时期。 (三)由对立走向共赢:新中国工会法的转变 前述工会立法都将工会与企业、工会与国家置于对立的地位,而自新中国成立后,法律之态度为之一变,即赋予工会组织充分而又全面的职权,同时又消解了工会与企业、工会与政府的对立状态而走向互利共赢的模式,工会成为政府政策法令的助推器。以1950年《工会法》为例,就组织而言,无论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无论工人人数的或多或少都可以组织自己的工会,且政府、企业的行政方面或资方都有责任提供必要的场所与设备;就职权而言,赋予工会应有的基本权利如交涉权、缔结集体合同权等,此外还赋予其抗议权、视察权等,工会职权全面而充分;此外,工会与政府始终保持密切的关系,能够协助政府完成各项事业,促进社会建设,如该法第九条即明确规定,工会应当教育并组织工人维护政府法令,推行人民政府政策,保护公共财产,反对贪污浪费,而对于私营企业,也强调要积极从事生产,以实现劳资两利[18](P3)。 之所以能够消解对立与对抗,应与共产党政权的性质密切相关。陈云曾认为工人阶级既然已经成为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在国营、公营和合作经营的企业中就不存在劳资关系的矛盾,因为职工已经是企业的主人,而在私营企业中,虽然有劳资关系的存在,但由于职工们在政治上、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就保障了职工们不致受到压迫和过分的剥削[19](P426)。正是基于此,新中国的工会法才能够全面赋权给工会组织的同时还可以消解对立的矛盾,而致力于国家建设。 综上所述,从工会组织的视阈而言,我国工会法的变迁并非同西方一样直线条的发展,而是经过曲折与反复,不同政权自身也经历过发展和倒退。而新中国的成立更是发展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工会法与工会组织,消解了对立和矛盾,走向了合作与共赢。 三、行为视阈:工会权利的变迁与罢工权缺位的分析 (一)工会权利的变迁 工会的组织涉及宪法的结社权以及劳动法的劳动团结权,而工会的行为主要涉及宪法的集会、游行、示威权和劳动法的团体交涉权和争议权,其中,争议权的最激烈形式即为罢工权。 就北京政府三部草案规定的工会职能而言,《工人协会法草案》规定了五项职能,分别是会员互助、雇用条件改善、劳动状况调查、立法参与与陈述意见、答复政府的咨询;农商部《工会条例草案》规定了包括职业介绍、储蓄、劳动保险、劳工为生、智识技能等共济职能,规定了劳动待遇改善的经济职能,规定了请愿权、陈述意见、调处纠纷等政治职能;交通部《工会条例草案》在农商部草案的基础上,增加了部分共济职能,如事业介绍、会员养老等,赋予工会调解会员纠纷的职能[3](P58-67)。此时期的工会法并未明确工会的团体交涉和争议权,更多关注的是工会的内部运行和共济。 工会权利被充分认可是在当时南方的国民党政权。1922年广州政府的《暂行工会条例》对工会列有十项职能,包括:图工业改良发展;法规参与制定与建议;设立合作社;设立图书馆等以促进工人教育;缔结雇佣契约;职业介绍;保障同业者的利益;纠纷调处;同业者的就业失业统计;劳动者的生活状况调查[10]。该法并未赋予工会以罢工权,但赋予了缔结雇佣契约的权利,此为团体交涉权的一种,相较于北京政府的工会法草案更为先进。修订后的《工会条例》更是赋予了工会同盟罢工权、团体交涉权、团体协约权以及国际联合权。尤其是罢工权,该条例第十四条即规定,工会在必要时可以根据会员之多数决议来宣告罢工[9]。这是中国工会法发展史上罕见的一部真正赋予工会以罢工权的法律。 再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工会立法。1929年《工会法》尽管赋予了工会以团体交涉权和罢工权,但笔者根据历史材料的分析发现,这两项权利仅仅停留在文本中,并未真正付诸实施。就团体交涉权而言,如前所述,该法赋予了工会缔结、修订和废止团体协约的权利,但同时要求必须要经过官署的准许;就罢工权来说,该法对罢工权做了程序方面的种种限制,所以时人对1929年工会法给予了此种评价:“夫工人之结社权、团体协约权、罢工权,在新工会法固皆承认,而因有种种消极制限的规定,适令原定权利之内容、效率,为之削减,此又吾人从历来工会法案中,可以历历寻出党国当局对劳工运动思想变化之迹,殊堪供人玩味。”[20]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1950年工会法还是1992年工会法都赋予了工会以各项权利,概括而言包括民主管理权、签订集体合同及提起仲裁和诉讼权、提出意见权、交涉权、劳动条件监督权、调查权、重大事故处理中的参与权、参加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组织文体活动、政策制定与立法中的参与权等十几项。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会组织主要职能在于通过团体交涉权以维权,同时承担了部分政府的职能而助力于国家建设,实现多方面的互利共赢。 (二)罢工权缺位的原因分析 纵观我国工会权利的变迁,除却革命时期的工会法赋予最激烈的罢工权外,各时期的工会法都很少赋予此项权利,或者即使赋予该项权利,也有诸多限制。这与西方国家的工会尤其是工会与企业的对立关系构成了显著的区别,原因除了与上述国共的政权性质原因外,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让我们始终规避劳工与企业、劳工组织与政府的对立?笔者以为这与我国的文明基础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 中国的核心文明源于农业,小农经济的基础决定着我们的文明特色和文化传统。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下,一家一户的独立运作足以保障基本的生存,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中人的基本生存可以依赖土地而自食其力,而不需要团结合作,只有在非常状态下如洪涝灾害,才需要合作[21](P31)。这就意味着中国人的生存和生活模式始终局限于家庭和家族这样的血缘关系群体,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始终突破不了血缘,也无需常态性地合作。当个体在家庭这类血缘性质的群体中生存和生活后,一旦进入到社会性组织,即会将血缘关系的生活方式和运作模式推广至社会,结果形成了无所不在的关系社会和伦理组织,这背后所见的尽是人情,如“师父”、“徒子徒孙”这类的称呼,即将血缘关系的父、子孙与社会关系的师和徒联结在一起,社会就难以形成对抗性的关系,故而中国的法律更多呈现出情理而非对抗的精神。也正是因为血缘关系的模式,社会组织难以形成完全性的竞争,也就难以出现集体合作的迫切要求,集体的合作与对抗一旦缺乏,中国社会的组织力即成问题。 反观海洋文明或者游牧文明,人们必须通过合作才可能赢得对自然的胜利,团体对于其生存至关重要[21](P31)。西方人在海洋文明及其基础上的商业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生活和训练下,他们始终在集团中生活,其组织力较强,个体意识也在团体中萌芽发展[22](P48)。在此种生活模式下,个人与团体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始终处于对抗状态,西方工会组织与企业之间的对立状态就源于此种集团生活的对抗模式。再反观前述的小农文明,此种文明下的中国人始终较为平和,每个个体始终在为家庭奔波奋斗,缺乏组织力,莫谈组织罢工,自身能组织成农会、工会都显困难。故而笔者以为我国工会法走向自身的特色,消解工会与企业、工会与政府的对抗,除了政权的性质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这没有突破血缘的社会结构中,中国人始终不会走向对抗,反而能走向建设,没有组织力,反而需要政府来主导。 本文从工会的组织和工会的行为两个维度去关注我国工会法的历史变迁,总体而言,我们并没有像西方工会法那样直线条的发展,而是经历了曲折与反复。同样的,我们也并未像西方工会那样始终与企业和政府处于对抗为主导的状态,而是走向了合作与共赢,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民众长期生活在没有突破血缘的社会结构中,始终形成不了对抗的组织,除非处于非常的革命时期,否则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其他各行业人员都难以组织起来去维护自身的权利。在此种传统的影响下,并基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工会始终以合作为主导,走向了自己特有的共赢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