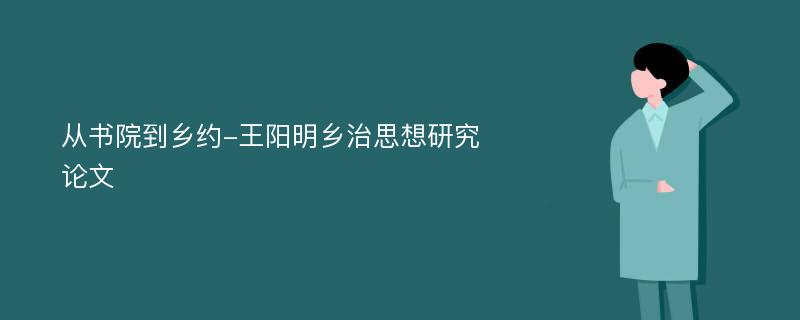
·哲学与文化研究·
从书院到乡约
——王阳明乡治思想研究
崔 树 芝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贵阳 550028)
摘 要: 王阳明的乡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乡约实践中。在乡约由民间走向官方,由地方走向全国的发展过程中,王阳明是过渡性的人物,他既焕发了乡约的新生命,在某种程度上也牺牲了乡约的民间自治精神。王阳明的乡约实践借助于他的行政权力,但不能简单理解为官方性质。与宋儒得君行道不同,王阳明选择觉民行道,并以书院讲学为主要载体。书院与乡约呈现体用或本末关系,乡约是书院讲学的延伸,是良知发用的治民事业,目的在于移风易俗。王阳明的乡治思想对当前的乡村振兴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王阳明;乡治;书院;乡约;觉民行道
王阳明(1472—1529),原名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他不仅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拥有卓著事功的政治家。他倡导知行合一,致良知教,既可以坐而言道,亦可以起而行道,在诸多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除了在儒学上的显著成就以外,他的乡约实践对中国后来的乡治格局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学者指出,王阳明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在江西推行的“南赣乡约”是明代第一次的乡约,是官办乡约的始发者。(1) 见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10页。此书最初出版于1937年,后来经学者考证,在王阳明之前即有人推行过乡约,但影响不及王阳明大,见董建辉:《明清乡约: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页。 经由王阳明及其后学的提倡,乡约治理模式借由官方的力量被推广到全国,一直延续到近代,就连梁漱溟从事的乡村建设,也是受到乡约的启发,大体上是采用乡约,对其补充改造[1]320。就当前的乡村振兴而言,也随处可见乡约的影响,如乡规民约的制定、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等,因而研究王阳明的乡治思想不仅具有学术价值,对完善基层治理亦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年轻时我们以自己为中心,中年后我们以世界为中心。年岁渐长,经历了太多起落,就会发现,我们没有征服世界,是世界征服了我们。这种“渺小感”,是生活赐予我们的领悟。我想,除了伟人站在高山之巅永远有气吞山河的气概和睥睨天下的豪情,我们凡夫俗子最终体验到的是“渺小感”。
王阳明的乡治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乡约实践中。要系统考察王阳明的乡治思想,不仅要从乡约发展史中找到王阳明乡约实践的地位,还要从王阳明整个心学体系来透视他的乡治思想,因为王阳明的心学是在书院讲学中完成,故而书院与乡约的关系需要引起特别的注意。
一、王阳明的乡约实践及其历史地位
王阳明的乡约实践于正德十五年(1520)正月。在此之前,王阳明于正德十一年(1516)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受命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十二年(1517)、十三年(1518)平定寇乱,他曾写信给弟子杨仕德,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十四年(1519)平定震惊朝野的宁王之乱。十五年(1520)正月,王阳明在江西推行“南赣乡约”。很显然,南赣乡约的推行最直接的诱因乃是社会的动乱。故而,王阳明希望通过乡约,来实现社会教化、移风易俗的效果。这一因时制宜的措施,影响了中国在此之后的乡治格局。
中国的乡村,秦汉以后一直没有组织起来,王权只是延伸到州县一级。秦汉以前的乡村,尚有乡里井田制度组织起来,在《周礼》中更是详细记录了“五家为里,五里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的乡官制度。秦汉时尚有乡治的余波,在此之后,乡村组织则每况愈下,而自东晋南渡、户口版籍丧失之后,乡治更是付之阙如。据杨开道考证,中国的乡村组织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周以前的传说时期,第二时期是秦汉以后的破坏时期,第三时期是北宋熙宁以后的补救时期。王安石的保甲青苗,吕和叔的乡约乡仪先后成立,才展开中国近代乡治格局[2]3。
保甲制首创于理学家大程子程灏,经王安石变法而推行各路,实际上并不是基本的农村组织。而吕和叔(吕大钧)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开创的吕氏乡约,却是真正的乡村组织,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举动,士人除了“学而优则仕”的选择以外,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实现抱负的领域,他们不是同政府,而是同人民打成一片,探索乡村自治之路。杨开道对吕氏乡约评价甚高,认为这一制度“打倒中国治人传统”“树立中国民治基础”[2]27-28。
吕氏乡约以乡为单位,易于实行,虽有乡村领袖倡议,但基本上还是乡民公约,并且自由加入,并无强迫。吕氏乡约的基本精神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这算是乡约的总纲,同时还有一套组织架构以及集会、赏罚机制。因为是初创,吕氏乡约也有一些局限。吕氏乡约并没有把农村事业打成一片,教育、经济、甚至已有的保甲也未能包含在内。故而,在一定意义上,吕氏乡约是乡民自治的道德教化、互助合作的共同体。
3)喷嘴烟气流速:再循环烟气在炉内需起到充分搅拌及降低炉温的作用,不同炉型、不同处理规模的焚烧炉对应的最低风速要求均不相同。喷嘴烟气流速需根据炉膛流场模拟进行设计,并结合运行情况进行优化。
乡约实践是书院讲学的延伸。换句话说,王阳明的书院讲学与乡约实践是体用或本末关系,乡约实践中灌注了讲学精神。
如上所述,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可作为学生初步参观学习的启蒙教育基地。此外,我们还可选择地坛公园中医药养生文化园、北京响水湖长城旅游景区名医塑像文化园、北京御生堂中医药博物馆、中国中医科学院古籍特藏部、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津门医粹”中医药文化博物馆等重要的中医药文化教育启蒙基地。
南赣乡约首先通过文告的形式澄清了实行乡约的目的及精神,而后就乡约的组织建设、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乃至举行乡约的仪式都做了明确的说明。鉴于当时动乱刚刚平定,王阳明又认为,风俗不美乃是祸乱之源,阳明进而指出:“民俗之善恶,岂不由于积习使然哉!”[5]507因而,要稳定社会秩序,必须从风俗入手,而要改善风俗,就要改变积习,逐步实现移风易俗的效果。所以,王阳明规定了乡约精神为:“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5]507这里不仅继承了吕氏乡约的精神,也糅合进了朱元璋的圣训六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的内容,在乡约仪式中,王阳明还专门设计了设告谕牌,宣读告谕的环节。自此,圣谕便加入了乡约的组织[2]105。
与吕氏乡约比起来,南赣乡约具有如下显著的特点:
这些区别,一方面使王阳明的南赣乡约激活了乡约的新生命,但是某种程度上也丧失了乡约的民治精神。杨开道不无批评地指出:“阳明提倡以后乡约完全成为地方施政的工具,清朝开国以后乡约又辗转成为政府宣传的工具,状况愈下,工作日卑,未始非阳明始作之俑。”[2]111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在乡约发展史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王阳明也成了乡约由民间走向官方的过渡性人物。
首先,吕氏乡约是乡民自治、较为自由的组织,具有鲜明的民间性。而南赣乡约则是政府督促、相对强迫的组织,具有鲜明的官方色彩;其次,吕氏乡约组织较为简易,约文是纲举目张的条款而南赣乡约组织较为严密,职员有十七人之多,约文也是一条条的文告,便于仿照执行;最后,从影响上来看,吕氏乡约推行不久便夭折,而南赣乡约借由官方的力量影响久远。
卧倒门液压缸额定启闭力为:推力,2×1 000 kN;拉力,2×600 kN。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液压缸无杆腔输出的最大推力约为1 100 kN,有杆腔输出的最大拉力约为660 kN,同时启闭机液压系统设有安全阀,启闭机的输出力理论上不超过额定启闭力。本文以1 100 kN推力、660 kN拉力作为启闭机启闭力的控制条件。
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一个现象,即王阳明在离开江西后,并没有急于推广乡约。王阳明父亲龙山公于嘉靖元年(1522)二月病逝,王阳明致仕守孝,直到嘉靖六年(1527)再次受命征讨思田之乱,王阳明在越六年,只是讲学,并没有在家乡推广乡约,可见王阳明对乡约还是持很审慎的态度。
良知发用为治民实践,但是治民实践又不止乡约一事,凡保甲、社学、社仓皆在其内。那么,乡约在王阳明这里到底居于何种地位呢?王阳明又是如何看待乡约的呢?王阳明在江西推行的南赣乡约,离任后并未在其他地方推行,乃至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五年(1521—1527)他闲居在家,六年时间专注于讲学,亦可以证明乡约是为政治民之事,闲居时则“思不出其位”。但是,王阳明在外任官的弟子中却有从事乡约者。年谱记载,嘉靖五年(1526)邹守益谪判广德州,筑复古书院以集生徒,刻《谕俗礼要》以风民俗。王阳明复书赞之曰:“冠婚丧祭之外,附以乡约,其于民俗亦甚又补。”[4]1067这个“亦”字,说明在王阳明心中,书院讲学乃是体,是本,而乡约乃是治民之用,之末。毕竟“理学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习日偷,风教不振。”无书院讲学,则理学不明,在此无突破,乡约实践即失去了根本。如果说乡约可以有所成绩的话,那么功虽在乡约,本却在讲学。
二、觉民行道与书院讲学
王阳明是一代儒宗,在幼年即有“何为第一等事”之问,而他的答案并非是如他父亲一般读书登第,而是读书学圣贤。纵观王阳明一生,他最关心的依然是体道、传道。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受命征讨思、田,赴任路上,他曾在寄给弟子的一首诗中说:“仗钺非吾事,传经魁尔师。天真石泉秀,新有鹿门期。”[5]656即便他在平定内乱上取得卓著的事功,这首诗流露出他的本怀还是在传道讲学。而在他平定思田之乱后,嘉靖七年(1528),他在南宁兴学校,王阳明曰:“理学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习日偷,风教不振。”[5]538这一年是王阳明生前的最后一年,也就是说,王阳明自始至终还是把昌明理学、移风易俗作为救世良方。而风俗的振兴,仰赖理学的昌明。因而有理由相信,王阳明起而行道的根据即在他坐而言道中,故而,要把握王阳明的乡治思想,必须要首先考察王阳明坐而言的道,也就是要回到书院讲学来看。
书院讲学自然可以起到移风易俗的效果,但还必须通过具体的治民实践。王阳明曰:“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在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则治民为一物;意用在读书,即读书为一物;意用于听讼,则听讼为一物;凡意之所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物非意之用乎?”[4]1064从这段引文中,王阳明揭示了良知发用的方式。良知应感而动为意,意之所在为物,此“物”即是“事”,治民乃是良知发用的一环,而乡约实践即是治民中事也。由此亦可以得出,王阳明的乡约实践若离开致良知教,即不能得到理解。
纵观王阳明的一生,他热衷以书院讲学的方式实现社会教化,而在政治上却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正德十五年(1520)的南赣乡约,并没有在其闲居时推广是一例,除此之外还有多方面例证。其一,正德十一年(1516)《谏迎佛疏》拟而不上。其二,正德十五年(1520)王艮初谒王阳明,纵言天下事,而王阳明答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王艮曰:“某草莽匹夫,而尧舜君民之心,未尝一日忘。”王阳明复答:“舜居深山与鹿豕木石游居,终身忻然,乐而忘天下。”[6]王艮纵言天下事,自然涉及政治批评,而阳明不答,以舜为比,乐而忘天下。其三,就连正德十六年(1521)至嘉靖三年(1524)震惊朝野的大礼议事件,(2) 正德十六年(1521)英宗暴亡,因英宗无子又无亲兄弟,堂弟朱厚熜以藩王继任皇位,是为明世宗。世宗欲尊生父为皇帝,遭到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为首武宗旧臣的极力反对,引发了震惊朝野的“大礼议”,最后世宗大获全胜,尊生父为“皇考恭穆献皇帝”,改明孝宗为“皇伯考”,涉事上百个官员下狱。 王阳明也不致一辞。年谱记载,嘉靖三年(1524)四月,霍兀涯、席元山、黄宗贤、黄宗明先后皆以大礼问,竟不答[4]1062。针对这一现象,余英时认为,儒学在宋明之际发生了转向,宋儒倾向于“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而因为明朝政治环境的苛刻,君主专制主义的加强,明儒更倾向于“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而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实开其端绪[7]。
余英时先生的分析不无道理,自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上疏救言官而遭宦官刘瑾之祸后,确实鲜有论政之举,《谏迎佛疏》拟而不上即是明证。但是若仅仅从政治环境来看王阳明的“觉民行道”,则会忽视王阳明心学的真见地。实际上,早在贬谪龙场前一年,即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有鉴于当时学者溺于词章记诵而不复知有身心之学,王阳明即批评这一风气,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至此王阳明即专志授徒讲学[4]1005。王阳明认为,祸乱之源乃是人心的陷溺,《寄邹谦之三》曰:“后世人心陷溺,祸乱相寻,皆由此学不明”[8]172。故而天下大治之道即是讲明良知之学。在与聂豹的书信中,王阳明坦言:“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知其量者。”[4]1070书院讲学乃是王阳明觉民行道,治世救民最主要的途径。在同一封书信中,王阳明进而曰:“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跻于大同……岂不快哉!”[4]1071
自龙场悟道直至王阳明去世的二十年间,王阳明外任加起来只有六年左右时间,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从事讲学事业。从《王阳明年谱》中随处可见书院讲学的盛况,如在贵州期间(1508—1510)主讲龙岗、贵阳书院;正德六年(1511)“职事之暇,始遂讲聚”;正德七年(1512)与徐爱论学,“闻之踊跃痛快,如狂如醒者数日,胸中混沌复开”;正德八年(1513)在滁,“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正德十三年(1518)在赣,七月“先生出入贼垒,未暇宁居……至是回军休士,始得专意于朋友,日与发明《大学》之旨,指示入道之方”;九月,修濂溪书院;正德十五年(1519)正月,“游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题识”;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集门人于白鹿洞;嘉靖三年(1524)八月,宴门人于天泉桥;嘉靖四年(1525)正月,作《亲民堂记》《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万松书院记》;九月,“定会于龙泉寺之中天阁,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为期”;十月,立阳明书院于越城;嘉靖五年(1526)三月,门人邹守益筑复古书院,先生复书赞之;嘉靖六年(1527)九月,在越天泉证道;十月,在南昌“谒文庙,讲《大学》于明伦堂,诸生屏拥,多不得闻”;至吉安,“诸生彭簪、王钊、刘阳、欧阳瑜等偕旧游三百余,迎入螺川驿中”;十一月,至肇庆,“方入冗场,绍兴书院及余姚各会同志诸贤,不能一一列名字”;嘉靖七年(1528)六月,兴南宁学校,“日与各学顺生朝夕开讲”,穷乡僻邑,不能身至其地,委任陈逅主教灵山诸县,季本主教敷文书院。
王阳明专注于书院讲学事业,这与其“理学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习日偷,风教不振”的认知是分不开的,因而他一生之中最重要的工作即在如何昌明理学、救助人心,以图改善风俗上,外任六年的为政经历只是坐而言道的实践。严格说来,王阳明觉民行道之路主要在讲学实践,为政中的平乱以及乡约实践,只不过是书院讲学实践的延伸。
乡约的重新兴起要从王阳明乡约实践说起。在王阳明之前,明代已有乡约实践。正德四五年间(1509—1510),吉水因“土贼作乱”就曾举行过乡约[3]。而正德五年(1510),王阳明也结束了贵州贬谪岁月,调任吉水相邻的庐陵知县,必已经听闻了吉水的乡约实践。而王阳明迟至正德十五年(1520)才推行乡约,这说明王阳明对乡约也有一个认识反省的过程。实际上,在正德十二年(1517),王阳明在推行十家牌法时,就曾发布多次告谕,这些告谕甚至在《王阳明年谱》中被认为是立乡约[4]1030。王阳明认为社会动乱之源在于风俗不美,其中一篇告谕中提到:“风俗不美,乱所由生”[4]479。故而,告谕目的即在移风易俗,“务兴礼让之风,以成敦厚之俗”[4]482。因为是在推行十家牌法同时告谕父老子弟,因而王阳明最初是融乡约精神于保甲之中,到明德十四年宁王之乱平定后,王阳明才于十五年春正式推行乡约。
三、从书院到乡约
因为没有官方的支持,也遭到世人的非议,吕氏乡约并没有推行多久,实际的效果也就很难估算。而康王南渡以后,吕氏乡约也就不复存在,经过朱熹的增损,吕氏乡约才重新为人所知。但是,朱熹的增损乡约,只是一种整理工作,并没有付诸推行,在此之后,也难见乡约的实行。
王阳明觉民行道,首先是书院讲学。书院讲学尚不能理解为仅仅是坐而言道,在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心学体系中,良知具有实践的品格。在《传习录》中,王阳明与弟子经常讨论知行关系问题。因徐爱未体会“知行合一”之训,王阳明曰:“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又曰:“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考,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症下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来是如此。”[8]3-4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始揭致良知之教,更是发挥良知的实践品格。如在嘉靖六年(1527)与门人黄绾的书信中说:“诸君知谋才略,自是超然出于众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端端休休体段耳。须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实康济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负如此圣明之君,方能不枉出世一遭也。”[8]186挽回三代之治,是古代读书人的理想。三代即夏商周,三代以及三代以前,在过去读书人看来是最理想的社会,孔子在《礼记·大同》中即表达了对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的向往。三代的理念,甚至被余英时看成是宋代政治文化的开端,是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主导观念[9]。三代之治是否真的存在过暂且不论,就其作为一种理想而言,三代代表了“道”的全面流行,在王阳明心中亦是天下大治的典范。而要实现三代之治,首先必须明三代之教,这正是王阳明书院讲学的重点,而王阳明也自信他的良知教正是圣门正眼法藏,是千古圣贤相传一点滴骨血[4]1050。由昌明致良知教,实现社会教化的效果,正是王阳明书院讲学的用意。因致良知教,并非仅仅是坐而言道,亦通向起而行道,故而王阳明曰:“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8]184。
那么,昌明致良知教的书院讲学,是如何通向社会教化的呢?实际上,讲学事业本身即是社会教化的一环。这方面实在不容小觑,明代自阳明先生而书院大兴,无疑起到了巨大的社会教化功能[10]。王阳明不仅自己亲自组织讲学团体,扭转士风时习,而授业的弟子亦有讲学之责。如嘉靖五年(1525),王阳明比较器重的弟子欧阳德给王阳明写信,在信中讲到自己刚出守六安州,“初政倥偬,后稍次第,始得与诸生讲学”。王阳明不无批评地指出:“吾所讲学,正在政务倥偬中。岂必聚徒而后为讲学耶?”又曰:“良知不因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4]1069也就是说,处理政务正是良知教的用武之地。这也是王阳明“在事上磨”的精义。王阳明曾经感叹道:“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事故,阔略伦物之病。”[4]1061“及闻孔子之教”在此即是听闻王阳明的致良知教,若仅仅满足于摆脱世俗的羁绊,满足于“豁然脱落”的欣喜,而不能“实践以入于精微”,终不免“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不能把良知发用为经世济民的人间事业。
王阳明于正德三年(1508)在贵州龙场悟道,旋即创办龙岗书院,开始书院讲学,第二年受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聘主贵阳书院,倡导知行合一。据年谱记载,王阳明结束贬谪生活之后,正德五年(1510)升庐陵知县,“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稽国初旧制,慎选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劝喻”,“立保甲以弭盗,清驿递以延宾旅”[4]1008。在知县任上共七月,当年十一月调离地方,入京觐见,即与湛若水和黄绾订与终日共学,直至正德十二年(1517)巡抚南赣,期间皆是与诸生讲学之事,惟有正德十一年(1516)八月拟《谏迎佛疏》论政,却拟而不上中止。由此可见,王阳明所关切的,并不在朝堂之上,而是在书院讲学。巡抚南赣后,行十家牌法、立社学、举乡约,只不过是庐陵为政的翻版,而南赣乡约中设置告谕牌、读告谕之制,吸纳朱元璋圣谕六条,也是“稽国初旧制”。在赣五年,平定漳寇和宁王之乱后,正德十六年(1521)六月归省,直至嘉靖六年(1527)再次受到启用征讨思田,王阳明皆是闲居在家讲学。在广西平乱期间,王阳明又是延续在赣的为政经验,嘉靖七年(1528)靖乱不久,王阳明于返回途中逝世。
毫无疑问,乡约实践是王阳明起而行道的一部分事业,但是要理解乡约实践对于王阳明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走进王阳明整个心学体系,才能对他的乡治思想有个恰当的理解。
本文主要讨论了在硬势和非角截断条件下矩的估计,可以得到与文献 [1] 中类似的结果,即任意矩具有瞬间获得性.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对碰撞核中的函数b(cosθ)作截断,然后分别估计, 通过泰勒展开来消去带有奇异性的部分.
1. 钢琴演奏中的心理因素(Psychological Factors)。人的大多行为都会受到心理活动的影响,心理活动即心理意识,它通过技巧把音乐的各要素如节奏、旋律、和声等融合为音响,其音响的振动、泛音等充分体现出演奏者的心理感觉、听觉、直觉和意志。演奏中会产生一系列心理活动,包括欲望、动机、情感、记忆、想象、应变心理、临场状态等心理因素,随之可能会产生各种演奏心理问题。例如,心理学研究常发现一种“特殊社交恐惧症”,表现在与人的一般交往并无异常,但演奏时就感到恐惧而出现脸红、口干、结巴、颤抖、演奏“抛锚”等现象,实为心理因素作祟,往往因过于紧张、焦虑导致压力丛生,然心理作用是也。
书院与乡约呈体用、本末的关系,还可以从思田兴学校一事得到佐证。嘉靖七年(1527)二月思恩之乱平定,王阳明认为“田州新服,用夏变夷,宜有学校”,但因内乱,生员不足,难以建学,可移风易俗,又不可缓,故四月案行广西提学道,尽可能地吸纳生员,委任教官一名暂领学事,“相与讲肄游息”,先奠定一个基础,休养生息一二年后再建学校。这个基础性的工作包括“或兴起孝弟,或倡行乡约,随事开引”。随后,揭阳县主簿季本呈为乡约事,王阳明盛赞季本“爱人之诚心,亲民之实学”,并勉励其他官员“使为有司者,皆能以是实心修举,下民焉能不被其泽,风俗焉有不归于厚者乎!”[5]533说明乡约已经在思、田推行,且可起到移风易俗之效果。只是季本在军门听用,阳明遂委任县丞曹森管理乡约一事,而季本本人则在两个月后即被委任为教官,赴南宁府主教敷文书院。由此可见,乡约是在书院讲学精神引导之下。
乡约是良知发用为治民中的一事,目的在于移风易俗,虽然具有官方的色彩,但因在讲学精神主导下,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官办性质。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与宋儒借君行道的上行路线不同,在专制压力严峻的明朝,儒生转而采取“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儒学从政治取向转为社会取向,王阳明可以说是创造者。”[11]因为严峻的政治环境,以及曾经因论政而下狱贬谪的经验,王阳明只是在现有的政治条件下尽可能地觉民行道。乡约实践中引入了圣谕的内容,更应该被看作是寻找护符的行为。虽然王阳明在地方的乡约实践,后来受到朝廷的注意并推广全国,乡约逐渐成为专制王权统治乡村钳制人民的工具,这岂能是先贤的初心。梁漱溟亦有见于此,认为王阳明的乡约实践虽是得力于他手中的行政权力,但是并不能算是政府的成功,而是靠“他本身是能代表乡约的精神”,“能发挥乡约的精神的人,以其讲学家的人格,与其所培养出来的学风,领导着他的学生去提倡实行,才能有点成功”[1]334。王阳明对于南赣乡约,自然本着讲学家的人格来实践的,其弟子的乡约实践亦是如此。邹守益的乡约附在书院之后,即是明证。王阳明后学,泰州学派的罗汝芳,出守宁国府,“以讲会乡约为治”[12],亦是王阳明讲学领导乡约精神的延续。
四、结论与启示
王阳明的乡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乡约实践中。他既继承了吕氏乡约的精神,也糅合进了圣谕的内容,因为是以行政权力为依托,因而其乡约实践具有明显的官方色彩。王阳明的乡约实践原本是地方性的,因为得到朝廷的注意而被推向全国,对之后的乡治格局发生了深远影响。在乡约发展史上,王阳明在客观上成为过渡性的人物。乡约由民间走向官方,由地方走向全国。在后来的发展中,乡约竟逐渐成为皇权宰制乡村的工具,正如杨开道所言:“老实讲起来,乡民组织的乡约,已经变成了民众教育的宣讲,人民自动的规劝,变成政府钦定的规劝了”[2]202。
定义学生的预期学习产出是OBE教育模式的关键环节。为了得到更合理、更适切的产出成果,我们把专业认证和行业能力需求两个方面作为主要参考而确定产出目标。[1]
但是,王阳明的乡约实践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官办性质。与宋儒的政治取向不同,王阳明更倾向于社会取向,虽然同样热衷于三代之治的儒者理想,他主要不是通过“得君行道”,而是“觉民行道”,书院讲学成为最主要的行道载体。王阳明希望通过书院讲学的方式,昌明致良知教,启发人人具有的良知,进而影响到家国天下,起到移风易俗这一觉民行道的效果。从王阳明整个心学体系来看,乡约是良知发用为治民中的一事,其目的在于移风易俗,并受到书院讲学精神的引导。实际上,王阳明更看重书院讲学事业,而乡约只是他有机会外任时,才推行的治民方略。王阳明为何在闲居期间并没有像吕和叔那样推行乡约,在此也可以得到解释,因“思不出其位”故。故而,书院讲学是体,是本,而乡约实践是用,是末。若无书院讲学,则理学不明;理学不明,则乡约亦不能成功。故而,王阳明是以讲学家的人格来进行乡约实践。
王阳明的乡约只是地方性的实践,是良知发用的治民方略。乡约是书院讲学的延伸,书院讲学的重点在于昌明理学,在王阳明这里则是致良知教,启发人人共有的良知而移风易俗。在与刘元道的信中,王阳明指出,养心之学,如良医治病,初无一定之方,而以去病为主[8]162。年谱嘉靖三年(1524)正月条亦有记载:“辟稽山书院……盖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先生临之,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至于至善,功夫有得,则因方设教。”[4]1060书院讲学,无一定之方;乡约实践,亦因方设教。乡约后来转变为全国性的,强制执行的官方组织,则是始料未及,恐怕亦非王阳明本意。但是,王阳明虽然能够以讲学家的人格来从事乡约,但是不能保证其他人亦能如此,而通过官方形式推行,终究是“治民”,而未能扩充“民治”的基础。从这个角度而言,王氏乡约与吕氏乡约相比较,不得不说是一种倒退。无怪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虽是采用乡约而改造之,却一定要绕过明清乡约,而要回溯到吕和叔那里了。
乡约是治民中事,而治民又不止乡约一事,凡保甲、社学、社仓等皆在治民之列。正如杨开道所指出的:“阳明有保甲,有乡约,有社学,然而他也没有看到乡治的整个性。”这要到陆世仪的《治乡三约》才有更完整的统一,他把乡约与保甲、社学、社仓三者看成是有虚有实有纲有目的系统,但可惜陆氏空有理论,并未见推行。
3.2 钢纤维再生混凝土的轴心抗拉强度和劈裂抗拉强度,均随着钢纤维体积分数的增大而提高。钢纤维对再生混凝土的轴心抗拉强度和劈裂抗拉强度的增强效果显著。当钢纤维的体积分数从0%增加至1%时,轴心抗拉强度和劈裂抗拉强度分别增长22%和70.8%。
根据上述分析和调查结果认为,水位的突然下降是由于井管老化微破裂造成的,破裂处裂隙逐渐增大,直到2017年6月29日突然变大,造成观测井中的大量水突然外泄。后来,水位逐渐恢复是由于井中水位与含水层中的地下水位逐渐持平,水力梯度开始变小,破裂处被水中杂质沉淀堵塞,裂隙变小,水的泄流量微乎其微。天津双桥井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车用太,1998;车用太,2004)。
王阳明的乡治思想和乡约实践既有长处,也有不足,但总体而言对当前的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第一,乡村振兴需要进行愿力建设。王阳明的乡约是书院讲学的延伸,是良知的自然发用,乡村振兴的各主体亦必须志愿真诚,尤其是乡民自身必须要以主人翁的姿态在建设乡村中发挥主动性,不能落入被动、机械或强制。第二,乡村振兴需要重视移风易俗。若风俗败坏,即便经济振兴也将失去意义。第三,乡村振兴是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各组织的配合协调,做好顶层设计。总而言之,当前或可以复兴乡约精神,以助于完善乡村治理,扩大民治基础,加快乡村振兴的步伐。
参考文献:
[1]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3] 董建辉:《明清乡约: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页。
[4]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5]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6] 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7] 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75—211页。
[8]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9]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94页。
[10] 崔树芝、林坚:《中国传统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文化学刊》2014年第6期,第155页。
[11]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36页。
[12] 黄宗羲:《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760页。
作者简介: 崔树芝,1989年生,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哲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4937( 2019) 05-0031-07
[责任编辑:张圆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