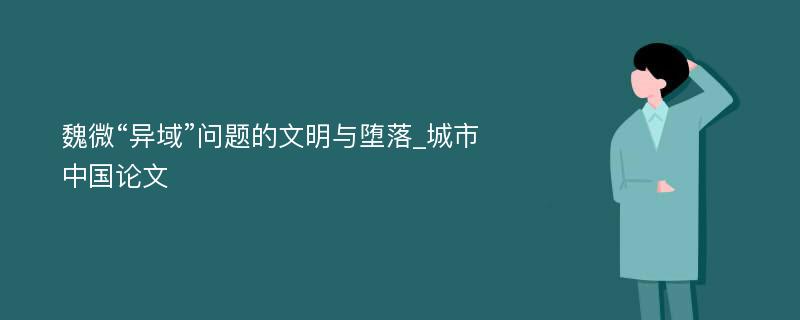
文明与堕落——关于魏微《异乡》所引发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乡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全球化正在进一步深化。同时,中国的发展正在造就这样一个事实:世界的全球化竭力勾引着中国的现代化,换句话说,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的全球化如影随形,已经趋向同步;而中国的小城镇发展战略使中国迅速城市化、都市化,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加快。中国的现代化似乎就是城市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崇尚工业文明、都市文明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更由于都市文明的诱惑,大批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争取新的生活资源和生活之路,随之产生了一个城市新群体——农民工群体。这只是城市化过程的一个初期结果。进入九十年代,一个深刻的变化是,在城市涌动的人口不再仅仅是农民工,许许多多知识群体的淘金者涌入都市,且农村的向小城镇蹭,小城镇的向城市涌,中小城市的向大城市涌,形成了全中国的人才大串联,随之产生的是一个城市白领打工族。其实,中国的这种城市化背景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是何等的相似。由于西方工业化的发展远远早于第三世界国家,早期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工大量涌入西方工业国家淘金,而后来则是大批的知识阶层涌入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谋求新的生活图景。于是,我们似乎可以认为,都市文明的本质就是让你背井离乡,跟随着都市的魂魄漂移。
但是,那些进入城市的人们的境况如何,都市文明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的身体、心理、灵魂等经历了怎样的折磨?魏微的《异乡》(《人民文学》,2004年第10期)中的许子慧是这样走过来的:“来这大城市三年,子慧换了十多家单位:图片复印社,广告公司,私人书店,GRE速成报名点……都是小街上的小店铺,三两间门面,里面可以搭火做饭,也有折叠床。子慧有时候就住在公司里。”“三年了,她居无定所,从东城搬到西城,她有一个大皮箱子,里面塞着床单和四季衣衫,这是她全部的家什。她漂在这城市,必须节衣缩食。冬天住平房里,得自己生炉子取暖,隔三五天到公共浴室洗澡。有一年冬天,气温降到零下二十来度,小火炉烧到半夜突然灭了,几个姑娘抖抖索索地挤到一张床上,外面是浩浩的风,天色有点惨白,在下雪么?是天亮了么?”
既然进入大城市,就要学会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就要适应都市文明的要求。“她一连报了好几个班,英语班,会计班,法律自考班……都是得用的专业。子慧对她的前途有隐隐的期待,她虽是中师毕业,可是并不自卑,她计划用两三年时间修个大专,再修本科,她一定会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两三年时间,谁说得准呢?或许她就碰上了一个青年,恋爱了,结婚了,有了房子和车。或许就出国了,升天了。谁说得准呢?”的确,大都市充满繁华,有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物流中心,有商场酒店,有豪宅别墅;有花天酒地,有歌舞声色。更重要的是,它似乎到处充满了机遇,能够把一个人的人生陡然放大,使贫穷的人一夜暴富,钞票滚滚而来;使默默无闻的人一下子名扬天下,大红大紫。这才是真正的诱惑。
不过,这种机遇好像并不怎么轻易垂青于某个人,有时候对某些人还十分吝啬甚至残酷苛刻,让你在城市的边缘上几乎坠落。毕竟,繁华的大都市犹如庞大的机器时时刻刻在高速运转,谁都想搭载进入它的轨道,但是稍不留意就可能被它轧得粉碎。就如子慧,虽然在这个大都市已经苟乞了三年,而且不断地学习在大城市生活的手段,不断地适应大都市的生活方式,但是,三年中换了十多家单位,仍然居无定所,从东城搬到西城,在城市的边缘折腾。为了能在这大城市生存下来,她们甚至想到了最原始、最便捷的方法,“像小黄和子慧这样的外地姑娘,能留在这城市的唯一途径恐怕还是嫁人。换句话说,她们和城市的关系,其实也就是她们和男人的关系”。小黄对这一点认识得更清楚些,“从来到这个城市的第一天起,她就和男人摽上了。小黄对待男人的态度简洁明快,第一,她不和他们谈情说爱,因为恋爱的结果就是分手;第二,不到万不得已,她不和他们发生肉体纠葛。”“可是小黄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走马灯一样去相亲,也有人看不上她的,也有她看不上人的。”子慧也有过一次恋爱经历,“然而她要的又不是这个男子,而是一桩婚姻,怎样才能使他明白,她需要一桩婚姻,就像需要空气和水!”为此,子慧放弃了自己的防线,和男人上了床。但上完床以后并没有带来她期望的结果。城市没有接受她们,城市的男人同样没有接受她们。
当然,在当下利欲升值和道德贬值的语境中,一些逾越普世规范的谋生手段依然潜存着。虽然大都市也享有光荣与梦想,但在都市的角落有可能潜存着污垢和罪恶。尤其是女人,在男人世界存在猎性需求的情况下,身体资源的开发常常成为一些女人谋求荣华和享乐的手段。这并不是什么秘密,甚至也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话题。子慧也清楚,“如今这世道,上床本不是什么大事”,而且这种生意对于年轻漂亮的女人来说非常容易。但是,在子慧看来,她毕竟还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女人,她有自己的自尊心,有自己的基本原则和防线。她相信,自己谋生的本事还不至于仅仅剩下女人这点东西,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够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最终,她凭借着自己三年的拼搏、磨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当上了“一家颇像样”的华美贸易行的会计师,成了切切实实的都市白领。
应该说,许子慧削尖脑袋、挤破头皮挣得了一份“体面工作”,使她有资格、有条件、有理由在这个城市安家落脚,在都市白领队伍中继续发达,永远穿梭于高级公寓、高耸的商住楼、星巴克、世都、银座……可是问题在于,一旦她有资格有能力进入这个城市的核心地带,却从灵魂深处本能地产生对这个城市的排斥性反应。“子慧第一次置身于这等富丽的环境,……不知为什么,她突然想回家,回她的吉安小城去,那儿有青山绿水,民风淳朴。那儿,才是她应该呆的地方。”子慧为什么想回去?说到底,子慧是小城镇甚或乡村文明的产物,她并没有完全认识城市文明,真正要让她融入都市文明,她便会从内心感到不由自主。如果说她还能够挣扎三年的话,那是因为在这三年的颠簸奋斗中或多或少能够呈现她的某些原生状态,而一旦命运改变,不能展示自己的原生状态时,她只有重新回复到原来的环境中去。
实际上,她与这个城市、与都市文明的不协调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都让子慧有切身的感受。首先,她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大都市,“她隐隐地想到,这些年来,她离开故土,流落异乡,其实并没有什么实在的理由,或许仅仅是为了离开”。“这二十年来,正是大量中国人热衷离乡的年代。他们拖家带口,吆三喝四,从故土奔赴异乡,从异乡奔赴另一个异乡。他们怀着理想、热情,无数张脸被烧得通红扭曲,变了人形。他们是农民,工人,国家公务员,小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老人,孩子……中国整个疯了,每个人都在做着白日梦。”不经意间即已随波逐流。或许是因为心中的骚动,因为对大都市的向往,因为生活落差的潜驱使。其次,她并没有真正认识这个大城市和都市文明。在她以往的认知中,大都市无疑是繁华、喧闹、膨胀、浪漫、激情的世界,但真正进入这个世界的疆域,繁华、浪漫的气息并不追随缠绕每个人。对于许子慧而言,感受最深最多的是孤寂、冷落、穷困。她以为大城市可以使人富足,地位提升,增加尊严和体面,而实际上,“她不过是一天天地呆着,茫然,贫贱,服从。大城市的穷困其实比小城更加不堪……”其三,大都市并不乐意接受她。子慧在这个大都市流浪、漂泊了三年,虽然她孜孜以求地学习在大都市谋生的手段,但并没有很快地结束在这个城市漂泊的生涯,以至于当大都市的人们合家团圆共度新春佳节时,她仍然蜷缩在都市的一隅;她不甘于这样凄凉和寒碜,“便强打精神去天坛逛庙会,那天太阳黄黄的,天照样的冷,她走在人群里,到处都是陌生人……她怏怏地走了一会儿,就出来了。”子慧恍恍惚惚走进一条胡同的一户人家门前,“一个年轻媳妇从院子里走出来,警惕地看了她一眼”,“还不待人转身关门,子慧突然发足狂奔……她简直疯了,她羞愤之极。”不仅如此,当她有了自己满意的工作,与小黄一起相看租房时,李奶奶对她和小黄进行了反复的盘查和审问,末了“嘴里兀自唠叨着:‘不是信不过你们这些外地人,外面世道这么乱,我年岁又大,怎能不多长个心眼儿?’”“小黄关上门,朝外呸一口说:‘老太婆以为我们是干那个的。’”其四,父母对都市文明的排斥和忧思不断地动摇着她安居都市的信心。自从她离开小城的那天起,父母无时不存在着忐忑不安的担心。在他们看来,大都市并不一定是光明堂皇的地方,世道上的传闻让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大都市生存随时都有变坏的可能,即使像他们的女儿这样纯净的姑娘,他们也有百分之一百二的不放心。“有一天晚上,她和母亲通电话,屋外突然传来摔酒瓶的声音,继而是一个男人哩哩啦啦的哭泣声。母亲警惕地问:‘谁在哭?’”“子慧不介意地说:‘隔壁的民工喝多了。’”“母亲一声尖叫:‘你和农民工住在一起?’”“母亲唤了一声子慧,突然哭了:‘你在那儿干什么?……你好歹也是教师……咱们是体面人家。’”显然,母亲非常痛心地认为自己的女儿已经被大城市的污浊所玷污,在都市文明中堕落。因此,隔三差五会打来电话突击检查。一次,子慧的旧同事来看她,母亲来电话,子慧正在说笑,“母亲狐疑地问:‘你身边有人?’”子慧给她撒了个谎说没有,“母亲突然厉声地说:‘许子慧,你在骗我。那个人走了,他是个男人。……妈一辈子清清白白,可不希望你出什么差错。’”“这世上每个人都有理由怀疑她,质问她。因为她身在异乡,她穷,她还有身体。……母亲的话已经很明显了,那意思简直呼之欲出了。子慧一阵羞愧。”其五,故乡情结已经成为子慧永远改变不了的生理印记和精神印记。许子慧虽然也是现代社会年轻一代的人,但她生于吉安小城,长于吉安小城,小城的山水风情、世道民风与生耳濡目染,渐渐浸化,已经深深镌刻在她的骨髓之中,成为她生命的重要特征。在她的记忆中,吉安是这么一个地方:
青石板小路,蜿蜒的石阶,老房子是青砖灰瓦的样式,尖尖的屋顶,白粉墙……一切都是静静的,有水墨画一般的意境。庭院里有樟树,槐树,榕树,推开后窗,就是清澈见底的小河,河水可以饮用,漂洗,夜里能听到流水的声音。……吉安是一座老城,迄今还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人们安静地生活着,家家户户,年年如此。
……这么说吧,吉安是个小城,它时而穷,时而富;它躁动不安,充满时代的活力,同时又宁静致远,带有世外桃源的风雅。它山清水秀,偶尔也穷山恶水,它民风淳朴,可是多乡野刁民。她喜欢她的家乡,同时又讨厌她的家乡。有一件事子慧不得不正视了,那就是这些年来,故乡一直在她心里,虽然远隔千里,可是某种程度上,她从未离开它半步。
她就像一只风筝,尽管在飘,但永远摆脱不了故乡的牵引。实质上,故乡是她的消尘器,她的激动、焦躁、痛苦、烦恼甚至羞愧、愤怒,一经故乡山水风情的消解,统统归于平静、乌有。
我们解读《异乡》文本最重要的感受是,作品所揭示的问题。
在我看来,作品最本质的问题是“异”字。子慧被都市遗弃至为关键的问题不在子慧本身,而是都市的问题。回到本文开始的思维路径,伴随着全球化、现代化进程,大都市不再是人们理想的、更不可能是诗意地栖居的,城市的功能在发生变化,城市的一切出现变异。首先,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历史性推进,大都市迅速市场化并成为巨型的超级市场,物流、信息流、货币流、人流、声浪流以及竞争、倾轧、牛市、熊市、暴发、破产等等结成大都市最敏感的神经链条,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不仅在物流领域发挥作用,而且在城市的其他领域充分发挥着作用,大都市的方方面面包括都市的人们都被安置在市场的链条之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奈市场化,那么,倘若要进入大都市就必须与之建立市场化关系。其次,都市各阶层发生重大分化。在市场化的大都市,经济成分的多样化体现得最为充分。与经济成分多样化相伴而生的是分配形式的多元化。我们完全相信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都市新贵阶层和贫困群体不能不说是多种经济成分和多元化的分配方式催生的。都市各阶层的分化组合意味着对人们身份地位的重新确定和认定,其实质上是对都市旧有秩序的颠覆和重构,自然这种颠覆和重构也会殃及人们的精神秩序。因之,都市精神秩序的某种紊乱或裂变即是可以理解的。再次,大都市的纯净度不再依旧。中国城市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也曾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对城市进行了彻底的整治,铲除了滋生污垢的土壤,建立了新的秩序,单位是国家的单位,人是单位的人,人们的身份固定化,成分单纯。八十年代后,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人与单位的依附关系渐趋松动,城市对人的控制失去了既往的力度,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腹地大大膨胀。同时,大都市与国际的接轨也使都市迅速复杂化。第四,大都市的运转节奏进一步加快,分贝加大,喧闹嘈杂,烘箱效能突出显现。
这种变异的城市结构、城市程序、城市生活却恰恰是现代人经常挂在嘴角、津津乐道的都市文明或现代文明。这就难免引发人们的质疑。中国大都市的现状究竟是否体现了现代文明的本质或者方向,这是身处其中的许多人试图探究明白的问题。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思索这一问题的关键不应该是城市自身如何,而应该是城市的功能对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据调查,城市居民中患有精神抑郁症、焦躁症、疲劳紧张综合症的是一个不小的比例;而另一项调查则指出,现代都市一族中感到压力最大的是三十至四十岁的人们。这更能说明问题。如果说都市的人们基本上是都市文明的产物的话,那么青年人百分之百是都市文明的产物,因为青年人中要么是城市原生的,要么是完全奔着都市文明涌进城市的,倘若他们认为都市赋予的生活难以承受的话,说明都市对他们的压迫即将超过限度。更重要的是它对人的生活的改变,对人的身份、地位、境况的巨大改变。你可以一夜暴富,就如许子慧梦想的,说不定有了房,有了车,出国了,升天了;也可能转眼赤贫,陷入跳楼的境地。而城市结构的调整便能使城市人群迅速产生分化,有人可能升迁优裕,有人可能沦落贫困群体。在生活的重大变故中,人们不能不面对现实,面对挑战。当然,应对有积极的应对,也可能有消极的应对,但都是为了找回被生活击碎的梦。积极应对成人,消极应对成鬼。在人与鬼之间有时的确存在着不确定因素,这就让人们对都市文明的道德属性难以界定,从而为人们质疑都市文明有了切实的理由。
于是,我们就不能认为子慧母亲的惴惴不安和李奶奶的盘查多余。况且,都市的影子已经迅速斜射到小城、乡村,比如吉安的商业街和大都市一样也是灯红酒绿,“街两旁全是摩肩接踵的店铺:洗头房,洗足房,桑拿房,练歌厅,也有星级酒店,百货公司。总之,走进这条街,人体的各个部位都可得到抚摸满足。一到晚上,街两旁就站满了形态各异的小姐——”是文明还是堕落?这真的不仅仅是子慧母亲和李奶奶的狐疑。实际上,有多少漂移到城市的儿女就有多少牵肠挂肚、惴惴不安的父母和家人,尤其是女孩子,世面上关于女孩子的故事太多,而都市的各种诱惑又是那么难以琢磨。计划经济时代,进入城市的人们等于拿到了铁饭碗,走上了正道,现时进入城市的人们完全要凭着自己的“十八般武艺”拼打,或许挣了票子,有了原始积累,立着了脚,但票子是不是干净,手段是不是光明,却常常成为质疑的焦点。而对于女孩子来说,这种质疑似乎更合情合理,因为说到女孩子在都市的作为,人们很容易想到歌舞厅、美容院、桑拿房以及身体、卖淫等字眼,自然,手中的票子就说不上干净。以农业文明的传统价值观审视,人的行为及其结果的道德属性比票子更重要,以至于要脸面不要票子是人们的基本选择。所以,当子慧的父母看到她回到家里的行囊派头后,对她的怀疑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加重了。在子慧父母看来,子慧如果寒酸地回到家里,他们心里则踏实;子慧揣着票子像模像样地回来,他们便觉得有问题。父母对子慧进行了全面的审讯,他们让子慧讲三年的经历,翻开子慧的皮箱,胸罩、内裤、睡裙等衣物一样样详细查看,他们从中看到子慧生活得很不错,有很多妖艳的衣服,这些全是堕落的疑点和证据。他们不允许子慧辩解,指责子慧尽管回到家里扮作良家妇女,心里仍然疑惑她是个妓女。子慧在父母的反复责问下,自己也失去了自信,仿佛自己真的做过妓女。
作品文本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如果是都市文明,那么都市文明中却包含着一种堕落。而文明与堕落在作品的文本中却是那样难以界定,以至于让许子慧十分迷茫。《异乡》是新世纪的问题小说。小说虽然篇幅短小,却揭示了当下社会的重大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确乎解放了生产力,拉动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否就如市场是把双刃剑一样,社会的文明进步一定要伴随着不文明的问题存在?换句话说,马克思指出的“异化”概念在我们的现代是否同样显现?这当然不是小说本身能够回答的问题。重要的是,小说表达了这一问题,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作品的意义正在于此。
标签:城市中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