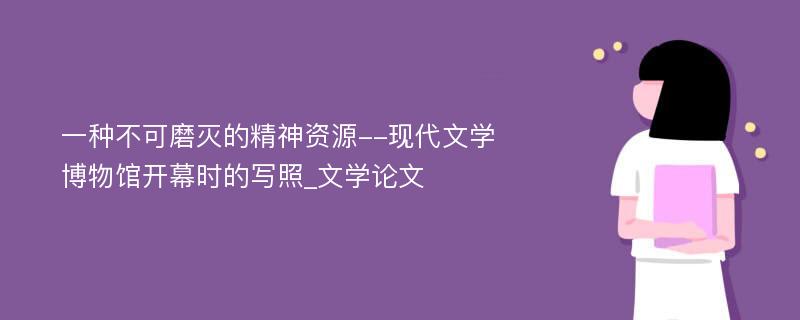
一个无法断裂的精神资源——写在现代文学馆开馆之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馆论文,写在论文,精神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文学馆正式开放后,社会各界对其渐渐发生了兴趣。我们终于有了一个群体作家的博物馆了。记得七十年代巴金倡导建立现代文学馆时,社会对此反应平平,原因是对中国新文学史,还缺乏一种“史”的认识。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不知道三四十年代文学的真相,不知道左翼文学与边缘化写作的历史过程。除了文学史专家外,我们的大众,知道昨日历史的机会,十分有限。
当一些血性的青年,高喊文学要“断裂”,要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致悼词”的时候,我疑心他们并未真正阅读或并未读懂现代文学的经典。那种虚无的态度,要么是为了争夺公共话语的时空的行为艺术,要么便是对历史的无知。在中国,漠视五四新文化传统,其实便割断了一种精神资源,而这个资源,在我们的现存文化中,是不可或缺的。
在鲁迅的背影下的写作者
许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当代文学与鲁迅传统》,谈及了当代文学中隐含的鲁迅传统。那时候限于阅力,许多作家的写作被忽略了。近来翻看几年来的报刊杂志,鲁迅名字出现的频率很高。甚至一些热点话题,也是由鲁迅引起来的。王蒙、林斤澜、邵燕祥那一代人不用说了,在刘恒、余华等人的创作里,也多少可以找到鲁迅的影子。赵园散文中的冷隽,我以为是流着鲁夫子的血液的,筱敏的文章中深切的思考,亦闪现着《热风》的某些思绪。王富仁在自己的随笔里,干脆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其中对文化难题的反诘,很得《随感录》里的要义。邓晓芒在《人之境》里表现的智慧,王乾坤《一路洋葱皮》中的玄想,一些重要的思路,是从先生那里转化出来的。余华在一篇文章说,自己一辈子也赶不上鲁迅。但他们那代人,有时又不得不重复着鲁迅的某些意象。有人在许三观的身上,就看出了阿Q的痕迹,说那是一种精神的延续, 想起来,也是有道理的吧。
在读《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时,我不禁想起了《阿Q正传》,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对国民性打量的时候,很难绕过五四情结。张大民的悲欣交集的形象,是市民生活的写真,其间何尝没有农民的影子?刘恒在慢条斯理的反讽里,将阿Q的血脉延续下来了, 虽然其中已有了许多的不同。
在另一类更年轻的作家如王开玲、朱铁志等人那里,我们照样可以看到类似的东西,甚至在学界,鲁迅治学方式对人们的潜在影响,也是深厚的。阅读近年几部走红的学术著作,如汪晖的《死火重温》,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其中不乏忧患透彻的反省,那阔大的哲思的喷涌,倘不是曾浸淫在鲁迅的传统中,是难能出现的。如果有人留意一下鲁迅对中国学人的精神暗示,当可从中品味出一点什么。
鲁迅在人格、艺术境界、人生哲学诸方面,是个说不完的话题。不同人的眼里,有不同的鲁迅。孙犁之走进鲁迅,与张承志不同,和林贤治等亦多有区别。不管人们以什么态度注视着他,他的内心深处迸发出的光芒,是无穷尽的。
京派与海派: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景观
文学的发生,非天上掉来之物,而是现实的折射。以京派海派为例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三十年代,上海有海派的文学,北京出现了京派的散文、小说,且风格各异。进入九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京派文学忽然升温,朱光潜、废名、知堂、林徽因等,有了许多继承者。而海派中的新感觉派文学,也在时隔半个余世纪后重新出现。尤其是海派的文学批评,和京派学人的重历史、谈掌故截然相反,它们以性灵的,诗化的表达式,述说着当下的文学话题。我在王晓明、张闳、徐麟等人身上,看到了海派批评的锐气,他们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虽有自身的缺陷,但话题的本身,是很有意义的。这让人想起二十年代末上海先锋派对全国文化的刺激。我们从这些人的精神深处,是可以看到某种历史的痕迹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京派散文在当代的复兴。知堂、废名、李建吾曾是北平时期很重要的散文作家。五十年代后,这些超于功利,沉于纯粹审美静观的艺术,中断了多年。八十年代,随着张中行、谷林、止庵等人的出现,“苦雨斋”式的散文,有了很大的市场。张中行谈老北大,以及记人忆旧之作,有知堂遗风;止庵的随笔老到平和,兼得苦雨翁和废名的神力。我们在上海的作家黄裳、邓云乡那里,也可以看到京派散文的流变。二人的审美偏爱是从《药堂语录》、《书房一角》那里来的。我们如果看不到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这种辐射,就无法理清当代文学的源头。当代人所以从现代作家那里寻找资源,一是生活状态使然,另一方面,是现代文学丰富的流向决定的。我们被“前定”在“现代性”的话语里,而这个话语,在我们的前辈那里,多少都涉及到了。
“新青年”并不“新”
八十年代后,文学流派渐多,风格趋于多元。而冠以“新”字的流派此起彼伏。“新写实”、“新体验”、“新青年”、“新文人”、“新新人类”,好似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已经到来。但我们认真看看“新”派的创作,则并无天外来客之感。作家们或模仿洋人,或走五四后一些文人的道路,或将东西文学有趣的东西嫁接起来。号称要与中国文学断裂的青年伙伴,自以为是横空出世的新族,仿佛天下惟我老大一般,岂不知道,这种骂倒一切的游戏,早在1928年,就被创造社的才子们玩过了。“新生代”一些作家或许在一些方面有些突破,视野里有了比前人不同的东西,但精神的深,则难及鲁迅、胡适、钱钟书等人。而在被喻为是“新青年”的作家那里,看到的则是对五四前辈的某种重复和借用。独特的精神范式,富有创见思想之火,是很少见到的。
王得后先生有一篇随笔,叫做《青年的新与旧》,他认为看一个作家,仅盯住头上的帽子是不够的。老年人也有很鲜活的思想的,自认是新青年的也可能十分守旧。因此,看一个作家的明与暗,新与旧,要阅读他的作品,看其中的实货。我以为这是应有的态度。现在的媒体,有许多时候,大炒新派的作品,以为是前无古人之作,忘掉了历史地看待问题,普遍缺乏“史家”的目光,是媒体与批评界的一个通病。
可惜当下的一些批评家,并未看到这一点。例如在很先锋的作家那里,我们是可以找到现代作家的脉息。潘军的小说在形式上多有创意,可他写《秋声赋》这类作品时,就走到了沈从文与鲁迅的某种叙述语态里。诗歌界一些探索者,在形式的陌生化里,至今难超越《野草》里的境界。我们例数一下当代一些有影响的作家,他们的身上,多少有些前人的东西,或是自觉的追随,或是无意的偶合。生在中国的、热爱中国的作家们,被相近的精神主题纠缠着,是一种必然。刘绍棠前面有一个孙犁,汪曾祺出于沈从文门下,陈建功喜欢过老舍,李辉得到了萧乾的某些智慧……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个链条一个链条的延续。简单地用“新”与“旧”看待文坛,我以为是不得要领的。
老问题与新话语
忘记是谁说的了,世界几千年,人类基本的问题就那么多,但各个时代的话语,却各有不同。这是一句有趣的话,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就是这个道理。进入九十年代,我们有过文艺的雅与俗之争,“人文精神”之争,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等等。有一些文化问题,确是过去未出现的,但一些精神的实质,在三十年代,就曾有过。鲁迅当年与胡适的矛盾,“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的冲突,比今天一些书斋里的文人的自言自语,要厉害得多。连汪晖也承认,当前学界的一些讨论,在质量上不及三四十年代的文化论战。而许多批评家的思想背景,也来自现代文学。走不出五四情结,确是当代文化的一个特征。
九十年代的学界,流行着“东方主义”、“后现代”、“现代性悖论”等术语,其中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百年的文化,如何看待知识者的社会作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人从当年的左翼文学中寻找参照,有人在“现代评论”派那里挖掘依据。学者们许多争论,都不由地回到二三十年代的话题上去。回到现代文学之中,并非文化的退步,而是20世纪中国文化母题的一种必然。翻看《当代作家评论》、《书屋》、《书与人》、《书城》等杂志,一些重要的、有分量的话题,都多少回响着现代文学的声音。“为学术而学术”也好,“关注平民”也好,“为农民写作”也好,这些讨论在蔡元培、知堂、陈独秀、瞿秋白那里,均曾出现过。尤其是关于“现代性”的争鸣,我以为是鲁迅与胡适之争在当代的流变。我们今天的作家、学人,要完全摆脱前人的影子,是困难的。
现代文学史虽然才三十年,但它的丰富性对未来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白话文的诞生,共产主义运动,左翼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都印在这三十年的履历里。不了解它的得与失,看不到它对今天的潜在影响力,大约不会懂得20世纪中国的文化。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对于想要创造新型文化的中国文人而言,了解那一段历史,是何等的重要啊!
标签:文学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作家论文; 散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