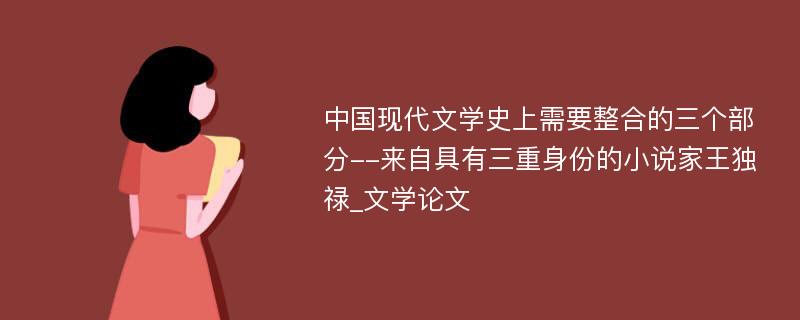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史亟待整合的三个板块——从具有三重身份的小说家王度庐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家论文,文学史论文,中国论文,板块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0)01-0098-04
一、问题的提出
从1980年代到当下,中国学术界关注文学史诸问题的热度一直持续不衰。文学史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一百多年前从西方引进的文学史概念已经沉淀为一种潜移默化的话语霸权,制约着文学史的写作模式。由于各种文学史背后都有一套相应的意识形态,它们所描绘的文学图景往往被纯化为单一的和清晰的“发展史”,而在历史中实际发生的文学,往往是多维并存和界限模糊的。仅就文学史料的发掘和整理而言,由于种种原因曾被遮蔽的重要文学现象一旦浮出水面,就会打破文学史叙述与历史想象之间原有的平衡,对以往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格局形成挑战,中国现代作家王度庐便是一个具有样板意义的个案。
王度庐1909年出生于北京一个贫寒旗人家庭,做过店铺学徒、小学教员、小报编辑,自幼爱好诗文戏曲,曾在北京大学旁听,积累了丰富的中外文学知识,十几岁开始发表杂文小品、侦探小说。1937年被困居在日本占领下的青岛,开始专事连载小说的写作。抗战胜利后,天津励力书局迁往上海,开始大量印行王度庐小说的单行本。上海育才书局、元昌印书馆、春秋书店及重庆千秋书局也出版过王度庐的作品。1949年初,王度庐举家移居东北,在中学谋得教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武侠言情类通俗小说退出阅读领域,直到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才解禁。2000年,中国台湾地区导演李安将王度庐1941年创作的武侠小说《卧虎藏龙》搬上银幕。翌年该片一举获得美国第73届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师、最佳音乐和最佳美术指导四项大奖,在新中国文坛默默无闻近半个世纪的王度庐再度引起大众传媒的关注。不过,学术界对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几乎没有他的位置。比如,从1951年至今,中国内地正式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约135部,只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1998年版)等极少数著作对其有简单的介绍,大多数著作均只字未提。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王度庐的沦陷区作家、满族作家和武侠作家等三重身份,而通过解析王度庐既有区别又有交叉的这三种身份,或许有助于重新估价中国学术传统,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研究思路,进而深化当下有关文学史的讨论,推进方兴未艾的重写文学史工程。
二、作为沦陷区作家的王度庐
沦陷区文学是一种特殊时空中的区域文学,从政治上为文艺松绑、在政治层面上作出恰当评价,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接纳这类文学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王度庐的所谓“鹤—铁系列”(《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传》和《铁骑银瓶》)等重要作品,是在日伪政权机关报《青岛新民报》上连载的。如果简单化地以作品载体的隶属关系为标准,就会对沦陷区作家作品作出负面的定性评价。只有把日本的侵华战争及其殖民统治放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语境和世界殖民史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分析其作品内在的文化认同取向,才会对沦陷区文学作出合乎历史的客观评价。
中国近现代文学是在殖民化语境中发生和展开的。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华帝国的门户,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曾经面临被殖民危险的日本在“脱亚入欧”、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之后,转而跻身殖民国家的行列,不断发动对外扩张战争。针对中国的标志性军事行动有1874年的侵台之役、1894年的甲午战争、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等。到1940年代,日本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殖民者,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中国领土被其染指。在这些地区,日本侵略者大体上建立起三种不同的殖民体制:第一种是台湾殖民地模式。即通过国家间的不平等条约霸占中国台湾地区,设立日本总督府(1895年)。到1937年9月,正式宣布将中国台湾并入日本版图。第二种是东北“满洲国”模式。即在东北占领区建立起新的“主权”国家,定都长春(改称新京),由前清逊帝溥仪担任“执政”(1932年3月1日)。两年后,将傀儡政权的政体从“共和国”改成“帝国”,首脑改称“皇帝”。第三种是关内沦陷区模式。即在关内占领区起用原中国政府的官员,陆续组建僭越中国合法政府的中国伪政权。如“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7年10月27日),定都归绥市(改称厚和特别市,现为呼和浩特);华北地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7年12月14日),定都北平(不久改称北京),后被日本降格为“华北政务委员会”(1940年3月30日);华东地区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3月28日),定都南京,后升格为试图统管关内所有日本占领区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40年3月30日),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三种殖民体制之间的关系,是所谓“国”与“国”的关系,关内几个伪政权实际上也是各自为政。各占领区的殖民当局隶属于日本的不同军兵种、派系,有各自的既得殖民利益,相互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中国被占领区的社会生态特别是文化传统有其历史的惯性,异族入侵者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颠覆。因此,日本在中国不同占领区所实施的殖民思想统治均有所不同,各地的中国区域文化面貌和特点也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特别是在关内的华北、华东等沦陷区,中国认同、中华文化认知、中华民族认同仍具有合法性,言说环境迥异于其他日本占领区。许多沦陷区作家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坚守自己的民族气节、文学信念和创作风格,发表和出版了大量具有相当水准的文学作品。但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沦陷区文学被打入另册近半个世纪。1990年代以后,《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1994年版)、《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1995年版)、《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1995年版)以及《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1999-2000年版)等著作陆续面世。这些研究成果表明,日本占领区的中国文学,无论是新文学还是通俗文学,仍顽强地沿着中国文学原来的路径迂曲地发展,蕴涵着殖民统治无法压制的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学要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尽管目前对沦陷区文学加以全盘否定的观点仍然存在[1],但是,21世纪出版的文学史著大多都增加了沦陷区的内容,而对于沦陷区文学的正面评价,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改变中国现代文学总体画面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在的问题是,沦陷区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比重太小,离均衡展现共时历史文学生态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以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而论,如果将日本占领区面积乘以沦陷时间,沦陷区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如果没有相应的篇幅作保障,很难完整地再现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文学历史全貌。从作品丰厚、影响广泛的王度庐这一个案可以见出,认真梳理、全面纳入沦陷区文学,是重写文学史无法回避的重要工作。正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专家黄修己所总结的:“沦陷时期的文学,至今仍是一个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对某些作家、作品应如何处理,有待进一步研究、分析,虽事涉政治,却不得不加以解决。这一地区文学史研究的突破,对整个新文学史编纂水平的提高,关系不小。”[2](P392)
三、作为满族作家的王度庐
中国是由汉族和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在少数民族中,人口超过百万的有壮、满、回、苗、维吾尔等十八个民族。
中国学术界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注,始于20世纪初现代中国学术的萌芽期。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实施民族扶持政策,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保护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最早发出权威声音的是德高望重的满族作家老舍。在1955年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上,老舍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强调收集、整理、翻译、研究、出版兄弟民族文学遗产的重要意义[3]。195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第一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座谈会,体现了国家在统一意识形态框架下展现和扩展少数民族文化空间的导向。1960年代初期,单一民族文学史的撰写工程启动。1963年、1979年召开的第二次、第三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改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1983年,中共中央同意将民族文学史编写任务移交给1979年成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198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这表明,服务于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民族文学史研究纳入学术范畴。目前,除撒拉族、俄罗斯族、门巴族、塔塔尔族和高山族外,多数少数民族都有了各自的族别文学史。囊括各少数民族文学或几个少数民族文学的综合性文学史,如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上、中、下)》(2002年版)等,也陆续出版了十多部。接下来的问题则是少数民族文学如何有机地融入中国文学史了。
少数民族文学史是中国文学专史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同时又是中国文学史的组成部分。撰写通史类中国文学史时,如果缺少了少数民族文学部分,很难说是一部完整和全面的中国文学史。其实,学术界早在1980年就认识到,应当改变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上都是汉族文学史的状况,要真正把现代文学史写成多民族的文学史[4]。此后,呼吁和探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问题的文章一直绵延不断,如周建江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创建并确立过程中不容忽视的若干问题》(载《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李光荣的《文学史观:〈中华多民族文学史〉建构的困境和出路——兼及当前的学术工作》(载《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等。不过,时至今日,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绝大多数的中国文学通史仍然只是对主流汉语文学的梳理。鉴于这样的文学史冠以“中国”这一限定词,大有名实不符之嫌,所以有的著作干脆明确将书名定为《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曹万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个别规模较大的文学史如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虽加入了少数民族文学,但新添加的材料未能与原来的内容有机融为一体。这说明,试图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文学史时,不但有待于各少数民族文学史自身的完善及有机地介入,还需要进一步变革和调整文学史观念。
民族文化是多元文化的基本要素。长期的民族融合,特别是现代以来的一体化世界潮流,使得少数民族文化濒危的速度加快。但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转换并没有降低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而是愈发彰显出其弥足珍贵。即使在世界经济、文化全球化步伐不断加速的背景下,整理、维护和表现少数民族文化,仍是维护文化多元共生的重要内容,仍是国家重要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形象工作。少数民族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化最为直观和最为集中的载体之一,它们各自的文学史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有其自立于民族之林的独立的文化历史价值,同时又是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少数民族文学纷繁多样,仅就语言媒介而言,作品文本分为民族语言和汉语两种形态。据统计,中国少数民族使用的口头语言有一百多种,少数民族文字五十多种,其中实际使用的文字二十多种,有不少少数民族已逐步改用汉语。但不管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阶段以及语言状况如何,各少数民族的文学都有其各自的文化传承和无法替代的民族内涵。以王度庐为例,从满洲肇始,到逐渐汉化,满族文学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涌现出纳兰性德、曹雪芹、文康等一大批民族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代表作家。因此,只有将整个少数民族文学有机地纳入文学通史,才能对诸如王度庐这样的现代满族文学大家作出恰当的文学史叙述和文学史定位。王度庐在通史类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缺席,也提醒文学史家在重写文学史时应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维度。
四、作为武侠作家的王度庐
在20世纪初,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理论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为五四文学革命作了充分的准备。在新民强国、救亡图存的强大内外驱力的作用下,以“民主与科学”、“反帝反封建”为旗帜,西方现代人文百余年的发展成果在中国横向移植的历程,被压缩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面对和走向世界的开放心态,“重新估价一切”的独立价值评判,以及尊重和张扬个性的“人的文学”,沉淀为五四文学精神,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的格局与走向,以及人的思维模式和情感方式,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文学形式方面,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在五四时期经历了一次全方位的转型。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大文学体裁在叙事、结构、韵律等方面从古代走进现代,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殊异、与西方现代化潮流同步的新的文学规范和创作法则。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是在批判旧文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不过,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梳理与继承。表现在文学上,则是认定通俗文学格调不高、商业气息浓厚、缺乏艺术性,因而对其持全盘否定的立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在指导方针和政策上的失误,放大了这一偏颇与缺失。故而新编文学史大多贬低和排斥包括章回体小说、现代旧体诗词等传统文学样式在内的所谓俗旧文学。
新时期以来的研究表明,雅文学与俗文学的范畴不是一成不变的。在20世纪,现代通俗文学以其独特的审美和教化功用参与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以王度庐为例,他的小说《卧虎藏龙传》讲述的是京城九门提督之女玉娇龙与沙漠大盗罗小虎之间的爱情悲剧。玉娇龙为维护家门,违心地嫁给丑翰林鲁君佩。罗小虎大闹婚宴,玉娇龙出走。她凭借盗来的青冥剑,横行江湖,又因盗“九华秘籍”而受制于女贼耿六娘。“侠义道”李慕白、俞秀莲等群起而攻之。玉娇龙得知母死家败后,施计遁迹。后与罗小虎有一夜温存,但终因门第悬殊,黯然离去。曲终人散之后,依旧是孤剑单骑。《卧虎藏龙传》长于人物刻画。侯门之女玉娇龙任性刁蛮、敢作敢当,却囿于封建纲纪,只能悲伤落寞地远走大漠。王度庐的爱恨情仇故事,长处不在武打,而在悲情。玉娇龙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深刻揭示了侠客“情”、“侠”不能两全的命运悲剧,产生了打动人心的震撼力,王度庐的这类作品因而有悲情武侠小说之说。此外,王度庐的语言风趣幽默,具有京味儿的特点。更为内在的因素则是,由于受过新文化运动的熏陶,王度庐在观念上认同五四新文学,在通俗小说中融入了新文学因素。可以说,王度庐的作品堪称优秀的现代文学遗产,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不过,消除对于通俗文学的偏见,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武侠小说入选中学教材所引起的激烈的争鸣与讨论就是例证①。2004年11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必修)》第四册设立了“神奇武侠”单元,节选的作品是王度庐的《卧虎藏龙》(第五课)和金庸的《天龙八部》(第六课)。反对者认为,武侠小说只是一种娱乐样式,大多宣扬善恶因果报应,不利于当代中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赞同者则肯定武侠小说蕴涵有中华文化的精粹,入选语文课本是一种必然。有关争论推动了武侠小说研究与中学教材和教学改革。
此外,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作为一个独立的专史进行研究,相对来说容易一些,目前已经出现了一批很好的研究成果,如范伯群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然而,更为难得是如何把武侠小说等通俗文学全面、客观、均衡地融入中国现代文学通史。因为后者不但有价值判断的问题,还有更为复杂的整合方式问题,亟待学术界予以重视和思考。
总之,理想的文学史是将文学故事合理有序地置于宏观的历史背景和微观的文本细读之中。与通俗文学家王度庐的名字紧密相连的沦陷区、满族、武侠小说这几个关键词,无疑会给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带来新的问题意识、研究视角和操作方式,从而有望以此改变目前对中国文学通史普遍评价不高的现状。
注释:
①参见邓琳《对武侠小说进入中学语文教材的思考》(《江西教育科研》2006年第4期)、慕毅飞《为〈天龙八部〉入选教材而忧》(《优秀作文选评(高中版)》,2005)、黄向荣《武侠小说入教材,是耶·非耶?》(《广东第二课堂》2005年第12期)、陈若水《武侠进课本,校园引争议》(《网络科技时代》2005年第5期)、夏青文《武侠作品不宜入选中学课本》(《神州》2005年第4期)等。
标签:文学论文; 王度庐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艺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