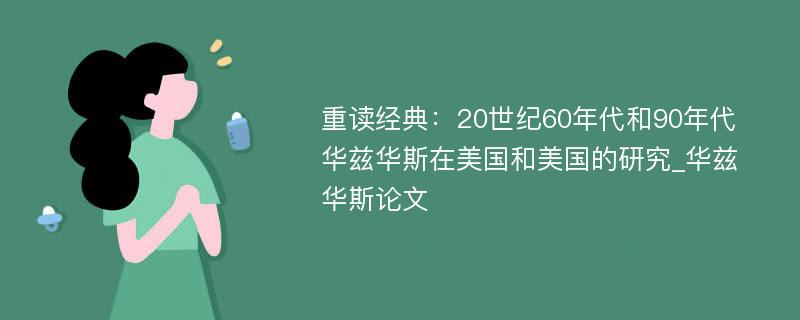
重读经典:本世纪60—90年代英美华兹华斯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兹华斯论文,本世纪论文,英美论文,年代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过去的解释是由过去和现代之间的对话构成的。面对任何一位历史上的作家,我们隔着时间的隧道、不同文明传统的山头,聆听着他那不熟悉的声音,让他责问我们现在所关心的问题。一个作家对我们说了些什么,其实就是我们从自己的现实地位上可能向他提出的问题,在作家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中,一切可能的理解产生了,这种理解总的倾向是生产性的:它总是意识到作家文本中新的可能性和可能出现的不同的理解。本世纪60—90年代是西方社会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轰毁、思想意识空前活跃与整合的时代,传统的经典作家作品不可免遭到现实需要的整合,华兹华斯也在所难免。
本世纪60年代开始的华兹华斯研究新阶段以身兼批评家、诗人和编辑的G·H·哈得曼(Geoffrey·H·Hartman)的著作《华兹华斯的诗歌:1787—1814》(注:《华兹华斯的诗歌:1787—1814》初版,1964,伦敦,本文论述、论文出自1987年版,第259—277页。)为起始,学术界公认这本书标志着研究华兹华斯的诗歌和一般浪漫主义运动的新纪元。从6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这本书都是英美大学文科语言类学生的必读书。首先,哈得曼至力于理解华兹华斯到底是个怎样的灵视诗人(Visionary Poet),在这方面,哈得曼无疑开辟了一块新天地。理解华兹华斯的自然观是理解华兹华斯作为灵视诗人的关键。在华兹华斯的理解中,自然完全可以等同于上帝,这个观点是60年代以前的几代批评家共同承认的。但是,哈得曼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观点提出了质疑:“华兹华斯需要去杀害或强暴自然,目的是为了获取灵视诗歌的黄金瞬间。”“黄金瞬间”是浪漫主义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普通事物和场景中灵性的外现的片刻。雪莱在《为诗辩护》中认为:这种令人销魂的“黄金瞬间”来无影去无踪,诗歌就是要赎(捕捉)上帝探访人间的这一时刻。传统观念认为,华兹华斯正是在诗中表现这种瞬间的高手,他的《四月里的两个早晨》、《孤独的割麦人》和《序曲》等都有对“瞬间”的出色的记述。在华兹华斯的意识中,以强暴自然为代价的灵视的诗歌正是基督教的传统,这个传统曾创造了17世纪的弥尔顿的《失乐园》,华兹华斯在小心提防着弥尔顿式的灵视诗歌的同时,也在预示着另一种新的意识:讨好自然,至少在想象中不要强迫自己去侵害它。而在实际的创作中,华兹华斯却不易被讨好,因为他自己经常被灵视(vision)困惑,甚至是处于恐怖的灵视中,用哈得曼的术语来说是处于“恢复意识”(coming—to—consciousness)的过程中。 哈得曼以“恢复意识”取代了华兹华斯的灵视。以此为前提,哈得曼将自己对华兹华斯的认识总结为:“想象(
imagination )的人格化 (humanisc)困难是我追随华兹华斯的主要方面。”
“人格化”一词是贯穿哈得曼全书的关键词。从浪漫主义的批评系统来看,“人格化”是想象的一种产物(注:参见艾布拉姆斯《镜与灯》,北大1989年版,第464—486页。)。在关于抽象观念是否合适人格化的问题上,浪漫主义者的主张是:情感所驱时偶而为之,而坚决反对将人格化作为平庸的修辞手段来运用。他们认为通过自己的生命和激情与那些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感觉物体融为一体而使自然产生生命的人性,是值得赞赏的人格化行为。当哈得曼解读《迈克尔》时,他强烈地感受到了华兹华斯试图人格化自我的灵视的过程。诗歌开头是一大堆散乱的石头,这是作者灵视的人格化的开始。通过这堆石头,华兹华斯被理解成能够人格化灵视的诗人,也正是在这点上,哈得曼保持着与主要传统相一致的看法,这种传统认为华兹华斯是个具有普遍性的诗人。
辛浦逊(David Simpson )的《华兹华斯的历史主义的想象:〈西蒙·李〉作为庇护者的诗人》(注:《华兹华斯的历史主义的想象:转移的诗歌》,1987年,伦敦,本文论述引文出自第149—159页。)运用了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历史主义,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总是用反人道主义的基本假设来代替理想文化的具有独创性的自我。这种基本假设认为,一切文化和社会现象,与一切自然现象一样,是外部诱发力量所产生的结果。这种诱发力量可以是文化传统、制度、民族、性关系、权力性质以及经济和物质环境。历史主义在新的阶段,抛弃了决定论的形而上学,同时又巧妙地保持了对因果关系准则的坚定信奉。由此推论,自我是我们自己无法控制的产物。那么,外在的诱发力的因果如何通过作家的自我而成为作品这个“果”的呢? 辛蒲逊提出了一个概念: 转移(displacement)。它不仅是针对华兹华斯的,也是针对一般的文学批评实践的。
《西蒙·李》创作于1798年,诗中讲述一个住在卡根郡的又矮又瘦的老猎人西蒙·李,他打猎已有35年的历史,从前又高又壮,而今却老迈不堪。诗歌最后谈到老人花了半天的力气都无法挖起的一块树根,“我”只一锄就将它挖下,老人为此说了不少感谢话,“我”听了反觉心酸。诗歌有一题证,记载着《西蒙·李》的本事。本事中说:故事发生在欧弗克斯丹,而不是风光秀美的卡迪根郡。辛蒲逊还通过其他材料,告诉我们“西蒙·李”原名克里斯多弗·崔奇(C·Tricky), 住的不是土屋而是狗圈(dog pound)等等。 这些本事又是如何“转移”成诗歌内容的呢?华兹华斯的家乡曾有过一个有才华而最终失败的诗人艾文·艾文斯,联系到华兹华斯写作《西蒙·李》时的自身处境,辛蒲逊认为诗人创作的动机是担忧(fear),自己最后也只能落个艾文斯式的下场,这种情感“转移”到西蒙·李身上,对西蒙·李晚年处境的描写就另有一番滋味了。华兹华斯在诗中将自己的渴望“转移”,当了老人的庇护人,那么他自己的庇护人又在哪儿呢?所以在诗中的“转移”对华兹华斯来说就是寻找语言(language)——此处指诗的结构,应该说辛蒲逊并不是简单地运用新历史主义进行文本解读的,他在很大的程度上还为《西蒙·李》建立了一个感情的心理学构架。
从50年代末起,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为依据的社会学批评重新在西方兴起,经过法兰克福学派的推动,这一流派的批评在西方有了不小的势力,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几乎都把批评的目标对准了华兹华斯的田园风格,认为这是诗人落后、 保守的象征。 典型的批评是沙尔斯(Roger Sales)的《1780—1830年的英国文学:乡村的和政治的》 (注:《1789—1830年的英国文学:乡村的和政治的》,1983年,伦敦,本文论述引文出自第52—69页。)。沙尔斯分析文学、评价文学人物时,总是毫不妥协地将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放在首位,因而也遭到了西方一些学者的非议。
一件艺术品的创造和它的被接受的关系永远是能动的。社会组织和关系的变化是一个大结构,这种历史意义的倾向改变了诗人在批评中的地位,诗人本身的问题从批评的中心走向了边缘,特别是对于浪漫主义诗人而言,最残酷的莫过于艺术家的“浪漫想象”,在批评者的“客观”的探照灯下变得没有任何真实的价值。象哈得曼一样,沙尔斯也将《迈克尔》作为一个主要的分析文本,只是在沙尔斯这里,我们看不到诗人在素材与情感之间想象的作用,只看到诗人在诗中描写了一个自给自足的、落后的、闭塞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村生活,而且这种生活在19世纪的英国农村是不真实的。因此,华兹华斯在诗作开头就引导读者离开大路(the
public
way ),
到了“一堆散乱的石头”处(straggling heap of unhewn stones)。这条“大路”代表着正统的历史进程,那“堆散乱的石头”则是被历史抛弃的、曾经有过的事实。迈克尔一家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如果没有那个事故的发生,他们的生活与世隔绝, 自给自足, 充满天伦之乐。 “家族的爱”(domesticaffections)是维持他们生活的支柱,而体现在这家人身上的节俭、俭朴、忍耐,正是华兹华斯发现的可以使被工业文明败坏的国家回到正确道路的处方。华兹华斯道德的栅栏终于没有建立起来,而象征着迈克尔一家道德力量的“晚上的金星”也终于熄灭了。诗作的开始也是诗作的终点,这个循环运动就象首挽歌,拒绝了任何社会救赎的有效机会。
沙尔斯还指出,华兹华斯在诗中有意识地模糊了经济的作用,拒不触及乡村生活内部的经济结构,他最了不起的就是提出了土地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湖区的农民凭着直觉也能提出:
我们这块土地,刚到我手里的时候
租子重着呢:到我40岁那年
这一份产业还有一半不属于我
《迈克尔》第374—76行
沙尔斯认为华兹华斯玩弄了一个“最古老的诡计”:他试图说明19世纪早期的乡村社会是前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应该说沙尔斯攻击华兹华斯的道德完善,事实上是在挑战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判断和它的文化上层建筑。
解构主义是近20年西方文化界一股强劲的批评思潮。华兹华斯的权威也自然是解构主义者“解构”的对象。关于解构主义,艾布拉姆斯在《欧美文学术语词典》中指出:解构主义是阅读作品的一种方式,它要推翻这样一种过于绝对的理论,即:作品有充分的理由在所使用的语言范畴内确立自己的结构、整体性和意义。解构主义借用了索绪尔的概念和基于这些概念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以达到推翻索绪尔的思想体系及结构主义理论基础的目的。60年代末,德里达在自己曾精心培育的结构主义开始茁壮成长、遍地开花的时候,突然从结构主义阵营中杀将出来。索绪尔认为:一种语言里口语和书面语的能指成分(signifier )和所指含义( signified)的同一性不取决于它们自身绝对的或客观的特征,而是取决于它们与其它音素、字符及概念含义之间的区别。德里达从这个观点推论出:出于意符和意表仅仅是不同方式的种种结合,因此两者之间的同一属性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从另一角度看,也不能绝对否定它们的同一性,因为在任何口头或书面的表达中,其表面意思是瞬间生成又即刻自消形迹(trace), 而这种瞬间生成的意义是通过它不同于其它所有未出现的意义的映衬而产生的。因此,德里达的结论是:从来没有绝对存在的意义,只有瞬间生成的意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涉及了作家、作品及读者接受过程,但其核心是从语言的所指与能指的差异所引发出来的。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从“作品”到“文本”的运动。过去把小说或诗歌看成一个封闭的实体,一个作家的完整的作品,具有明确的意义,批评家的任务就是去破译它。伍德曼(Ross Woodman)1988年在春季刊《浪漫主义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华兹华斯放牧的游牧者:〈序曲〉和疯狂的命运》的长文,这篇长文被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 )称为是“实践德里达和保罗·德曼的解构主义方法原则和文学批评的成功之作”(注:《华兹华斯·当代批评文集》约翰·威廉姆斯编辑1993年,伦敦第26页。)。伍德曼应用隐喻的观点看待《序曲》,使得这部传统认为最能体现华兹华斯的统一性的自传性作品变得支离破碎。 作为诗人, 他的心灵从童年开始到1792年从法国归来的17年间是如何成长的,他是如何从大自然中感悟到上帝的力量,又如何在现实的普通人身上不断印证这种力量。伍德曼的行文本身就是一个解析主义的迷宫,要在支离破碎的行文中用传统的“意义清晰”的方法复述出他的大意,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我们承认语言的隐喻性性质,那么过去我们曾经确认不移的东西就似是而非了,伍德曼将矛头直指华兹华斯作品的“儿童”形象,诗人明确指出“儿童是成人的父亲”,因为他刚从上帝那儿来,上帝的灵光尚未被尘世的灰土所遮敝。成人可以从儿童身上重新感受到上帝的意旨。在“隐喻”的关照下,“儿童”只是诗人的父亲了,且儿童与用讽喻的方法幻想出的“伟大的母亲”(自然)的结合,实在是不神圣的激情。儿童所创造的世界组成了一个不自觉的自我神化的过程,儿童就象登山为王的耶和华在巡视自己的创造物。关于神的隐喻不仅包括耶和华,也包括撒旦,于是儿童也可能成为一个罪犯,儿童的乐园也可能成为弥尔顿的地狱。伍德曼认为这种命运完全是叙述者在书中描绘的,他所作的工作只不过是把它显露出来而已。
伍德曼详细比较了《序曲》在1799年、1805年和1850年三个不同的文稿,指出《序曲》中隐喻与讽喻完全是一组作用相反、相成的力量。自从理查兹将隐喻分解成要旨(tenor )——隐喻的抽象意义或本义、和媒质(vehicle)——隐喻的具体含义或比喻义, 这种分析方式已被接受。解构主义明确指出,要旨与媒质的关系决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混乱的、含糊不清的,一个要旨可以有无数的媒质与之相对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序曲》中所记载的事件就成了不断否定华兹华斯写作意图的典型事例。隐喻颠覆了作者的自我要求,讽喻又从另一方面为自我保护了这个要求。讽喻是一种主要的象征方式。其中人物、行动和景物都具有系统的象征意义,它不仅是一种字面上的象征手段,更是一种结构上的象征手段(注:参见《当代批评术语词典》,罗吉·福勒主编,1987年,纽约,第5—7页。)。讽喻主要通过长诗中不懂世故、天真纯朴的“我”所领略的一系列人生经验,诸如考验、圈套、想象中的满足等,以达到作者通过想象的方式对现实世界进行解剖。隐喻与讽喻,这两股力量的冲突构成了《序曲》的形式(shape), 而这两种力量的合力就象是摆脱不了的梦魇,使得诗人的意图几近崩溃。
在传统的文论中,写作与阅读一直是两码事,伍德曼通过《序曲·第四章》的分析指出:华兹华斯遇上了济慈在《海波里尔的堕落》中所声称的问题:“温暖刻写我的手。”写作的感觉变成了阅读的感觉。从中读者感受到,诗人自我既不是一个疯子,也不是一个极端的自我主义者,而是一个在自我塑造过程中的灵魂。通过这种写作和阅读的同体活动,伍德曼明确地暗示我们,解构主义的批评是一项逃避所有政治问题的便利方法。从马修·阿诺德在19世纪末为我们确立的重教化、讲政治的传统开始,到20世纪末,文学的趣味的确是变了。
当代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与解构主义思潮有着紧密的联系。女权主义当然离不开女权运动,女权运动传达的信息并不象一些局外人解释的那样,只是妇女应该和男人得到同等的权利和地位,而是向所有这些的权利和地位提出质问。因此,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不是一个和其他政治项目并行的独特的运动,而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揭示和探索个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应该承认,性别批评不是女性批评家独有的权力, 它也能成为男性批评者的一种新的角度。 就象巴利尔(JohnBarrell )在《多萝西的用途:〈丁登寺〉中的语言感觉》(注:选自《诗歌、语言和政治》,1989年,曼彻斯特大学,第141—67页。 )中所表现的一样,性别批评与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溶为一体。文中,巴利尔充分利用了最新的语言学理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两个重要命题(themes):阶级结构对写作结构的影响;文学中性别区别与阶级区别的关系。
华兹华斯的自传体长诗《序曲》原计划是哲学诗巨著《隐者》的“序”,结果,《序曲》发展成一部独立的著作,几经修改直到1850年诗人去世时才出版,被公认为是诗人最重要的作品。前面介绍的多种文学批评也将《序曲》当作自己批评的对象,当代活跃的两位女性主义批评家斯宾瓦克(G·C·Spivak)和杰卡布斯(Many Jacobus)都不约而同地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1805年的《序曲》初稿。斯宾瓦克的论文《〈序曲〉第9—13章(1805 )中的性别与政治》(注:《英诗的后结构主义阅读》,里查德·玛琼,克利斯托天·诺内斯编辑,1987年, 剑桥第183—204页。), 和杰卡布斯的《类型性别和自传:汪卓考儿和朱丽叶》(注:杰卡布斯:《浪漫主义、写作和性别差异:〈序曲〉批评文选》,1989年,牛津,第187—205页。)在写作上都有一些共同点,那就是她们在自己的批评文章中几乎实践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所有的批评方法:心理学的、文本细读、历史主义、超验主义、自传、风格和性别等等。这种写作是典型的学院风格,阅读它的人同样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斯宾瓦克认为《序曲》中的顺序决不像它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是按时间顺序发展来安排的。它实际上是按诗人给定的文本和叙述的顺序来安排的。
斯宾瓦克由此提出了三个论点:(1 )华兹华斯不仅需要驱除他的非法的父权,而且需要重新确立他自己的性别意识以期表明他的想象力的恢复。实际上在这一部分,作者远超出了性别差异的讨论,象巴利尔一样,历史与性别的关系在作者看来是十分重要的。(2 )华兹华斯将法国大革命的经历转换成一个传统的文本,对此,他即可以写它也可以读它。华兹华斯也由此成为这一事件的主人。(3)诗人建议, 对于医治人类的疾痛,诗歌是比政治经济学和革命都好得多的灵丹妙药,而诗人自己正是为完成这个责任而来到人世的。
在讨论这三个论点中,斯宾瓦克借用了德里达的印迹(trace )和印迹结构(trace structure)的概念。印迹是我们熟悉的, 那么什么是印迹结构?她认为当我们努力去界定一个事物时,我们都在寻找原初,而每一个我们似乎已经确定好的原初又使我们看到了更前的一些东西,同时又包含了向后发展的某些东西。换一句话说,一个事物的印迹看来是自我包含着原始的,这就是斯宾瓦克的印迹结构,印迹是已出现的,原初是未出现的,如果印迹已包含着原初,那么,出现的和未出现的,存在和不存在的都表现在同一符号里,所以每个符号都若有若无,象是被划掉一样。虽然斯宾瓦克提出的论点在我们听来有点愕然,但她的解读与其他的解构主义一样是认真的,事实是华兹华斯这位“伟大的诗人”在她的论文中完全被放倒了(put down)。
能够界定写作风格或类型,长期以来都是文学研究的基本设想,类型的确立能够帮助建立适当的批评方法。近几年来,许多女性主义批评探索理论和性别的关系,杰卡布斯的批评也不例外,关心类型与性别,特别是华兹华斯自传体诗歌的类型和性别与有关的问题之间的关系,使得杰卡布斯向德里达的《类型的法律》求救。德里达认为:“有关文学类型的问题不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包括一般律法的主题;在自然和象征的感官中生成的主题;自然的和象征的感官中出生的问题;差异生成,在女性和男性的类型/性别差异的主题……在女性和男性之间差异界定的问题。”(注:杰卡布斯:《浪漫主义、写作和性别差异:〈序曲〉批评文选》,1989年,牛津,第187页。 )类型问题在此已完全溢出了文学研究的范围而走向了文化研究。1805年初稿《序曲》第9 章中有关汪卓考儿和朱丽叶的爱情故事成了实践解构主义类型理论的材料。汪卓考儿的父亲反对他们的婚姻,最后汪卓考儿屈从于父亲的意志,离开了自己的爱人和那个永远无法进入父亲的名字保护之下的孩子。父亲的理由是反对和平民联姻。这段故事在1850年的版本口已被大量删除,只剩下一些暗示性的诗句:
啊,年轻的恋人的幸福时刻,
(这样我的故事就要开始了)多么温馨的时光,
在女郎的呼吸声中爱情轻轻叩击,
比最美的星辰还要美的星光闪在天空!
这样吧,序曲已经开始,
用公正的字句写下的记录,
是令人悲哀的结局。
(1850年版,第9章 第553—9行)
由此,她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即生成问题、律法问题和性别差异问题作为叙述的中心,来解读文学类型的理论。杰卡布斯的这种方法挑战的不仅是大学英文系多年以来建立的有关文学的熟悉的思维方法,而且也反对给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文学科的定律有凌驾于其他学科的特权的倾向。对于20世纪末的知识界来说,前一部分体现了解构主义的威力,后一部分表现了解构主义的魅力。杰卡布斯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一事件不仅威胁和破坏了华兹华斯个人的“生成问题,律法和性别差异问题”,而且也威胁着要毁掉他的自传体诗的类型。
一个世纪前,马修·阿诺德在英语国家里树起了华兹华斯这位浪漫主义时期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和英诗传统中继莎士比亚、弥尔顿之后最伟大的诗人的路标。一个世纪以来,华兹华斯作为经典作家在大学文学系中的地位坚如磐石。华兹华斯不愧为英诗中的大家,他的诗作不仅经得起各种理论的检验,而且他所关注的问题至今还与人们的生存息息相关。当然,并不是说华兹华斯的所有诗作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他的好诗与劣诗相差如天悬地隔,象爱默生所说的,他的好诗标志着19世纪诗歌的最高水平,劣诗则伧俗鄙陋,味同嚼蜡。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其他伟大的作家身上。华兹华斯有自知之明:
我们只求:自己的劳绩,有一些
能留存,起作用,效力于未来岁月;
(《追思》第10—11行)
华兹华斯做到了这点。无论是批评还是赞誉,他的诗作都给现代人思索生活状态以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