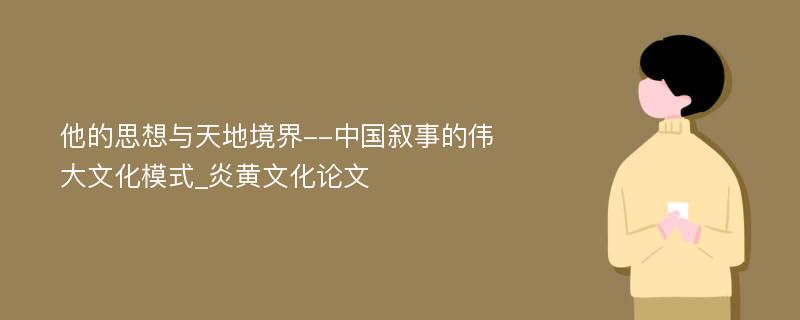
六合思维与天地境界——中国叙事的大文化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境界论文,思维论文,模式论文,天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08)10-0148-16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在近代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历史上罕见的思想、文化、学术大变革——由传统“中学”向现代“西学”转换的大转型。中国现代以来的一切问题都由此生出,而所有的问题又都可以基本简化归约为“中西关系”或中学与西学的矛盾。诸如全盘西化、国粹主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都是这一根本问题的不同症候、镜像或表征。笔者无意去重翻历史的旧账,而是想切实地面对这一矛盾的“当下时态”,并借中西之异的立场,来提出和建构不同于西方文化谱系的中国自己的叙事文化模式。
从比较的意义上看,西方文化在17世纪已开始进入现代形态,20世纪中期又发生了后现代转型。而中国文化的古典周期则比较长,直至20世纪初才开始现代性建设。①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西之异并不仅仅是一个时代问题或历史阶段问题,还存在着民族之异,即中西文化原是在存在较大差异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生成,是两种有重大不同的文化体系。其内在的文化价值、文化结构模式以及基本的文化话语、文化经验都存在着结构性和价值性的不接榫、难通约之处。正如杨义所指出的:“西方理论难以充分地覆盖中国文学经验和文化智慧的精华。”②简要说来,西方文化主要是一种科学文化体系,这一点随着现代科学的全面扩张,特别是西方发生“语言论转向”之后更显突出。而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一种诗性的、统合的体悟性文化,不重概念分析,而重直觉、整体和生命体验。有鉴于此,笔者曾提出中西哲学的元范型分别为:生命模式、气化理性;技术模式、实在理性。③目的仍在于要强调这“不同”和想坚持这“异质之思”的清醒、自觉,不使“中西之异”在现代性的“全球化”趋势中被无意遮蔽或盲目地“虚无化”。但事实是,中西不对接、不融通的矛盾不仅没有真正解决,而且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近百年来的相互“磨合”似乎变得更加隐性和内在。实际上,在人们的习焉不察中,中国当代学术研究因为中西的不合榫已出现严重的谱系断裂和“削足适履”现象。正是因为对此有自觉的省察,杨义先生才有意另辟蹊径,提出并已自觉实践:“立足于中国文学的经验和智慧,融通东西方的理论视野,探索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学理体系”的新的学术之路。④无疑,杨义的主张,对“中西矛盾”的解决是具有“当下时态”的推进意义的,但问题似乎并不这么简单,其中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不是是否敢于质疑西学,自觉到中西“有异”,而是要真正认识到两者之“所异”,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的本质之“异”。因为,受西学的强势“殖民”,中学真正的独异性其实已被覆盖、遮蔽、扭曲或改写了。所以,杨义先生的“返回原点”之思、之求是真正的真知灼见。但是要真正实现此目的,却远非易事。因为,任何还原其实都是相对的,都必然是一种超时空或“异时空”的对话,在今天则不仅是古今的对话,其实其中也早已内含着中西的对话。因为“返回原点”的目的并不是为返回而返回,而是为了新建“中国现代学理体系”,而体系的建构最终又不能不借助于现代的“概念”和“形式”,只有这样才会为已然被西学现代理性所笼罩的时代和学术群体所共享。这里便埋伏着一个概念或形式上的悖论。为了说清这个问题,同时也为了回到本文将要阐论的叙事文化模式问题,下面将连缀出这样一条“中国化学术建设”线索。
在现代中国的“中西矛盾”的“融化”之路上,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建设很有代表性,也很富启示性和建设性价值。冯先生曾自觉地申明他的新理学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这是它连续性的一面,但新理学之“新”又表明它是对旧理学(宋明理学)的超越,其目标则是要建立新的“中国哲学”,而不是“哲学在中国”。换言之,他要建立的是中国式的现代哲学。而“理性”正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同时现代理性又是以逻辑分析方法为其重要特征的,它的代表性资源正在现代西学之中。也就是说,他要建立的新理学说到底又必须是以逻辑分析为特征的理性哲学。但冯先生又认为,科学可以直接从西学中拿来,而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则不能直接从西方拿来。比如中国哲学中具有内在价值或终极性价值的内容便无法“西化”,属于最具特色、最本质的部分,也是最无法用西学概念、范畴言说的部分,而只能用中国的方法去“直觉体验”。他把这个核心的内容称为“通天人之际”,并把它提炼升华为“天地境界”,亦即他的“人学形上学”:自然或宇宙是包括人在内的“大全”整体,对这一“大全”的觉识便是“天地境界”,它要求人从比社会更高的观点即从宇宙“大全”的观点看人生。这就是他的新理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⑤冯先生的贡献,简单地说主要有两点:第一,要建立现代“中学”,就要借助现代西学的概念进行转换,把它变成“现代的”;对不能转换的部分则要保留。前者为“可言说者”,后者为“不可言说者”。前者靠概念认识,后者主要靠直觉领悟。但对后者也要用“言说”来促使它显示出来,以便更好地为人领会。第二,在方法论上提出概念认识和直觉体会的“结合”。冯先生通过中西比较和互释所得出的“天地境界”理论,是非常深刻的中国化的“还原(超越)”之论。但惜乎仅限于哲学,还没有打通大文化内部的壁障,达到应有的整体性的文化圆融贯通之境,所欠缺者则是整体性的整合、贯通。
大约与冯先生同时,宗白华先生也提出中国艺术意境具有生命意识、空间意识和动态的生成性等特征,并也不时语涉“通天尽人”、“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同样触摸到了中国大文化的内在真谛。⑥其所长在于中国式的诗意话语和感悟形式,所欠缺者则是现代理性的本质提炼和整体性的整合、贯通。
从叙事文化学的角度而言,美国当代学者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认为,中国的叙事模式起源于“史文”而不是西方的“史诗”,⑦指出,中国叙事的远源应是中国神话:“中国叙事文的‘神话——史文——明清奇书文体’发展途径,与西方‘epic—romance—novel’的演变路线,无疑能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对比。”⑧而中国神话则是“空间化”的,是一种“非叙述性”的原型:“中西神话的一大重要分水岭在于希腊神话可归入‘叙述性’的原型,而中国神话则属于‘非叙述性’的原型。前者以时间性(temporal)为架构的原则,后者以空间化(spatial)为经营的中心,旨趣有很大的不同。”⑨“希腊神话的‘叙述性’,与其时间化的思维方式有关,而中国神话的‘非叙述性’,则与其空间化的思维方式有关。”⑩很显然,在学理上这一论见同冯友兰的“天地境界”和宗白华的“空间意识”都存在可对接和源流贯通性。而也非常显见的是,这一论见仍然限于局部和相对感性,因为他把缘由归结为“先秦根深蒂固的‘重礼’文化原型”,(11)这视点就有欠整体和深刻。
更有代表性、同时也更具有“当下时态性”的则是杨义的学术中国化建设。他不光有自觉回到原点的意识,而且也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集中体现在他的三个研究板块之中:中国叙事学、中国诗学、中国文学图志。在叙事学方面他的主要发现有:(1)在“叙事”概念上,指出中国的“叙事”原为“序事”,而“序”的本意原指“堂屋上面的墙”,是个空间关系概念,因而可看出中国之“叙事”早就内含着“空间”的内涵;(2)在结构上,中国叙事是作者内含于结构之中,具有生命性、生成性等特点;(3)在时间上,中国是先“年”,其次是“月”,最后是“日”,具有以大观小的统观性、综合性;(4)在视角上,指出中国小说的视角是流动性和视角限制性的辩证统一,具有散点动态生成性;(5)指出中国小说存在“多祖现象”,具有某种程度的“复合性”和文化杂体性,等等。在中国诗学方面,他提出中国诗学是一种生命诗学、文化诗学和感悟诗学。(12)杨义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认识,仍未达到理想的理性通贯之境,其叙事学研究与诗学研究并没有在学理上“打通”,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合铆接榫。其根源可能主要来自他“参照西方现代理论”的一个基本观念,而不是像冯友兰先生那样要把中学转化为西学概念。在主观上他大概是想用接近中国诗性智慧的“理性”来阐释中国的诗性智慧,追求工具和内容的最大“契合性”,因此也就有意无意地在根本上排斥了那种西学式的整体性的“本质化”。
总之,在如何看待中学之“异”方面,以上都缺乏应有的本质化的整合与贯通。而笔者认为无论从大的精神生产来看,还是从中国叙事的大文化模式来看,中国式的具有整体可贯通性的大文化模式应该是“六合思维与天地境界”。六合思维是指主体运思的轨迹、范围、框架,它是上下四方(六合)立体化的,而不是线性的、片段的和平面的;天地境界是指文本最后或最高的“世界图景”,或涵摄文本的最后、最高的文意、理趣、哲思;或最高的表情达意境界:与天地的自然大化之道同一、合游的境界。
还是回到叙事问题上来。本文讲的叙事是一种大叙事观,六合思维与天地境界正是这种大叙事的大文化模式。叙事具有构建社会文化形态、塑建社会文化人格的大文化功能,它是生产部族和个体,特别是形成民族共同体的重要途径。在此意义上说,任何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都是叙事“叙”出来的。叙事有大叙事与小叙事之分,前者即社会的大文化建构模式,后者即一切具体的叙事性作品,如神话传说、小说、史传、戏剧、影视等不同的叙事性“文本”类别。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是大叙事。大叙事也如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罗兰·巴特所说的:人类一切活动都是叙事。人是“总在进行讲述的动物”,因为“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社会中……都在呈现着叙事。叙事是普遍的、永恒的、跨文化的:它就存在于那里,就像生活本身。”(13)也就是说任何民族、任何不同的文化都有叙事存在,叙事同族群、文化一样的古老。同时,作为一种大文化的生产和建构模式,叙事又会覆盖和弥漫于一个文化族群的方方面面,表现出某种全方位性,正如国内有论者所指出的:“叙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基本的人性冲动,它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叙事的范围并不囿于狭隘的小说领域,它的根茎伸向了人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一首童谣、一段历史、一组漫画、一部电影,实际上都在叙写某个事件;一段对话、一阵独自、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实际上都在讲述某些东西……在所有文化、所有社会、所有国家和人类历史的所有时期,都存在着不同形态的叙事作品。”(14)这一点,在“天人两分”和长于逻辑分析的西学中也许还不太具有说服力,因为在这种文化体系中,叙事、抒情、表意的“类化”分属会更早、更自觉、更严格些,比如叙事主要由神话、史诗、戏剧、小说、影视来承担,抒情主要由抒情诗来承担,表意则主要由现代派以来的以哲理象征为追求的新的艺术群体来承担,等等。而对以崇尚天人和合、以统合思维为特征的中国文化来说,则具有本质的和全局的意义。因为中国式的叙事、抒情、表意的“类化”分属并不明显,以研究小说美学著称的金圣叹为例,他曾提出一个“六才子书”的概念,即把《离骚》、《庄子》、《史记》、杜甫诗、《水浒传》、《西厢记》统归在一起,就表现出一种典型的“文史诗剧小说”混杂统合意识。
要而言之,中国叙事是自有格局,自有体系,是一种典型的大文化叙事模式。西方的叙事理论,尤其是以形式和结构的“数学化”分析为特征的西方现代叙事学,不太适合中国传统的叙事经验,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形式是诗而不是小说和戏剧,此外则是散文(包括先秦诸子散文、历史散文和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散文)。第二,中国的叙事艺术若以西方的范式看,其出现是非常晚的,像某些论者所指出的:“中国的叙事艺术传统似乎比许多民族尤其是以希腊、罗马文化为源头的西方传统要弱得多。在中国,成熟的叙事艺术如史诗式的长篇叙事文学、具有完整情节的戏剧都出现得很晚……事实上,中国早期的叙事传统是以更加理性、更加实用的“史”的形式发展的,因而作为想象和虚构的艺术的叙事文学的发展则相对滞后了。”“中国的叙事艺术真正有了重大发展的时期是宋元以后的近古时期,最重要的标志是自元杂剧以来走向成熟的戏剧叙事和元末明初从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15)第三,中国传统的叙事正是一种大叙事,它应该在“人猿相揖别”时就产生了,它是中国民族讲述经验、生产意义、生产民族个体和民族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早期存在不存在叙事,而是要指出中国叙事不同于西方的特异之处在哪里。我认为除了“文史兼涵”或叙事“史传”化这些中国叙事的原始特征外,叙事中的特殊的思维方式、天人关系、世界图景更为重要,这就是在根本上影响和统贯中国叙事艺术、叙事文化的大文化模式:六合思维与天地境界,这也是上述中西矛盾、中西之异的文化比较、对话谱系演进过程中还处在模糊或非澄明状态的问题,或曰还未找到更加深入和整体性的表达它的理论形式。
作为一种大叙事的大文化模式,这一思维同时也是结撰为文的文本生产范式,在中国,不仅渗透贯彻在规范的叙事性文学作品之中,而且还体现在诗、史书、词、文等几乎所有的精神文本之中,是一种在特定哲学—文化中形成的大的文化叙事范型,它是由特定的气化的天人关系模式所决定的,在根本上则首先依赖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天人哲学大范型。因此,我们的研究或范型建构,首先须从哲学范型开始。
二、天人哲学:从天人关系到气化宇宙观
文化模式是指稳定的文化结构,它是精神性、价值性的心理或文明机制。文化模式在共时态方面表现为民族心理和民族文明形态。民族心理也被称为国民性,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等。民族文明形态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模样”。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曾论述了酒神型文化模式和日神型文化模式,指出美国以及墨西哥印第安人在整体上属于酒神文化模式,而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人则属于日神型文化模式。(16)中国民族的文化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则是一种“气化理性”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对中国的叙事模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气化理性”的形成在根本上则是由特定的“天人哲学”所决定的。
中国哲学的一个主要的奠基石、主体骨架就是“天人关系”,“中国古代哲学可以称为‘天人之学’。‘天人之际’是中国哲学的总问题”,(17)到了宋明理学那里甚至认为“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外篇》)中国古人的特殊智慧首先就表现在他们对天人关系的重视上,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人与天是否有必然关联、两者是否可以统一?也就是“天人交通”问题。对天人关系的重视使中国哲学在根本上成为一种“天人哲学”,其内涵有四:有机、统一、同构、和合(和谐),即认为天人不可分割,不能分开思考、理解。正如英国的李约瑟博士所说:“在希腊和印度发展机械和原子论的时候,中国则发展了有机的宇宙哲学。”(18)有机的整体观必然连带地形成天人统一观,而这种统一又是以天人同构对应的和合观念为基础的,比如《吕氏春秋·情欲》即认为“人与天地同”,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提出“人副天数”的观点,把人的特征、特性和天地作了一一对应的解释。但是,中国哲学并不仅仅满足于纯理论性的认知表述,还特别注重“知行合一”的世俗落实。因此光靠理性来统合天人、弥缝天人之际的“巨大缺口”,肯定是难以圆通的。而“气”的哲学化提升则有效地弥补了纯粹哲理缝合的僵硬和简单。在中国,正是“气”这种特殊的物质“填补了人同天之间的距离(空白),满足了人们连通天地的愿望,充当了先民理解、掌握神秘的‘无限’、‘大全’的‘理性以太’。如气:第一,无处不在,无远弗届,具有充塞天地的弥漫性,正可把天地人、万事万物都连通起来;第二,无形、无色,显得虚幻,但又实实在在地存在,具有一种神秘性(神性);第三,生死攸关。有气则生、则活,无气则死、则枯,人和自然皆莫能外”。(19)李存山先生还把气论同西方的原子论作了比较:“中国气论与古希腊原子论虽然都属于素朴唯物主义学说,但它们的基本思想和历史作用有很大的不同。‘原子’是一个个被‘虚空’间断的、有形的、不可分、不可入的微小粒子;而‘气’则是充盈无间、至精无形、能动的、可入的、无限的存在物。”(20)而且他还不无透辟地指出:“‘气’与‘仁’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初始概念,也是贯穿中国传统哲学始终、决定其基本发展方向的主要范畴。中国封建文化之所以具有入世的而非出世的、伦理的而非宗教的、君权的而非神权的特点,从思维方式上说,是被气论与仁学相互作用或气论服务于仁学的机制所决定的。”(21)也就是说,进一步看,中国传统的天人哲学又是一种气哲学、气化的宇宙观。气哲学在中国有多种面貌,是一身而多相。因为“气”是中国文化的基元性范畴,为不同领域所用,而且它往往还一物多名、一体而万象,或往往与别的事物杂糅混融在一起,因为按照中国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看,气正是构成万物的基本物质。如张载即认为:“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22)还说:“凡象,皆气也。”(23)他认为所谓的天、道、性、心、象等,说白了都是气之别名。
我认为张载的观点至少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气哲学的一种极具针对性的方法。由是观之,我认为气之在中国至少具有五种文化形态:宗教气、自然气、道德气、理气、文气(诗气)。
宗教气,“由于甲骨文、金文(除‘行气柲铭’之外)和现存《尚书》、《诗经》没有给我们留下名词气字的直接材料,这就使得对气概念原始意义的探讨成为一项困难的工作”,“这种情况与春秋以后出现的大量的气的思想相比,形成了一个‘大的断层’”。(24)气在殷商甲骨文和西周、春秋的金文中是以“乞求、迄至、终讫”的面貌出现的,是动词或副词,祈祷礼拜(乞求)、到达欲达之境(迄至)、愿望的实现、完成(终讫),这些都具有巫术和宗教的意义。而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气为“云气,象形”,这是自然之气。属于自然之气的有:西周时太史伯阳父论地震提出的“天地之气”(《国语·周语上》);《左传》中《昭公元年》医和提出的“天生六气”:“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昭公二十年》晏子所说的“味气”:“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昭公二十五年》子产的“五味气”:“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提出的人之“血气”;还有见诸先秦典籍的烟气、蒸气、云气、雾气、风气、寒暖之气、呼吸之气和“五行之气”。道德之气以《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的“浩然之气”为代表:“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理气有老子、庄子的“道气”、《管子》的“精气”、《周易·易传》的“阴阳”、《淮南子》的阴阳和太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气,特别是张载的气本一元论,当然还有朱熹的“理气”论、明王廷相的“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雅述》)、清王夫之的“气在空中,空中无非气,通一无二者也”(《正蒙·注》)、清戴震的“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孟子字义疏证》),认为宇宙无非生生不息之气化流行。文气可以曹丕《典论·论文》的“文以气为主”为代表。
气哲学主要指理气和道德气,它们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的气化理性,它们同宗教气等一起构成了我们民族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基因、气集体无意识,在根本上影响了中国的文艺理论和叙事艺术。
三、气化诗学:从道、易、味、神、兴、象外、交感到游
气哲学、气化理性对中国诗学(文艺学)的影响是总体性的。无疑,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道”都是中国诗学最重要的基元性范畴。《说文解字》释“道”为:“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这虽是汉人的解释,但却接近道的本义。我们迄今尚未发现甲骨文中的道字,而西周金文中已出现道的七八种写法,说明至迟在西周时,道被广泛应用。写法虽异,但基本的结构却一样,即都是“行”字中间加一“首”字。行字好理解,就是指人行的道路,关键是首字有歧解,首即人头是没有问题的,有人据此解为“以首代人”,“‘道’字从行从首,实为从行从人,故‘道’是取人行于路途之象。”(25)而我认为在这里“首”并非真指人首,极有可能是指人头顶上的天空,是“以首代天”,这样道就非“人道”而是指“天道”,但又假人首言天,实反映了周时由“天道”向“人道”的归趋、过渡。《老子》中的“道”用的就是道的初义:天体日月运行之常规常则,所以才会那样看重往复循环之“反”、“逝”、“远”。其实儒家也一样,《周易·易传》也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都对“天道”心怀崇仰。
道在中国文化中也是一身而多相,有研究指出:“中国道范畴的演变,自殷周直至清王朝灭亡,历经三千余年漫长的岁月,经过了道路之道→天人之道→太一之道→虚无之道→佛道→理之道→心之道→气之道→人道主义之道九个阶段。”(26)应该说这种分法未必就很确当,但指出道在中国的“无量”和“多相”则无疑是正确的。我认为道在中国文化中大致有这样一些域属:(1)自然之道;(2)哲学之道(包括宇宙论、发生学、本体论等),如老庄之道;(3)伦理道德之道和政治之道,如儒家之道;(4)学术家法、谱系、道统,如孔子言“吾道一以贯之”,后来韩愈和朱熹所祖述、张目的“道统”;(5)技术技巧之道。而此处讨论的是对诗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气化之道”。
气化之道源自老庄之道。老庄除了肯定道是世界的本源,具有象而非象、言与不可言、无目的而有大目的、无为而有大为等矛盾二重性外,还强调道之虚无、道之具有气化特征,如《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42章)等等。正因为有这样的“道论”,才会引出后来的“精气”、“无极”、“太极”、“太一”、“元气”、“太虚”、“道气”、“理气”等一连串的话语生产;也才会有张载的“由气化,有道之名”,“凡象,皆气也”之说。同时,正因为道体是气化的、宇宙是气化的,像老子这样的智者才不光认识到万物是往复循环的。正因为是气化之道,老子也才会有“味喻”:“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第35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第63章),主张以无味为味,即以恬淡为味,实为后世“品味”之道的滥觞。
冯友兰先生就曾十分敏锐地指出:“《老子》书所说的‘道’很像阿那克萨哥拉所说的‘奴斯’,一方面是‘世界智慧’,一方面又是极细微的气。”(27)而庄子更是明确主张“听之以气”,“唯道集虚”(《人间世》),“通天下一气耳”。道的这种气化性,在根本上影响了中国诗学,使中国传统的文学及其理论在根底上也以“气”为内质,尚虚贵真,追求空灵玄远,追求神秘的“气动”、“气悟”。换言之,中国的天人—气化哲学主要是通过老庄气化之道的中介而在根本上作用于中国诗学的,进而形成一种特殊的气化诗学。
“易”字在甲骨文中,“其字形和本义都是把满杯中的水倒入另一相对不满的杯中”,“所反映的是大自然中损益、盈缺的原理和法则”。(28)而《说文解字》把“易”释为“蜥蜴”,蜥蜴同蛇一样在古人心中都是典型的能变化形态的动物,“变易”的含义自在其中。其实“易”还有另外一解,即认为“易”字由日与月二字合成,“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29)《周易·易传·系辞上》也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易》道即“阴阳”。阴阳就是气,从气化的宇宙观来看,日月也无非由气构成,所以阳气即日,阴气即月。由是观之,易亦即气。至于第一解“杯中水的变化”义,也可以此通融:气与水本有相通之处,气可凝结为水,水亦可升华为气。总之,“易”也是气化的。
这气化的“易”对诗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变易、化生的追求上。其实是“道”在实际运用中的具体展开,即易是由道发展来的,尽管有人认为易是比道更早的概念,(30)但就《易传》来说则肯定在老子提出“道论”之后。说它是道的发展也还另有根据,如杜而未就指出《易经》与《老子》之间有许多关联处;(31)汉桓谭《新论》也早就指出:“言圣贤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而因附续万类,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谓之‘易’,老子谓之道”,意思是易道原本实为一物。两者不同的地方在于“易”比“道”似更加强调阴阳二气的交感和合、变易运化,使中国文学在暗里加进了一种隐形的流动变化的“气”,有了灵动的气化的质素或基因。如刘勰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神与物游”(《文心雕龙·神思》);金圣叹说:“文章最妙,是目注此处,却不便写,却去远远处发来,迤俪写到将至时,便且住,却重去远远处更端再发来,再迤俪又写到将至时,便又且住;如是更端数番,皆去远远处发来,迤俪写到将至时,即便住,更不复写出目所注处,使人自于文外瞥然亲见,《西厢记》纯是此一方法,《左传》、《史记》亦纯是此一方法。”(《第六才子书》)是在直接强调写小说别太直太露,实际上是指通过曲折之法来制造生动、变化和扩大可让人想象的空间。应该说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大都具有这种有道气氤氲流化的“气场”,或“气动”、“易动”空间。
有人指出“味”产生于中国的饮食文化,(32)《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本味篇》载:“汤得伊尹,祓之于庙,爝以爟火,衅以牺猳,明日,设朝而见之。说汤以至味”,提出了“至味”这一概念。《论语·乡党》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述而》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等,都表达了对美味的重视。孙中山先生也曾说:“烹调之术本于文明而生,非深孕乎文明之种族,则辨味不精;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中国烹调之妙,亦是表明文明进化之深也。”(33)《说文解字》也解:“味,滋味也。”但是,真正把“味”提升到哲学高度并作为动词来使用,应该说是肇始于《老子》的“味无味”。味者实气,即人们常说的“气味”。而“味”字动用,即味“无味”(味道)、味象、味文、味诗,或如南朝宋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所说是:“圣人含道暎物,贤者澄怀味象”,总之,我认为不管味的对象为何,味总与气分不开,味为气,而被味的对象也必然与气有关,不然就无法味和不必味了。因此完全可以说中国古代肇于《老子》的所谓“味”的活动,其实质则是:以气感气、以气悟气,以主体的“气场”来感应、体悟客体的“气场”。味的活动无他,正是一种特殊的气化、气感活动。日本学者笠原仲二认为:中国人原初的美意识起源于味觉,然后依次扩展到嗅、视、触、听诸觉。随着文明的发展,又从官能性感受的“五觉”扩展到精神性的“心觉”,最后涉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整体,扩展到精神、物质生活中能带来美效应的一切方面。(34)此见是有道理的,而其根据则在“气哲学”这个基元性的文化土壤。
“味感”范畴移用于诗学大致有如下表现: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提出:“繁采寡情,味之必厌”,主张“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文心雕龙·隐秀》);钟嵘《诗品序》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唐代的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主张“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并提出文学应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后来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对司空的观点又作了发挥:“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这就是文论中的“味外味”之所自。可见,从“味之必厌”、钟嵘的“诗内滋味”,到司空图、苏轼的“味外之味”,中国古代的“味”诗学呈现出一条递进深化之路。此外,味还同品相连组成“品味”一词被广泛使用。在甲骨文中“品”为一种“祭名”。《说文解字》释为“众庶也,从三口”,意为众多。但不管如何,“从三口”说明它与口有关,亦即同口感、口味有关。或者可解为气味之进入处:两鼻孔一嘴巴(三口)。这样,使用“品味”便会有主体主动施动的感觉在,因而也就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或者说其更为流行的原因或许就在于它正内含着一种张扬主体的人本意义。于是中国古代的各种各样的“品”也就大蔚大盛,如:诗品、画品、书品、曲品等。有人甚至认为“意境理论本质上是一种东方品味理论,典型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西方造象理论”,(35)应该说是言之有理的。
《老子》已有语涉“神”,如“谷神不死”(第6章),“神得一以灵”(第39章)。老子是泛神主义者,其“神”是指一种神妙、灵妙的难以把握的事物,“谷神”即道,具有本体意义,而“神得一以灵”的“神”只是指某种玄虚神妙的事物,它靠秉有“道”(一)而灵妙。后来《易传》基本上延续了这种概念:“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说卦·传》),“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上》),都是指“神妙”的作用而非“神灵”。《孟子·尽心下》谈到人格境界时说:“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种不可知的“神境”,在孟子是指与天地大化融为一体之境,用老庄的概念来说便是与道为一之境。《庄子·达生》有“舟人操舟若神”的寓言,其神也是指得道的自由境界。总之,“神”在先秦的文化中主要是指某种神妙的性质、能力、功能、作用。后来才变成泛指事物的“内在精神”,或“神采、灵魂”。其实,说透了,神也是气,如《礼记·祭义》说:“气也者,神之盛也。”《大戴礼·曾子无园》说:“阳之精气曰神。”《白虎通·情性篇》说:“神者,恍惚,太阳之气也。”《太平经》说:“神者乘气而行,故人有气则行,有神则有气,神去则气绝,气亡则神去。”一句话,“神”之奇妙,正与气的神秘性相同,或毋宁说其原本正是因气而“神”的。
“神”用之于诗学则有:“诗的极致有一,曰入神。”(严羽《沧浪诗话》)“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苏轼语)“体物而得神,则自有通灵之句,参化工之妙。”(王夫之《姜斋诗话》)还有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的主张。作为范畴则有:神品、神气、神理、神采、风神、传神、神韵、神情、神遇、神会等。
兴在甲骨文中是“象众手托盘而起舞之形”,《说文解字》释为:“兴,党兴也。”《尔雅·释言》释为:“起也。”其本义就是“众手举起”的意思,解为“兴起”应该是不错的。但后来同《周礼》的六诗、《毛诗》的六义搅在一起就衍生出了政治和道德意义,汉代经学家如二郑(郑玄、郑众)就把它解释为“譬喻”和“美刺”:“托事于物”、“取善事以喻劝之。”(36)后来,朱熹在《诗集传》里的解释应该说是最为经典切要的:“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除了“起”、“譬喻和美刺”,兴的第三种含义则是美学的“感兴”(朱熹的解释已有“感兴”之意),如今人王一川援引署名贾岛的《二南密旨》的话:“感物曰兴。兴者,情也。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曰兴”,把兴解释为:是外感事物、内动情感而又情不可遏这一特殊状态的产物,其基本意思就是感物起兴或感物兴起;感兴是指人在现实中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37)彭锋在《诗可以兴》中把“诗学传统”中的兴义归纳为三点:(1)触物起情,(2)乘兴而为,(3)意余言外。(38)汪涌豪在《范畴论》中则指出兴具有“主客交融”的特点。(39)
上引几种观点都没有注意“兴”和气的关系。我认为兴的土壤正是气文化、气哲学,“兴”是为情所动,并携带着气场而出者,始终不离气化之境,因而具有强烈的场景感和氛围感。王夫之说:“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船山遗书·俟解》)徐复观先生也认为:兴句的意义不是表示实在的具有概念的意义,而在于“形成一首诗的气氛、情调、韵味、色泽。”(40)这已说得很清楚,“气氛”即气,同“情调、韵味、色泽”合起来,仍然不离气,或者说无非是气化态的审美时空而已。因此,可以说:兴也是气化诗学的一个核心范畴;兴者亦气。
要论“象外”,必先解“象”。庞朴先生曾引《韩非子·解老》来说明:“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见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审)见其形,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认为韩文没有区分常人想见之象和老子的“道象”是不妥的,并依《易传》的“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象也者,像也”的说法区分出两种象:客观的象(天垂之象)和主观的象(圣人所立之象)。特别是根据《易传》的“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提出一个道、象、器的三分结构:“可以看得出,在《易传》作者们那里,形和器异名同实,而象和形是不等值的。因此可以这样说,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外或之间,更有一个‘形而中’者,它谓之象……道无象无形,但可以悬象或垂象;象有象无形,但可以示形;器无象有形,但形中寓象寓道。或者说,象是现而未形的道,器是形而成理的象,道是大而化之的器……象之为物,不在形之上,亦不在形之下。它可以是道或意的具象,也可以是物的抽象。”(41)指出“象”为“形而中”,具有具象和抽象的二重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中国文化中的“象”一般并非指实物、实象,而是如韩非所言是“想见”的,或如《易传》言是“象之”。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也区分了“天地自然之象”和“人心营构之象”。质而言之,中国的“象”虽后有象形、意象、物象乃至形象等专词,使人遂形成某种定见:“象”即实的东西,或至少是要以“像也”、“指实”为鹄的、旨归的。殊不知,其还有另一基本面目:虚象,甚或说是超象的,或至少如庞朴言是“形而中”的。其起源便是《周易》的“象”,易象非实,其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的符号:卦象。后又有《老子》的“道象”:“大象无形”,“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这样,由易而老,由卦象而道象,原本为“中”、为“模拟”(虚)的“象”,逻辑性地演进为“象外”也就顺理而成章了。
对“象外”概念的生产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庄子》的“得意忘言”之论,这引发了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魏时的荀粲正是在论及“言意”关系时第一次提出了“象外”的概念。(42)王弼接着在《周易略例·明象》中直接明言要“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两者可以说是在哲学或语言论的意义上高举起了“言外”、“象外”的大旗。在诗学上直接标举“象外”的是唐代的刘禹锡,他在《董氏武陵集纪》中说:“诗者,其文章之蕴邪!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象外”之说后来又发展为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到清代的叶燮则演化为:“泯端倪而离形象”,“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原诗·内篇》)。这种“象外”的超象路径正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一大“主脉”,著名的意境理论正是在这条途径上产生的。
象本来非实,而象外就更虚灵了,是“思而得之”的东西。质言之则是“想象态的时空”,或对话结构的、开放的、未完成的、动态化生的“气化之境”。没有气哲学、气化的文化座架,所谓的“象外”范畴就会完全成为凌空蹈虚的“空壳”。叶燮以“理”、“事”、“情”总括万物并以之论诗,但他很清楚:“然具是三者,总而持之,条而贯之,曰气。事、理、情之所为用,气为之用也……三者借气而行也。得是三者,而气鼓行于其间,絪缊磅礴,随其自然,所至即为法,此天地万象之至文也。”(43)借叶氏之论,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象外”即气,因为“象外”再大,也总难越出事、理、情合一的“絪缊磅礴”之外。按叶燮的说法,世间所有的“理、事、情”都是被气“总而持之,条而贯之”的。象、象外,都是气。
“交感”作为气化诗学范畴是直接由“天人哲学”、天人文化衍生出来的,它是指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中存在的人同外物间感应、互动、以至于和合、化生的关系,源出于《周易》的阴阳三才图式和《老子》的“四大”结构。后来《孟子·尽心上》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所以,“天人可交感”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交感在哲学可以说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而在诗学则被称为“物感”。《礼记·乐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地气上齐,天气下降……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认为“乐和”与阴阳之“天地之和”应该是统一和谐的。在文论方面,陆机在《文赋》中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直接提出了“文学应感说”:“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及還,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提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钟嵘在《诗品》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讲的都是典型的天人、心物、主客的“交感”。后人李梦阳在《鸣春集序》中所说“夫天地不能逆寒暑以成岁,万物不能逃消息以就情,故圣以时动,物以情征,窍遇则声,情遇则吟,吟以和宣,宣以乱畅,畅而永之而诗生焉”,讲的也是“交感”。那么交感发生学的内在条件是什么呢?我认为仍是一气贯通使然。诚如清方东树《昭昧詹言》所说的:“观于人身及万物动植,皆全是气所鼓荡,气才绝,即腐败臭恶不可近。诗文亦然。”也如《庄子·逍遥游》所说是“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正是有气的存在,人和物才可以因气相通相感,出现从物质到精神的“化学反应”(感应),无疑,“交感”也正源自气化。
“游”是中国诗学的最高境界,当然也是气化诗学的最高境界。它指的是通过审美气化、审美交感而达到的把主体提升到与宇宙本体(道)同一的自由之境,《庄子》的“虚己以游世”、“逍遥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是其所本。而《庄子》之本却在《老子》的“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反者道之动”,即宇宙大化流行的周行赅遍和循环往复性质。这样,要体道、与道为一,就必须像道那样去周行、巡游。于是,“游”便成了一个极其特殊和重要的概念,也是《庄子》一书中最为华彩的“语词”。我们发现“庄游”有这样几个特点:(1)无心、无目的、无为;(2)乘气而游;(3)游心,达到精神的高度自由;(4)与道为一;(5)出入六合,与天地精神往来。六合者,上下四方之谓也,一般是指空间上的全整性。
《论语·述而》也讲“游”:“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的“游”主要是指艺术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修养和化成,虽意在仁礼教化,但也仍然不离审美,而把它作为人格的最后完成环节,又赋予“游”在儒家伦理价值系统中的特殊位置,这样,“孔游”就和“庄游”形成了强大的互补合力,这一合力最后又共同影响了气化诗学,使之有了最高和最后的归依处:与天地同境界的“神游”。如陆机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文赋》);刘勰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神与物游”(《文心雕龙·神思》)。
《庄子·大宗师》中假孔子之口说:“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区分了“方之内”、“方之外”两种游,也就是分判开尘世外和尘世内两种境界。我们或可借此说,孔游主要是“世间”游,庄子把这种“世间游”提升发挥到了老子的“体道”之境,生产出了“世外游”,也就是逍遥的天地之游。而这种游在本质上又是“游乎天地之一气”,是御气而行,是“气游”。若此,才可臻达世外的“天地之境”。
气化在中国文化里不唯基元,而且还是一个极为普泛广适的范畴,如有天气、地气、人气、文气,连传统的“二十四节”也称为“二十四节气”,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气家族,有人统计固定的气词汇就有168种之多。(44)
与此相应,文论中也有一个丰富的气群,以上所论只是其中的大者、要者。
四、对话文本:从辞、史传、赋、诗、笔记、词、散文到戏剧、小说
《庄子·大宗师》中对“方外游”有一个“注解”:“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三人之所以可以莫逆是因为他们都无功利计较、都能超然于生死之外,因而也都能像大道那样遨游无羁。结合《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等言论,我们可以看出,“庄游”包含着两个重要内涵,或曰为中国哲学、美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生产出了两个重要的精神产品:六合思维和天地境界。为中国文人提供了一个致思、运思,抒情、叙事,表征万物,建构世界的根本性的元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六合思维是指运思的轨迹、范围、框架,它是上下四方(六合)立体化的,而不是线性的、片段的和平面的;天地境界是指文本最后或最高的“世界图景”,或含摄文本的最后、最高的文意、理趣、哲思;或最高的表情达意境界:与天地的自然大化之道同一、合游的境界。
当然,这一元结构并非《庄子》首创,应该说是由《周易》和《老子》开其端,由《庄子》彰显、强化和最终完成的。关于“天地境界”,《庄子·知北游》也有“点睛”之笔:“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原天地之美”、“观于天地”,说的就是本于天地之“美道”,体会遵循天地运化之道的意思,其实也就是“天地境界”,即把人提升到天地的高度、境界去认识、行事,去生存、处世、“发展”。而同时也就是一种主体的思维模式和人的世界图景:思考问题要站在宇宙自然或天地的境界,要用“想天想地”的大思来统御处理世间的万象万理。
西方人的“世界图景”是科学加上帝的“伊甸园”,而中国儒家的“世界图景”是“修齐治平”、“达兼独善”,或如《庄子》所言是“身在江海”而“心居魏阙”(《让王》),宋元以后才在“江海”和“魏阙”之外又加进了一个“商界”。在儒家的图景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图景即《庄子》最终构建的道家世界图景:天地境界。这样,原来的儒家图景就有了变化,或融进“天地境界”,或完全为其所置换。天地境界的前身原本就已存在于儒家的“易道”之中,换句话说,《庄子》的天地境界之所以对中国文化、中国文人士夫具有巨大影响,“易道”甚至《老子》的“四大”架构都是提供了强大的助力的。儒道于此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合构、合力,而由《庄子》最终建构和彰显的六合思维和天地境界也就由之而“弥纶天地”、“苞裹人伦”,成了经天纬人的思维和文化生产模式了。
已见前述,“天地境界”这一“专名”是现代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提出来的,他在《新原人》中说:“天地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事天’底。在此种境界中底人,了解于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人必于知有宇宙的全时,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展,始能尽性……他已知天,所以他知人不但是社会的全的一部分,而并且是宇宙的全的一部分……他觉解人虽只有七尺之躯,但可以‘与天地参’;虽上寿不过百年,而可以‘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并且认为他的“天地境界”就是道家或《庄子》的“道德境界”(天地境界)。(45)
冯氏的“事天”同《庄子》的“齐物”、“天游”的意思是相近的,总之都没有超出上述笔者所解的“天地境界”的含义之外。
在先秦典籍中对六合思维运思方式的具体表述则是前述《易传》的“俯仰天地”或“仰观俯察”。也如《中庸》所说:“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而其内在实质则是“时间空间化”、“循环时间”、时间最终凝聚、消融在空间之中的“中央空间”结构。即中国古人长期以来,不光认为“天圆地方”,而且还认为自己身居中央之国,由此而形成一种独特的“中央空间”意识,再加上道家、儒家、阴阳家等都有的循环宇宙观和循环历史观,如把五行方位化(空间化):木—东、金—西、火—南、水—北、土—中;崇尚“天不变,道亦不变”,“五德终始”的“天道”规律等等,结果就铸成了一种独特的时空模式:时间空间化,同时也造成了中国叙事作品(亦包括抒情作品)的强烈的“空间倾向”,如中国叙事作品多以“空间”命名,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西厢记》等。
宗白华先生也说:“中国人的宇宙概念本与庐舍有关。‘宇’是屋宇,‘宙’是由‘宇’中出入往来。中国古代农人的农舍就是他的世界。他们从屋宇得到空间观念。”(46)“中国人不是向无边空间作无限制的追求,而是‘留得无边在’,低徊之,玩味之,点化成了音乐。于是夕照中要有归鸦。‘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陶渊明诗)我们从无边世界回到万物,回到自己,回到我们的‘宇’。‘天地入吾庐’,也是古人的诗句。”(47)这其实是指出了中国人空间的内化现象,而这个“内化的空间”恰恰又是源于天地境界或“天人一体”的宇宙模式的。宗先生在评价谢灵运的《山居赋》里写出了“网罗天地于门户,饮吸山川于胸怀”的空间意识后紧接着指出:“中国诗人多爱从窗户庭阶,词人尤爱从帘、屏、栏杆、镜以吐纳世界景物。我们有‘天地为庐’的宇宙观。老子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庄子曰:‘瞻彼阙者,虚室生白。’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中国这种移远就近,由近知远的空间意识,已经成为我们宇宙观的特色了。”(48)
原因就在于本来天人哲学就认为“天人一也”,天地也就当然可以被吸纳微缩于屋宇、庭院、尺幅、篇什之中,但是,这天地宇宙的“亲人”、在场,又断断离不开那个潜藏在、内化在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天地境界”、世界图景,那已变为士夫文人内在文化—心理或文化人格的六合思维和天地境界。中国古代的明堂就是一个显例,它是古代最高等级的皇家礼制建筑之一,是帝王颁布政令、接受朝觐和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实际上就是“天地”微缩于建筑的一个典型代表,它下方上圆——仿天圆地方模式;立体的三层结构——对应天地人三才;四周多扇的门窗代表着四方八面等等。
六合思维与天地境界融渗贯彻在辞、史传、赋、诗、笔记、词、散文、戏剧、小说等各种文本之中,使中国的文学或文化文本至少产生两大特点:第一,大多呈现出一种天人对话的结构,尽管有隐显强弱不同,其具体表现都是仰观俯察、宇宙之思、天地之问;第二,历史时空与幻想时空往往被统归提升为“天地位格”的“天人时空”,这在《史记》、陶诗、《春江花月夜》、苏诗、《桃花扇》、《红楼梦》中则有具体的不同表现,即或表现为历史哲思、自然真意、宇宙本体追问、虚无确证,或道境的本体时空。
在文学上使这一叙事(亦是言情)范式真正首次得到完型、奠基的是屈原的《离骚》。在《离骚》众多的优长中,那种呼天抢地式的痴迷求索、追问,无疑更为重要。诗人在作品中所展现的正是上下四方的六合思维和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上天见帝”,“下求美女”,“问卜灵氛”,“决疑巫咸”,而且还要假善鸟香草、虬龙鸾凤,不光要问政、问人、问己,还要问鬼、问神、问天,把理性的探索和神巫的迷狂混融为一。在思维和表意方式,或文化表征类型上看,就不光是天人合德、天人合情、天人合思,而且是天人合道了。所展现的就不仅仅是神巫思维的文学化或文学同神话、宗教的融合问题,而且还是交感思维、对话文本的完型、奠基问题。从特定意义上说,该诗为中国文学所提供的一个最大的“典范”也许正是这个“问”:问人问政问神问鬼问天问地。“问”非他,其实正是以天人合一为基础、气化交感思维为连通的“对话”,其虽完全以“心灵追问”的形式呈现,但由于有天人哲学、气化理性的地基,这种心灵化的追问实际又是超心灵、超人世的,其边际直达天地大道。正是因为《离骚》对接了从《周易》、《老子》、《庄子》一路下来的六合思维和天地境界模式并用文学的形式使它得到完型化表达,才使它成为百代法式,具有真正的元典意义,后来的司马迁以至曹雪芹都可以视为是对它的某种赓续。
鲁迅说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虽为比喻之辞,但也的确触到了《史记》与《离骚》近似的实际。两者的似正似在相同的“叙事”模式上。这个模式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天人之际”转换成叙事模式就可以和六合的思维、“天地的”致思哲思(境界)相对接。这也正是《史记》所实际达到的境界:《史记》除了用诗化的文学之眼看历史之外,还特别地表现出了一种哲思透视的高远向度。进而逼视出了历史与文学、现实与理想、历史与道德或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现实政治与美好人性和合理的文化理想之间的巨大的不可调和性,在这不可调和性中,我们不光可以看到太史公那悲天悯人之大悲情、大悲美,而且还会感受到他那种参透天人的大理性、大哲思,这样,这个特殊的历史巨构不光真正打通了史学与文学之间的壁障,为后世确立了史与文、理与情、史与诗之二元结构范式,而且还为文本打开了一片超现象的哲理真实的天空,使六合思维与天地境界的叙事范式在历史与文学相淫渗、结合的地带得到了创造性的建构。
董仲舒神秘的“天人感应”哲学,从思维层面看,其实则是儒家的“比德思维”、楚骚的“神巫思维”和道家(包括易学)的六合思维的混合物。它通过意识形态化的途径向诗学发力,结果便使一种宏大叙事的诗学模式以“政治诗学”、“国家诗学”的面目隆重登场,这就是著名的汉赋。汉赋的特点是“铺采摛文”,夸张扬厉,辞藻富丽,结构宏大。也就是《西京杂记·卷二》记载的司马相如所言:“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苞括宇宙,总揽人物”,便同六合、天地相对接了。具体的行文特点则是:时空的全整化,如司马相如《子虚赋》记楚王游猎,从出猎、射猎、观猎、观乐,一直到夜猎、养息,呈现的是一个活动的全息性图景;写云梦泽中的小山,从“其东”、“其南”、“其中”、“其西”,一直写到“其北”,用全面的空间图景框架结构起一种超时空的“宇宙想象”。足见,汉赋模式所祖述宗法的仍然是六合思维与天地境界。
文学发展到陶渊明的田园诗,六和思维与天地境界的叙事模式又有了一种新面貌:从田园到“天地”之境或田园的“天地境界”化。《饮酒》其五可为代表:“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显见,这里的“田园”是比较特殊的,诗人在这里可以终日与南山为邻,与飞鸟相伴,既可悠然采菊,又能领赏山野佳气。而这一切的根由则在于诗人的“心远”和得“真意”。“真意”根源于“心远”,而这“心远”则应是游心于物外的天地境界使然。这种用田园装点的境界与庄子在“道境”上契合,后又在山水诗和人物品藻中转化为纯净的“自然美”,是道成肉身,道直接消融在山水和人的身体之中。如“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任诞》)“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言语》)
在唐诗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刘希夷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代悲白头翁》)、张若虚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春江花月夜》),所传达的正是宇宙之思、天地之问。而李白的“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杜甫的“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等都可看出“天地”叙事模式的影子。
宋代苏轼“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特别是他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都渗透着一种宇宙之思、天地之问,而且是直叩“青顶”,显出一种以天地境界为趣的高越风致。同样,这一高远的哲理风致也贯彻在他的散文中,如“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我皆无尽也……”(《前赤壁赋》)等,文中所明显内含的“万物齐一”、与天地同道的神思理味是不难感受的。
宗白华先生在《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一文中谈及:“诗人对宇宙的俯仰观照由来已久,例证不胜枚举。汉苏武诗:‘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魏文帝诗:‘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曹子建诗:‘俯降千仞,仰登天阻。’晋王羲之《兰亭诗》:‘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又《兰亭集叙》:‘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谢灵运诗:‘仰视乔木杪,俯聆大壑淙。’而左太冲的名句‘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也是俯仰宇宙的气概。(49)他还指出张孝祥的词句:“万象为宾客”是对空间之超脱,“不知今夕何夕”是对时间的超脱,(50)这两个超脱所采用的仍然是六合思维与天地境界的“叙事”模式。
中国这一特定的叙事模式在戏剧和小说作品中也同样存在。如关汉卿《窦娥冤》有这样的唱词:“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呼天抢地,问天责地,几乎是《离骚》“上下求索”式的“天问”之戏剧版。孔尚任的《桃花扇》更为典型,这也是一个悲剧,但悲剧的原因却与别的剧不同。全剧结束时的最后一首诗这样写道:“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完全是悲观无解的调子,没有一点亮色,不同于《窦娥冤》最后还有“三年亢旱”、“六月飞雪”。而更重要的是作品把悲剧的原因推向了宏大的超主体的非人力所可企及的“世界本体”。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这个大的悲剧背景就是明朝从衰败到灭亡的历史过程……故事中真正的悲剧灾变是南明的覆亡,这一灾变对侯、李二人的情感生活当然要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故事中悲剧的主要后果。至于最后二人斩断情丝披发入山,显然不是一个情感挫折的问题,而是作者对整个人生悲剧寻求最后解脱的答案……伦理主体的不幸是殉道……情感主体的不幸是殉情……《桃花扇》中主人公们的不幸却是对虚无的确证。这种观念体现于整个故事中主人公作为悲剧主体的无能为力上……《桃花扇》中的悲剧主体是历史-哲学主体……《桃花扇》的悲剧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的社会政治题材,更重要的在于通过作品中的世界图景所显示出来的悲观主义哲理意蕴。”(51)
这种悲观主义、虚无主义,过去我们多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今天看来是不对的,因为这其实所关涉的是作品的最后境界问题,作品把自己的终极指向“虚无”,看似消极空洞,而实际上却是更高一筹的处理手法,因为这“虚无”不是别的,它往往就是“世界本体”本身,或换言之就是那个最高的“道”、“宇宙主体”,同时也就是超人世又含人世的“天地境界”。
这种境界早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三言”、“二拍”等作品中出现了,及至《红楼梦》则达到了它的顶峰。《红楼梦》在一开篇即开宗明义说出故事的来由:女娲补天,遗落灵石一块,在人间自怨自艾,“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可以看出,故事最初源自“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那块“弃石”不能补天,只好历世,这本是个哲学人类学的命题,可是却被作者罩上了一层虚无的色彩。故事虽为石头亲历,然却是因了“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的帮助才得以实现的。或者毋宁说这故事的第一生产者根本就是这两位槛外之人。接下来,则是经空空道人抄录,改“石头记”为“情僧录”,吴玉峰题为“红楼梦”,东鲁孔梅溪题为“风月宝鉴”,曹雪芹题为“金陵十二钗”,脂砚斋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以上又可以看做是对叙述者的交代:这不是一个叙述者,而是一个叙述群体。受小说评点的影响,作者把评点的环节(脂砚斋)也考虑了进来。以上交代传达给我们这样五点信息:(1)故事起源于神话传说。(2)故事文本不是线性的时间链条,而是复数的时间厚度叠加起来的,其多重的叙述者消解的正是单维的时间链,所建构的却是循环的、空间化的不变历史。(3)从“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到脂砚斋,从“石头记”再到“石头记”,中间虽经空空道人等四度易名,最后仍复归原初,说明易名之举始于“空空”道人本身,就意味着徒劳。而文本第一生产者即为“茫茫”、“渺渺”,全是空虚意象。因此,(4)文本一开始就为作品奠定了统御总体的境界:空幻、虚无。加上书中关于西方灵河、太虚幻境等描写,我们完全可以判定,《红楼梦》中最高的“世界图景”不是别的,就是本于佛道自然或太虚本真的“天地境界”。(5)同时还可认定:脂砚斋非他,同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空空道人、吴玉峰、东鲁孔梅溪一样,也是作者虚构出的叙述者。把他作为最后一个叙述者的原因可能源于作者认为小说只有经过阅读评点才算最后完成,这无疑是受金圣叹等小说评点诗学的影响所致。
从时间空间化角度看,《红楼梦》共有四个世界:现实世界(历史时空,大观园以外的现实生活)、理想世界(理想时空或幻想时空,即大观园生活)、佛道世界(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西方灵河、太虚幻境。是理智或认识时空,即本文所说的“道境”或“天地境界”)、神话世界(女娲造人神话,为神话时空,是历史时空的附属,因为在中国古史中,神话传说已被整合为古史之源)。在这四重世界中,叙述动机虽来自神话世界,但真正具有推动力的却是佛道世界,而且主人公最后也被规定为向这个世界回归:来彼大荒,归彼大荒。要之,道境大荒才是真正统摄文本总体的“最高结构”。历史时空、理想时空、神话时空,最后都化归于这个最高的本体时空:天地境界。一部《红楼梦》的道枢、玄机就在于此。
中国式的叙事模式:六合思维与天地境界,由易与老庄开其端,经屈骚、《史记》承其后,至《红楼梦》可谓发展到了顶峰,《红楼梦》是这个模式的最后完成者和总结者。中国叙事学于此找到了最经典的安顿处。
六合思维与天地境界是我们民族组织、表述并记忆信息的共同方式,它叙述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共同体,同时也生产着它本身……张岱年先生说:“中国哲学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个无形而连续的气联结起来的息息相关的整体,如《淮南子》说:“万物有以相连,精祲有以相荡。”精祲即渗透到万物之内的精气,它和存在于虚空中的气连成一片,不断地运动,万物也就在这种气的海洋中相互激荡。对于万物之间这种普遍的联系、普遍的相互作用,中国哲学谓之“感应”。中国人早就发现,乐器可以共振、共鸣,阳燧可以聚焦日光,磁石可以吸铁,琥珀可以“拾芥”,某些海生动物随月的圆缺而盈缩,“日月吸地海成潮”,对于这些现象,中国哲学统统以感应论解释之。”(52)
移而言之:有天地境界的文本在气化哲学的土壤里又是天人感应、天人对话的文本。
最后还是让我们用这样的表述来作总结:“凭借着各种各样的语言、图像、姿势等形式,人们的叙事无所不在。它们的身影可以出现在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小说、史诗、历史纪录、悲剧、戏剧、喜剧、笑剧、绘画、电影、照片、彩色玻璃窗、滑稽剧、报纸以及谈话之中。”(53)除了以上域界,中国的叙事还以六合思维与天地境界的模式存在。
注释:
①学界一直有把中国现代性发端的时间不断前移的趋势,比如上推至“甲午海战”、晚明,甚至“两宋”,如所谓的“内藤湖南命题”,即认为宋代为中国的“近世”,中国在唐宋已开始转型。可算不同之见。
②杨义:《中国叙事学的文化阐释》,载《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③见杨矗:《中西哲学的元范型阐释》,《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④杨义:《中国叙事学的文化阐释》,见《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
⑤参见蒙培元:《“接着讲”与“天地境界”》,载杨矗《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5-407页。
⑥参见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⑦参见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0页。
⑧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0页。
⑨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9页。
⑩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11)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3页。
(12)均参见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3)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雯妍、张亚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45页。
(14)见《“叙事学研究”专栏开篇辞》,《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
(15)高小康:《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16)参见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17)张岱年:《文化与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
(18)于希贤:《法天象地》,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第6页。
(19)参见杨矗:《中西哲学的元范型阐释》,《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20)李存山:《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页。
(21)李存山:《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页。
(22)张载:《正蒙·太和》,引自郭齐勇《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77页。
(23)张载:《正蒙·太和》,引自郭齐勇《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80页。
(24)李存山:《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1、15页。
(25)孙熙国:《先秦哲学的意蕴》,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26)张立文主编:《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27)冯友兰:《关于哲学的两个问题》,《老子哲学讨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8)孙熙国:《先秦哲学的意蕴》,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76页。
(29)叶舒宪:《老子与神话》,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4页。
(30)孙熙国:《先秦哲学的意蕴》,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76页。
(31)参见叶舒宪:《老子与神话》,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0-51页。
(32)参见皮朝纲:《论“论味”》,载李天道主编《古代文论与美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33)皮朝纲:《论“论味”》,载李天道主编《古代文论与美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83页。
(34)笠原仲二:《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引自蒲震元《中国艺术意境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7页。
(35)蒲震元:《中国艺术意境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4页。
(36)汪涌豪:《范畴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37)王一川:《文学理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8页。
(38)彭锋:《诗可以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5-140页。
(39)参见汪涌豪:《范畴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66页。
(40)转引自童庆炳等:《中华古代文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329页。
(41)庞朴:《原象》,《庞朴文集》第4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0-236页。
(42)参见汪涌豪:《范畴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76页。
(43)叶燮:《原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1-22页。
(44)参见蒲震元:《中国艺术意境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2-113页。
(45)参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冯友兰卷》(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30-531页。
(46)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6页。
(47)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7页。
(48)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4页。
(49)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1-112页。
(50)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7页。
(51)高小康:《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0-67页。
(52)张岱年:《中国文化论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6页。
(53)奈杰尔·拉波特、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雯妍、张亚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