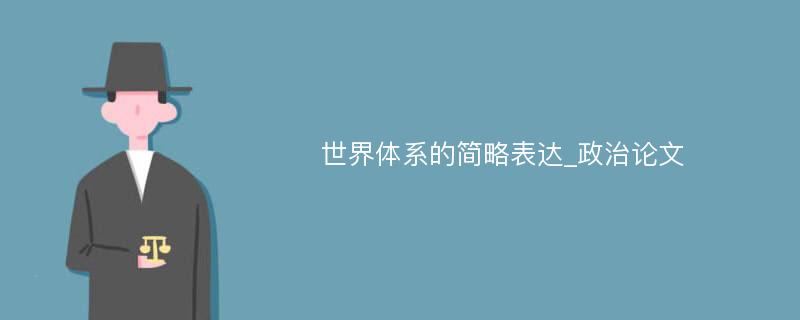
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简要论文,体系论文,天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8)10-0057-09
一 天下的重构及其疑问
天下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中国思想关键词,它作为理论概念的含义与作为日常语言词汇的含义有密切关系,但不完全相同,即使就其深层的理论含义而言,各家的理解也会有某些出入。对于一个基本思想概念来说,意义的分歧和演变是正常的,这正是基本概念具有巨大思想潜力的表现。一般地说,天下概念在中国古代周朝时期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春秋战国时百家仍然主要沿用其政治含义,但儒家又强化了它的道德意义。秦汉以后,政治制度发生根本变化,天下观念与政治实践脱节而失去了实质的制度性意义,基本上退化为政治和道德的象征和想象。直到明末黄宗羲等人才对天下概念进行反思,主要是对天下的政治古意的怀想。现代则有梁漱溟把天下意识看做是中国区别于西方的一个文化特征。毛泽东思想中那种“放眼世界”的自觉意识以及试图让全世界人们团结起来的国际努力也表现了天下意识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实践意图。
笔者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从哲学角度去开发天下概念所蕴涵的中国政治哲学原则,并且试图重构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天下理论。国内外一些学者对笔者所重构的天下理论既有所支持也有所批评,①其中包括以下三个疑问:(1)天下理论暗含了中国领导世界的想象,如“中国治下的和平”的野心(柯岚安的说法);(2)天下理论并非对古代天下概念的写实,而是在歪曲的基础上重新构思的天下;(3)天下理论隐瞒了中国“华夷之辨”的观念。
疑问(1)完全是一个误读。天下理论非常明确地说明了天下体系是一个反帝国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向世界万民平等开放的政治体系,天下不仅“无外”而且“为公”。这种误读可能来自西方学者对“中国威胁”的过度联想。除非故意误读,只要忠实于文本,这种误解即可消除。此类误读还可能来自一个未予明示的原因,西方价值观长期处于垄断地位,一旦发现某种超出了西方思想框架的新观念,就难免有所疑心和不安。
疑问(2)是有意义的。笔者愿意承认,天下理论确实并非古代概念的完全写实,不过仍然源于古代思想,是古代思想的一种当代演变。事实上任何一个重要观念都是开放性的概念,其意义都在不断演变,就像希腊民主不同于现代民主,古代人的自由不同于现代人的自由(贡斯当的说法)。所以对天下观念进行重新创作,是为了面向未来并且适用于未来。一个古代观念能够不断被赋予当代意义,这正是古代观念的活力所在,否则只是博物馆里的文物。
疑问(3)是对不同问题的一种混淆。就像西方思想体系中包含着各种互相矛盾的观念,中国思想体系中也包含许多互相矛盾的观念。问题是,天下观念与华夷观念是两个不同的观念,它们代表了不同的问题。在讨论天下观念时不一定非要讨论华夷观念(其实笔者在《天下体系》一书中已经分析了华夷观念的错误)。毫无疑问,华夷观念是一个错误观念,应该被纠正。一般地说,盛行天下观念时,华夷观念就比较淡化;盛行华夷观念时,天下观念就被削弱。进一步说,天下观念本来就意味着反对华夷观念。
在这里,笔者愿意对天下理论进行一个非常简要而明确的说明,以便阐明相关的各种问题。请原谅在此没有对众多学者的一些细节批评逐一回应,因为那样的话将使文章非常琐碎,而且许多细节问题涉及主观解读和理解,并没有客观或标准答案。另外,笔者提出的天下理论本来就不是对古代社会的一个历史描述,而是试图利用古代资源提出一个当代问题和当代思路,以此期望理论创新。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种种弊端,比如缺乏个人权利和民主,当然是事实,但这是需要另文讨论的问题,②与我们这里所关心的世界政治问题并无直接关系。总之,与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一样,天下理论不可能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科学理论,它只不过试图提供思考政治问题的一种视角和思路。至于天下理论如何成为制度设计,这是许多人的一个疑问,其实也是笔者至今没有想透的问题,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新事物很多,一个比较好的制度设计远非哲学所能独立完成的。
二 政治理论必须足以覆盖任何政治问题
国际社会至今一直是无政府状态,或者说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不过霍布斯对自然状态里人人互相为敌的想象太过夸张,既不真实也不合理。荀子也有一个自然状态理论,可能比霍布斯的设想更符合现实。荀子相信,出于生存需要,人们从一开始就必须有合作关系,即一开始就有“群”的存在,共存是任一个体得以存活的条件,于是,人际冲突并非源于独立个人之间的争夺,反而是群体内部关系所导致的矛盾。人们首先合作而成为群体,而人人要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都试图多占与他人合作所共同创造的财富,为了多占便宜就必须把他人的利益最小化,因此,恰恰是合作之后出现的如何分利的问题才导致了冲突。就是说,合作先于冲突,而且正是由于合作——不公正的合作——才又导致冲突。③不过,尽管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设想对于人际关系是夸张的,但如果把它改造成为群体之间关系的自然状态,就比较合适了,而且能够用于表达国际状态。这样,荀子和霍布斯的问题就形成了互相配合。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有理由提问:人类是否能够作为一个总体的群而合作?在人类的合作中又如何能够保证合作压倒冲突?或者说,是否存在着对人类冲突的一个普遍有效的合作解?天下理论就是在寻求对人类冲突的普遍有效合作解。
中国政治概念是社会性的而不是国家性的,中国哲学家普遍相信政治的目标是形成“治世”而避免“乱世”。“治”被认为是实现政治的任何其他目标的必要条件,而“乱”则破坏一切好事。因此,“治”是中国政治哲学的第一原理。这一点对理解中国政治非常重要。一个“治世”未必是一个最好的社会,也未必是人人满意的社会,因为无论什么秩序总会限制某些自由。但只有在“治世”条件下才有可能去改善任何事情,因此,“治世”被认为是任何好社会的出发点和基本保证,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政治家最关心的总是社会稳定。
有人请教孔子什么是政治,孔子的回答是“政者正也”④(意思是“摆正各种秩序和关系”)。孔子的政治定义表达了中国对政治的典型理解,它与西方政治概念的着重点有所不同,既不同于希腊的城邦国家(polis)和罗马的共和国家(res publica)或者罗马帝国的“罗马治下的和平”,也不同于马基雅维利的超越了道德的政治,不同于霍布斯和洛克以来的权利为本的政治,更不同于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以敌人意识为主导的政治。对于中国思维来说,各种事物、各种人之间关系的正当性就是政治的根本问题,只有优先明确了关系的正当性,才能够进一步明确政治实体(比如个人)的权利和利益的正当性,因此政治总是以道德为标准的,政治是达到道德的途径,道德是政治的目的,政治则是道德的制度条件。政治试图以制度去治理人性,这里的制度不仅包括法律和权力体制,还包括文化制度,即所谓“礼乐”。孔子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⑤孔子将人情比做需要耕作的田地,如果不予耕作,人情之田就会杂草丛生,所以需要以秩序、责任、知识、仁爱以及美学经验去引导人性。可以看出,中国所理解的政治不仅事关利益分配,而且事关精神品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政治关心的是共同幸福的社会条件,而不是个人自由的国家条件。
可以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秩序的“社会”而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国家”,尤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中国的传统社会没有一统心灵的宗教,因此没有宗教性的边界,也不具有国家的那种主权边界。社会是一个可以无限延伸扩大而连续展开的文化—生活空间,不同社会之间的过渡是模糊的混合交融,就像两条河流的汇合,因此中国政治思想中没有不可兼容的他者,没有不共戴天的异教徒,没有不可化解的绝对敌人,即卡尔·施米特意义上的公敌或者绝对敌人(hostis)。社会可以无限扩大,文化可以无限交融,所以政治也可以无限延伸。如果一种政治完美到万民归心,就将成为整个世界社会的政治。这个“世界性社会”被称做“天下”。这是中国在三千年前出现的一个政治概念(最早见于《尚书》和《诗经》),它表达了中国的政治世界观。
按照天下理论,当一个社会为全人类所接受,它就成为世界。根据这个标准,目前的无政府“世界”就仍然没有成为世界,或者说,政治意义上的世界还不存在,而只有地理意义上的世界,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个非世界(non-world),所以国际冲突不断而且无法解决。巴以冲突模式是一个最能表现问题的隐喻,它暗示了西方政治思维无助于解决甚至反而导致了各种深刻的国际冲突或者文明冲突。关键之处就在于西方政治思维看不到在国家之外还存在着世界公利,所以不可能发现国际冲突和文明冲突的合作解。西方现在又强调人权高于主权,这更加不是国际冲突和文明冲突的合作解。个人是比国家更小的基层政治单位,如果真的以个人权利去解构国家主权,只能导致效果更差的霍布斯状态(甚至达不到荀子状态),很显然,人权的合法性如何证明?哪些具体权利项目能够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而哪些又不能?每个人都需要的社会公共空间如何规定?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一切由谁又根据什么说了算?这些问题都是人权政治无法解决的,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落在“个人”这一政治单位之外,甚至落在“国家”之外。天下理论强调必须把“世界”当做一个政治分析单位,就是为了建立一个足以覆盖任何政治问题的分析框架。如果不能建立天下政治,就必定有一些要命的政治问题逃逸在外。
由于早期社会的政治经验不同,西方和中国各自发展出在分析框架、问题体系和价值观上都有很大差异的政治思想传统。西方政治是从城邦国家(polis)和共和国家(res publica)开始的,因此西方政治思想的出发点是“国家”,西方现代政治又追问自然权利,因此又突出了“个人”。西方政治问题就在“国家—个人”这一空间中展开,其最大伸展度无非是“国际(international)”。正如前面分析的,西方政治框架对于可能出现的政治问题来说太小了。中国政治是从“天下”开始的,因此中国政治思想的出发点是“世界”,同时中国又以“家”作为基层政治单位,因此中国政治问题就在“天下—家庭”的空间中展开,而国家是一个中间层次,所谓“家国天下”。不难看出,中国政治思想空间的伸展度明显大于西方。天下意味着关于世界总体的一种政治观点,而国际至多意味着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
不同的政治出发点决定了对政治问题的不同理解,这种差异本来意味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应该能够形成良好的互补。从思想结构上看,中国思想更有开放性,更能够包容西方思想,因为天下已经是一个最大的思想尺度和政治空间,任何问题都可以进入并且被重新反思,即使是对中国思想形成挑战的问题。与此相反,西方思想在遭遇中国思想时有一种不适,因为许多问题落在西方的思想框架之外,比如说,天下问题显然就是国家或者国际框架所无法表述的。当然,西方也有一个与天下具有同等伸展幅度的观念,那就是基督教的上帝或者上帝之城,可是属于“天上”的上帝之城在地上不可能完成(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都说明了这一点),它是上帝的政治而不是人的政治。中国试图建立一个“天下”的政治普遍概念,“天下”如果成为可能,天上的上帝之城就将失去政治意义,这对西方思想形成一个难以接受的挑战。这一挑战的实质就在于,西方所谓的普世主义的理由是虚构的,无论是天国还是自然法都是虚构的,并没有实在证据能够给予证明,而且,即使不是虚构的,也没有必然理由能够证明上帝之法或自然法对于人类社会的必然有效性;而中国普世主义则只在人间寻找根据,仅仅从人之间的共存关系去发现普遍原理,显然,人间证据是唾手可得的。人的问题只能在人间得到解决,而不可能在上帝那里或者在自然权利那里得到解决。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⑥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⑦都是这种人间精神的表现。
从理论结构上看,以中国思想去兼容西方思想,从而形成一种丰厚的新思想是更为可能的。笔者愿意相信,西方政治思想的成就主要是在国家理论上,它在国家的合法性和政治权力结构等问题上有着出色的成就,但在国际政治方面的思路却比较可疑,几乎无法解决国际社会的霍布斯状态,当然也就更不可能去解决世界总体的政治问题。与此相反,中国政治思想的长处却在世界理论上,它对解决世界总体政治问题有着深远的潜力,但在国家政治观念上却比较薄弱(这是需要加强的)。因此,如果以国家为核心的西方政治思想能够与以世界为核心的中国政治思想走向一种良好的会面和融合,很可能就会形成一种在理论上更全面、更有效的政治思维。
如前所论,全球化所引发的许多世界性的新问题无法在“国家—国际”这一框架中被有效地分析,因为“国家—国际”这一框架不够大,而且缺乏世界公共性或者世界公心,于是,涉及世界总体的政治问题(比如,世界公利、世界制度、世界合作、世界治理以及文化冲突等问题)就很难在国家—国际理论中被正确而公正地讨论。因此,政治理论需要一个结构性的改进。如果引入天下这一维度,就可以把政治理论由“国家—国际理论”扩大为“世界—国际—国家理论”,这样才能包含所有的政治问题。在今天,尤其在未来,以国家—国际理论为眼界的政治理论已经越来越不够用了,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问题越来越变成世界政治问题,这意味着需要一个“政治学转向”,把政治分析的重心转到世界政治上,于是,一个以世界政治问题为核心的政治理论对于未来政治可能是更合适的。
三 一个从世界问题出发的古代故事
这里需要讨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故事,其重要性类似雅典城邦国家(polis)的故事。与西方的政治历史不同,中国政治不是从国家问题开始的,而是从世界问题开始的。根据文献可知,从世界问题出发的政治观念是周朝的创造。在周朝之前,中国的政治状况仍然是酋长部族的松散合作关系,圣王只不过是各部酋长自愿或不自愿承认的强势盟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君主。⑧周朝创造了天下体系,试图把世界看成一个完整的政治单位去治理,而天下体系就是世界制度。三千年前的周朝政治为什么会从世界问题开始,而不从国家问题开始,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似乎不合常理。通常的情况应该是部族演变出国家,因此,人们首先发现国家政治,这才是自然而然的。以世界问题为核心的政治思维不仅在古代是一个独特的超前创造,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很前卫的政治观念,它所提出的政治问题甚至超出目前的政治现实而属于未来。那么天下体系的故事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它一定有特殊的原因,否则难以理解。
在殷商部族体系中,周是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的一个小部族,人口最多6万~7万,战车300乘而已。⑨周文王和周武王成功联合了西部和中部的许多小部族,但与盟主商朝相比仍然很弱。商在东部的核心领地是最发达地区,人口超过百万。周武王领导友邦兴兵攻商,虽然商纣王军队远远多于周联军,但商纣王一向暴虐无道,大失军民之心,结果是大部分部队哗变倒戈,以致周武王一战成功。⑩周虽夺取了领导地位,但殷商遗民人数众多,其心未稳,而且还有许多亲近殷商的部族以及一些本来就桀骜不驯谁都不服的部族。据说当时部族多达800~1000个以上,(11)而且属于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既有农耕民族也有游牧民族,可能既有黄种人也有白种人,文化更分东西南北。因此,以小邦而居万邦主位的周政权面临一个全新的挑战性政治问题:如何能够做到以一治众并且以小治大?
传统的以一治众的模式总是由一个最大、最强的霸主来实现的,这是自然的统治方式。但周乃小邦,本部人口非常有限,这意味着在发生变乱的情况下绝对可靠的“自己人”并不多,这显然不适合采用传统的霸主或盟主的统治方式,周朝政府不得不以谦虚审慎的态度去思考如何设计一个能够让众国万民都愿意承认和接受的全新政治制度,以制度的优势和吸引力代替武力的威慑。这个新制度要求做到:无论存在多少部族和多少种文化,这个新制度都能够获得人们的普遍同意和支持,能够摆平各种可能的冲突。只有当所有部族承认的是一种普遍制度而不是一个特殊权威,周这个小部族才有可能代表这个制度去管理世界。正是“如何以小治大”这个特殊问题迫使周去思考世界政治制度问题,于是,政治就从世界问题开始了。
这个世界制度把地理意义上的大地变成政治意义上的天下。这是“世界治理”问题的第一次提出。“治/乱”本是任何一个社会的内部问题(如一个部族或者一个国家的内部秩序问题),而对于外部关系,一般是采取武力威慑甚至征服的策略。但周朝发现,当一个大规模社会包含着各种文化和各种共同体时,就必须去创造一种普遍有效的制度,否则不可能获得天下人心,也就是说,世界不可能通过征服去得到,而只能通过一个普遍承认的世界制度去创造出来。世界制度先于世界,只有当创造了一个世界制度,且这个制度对各个国家都有好处,以至于各个国家都愿意加入这个制度时,这样才拥有了世界。世界政治成为国家政治的必要条件,有序世界成为有序国家的必要条件,世界之治成为一国之治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中国政治思想的关键所在。根据《尚书》等文献,周朝的“世界制度”是周公和召公为首的周朝高级智囊集团的创作。
在古代,由于交通与地理知识的限制,人们所知道的“世界”只不过是今天中国的一部分而已。尽管人们所知道的地域不大,但它是被当成“世界”去分析的。重要的不是真实面积,而是世界意识。周朝创造的作为世界制度的天下体系试图满足这样的基本原则:(1)天下体系是一个利益普遍共享体系,其基本信念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因此“天下无外”;(2)天下体系制度能够保证各国都获得足够大的权力和利益,以至于各国加入天下体系的好处明显大于独立在外的好处,从而使各国都愿意承认并且加入天下体系;(3)天下体系能够形成各国利益互相依存的互惠关系,如互相救难、互通有无,从而保证和谐共存关系,这是世界共荣与世界和平的条件。
周朝创造的是一种网络型天下体系,它由一个作为世界政治中心的天子之国(天子直辖特区)和大量诸侯国组成的政治分治网络。这个政治网络具有一些重要的结构特征:首先,每个局域结构都是总体结构的复制,每个局域又都是一个完整系统,因此,政治秩序既是普遍传递的(transitive),而各部分又是独立自治的。这个结构意味着,存在一个为世界秩序和世界利益负责的政治制度,同时各国高度自治,各地解决各地的内部问题,各地解决不了的大问题则求助于天子或者周边友邦,而天下体系的政治中心负责那些需要总体协调配合的世界性问题。其次,每个局域(即诸侯国)都潜在地有可能成功发展成为天下网络的新核心而取代旧核心,而制度保持不变,政治核心的变更不影响整个体系的政治性质,因此天子和诸侯都不得不“勤修德”,以此维持和增加威信。
具体地说,周朝的天下体系是一个分治而一统的分封制,其中的权力和权利分配大致是:第一,天子管理天下公共事业和公共秩序,负责促进世界利益和世界正义,并且拥有相对最大的一片土地作为直辖区(天子之国),约为一个大诸侯国的四倍面积(考虑到那时有数百诸侯,这一面积并不具有压倒优势),天子还拥有对各种不可分割给各国以及不宜由某国垄断的世界公共资源的管理权,以便维持世界公正和普遍利益,那些公共资源包括跨国的河流、湖泊、名山以及某些重要矿物(按照这个逻辑,如果在今天的话,太空、海洋、重要能源如石油、核原料等就会被考虑在内)。第二,诸侯国拥有国内高度自治权,并且有义务分担天子之国在维持世界秩序上的成本,因此必须向天子纳贡赋役。第三,天子之国拥有相对最大军力,诸侯国则按照人口和土地大小拥有成比例的军力。天子之国军力虽然最大,但没有压倒优势。制度规定,天子之国军力为6军(大概相当于现代的师),约6万至7.5万兵,大诸侯3军,中诸侯2军,小诸侯1军,如此等等。(12)这样的配置比例形成实力制衡,不可能出现超级大国。如果某一诸侯作乱,显然很容易平定,如果天子暴虐无道,几个诸侯的革命联盟就足以颠覆之。
可以看出,周朝制度的基本精神是创造世界范围的合作最大化并且使冲突最小化,同时创造优先发展世界公利的政治条件。周制度虽然优越,但具有讥讽性的是,维持了数百年的周制度恰恰最后由于其优越性而崩溃——这是今天仍然值得反思的问题。在周朝后期,诸侯们发现中央政府过于仁慈宽厚,只奖不惩,而且已经无地可用于新的分封,尤其是在经济上和军力上已经失去维持世界秩序的实力,于是,某些诸侯试图发展成为超级大国,以霸权体系去解构天下体系,结果进入长期的列强争霸时代,最后在公元前221年秦国征服了所有中原诸侯而建立了中华帝国,天下体系终结了。帝国体系虽然继承了天下体系的某些话语和观念,但在制度上却进行了根本的改变。从此天下体系成为往事,就像希腊和罗马成为往事一样。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只不过是中华帝国的形象,这是对中国思想的一种深刻误解。作为周朝思想遗产的“天下观点”尽管不再是政治实践,但仍然一直是中国的世界观,中国历代哲学家不断给予翻新的解释,笔者在这里所做的同样也是一种翻新的再创造。天下世界观一直影响着中国对政治的理解,如果不理解天下观点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的政治价值观。
四 作为世界观的天下观点
“天下”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多重含义的饱满的世界概念:第一,在地理学意义上,天下指整个大地,即人类可以居住的整个世界。第二,在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上,天下指所有土地上所有人的心思,即“民心”。人甚至比地更重要,所谓“得天下”的主要意思并不是获得了所有土地,而是说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民心(如果能够获得所有人的民心就完美了),正如荀子所说:“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13)(意思是:得到天下不是说人们献出土地归顺强者,而是说某种制度和价值观得到了天下人的一致同意)。第三,在政治学意义上,天下指的是世界政治制度。世界制度定义了普遍秩序,因此使世界政治一体化而结束世界的乱世状态。作为世界制度的天下才是天下概念的最后完成形式。管子所说的“创制天下”(14)正是这个意思。因此,“天下”所指的世界最终必须是个“有制度的世界”。总之,“天下”概念是地理学意义、心理学意义和政治学意义的合一存在,是大地、普遍人心和世界制度的三位一体。
有个古代故事,未必是真的,但很能表现天下胸怀:荆国有人丢了弓却不肯去找回来,他解释说:“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听说后评论说:要是去掉“荆”字就正确了。老子听说后进一步评论说:要是再去掉“人”字就完全正确了。(15)这一天下胸怀肯定是文学夸张的,但它仍然有着象征意义,它指出了一种以共同幸福为目标的世界观,其根本点在于,这一世界观没有排斥任何他者,而是试图把“他者”都转化为“自己人”,这是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观,想象着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16)尽管一切完美社会都是事实上不可能的,但“想象的政治”深刻地影响着“现实政治”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它是一种积极的导向,而且它也有可能会部分得到实现,这已经足够好了。
中国人推崇的政治价值观,比如和谐原则,就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天下世界观。和谐观念出现在中国第一本政治著作《尚书》(17)的第一节,最早表达为“协和”,所谓“协和万邦”,后来通常简化为“和”。两千多年来关于和谐有过许多讨论和不同理解,就像西方对正义、自由、民主等基本概念也有着多种不同版本的理解一样。在中国传统思想里,人们特别关心的焦点问题并非“和”还是“不和”,而是“和”的策略还是“同”的策略何者更能解决冲突问题。春秋时就有过关于“和”还是“同”的著名争论,大概是说:差异往往形成冲突,于是有两种解决策略,一是“同”,就是消灭差异变成只有一种格式,这个策略被认为是坏的,理由是万物如果失去多样性就都无法存活,因此,思想和文化失去多样性也同样危险;另一种策略是“和”,就是维护差异和多样性并且利用多样性去创造能够形成优势互补的最优合作关系。(18)
按照中国观点,西方的典型策略都属于“同”,因为西方总是希望能够通过“普世化(universalizing)”西方价值观去解决冲突,从基督教试图一统精神世界到现代西方试图以自然人权去统一世界的价值观,都是试图消灭价值观差异的做法。西方这种错误的政治追求很可能源于西方的一元真理观。西方主流哲学相信,对于一种事物,只能有唯一为真的真理。这种真理观对于客观事物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对于人的事实就变得非常可疑。“人的事实”是人做出来的,所谓事,就是人之所为,不同观念导致不同所为,因此,“人的事实”本身就包含了不同人的主观观念,于是,对于一种人为事实,至少存在着两种以上同时为真的真理。这样的话,解决人间冲突的唯一有效策略就只能是“和”而不可能是“同”。
在这里笔者想再次陈述关于古典和谐原则的一种当代理解(已经多次表述过了)。和谐原则的关键理由是:第一,事物的多样性是每个事物能够生存的必要条件。一种东西单靠自身不可能生存,而必须与另一些东西互相依靠而共存,于是,共存先于存在,共存(co-existence)成了存在(existence)的先决条件。这是中国式的存在论观点(ontology)。第二,各种事物只有互相配合才能使其中每个事物达到其最优状态,同样,人与人之间的互惠关系将使每个人的利益都获得改善。可以说,和谐的基本精神就是兼容才能共荣。于是,和谐策略意味着:某一方X要获得利益改进x +,当且仅当另一方Y必定同时获得利益改进y +,反之亦然。于是,促成x +的出现是Y的优选策略,因为Y为了达到y +就不得不承认并促成x +,反之亦然。由此和谐策略可以理解为一个强化的帕累托改进,它能够解决一般的帕累托改进所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只有和谐策略才能产生普遍公正的、人人同样满意的利益改进。它不仅是所谓“你有活路我也有活路(live-and-let-live)”,而且是“你有活路当且仅当我有活路(live-iff-let-live)”,尤其是“你得好当且仅当我也得好(ireproved-iff-let-improved)”。我愿意将和谐策略称为“孔子改进(the Confucian improvement)”以纪念孔子的一个简练而优美的表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9)
天下世界观以及和谐观念暗示了一种中国式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中国传统思想从来都是普遍主义的——天下概念的眼界就已经注定了这一点——绝非一些亚洲国家所主张的地方性的、特殊性的“亚洲价值”之类的相对主义(亚洲价值之类的概念根本就不成立)。中国的普遍主义是一种兼容普遍主义,它的思想基础是前面所述的中国式存在论:共存先于存在。西方存在论的分析单位是个体,因此西方的普遍主义追求的是对于每一个体普遍有效的普遍原则;中国存在论的分析单位是关系,因此中国普遍主义关注的是对于每种关系普遍有效的普遍原则。这两种普遍主义的分析对象不同,各有各的用处。由于立足点是关系而不是个体,中国普遍主义强调这样一个检验标准:一种关系或者一种涉及他人的行为方式如果是普遍有效的,那么它必须获得他人的普遍承认,并且这种关系或者行为方式必须能够经得起普遍模仿的检验,即,当他人普遍模仿这一关系或者行为时,没有任何人的利益因此受到损害。很显然,假如一种关系或者行为经不起普遍模仿而导致玩火自焚,作法自毙,那么它一定是坏的。比如说,漠视他人利益的自私的利益最大化行为一旦为他人所普遍模仿,不但自己占不到任何便宜,而且大家利益都受损。这显然就是一个经不起普遍模仿的坏策略。
五 第四种文化
既然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超级大国就成为其他国家的现实或潜在的威胁。历来西方各个帝国主义强国都是对弱小国家的威胁,特别是史无前例强大的美国,更是对整个世界的威胁。习惯于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的西方一旦发现非西方国家变得强大起来就会加倍地视其为威胁,所以对今天正在追求和平发展的中国就有一种过敏和过激反应。尽管中国声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而且历史事实也表明中国是诸大国中历来最少具有主动侵犯性的国家,但西方仍然把中国视为“威胁”。西方对中国的特殊敌意很可能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政治的习惯性敌人意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西方对中国世界观的不理解。
按照温特的说法,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存在着“三种文化”:第一种是眼中只看到敌人的霍布斯文化,第二种是以竞争代替战争的洛克文化,第三种是与朋友建立同盟的康德文化。(20)根据这个标准似乎可以说,欧盟对内是康德文化,对外是洛克文化。美国则兼有三种文化:对英语盟友们算是康德文化,对欧洲大陆是洛克文化,而对其他国家基本上是霍布斯文化,其中许多国家被美国定义为“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流氓国家”或“专制国家”等等,总之都是一些“坏”的国家。温特不支持霍布斯文化,他似乎相信,假如国际社会能够以康德文化为主流,就能够成为一个好世界。温特无疑是善意的,但问题却没有如此简单。其实,这三种文化都经不起普遍模仿的检验,因为它们终究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排斥他者的文化,而排斥他者的行为也会被他者所模仿,结果必定促进不合作。这里值得分析的是善意的康德文化,康德追求“永久和平”的思想热情一直都令人感动,但康德毕竟受制于西方政治的思想框架而无法超越通向永久和平的障碍。按照康德文化,自由国家总会与作为自己人的其他自由国家结盟,那么与那些不属于自己人的其他国家的关系又应该如何处理呢?假如其他国家既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也不愿意接受西方文化,又怎么办呢?尤其是,假如非西方国家强大起来并且反过来向西方推销非西方价值观,又怎么样呢?康德对付不了文化冲突的问题(即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那些不符合康德的结盟条件的文化和国家就仍然是分裂的世界的另一方。(21)也许在这样的情况下康德文化就只好退化为霍布斯文化了。可以说,康德文化虽有善良意愿,却在本质上同样缺乏兼容异己的原则和能力。毫无疑问,寻找朋友的康德文化总要比寻找敌人的霍布斯文化好得多,但寻找朋友仍然解决不了冲突问题,因为寻找朋友仍然做不到化敌为友,这是康德文化的局限性。化敌为友正是中国的天下世界观的基本精神,只有化敌为友才是唯一能够经得起普遍模仿的正确策略。天下观点正是西方所没有的第四种文化。
与欧洲观念相比,美国的世界观更为诚实质朴,因此也更明显地表现出西方国际政治的底牌。这一底牌就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施米特式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解,同时又是基督教式的以异教徒为敌的使命感,于是形成了一种以硬实力和软实力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对所有他者进行双重支配的霸权世界观。美国是一个新品种的帝国,它不像罗马帝国那样去扩张,也不像大英帝国那样去建立无数殖民地,它追求的不是“美国治下的和平”而是“美国领导下的和平”。“领导”甚至比“统治”更自私自利,因为统治需要付出很大的社会治理和管理成本,而“领导”则是一切利益都向自己倾斜而拒绝付出社会治理和管理成本。美国动画片《狮子王》就是美国领导的典型隐喻:世界上有坏狮子以及一些流氓动物,还有需要被拯救的无助动物,好狮子战胜困难终于打败了敌人,在秩序上和精神上领导了世界。美国文化不断在重复编造战胜各种想象的敌人的故事,其中的敌人意识如此夸张,实在令人吃惊。在这种排斥他者的美国世界观眼中根本没有世界,而只有美国之外模糊一片的“其他地方”,如果其中某个国家发展了而居然被注意到,无非就变成一个显眼的敌人,一个被想象的敌人。
中国的发展就被认为是对美国体系的挑战。近来G·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在一篇广受关注的文章中认为:(22)西方必须想各种办法诱导中国接受“西方秩序”而不要强迫中国去挑战它(西方秩序大概指由西方价值观所规定和指导的政治制度和游戏规则),因为,如果中国成为一个新的超级大国(这一点看来非常可能),这还不算要命的事情,但假如中国的野心大到不仅想成为一个西方秩序中的新超级大国,而且试图推翻西方秩序就麻烦大了,就是说,假如中国将来甚至想在价值观上获得领导地位,则是万万不可容忍的。不过,经过分析之后他给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假如21世纪的最后决战发生在中美之间,那么中国可能会占优;假如这个最后决战发生在中国和与时俱进的西方制度之间,那么西方可能会胜出。理由是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毕竟是难以撼动的。可问题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意识中恐怕没有西方这样紧张过敏的对抗想法,“最后决战”是西方典型的妄想,恐怕与基督教观念有关。在中国文化中影响最大的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里都不存在紧张对抗之类过于激动的观念,因为中国文化里没有上帝与魔鬼、信徒与异教徒之类的紧张对抗结构以及“末日审判”之类的想象。西方以西方之心去猜测中国之心就难免出现错误判断,单方面想象了一种只有自己单独上场的最后决战。
按照中国思想的逻辑,如果中国真的发达了,也不会称霸,而将更有实力去化敌为友。至于价值观方面,中国未必会如西方所愿去完全接受西方秩序,因为中国的价值观很可能会被证明是一种优越的价值观(汶川地震时中国人所表现的伟大中国精神就是一个证明),而且,中国价值就是一种普世价值。一种价值是不是普世价值,这不是西方观点所能够定义的,而只能由是否有利于普遍合作和世界公益去证明。中国也不会拒绝吸收有益的西方价值观,因此,最可能的情况是,中国将综合中西价值观而完成一次价值观创新,而这正体现了天下观念的兼容性。古人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23)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24)这已经非常明确地说明了,如果不能兼容他者就是否定世界。笔者相信中国式的存在论是对的:共存先于存在而且是任一存在的条件,而以某种独立存在为根据的眼界是看不到世界的。因此,笔者也相信基于关系眼界的中国价值观是对的,它是克服冲突的一个良好思路。也许中国古代的天下体系制度对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合适了,但它的思想遗产仍然具有启发性,我们可以重新想象一个能够创造世界共同利益和共同幸福的新天下。老子说:“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25)这就是说,要理解世界,就必须以世界观点去看世界。老子可能说对了。
[收稿日期:2008-05-15]
[修回日期:2008-07-06]
注释:
①对笔者的天下理论的评论在此不便一一罗列。其中包括有:[美]柯岚安(William A.Callahan):《中国视野下的世界秩序:天下、帝国和世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49~56页;Aain Le Pichon:Philosopher Kings,欧盟—中国社会科学院“治与乱”国际会议论文,2007年3月,北京;郗士(Francesco Sicsi):《战争与秩序》,载赵汀阳主编:《年度学术200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49页;Shijun Tong,"Chinese Thought and Dialogical Univesalism," in Gerard Delanty,ed.,Europe and Asia beyond East and West,London:Routledge,2006;周濂:《天下体系的两条方法论原则》、张曙光:《天下理论和世界制度》、干春松:《天下,全球化时代的托古改制》、王峰:《天下观的冒险》(以上四篇文章均载《中国书评》,第5辑,2006年,第5~49页);徐建新:《最坏的国际关系理论与最好的天下理论?》,载《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2期,第113~142页;屠凯:《对康德永久和平理念的批判研究以及“天理民彝”:汉语文明构想的世界法律秩序可能》,载《清华法治论衡》第七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弊端的批判,参见赵汀阳:《反政治的政治》,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12期,第30~41页。
③《荀子·王制》。
④《论语·颜渊》。
⑤《礼记·礼运》。
⑥《左传·昭公十八年》。
⑦《论语·卫灵公》。
⑧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6页。
⑨许倬云:《西周史》,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7~78页。
⑩《尚书·武成》。
(11)《史记·陈杞世家》:“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吕氏春秋·观世》:“周之所封400余,服国800余”。
(12)《周礼·夏官司马》;《左传·襄公十四年》。
(13)《荀子·王霸》。
(14)《管子·霸言》。
(15)《吕氏春秋·卷一·贵公》。
(16)《札记·礼运》。
(17)《尚书·尧典》。
(18)《国语·郑语》。
(19)《论语·雍也》。
(20)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chapter 6.
(21)屠凯对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有一个特别清楚的批判,参见屠凯:《对康德永久和平理念的批判研究以及“天理民彝”:汉语文明构想的世界法律秩序可能》,载《清华法治论衡》第七辑,2006年版。
(22)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Vol.87,No.1,2008,pp.23-27.
(23)《吕氏春秋·卷一·贵公》。
(24)《六韬·武韬·顺启》。
(25)《道德经·五十四章》。
标签: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周朝论文; 尚书论文; 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