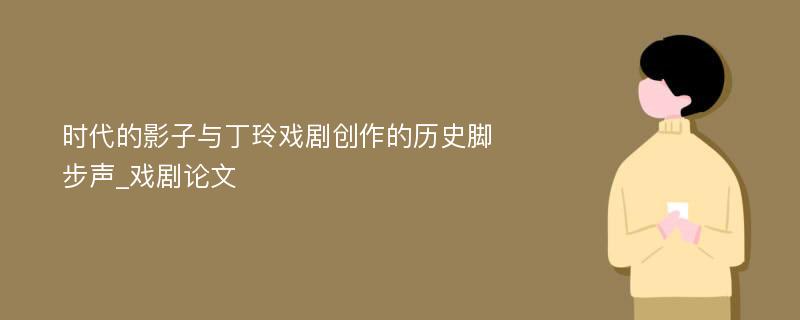
时代的影痕 历史的足音——论丁玲的戏剧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足音论文,戏剧论文,时代论文,历史论文,丁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236(2007)04-0037-05
丁玲是向以小说创作闻名中外的作家,散文、报告文学在她的全部创作中也占有重要位置,颇有影响。但可能许多人尚不知她还兼剧作家,写过三个剧本,并在其问世当时具有一定号召力、影响力,是丁玲著作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丁玲在《丁玲戏剧集》[1](P1)一书的“代序”:“我与戏剧”和一些剧评中剖白了自己与戏剧的关系、缘分。她虽然总是谦称“我对戏剧是外行”,“只是一个‘戏剧爱好者’”、“热心的观众”,但其实她确乎是个编、导、演、评四者集于一身的全才戏剧家。她读过王尔德、易卜生、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看过梅兰芳、欧阳予倩、洪深的戏,扮演过丫环、八路军女宣传员粉墨登场,导演过歌剧《刘三姐》,评论过《打红台》、《陈毅市长》等戏。她不是一般的戏剧爱好者,而是酷爱戏剧艺术的作家,她对剧艺感触的神经特别敏感易动。她回忆说幼年“偶尔看一两次戏”,便“很受感动”,被“迷住了”;在延安时“真正对京剧发生兴趣”;解放后“只要一有演出,我总希望看到。”看罢沙叶新的《陈毅市长》觉得“他们给了我最高的艺术享受”,“不愿克制自己看戏以后的激动,更不愿在好戏面前保持冷漠”,所以马上欣然命笔写出该剧剧评。可见丁玲动笔从事戏剧创作是渊源有目的,同她毕生对戏剧的热爱、偏爱是分不开的。只不过因为她已选择了以写小说为主攻方向的创作道路,且时间和精力有限,故没有专事戏剧创作,戏剧创作成果不丰。丁玲一生共创作了三个剧本,外加一个应中央电影局局长袁牧之之约赶写的反映抗美援朝的未投拍的电影短片文学剧本《战斗的人们》。
1937年8月完成于延安的独幕话剧《重逢》写抗日战争中发生在日寇占领的小城敌特密室里的一场生死较量。四位抗日军政干部被日寇逮捕,在遭敌人杀戮前三位年长的同志要求19岁的年轻女干部白兰伪装本地中学生潜伏在敌人心脏,继续为党做地下工作。白兰受命自存与敌人周旋,被日军特务部队长山本看中,欲强纳为妾,命其部下情报科长马达明从中说服。白兰与马达明恰巧原来是一对恋人、战友,白兰以为马达明变节投敌,气愤之下手刃马达明。死前马说出自己乃是受我党组织派遣打入敌营工作的真相,白兰悔恨含悲带着马收集的敌人情报和钥匙从虎口脱险。此剧原载《七月》,以情节紧张曲折制胜,演出效果甚佳,颇受好评,曾在国立戏剧学校和延安、山西、西安等许多地方上演,并被译成英文,还在印度演过。
1938年6月作于西安的三幕话剧《河内一郎》表现“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热恋故土的日本士兵河内一郎原本厌恶侵略战争,但出于愚忠“天皇圣战”,被强制绑上战车,充当日本军国主义炮灰。在兵败被俘后受到八路军的宽大优待,在我军俘虏政策的感召下忏悔反省,转变立场,终于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走上联合反战的光明之途。写此剧过程中曾得到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同志和著名戏剧家塞克、作家端木蕻良的帮助,在延安协助我军工作的日本友人泽村利胜先生“看后说很感动,并且修改了我(作者丁玲)画的舞台面。”[2](P72)该剧流传到国统区,在多处演出过。
三幕话剧《窑工》是1946年春在张家口完稿,系与她的战友逯斐、陈明合作。该剧描写“八·一五”抗战胜利、光复前后,发生在河北宣化某瓦窑厂底层广大劳工同日本帝国主义掠夺者走狗、工贼之间展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森下瓦窑厂经理张永泉仗恃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大施淫威,对工人重利盘剥、欺诈打骂、虐待、残杀,无恶不作。工友们不堪忍受,奋起反抗,最后在日本主子垮台之后,在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府支持下彻底清算严惩了“活阎王”张永泉的滔天罪行,实现了翻身自主。
综观丁玲的三部剧作,其总体共同特征还是鲜明可见、不难梳理概括的:
一、创作动机:战斗任务的驱使、革命工作的需要。
丁玲之所以“触戏”,皆缘起于工作任务的需要:写《重逢》是因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央军委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任命丁玲为主任。“西战团除了写通讯报导以外,主要是各种形式的宣传演出,并且常常以话剧为主。这样我不能不参与剧本、审查节目,或者动手写。”[3](P5)“那时召开一个剧本的创作会,分配我写一个女青年在敌占区,在特殊条件下努力开展新的工作的。”[4](P71)于是便有了《重逢》;写《河内一郎》“也是战地服务团同志们的包围和催促。缺乏剧本是实情,我们又准备到西安去,到西安后,总要一个像样点的剧本,于是我就着手写。”[5](P71);写《窑工》时,“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不久,全面内战的危险迫在眉睫。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巩固胜利,巩固新区,这成为当时的严重课题。出于一种责任感,逯斐、陈明,我们三个,不顾长途行军后的疲劳,也不考虑人地的生疏,便赶到宣化采访材料,匆匆写了此剧。”[6](P5)可见,丁玲写戏的动机正如她所说:“都不是我本人在生活中有什么灵感,也不是经过仔细酝酿构思、精雕细刻出来的作品,而只是适应宣传工作的需要,完成戏剧组分配给我的一项写作任务。”丁玲写戏既是战斗任务、本职工作的需要、“逼迫”,又是她素来对戏剧的天然爱好使然,也是她深厚的文化底蕴积淀的果实。她的剧本是货真价实的“遵命文学”,自觉听从无产阶级将令,“演戏需要剧本,她就写;戏里缺角,她就粉墨登场。”[7](P2)写戏从另一个侧面见出作为一个直接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士的丁玲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责任感、使命感。
二、创作源泉:源于生活,出之自然。
丁玲的剧本所写的人和事都来自现实生活,都有现实生活的原型或根据,没有凭空臆造,去粉饰,无做作,少雕琢,还原生活的本真。让人看了后感到一切都那么实实在在,合情合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正惟写实,转成新鲜。”丁玲在《两兄弟》座谈会上的发言曾批评“作者没有从生活体验出发,熟悉了人物、掌握了人物之后去写;而是找来一些人物凑起他的主题思想。……不是从实际生活出发,来研究人物的必然发展”,“决不是你可以凭主观去臆造”[8](P172)。丁玲还说过;“我最兴趣的是观察活着的人和在发展变化的事。给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丰富的现实的社会。”她的这一从生活出发的创作思想,在陈明的论述中也得到印证:“丁玲的创作源于生活。她作品中的人和事,大多是她经历过或看见过的。她的小说,没有生编硬造的情节,没有悬空虚构的人物。她从生活中撷取人物和事件,用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感情去刻画,去塑造……往往能找到生活中的原型,但又与生活中的人物、事件不完全一样,……更加典型化了……容易使读者相信确有其事,确有其人。”[9](P3)《重逢》里坚持在敌人魔掌中继续战斗、为我军传递军事情报的爱国女青年的斗争事迹是抗日战争中司空见惯的;《河》剧中的日本普通一兵河内一郎对乡土的眷恋,对战争的憎恶,对和平的期盼显然是大多数被卷入战争狂流的日本士兵的普遍心态,很切合日本军人的思想实际,所以日本友人看了之后能很感动;《窑工》里所写为虎作伥、恶贯满盈的日本帝国主义走狗、“活阎王”张永泉的恶行劣迹、肮脏嘴脸也是现实生活中坏人坏事的麇集,桩桩件件都是有生活依据的,绝无无中生有的凭空杜撰。
三、思想力量:高扬中国话剧的战斗传统
中国话剧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以来,就一直贯穿着两条鲜明的红线,即被戏剧理论界普遍称道的“战斗传统”和“现实主义传统”,两个传统是中国话剧引为光荣自豪的亮点、突出特征。所谓“战斗传统”,就是说话剧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紧密配合时代斗争的中心任务,把自己作为直接表达政治需求、政治激情的武器,使话剧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唤醒民众、拯救祖国的使命,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民族革命战争的战斗号角,充分发挥政治功利性和宣教功能。丁玲向以“写历史的变革、社会的兴衰”、“一往情深”全身心地“拥抱时代”为己任,她的戏剧创作一如她的小说创作一样,也是紧跟时代大潮的趋势,把握时代的脉搏,自觉地为革命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而“鼓与呼”,而推波助澜。她的三个剧本都写于残酷的战争年代,都是直接为鼓舞士气、打击敌人、推动人民战争走向胜利服务的。《重逢》里的抗日军政干部被日寇俘虏后坚贞不屈,在英勇就义前还安排自己的同志白兰保存生命“卧底”以求继续为党工作;白兰也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必欲同敌寇以死相拼,但又服从组织安排,凭智斗躲过一劫,终于获得了敌军情报贡献给党。他们的壮烈事迹足以鼓舞同日寇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华儿女,为活着的人们树立可资效仿的光辉榜样;《河内一郎》昭示出日本士兵们是被强迫驱赶到侵华战场上来的,是厌战、反战的,中日人民同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理应联合起来共同制止战争。这个剧对于瓦解敌人、扩大统一战线的舆论宣传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窑工》则写于解放战争前夕,工人群众在民主政府领导下团结起来扳倒骑在他们头上的日本帝国主义走狗、恶霸张永泉的故事,生动鲜活地教育启示着国人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巩固胜利、巩固新区”的严峻课题,让老百姓不停顿地跟上历史前进的脚步,夺取继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胜利。这些著作里无不回荡着一个响亮的音符——为人民解放而战,这无疑成为那个时代面貌的真实缩影,既充分反映了时代精神,又灌注了激励斗志的强烈主体意识,可谓高标中国话剧战斗传统的具体体现和上佳范例。
四、创作方法:秉承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
所谓“现实主义传统”,就是高举艺术“为社会”、“为人生”的旗帜,“以严格地忠实于现实,艺术地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反转来影响现实为自己的任务”。作家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按照生活的全部真实性和本来面貌再现现实,积极干预实现人生,寓教于乐,在对民众进行现代思想启蒙方面发挥巨大历史作用,成为时代的启示者。
丁玲笔下的戏剧人物形象虽不多,未能组成一个戏剧人物形象画廊,但每个戏的主角形象都较为生动流走,立体多维,而非干瘪概念,扁平单一。《重逢》主角白兰既单纯又刚烈,既胆大又细心;既有固执的当儿,又有随机应变的时刻;既有对敌人怒目金刚的一面,又有对恋人柔情似水的一面。《河内一郎》的主角河内在妻儿面前是好丈夫、好父亲,在父亲面前是大孝子,在天皇面前是顺民,在战场上是仇视“支那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称呼)的凶狠杀手,但非常厌恶奸淫中国妇女的同伙,不屑与他们为伍。而当了阶下囚后又转弯较快,较顺利地转化为反战的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一员。其“社会角色”的转换有如川剧的特技“变脸”,由作家一层层地撕开翻新,尽管“脸谱”多变,但这个“一郎”“全人”始终还是这个“一郎”,完全顺着他本人的必然行动发展逻辑前进,并不曾变成他者;《窑工》的主角是反面人物张永泉,作者在他身上着墨最多,这在创作理念上对必须以正面人物为主人公的框范是个大胆突破。剧作庶几写足了张永泉的复杂性、整体性、集万恶之大成性。这只日本鬼子的走卒鹰犬,在日本人跟前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为了讨好日本主子竟至把自己糟蹋过还嫌不够的养女、黄花闺女送给东洋鬼子去糟蹋。而对中国“苦力”则是百般压榨、残害,他善于伪装、拉拢人、蒙骗人,既阴险奸诈,又贪财好色,狐假虎威,世故圆滑,巧言令色。对这个反面人物作家没有简单化、脸谱化、漫画化,而是还其“活阎王”的真面目。丁玲懂得戏剧艺术的重要特点——凸现戏剧人物行动性和内心情感的重要,她说,“要写行动里面的人,要从很多行动里去塑造人物。……要写在生活变化中的人物”[10](P172)。她善于将人物置于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的湍流旋涡中,随着矛盾冲突的进展层次分明地揭示人物心理变化的轨迹。白兰开初只想与日寇拼个鱼死网破,不存求生幻想。继而战友让她“设法活”,“表面上顺应敌人,骨子里为我们自己人工作”,她断然拒绝:“我做不了,白兰可以死一百次,也决不会投降的,哪怕是假投降。”可战友遇难后,她猛醒自己应该接受战友的嘱托坚持人自为战,于是同敌人虚与委蛇;及至见到昔日的恋人变成今日的叛徒,怒不可遏,终而亲手杀之。最后“发现”错杀冤枉了自己人,复“突转”大悲巨恸。白兰的情绪大起大落,几经翻腾,而其忠贞爱国的一贯性、整一性,就在这瞬息万变的斗争风云中浮雕般地显露出来。河内一郎亦然,开始在家乡他表现为一个深怀“恋乡情结”的善良正直的日本农村青年,到了战场,他一面质疑、诅咒战争;一面在交战中又效忠天皇,陡然变成一头嗜杀成性的野兽,只缘误解被“支那人捉去是要砍头的”;而被俘虏后人类良知良能重又在他身上复苏;最后他发自内心忏悔谢罪,厕身于反战同盟,其心理过程的每一阶段变化都是入情入理,契合一郎“这一个”(恩格斯语)人的个性特征的。在人物刻画方面,丁玲很会运用人物之间的对比映衬的手法,如用狗腿子张生财的“坏”来陪衬他的主子张永泉的更“坏”,沆瀣一气;用花钱买来的小老婆凤仙都恨透了她男人张永泉来反衬张永泉招惹的天怒人怨。丁玲还擅长描画群体形象,瓦窑厂众劳工形象、我军战地医院医护人员群象、战地日军官兵群象都性格各异,人自有貌,栩栩如生。
丁玲戏剧的情节结构遵循传统话剧的分幕分场,起、承、转、合的结构方法,看不出精心安排设计的痕迹,好似生活流程本身一样顺其自然地延展推进。但分析起来那里面的戏剧性、可看性很强,不乏艺术技巧。既有情节的环环相扣,层层推进,又有节奏的徐疾顿宕,兔起鹘落,也有悬念丛生,高潮迭起。人物命运总会擒住观众的心绪,让你引颈在望,欲罢不能。白兰能不能活下来?她将怎样面对日本鬼子的“降敌”的恋人?河内会不会断送性命?被俘后他的际遇结局如何?工友们能不能斗倒老奸巨猾的张永泉?这些悬疑都足以吸住观众的心绪甘愿把戏看到底而不至中途“起堂”,说明情节的魅力抓人。在情节构思上偶然、巧合手法的运用很高明:白兰在密室相遇的前来诱降的敌情报科长马达明恰恰是自己暌别一年的恋人、同志;刘文发被招工从天津来到森下瓦窑厂正好同他要寻找的散失多年、卖给张家的女儿小玉相会;河内从军离家三载好不容易盼到了回家探亲这一天,偏偏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天皇下达“召集在乡军人令”的一天,结果他连儿子也来不及见就匆匆离去赴戎,相聚的片刻欢乐顿时化作伤离的泪雨。
丁玲写戏的艺术技巧表现在颇多侧面描写上,如通过河内一郎同父亲的对话反映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战绩:“满洲的义勇军听说厉害得很”,反映日本军国主义对日本民众的蒙蔽欺骗宣传:“我们的司令官常常这么告诉我们:支那那个国家实在弄得不好,他们的政府没有能力去振兴自己。如果我们不去,支那就会亡国于白种人的,我们应该去帮助他们剿灭共匪建设国家”。细节描写的反复出现更加深观众的印象,并起结构上前呼后应、针线紧密的联接作用。如多次提到的张永泉给劳工吃掺沙子的霉米,老杜望着自己赖以生存的葡萄园被张永泉霸占心痛欲裂,使观众对张永泉的可恨可恶感到震惊气极;河内一郎父亲说要到当铺去把困难时当掉的书赎回来,以供归家的一郎阅读,这一个小细节既折映了一郎好读书上进的为人品行,又传达了父子深情;再如《窑工》第二场一开场就是凤仙看家信,至第三幕第一场末尾张永泉被八路军逮捕,凤仙自己忖度“怎么办?”,然后“(从怀中取出家信,阅后揉成一团)说‘只有这样办’(拿一包袱下)”。下一场再由工人交代:“他老婆(指凤仙)也卷着铺盖走了。”这样前后连贯,既揭示了张永泉众叛亲离的下场,又显得针脚绵密,结构严整。丁玲也善于让道具“说话”,白兰在敌我双方混战中从地下拾到小刀,这把小刀藏露多次,最后成了杀死自己人的凶器,在情节的关节点上起了决定性作用;河内妹妹菊子多次提到请人买几个桃子,她记得哥哥喜欢吃桃,桃子成为兄妹情的象喻意象。
丁玲戏剧的语言是相当生活化的、口语化的,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故事发生地惯用的方言土语也往往俯拾即是,她注重对群众口头语言的提炼,力求让人物“开口就响”(老舍语),台词富于表现力,用简练利落的语言表达深厚的内涵,如有的工人对“汉奸的老婆跑了”颇感遗憾,不辨黑白,而小玉只一句话:“跟她有什么相干,她还不是受张永泉的气?她是好人。”就澄清是非,一锤定音;再如一郎在遭日寇毁坏村庄发泄对现状的愤懑说:“什么生活?白天,灰尘;夜晚,寒冷。烧杀、血肉,世界上就只有互相的仇恨吗?”寥寥几字,就勾勒出一幅凄凄惨惨、昏天黑地的日寇暴行图,也饱含了充满爆发力的憎恶诅咒战争的怨声。似这样的潜台词丰富的语言在丁玲剧作中随处可见。丁玲也会用音响效果渲染气氛,仅举一例:古钟沉郁幽幽的钟声、远处时不时传来的狼叫声,渲染张永泉制造的人间地狱——“望乡台”的阴森恐怖气氛。
绾而言之,丁玲很有自知之明且严于律己,她对自己的剧本作过自我批评说,《河内一郎》“觉得第一幕还勉强有点文学意味,第二、第三两幕实在缺乏生活,较公式而且乏味”;《窑工》“粗糙,人物概念化等毛病是很明显的。”这当然包含大作家虚怀若谷的谦词,但也不无几分公允之论。丁玲剧作平心而论,总体上看其艺术成就远不如其小说大,难称经典。但把它们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下审视之,这些剧作确有很强的政治思想张力,“能振奋启示年轻的一代:中华民族是永远不会沉沦的。”它们也有艺术,有文学性,还有历史文献价值,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丁玲曾这样评价抗战时期血与火中锻铸出来的作家:“抗日战争时期培养出来的这一代作家,与人民一道滚过几身泥土,吞过几次烈火浓烟,学过使枪,学过使锄,比较熟悉劳动人民,生活底子厚,受党的教育多,他们是热爱人民、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代作家。”[11](P202)这段话诚可视为丁玲的“夫子自道”,是抗战期间丁玲风姿的真实写照,用以评价丁玲本人正恰到好处,合若符节。丁玲在1982年3月为自己的戏剧集出版而撰写的自序《我与戏剧》中总结说:“今后,我再写剧本,做演员,当导演大概都是幻想中的事了。这次收集刊印可以作为我在戏剧方面工作和学习的一个小结。今后我仍将当一个热心的观众,为那些有成就的、有贡献的、老的和新的戏剧工作者鼓掌叫好,向他们学习,写点东西,以充实我的战斗的晚年。”足见丁玲终其一生直至耄耋之年依然怀抱深深的不稍减褪的“戏剧情结”,可惜只因种种客观条件的局囿,她的写戏才华学养未得发挥尽致。不然,倘假以时日,有条件操刀写戏,她真可能当之无愧地入列一代戏剧大家之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