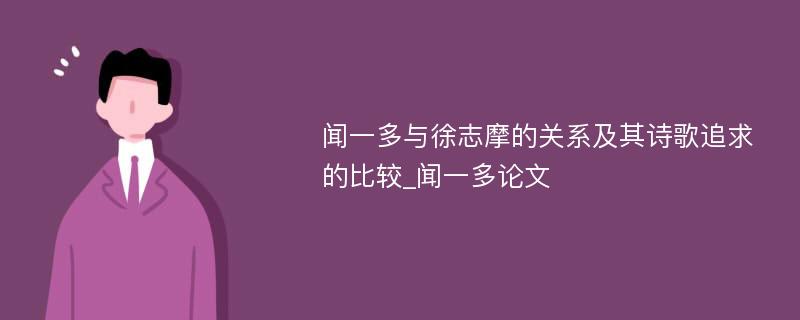
闻一多与徐志摩的关系及其诗学追求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摩的论文,关系论文,闻一多论文,徐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5)04-0086-(08) DOI:10.13852/J.CNKI.JSHNU.2015.04.011 如果将闻一多和中国现代诗家比较,徐志摩当是最重要者。因为他们在相识初始阶段就共同创办《诗镌》专栏,倡导新诗的“格律化”,创作出诸多“三美”新诗,而后还共同编辑《新月》杂志等,强调文学的“健康”和“尊严”,为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新诗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同属“新月”诗派的两大支柱。虽然如此,由于他们的美学追求同中有异,特别是性格更兼情操差异,最终各自内心产生罅隙,甚至言语相讥,以致徐志摩突遭空难,闻一多竟没写纪念文字。研究闻一多、徐志摩美学追求异同及其他,对于总结他们倡导新诗创作“格律化”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意义。 一、闻一多与徐志摩的初始关系及其创办《诗镌》 闻一多和徐志摩一经相识,就具有非常融洽的关系,这在其家信中就有表现。1925年6月初,闻一多留美归国在老家浠水一段时日后,中旬即赶到北京谋取职业,并在其后认识了徐志摩。他和当时诗坛享有盛誉的徐志摩相见,最迟是在1925年的8月9日。因为闻一多在此后的11日早上写信告知驷弟,他已“正式加入新月社”,并在“前日茶叙时遇见社员多人”,其中就有时在北大任教授的徐志摩。当时闻一多对徐志摩尤感兴趣,他在信中说“徐志摩顷从欧洲归来,相见如故,且于戏剧深有兴趣,将来之大帮手也”。闻一多所说前者“徐志摩顷从欧洲归来”,不是徐志摩1922年10月所结束的留学生涯回国,而是其1925年上半年的苏联、法国、德国和英国之旅。而其所说后者“将来之大帮手也”,则是闻一多拟借助徐志摩实现留美时同人欲创办剧社的宏愿。就在此前的7月,闻一多已和赵太侔、余上沅、孙伏园等拟就《北京艺术剧院计划大纲》。因为与徐志摩“相见如故,且于戏剧深有兴趣”,所以闻一多才认其为“将来之大帮手也”。闻一多此说并非没有根据。因为就在这封信中,他还说徐志摩约其“今日午餐,并约有胡适之,陈通伯(即《现代评论》署名陈西滢者),张欣海,张仲述,丁西林,萧友梅,蒲伯英等在座”,为的就是“讨论剧院事”。这又是因为,“消息谓萧友梅(音乐家)与某法国人募得四十万资本,将在北京建筑剧院。故志摩招此会议,商议合作办法”。[1](P226)闻一多这封信是他还未和徐志摩等人聚餐的当天早上所写。他和徐志摩等会商的相关情况如何,闻一多在当天聚餐后的家信中又详述徐志摩欲推荐他任《晨报》副刊《副镌》编辑一事。他说,“北京《晨报》为国内学术界中最有势力之新闻纸,而《晨报》之《副镌》尤能转移一时之思想。《副镌》编辑事本由正张编辑刘勉己兼任。现该报拟另觅人专管《副镌》,已与徐志摩接洽数次”。闻一多说因“徐已担任北大钟点”,更兼“徐之友人不愿彼承办《晨报》,故徐有意将《晨报》事让”闻一多“办理”。信中还详述徐志摩曾问闻一多“谋到饭碗否”。当得到否定回答并求“想想法子”后,徐志摩就欲推荐闻一多操办《副镌》之事。这对当时的闻一多来说当然求之不得。因为其正处在待业焦急之中,不然他就不会当天写信将此信息告诉家人。而且编辑的报酬也相当可观,闻一多说“据徐云薪水总在二三百之间,大约至少总在百元以上”。[2](P227)虽然闻一多编《晨报》副刊事宜因他故未能如愿,最终仍由徐志摩承担《晨报》副刊主任职务,但毕竟徐志摩又为他推荐到国立北京艺术学院任职。徐之所以待闻一见如故,当有诸多原因。首先是因闻一多当时的诗坛影响。徐志摩1923年读到刚出版的《红烛》后,就对闻一多非常崇敬。尤其闻一多在归国后的短短时日,相继又在当时重要刊物《现代评论》和《大江季刊》等发表了他的诸多爱国诗,如《醒呀!》《七子之歌》《爱国的心》《洗衣曲》即后来更名的《洗衣歌》,和《长城下之哀歌》《我是中国人》等。闻一多这些爱国诗作,立即引起国内文坛注意并得到好评。作为敏感诗人的徐志摩,不能不因此而对闻一多再添敬意。其次是因他们相同的欧美留学经历,已经结成“新月”社团,因此具有共同语言。当然,还因被称为“新月的灵魂”[3](P41)徐志摩与生俱来的热情性格。 闻一多和徐志摩合作,是他们从共同创办编辑《晨报》副刊的《诗镌》专栏开始的。因学缘关系,此前不仅有被称为“清华四子”的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和孙大雨经常踏破闻一多租屋的门槛,而且他们还团结刘梦苇、朱大枬和骞先艾等新诗爱好者,讨论诗之发展和建设即新诗的格律化问题,更欲借《晨报》副刊版面创办《诗刊》专栏,以之实现闻一多刚到美国就欲“打出招牌”,[4](P215)意“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径直要领袖一种文学潮流或派别”[5](P80)的宏愿。当被公推为联系者的闻一多和徐志摩接洽后,徐志摩就毫不犹豫爽快答应。徐志摩还亲到闻一多寓所考察,更极力夸赞其艺术家气质,说单看“一多那三间画室,布置的意味先就怪。他把墙壁涂成一体墨黑,狭狭的给镶上金边,像一个裸体的非洲女子手臂上脚踝上套着细金圈似的情调。有一间屋子朝外壁上挖出一个方形的神龛,供着的,不消说,当然是米鲁薇纳丝一类的雕像……”等。徐志摩对闻一多十分崇敬,他肯定这“确是一个别有气象的所在”,还说此“有意识的安排,不论是一间屋,一身衣服,一瓶花,就有一种激发想象的暗示,就有一种特具的引力”。这就“难怪一多家里见天有那些诗人去团聚”,徐并因此而“羡慕他”。徐志摩还强调这“不仅是一多自己习艺的背景,它们也就是我们这《诗刊》的背景”,因此“期望我们将来不至辜负这制背景人的匠心,不辜负那发糯米光的爱神,不辜负那戴金圈的黑姑娘,不辜负那梅斐士滔佛利士出没的空气”。[6]当诸多事宜商定之后,闻一多更展示其绘画专业才能,为《诗镌》专栏设计伸展双翼而欲腾空的“神马”刊头。“诗刊”两字则由著名书法家蒲伯英用隶书题写。但因隶体没有“刊”字,于是就用内涵相同的“镌”字代替。就这样,被闻一多“预料《诗刊》之刊行已为新诗辟一第二纪元”[7](P233)的《诗镌》专栏,于1926年4月1日正式问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新诗格律化运动从此开始。 二、闻一多与徐志摩诗之“三美”理论阐释及其“创格”表现 闻一多当然不负众望。1926年5月13日,他在《晨报》副刊《诗镌》专栏发表《诗的格律》这篇诗学论文,系统阐述他的新诗格律化主张,提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8](P141)相对其他新诗格律化倡导者的主张,如饶孟侃的《新诗的音节》强调其“实在包含的有格调,韵脚,节奏和平仄,等等的相互关系”[9]问题,闻一多则更多阐述诗之“建筑美”内容。他说,“这一来,诗的实力上又添了一支生力军,诗的声势更加浩大了。所以如果有人要问新诗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应该回答他:增加了一种建筑美的可能性是新诗的特点之一”。在回答有人“对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表示怀疑,以为这是复古的象征”时,闻一多质疑说:“现在把节做到匀称了,句做到均齐了,这就算是律诗吗?”他的回答是否定的。虽然“律诗也是具有建筑美的一种格式,但是同新诗里的建筑美的可能性比起来,可差得多”。这是因为“律诗永远只有一个格式,但是新诗的格式是层出不穷”的,并且表现为“相体裁衣”。其次为“律诗的格律与内容不发生关系,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第三则是“律诗的格式是别人替我们定的,新诗的格式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匠来随时构造”。闻一多还针对有人“觉得把句子切得那样整齐,该是多么麻烦”,并且“做诗要是那样的麻烦,诗人的灵感不完全毁坏了”的质疑,他肯定“灵感毁了,诗也毁了”,但他更强调的则是,“字句锻炼得整齐,实在不是一件难事;灵感决不致因为这个就会受了损失”。如若“那一首诗没有做好,只应该归罪于他们还没有把这种格式用熟;这种格式的本身不负丝毫的责任”。对此,闻一多还通过实际诗例比较,强调“句法整齐不但于音节没有妨碍,而且可以促成音节的调合”。闻一多当然承认“字数整齐了,音节不一定就会调合”。他解释说“那是因为只有字数的整齐,没有顾到音尺的整齐”。然而“这种的整齐是死气板脸的硬嵌上去的一个整齐的框子,不是充实的内容产生出来的天然的整齐的轮廓”。“音尺”是闻一多借鉴的外来概念。所谓“音尺的整齐”,就是每行诗的音顿或字数有规律可循,其实就是诗之节奏的整齐。如果这样,闻一多认为“音节一定铿锵,同时字数也就整齐了。所以整齐的字句是调和的音节必然产生出来的现象。绝对的调和音节,字句必定整齐”。但我们切莫据此认为闻一多就是形式主义者。他所强调外在形式即字数整齐的“建筑美”,是在“证明诗的内在的精神”,即“节奏的存在与否”。其实闻一多最看重的还是诗的“音乐美”即诗之节奏的匀称。他在分析诗之格律的“原质”时,就阐述过“音乐美”和“建筑美”的辩证关系。虽然他承认“从表面上看来,格律可从两方面讲”,即“属于视觉方面的”和“属于听觉方面的”,但他更强调“这两类其实不当分开来讲,因为它们是息息相关”的。闻一多举例说,“譬如属于视觉方面的格律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属于听觉方面的有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但是没有格式,也就没有节的匀称,没有音尺,也就没有句的均齐”。闻一多之所以较少论证“音节”问题,那是因为饶孟侃在闻氏发表《诗的格律》之前,已在《新诗的音节》和《再论新诗的音节》中,将其“讨论得很精细”的缘故。虽然如此,闻一多仍在讨论“节奏”的时候更强调“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他说“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觉得格律的缚束。对于不会做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然而“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8](P137~144)闻一多将“音节”视作新诗格律的重要质素,除《诗的格律》内容能够说明外,还能在其书信内容中得到补充。就在发表该文之前的4月15日,他就说《诗镌》同人“皆以其注意形式,渐纳诗于艺术之规。余之所谓形式者,form也,而形式之最要部分为音节”。闻一多同时还夸奖“《诗刊》同人之音节已渐上轨道,实独异于凡子,此不可讳言者也”。[7](P233) 关于中国新诗格律化的倡导,我们当然肯定闻一多作为主帅的地位。但作为报幕,最早发布铅字提出者,却是徐志摩。他作为《诗镌》专栏主编,根据同人共同主张,在其发刊词即《诗刊弁言》中,就不仅“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作一件认真事情做”,而且更宣言“我们几个人都共同着一点信心: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性质的;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没有一部像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我们信我们自身灵性里以及周遭空气里多的是要求投胎的思想的灵魂,我们的责任是替它们搏造适当的躯壳,这就是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现”。徐志摩还强调,“我们信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现;我们信文艺的生命是无形的灵感加上有意识的耐心与勤力的成绩;最后我们信我们的新文艺,正如我们的民族本体,是有一个伟大美丽的将来”。[6]虽然徐志摩和闻一多共同倡导新诗格律化,更非常肯定闻一多发表在《诗镌》专栏上的“格律”新诗,但其“创格”追求却和闻一多不完全相同,而对闻一多追求的绝对化有所检讨。他说“我们觉悟了诗是艺术;艺术的涵义是当事人自觉的运用某种题材,不是不经心的一任题材的支配”。虽然“我们也感觉到一首诗应分是一个有生机的整体,部分与部分相关联,部分对全体有比例的一种东西;正如一个人身的秘密是它的血脉的流通,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的匀称与流动”,但“明白了诗的生命在它的内在音节(Internal rhythm)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的趣味”。这是因为“不论思想怎样高尚,情绪怎样热烈,你得拿来彻底的‘音节化’(那就是诗化)才可以取得诗的认识,要不然思想自思想,情绪自情绪,都不能说是诗”。徐志摩更进一步阐释说,“但这原则却并不在外形上制定某式不是诗某式才是诗,谁要是拘拘的在行数字句间求字句整齐,我说他是错了”。因为“行数的长短,字句的整齐或不整齐的决定,全得凭你体会到的音节的波动性”。徐志摩强调,“这里先后主从的关系在初学的最应得认清楚,否则就容易陷入一种新近已经流行的谬见,就是误认字句的整齐(那是外形的)是音节(那是内在的)的担保。实际上字句间尽你去剪裁个齐整,诗的境界离你还是一样的远着”。徐志摩为此做一形象比喻,他说“你拿车辆放在牲口的前边,你那还赶得动你的车”?因此他的观点是,“正如字句的排列有恃于全诗的音节,音节的本身还得起原于真纯的‘诗感’”。他并且“再拿人身作比”,认为“一首诗的字句是身体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否则,那就“他戴了一顶草帽到街上去走,/碰见了一只猫,又碰见一只狗”,这“一类的谐句都是诗”。据此徐志摩说“已经发见了我们所标榜的‘格律’的可怕的流弊!谁都会运用白话,谁都会切豆腐似的切齐字句,谁都能似是而非的安排音节——但是诗,它连影儿都还没有跟你见面”。因此他认为“单讲外表的结果只是无意义乃至无意识的形式主义”。[10]闻一多虽然承认字数整齐音节并不必然调和,但他更强调整齐字句是调和的音节必然产生出来的现象。徐志摩则强调“诗感”跳动和“血脉”流转,从而构成诗之外形;说到底,其实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因为徐志摩和闻一多追求的“建筑美”理念有所差异,所以徐志摩并不完全赞成闻一多的格律诗论。 三、闻一多与徐志摩诗之“三美”的“创格”表现 虽然如此,无论闻一多抑或徐志摩,他们的诗作都表现出“三美”追求。因为我国古诗往往是为歌唱,所以音乐性就成为诗家追求的最重要美学特征,闻一多这才将“音乐美”放在诗作首位。而诗之所以能唱,正在于诗的音节具有“均齐”特征。闻一多将“此均齐之组织……谓之节奏”。[11](P156)诗就是在此强烈节奏里体现出一种强烈的音乐性,这才有闻一多《诗的格律》中关于“诗底价值是以其情感的质素定的”,并且“诗的所以能激发情感,完全在它的节奏”之阐述。这就说明情感是诗歌创作的目的,节奏则是表现其情感的方法,并且节奏是诗歌具有音乐性的最重要因素。闻一多《死水》诗的节奏,就表现为“每一行都是用三个‘二字尺’和一个‘三字尺’构成的,所以每行的字数也是一样多”。[9](P156)其“音尺”一致形成字数一致。虽然字数一致并不必然导致节奏一致,但“音尺”一致造成节奏一致,读起来就必然具有音乐性。在“音尺”规范方面,还有《罪过》,也是每个诗句三个“音尺”,并且每个“音尺”都是“三字尺”。这比《死水》诗更具规范的节奏,读起来就更具音乐性。此外,《洗衣歌》也具有强烈节奏,因此具有极强的音乐性。闻一多诗作具有“音乐美”,除其节奏因素外,还有用韵特色。押韵也是诗歌的重要特征,必然能给诗歌增添音乐美感。闻一多就说:“用韵能帮助音节,完成艺术;不用正同藏金于室而自甘冻饿,不亦愚乎?”[12](P78)如《一句话》从头到尾一韵到底,读起来一气呵成,从而构成强烈气势。但更多者还是首联押韵,并在此后偶句押韵的形式,如《也许:葬歌》和《你莫怨我》等诗。此外,还有每段的暗中换韵式如《你看》,抱韵式如《忘掉她》等。闻一多也运用双声叠韵词语,以之增强诗歌的和谐悦耳,如《心跳》和《泪雨》等。闻一多诗作的“音乐美”还表现在诗句的回环往复,突出者除《洗衣歌》外,还有《忘掉她》、《我要回来》和《你莫怨我》等,都是在段之首句和段之尾句重复着同样的内容;这就犹如音乐的和声,不仅通过回肠荡气的旋律加强诗之音乐感,更在抑扬顿挫中加强诗歌情感。闻一多的“绘画美”追求虽然主要是词藻优美,但还有诗中有画的因素。他认为“从来那一首好诗里没有画,那一幅好画里没有诗?”[13](P163)更强调“一样颜色画不成一幅完全的画,因为色彩是绘画底一样要素”。[14]因此其诗作就呈现很多五彩斑斓的画面。如《口供》中“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国旗在风中招展”,包括“鹅黄到古铜色的菊花”等。再如《收回》中“那斑斓的残瓣”,连“一串心跳”也是“珊瑚色的”,就更莫说让“你戴着爱的圆光”。当然,最富“绘画美”者要属《死水》诗,其中的“翡翠”“桃花”“罗绮”“云霞”“绿酒”等,更蕴藏着感情色彩。诗人是要通过意象之美表达现实之丑,越用优美词语,就越能将丑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就表现出闻一多“屠龙”般驾驭诗艺的高超技能。闻一多的“建筑美”更创造出很多形式:“参差行式”,如《末日》和《大鼓师》等;“高层立体形”,如《死水》和《夜歌》等;“菱形式”,如《我要回来》和《你莫怨我》等;“夹心形式”,如《忘掉她》;“副歌形”,如《洗衣歌》等;“倒顶式”,如《口供》和《春光》等;还有根据内容表达需要,变异“倒顶式”形成的“结尾爆发式”,如《一句话》。以上这些诗作形式,都具有独特的“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特点,并且都是“相体裁衣”,根据自己意匠构造的结果,从而达到“精神与形体调和的美”。这种表现除给读者多种形式的美感外,更重要的是不仅促成音节即节奏调和,从而使之更富音乐美感,而且还在寓意表达方面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如“夹心形式”是将诗之表达中心内容夹在段之首尾两行诗的中间,虽题名为《忘掉她》,却又挥之不去地达到始终驻留读者心间的效果。变异“倒顶式”即“结尾爆发式”的《一句话》,其在内容方面先极力铺垫,然后在强烈抑压之时,再由抒情主人公银瓶炸裂般一声呐喊,达到契合读者审美期盼之目的。 徐志摩诗作也特别注重“音乐美”。他曾说“音乐与其它艺术不同,是真正的艺术类型,是衡量完美艺术的尺度;音乐能更深地打动人心的素质,能更信服,更不可挡,更强有力,更理想地向有鉴赏力的人传递思想和感情”。[15](P65)因此“诗的灵魂是音乐的,所以诗最重音节”。[16](P277)但徐志摩和闻一多有所不同,他所强调者不仅“匀称”,而更“流动”,就如人之“血脉的流通”一样,追求的是其“内在音节”。因此其诗就成为他“筋骨里进出来,血液里激出来,性灵里跳出来,生命里震荡出来的真纯思想”。[17](P94)其最典型者如《雪花的快乐》《为要寻一个明星》《再别康桥》,乃至《我不知道风在那一个方向吹》等,都是他极具“音乐美”的佳篇。即如《雪花的快乐》而言,其音节显然缺乏闻诗的规范,因为每行的字数并不相同,并且每行的“音尺”也不相同,但是读起来却给人和谐的韵律感。《再别康桥》诗中“轻轻的”状语连环出现,也和《雪花的快乐》中“飞扬,飞扬,飞扬”一样,节奏的抑扬顿挫自然呈现。这种律动的“音乐美”,在徐志摩诗中比比皆是。《沙扬娜拉》也堪称典型,因为其将外部节奏和内在旋律紧密结合,从而呈现出表现对象恋恋不舍的柔软妩媚。徐志摩诗之节奏舒缓自如,诗如其人,是由“原动的诗意”,催动其“血脉的流转”,因此其诗亲切而绝无虚假感觉。和闻一多一样,徐志摩诗作并不拘泥于绝对韵式,而根据内容表达需要进行新的创造。虽然他有诸多偶句押韵的常规韵式,但更多者则是一段一换韵。这虽不具强烈气势,但因他由“心脏的跳动”表现外部节奏,就不仅表现出“音乐美”,更能表现出“真纯的诗感”。《再别康桥》就是最好的例证。徐志摩也有一段两种韵式者如《雪花的快乐》。这种韵式是每段五行,构成AABBB的特点。如“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这种暗中换韵方法,由于前两行和后三行各自押韵,不仅不露雕琢痕迹,反倒更能表现抒情主人公欢快情绪。徐志摩诗作也有运用“抱韵”格式者,《为要寻一个明星》就和闻一多的《忘掉她》韵式相同。他也经常运用叠字或双声叠韵的连绵词增强诗的韵律感,但最突出者还是重复诗句构成回环往复的旋律。如果认为《残破》4段每节首行都重复的“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诗句并不特别突出,那么“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均占据该诗6段的前三行,而全诗内容只有每段诗之最后一行构成的这种特点,就堪称典型。回环往复诗句构成一咏三叹的旋律,从而强化诗人的迷茫和失落感。徐志摩的诗歌语言典雅华美,极具色彩感。他“诗的每一行无不灿烂夺目,无一字不妥帖精当”。并且“最大的本事在于每一句都是一清二白的口语,但却是光彩四射的诗句”。[18](P201)这因他诗句是从心灵流淌出来的结果,《再别康桥》也是最好的例证。如“河畔”有“金柳”,“夕阳中”有“新娘”,“波光里”有“艳影”,“软泥上”有“青荇”,“康河里”有“柔波”,另外还有“天上虹”、“彩虹似的梦”、“星辉”、“放歌”、“笙箫”和“夏虫”等等,都构成美景如怨、情怀如诗的氛围。还有《黄鹂》的“艳异照亮了浓密——/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等候它唱,我们静着望”,这诗画相融的效果,更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徐志摩诗作注重“建筑美”程度并不亚于闻一多。他在1924年11月,就说“我们得同时做两种功夫:一面造匀称的瓦料,一面打造将来建筑的图样”。[19](P204)徐志摩说到做到,他后来“创格”的“建筑”新格式,也有“高层立体形”如《爱的灵感》;“参差行式”如《再别康桥》;“夹心形”如《再不见雷峰》;“双轨形”即每节两行的《火车擒住轨》;“托塔形”即每节5行,首行只有两字并且和其后三行长句对齐,最后一行只有三字,但和中间三行尾字对齐的《为的是》;还有段之前三行对齐,最后一行退后一字排列的“倾斜形”《我有一个恋爱》,除此还有散文诗式等等。虽然就“建筑”实践来说,徐志摩诗作也许没有闻一多诗作严谨,但他诗之层出不穷、错落有致的“建筑”形态,却和其音节波动互为因果,彰显出深厚的艺术功力。 四、闻一多与徐志摩关系演变及其诗作主要倾向 徐志摩对闻一多非常佩服也非常敬重,他在《诗刊弁言》中对闻一多的热情介绍就是证明。后来《诗镌》专栏停刊,徐志摩又对闻一多的贡献充分肯定,说“同人中最卖力气的要首推饶孟侃和闻一多两位”。他认为闻一多发表在《诗镌》专栏上的“《春光》,《死水》,都是完全站得住的;《黄昏》的意境,也是上乘”。[10](P134)许多年过去,徐志摩还在《〈猛虎集〉序》中,夸奖“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更承认“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他还说,“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虽然徐志摩因其“素性的落拓”,自谦始终不容“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功夫”,但他第二本诗集《翡冷翠的一夜》还是得到闻一多对其艺术的肯定,夸赞“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20](P181)1931年1月新的《诗刊》杂志出版前,徐志摩为向闻一多约稿,从上海给青岛的梁实秋写信要其催促。他说“一多非得帮忙,近年新诗,多公影响最著,且尽有佳者。多公不当过于韬晦,《诗刊》始业,焉可无多,即四行一首,亦在必得,乞为转白多。诗不到刊即不发,多公奈何以一人而失众望”。[21](P415)闻一多后来寄上他的新作《奇迹》,徐志摩大喜并在刊发该诗的《诗刊》杂志创刊号上,说“《奇迹》是一多‘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奇迹”。[22](P182) 徐志摩既与闻一多有此亲密关系,但在前者因飞机失事英年早逝,“新月”同人纷纷撰文纪念的情况下,闻一多虽也震惊但却没任何哀悼文字见诸报刊。而当朋友问及徐志摩是其“公认的好友,为什么没有一点表示”时,闻一多回答却是“志摩的一生,全是浪漫的故事,这文章怎么个做法”。[23](P417)徐志摩确有很多“浪漫”故事。先在英国为追求才女林徽因而和无辜的结发妻子张幼仪离异;被林徽因甩脱后,又不顾社会舆论,最终与有夫之妇的交际花陆小曼结合;而和陆小曼婚姻酿成悲剧后,复再移情于已经嫁人的林徽因。其实徐志摩的死,就是因为林徽因,即后者做学术报告,前者要为其捧场,才从南京乘机赶赴北京,不料竟出事故酿成悲剧。作为道德君子的闻一多,也就因此而对徐志摩之死失语。我们虽不肯定闻一多的旧式婚姻,但应赞赏他之因爱而为对方付出的“牺牲”。这是一种崇高人格的表现。徐志摩显然没有这种人格。但闻一多对徐志摩死之失语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在此表象背后还有其他原因。这就是闻一多和徐志摩的关系并非如他人认为的那样和谐,而是因诗学追求差异有所攻讦。论据是徐志摩背后曾说:“一多怎么把新诗弄得比旧诗还要规则?”而且“平时与他人称闻一多总是代以‘豆腐干’”。徐志摩如此妄议闻一多,闻一多对徐志摩也不客气,他在背后则说“志摩的诗,不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散文而不是诗”。[24]总之,闻一多是嫌徐志摩“格律”追求不够,徐志摩则嫌闻一多“格律”追求过度。虽然他们所说都在某种程度上很有道理,因为闻一多诗作尤其是《死水》诗集确实过于追求整齐,而徐志摩诗作确实格律和自由及散文诗并存。但这也并非闻一多对徐志摩之死失语原因的全部,而还有他故。这即1928年创办《新月》杂志时,内部传出“刊物决定由胡适之任社长,志摩任编辑”消息后,当即就遭到同人反对。因为他们认为“不应该这样的由一两个人独断独行,应该更民主化,由大家商定”。[25](P110)结果又增添闻一多等几人共同编辑这才作罢。不仅如此,“据饶孟侃说,创刊号上志摩那篇《新月的态度》,闻一多和他都不同意”。[26](P470)还有后来徐志摩推荐发表彭基相的译文《文化精神》,“一多、实秋”也“都同声反对”。[27](P328)也许,徐志摩在《〈诗刊〉放假》中检讨他们格律追求过程中表现出弊端时,闻一多就对徐志摩不满。因为理念认识的契合与差异,对人之关系至为重要。 但无论闻一多因何原因没为徐志摩写哀悼文字,闻一多总算找到了他的借口。如果从这角度看,似乎也有道理。因为从徐志摩诗作中就能看出闻一多所说的问题。虽然他们的诗作内容都很复杂,但从总的倾向看,闻一多较多爱国诗篇,徐志摩则较多爱情诗篇。闻一多诗篇如《忆菊》《太阳吟》《洗衣歌》《死水》《心跳》等,就分别歌咏如花的祖国,表现祖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描写留学生的血泪,谴责罪恶社会的丑相,抨击军阀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等。闻一多只有《一个观念》,那就是“五千年的记忆”。他因此《发现》祖国竟在自己“心里”。于是他《祈祷》“这民族的伟大”。即便《一句话》,爆出的也是“咱们的中国”。闻一多热爱祖国,关心人民疾苦,因此他在《飞毛腿》中,书写“河里飘着”拉车养家糊口的“飞毛腿的尸首”,这是因为其“老婆死得太不是时候”。闻一多面对苍天高呼,这是谁的《罪过》。而翻检徐志摩的创作,虽然也有忧国忧民的诗篇,但爱情类却占主要比重。经相关学者考证,写给林徽因的情诗就有《爱的灵感》《再见吧康桥》《云游》《希望的埋葬》《悲思》《明星与夜蛾》《一个噩梦》《我有一个恋爱》,还有借英国拜伦《雅典的少女》向对方倾诉衷肠。写给陆小曼的情诗则有《情死》《翡冷翠的一夜》《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鲤跳》《别拧我,疼》《起造一座墙》等。另外还有写给凌叔华的情诗《问谁》和《为要寻一个明星》。[28]徐志摩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情诗,著名者就有《雪花的快乐》和《恋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等等。 虽然断定徐志摩这些情诗为谁而写未必准确,但研究者毕竟有些相关证据。虽然不能因作者写情诗而否定其人品,但徐志摩和情诗同步的婚外移情之恋毕竟不符合传统道德。虽然如此认识有泛道德论之嫌,但任谁都不应触犯“公约”而游离其外。虽然闻一多也在学习或工作中擦出过“爱”的火花,写有情诗如《相遇已成过去》和《奇迹》,但其有着强劲的自我约束力,在不当之“爱”刚萌生时就将其掐死。闻一多既有如此情操,他对徐志摩“浪漫故事”的态度就在情理之中了。 闻一多的《红烛》“最为繁丽”;“《死水》转向幽玄,更为严谨;他的诗有点像李贺的雕锼而出,是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的驱遣多些”。徐志摩显然“没有闻氏那样精密,但也没有他那样冷静。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29](P97)如果认为“志摩的诗以灵感见长,一多的诗以功力胜”,因此前者风格“轻灵”,后者风格“沉郁”[30](P128),这种评价并不全面,那么我们可做如下补充,即:闻一多的创作举轻若重,因此其诗内容厚重,风格则给人抑压之感。徐志摩的创作举重若轻,即便风格轻快,但却隐藏着哀怨之情。虽然如此,徐志摩诗轻灵却很自然,闻一多诗沉郁却也蕴藉,都是复杂的金银盾。如果认为其诗如人,徐志摩胸无城府,热情澎湃,那么闻一多则是憎爱分明,疾恶如仇。如果徐志摩信仰单纯,“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31](P236)那么,闻一多更堪当为之。不过徐志摩所爱者是移情别恋,罔顾道德和舆论,自由追求美的女性;闻一多所爱者则是他的祖国和人民,为了人民自由和美好,他甘愿赴汤蹈火,面对手枪毫不畏惧。虽然两人最终都为自己的追求献出生命,但徐志摩之死留给后人无尽话题和唏嘘,闻一多的牺牲则让人永远赞颂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