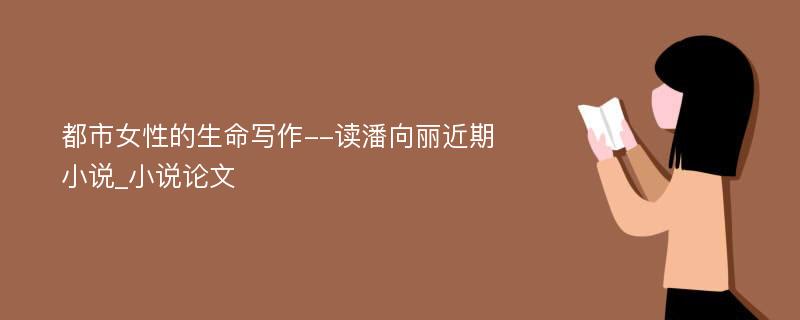
都市女性的生命书写——读潘向黎近期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期论文,生命论文,都市女性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潘向黎的小说集《白水青菜》,辑录了她近三年的10篇中短篇小说及3篇在“个人写作过程中有特殊意义的旧作”①。我之所以选择这本小说集,一方面诚如作者本人所说,它相对完整地体现了她的创作个性②;另一方面我认为,它显现出作者近年来小说创作上的自我超越。此外,随着潘向黎创作个性的日臻成熟,评论界对她以往的小说有过不少卓有见地的阐述,为了避免重复,我主要论述她的小说近作。
1 潘向黎的作品执著表现现代都市女性的
情感世界,以及由此生发的种种难以消解的生命困惑。具体地讲,一方面她悉心谛听来自都市女性激情发源地的涓涓细流,理解凡庸琐碎人生中现代都市女性的生命意义追问,尤其是情感世界的美好想象。另一方面,她又深情关注现实人生中现代女性纯粹爱情的遍体鳞伤,清醒地戳穿被大众社会称道的“终成眷属”或“一见钟情”之类自我迷醉的神话,并揭示现实生活中隐含的以性别支配为基点的文化权力的弊端。因此,细读她的作品我有这种感觉:她小说中的爱情既是一个焦点,凝聚着创作主体对于现代都市女性人生境况的深切体验,也是以女性主体意识透视情感生命的一道强烈光束,穿越女性的心灵世界、人性奥秘及生存悖论。
论述潘向黎的创作,必须提出并重新思考一个与她的创作相关的理论性问题,这就是以性别意识书写都市女性情感生活的价值意义。在以宏大叙事为轴心的审美图式环视下,现代都市女性的情感世界似乎是个狭小的书写空间,如果再以性别意识加以限定,这个书写空间仿佛显得更为狭窄了。可是我却不这么看,且不说每个作家如何真诚地对待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的问题,就是性别意识中的都市女性感情视域本身,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乃至于可望的将来,一个不容忽视的充满生命意蕴的诗意空间,因为我们不能用惯常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来限定这个特定语境下涨溢的能指。
为什么潘向黎创作中女性情感的意义,有时超出具体的爱情范畴而上升为生命意义范畴,并在多个文本之中形成一种弥漫性的思想情绪?显然,她将爱情提升为切己的生命要义。从一般意义上讲,现代女性把生命的激情投向情感世界,或者说把情感作为生命意义的替代物,原本就是现代社会信仰危机的表征之一。人作为有目的存在,生存意义的缺席必然形成失衡甚至空虚的生命状态。对于现代人尤其是缺乏神学文化背景的现代中国人来说,曾经的信仰业已失去权威性,与其把生命的激情投向辽远、缥缈和虚妄的星空,不如转向切己的爱情,以此填补生命的空寂和获取人生的意义。与此同时,相对传统的乡村宗法社会而言,现代都市是一个充满陌生面孔与疯狂追逐功利的欲望世界,“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③,人们似乎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心理安全感和社会参与感,“主观性和内在性一下子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丰富和发达,更加孤独和身不由己”④,由此男女之间的情感世界得以突现。
当然,这还与这一代女性作家的精神特质相关。对于她们来说,这个世界过于透明,诚如《我爱小王子》的主人公叶蓓所说,“我们这一代,从一开始,就没有谜语。所有的一切都在我们长大的同时真相大白,没有悬念,没有余地,没有意义。没有人骗我们,没有人耽误我们,但是我们的人生一览无余,像无边无际的沙漠,没有方向,没有路标。”⑤而且,她们对于自己的人格分裂泰然处之,一方面内心拒斥世俗的现实,另一方面又顺从现实的游戏规则:“在粗糙忙乱的生活里,因为小王子,我们就肩负了某种神圣的使命,我们是卧底,表面上和成年人的世界——肮脏、势利、无耻、可笑的世界——相安无事,但实际上,我们是他们的敌人,我们等待着时机要改变这一切,去恢复这个世界上纯真的秩序,让所有小孩子喜欢的那种感觉。”⑥在这种文化语境与精神背景中,能够确切体认和清晰把握的,也许莫过于个体的感性生命与情感世界。
我们应该承认,凡是涉及男女情感世界的作品,因书写主体的性别不同而造成的文本差异是一直存在的,只是近些年来随着女性主体的觉醒与文学生态的变化,这种差异突现出来而已。一般地说,男性创作中的情感生活往往是生命要义的一种附丽,或者是漂泊人生中心灵将息的一块暂栖绿洲;而女性创作中的情感世界原本就是生命要义中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或者原本就是疲惫人生不可或缺的心灵栖息地。这就是说,女性的情感需要显然比男性更为丰富和更加强烈,所以对于爱情,自然被女性所更为看重。从这种意义上讲,伴随着女性主体觉醒的并不是如释重负的生命解放,而是疑虑重重的情感困惑。
其实,不仅是感情生活因性别的差异而显现出不同的意义,即使是“宏大叙事”也是如此。在《白水青菜》这部小说集中,我注意到两篇较为独特的作品:《守》和《鸽子》;前者的笔触伸入硝烟的历史,后者贴近艰难的现实。然而,小说的叙事焦点没有放在作为牺牲与苦难的直接承受者男性身上,而是置于被人们忽视或者遮蔽的直接承受者的妻子身上。世人只知道成功的男人身后有女人,而没有意识到在牺牲与苦难的承受者后面,还有比他们更为痛楚的女性。虽然她们置身于历史现实的无情战场与市场之外,但她们的身心不仅被残酷的战场与市场的磨难牵连,还被她们苦难的男人牵系。也许逝者已去,生者犹存,但生者还必须继续承受生存的重扼。这种特殊的性别视角,在习以为常的历史现实中发掘出曾经为我们熟视无睹的隐秘一角。
总之,潘向黎的创作祛除了前辈作家那种社会性的叛逆精神和激愤情绪,卸去了文学叙事中的非个体性和非性别化的社会悲剧的重负,似乎无意与铜墙铁壁一般的现实社会直接抗衡。她的小说专注于个人性的生活体验和女性生命的思考,特别是将审美目光投向现代都市女性,凝视她们对完美爱情的真诚向往而不断失望,对感情世界的不懈守望而屡受伤害;这种性别书写实质上是一个能指涨溢而所指难以规限的话语空间,是我们这个无名时代颇具诗意的生活见证。
2 同样是现代都市女性的生命书写,潘向黎与那些以躯体语言冲决道德禁忌,用异化的人性和畸形的人生隐喻历史现实的女性文学不同,她似乎一开始就没有极端个人性或私人性写作的抉择姿态,也没有去刻意建构个人与社会的文化对立关系,而是从个体性别体验出发并向都市女性情感生命延伸;同时与媚俗的市民社会格格不入,敬而远之,因而在生命需求、物质世界与精神自由的契合点上书写女性的情感体验及其生存困境。简言之,如果说她同时代一些女性作家的创作较多地体现为一种先锋性质的青春表演,而潘向黎更多的则是自斟自吟式的青春诉说与女性的情感生命的体味。
她笔下的形象多为都市女性,往往是置身现实而向往完美,矜持自怜而渴望真情,个性孤傲而暗自感伤的中青年女性,总爱在理想的完美与现实的缺陷、意义的追寻与虚无的发现之中纠缠不休。如果进一步细分的话,大致可按其年纪及其情感遭遇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着完美追求但失去追求对象的年轻女性,如《我爱小王子》、《弥城》和《碎钻》等,特别是更早一些的作品,如《无雪之冬》、《轻触微温》、《缅桂花》等等。另一类是面临情感危机的中年女性,如《白水青菜》、《女上司》及《永远的谢秋娘》等。⑦其实,无论哪一类女性的感伤或疼痛,都与现代社会的某种精神症候关联,并且关涉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伦理自身的困境与悖论。
第一类形象是年轻的都市女性,她们需要感情的抚慰,而且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弥城》中的主人公承认,“无论如何,爱恋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多么美好,多么轻柔,多么让人心动啊”⑧。《我爱小王子》中的叶蓓奔波于沙漠般的城市,内心像需求一眼清澈的水井一样,向往并坚守着自己的梦想——小王子。这种完美的男人“年轻、优雅、善解人意”和“又帅又干净”,而且具有勇于承担日常生活的责任和敢于冒险的秉赋。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生命存在决定了情感需求,明知理想对象的难觅但还是难以压抑感性生命的冲动。尽管她们心高气傲,宁可承受世俗的误解也不愿苟且屈就;尽管她们个性独立,甚至具备与其年龄不太相称的成熟思想与人生洞见,但毕竟需要以异性的温存和体贴来抵御个体生命的寂寞感和漂泊感。
然而,她们却往往失去可选择的理想对象,并且对于是否沿袭恋爱——婚姻的传统人生轨道也显得忧心忡忡。从现实层面讲,人海茫茫中“小王子”可遇而不可求,诚如《无雪之冬》的叙述者所说,“遇见的男人不是有太太兼妻管炎的,就是才二十啷当岁,只想泡妞根本不想结婚的”,自己不知道何处寻觅“命中的真龙天子”。⑩可是真正深入她们的内心可以发现,她们既是爱情的唯美主义者,又是完美爱情的怀疑主义者。因为对于是否真正存在这种既有纯度又有长度的爱情持以经验性的怀疑,所以她们一再告诫自己为了避免致命的精神伤害应该抵御爱情梦想:“我不要人家对我专一,也不要人家对我负责。……我是个成人,我对我自己负责,我干吗要别人来负责?一旦进入那种一对一的关系,剩下的就是猜疑、伤害和背弃、厌倦了。正经一点的说法是:把自己的心放在别人手上,那种风险太大,大到可以和在爱里合而为一的诱惑抗衡。”(11)
应该说,这类女性感情生命的困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有的女性批评认为,由“阉割文化”主宰的社会中的男性,披着道貌岸然的外衣,戴着种种人格面具,奔走在他们认同的人生价值实现的路途中,利欲熏心而生命萎缩,业已失去健康人格和完美人性。(12)简言之,这个世界很难找到纯粹的“小王子”。不过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并非是这么简单,因为这个问题原本就包含着两重困境。一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伦理自身的困境。女性解放的过程与现代启蒙思想之路是同行的,也要经历一个从外在性自由到内在性自由的过程。限制外在自由的是社会化的各种条件,如社会制度、政治行为和文化习俗等,这些条件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尽管过程艰苦而漫长;限制内在自由的是人自身,而人自身是很难按人的欲望或意志来改变的,这是人的有限性造成的。从突破外在的思想文化禁锢,走向突破内在个体激情与感性的禁锢,也是现代女性解放的必由之路;但是“个体幸福的自由想象不可能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易碎的激情”(13)。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自由想象是无限的;而现代个体生命很容易陷入人的有限性与理想欲求的无限性困境之中,如果一旦陷入困境而又找不到自我超越的方式,将会深感苦闷甚至悲观失望。当然,从性别书写的角度讲,女性的感情需求往往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也有呵护感情的能力,即使她们丧失这种能力,也定是由于后天的男性的伤害而造成的,而非与生俱来的,《碎钻》的女主人公是一个例证。
二是爱情自身的困境。爱情发生在俩人之间,真正的爱情必然含有自私的成分,其表现在于个人要向对方的自我深处延伸,这就意味着对方必须得让渡部分内核性的自我,而这种让渡又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代价的。如果为了幸福而完全交付自我的结果不是被呵护,而仅仅是被占有甚至是被背叛,则会造成彻底的伤害;如果为了防止伤害而竖立坚固的自我防线,不让对方深入,又很难成全纯粹的爱情。这样一来,爱情似乎成为两个生命之间的自我博弈。面临这种困境,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便显得犹豫不决,如《弥城》的女主人公。
第二类形象是面临感情危机的中年女性。虽然这类女性无论是外在资质还是内在气质,都与上述的年轻女性形象系列有着家族式的相似性,但是,她们毕竟是遭遇另一种情感问题,因而也融入了作者女性创作的新的思考和探求。从这意义上讲,作者试图突破青春写作的束缚,以拓展女性写作的空间。
《白水青菜》和《女上司》的女主人公婚姻,都是在自由恋爱的情感基础上形成的,而且情感危机的原因都是男人有了外遇,她们都是无辜者。显然,她们感情失败的缘由主要源自爱情与人性的关系,确切地说是男性的幽暗人性。因此尽管她们具有现代女性的刚毅和自主,但她们的被伤害感及悲愤感还是让人们强烈感觉到,那些包括爱情在内的被认为具有永恒价值的情感、真诚和承诺,在人性的弱点面前显得如此的脆弱和纤细。
对于这种人性的缺陷,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一书中作了深入而富有启示的分析。他认为,现代爱情的价值意义在于两情相悦,然而感情却是不可靠的。这还不是说人的性情易变,因此不可靠,而是说个体性情极具差异,个体性情中的欲望极其多样,如果婚姻以性情为基础就不可靠了。(14)(其实作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弥城》的叙述者说:“什么感情都经不起考验,你如果珍惜什么感情,就千万不要考验我。这是我的经验。”(15))而且问题的症结在于,现代自由伦理已经将道德的立法权利交给了个体,让个体遵从道德的良知去把握生活;可是现代之后,理性的道德良知演变成了感觉的道德良知,“就是从自由意志到自由欲望的转变——意志的向善成了感觉的自适”,以致连社会的伦理秩序也感觉化了。(16)这就是说,并不是社会道德秩序彻底紊乱,也不是人完全失去道德意识,而是人的道德意识的内涵发生了悄然变化,感性欲求在道德领域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而且位置举足轻重。
对此,人类有过两种彻底解决的方式,一是道德寂静主义,认为个体生命热情和愿望都是徒劳无益的,人们应放弃自己的热情和愿望,安于自己生命的有限性。二是道德理想主义,认为人们应该把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愿望转移到集体性的理想之中,由此克服个体生命的有限性。(17)然而,这两种彻底的方式在多元的现代社会显然不具普适性的价值意义;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现代人还没有成熟到为我们的爱情生活提供一劳永逸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体系。既然如此,对于既没有宗教理想又不信世俗天堂的现代人来说,何以摆脱爱情中的生存困境和生命焦虑呢?倾向于个体为自己立法的现代性生活伦理认为,对于生命的悖论既不逃避也不僭越,但也不是仅仅认同人生悖论根本不可解决的宿命以及人性的脆弱,而是珍惜生命悖论中爱的碎片。“即便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在无从避免的生活悖论中被撕成了碎片,依然是美好的人生。”(18)对于旁观者而言,这不失为一种审美的乌托邦;而对于身处其中的女性而言,无疑是一种严峻的生活考验。其实,对于这种悲观的论调,作品也有过清醒的思考,《碎钻》的叙述者说:“当年的我们,人生是一条长长的路,走下去会有钻石般熠熠生辉的幸福在等我们。其实钻石早就碎了——它从来就是碎的,无数碎钻在我们不知情的瞬间闪闪烁烁,而我们只顾往前走,等待那块巨大而完整的钻石”(19)。
尽管隐含的叙述者清醒地意识到,只要现实社会不完美,人性深处有幽暗,所谓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就是一个迎合庸人的梦想而缺乏现实性的遥不可及的神话;但是,她还是坚持认同浪漫的纯情,肯定两性关系中的美好情感价值,尽管它可能破裂成为“碎钻”。
3 优雅清丽,细腻轻灵,而且充满睿智,这是潘向黎小说一以贯之的艺术个性。然而,她的近作《永远的谢秋娘》和《弥城》却出现了令人惊叹的自我超越的迹象,它们不仅将纯熟的优雅、细腻和睿智的艺术个性,推至行云流水般的自如境地,而且在小说形式方面显现出自觉的创新追求。《永远的谢秋娘》的互文性写作和《弥城》的套合式叙述结构,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小说的女性主体意识。
《永远的谢秋娘》最先触动我们的是标题与开头的“谢秋娘总也不老”(20),它们显然脱胎于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按常理说这是一般的作家想极力规避的,但是小说就这么用了!细读之后才明白,这绝对不是文本影响的关系,也不是文本戏仿的关系,而是明确的互文性标示。这种互文性关系在于,一方面《永远的谢秋娘》用锋利的女性意识,解构白先勇在尹雪艳身上所淤积的集“仙女”与“恶魔”两种极端性格于一身的男性文化意识;另一方面以女性的温情重新形塑一位从历史沧桑与世俗尘埃中挣脱出来的冷艳华丽的女性形象。
由两个互文关系的文本构成的话语空间,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想象与人性思索。白先勇笔下的尹雪艳,尽管有些神秘但并不复杂,一方面她是着实迷人、善解人意和自信独立的女性,似乎是个永远年轻的“仙女”;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煞气”厚重,似乎不可理喻的人间“祸水”,数位迷上她的男性,无论是商人还是官员最终都不得善终,在上海如此在台湾还是如此。然而,经过女性温情过滤升华后的谢秋娘,并不神秘却有些复杂。小说运用虚化的笔触暗示她生命尺度的累累伤痕,尽管尺度上的伤痕读数模糊不清,但任何不曾遗忘历史与不想回避现实的读者都不难理解,她劫难的缘由并非仅仅源于命运,更多的源于动荡的历史与不测的人生。因而在他人眼中永远姣美并风姿绰约的谢秋娘,却自认为“从来没有年轻过”;历史现实场景的巨大变幻,仿佛只是成就了她那双穿透人生和命运的锐利目光,而无法愈合她心灵的创伤。也就是说,那种藏匿于历史幽暗处的人生劫难,隐匿在她的内心深处,被坚硬的自我外壳密密包裹,这似乎成为谢秋娘生命忧郁的自我见证,以致幻化成她对世事人生的冷艳和距离。当然,也有偶然的真挚情怀使她动心,情感的自我从虚无的坚甲中逸出,表明她并不是一个性情彻底泯灭的女性,幸福的祈望依然潜存。但是,终归还是不幸的结局,这种无情的现实厄运,与其说是以偶然灾厄的方式浇灭了她生命希望的火苗,还不如说是再一次召唤起她记忆中的悲剧命运,再一次证实了人生希望的虚妄。她无奈地重新用坚硬的自我包裹起鲜嫩而脆弱的心灵,继续以矜持的自重自我抚慰,用世俗的成功挑战世俗人生。这是一种深切的同情和惋惜,也是一种凄美的绝望。如果说“仙女”与“祸水”是白先勇笔下尹雪艳的一体两面,那么极致的美丽与极致的苍凉则是潘向黎形塑的谢秋娘的一体两面;男权意识中的尹雪艳令人费解,而女性意识中的谢秋娘使人扼腕。不同的性别意识基点,生发出不同的美丽书写。
尽管我理解极致的谢秋娘,但我还是想说,也许美好与完全的东西,都像小说结局中那只精美的茶杯一样脆弱,因为人的世界原本就是一个永远充塞着千疮百孔的时空。谢秋娘有能力成为世俗社会的成功人士,而今生今世的唯美人生可能是一种虚妄,也只有永远深藏在他人无法穿透的心灵内核。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艺术乌托邦。由此来看,互文性的话语空间可以开辟无限的想象空间。不过,也只有富有创造力的作家才有勇气直面“影响的焦虑”,用独特的观念和想象挑战前辈名篇。
再说《弥城》。在我看来,这是作者小说创作中叙述结构最为复杂与精致的一个中篇小说。文本的叙述结构共含三层,首先是主叙述层次,叙述者讲述自己的历史现实人生,其中以她叙述与三位男友(同居的男友薄荷、知心男友豆沙和初恋男友木耳)和父母的生活为主。其次是次叙述层次,其中包括两个并列的叙述单元:一是叙述者与一位男友相互编撰情书,进行游戏般的情感交流;二是叙述者作为作家,与杂志的读者(为爱情所困者)交流。最后是次次叙述层次,也有两个并列的叙述单元:一是叙述者较详细地讲述了她的爱情小说的创作过程;二是叙述者为时尚杂志编撰的世俗爱情故事。如果用叙述空间的概念表述,那么这是一栋套合式的三层楼建筑:具有多个层次分明、相对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单间,同时又是一个错落有致的整体艺术建筑。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复杂的叙述结构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功能。一方面文本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以真切地表现隐含叙述者复杂的思想感情;但是为了立体地呈现这种错综复杂的思想情感,又采用了分层叙述的方式。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这种套合式的立体结构,充分表现出叙述者纠缠于生活与写作、现实与梦想之中;同时也表明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是可以相互影响甚至于相互转化的。我们从纷繁复杂的叙述中可以发现,主叙述层叙述者自以为是的深刻爱情观念,被次叙述层的叙述者之一(为爱情所困的读者)单纯而执著的爱情信念和行为震撼;而被震撼的主叙述层叙述者的思想情感,又改变了由其控制的次次叙述层人物的爱情命运。
另一方面,文本中的诸种观念形成复调的意味,当然也显现隐含叙述者本人复杂而矛盾的心理,或者说情感与理智、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也许,我们可以用小说中的两句话来概括《弥城》这部中篇小说的题旨:一是贴近自己的日常生活,让人们知道生活与写作的互相成就和互相打扰。二是远离这个城市和正常生活,讲述一个关于梦想和伤害、漂泊和回家、死亡和信念的故事。(21)然而,我认为这仅仅是支撑文本话语空间的两根支柱,而充盈其间的则是言犹未尽的女性感情生命的真切书写,因为围绕现代社会各种女性的爱情与婚姻问题,小说始终存在着诸种不和谐的声音:贴近困境的现实,则是爱情信念大厦的嘎嘎动摇;执著完美的理想,则是幸福的爱情遥遥无期;不幸的记忆构成抵御现实伤害的经验,而经验的自我又阻碍纯粹爱情的重新发生;……这种形式正如巴赫金所说:“思想就其本质来讲是对话性的。”(22)读者从对位式的意识交锋中进行判断得到启示,而意义就在判断启迪中产生。
我相信,《永远的谢秋娘》的互文性写作和《弥城》的套合式叙述结构,既是创作主体形式创新的自觉追求,更是思想意蕴水到渠成的造化,从而表现出潘向黎难以意料的创作锐力、文学悟性和创作潜质。
注释:
①②潘向黎:《白水青菜·我不识见曾梦见》,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④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页。
⑤⑥⑨潘向黎:《白水青菜·我爱小王子》,第39页,第40页,第44页。
⑦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分类只是为了便于分析而进行的,具体的文本总是比理论形态的分类丰富得多,事实上也有个别的作品还很难归类。
⑧(11)(15)(21)潘向黎:《白水青菜·弥城》,第142页,第141页,第169页,第127页。
⑩潘向黎:《白水青菜·无雪之冬》,第200页。
(12)徐坤:《双调夜行船》,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152页。
(13)(14)(16)(17)(18)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8页,第289页,第275页,第286页,第251页,第251页。
(19)潘向黎:《白水青菜·碎钻》,第94页。
(20)潘向黎:《白水青菜·永远的谢秋娘》,第51页。
(22)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第133页,第1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