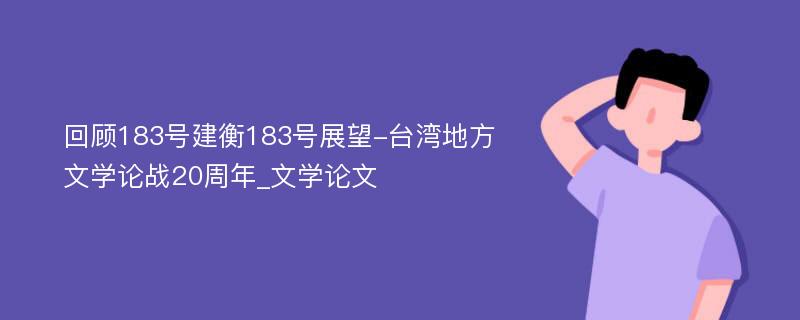
回顾#183;鉴衡#183;展望——台湾乡土文学论战2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土文学论文,论战论文,台湾论文,周年论文,鉴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人类的历史,只是整个宇宙历史的一个小小的段落。而每一种社会形态,又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小小的段落。因而所谓漫长的岁月,都不过是历史的一个瞬间。1977年至1978年之间发生在台湾岛上的乡土文学论战,那恐怖的气氛和交战的声音,仿佛还在眼前晃动和耳边回响。人们记得,那时台湾还是蒋家小朝廷的天下,反独裁、反专制、反迫害,是全岛人民的利益,也是全岛人民的呼声。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鲜明地划分为两个阵营:一面是官方的文学,站在台湾当局一边,成为蒋家小朝廷的保皇派;一面是民间文学,站在反独裁,反专制的民主运动一边,成为台湾历史潮流的推动力量。
就台湾文学的新生力量,新崛起的乡土文学来看,他们的中心任务,是努力发展描绘台湾普通劳动者和中、小工商业者及中下层知识分子生活,反映他们的意志和要求的大众文学。这种文学外反掠夺,内反独裁,把被歧视、被残害、被剥削的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作为文学的主人公,给以同情、支持和歌颂。而把官方文学中的主角、大官、资本家和跨国公司的老板、工头等,置于揭露、批判和鞭打的地位。他们要在文学上完成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重任。陈映真笔下的一系列小知识分子的形象;杨青矗笔下产业工人的形象;黄春明笔下农民的形象;王拓笔下渔民的形象;王祯和笔下小市民的形象,构成了一个五彩缤纷,波澜壮阔,而又崭新的、划时代的文学画廊。他们以摧朽拉枯之势,从政治上、舆论上、思想上、艺术上席卷着、吞没着官方的文学阵地,威慑着御用文人们的地位。于是,台湾当局惊慌了,恐惧了。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巨大的政治阴谋,穿着破旧的文学外衣出笼了。
台湾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总主笔彭歌,于1977年8月17日至19日,在台湾最大的报纸《联合报》上,连载了发难性文章《不谈人性,何有文学》,一口气点名攻击了三位重要的乡土文学作家,即陈映真、尉天聪、王拓。他在攻击王拓时写道:“不以人而以物为标准,这种论调很容易陷入阶级对立,一分为二的错误。这种态度上的偏差,伸延到文学创作,便会呈现出暖昧、苛刻、暴戾、仇恨的面目。”“令人感到并不是要‘正确反映’,而是有着恶化‘社会内部矛盾’之倾向。”他还写道:“反帝而不谈反共,这是没有掌握到时局的重点。反帝如只是反对以美、日为主的外来资本,是否是一种极不高明的转移目标?”[①]彭歌这里既攻击了王拓,又暴露了他亲美亲日的倾向。
彭歌在攻击陈映真时说:“读者有权知道,陈先生心目中如此鄙视、并“预见其必将颓坏’的旧世界,究竟何所指?而他那样向往而又不能去‘认同’的新世界,又指的是什么?”[②]彭歌暗藏杀机,要把陈映真置于死地。这段话中明明是说陈映真反对国民党而认同共产党。当时这样的罪名百分之百的是要杀头的。那时台湾有一个人,幼年在大陆参加过儿童团,70年代说了一句“长江上架起了一座大桥”,就被杀了头。按照彭歌给陈映真加的罪名,那是定死无疑的。
彭歌在攻击尉天聪时写道:“他虽然时时以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出现,但他这些高见对中国文学、历史、文化的诬蔑与损害,恐怕比那些被他诟骂为洋奴买办的西化派,有过之无不及。”[③]彭歌在长达万余字的文章中,口口声声说文学要讲人性,字字句句攻击乡土文学作家只讲阶级性,但是当人们细读他上面攻击王拓、陈映真和尉天聪的那些杀气腾腾的话,会发现彭歌谈人性是假,而要借文学杀人是真。
然而彭歌的文章不过是打头阵而已。随着这篇文章的出笼,便掀起了一个巨大的围剿运动。政界和军中的许多作家都参加了围剿,他们不仅要把刚刚崛起,尚在发展中的乡土文学夷为平地,而且要将之焚尸扬灰。有一位御用诗人,本来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闻到火药味之后,便立即赶回台湾,在1977年8月20日的《联合报》上发表了一篇《狼来了》文章。该文写道:“北京未闻有‘三民主义文学’,台北街头却可见‘工农兵文艺’,台湾的文艺界真够大方。说不定,有一天‘工农兵文艺’还在台北得奖呢。正当我国外遭逆境之际,泰(然)有人内倡‘工农兵文艺’,未免太巧合了。”[④]按照这位诗人的说法,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国际上纷纷与台湾“断交”,给台湾造成的“外遭逆境”,都是乡土文学之过或者之功了。他未免把文学的作用和地位估计得离了谱。诗人之所以如此高估,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抬高乡土文学,恰恰相反,是为了扼杀乡土文学。请看:“不见狼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问题不在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⑤]这里,他直接了当地把文艺等同了政治,还明白地要官方动用政权机器,来整乡土文学作家。在台湾那种白色恐怖下,该诗人这篇文章将产生怎样的后果,不是可想而知的吗?国民党逮捕过许许多多台湾作家,如陈映真、柏杨、王拓、杨青矗等等,都曾在国民党的监狱中渡过鬼门关。
然而,70年代如春苗般遍地崛起的台湾乡土文学,并不是一阵寒流就能冻死的。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它不仅有能力与旧事物对抗和较量,而且必定要取而代之。台湾的乡土作家们,在前辈作家支持下,在全世界华人作家和正义力量的声援下,勇敢地迎接了挑战。他们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尖锐、泼辣、锋芒犀利,现实性、战斗性、理论性极强的文章。例如:陈映真的《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尉天聪的《什么人唱什么歌》、《文学为人生服务》、《乡土文学与民族精神》,王拓的《拥抱健康的大地》,高准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王晓波的《中国文学的大传统》等等。这些文章是火线上磨利的匕首,是激战中烧热的大炮,既以强大的威力和声势扑灭了敌人嚣张的气焰,又以通俗但却精辟的理论教育了人民;既有力地批驳了敌人的谬论,又较完整地建立了乡土文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有下列几个方面:
1.台湾的乡土文学即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学。陈映真的《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和尉天聪的《乡土文学与民族精神》诸文,都深刻地阐述了这一根本理论原则。陈映真写道:“在他们已经发表的作品中,他们使用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文字形式,美好的中国语言,表现了世居在台湾的中国同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以及在这生活中的欢笑和悲苦;胜利和挫折……。这些作家也以不同的程度,挣脱外国的堕落的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扬弃了从外国文学支借过来的感情和思想,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形式,生动活泼地描写了台湾——这中国神圣的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民众。正是他们的文学,使三十年来台湾的中国文学,头一次有了生动的、具体的社会生活,和亲切、感人的为生活而辛勤工作着的同胞的面貌。这些作家们,更以描写外来经济和文化的支配性影响下农村中的人的困境,和被外来经济和文化‘国际化’了的都市中人的诸形象。批判了台湾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殖民地化的危机,从而在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上,高高地举起了中国的、民族的、自立自强的鲜明旗帜。”[⑥]尉天聪说:“我们所说的乡土文学也必然是反对分裂的地方主义的;当然它也必然地要反对崇洋媚外的买办作风的。这样说来,乡土文学也就不是指专写农村或工厂生活的作品了,只要是爱国的,关心民族前途的作品,都是乡土文学。”[⑦]陈映真和尉天聪的这一论述非常重要。在乡土文学崛起之时,他们就为乡土文学规定了明确的性质和方向,并为“台独”分子歪曲和利用乡土文学预设了坚固的理论防线。
2.乡土文学是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文学。尉天聪说:“我们批评一个人或一部作品,应该看这个人或这部作品所坚持的理想对不对,合不合乎多数人利益。谈到一部作品的内容,更应该予以检查,如果这部作品所赞扬的,是合乎多数人的利益的,就值得赞扬;如果它批判的,是违犯大多数人利益的,就应该批判。”[⑧]是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还是代表极少数人利益,这是一个根本的立场坐标问题。世界上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世界的方向,就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把乡土文学定位在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坐标上,就确定了这种文学人民性和先进性的本质。
3.乡土文学的任务和目的,是描写工人、农民、渔民等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和形象,鼓起他们的勇气和信心,为祖国独立、民族自由而共同奋斗。陈映真写道:“他们描写在激变中的台湾农村、渔港和无数厂矿中,为生活而奋斗的人们;描写处在社会转型期乡村同城市中人的困境;描写外国的经济和文学的支配性势力下中国人的悲楚、曲折、反抗和胜利。不为别的什么,而为的是他们这一切之中看见了人性更高的庄严,从而建造了这庄严为基础的自己民族的信心。”“中国的新文学,首先要给予举凡丧失的,被侮辱的,被践踏的,被忽视的人们以温暖的安慰;以奋斗的勇气,以希望的勇气;以再起的信心。中国的新文学,也要鼓舞一切的中国人,真诚地团结起来,为我们自己的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努力奋斗。”[⑨]
关于乡土文学要以中国现代的白话语言的工具,以大多数中国人喜欢的民族风格和形式进行表达等问题,他们也都进行了或详或简地论述。陈映真、尉天聪、开拓等阐释的文学理论与御用文人们的文学理论针锋相对,根本对立。这一场论战是官方和御用文人们挑起,以打击和摧毁乡土文学为目的的政治镇压运动。由于乡土文学是新兴之师、正义之师,他们的正确理论和反映人民意志的作品,得到了广大人民的坚决拥护和支持。他们的事业,他们的主张唤起了全世界华人的同情和共鸣。于是台岛内外和台岛上下形成了一个一呼百应,纷纷而起的群众运动。在强大舆论的震撼和压力下,台湾当局感到大势不妙,便紧急煞车。论战虽然草草收场了,但乡土文学却从道义上、舆论上、理论上获得了巨大胜利。乡土文学借着这个胜利的形势,得以迅速而蓬勃地发展壮大,跃居台湾文学的主流地位。因而乡土文学论战是一场民间与官方,正义与非正义,新事物与旧事物,全盘西化和反对全盘西化的你死我活的一场大论战。
二
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令》,进而开放党禁、报禁,同意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台湾社会开始了多元化的进程。各种社会文艺思潮空前活跃;各种党派社团纷纷竖起旗帜;各种政治势力重新进行了分化组合。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台湾岛内隐蔽着的“台独”分子,纷纷露出了本相;而被美、日豢养,入不了境的海外“台独”分子,也大摇大摆地回到了台湾。台岛内外“台独”分子的汇合,使台湾的“台独”势力迅速扩大,他们的嚣张气焰也日益高涨。
1977年至1978年间参加过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双方,他们的状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参与围剿和镇压乡土文学的作家们,由于他们基本上都是于1949年去台湾的大陆人,现在被抛在了台湾的政权圈子之外,又受到“台独”威胁,于是失落之情更加浓烈。对于他们来说,发生于20年前的乡土文学论战,已激不起兴趣。在目前以祖国统一和“台独”为分水岭的政治分野中,他们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如彭歌和那位诗人,均已到过大陆探亲和旅游。对于他们已经成为历史记录的过去,人们也仅仅作为历史进行阅读。
在这场论战中处于被围剿地位的乡土文学作家和理论家们的变化,令人惊讶。一部分人是祖国和民族忠实的儿子,是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事业的坚决捍卫者。而另一些当年也曾经参加过乡土文学论战的人们,很可惜却倾向“台独”那一边。
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对外反对全盘西化,反对崇洋媚外,矛头直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经济文化入侵,对内反对法西斯专政和独裁统治,矛头直指以蒋家为首的国民党政权。而如今,“台独”势力的矛头却是指向中国,指向中华民族的。
“台独”势力要把台湾从祖国的肌体上割裂出去,成立所谓“台湾共和国”,其性质与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要把台湾从中国割裂出去的性质是一样的。何况“台独”本来就是美、日反华势力操纵的一粒“卒子”。由于台独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割裂出去,他们就极力夸大和捏造所谓“台湾与中国不同之处”;制造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国领土的神话,故意歪曲台湾的历史和文学史,歪曲和涂改台湾日据时期抗日爱国作家的作品和遗训,企图把那些深深热爱祖国和中华民族的爱国作家,例如张我军、赖和、吴浊流、杨逵、种理和等也拉入“台独”的泥沼之中。他们企图利用国民党在台湾干下的坏事和大陆“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移花接木,煽起台湾老百姓对祖国的不满和仇恨。他们无中生有地口口声声说什么“台湾民族”,仿佛他们从来就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曾经在70年代台湾的新诗论争和乡土文学论战中活跃过的,如今号称“台独”文学理论家的陈芳明,是近年来从事“台独”文学理论最活跃,最具代表性的投机人物。陈芳明1970年曾是台湾新诗回归运动中首先崛起的,高举中国诗的旌旗,向西化诗风冲锋陷阵,名满台湾的“龙族诗社”的发起人之一,担任过《龙族诗刊》主编之职。当年他也写了不少歌颂中国诗歌精神和风格的文章。还是这个陈芳明,到美国去镀金,受了一段时间的熏陶,再回台湾之后,名字变成了“宋冬阳”(如今又回归“陈芳明”),人也变成了一个“台独”逆流中的死硬分子。他强烈地反对“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部分”,他在《现阶段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一文中写道:“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无疑是受到中国五四文学的启蒙与刺激,从这个历史角度来看,把台湾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要谈历史问题,就不能以孤立和抽离的方式来观察,因为在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家也颇受日本文坛与政治运动的影响,这一点在杨逵、叶石涛的小说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同样的,战后的台湾小说家,如林怀民、黄春明、陈映真等人,也颇受西洋文学的冲击影响。从相同的历史角度看,台湾文学甚至可以说是日本文学和西洋文学的一部分了。”[⑩]陈芳明竟以诡辩的方式来戏弄历史。不仅如此,他还激烈地攻击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一部分”的陈映真。陈芳明写道:“然而陈映真的历史观如此,他的文学理论又是以此而发展出来,所以在他的行文之际,凡提到台湾文学之处必然以‘在台湾的中国文学’来概括。这个名词,与其说是文学语言,倒不如说是政治语言。在他的思想模式中,‘台湾意识’既然是附属于‘中国意识’之下,那么,台湾文学也就无可避免是中国文学一支流了。”[11]查一查“在台湾的中国文学”这句话的最初版权并不是陈映真的,而是最受陈芳明崇敬的。提出“台湾意识”的是叶石涛。叶石涛早在1977年5月号《夏潮》杂志上发表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中就有“台湾意识——即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的共同经验”。他1982年1月15日发表在《台湾文艺》上的《台湾小说的远景》一文中也有“台湾文学是居住在台湾岛上的中国人建立的文学。”象这样的句式,在叶石涛的其他著作中也有。至于“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或“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支流”更是台湾许多前辈作家共同的版权,是被他们一再肯定和阐释过了的结论。现举数例如下:台湾新文学理论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张我军在《请全力拆下这座野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中说:“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一支流。”《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的作者陈少廷说,台湾文学“是发源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支流”[12]。叶石涛在《论台湾文学应走的方向》一文中说:“拥有几达六十年历史的台湾文学,一直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可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支流”的论点,也并非陈映真的发明。陈芳明企图用几句胡诌的话来否定和歪曲数百年,千百个台湾作家用血泪和智慧写成的文学史的性质,恐怕也是万万办不到的。台湾文学史的创造者和目击者用心血写成的结论,不是陈芳明能够用水调成的墨可以改变的。陈芳明为了为他的“台独”活动寻找历史依据,竟任意纂改和歪曲台湾的新文学史实,诬蔑台湾的革命者和前辈作家。他说:“客观的历史告诉我们,1919年,林呈禄、蔡培火、王敏川、蔡式谷、郑松筠、吴三连在日本东京筹组‘启发会’时,就提出‘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之主张……这些右翼组织,全然是以追求台湾人的自治为终极目标。至于左翼团体如台湾共产党者,则进一步主张‘台湾独立’。[13]陈芳明故意偷梁换柱,转移历史的背景,改变历史的内涵来谈历史。台湾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启发会”和30年代的“台湾共产党”提出的“台湾自治”和“台湾独立”,其抗挣对象是日本占领者,目的是要摆脱日本血腥的殖民统治,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中来。当时“启发会”提出的“与祖国取得联系”,“争取祖国的声援”,“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带着祖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意愿去台湾开展抗日活动,不正好都是对陈芳明的一种驳斥。“启发会”的“台湾自治”和“台共”的“台湾独立”是以祖国、民族为后盾,将被日本人占领的台湾夺回到祖国和民族的怀抱中来。正体现了他们忠于祖国、忠于民族,心向祖国、心向民族的品质。而陈芳明如今搞的“台独”却是反祖国、反民族的,是要把台湾从祖国、民族的肌体上割裂出去。陈芳明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事实证明,这些被欺凌、践踏、损害,以至被迫走向死亡的知识分子,全然是遭到‘中华民族主义’的压迫。这原是残酷的历史嘲讽,当他们含泪地高举‘中华民族主义’的旗帜时,他们内心必然感到神圣而不可侵犯;很不幸的,他们的悲剧结局,竟然也是仆倒在‘中华民族主义’的旗帜下”[14]。陈芳明是如此仇恨“中华民族主义”。
企图利用历史,而又歪曲历史的人,不是心术不正,就是别有用心,最后必被历史所淘汰。70年代台湾的新诗论争和乡土文学论战,是台湾文学中反西化,反崇洋媚外和中国民族文学精神与风格复归的历史;是反专制、反迫害和争取民主自由的历史;是充满中国精神、体现中国民族风格的乡土文学大崛起的历史。我们只有坦然面对这样的历史,正确地总结和发扬这样的历史,而不是回避和歪曲这样的历史,才能够站在历史的根基上,展望台湾文学的未来。
三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意志,理想和利益的不同和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处于这种层出不穷而又变化莫测的矛盾运动中的人们,就像搅拌机中的水泥和石粒,在不断的搅拌中加强其混合。而人类社会群体的组合,是由理想和利益驱动的。它比水泥和石粒的混合更为复杂。其中有正义的,有非正义的;有为理想而成团,有为利益而结伙;有为掠夺而拜把,有为奉献而结义。不管是哪一种类型,这种混合过程都会直接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距今已经20年,在这20年中社会组织结构和情感结构的变化引起对它看法的变化有之;历史变迁和人们兴趣的转移引起对它看法的变化也有之。6年前,即1991年元月,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14周年之际,台湾《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曾动用人力财力,辟专门版面举行了一次乡土文学论战专题回顾和讨论,从元月4日至7日在《走过七○年代的文学标竿——回顾乡土文学论战专辑》的标题下,连续发表了叶石涛、黄春明、陈映真、蔡源煌、张大春、应凤凰等人的文章。这次回顾和讨论的主办单位,希望借重这些作家、学者的回顾和讨论,“使重新出土的‘乡土文学论战’能够成为刺激台湾文坛向前迈进的良性效素。”参加这个专辑的作者,除了陈映真和黄春明是当明事件的中心人物外,叶石涛、应凤凰是论战的边际人物,至于张大春和蔡源煌却是未着边际的人物。因而他们对乡土文学论战看法,有着极大的区别。有肯定的,有否定的,有模棱两可的。例如处于当事人地位的陈映真和相关地位的叶石涛就与处于不着边际人物的张大春和蔡源煌的看法,截然不同。陈映真认为:“19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提起,是针对1950年代以降支配台湾文坛20年之久的,模仿的,舶来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批判和反论。”他认为:那次“乡土文学论战不够深入,理论发展不足,乡土文学、民众文学、民族文学缺乏理论定位,对现代派文学的分析批判理论也嫌贫弱。……理论的发展不足,对于其后台湾文学迅速的商品化,和荒废化,以及运动的不曾持续发展,起到主要的影响。”[15]叶石涛认为:“陈映真、王拓、尉天聪等作家只是努力要把以往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的反共八股文学及60年代的西化无根的放逐文学,从歧路上拉回传统的写实主义文学的道路上来,反映这块土地的人民真实的生活状况而已。……不幸昧于知悉海峡两岸文学写实主义发展历史的一部分作家,却指控乡土文学有与‘共匪’隔海唱和,提倡工农兵文学之嫌。由两岸文学交流日渐频繁的今天来看,这有些荒谬而滑稽。”而不着边际的蔡源煌和张大春,不是隔岸观火,就是各打五十大板,或者一股脑给予否定。蔡源煌认为:“加入论战的人愈多,意见愈杂,双方都说了好些有道理和无道理的话,而且往往只凸显了情绪上的立场,理论基础很薄弱,离题的言论也很多。情急之际,‘三民主义的文学’这番大道理也让‘被告’的一方搬出来解危、辩护。连什么‘社会写实’,‘社会主义写实’,两者如何区辨,竟然成了一时的热门话题,大伙儿不厌其烦地竟相申论。”[16]而张大春则说:“依我看,‘乡土文学’四个字的匾是被自己心里明白的两面挂起来了,可两面的眼力都聚不到匾上,便都急慌慌地误以为对方是来摘匾的,争吵之间,也无可质证,索性把匾砸了,然后互相埋怨对方是存心来砸匾的。一场论战搞砸一块招牌,真是不堪回首得很。”[17]
一声因政治利益引起的迫害和反迫害的政治阴谋;一场尖锐激烈,壁垒分明的以文学名义进行的政治性斗争;一场反西化,中国文学精神和风格的复归和重建运动;一场关系到台湾文学前途,由全社会卷入的乡土文学大论战,在有些作家的笔下,竟变成了无是非的儿戏;变成了双方都存心“摘匾”又各自耍赖的骗局,“真是不堪回首得很”。这种看法上的巨大差别,并不是事物本身有什么变化,完全是不同利益下的立场问题。
历史是不能改变的,但历史却是可以改写的;历史的总方向是不变的,但历史的道路却是曲折的。陈芳明等人不是时时刻刻企图改写台湾的历史和文学史吗?台湾文学史的重要一章——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已经出现了被人改写的趋向,如今在它发生的20周年之际,台湾各方都已开始筹备纪念和研讨活动,这段重要的历史将面临着继续被改写和歪曲的危险。面临这种复杂的形势,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的见证者们肩负着神圣的使命,那就是以自己亲身经历和目睹的历史事实,努力阻止将历史任意改写和歪曲的任何企图,使历史以其本来的精神面目传承给后人。在当前尤其要注意某些人否定和歪曲那次乡土文学论战的灵魂——中国文学之魂和中华民族文学传统和风格的复归和重建。作为炎黄子孙,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注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尉天聪主编,《乡土文学讨论集》第249、253、257、266、267、335、163、159、338-339页,台湾远景出版公司1980年10月出版。
⑩ 11 13 14陈永兴编,《台湾文学的过去与未来》第19、17、16-17、29页,台湾文艺杂志社1983年3月出版。
12陈少廷编写,《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第162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5年5月出版。
15 16 17台湾《中国时报》1991年1月6日、1月4日、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