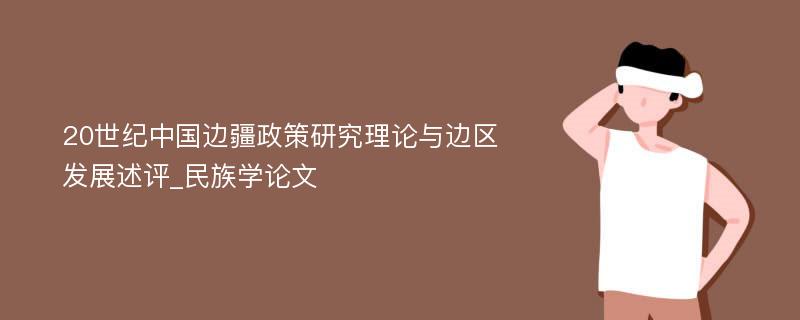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边政研究与边区开发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区论文,述评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20世纪中国西部边区开发研究的几个阶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迫于国家民族危亡之压力,内地的政治、教育、学术文化机构纷纷迁至大西南后方。一时间,除重庆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外,昆明、桂林也成为学术文化中心。为了巩固边疆,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将边区开发列为主要政务。当时边疆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居民复杂、语言文字殊异、风俗礼制不同,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情形与内地汉族地区差别较大,政务往往难以顺畅推行,中央政府对许多边疆地区无法实施直接管理。为此了解边疆民族情况成为当时南京、重庆国民政府的迫切需要。在政府大力倡导下,中国民族学界兴起了民族学中国化运动;注重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出版了《边政公论》、《新亚细亚》、《边疆研究论丛》、《西南边疆》、《东方杂志》、《中国边疆》、《责善》、《边疆人文》、《中国文化研究汇刊》、《西南边疆问题研究报告》、《旅行杂志》、《史语所集刊》等数十种专门刊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深入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搜集调查政治、经济、历史、风俗、宗教、语言等状况报告的刊物[1],作为国民政府治理和开发边疆地区的决策依据。政府的大力倡导、资助与当时民族学中国化运动,提倡联系实际救亡图存,研究边疆、建设边疆的目标达到了很好的统一。
研究中国民族学史的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民族学家的工作除“努力于史学的、语言学的、民族学的一切资料之有规律的搜集”外,还参与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作西南、东北各地民族的体质调查与分类;对公众和学生介绍国内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和各民族历史、文化情况;著文呼吁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少数民族的轻视;1937年进行筹划的全国风俗简易调查;部分民族学家积极参与建设一门新的关于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边政学”[2]。
从机构建设上来说,国民政府当局积极支持成立了主要由民族学家组成的边政学会;在中央政治学校特设了边政专修班,蒙藏委员会开设了蒙藏政治训练班;西北大学、中央大学相继成立边政学系。一些大学也开设了边政学课程。吴文藻任重庆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参事、蒙藏委员会顾问、边政学会常务理事并主持《边政公论》,吴景超、张镜予、陈国钧、杨成志、梁钊韬、江应梁等民族学家也在中央地方各级政府担任与边政有关的职务,致力于将民族调查研究成果和民族学系统知识贯彻在实际工作中,如江应梁主持编著了《边疆行政人员手册》,参与草拟了《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思普沿边开发方案》等,指导云南地方行政当局和人员。凌纯声、吴文藻等人也在抗战时期参与了边疆文化教育工作,凌纯声担任了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
许多民族学家撰文阐述民族学与边政研究相结合以及发展应用人类学的主张。杨希枚先生指出:“今日边政的改善,已是人类学界所共鉴而不可或缓的事实;而它的改善复需要人类学的辅导,所以今后的人类学界,不仅趋向综合的研究,更应趋于实际问题的研究,始能担负新的任务”[3]。
民族学家们希望以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理论方法去整合各分支学科,以推进边政研究的规范和整合,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用。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凌纯声的《中国边政改革刍议》,黄文山的《综论殖民地制度及其战后废止的方案》,吴泽霖的《边疆问题的一种看法》,卫惠林的《战后世界民族问题及其解决原则》和《论世界文化与民族关系之前途》,杨希枚的《边疆行政与应用人类学》等文章都体现了这种思路。这些努力使得民族学人类学成为抗战前、抗战时期至抗战后对中国政治当局和学术界影响力极大的学科。
从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提出边政学的纲要,阐明人类学在边政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后,随着边区开发工作的进展,理论认识逐渐深化。至1941年,马长寿、杨成志等民族学家已提出系统的处理边疆民族政治地位、文化价值的基本原则和建设边疆的具体措施,如边疆武力的国防化,边疆政治的民族化,边疆经济的现代化,边疆语文的国语化,边疆官吏的专门化等途径[4];并从理论高度思考边疆少数民族在抗战后出现的新问题,指出蒙古族、苗族、彝族和新疆各民族问题的尖锐化反映了“国内一切民族平等”的政策未见实施和边政设施建设缺乏,加剧了民族问题的严重性,要从当时国际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民主运动发展潮流的背景来认识上述问题,边疆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若无妥善的办法应付,或许会引起领土和国际纠纷的问题[5]。
从上述情况看,从1930年前后杨成志先生、凌纯声先生等人深入西南、东北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带动大批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家进入中国东北、西北、西南地区开展学术活动,到抗战时期“边政学”的兴起,再到抗战后对边疆民族地区开发问题的关注,反映了这一阶段在20世纪中国边区开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间所产生的理论主张值得今日西部开发予以借鉴。
二、《边政学发凡》所体现的系统思想
吴文藻先生的《边政学发凡》[6]一文,在边政学会和《边政公论》自1942年至1948年所刊发的大量中国边疆民族地区调查报告与论文中,具有“总论”的性质。这不仅仅是吴先生所担负职务带给他宏阔的理论视野与切实的现实观照,亦是吴先生在中国民族学界的学术地位以及一贯的学术思想的体现。
吴先生在文中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概念,现归纳于下:
首先,“研究边政学的目的有二:一是理论的,一是实用的。”从理论建设来说,“边政学原理的阐发,可使移植科学迅速发达,专门知识日益增进(即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诸外来学科的中国化和系统化——引者注),举凡人口移动、民族接触、文化交流、社会变迁,皆可追本溯源、探求法则。这是边政学在理论上的功用。边政学范围的确定,可使边疆政策有所依据,边疆政治得以改进,而执行边政的人对于治理不同文的边民,亦可有所借鉴。‘为政由学始’就是这个道理。这是边政学在实践上的功用”。
第二,提倡边政学实用研究的意义在于:“第一、在本国的意义,中国这次抗战,显然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而不是国族内某一民族单位的解放战争。全民族求得解放,达到国际平等的地位以后,就须趁早实行准许国内各民族地方自治的诺言,而共同组织成为一个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族。建立一个多民族国家。”“第二、在国际上的意义,中国是反侵略的先锋,是抵抗强权的领导。……这次抗战的胜利,对外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对内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以后,可在和会席上,提高我们的地位,加强我们的发言权。”
第三,研究边政学的观点即出发点,吴先生认为,“一是政治学的观点,一是人类学的观点”,“兹以人类学的观点为主,而以政治学观点为辅,来作边政学初步的探讨”。认为政治学教授及学者,大多对边政学研究态度淡漠,有的学者甚至根本否认边政研究的需要,以为中央政治一上轨道,抗战胜利一有把握,所谓边疆民族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人类学者则认为:必须乡政与边政首先切实上了轨道,中央政治才能真正走上轨道。“甚至可以说,边政与乡政是吾国现阶段上中央政治的核心问题”。
吴先生认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要在理论和应用上同时并进,应用则以资政为要。他说:“西洋所谓应用人类学,大都是以殖民行政、殖民教育、殖民福利事业,以及殖民地文化变迁等题目为研究范围。在中国另换一种眼光,人类学的应用,将为边政、边教、边民福利事业,以及边疆文化变迁的研究。”因此,“应以边政学为根据,来奠定新边政的基础,而辅助新边政的推行。”
在此,吴先生提出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中国边政学是以应用人类学为理论模式;二是须以人类学为核心观点来整合、检视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的观点。
第四,关于边政、边政学的定义,吴先生认为,“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通俗地说,边疆政治就是管理边民的公众事物。用学术语,边政学就是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边疆政治是地方政治的一种,系对中央政治而言。”
第五,关于“边疆”的涵义,吴先生认为,一是政治上的边疆,一是文化上的边疆。前者涉及国界、边界、以地理上的边疆为基础。国界包括陆界、海界,而过去称边疆为“塞外”、“域外”、“关外”,称内地为“中原”、“腹地”、“关内”则代表了政治及地理的观点。“文化上的边疆,系指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而言,所以亦是民族上的边疆”,以文化划分边疆,出现“我群”与“他群”的观念,旧称边疆为“化外”,亦代表文化的观点。“边政学是从政治学与人类学同时着眼,所以边疆的定义,亦应该同时包括政治上及文化上两种意义,兼而有之,才属恰当。例如以往沿用‘蒙疆’、‘藏疆’‘回疆’、‘苗疆’诸名称,本含有双重的意义,一面是国界上的边疆,一面是民族上的边疆”,“边疆是指:中部十八省以外而邻近外国的地方而言,如蒙藏及辽吉黑热察绥新宁青康等省是;中部十八省中住有苗夷羌戎各少数族的荒僻之区而言,如陕甘湘桂川滇黔等省之边区是。”
第六,关于“民族”的定义,吴先生认为,民族与种族有别,民族乃社会人类学研究之对象,故为文化的概念;种族乃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故为一生物的概念。文化上的民族与生物上的种族,二者绝对不能混作一谈。
第七,关于边疆民族的类型,吴先生认为,“边疆民族系指国内僻居边地或邻近边地的各种少数民族或浅化民族而言。有全民族聚居于一个区域,别无他族混杂其间而自成一个政治单位者;有全族聚居于一个区域,虽有他族杂居其间,仍不失为该区内最大多数的民族;又有许多零星小族散布于各边省荒僻之区;复有若干混合民族——即中华民族所赖以构成者——分布于幅员辽广的边远省区以内,其涵化程度,介乎纯内地与纯边地人之间,能通两种语言,过惯边缘文化生活。如来自各族而被国族化的边地人,及去自各省而被土著化的内地人是。”这被文化人类学或社会学称为边缘人。“边缘人因受文化交流的冲击,性情尤为活跃,在沟通边地与内地的民情上,在融恰民族的感情上,尤处于重要的地位。凡从事边政学的人,对于边缘文化及边缘人,应该特别予以重视。边政之能否有效促进,实以此辈边缘人为关键”。
这里,吴先生不仅精确地描述了边疆民族的类型,特别指出处于民族交流、民族融合的“涵化”过程中的边缘人及边缘群体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对此的探讨能推进中华民族国家内各民族的相互融合。
三、其他边区开发理论探索述评
进入20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以后,费孝通先生在其以往对中国社会文化特点与规律的把握基础上,提出一系列边区开发理论观点。
第一是早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乡土中国》就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作为农业社会的乡土文化特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具有乡土文化特征[7]。
第二是秉承社会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模式,提出研究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三层架构理论,由社区村落——小城镇——区域中心(都市)三个层次组成的由微观到宏观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功能系统[8]。
第三是自1989年出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理论研究,于1999年出版了由马戎、周星主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系统阐述了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理论基础,对于解决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之间、中部与西部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民族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是费孝通先生主持并推动了一系列与边区开发相关的国家级重点研究项目,如1984年,他在考察了内蒙古赤峰地区和包头市之后,写下了《赤峰篇》和《包头篇》,明确提出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边区开发是一个与沿海地区发展同样重要的大问题,促使边疆地区发展问题成为当时刚刚成立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两大研究领域之一;费先生于1985年至1990年期间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七五”重点课题“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并提出了研究的整体设想和基本思路,分为13个研究专题:人口迁移、民族关系、民族教育事业、资金引进、外来大企业的作用、商品流通与边境贸易、基层经济组织与社区发展、小城镇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人口增长与计划剩余、国外影响与跨境民族、宗教与传统文化。这13个专题涉及到我国边疆地区发展中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以及影响发展的主要因素。
继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潘乃谷教授连续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八五”规划课题“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和脱贫致富问题”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课题“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前者的研究成果汇集为《多民族地区:资源、贫困与发展》(潘乃谷、周星主编),后者在对我国西部三个最重要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新疆、西藏的经济发展进行区域性模式研究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研究》[9],这些研究课题均体现了费先生边区开发理论的基本倾向。
第五,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之后,费先生在以往关注经济发展、社会组织的基础上,提出了从文化的、民族的角度整体上推动西部边区开发的重要观点。他说:“是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人文资源的认识,反过来,对人文资源的认识也将促进人们对经济发展的更深一步的认识。人们将认识到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我们的唯一目的,经济的发展只能解决我们生存的基本问题,但如何才能生存得更好,更有价值,使自我价值的发挥得到更宽阔的拓展,并从中发展出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是需要在原有的人文资源的基础上,用文化和艺术的再发展来解决的”。“开发和利用人文资源不仅能产生新的人文精神,同时也能创造新的经济价值”[10]。费老认为,“围绕着西部的文化变迁和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这个主题”是可行的。可采用社区研究的方式来做,注意类型对比和理论联系实际。这些话虽只是费先生与其弟子交谈中的片言只语,但仍体现了从整体上考虑西部边区发展的思路。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从“八五”、“九五”到“十五”期间开展的第一期和第二期“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以县域为单位开展的调查也提出一些发展思路;近来又开展了沿边地区小民族生存发展的研究。云南大学于2000年进行的跨世纪云南民族调查及其后推出的《跨世纪云南民族调查丛书》,以调查报告和专题研究的方式,从社区村落入手,探索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协调发展问题[11]。
在20世纪后半期的西部边区开发理论探索中,还应提及云南教育出版社于1992年至1997年推出的《西南研究书系》,该套丛书贯彻了总序中对西南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状况的重新定位,以及对西南与中原、西南与周边地区及文化圈关系的人类学思考,是具有“主位”理念与视角的西南边疆研究的宣言[12]。
标签:民族学论文; 边疆论文; 人类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政治论文; 吴文藻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