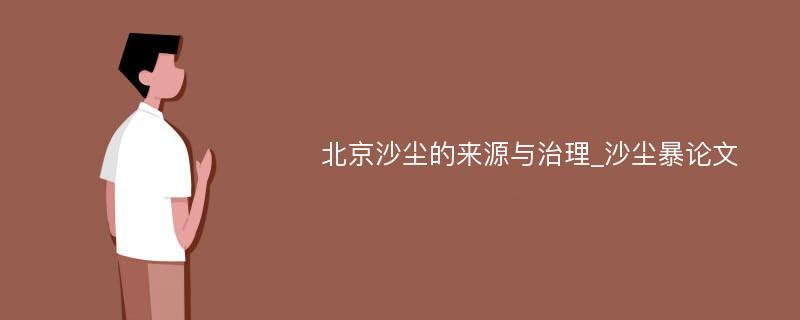
北京沙尘天气的沙尘来源及其治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沙尘论文,北京论文,天气论文,来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北部,太行山和燕山分别横垣于城市的西侧和北侧,使北京本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然而,由于受东进及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常常受到风沙的侵袭。
虽然,从第四纪以来北京就饱受风沙的危害,但最为严重的时期是在距今12万~1万年间的晚更新世。这是我国大陆第四纪以来最为干冷的一个时期,我国西北的主要沙漠在这一时期得到全面扩张,一些内陆河湖由于缺水而干涸。盛行的西北风将中亚及我国西北地区的大量表土刮起,输送到几百以至上千公里之外又抛洒下来,形成一层厚厚的黄土,覆盖在北方的大地上。这层黄土在20世纪20年代为地质学家在北京西郊门头沟区斋堂镇马兰村发现,并与此前形成的午城黄土和离石黄土相区分,命名为马兰黄土。从这里可以看到,北京受到风沙危害是故已有之。进入全新世(1万年前至今)后,我国大陆进入了有史以来的最适气候期,气温和降水都比以往高得多,干旱区范围及干旱强度也小得多。这一时期全球海平面大幅度上升,我国渤海海面的上升曾导致河北黄骅、献县遭到海侵,表明海岸线比现代西移了大约50公里。植物的旺盛发育,使一些沙地的流沙得以固定,风沙危害也大大减弱。在最近的两三千年里,气候虽有多次冷暖干温的变化,但总体上北京受到的风沙危害远未达到1万年前那样的程度。
近50年来北京的沙尘天气概况
据有关统计资料,北京地区的沙尘天气与我国北方地区的总体情况相似:最严重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6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减轻,80年代以来发生日数呈明显下降趋势,到90年代中后期年均发生日数降到建国以来的最低点(表1)。
表1 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京沙尘暴和扬沙天气统计
年代 沙尘暴(日数)
扬沙(日数)
合计(日数)
1954-1960 4.1 52.156.2
1961-1970 4.6 20.825.4
1971-1980 1.4 22.323.7
1981-1990 0.7 12.3 13
1991-2000 0.4 4.7 5.1
1956-2000 1.9 17.9 19.8
2000 0
14
14
2001 099
然而,近年来沙尘天气发生次数呈现急剧上升趋势。1998年4月16日的沙尘天气由于正好和一次小的降水过程相遇,在北京及华北地区造成大范围的泥雨,并波及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2000年4月6日的沙尘暴造成首都机场上百次航班延误。2001年1月1日,正当人们欢庆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是沙尘暴取代了新年的钟声将中国带进了21世纪。2002年春的沙尘天气强度之大,每次沙尘天气过程持续时间之长,都为多年来所罕见。
据统计,2001年我国北方地区分别发生沙尘天气18次(强沙尘暴3次、沙尘暴7次、扬沙5次、浮尘3次)。受其影响,2001年北京地区出现沙尘天气11次,其中浮尘间有扬沙的6次,浮尘3次、扬沙2次(表2)。
表2 2001年3~5月北京地区主要沙尘天气过程概况
日期
天气现象
持续时间
路径
主要影响系统来源
1.1
浮尘、扬沙
西北 蒙古气旋和冷空气;
西北地区及内蒙
3.2-3 浮尘、扬沙
18小时
西北
蒙古气旋和冷空气;
西北地区及内蒙
3.5-6 浮尘、扬沙
15小时
偏西
蒙古气旋和冷空气;
西北地区及内蒙
3.13 扬沙 3小时
偏北
蒙古气旋和冷空气;
内蒙及陕宁北部
3.21-22 浮尘、扬沙 20小时
西北
蒙古气旋和冷空气;
内蒙中部、陕北及宁东
3.24
浮尘、扬沙 10小时
偏北
蒙古气旋和冷空气;
河西走廊及其以东
4.7
浮尘(部分) 12小时
西北
蒙古气旋和冷空气;
西北地区及内蒙
4.9
浮尘(局地) 3小时
西北
蒙古气旋和冷空气;
本地
4.17
浮尘(局地) 6小时
蒙古气旋和冷空气;
西北、内蒙西部
4.29-30
浮尘
15小时
西北
蒙古气旋和冷空气;
西北地区及内蒙
5.13-14 扬沙、浮尘
蒙古气旋和冷空气;
西北地区及内蒙
资料来源:国家气象局
沙尘天气带来的大量可吸入颗粒物长时间悬浮在空中,成为北京大气污染的重要类型,与城市废气共同成为影响北京大气质量的两大灾害。日趋严重的沙尘天气给北京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发展及市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也使北京作为第一流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受到损害。
北京地区沙尘天气的沙尘来源分析
(一)北京沙尘来源分析
风沙动力学实施证明,在风力作用下,沙砾一般以沿地表滚动方式移动;粗沙一般呈跳跃方式移动,跃起高度可达几十厘米;细沙可被吹扬起2m,小于40μm(微米)的粉沙则可被带入4000m以上高空,空中输移距离可达数百公里;12μm的粘粒随风输移距离可达3000km;小于12μm的可达7000~10000km。
关于北京地区的沙尘来源,虽有种种说法,但多为定性描述。近两年来,随着人们对北京沙尘天气状况更加关注,以及监测手段的提高,一些学者开始对北京地区沙尘天气的沙尘来源进行定量性研究,也得出了一些初步结论,初步揭示出北京地区沙尘来源的基本情况。
1.悬浮颗粒物的机械组成分析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利用激光雷达和地面监测系统对沙尘天气的监测结果表明,“北京的沙尘多是从近4000m高度进入北京上空,并随时间推移沙尘团逐渐下降到地面,对近地面大气颗粒物浓度产生影响”。他们将北京冬春季沙尘天气分为:高空传输-地面扬尘混合型(占40%);高空传输-沉降型(占40%);地面扬尘型(占13%);高空传输过境型(占70%)等4种天气类型,并确定了不同天气类型时外来沙尘对北京市大气颗粒物浓度的贡献率,其贡献率范围在53%~72%之间。
北京师范大学庄国顺对北京沙尘天气大气悬浮颗粒物的分析表明,粒径小于2.1μm的细颗粒占总颗粒的6.1%,小于9μm的细颗粒占总颗粒的76.9%。
从风沙动力学原理看,北京地区沙尘天气中的大部分沙尘,应是从距北京较远区域经长距离传输而来的。
2.悬浮颗粒物的化学成分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庄国顺对2000年北京沙尘天气期间大气悬浮颗粒物的化学成分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在平常时期,悬浮颗粒物中铜、锌、铅、镉4种金属元素的含量很高,而在沙尘暴期间四种元素的含量却仅为平常的1/5~1/3。这四种金属元素在大气中的分布,往往与冶炼业及金属加工业较活跃的工业化城市关系密切,表明这些元素主要来自北京市区及近效地区,亦即沙尘主要来源区不是北京及其附近。悬浮颗粒物中化学元素的富集程度分析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结论。
在沙尘暴发生期间,悬浮颗粒物中砷、硒、锑三种元素的富集系数却分别由平常时期的253、2097、516增加到274、2243、894,由于这三种元素是煤的主要杂质,说明有相当部分的沙尘来自于晋、陕、蒙等主要产煤地区,或在途经这些地区时得到大量地面沙尘的补充。
3.卫星云图的分析
从2001年北京地区11次沙尘天气的组成来看,浮尘天气有2次,浮尘间有扬沙7次,扬沙2次。在去年的11次沙尘天气中浮尘总次数达9次,占沙尘总次数的82%。可以肯定,这9次沙尘天气的沙尘主要源自北京以外的远距离沙尘源区。
扬沙天气有两种情况,沙尘可能源于本地,也可能随着强风来自于距离较近的北京周边地区。由于北京的沙尘天气是受大尺度天气状况控制的,一般能导致北京发生较大范围扬沙的大风天气,通常是挟带着沙尘的冷空气或蒙古气旋。因此,无论冷空气到达时北京本地是否发生扬沙,浮尘都已发生了,都已构成了北京的沙尘天气。再让我们看看今年春天发生的几个例子:
一是2002年3月20日的沙尘天气,前一天(即3月19日)北京天气比较平和,没有大风,更没有发生扬沙,然而20日晨北京下了一场泥雨,使停在路边的汽车,周身泥迹斑斑。那么,沙尘是哪儿来的?原因是19日晚上内蒙古发生了一场强沙尘暴,其沙尘在20日清晨已漂移到北京。
二是2002年4月5日,在人工增雨措施配合下,北京地区普降中雨(10~20mm),此后的几天内,地表一直处于湿润状态,不可能扬沙起尘。然而,4月6~8日北京地区却出现了今春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强度也较大的扬沙及浮尘天气。显然,用本地扬沙的原因是难以解释的,气象卫星云图揭示的原因,是受来自蒙古国并在我国内蒙古得到加强的强沙尘暴影响所致。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2000年《关于我国华北沙尘天气成因与治理对策》的咨询报告,以及有关专家的研究结果也都表明北京地区沙尘天气的沙尘主要来自于北京以外的地区。
4.地面实地调查(监测)结果
1994年和1999年国家林业局先后组织开展了两次全国荒漠化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建立了沙化土地数据库和图库,沙化地区近40万个沙化土地地块的基本资料——包括土地利用类型、沙化状况,植被种类、覆盖度、面积、适宜治理情况等数十个因子,全部进入了数据库。将监测结果与沙尘天气的卫星云图对应分析表明,卫星云图沙尘浓厚的地方与其所经过地区地表植被状况关系非常密切。这些严重沙化土地正是东部地区沙尘的重要源地。
此外,北京市大气观测结果也表明外地沙尘对北京的影响很大。密云县上甸子观测站,地处北京最北部,海拔较高,受北京市区大气污染的可能极小,可作为北京大气零污染的对照点。然而,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该点可吸入颗粒物的年日均值为每立方米70μg(微克),而国家质量目标要求是每立方米100μg,这就意味着即使市区一点儿也不排放,可吸入颗粒物已接近最大上限。显然,即使在平时北京市可吸入颗粒物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外地。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导致北京地区沙尘天气的沙尘既有北京以外地区,也有北京本地,但主要来自于北京以外的地区。北京本地的沙尘,往往是在带有大量沙尘的冷空气或蒙古气旋侵入时伴随发生的,对已经形成的沙尘天气起到了加强的作用。
(二)北京沙尘源区的具体地理区域
北京沙尘源的具体地理区域主要包括北京周边地区、西北地区、北京本地及境外共四个方面。
华北北部(北京周边)地区,主要包括内蒙古高原中南部的锡林郭勒草原、浑善达克沙地、乌兰察布高原-河北坝上-山西雁北的农牧交错区。这里干旱少雨(一般年降水量为200~350mm),值被稀少,沙尘物质丰富,加之近年来过度放牧、毁林毁草开荒造成大范围土地严重沙化,是离北京最近的沙尘源区。有意义的是,打开近几年偏北路径沙尘暴卫星云图,沙尘浓度最高的正在锡盟草原西北部,这恐怕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这里地势高出北京1000m以上,离北京直线距离仅有二三百公里,且处于南下冷空气的通道,因而对北京环境威胁很大。2000年4月6日袭击北京及华北地区的特大沙尘暴就主要起源于这里。
西北干旱区,主要包括河西走廊与阿拉善高原及新疆东部、乌兰布和沙漠与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河套地区(主要是耕地裸露)、黄土高原北部等地。该范围除贺兰山以东年降水量高于200mm外,其余地区年降水量多在150mm以下,属典型的荒漠或半荒漠地带,气候极端干燥,我国的主要沙漠都分布在这一地区。这里土质疏松,沙尘物质十分丰富,植被极为稀少,是我国沙尘暴的高发区。2001年影响东部地区的沙尘天气,多数来自于这里,或在途径这里时得到大量的沙尘补给。
西北地区虽然距离较远,但因其地处西伯利亚冷空气东进的通道,且受青藏高原隆起的影响,导致风力十分强劲,沙尘经高空气流输移,往往以浮尘形式直接影响北京及整个东部地区,2000年及2001年影响北京地区沙尘天气的沙尘就主要来自于这些地区。
北京近郊及市区的就地扬沙,也是导致北京沙尘天气的沙尘来源之一。北京近郊和近郊地区处市区外围,是风沙进入市区的必经之地,由于耕作的习惯,冬春季节市郊的农田完全呈裸露状态。此外,近些年北京城市建设加快,建筑工地的堆挖填土多数不加覆盖。这些裸露的土地,在冷空气到来时,便尘土飞扬,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沙尘天气的强度。但总体看北京本地起沙一般发生规模不大,影响范围较小,持续时间不长,影响高度也极为有限,且具有明显的阵发性。
国境以外地区。近年来的气象卫星云图曾清晰地显示出,一些冷空气在侵入我国之前就已挟带了浓厚的沙尘。所以,北京沙尘源区也包括境外的一些地区,如蒙古及中亚诸国。
(三)沙尘形成的主要土地类型
沙漠、戈壁、沙化草原及裸露耕地是沙尘产生的四种主要土地类型。在北京周边及西北地区分布着大片草原,近年来由于过牧等原因导致草原严重退化以至沙化,植被盖度明显降低,成为产生沙尘的重要场所。此外,这一地区由于气候寒冷,作物难以越冬,所以一般一年只种一季作物,冬春季节地表没有作物覆盖而呈裸露状态,在强风作用下,扬沙起尘,也是产生沙尘的重要场所。对于草原和耕地的起沙,意见比较一致。但对沙漠这一重要沙源,有些人则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沙漠中的沙粒主要是细沙或粉沙,这样的颗粒是难以吹扬到上千米的高度再输移到北京的,据此否定沙漠对北京沙尘天气的影响。其实,这种看法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沙漠中的沙粒虽然不能直接吹扬到高空,但在强风作用下,沙粒以跳跃或蠕动的方式不断地运动。运动中的沙粒不断发生碰撞、磨蚀,从而产生大量的粉尘。小范围沙漠产生的粉尘也许并不重要,但是几万、几十万平方公里沙漠产生的粉尘则是难以用数字来估计的。如果沙漠在强烈的运动中产生不了粉尘,那么,对于沙漠中每年发生数十次甚或上百次沙尘暴的现象,应该作何解释?同样,也无法解释全球沙尘暴的高发区为什么都集中分布在干旱沙漠及其周边地区这一事实。从沙漠的发生学看,细小的沙粒都是由最初的块石、砾石、沙粒经风化并在不断的运动中经过反复的破碎与磨损形成的。如果导致沙粒风化的剧烈变化的气候还存在,如果导致沙粒强烈运动的气流运动还存在,那么,就没有理由断定这些细沙、粉沙在运动中不会变得更细,不会产生粉尘,不会被大风搬运到北京。
关于沙尘侵入北京的路径,可以大体归纳为偏北和偏西两个方向。冷空气一般是以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宽度前移的,并非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犹如一条河流,沿着沟谷或河川进入北京。因此,对于像北京这样较小的地域,将冷空气侵入的路径过细划分与描述,往往反倒让人难以理解。沙尘随气流前移的高度一般可达两三千米以上,这时百米左右高度的起伏地形或其它地上物对其运行轨迹和强度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待和分析北京的沙尘天气,也许更为客观、更为清晰、更为符合实际一些。
研究及分析北京沙尘天气,搞清楚沙尘来源,对于沙尘治理中的科学决策是十分重要的。北京地区沙尘天气的形成受控于北半球的大尺度天气状况。沙尘天气是一种超越行政界限甚至国界的大尺度自然现象,只有把北京的沙尘天气放到全国沙尘天气的大框架中去考虑,才有可能获得客观而准确的结论。如果把北京的沙尘天气与我国北方地区的沙尘天气割裂开来,就北京论北京,那就很难找到影响北京沙尘天气的主导因素,也就无法得到治理北京沙尘天气的真谛。
恢复与重建沙尘源区植被是关键
沙尘天气的形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目前有关沙尘天气形成的许多机理尚不清楚。尽管对于沙尘天气形成的许多条件,人类尚无法控制。但是,目前人类并不是对沙尘天气只有俯首听命,而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行动对沙尘天气的形成、强度及其危害进行影响。这就是恢复植被。国内外的实践与经验都证明,目前在缓解沙尘天气方面,人类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恢复沙尘源区的植被覆盖。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恢复沙尘源区的植被覆盖,减少起沙尘源区的裸露土地。那么在同等天气条件下,沙尘天气就一定会得到缓解,风沙危害会不断减小。因此,恢复植被是缓解北京沙尘天气的根本途径。
2000年春我国北方地区发生大范围沙尘天气之后,国务院决定规划并启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范围包括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赤峰、河北省张家口、承德及北京市和天津市的9个盟、市(地)的75个县旗,总面积46万km[2]。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主要通过沙化草原区的围栏封育(轮牧)、推广舍饲、半舍饲,农牧交错区的退耕还林,流动沙地的造林种草以及低山丘陵区的小流域治理工程等措施,逐步恢复沙化土地的植被覆盖,降低地表裸露,减少这些地区的扬沙起尘,从而起到削弱沙尘天气的强度、规模及危害。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目标是:通过10年的建设,力争使这一地区林草植被得到有效的保护和恢复,土地沙化扩展的趋势得到遏制,裸露土壤减少,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华北和京津地区的风沙危害明显减轻。
做好北京近郊裸露耕地及市区建筑工地扬沙起尘的治理是必须的,也是第一步的。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必须看到,北京沙尘天气的形成主要受制于我国北方沙尘天气的总体影响。因此,北京沙尘天气的根本改善不仅取决于北京本地情况的改善,更取决于北京周边及整个西北地区沙化土地的治理,有赖于我国北方沙尘天气的整体改善。如果忽视了这一点,让我们苦苦期待的也许只有失望。鉴于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范围主要是北京周边地区,只覆盖了46万km[2]的面积。因此尚不能解决广阔的西部地区的土地沙化治理问题。鉴于我国沙化土地的主体在西北地区,风沙危害最严重且对东部地区影响最大的也是西北地区,因此在重点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同时,经国务院批准,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也于2001年正式启动,并将防沙治沙作为工程建设的重点内容。
可以相信,通过上述两个重点工程的建设,再加上分布在这一地区的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草原治理工程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实施,以及做好北京近郊裸露耕地和市区建设工地露天作业的保护工作,北京沙尘源区的生态环境必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北京地区沙尘天气也将得到较明显的缓解。
治理北京地区沙尘天气是一项长期任务
对于北京沙尘天气及其治理,我们应该采取一种理性的心态。既要排除那些认为沙尘天气自古就有、人类根本无法改善的悲观论调,又要防止那些错误估计形势,盲目乐观的思想。应该看到,北京地区沙尘天气的改善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这是由以下几个原因所决定的。
影响北京地区沙尘天气的地域极为辽阔,仅国内沙尘源区的总面积就达200万km[2]以上。就目前的技术条件及经济支撑能力来说,治理的重点主要是那些自然条件相对较好,治理难度相对不大,比较容易见效的地方。近年来投入力度虽然明显增大,但治理面积和起沙面积相比仍然显得太小。即使经过几十年治理之后,仍将有上百万平方公里的沙漠、戈壁存在。这些地表裸露都极高的沙尘源地,在强风作用下仍将产生大量的沙尘,这些沙尘仍会影响北京及我国东部地区。此外,境外沙尘源植被状况的改善,目前还是一个难以确定的因素,它取决于这些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认识、采取的政策及经济承受能力。可以估计,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除非气候状况出现明显的湿润趋势,境外沙尘源区植被状况尚难显著改善。
由于人们还不能控制沙尘天气形成的主要条件,因此,对风沙天气,特别是沙尘暴(上风向的沙尘暴往往是下风向浮尘天气的根源)就不能指望完全消除它。目前人们只是通过恢复与重建沙尘源区的植被,减少地表裸露,减少沙尘来源,从而削弱与缓解其强度与危害。但是,必须看到的是,这些地区的自然条件相当恶劣,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林种草的立地条件会越来越差,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降水趋于减少,使得恢复植被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这就决定了北京地区沙尘天气的治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