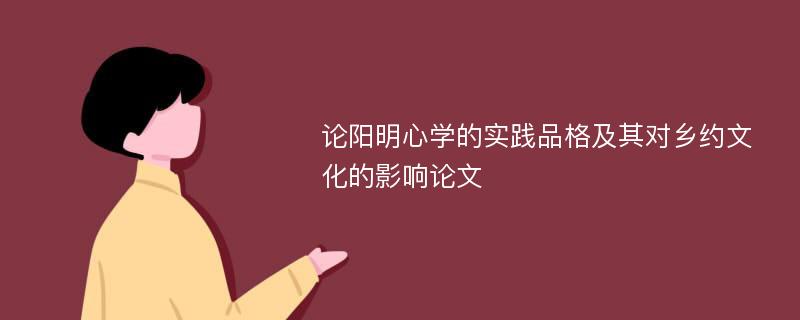
论阳明心学的实践品格及其对乡约文化的影响
杨亮军 冯澍滢
摘 要: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不仅是思想和理论上的创造性反思,也是对身心修养与道德实践体验的直接描述。他继承和发扬了儒家“内圣外王”的传统,主张在伦理教化与道德实践的内在统一中实现救治社会弊病和重建社会秩序之目的。王阳明通过对“心即理”“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进行创造性的诠释来展现自己心学的实践品格。在阳明心学实践品格的影响下,孔孟之道不再是那些掌握话语权的读书人的专利,而是成为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拥有的思维模式和生活常识。阳明心学的实践品格在肯定普通民众道德实践价值和意义的同时,为中国古代的乡治实践和乡约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学理性支持。
关键词: 阳明心学;明代儒学;乡约文化
作为明代儒学领域中最为活跃的思想家之一,王阳明不仅重视立志和修身的功夫,而且还躬身践行“治国平天下”之理想。他将心学理念创造性地运用到军事谋略、社会组织、地方政府治理以及社会秩序整合等方面,极大地带动了普通民众德行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然而,在一些研究者看来,阳明心学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它很难对社会实践予以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指导;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依据王阳明对“立志”“诚意”“良知”等心性方面内容的重视,认为阳明心学犹如“心灵鸡汤”,其实质无非是教人如何做好心灵修炼以化解现实生活的挑战;还有一些研究者以阳明心学对道、释两家某些观念的借鉴和发挥为论据,认为阳明心学与释、道两家殊途同归,都具有消极遁世的“出世”倾向,等等。(1) 如侯外庐先生在谈到王阳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等观点时指出,这都是从“心”派生出来的,是陆象山“宇宙便是吾心”的发展,也是禅宗“心是道,心是理,则是心外无理,理外无心”的再版。而对王阳明“岩中花树”问题的分析,侯先生更是指出,这不仅是“背离事实的捏造”,而且还是“背离思维规律的诡辩”,因而完全是对唯物主义的“反动”。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55-156页。 本文以阳明心学实践品格形成的现实基础为依据,在分析其内在的展现路径的同时,客观地认识阳明心学的实践品格对乡约文化的影响以及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所具有的积极作用,进而为当下中国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寻求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与历史经验。
一、阳明心学实践品格形成的现实基础
一种理论的产生,一个思想体系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渊源。阳明心学的形成是王阳明对他所在的那个年代之政治现实、程朱理学之脱离实际以及个人生活际遇等现实情形进行理性反思的结果。在明成祖时期,封建政府依周、程、朱、张诸儒性理之书类聚而编成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将宇宙天地、社会生活、理气信仰、鬼神夷狄等各方面内容囊括其中,以“有发明经义者取之,悖于经旨者去之”(2) 朱棣:《御制序》,载张辅、杨士奇纂:《明太宗实录》(卷一六八),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873-1874页。 为宗旨,在15世纪初逐渐确立了一套以“道”为核心的普遍而绝对的思想诠释体系。这几种大全与朱子所注的《四书集注》一起,逐渐成为儒生参加科举考试和进入王权专制政治体制的必修课程。但是,程朱理学在思想和知识领域权威地位的形成,对自身的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够在专制国家政权的保驾护航下得到最大限度的流播、兴盛;而另一方面,当它精致的形而上理论体系在国家力量的助推下逐渐转变成经院形式后,其批判精神、创造性思想、道德目的和论证活力等也逐渐僵化,最后避免不了逐步虚伪化以致失去原有思想活力的命运。随着程朱理学程式化和标准化特征的日益凸显,其原有的思想价值逐渐湮没在一套倡导死记硬背的教条式的文本系统当中。正如葛兆光在谈到程朱理学的这一特征时所说:“一种本来是作为士绅阶层以文化权利对抗政治权力,以超越思想抵制世俗趋向的、富有创造性和革命性的学说,当它进入官方意识形态,又成为士人考试的内容后,它将被后来充满了各种世俗欲念的读书人复制(copy),这时,它的本质也在逐渐被扭曲。”(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2页。 及至王阳明生活的明代中期,由社会发展特别是由商业经济发展而引发的社会秩序紊乱使程朱理学自身的缺陷更加明显,其理论解释力在社会变革中进一步弱化,那个能为国家政治、伦理道德、社会秩序、宇宙框架以及自然知识提供同一性的“理”逐渐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挑战。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发现,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思想资源已无法回答各种异于往常的社会现象,也无法回应社会秩序的种种变动,更是无法救治这些变化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创伤。(2) 葛兆光先生认为,明代社会生活与传统社会生活的断裂是造成这一时期思想世界严重危机的重要原因。这种断裂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皇权笼罩下的区域表面同一性被打破,地区与地区之间出现了文化断裂;二是城市(特别是江南地区)与乡村原来的同一性被打破,原本一体的城市与乡村发生了断裂;三是士人内部原来生活的同一性丧失,知识阶层内部的观念世界发生了断裂。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292-293页。 社会现实的无天理,最高统治者恃势而不恃理,“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残酷现实,使人们将批判的焦点投向了逐渐僵硬化、虚伪化和碎片化的程朱理学。
作用机制 依米珠单抗是一个人源化单克隆修饰免疫球蛋白G4(IgG4)抗体,从基因工程的哺乳动物细胞中提取而来,分子中含有结合活性FⅨ和FⅩ的双特异性抗体结构[8]。血浆中依米珠单抗代替失活的FⅧ,与活性FⅨ和FⅩ结合,实现有效止血作用[9]。依米珠单抗在卵磷脂存在条件下同步与FⅨ和FⅩ结合形成三元复合物,复合物的浓度与依米珠单抗浓度呈钟形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依米珠单抗通过温和的作用力与FⅨ、FⅨa、FⅩ及 FⅩa的EGF像域识别结合,KD分别为 1.58、1.52、 1.85、0.978 μmol·L-1,大多数的 FⅨ、FⅨa、FⅩ和 FⅩa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发挥凝血作用[6,10]。
在农民培训过程中,农民科技教育中心承担着重要的工作职能,参加培训农民的组织和管理以及培训内容和项目的策划,都需要农民科技教育中心提前进行规划和设计。在此过程中,农民科技教育中心应该不断地强化自身的管理水平,对农民教育培训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展开深入的调研和探讨,然后结合农民的实际学习情况,对于培训内容提出相应的合理建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阳明逐渐建构起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在分析当时社会弊病时说道:“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无怪于纷纷籍籍,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1) 王阳明:《答聂文蔚》,载王守仁撰:《王阳明全集》(上册),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9-70页。 政治的黑暗、伦理道德的名不副实以及人们的自私自利与相互倾轧行为等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紊乱,使备受打击的王阳明屡起归隐之心。但是,儒者固有的治世情怀却让他时刻谨记“治道”“君道”“臣道”之信念,生活的挫折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了维护和践行这些信念的决心。
最后,阳明心学的实践品格还体现在他对“知行合一”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当中。我们常说儒家学问皆是“生命的学问”,那是因为在儒学思想家看来,唯有透过人的实践活动,伦理规范与道德秩序的本体意义和永恒价值方能展现出来。道德实践上的“知”与“行”的问题,一直是儒家实践学问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然而,将“知”和“行”的问题上升到哲学地位并加以讨论始于宋代理学。朱子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在程颐和胡宏的基础上,将“知”和“行”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学理性整合,提出了“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著名命题。由于宋明理学将“道问学”与“尊德性”视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所以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宋明理学中关于“知”和“行”的问题看成是人们对如何获得优良道德品质以及如何实践这些品质的论述。
二、阳明心学实践品格的展现路径
其次,阳明心学的实践品格还体现在他对“格物”路径的创造性诠释上。通常情况下,“宋明理学”这样的统称虽然能够概括出宋明时期的儒学思想之间的承继关系及其共同关注的中心问题,但有时也会使人们忽略这二者之间的具体差异。在王阳明之前的儒学思想家那里,“格物”一直被看成是儒家实现“修齐治平”之政治理想的逻辑起点,因此也就成了他们阐述的一个重要话题。但“格物”一词在思想史上却有着多种解释。(1) 杜维明先生对宋明以来“格物”的不同释义作了概括:一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思想家将“格物”作“防物”来解;二是以朱熹为代表的思想家则遵循程颐的解释,将“格物”理解为“达到事物”,或者是通过系统的研究和学习以掌握事物固有之理的过程;三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思想家,将“格物”解释为“纠正或改正自己的观念或思想的过程”。参见《杜维明文集》(第三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174-175页。 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格物”被看成是“研究事物”的过程,认为读书、静坐、习礼等渐进过程和措施是理解多彩世界、掌握客观真理和成圣成贤的前提。但是,如果按照朱子的这套“格物”路径去实现儒家道德实践和重建秩序的话,那么就需要将事事物物之“理”完全“格”出来并掌握之,才能最终完成“治国平天下”的责任。这样一来,朱子的“格物”之路便充满着艰辛与不确定性,就连王阳明这样遍读经典的天才思想家也落下一个半途而废、一病不起的结果,更何况那些市井俗子和平民百姓。正如沟口雄三所说的那样:“朱子之学注重读书与静坐,这与一般平民的生活距离太远,不能不成为士大夫与知识分子或官僚阶层的学问。到了儒教在民间广泛传播的明代,这样一种修养实践便作为‘道学先生’的不切实际的生活态度而受到嘲弄。”(2) 沟口雄三:《中国的思想》,第71页。 总而言之,朱子的“格物致知”路径看似通畅,但实质上增加了“格物”主体的道德实践困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的可能性大打折扣。所以,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后,对朱子的“格物说”进行了严厉地批判:“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夫求理于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其亲之谓也。求孝之理于其亲,则孝之理其果在于吾心邪?抑或在亲之身邪?……夫析心于理为二,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之所深辟也。”(3) 王阳明:《答顾东桥书》,第39页。
当理学发展到明代中后期时,学术风尚出现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倡导对生活实践的回归。一些思想和文化界的精英尖锐地指出,理学所讲的那套宇宙本体论、知识和思想体系必须以生活实践为基础才不会流于空谈和虚无。从这方面来看,明代心学发展的逻辑起点不再是经典的知识或宇宙本源,而是与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的功夫,阳明心学则是对这一实践功夫的创造性诠释。(1) 参见朱汉明:《宋明理学通论——一种文化学的阐释》,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33页。 虽然有些研究者以王阳明龙场顿悟前后思想的转变为依据,认为王阳明在顿悟之后所建构起来的心学体系说明了传统儒家那种修齐治平、以身任天下的血脉在他那里已逐渐减弱,只是专注于“心性的自我超越”。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阳明心学受佛老思想的影响,对“心灵秩序”的强调是以内圣和修身为其中心目标,而经世精神衰退,外王之志趣不张。总的来看,这些论说都有一定道理,但这仅是阳明心学的一个面向而已。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指出,由于地主阶级经济力量和地主制政治秩序在宋明时期的不断强化,那些以血缘、伦理和地域为基础而形成的乡约共同体、宗族共同体等社会组织,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儒教的孝悌即尊卑上下的秩序伦理作为这些共同体的伦理轴心,在灵活运用中得到发展。在沟口雄三看来,朱子学是这个过程的早期阶段,而阳明心学则是其集大成的完善阶段。特别是王阳明对“心即理”“致良知”“满街圣人”“事上磨练”等理学范畴的重新论述,使宋明新儒学所强调的道德实践方法更加简化,易于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建立紧密的联系。(1) 参见沟口雄三:《中国的思想》,赵士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89页。 概括地看,阳明心学的实践品格是通过以下路径来展现的。
在王阳明看来,古本《大学》中的“格物”之“格”并不全是朱子所理解的“到达事物”或“通过艰苦的学习过程掌握事物固有的理”,而是指“正”,或“纠正”之意;“物”也不全是外在于人的客观事物,而更应该是“心”或“事”。他说:“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格’字之意,有以‘至’字训者,如‘格于文祖’、‘有苗来格’,是以‘至’训者也。然‘格于文祖’,必纯孝诚敬,幽明之间,无一不得其理,而后谓之‘格’,……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类,是则一皆‘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义,而不可以‘至’字为训矣。且《大学》‘格物’之训,又安知其不以‘正’字为训,而必以‘至’字为义乎?”(1) 王阳明:《答顾东桥书》,第42页。 王阳明将《大学》之“格物”进行这样的诠释,主要目的就在于更加突出“心”与“理”之间紧密关系这一命题,进而激发“格物”之主体的道德责任感和积极性。他向弟子徐爱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不能完全在客观之物上求理时说道:“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中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2) 王阳明:《传习录》,载王守仁撰:《王阳明全集》(上册),第2页。 在王阳明这里,“格物”也就变成了“格心”,也就是要求人们祛除心中的私欲,将儒家的忠孝仁义等伦理道德运用到日常生活中,以整饬由于“天理”被蒙蔽而引发的秩序紊乱。至于“格物”的方法,王阳明认为也不是主敬、静坐那样冥想,而是各色人等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进行真真切切的磨练和实践:官吏通过处理衙门里的公文事务、农民通过田间劳作、商人通过商业交易等日常行为,分别在他们的日常行动中发挥各自的社会作用,从而将相应的道德规范运用到社会秩序的维护当中。这样,王阳明通过对“格物”的重新诠释,进一步降低了道德实践的难度,完成了道德实践的平民化趋向,使作为道德之学的心学扩及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也正是有了龙场悟道后这样的重大“发现”,王阳明才会满怀信心地认为,通过“格物”路径的转化,那种“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1) 王阳明:《南赣乡约》,载王守仁撰:《王阳明全集》(中册),第507页。 的社会风貌最终会得以形成。
那么,如何在天理尽失的社会现实中重构一种与程朱理学不同且能够指导社会秩序重建的理论体系呢?王阳明最初和其他理学者一样,走的依然是“格物致知”的老路,希望通过“格竹”的路径进行一种精神上的探索(2) 根据弟子钱德洪在《王阳明年谱》中的记载,王阳明早年曾两度与朱熹“格物致知”学说奋斗:第一次是弘治五年(1492年)“为宋儒格物之学”;第二次是在十一年(1498年),依照朱熹“循序致精”之教求理,依然不得而致旧疾复发,最后不得不放弃。参见钱德洪:《王阳明年谱》,载王守仁撰:《王阳明全集》(下册),第1002-1003页。 ,尝试着把一种具体的自然现象的客观理解同自我实现的内心关怀联系起来,试图解决自我体验与外部知识之间的张力问题,进而实现“内”与“外”(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平衡。在经历了两次“格竹”的惨痛失败之后,龙场顿悟的狂喜使他认识到,作为一个真正的儒者,无论外部的局势多么令人绝望,他都应该矢志不渝地争做“圣贤”,因为每个人(包括普通民众)的“内心本性”能够承担起他做“圣贤”的重任。于是,王阳明认为,决定事物特质的最高权威,不是别的外在客观事物,而是那个自发、自决和自善的“心”,而这样的“心”也就成为王阳明修正程朱理学和建构自己学说的起点,成为构筑“理”之最高权威的本体性依据。至于“心”对“理”之重构的重要性,王阳明在他的数首诗中有着精彩的概括。例如,在《咏良知四首示诸生》中他这样写道:“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1) 王阳明:《咏良知四首示诸生》,载王守仁撰:《王阳明全集》(中册),第652-653页。 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在分析阳明心学的这一特征及其意义时指出:“阳明心学根据圣人是人之自然的规定,去掉了偶像化,而将其权威转移到了人的一侧,而且人的自然,是政治文化人伦以前的东西,反而是流出制度文为、礼乐名物、亲义别序信、治国平天下之理的根源。”(2) 岛田虔次:《中国思想史研究》,邓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7页。 这样,王阳明在反思社会现实、总结自身生活体验以及修正程朱理学的过程中逐渐建构起了自己的心学体系,从而将人的道德主体性以及道德实践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从外在的权威转移到内在的自我修养上。在他看来,即使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如贩夫走卒或愚夫愚妇,只要他们能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本心”的善,同样也能为社会的稳定作出自己的贡献。王阳明在主政江西时,就将这些理念融入到他的乡治实践中,认为化解乡民矛盾与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必须依靠经由“人心”开辟出来的那条循序渐进的道德修养和实践路径,而对于那些作奸犯科、为非作歹,不利于乡村秩序维护的违背了“本心”的乱民,人们也不要急着一棍子打死,而是要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们,尽量使他们洗心革面、弃恶从善,实在教化不了的才报官,由政府来处置。
在王阳明生活的时代,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封建士大夫一面高举道德理想主义大旗,一面蝇营狗苟,背地里干着背信弃义、投机钻营等有损道德秩序的勾当。面对政治生态的不断恶化以及日益盛行的“行不顾言,言不顾行”之社会风气,王阳明对此予以尖锐的批判,并对其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知行合一”主张用以救治时弊。在《书林司训卷》一文中,他喟叹道:“昔王道之大行也,分田制禄,四民皆有定制。壮者修其孝悌忠信,老者衣帛食肉,不负戴于道路,死徙无出乡,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乌有耄耋之年而犹走衣食于道路者乎!……逮及后世,功利之说日浸以盛,不复知有明德亲民之实。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吾为此惧,揭知行合一之说,订致知格物之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说,以求明先圣之学,庶几君子闻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泽。”(2) 王阳明:《书林司训卷》,载王守仁撰:《王阳明全集》(上册),第237页。 人们常常把儒家道德哲学中人的道德认知称之为“知”,而将人的道德实践称为“行”。但在现实生活中,知与行却是一个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动态过程。一方面,“知”本是道德认识的意识活动,但从整个动态过程来看,“知”又是道德行为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道德行为的发起点(意识之“行”);另一方面,“行”本是道德行为的实践过程,但这种“行”总是以道德观念为指导,是将道德观念付诸实践行动的过程。所以,我们也可以将“行”看成是“知”的结果和完成(道德意识的作用过程)。王阳明的“知行观”正是抓住了现实生活中“知”和“行”的这一相互包含,不可分割的特点,批判了朱子于心外求“理”,“心外求物”的观点,认为朱子的“知行观”很容易导致“知”和“行”的相互分离,使道德规范有脱离“心”而存在的危险,在实践中也不利于道德秩序的重建。鉴于此,在谈到自己的“知行合一”观时王阳明讲道:“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1) 王阳明:《传习录》,第84-85页。 在王阳明看来,一方面,由于“一念发动处”就是“行”了,所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时刻准备着去克倒那个不善的念头,这样才能在道德实践中做到“知”与“行”的内在统一。例如,他在主政江西地方和推行其乡治理念时就经常告诫父老乡亲:“尔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旧恶而不与其善,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持为良民而不修其身,尔一念而恶,即恶人矣;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尔等慎思吾言,毋忽!……投招新民,因尔一念之善,贷尔之罪,当痛自克责,改过自新,……如踵前非者,呈官惩治。”(2) 王阳明:《南赣乡约》,第508-509页。 另一方面,王阳明同时承认要“克倒”这些不善的念头的确有一定的困难(即“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3) 王阳明:《与杨仕德薛尚谦》,载王守仁撰:《王阳明全集》(上册),第144页。 ),只有经过不断地磨练和刻苦学习,才有可能真正地做到弃恶从善,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和谐。所以,王阳明特别注重在社会实践中进行学习的重要性。因为“儒家的所谓学习,不仅是指书本的学习,而且还包括礼的实践。在儒家看来,通过形体和精神的修养,人将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并且,在这种修行中,人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而是作为生存共同体——家庭、乡里、国家和世界——的积极参与者而出现的”(1) 杜维明:《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化的自我》,曹幼华、单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7页。 。王阳明还特别地指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表现出“知行不一”,做出那些有悖于道德秩序的恶行,并不是本性使然,而是由于有司治理无方、家庭教育缺失等造成的。他说:“民俗之恶善,岂不由于积习使然哉!往者新民盖常弃其宗族,畔其乡里,四出而为暴,岂独其性之异,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尔父老子弟所以训诲戒饬于家庭者不早,熏陶渐染于乡里闬者无素,诱掖奖劝之不行,连属叶和之无具,又或愤怨相激,狡伪相残,故遂使之靡然日流于恶,则我有司与尔父老子弟皆分受其责。”(2) 王阳明:《南赣乡约》,第507页。 鉴于此,王阳明也就尤为注重家庭、宗族、有司以及乡绅在道德实践与社会教化中的作用,认为在这些乡村共同体的一致努力下,人们会逐渐养成知行合一的习惯,自觉地去履行道德规范,社会秩序的恢复和重建也就有了希望。
三、阳明心学实践品格对乡约文化的影响
(2)患者准备对检验结果的影响至关重要,采集检验标本前,患者的生活起居、饮食状况、生理状态、病理变化、治疗措施等对标本的质量都有影响[2],应提前告知患者及其家属。
就阳明心学的实践品格对乡约文化的影响而言,由于它从学理上对社会成员的道德实践的主体意识予以强调,进而提高了人们实践德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约文化的社会化进程。自北宋熙宁年间《吕氏乡约》创制以来,乡约的设置及运行方式虽然发生了多次变化,但其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核心内容的道德实践主张却未曾发生本质性的变化。(2) 参见吕大钧:《乡约》,载陈俊民辑校:《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中华书局,1993年,第563-565页。 及至王阳明生活的明代中后期,基层社会秩序的混乱使乡约实践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而阳明心学的实践性无疑为乡约的推广和实践提供了学理性支持。
首先,阳明心学的实践品格是通过他对“心即理”的重新诠释来展现的。通常情况下,我们往往习惯于将王阳明之前的宋明时期的儒家学说称为“理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时期的一些儒学家在阐释传统儒家经学义理时,逐渐建构起了一个以“理”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理”作为唯一的绝对,不仅是永恒的存在,而且还是一切事物的主宰,即所谓“天下只有一个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在朱熹那里,“理”更是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理性思辨和结构严密的形而上理论体系。一方面,“理”就是“天道”,既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或根据,又是宇宙最高的主宰,它的至上权威性和绝对主宰性使其能够像先秦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天”那样,成为人们所敬畏的对象;另一方面,“理”还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伦理道德原则,是日用伦常和礼乐制度运行必须遵守的普遍法则,即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2) 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第77页。 同时,由于“理”可以借助于“气”而变异万事万物,犹如天上的一个月亮(“理一”)映射为江河湖海中的千千万万个月亮(“分殊”)。所以,认识主体对于“理”的体认,就只能是对一事一物进行穷格,直到实现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由积累而到豁然贯通之结果。(3) 参见张立文:《朱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7页。 然而,程朱理学建构起来的这种宇宙本体论却在明代受到了来自阳明心学的巨大挑战。龙场格竹的惨痛失败使王阳明意识到,遵循程朱理学而通过外在于主体的“格物”路径无法获得“理”的道德本体性,必须对以前的“格物寻理”的方式进行反思。弟子钱德洪对王阳明的这一反思过程有着详细的记载:“先生始悟格物至知。……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1) 钱德洪:《王阳明年谱》,第1006-1007页。 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逐渐展开了对“心即理”的阐释,并且建立了一个以“心”“良知”为第一原理的人格论形而上理论体系。从整体上看,这个体系的基础不是建立在“我思故我在”的逻辑的、思辨的第一原理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我在故我思”的存在的、实践的日用功夫的基础上。王阳明在向弟子解释“心即理”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心性”的实践意义,他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2) 王阳明:《答顾东桥书》,载王守仁撰:《王阳明全集》(上册),第37页。 王阳明如此强调“心”的重要性,主要是为了从认识主体本身去寻求道德实践的形而上依据,以修正程朱理学从天地万物中寻“理”之路径给人的道德实践所带来的困境。王阳明特别地指出,体现仁义礼智、忠孝信友等纲常伦理的“天理”,不是某种外在的东西,而是来源于“吾心”。这样,“吾心”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本原,整个世界所需要的人伦秩序也都来自人的“本心”。即所谓“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然后知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3) 王阳明:《博约说》,载王守仁撰:《王阳明全集》(上册),第225页。 。从实践论方面来看,王阳明“心即理”“心外无理”本体论的提出,将伦理规范的实践性推到了极致,使其上升到了另一个层面,对提升主体道德实践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就王阳明自己来说,他在平定江西南赣匪患之后,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和更好地治理当地社会,就把工作重点放在民众的道德教化上,将其心学理念融入到社会治理的实践当中,为此还专门颁行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治乡措施,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1.坚定不移地狠抓基础免疫,确保有效防控重大动物疫病。围绕国家强制免疫病种,强力开展常年免疫、三旬分类免疫和春秋两季动物疫病综合防控行动。自2007年以来,全区坚持推行生猪口蹄疫、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30日龄阉割时三针首免,一个月后加强一次免疫和春秋两季集中免疫相结合,牛羊及家禽实行春秋两季集中免疫与常年补免相结合,监督规模养殖场按备案免疫程序开展自主常年免疫的程序。按照“政府保密度,业务部门保质量”的要求,制定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实施方案,二次强化免疫、常年免疫推行面达100%,强制免疫密度和质量达到和超过农业部规定标准,保障了近年无重大动物疫情发生。
儒家学说常常被人们称之为“实践的哲学”,原因就在于儒家的知识系统和思想体系总是和社会现实、生活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社会现实与生活实践既是儒家思想形成的动力,又是儒家思想彰显其价值所在。例如,儒家经典《论语》对“修己治人”的解释实质上是表明:一个人的生命以修身为开端,但必须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人的修身和成德过程需要参加政治、领导社会、教育民众,建构和谐秩序等入世性的活动才能够完成。据此,有学者将儒家学说中的经世和修身比作“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并视为儒家人文思想的中心主题。(3) 参见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73页。
如果我们将王阳明的学术人生、文韬武略和事功修行等作一全面考察,就不难得出其“心学”实质上是对“经世”这一儒家传统观念另辟蹊径的阐释和践行。“以道自任”的儒家精神依然是王阳明所坚守的,宋代儒学思想家所倡导的秩序重建也是他所追求的。但是不断恶化的政治生态迫使他再也不能像宋儒那样“明目张胆”地践行“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信条,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将目光投向下层社会和平民身上,以“觉民行道”的方式来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进而达到“平治天下”的目的。这就是张灏所说的:“凡是宋明大儒的思想,我们只要不断章取义,以偏概全,而就其论著全体而论,未有不强调经世在儒家思想的义理结构中的重要性。在这些宋明大儒心目中,经世而不修身,落入申韩法家,固是他们反对,修身而不经世,落入佛老二氏,也是他们反对。”(1)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78页。
“没关系的,”青辰道,“族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咱们的失踪,他们很快就能找过来。最多傍晚,他们一定能找过来。”
宋明理学虽然以“内圣”显其特色,但“内圣”的终极目标并不仅仅是让人成圣成贤,而是要通过人的实际的道德行动来重建合理的人间秩序,用古典儒家的话来说就是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的实践过程。然而,由于理学家们热衷于讨论“理气”“有无”“心性”等抽象和玄虚的概念与哲理,讲究静坐冥思等自我体悟,所以,当时一些倡导务实之学的思想家批判理学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事一死报君王”的无用之学问。
1.物资需求计划不准确,个性化非标产品凌乱。需求计划是根据生产经营、工程建设需要编制并审核确定的一定时期所需物资的具体安排,主要解决需要什么、需要多少、何时需要等问题。需求计划提报不准确造成的物资错误采购、重复采购和不及时采购,不仅难以满足生产经营和工程建设的需求,还可能造成采购物资无使用方向,形成库存积压。
首先,阳明心学的实践品格使人们的德行实践路径发生了由外而内的转化,提高了乡民践行乡约的自觉性、自信心和积极性。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心即理”的内在规定性意味着他们的德行实践是“理”的要求,是他们应尽的社会责任,遵从乡约以实践德礼的要求实质上是遵从自己“本心”之要求;而对于王权政治体系的统治者而言,“心即理”则意味着他们的政治统治也要接受“心”和“理”的检验与监督。王阳明倡导的“格君心之非”“破心中之恶”等道德实践口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将至高无上的王权专制政治纳入“心”的范畴,接受“理”的检验和监督,迫使统治者以“德治”和“仁政”的统治方式来回应乡约的运行,从而在实现乡村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上增强王权政治的合法性。例如,在回答弟子陆澄问格物方法时王阳明又说道:“工夫难处,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诚意之事。……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虽亲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便似老、佛。”(3) 王阳明:《传习录》,第22页。
其次,阳明心学的实践品格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距离,拓宽了儒家“经世致用”和“内圣外王”的德行实践路径,使乡约的实践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王权国家的认同和支持。王阳明对《大学》三纲目之“亲民”进行阐释时,坚决维护古本之意,认为“亲民”并不是朱注所言的“新民”,而是孟子所讲“亲亲仁民”的政治实践路线。他给弟子徐爱作解时说道:“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之意。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1) 王阳明:《传习录》,第1页。 在王阳明看来,“亲民”体现出来的这些内涵和特征,不仅意味着王权专制国家的统治理念要体现出“亲百姓”和“安百姓”的精神,而且还意味着统治者要对普通老百姓的道德实践行动和自治能力的信任和支持,这无疑有利于乡约的制度化建设及其推行。除此之外,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也强调了经典儒家“内圣外王”之精神,指出三代以下治道与世道的紊乱,皆由圣人之学日晦芜塞所致,其根本解决之办法就是恢复圣人之学的应有之意,而乡约是人们将“内在的自我超越”与“外在的经世致用”紧密结合起来以实践“圣人之学”的最佳路径。他说:“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焻,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世之儒者,慨然悲伤,搜猎先圣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补于煨烬之余;盖其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2) 王阳明:《答顾东桥书》,第48-50页。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阳明心学的实践品格一方面是在教育民众要遵循一种理性的生活秩序,使长幼有序、尊老爱幼、怜贫恤寡、扶助乡里、少争息讼、勤俭节约、恪守本分等伦理规范和社会道德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作用;另一方面,阳明心学的实践品格又和国家法令和制度设置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制约着那些无论是在家族内还是在家族外,无论是读书人还是普通民众的行为,使他们在日常活动中将秩序的维护看成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这种通过道德实践主体的内在修养和外在实践行动的统一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有序,在王阳明设计和推行的治乡理念和实践中就有明确的体现:“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1) 王阳明:《南赣乡约》,第507页。
概括而言,阳明心学从学理上强化了儒家道德实践的传统,使乡约在实际运行中能够获得更多的思想资源与学理性支持,对乡约文化的繁荣与传播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就指出:“所谓‘心即理’、所谓‘致良知’、所谓‘满街圣人’、所谓‘事上磨练’,贯穿它们的一个共同点是道德实践的方法简略,易于和日常生活建立紧密的联系。……阳明则还以推广所谓乡约即乡村共同体规范而著名,这一乡约才是谋求由乡村每个成员维护道德秩序。那一道德秩序,是前述阳明期待于聋哑农民的孝悌恭顺的秩序。一句话,那是乡村家长制的地主制秩序。……阳明学可说是影响了这样一种乡村秩序体制形成的时代趋势。”(2) 沟口雄三:《中国的思想》,第89页。 至于具体方面的影响而言,作为阳明心学实践品格直接体现的《南赣乡约》,在当时广受地方官员和士大夫的青睐,在一些地方进行了实验和推行。门生如季本、聂豹、徐阶、邹守益、欧阳德等人秉承师学,将倡导和推行乡约看成是践行“心学”的一个重要途径,并且在乡治实践方面取得了不小成果。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一些与乡约、乡治相关的著述也不断涌现,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有黄佐的《泰泉乡礼》、曾惟诚的《帝乡纪略》、章潢的《图书编·乡约总序》、尹畊的《乡约》、吕坤的《实政录·乡甲约》、刘宗周的《乡保事宜》及陆世仪的《治乡三约》等。到了明万历以后,在各地乡绅的推动下,乡约文化较之以前又取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当时南直隶的徽州、池州、扬州、宿州、应天、松江;江西的南昌、建昌、抚州、赣州、吉安、南安;福建的漳州、泉州、延平、建宁;河南的陈州、许州、磁州、开封;山西的潞州、解州、蔚州;山东的泰州、德州;北直隶的顺天、通州;陕西的西安、同州以及湖广的黄州等地,都先后举行过乡约。(1) 参见曹国庆:《王守仁与南赣乡约》,《明史研究》,1993年第3辑,第78页。 后来清代乡约的泛滥可以说与此有着紧密的联系。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王阳明心学体系是建立在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它和佛、老的出世情怀有着本质的区别,更不是所谓疗治心理创伤的“心灵鸡汤”。相反,阳明心学所展现出来的实践品格可以说是对人们身心修养与道德实践体验的直接描述。王阳明通过对程朱理学的修正而建构起来的心学体系,极大地解放了人性,在理论上将人性视为不需要任何修饰的完全善美之物,给予“人”以平等的道德实践地位和机会,进一步拓宽了农、工、商贾等下层民众的为学与道德实践之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更是培育了普通社会成员的自我行动意识和以身作则的天下担当精神。《南赣乡约》的颁行则是王阳明将他的心学理念运用到乡村社会治理的典型,不仅为恢复当地的社会秩序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而且还为扩大乡约的影响奠定了一定基础。乡约在明代中后期的勃兴无不与阳明心学实践品格的影响以及王阳明本人身体力行的推行息息相关。
作者简介: 杨亮军,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冯澍滢,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明代的乡约与乡村社会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8XZZ00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刘学斌)
标签:阳明心学论文; 明代儒学论文; 乡约文化论文;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