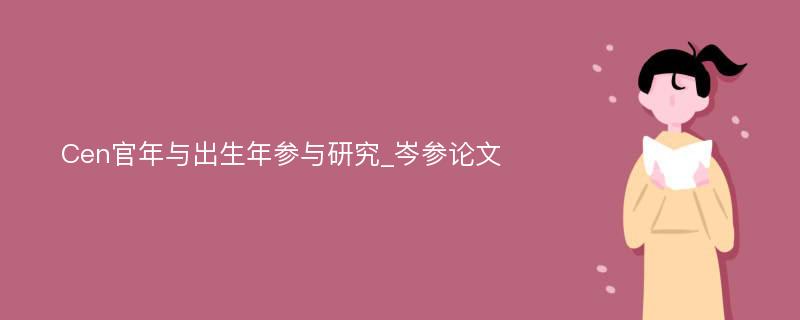
岑参入仕年月及生年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月论文,岑参论文,生年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杜确《岑嘉州诗集序》谓岑参“天宝三载,进士高第。解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注:《全唐文》卷四五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92页。)。于是,闻一多先生《岑嘉州系年考证》(以下简称《考证》)、李嘉言先生《岑诗系年》(以下简称《系年》)、陈铁民先生《岑参集校注·岑参年谱》(以下简称“陈谱”)、刘开扬先生《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以下简称“刘谱”)俱将岑参释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系于天宝三载(744)下,并据以推其生年。然根据唐铨选制,这一说法是有问题的。
一
按唐铨选制,进士及第并经吏部关试后,并不能立即授官,还得通过守选,才能参加吏部的冬集铨选而授官。宋《蔡宽夫诗话·唐制举情形》就说:“唐举子既放榜,止云及第,皆守选而后释褐。”(注: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卷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8页。)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八《诂笺三》“进士科故实”条也说:“关试,吏部试也。进士放榜敕下后,礼部始关吏部,吏部试判两节,授春关,谓之关试。始属吏部守选。”所谓守选,就是守候吏部的铨选期限。这是唐代为缓解选人多而官阙少这一社会矛盾所制订的一项政策。
唐代及第举子的守选,大约自太宗贞观年间就开始了。《唐会要》卷七五《贡举上·帖经条例》载:“贞观九年五月敕:自今已后,明经兼习《周礼》并《仪礼》者,于本色量减一选。”就是说,应明经试者中所习经为《周礼》和《仪礼》者,及第后可在其应守选的年限中减免一年。按,唐人将守选一年称作一选。只有守选,才能减选;若无守选,何以减选?由是知贞观九年(635)明经已经有守选制了,则进士科和其他科的及第举子也当同样存在着守选这一制度。
在唐代,各科及第举子的守选年限是不一样的。进士及第,一般是守选三年。《册府元龟》卷六三五《铨选部·考课一》载玄宗开元三年(715)六月诏云:“其明经、进士擢第者,每年委州长官访察,行业修谨、书判可观者,三选听集。”所谓“三选听集”,就是守选三年才听任其参加吏部冬集。该书卷六四一《贡举部·条制三》又载文宗大和九年(875)十二月,中书门下奏云:“起来年进士及第后,三年任选,委吏部依资尽补州府参军、紧县簿尉。”所谓“三年任选”,就是守选三年才任其参加吏部铨选。这一现象直至宋初仍然存在。《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四》载有太宗淳化年间(990-994)各类人的守选年限,其中,“进士、制举,三选”。就是说进士出身与制举出身者,守选三年。宋初多承唐五代之制,既然宋初进士出身是守选三年,则唐五代进士及第也当守选三年。由以上开元三年、大和九年和宋初淳化年间进士及第都是守选三年可知,有唐一代进士及第者的守选期限皆为三年(注:进士及第守选及守选三年之详情,可参阅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第二章,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6-63页。)。
进士及第守选三年,这在唐代诗文中亦可找到证据。王冷然有《论荐书》一文,是他于开元十一年(723)上书宰相燕国公张说的。书中说:“长安令裴耀卿于开元五年掌天下举,擢仆高第,以才相知;今尚书右丞王丘于开元九年掌天下选,授仆清资,以智见许。”(注:《全唐文》卷二九四,第2981页。)开元五年(717)春,王冷然进士及第,时知贡举者为考功员外郎裴耀卿。至开元八年(720)春王冷然守选期满,是年十月赴吏部参加冬集,第二年即开元九年(721)春被吏部侍郎王丘铨选为太子校书郎,即“清资”。由开元五年进士及第到开元八年冬集,这就是所谓的“三选”,即守选三周年,所谓“长安令”、“尚书右丞”,是王冷然上书时即开元十一年裴耀卿、王丘的官职。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谓孟郊:“年几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来集京师,从进士试,既得即去。间四年,又命来选,为溧阳尉。”(注: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第六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46页。)孟郊于贞元十二年(796)进士及第,至十六年(800)被吏部铨选为溧阳县尉,恰为四年,与《墓志铭》“间四年,又命来选”相合。由贞元十二年进士及第到贞元十五年(799)冬集,为三年守选期。晚唐诗人许棠在《讲德陈情上淮南李仆射八首》诗中写道:“应念无媒居选限,二年须更守渔矶。”(注:《全唐诗》卷六○四,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985页。)据《唐才子传》卷九载,许棠,咸通十二年(871)进士及第。此诗是他于咸通十三年(872)春上于淮南节度使李蔚的,在诗中他慨叹自己进士及第后却无人汲引,只好在家“居选限”守选,实际上是希望李蔚能提携自己入幕府为幕僚。因诗写于他进士及第后的第二年春天,已守选了一年,还得再守选两年,故曰“二年须更守渔矶”。由以上三例可知,唐代进士及第,一般是守选三年。
进士及第后,想不等守选期满就提前入仕,可参加制举或吏部科目选试,登科后即可授官。如杜牧大和二年(828)正月在洛阳进士及第,二月回长安过关试,是年三月又参加了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登科后授予弘文馆校书郎,仅守选一月。刘禹锡贞元九年(793)进士及第,贞元十一年(795)应吏部科目选博学宏词科试,登科后授太子校书郎,守选二年。自居易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贞元十九年(803)应吏部科目选书判拔萃科试,以甲等登科,授官秘书省校书郎,守选三年,较常调铨选提前一年入仕。
二
岑参于天宝三载进士及第,之后,有关他生平的所有文献均未言他以制举或宏词、拔萃登科,可见他是按吏部常调即守选期满经冬集铨选而释褐的。杜确序不言他守选,只在他“进士高第”后紧接着说“解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是因为守选在唐代人人皆知,无须明言,后人不晓,连读以为解褐授官也在天宝三载,乃误。
且岑参守选,也有证可稽。
《系年》谓:“天宝五、六两年公行事不明,游永乐、平阳疑即在此二年间。”陈谱也认为岑参游绎、晋、淇是在天宝五、六载间,刘谱更以为天宝三、四载岑参还去过黎阳、新乡等地。试想,若天宝三载岑参进士及第后即解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他怎能长期离职出外漫游呢?按唐制,凡官吏请病假满百日就要解职,更何况两三年出外不归去漫游,这对一个居官在职的人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岑参之所以能外出漫游如此之久,这恰恰说明了他在这一时期没有授官,正在守选。又,《河南千唐志斋藏石》收有兵部郎中邵说撰写的《唐故瀛州乐寿县丞陇西李公墓志铭》,云:
惟陇西李公湍,地望清甲,冠于邦族……公始以经术擢第,署滑州匡城尉,次补瀛州乐寿丞。理尚刚简,盖肃如也。酷好寓兴,雅有风骨。时新乡尉李颀、前秀才岑参皆著盛名于世,特相友重。方振雄藻,比户英达,孰是异才,而无显荣?以乾元元年终于贝丘。凡百文士,载深恸惜……即以大历己酉岁冬十二月甲寅,葬我公、夫人于邙山之茔。(注: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1页。)
“大历己酉岁”,即大历四年(769),知李湍卒于乾元元年(758),大历四年始与夫人合葬。《墓志铭》称李颀为“新乡尉”,当是李颀尉新乡县时与李湍相识的。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载:“颀,东川人。开元二十三年贾季邻榜进士及第,调新乡县尉。”按李颀于开元二十三年(735)进士及第,亦当守选三年而后铨选为新乡县尉的,则其尉新乡应在开元二十七年(739),时李湍亦正尉匡城。匡城属滑州,新乡属卫州,两地相距甚近,且二人又同为县尉,故可时常往来而“特相友重”。
《墓志铭》又称岑参为“前秀才”。秀才原是唐初贡举之一科,后因取人严峻,举子多不敢应试,州府也不愿举荐,故于高宗永徽二年(651)就停止了(注:《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63页。)。以后唐人就多将进士称为秀才,明经称为孝廉。“前秀才”,就是前进士。前进士是及第进士关试点的称呼。《唐音癸签》“进士科故实”条谓:“放榜后称新及第进士,关试后称前进士。”《蔡宽夫诗话·唐制举情形》也说:“关试后始称前进士。”及第进士之所以关试后始称前进士,是因为关试后新及第进士就成为吏部的选人了,“始属吏部守选”,故前进士实质上就是及第进士在守选期间的专称。及第进士无论其守选时间多长,只要尚未授官,都可称作“前进士”。皮日休有一首诗,题作《江南书情二十韵寄秘阁韦校书贻之商洛宋先辈垂文二同年》,云:“四载加前字,今来未改衔。君批凤尾诏,我住虎头岩。”(注:《全唐诗》卷六一二,第7064页。)据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卷八载,皮日休,咸通八年(867)进士及第,之后,于咸通十年(869)被苏州刺史崔璞辟为从事,至十二年三月崔璞解任后始离去,此说可信。诗谓“四载加前字,今来未改衔”,是说进士及第四年来,未曾授官改衔,仍以前进士称。则知诗写于咸通十二年秋,时在苏州,故曰“我住虎头岩”。韩愈贞元八年(791)进士及第后,“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于贞元十一年春三上书宰相求荐,仍自称曰“前乡贡进士韩愈”(注:韩愈《上宰相书》,《韩昌黎文集校注》第三卷,第153-155页。)。《河南千唐志斋藏石》收有寇泚撰写的《前国子进士上谷寇堮墓志》,云:“大唐开元十四年正月癸未,前国子进士上谷寇堮卒……廿五擢第,卅而终。”(注:《唐代墓志汇编》下,第1312页。)知寇堮及第已五年,未曾授官,以前进士终。按,由州府解荐而得第之进士,曰“前乡贡进士”,由国子监生徒而举进士及第者,曰“前国子进士”,然统简称作“前进士”。邵说《墓志铭》谓岑参“前秀才”,即前进士,当是岑参进士及第后尚未授官前也就是守选期间与李湍结识的。按前所述,李颀尉新乡是在开元末,时李湍尉匡城,二人相识。至天宝五、六载,李湍已补瀛州乐寿县丞,时岑参游河朔至乐寿县,故与之结识而“特相友重”。
有人以为岑参是开元末与李颀同时结识李湍的,时李颀为新乡尉,而岑参尚未登第,故曰前秀才;前秀才者,登第以前之秀才也。此说不确。按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载,进士,“通称谓之秀才”,“得第谓之前进士”。就是说进士未第前通称曰秀才,及第后才称为前进士。若岑参是未及第前与李颀一起结识李湍的,则邵说《墓志铭》当云“时新乡尉李颀、秀才岑参皆著盛名于世,特相友重”才对,而不应再在“秀才”前加一“前”字。在秀才、进士前加一“前”字,就变成专有名称即已第进士在守选期间的称呼了。还有人认为,只有前进士是得第进士之专称,前秀才不是专有名称,恐怕就不是这种意思了。我们说,既然进士可以俗称为秀才,那么前进士当然也就可以俗称作前秀才了。李商隐有《奉和太原公送前杨秀才戴兼招杨正字戎》一诗,据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一注,“太原公”为王茂元,可信。“前杨秀才戴”,即前秀才杨戴;“杨正字戎”,即正字杨戎。《唐摭言》卷八《及第与长行拜官相次》载:“杨敬之拜国子司业,次子戴,进士及第;长子,三史登科,时号‘杨三喜’。”“长子”即杨戎。知杨戴、杨戎为弟兄俩,二人同时及第登科。据《登科记考》卷二一载,杨戴进士及第,杨戎三史登科俱在开成二年(837),当从。杨戎登吏部科目选科后即授与正字,杨戴进士及第后还得守选三年,故曰“前秀才”。又,陆龟蒙在《书李贺小传后》说:“余为儿时,在溧阳,闻白头书佐言:孟东野贞元中,以前秀才家贫受溧阳尉。”(注:《全唐文》卷八○一,第8418页。)由以上二例知,“前秀才”就是前进士,可见唐人将前进士也称作前秀才。
岑参守选期间,不仅到过绛、晋、淇、黎阳、新乡、大梁等地,而且也到过河朔。他在《送郭乂杂言》诗中说:“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其河朔诗有《登古邺城》、《邯郸客舍歌》、《冀州客舍酒酣贻王绮寄题南楼》、《题井陉双溪李道士所居》等。其《冀州客舍》诗云:“忆昨始相值,值君客贝丘。相看复乘兴,携手到冀州。”冀州距瀛州乐寿县不远,岑参到冀州后又北上赴乐寿,与李湍相识当在此时。诗题下有作者自注:“时王子应制举欲西上。”刘谱承《考证》之说,将此诗系于开元二十九年(741)下,而陈谱却系于开元二十七年(739)下,理由是:“历考诸书,则未见开元二十九年春有制举。”并引《册府元龟》卷六八及卷六四五,谓开元二十七年春有制举。其实,开元二十七年的制举,非王绮所应之制举。《登科记考》卷八引《册府元龟》与《唐大诏令集》云:“正月,制令诸州刺史举德行尤异,不求闻达者,特乘传赴京。”“二月己巳,加尊号,大赦天下,制曰‘草泽间有殊才异行,文堪经国,为众所推,如不求闻达者,所由长官以礼征送’。”正月、二月这两次的制举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举者为不求闻达科人。不求闻达科是自己不能应举,而由各地长官访察举荐,然后“以礼征送”,“乘传赴京”。王绮却是自己赴长安应试的,与开元二十七年制举不符。由是可知此诗既不作于开元二十九年,也不作于开元二十七年,而是作于天宝六载(747)。《登科记考》卷九载:
(天宝)六载,正月戊子,南郊礼毕,大赦天下,制曰:“……天下诸色人中,通明一艺已上,各任荐举。仍秀所在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流辈,远近所推者,具名送省。”
王绮所应即此制举,此制举所试为诗、赋、论,与《冀州客舍》诗谓王绮“富学赡清词,下笔不能休”相符。这次制举考试的结果是,王绮与杜甫、元结一样,都落榜了。因这次制举试被李林甫耍了花招。他恐举子斥言其奸,便改变了制举试的内容与形式,而且未录取一人,然后表贺“野无遗贤”。
《考证》、刘谱、陈谱均将岑参游河朔诗系于开元末年,还有一个原因,即认为天宝元年(742)改州为郡,岑参《冀州客舍》诗不称信都郡而称冀州,必是天宝元年更名前所作。按,此说未必。虽然天宝元年改州为郡,至至德二年(757)始复旧,但唐代文人有一习性,多喜欢沿用旧名、古名。岑参于天宝八载(749)赴安西途中写有《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不称陇西郡而称渭州;天宝十载(751)在河西写有《登凉州尹台寺》;天宝十三载(754)赴北庭途中又写有《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均不称郡名武威而称凉州,可见诗人写诗用州名,还是用郡名,并不以天宝元年更名为界。
三
岑参天宝三载进士及第,守选三年,于天宝六载春守选期满。按唐制,是年十月他就可以到长安参加冬集,第二年春铨试授官,则释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必在此时。
在这里,还有一诗需先辨明。《送郭乂杂言》诗,《考证》、刘谱、陈谱皆认为作于岑参游河朔的第二年春归来时。以为诗中首四句“地上青草出,经冬方始归。博陵无近信,犹未换春衣”是说岑参经冬至春始由定州博陵郡而归。其实,这一理解是错误的。按全诗共二十四句,前十六句皆言郭乂,自“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始写自己。首四句谓郭乂在长安经过了冬天,至春天青草出时始归家乡博陵郡,由于家乡近无音信,未寄来春衣,只好着冬装归家。岑参此诗当作于天宝七载(748)春,而岑参自河朔归长安,则至迟有天宝六载秋冬之际。《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谓选人“以十月会于省,过其时者不叙”,则岑参必须于天宝六载十月赴长安参加冬集。
天宝七载春,岑参被授与右内率府兵曹参军,时写有《初授官题高冠草堂》一诗,云:
三十始一命,宦情都欲阑。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涧水吞樵路,山花醉药栏。只缘五斗米,孤负一渔竿。
经过数年的漫游隐居,也随着年岁的增长,岑参已不再像应进士试时那样对仕途充满了幻想,故曰“宦情都欲阑”。时岑参三十岁整。由天宝七载年三十逆推,则其生年当为开元七年(719)。而二谱俱承《考证》、《系年》之说,将岑参《初授官题高冠草堂》诗系于天宝三载下,于是,陈谱推岑参生年为开元三年,刘谱则又参照《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一诗,推其生年为开元四年(716)。
岑参在诗文中多处提及年岁,若以开元七年生来考定,则每每相合;若以二谱推算,却多有抵牾。抵牾处,二谱便以“约举成数”而言之。现将其诗文胪列如下。
《感旧赋》云:“岑年三十,未及一命。”当为岑参天宝七载正月初铨试授官前所作,按吏部授官,多在三月进行。而二谱却将此赋系于天宝二载(743)下,陈谱谓岑参是年二十九,刘谱谓二十八,均以为“约举成数”。按,“一命”者,第一次命官,初次授职也。命官授职,属吏部选事,与礼部贡举考试无涉,这由唐人进士及第诗与落第诗均无“一命”之词可知。由是知,此赋必作于吏部选官前,而非进士举试前。所谓《感旧赋》,也就是思昔赋,是作者即将步入仕途前,抚今思昔,感慨万端,对以前十年生活的一次总结。若此赋作于天宝二载,时作者尚未登第,而且也不可能知道他第二年会登第,则“今”与“昔”并无不同,何以有“感旧”之叹?且此赋末句“思达人之惠顾,庶有望于亨衢”,明明是一副即将授官、有望仕途通达之口气,这种口气是进士及第之前绝不会有的。《感旧赋》又云:“参,相门子,五岁读书,九岁属文,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我从东山,献书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岑参二十岁当为开元二十六年(738)。是年,岑参由隐居地嵩山少室来到长安,开始了他应进士举的所谓“献书”生涯。而陈谱推岑年二十为开元二十二年(734),刘谱则以为是开元二十三年。然开元二十二年正月至二十四年十月玄宗是在东都洛阳,进士考试也当在洛阳举行。于是二谱作者解释赋中的“西周”说:周赧王时,东、西周分治,西周王城在今河南洛阳一带,岑参因是到洛阳献书的,故将洛阳称作西周。但这一解释无法自圆其说。岑参《冀州客舍酒酣贻王绮寄题南楼》诗云:“夫子傲常调,诏书下征书。知君欲谒帝,秣马趋西周。”二谱作者在诗注中又俱将“西周”解释作长安。岑参此诗与《感旧赋》的写作时间相隔不到一年,不可能一会儿在诗中说西周是长安,又一会儿在赋中说西周是洛阳,岂不自相矛盾?在唐人诗文中,称洛阳为西周者尚未及见,而称作东周者却不乏例:梁肃《明州刺史李公墓志铭》云:“天宝十五载,大盗覆东周。”(注:《全唐文》卷五二○,第5291页。)欧阳詹《上董相公东风诗启》云:“昨以赴调东周,又聆相公此方镇安之美。”(注:《全唐文》卷五九六,第6026页。)二文之“东周”,俱指洛阳。由此可见,唐人均以东周指洛阳,把长安称作西周。故岑参是到长安献书的。所谓“蹉跎十秋”,是指开元二十六年至天宝六载这十年时间,包括应进士试与及第守选在内,若仅仅理解为是应进士试之献书十秋就不对了。
《银山碛西馆》:“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二谱定此诗为天宝八载赴安西途中所作,是对的。然陈谱谓是年岑参三十五岁,刘谱谓三十四岁,这都距约举成数之“三十”较远。其实,岑参是年三十一岁,故云。
《北庭作》:“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二谱将此诗系于天宝十四载(755)春,陈谱云岑参时年四十一岁,刘谱云四十岁。按,诗当作于至德二载春岑参由北庭赴凤翔前。时岑参三十九岁,与《行军二首》诗为同年作。
《行军二首》:“吾窃悲此生,四十幸未老。一朝逢世乱,终日不自保。”题下自注曰:“时扈从在凤翔。”二谱均将此诗系于至德二载六月,是对的。陈谱谓岑参是年四十三岁,刘谱谓四十二岁。然天宝十四载与至德二载相距三年,岑参绝不会将此相距三年的岁数俱称作四十的。故知《北庭作》与《行军二首》俱作于同一年,即至德二载,时岑参三十九岁。
《太一石鳖崖口潭旧庐招王学士》:“偶逐干禄徒,十年皆小官。”二谱均将此诗系于天宝十二载(753)下,则非。岑参于天宝十载秋自安西归京后的两三年中,并未入朝做官,也就是说时已罢高仙芝幕府职,即右威卫录事参军、充安西节度使掌书记职,仍以前资官身份守选。而此诗却说:“抱板寻旧圃,弊庐识迅湍。君子满清朝,小人思挂冠。”“板”即笏,上朝时所执之手板。“小人”,岑参自称。“挂冠”即弃官。由是知,时岑参正在朝为官,则诗当作于乾元元年(758)在长安为右补阙时。“王学士”是否为王维,可存疑,王维有《谢集贤学士表》作于乾元元年春。且岑参此时与王维、杜甫、贾至过往较密,有《早朝大明宫》等诸诗相互酬唱。又,补阙为从七品官,当然是小官了。由天宝七载岑参释褐为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到乾元元年,恰为十年,故曰“十年皆小官”。
《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年纪蹉跎四十强,自怜头白始为郎。”二谱将此诗系于广德元年(763)下,是对的。陈谱谓是年岑参四十九岁,刘谱谓四十八岁。然不论是四十九岁,还是四十八岁,都更接近五十,约举成数也当曰“五十”。且古人举年岁多不说二十九、三十九、四十九,而曰三十、四十、五十,如《北庭作》和《行军二首》不言三十九而曰四十,就是如此。即使今天,好多地方仍然还有这种习惯。正因为如此,刘谱才据此诗将岑参生年推迟一年,定为开元四年,认为广德元年为四十八岁。其实,岑参是年四十五岁,故曰“四十强”。一般来说,所谓“四十强”,是指四十岁所过不甚多。大历诗人钱起有首《送裴迪侍御使蜀》,约写于肃宗上元元年(760),诗中说:“柱史才年四十强,须髯玄发美清扬。”(注:王定璋《钱起诗集校注》卷八,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55页。)裴迪此时可能只有四十三四岁,最大也不会超过四十五岁,若是四十八九岁,绝不会是“须髯玄发美清扬”的。所以把四十八九岁说成“四十强”,是解释不通的,也不合习惯与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