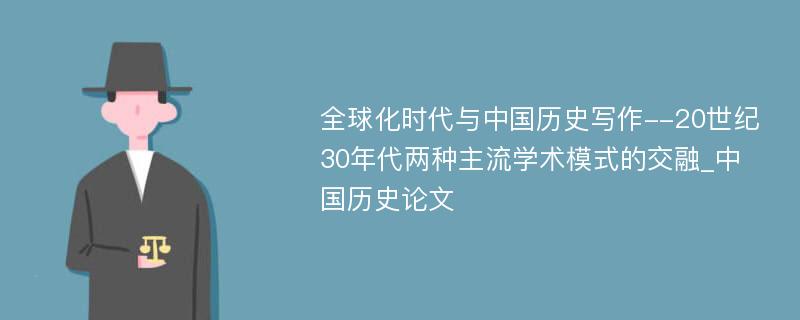
全球化时代与中国历史的书写——1930年代两个主流学术典范的交融会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历史论文,典范论文,主流论文,年代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0)03-0152-10
全球化发展对未来史学将产生什么影响,是当前国际史学界思考的重要问题。以世界学术领导者自居的美国来看,芝加哥大学美国史研究的资深教授方纳(Eric Foner)于2000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以全球化为题发表就职演说,指出这一发展将使美国历史学家更清楚地认识到必须以不同方式思考历史,称:“大约五十年前,Geoffrey Barraclough怀疑‘目光短浅地局限在单个国家’的历史学家们能否有效地阐明‘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对于美国历史学家来说,今天思考这个问题尤显重要。”①在这位身任新世纪第一位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方纳看来,美国作为世界上无可争议的超级军事、经济和文化强国,将要回答全球化到底是向一个均衡化和“美国化”的世界演化;抑或发展成为多样性的社会变革,在全球日益频繁的文化和物质持续交流中如何与本土化合为一体?正如此次演说的题目,方纳神往的是“全球化时代的美国自由”。②当然,“美国自由”不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当务之急,处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弱势的国家和地区可能更需要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类涉及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仅以变动中的中国意象来看,相对于前天的中国、昨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已被认为是一个不断强大的世界性力量,而非以往积弱积贫、拼命摆脱困境的老大衰败帝国。影响到对中国历史的认知,民间私下流传的一个黑色幽默,是一位小学老师对学生说:“我们中国强大之后,不再受人欺侮,也不会欺侮别人。”或许听了太多关于列强欺侮他国,中国被列强欺侮的历史,一位学生举手问道:“老师,如果我们不欺侮别人,怎么知道自己强大了呢?”
全球化时代需要更为包容、多元和开放的中国历史研究。作为中国大陆历史学主流学术期刊的《历史研究》,早在2002年第1期就以“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挑战与思考”为题编排了一组文章,编辑部按语称当前中国大陆史学面临“作为人文学科的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界定和关系问题,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在国际化的背景下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建立中国史学自己的话语系统问题”。③不过,令人多少有些难堪的是,中国大陆史学界迄今为止尚未见到一篇回应这些问题的理论反思和探讨。学术犹如积薪,对任何一个历史问题的研究,必须首先反思这一问题本身的历史。毕竟,相对于历史上的先秦、汉学、宋学、清代考据,乃至20世纪初的新史学各家,在关于什么是“中国”,以及如何进行“中国史”研究的问题上,1930年代形成了对我们今天影响至为深刻和全面的两个学术典范:一是1927年国民政府定鼎南京之后,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汇聚陈寅恪、李济、董作宾、顾颉刚等人,形成了科学实证主义,或者说史料派的研究旨趣,是1949年建国之前,及此后台湾的主流学术典范;另一是1928年前后,以郭沫若、范文澜,及同一时期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陶希圣等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或者说史观派的研究取向,1949年建国后是中国大陆的主流学术典范。长期以来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之争,这两个主流学术典范曾经冰炭不容,并影响到此后学者大都从二者的政治对立,或将之作为前提展开研究。1990年代以来,各种纪念性、缅怀性或总结性的论述,尽管尝试政治与学术的分离,但关注中心仍然是各自的学术贡献和影响,似还未走向一个交融会通的反思路径。鉴于此,本文不再着意于那个年代关于政治立场或思想观念的是非之争,而是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叩问今天全球化时代面对问题的答案和启示,以求将其作为未来学术发展的源头活水。
一 种族、语言和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切入角度
将“中国”置于历史理解的中心,视之为万国史一部分的中国史研究,并非是中国学术的固有问题,而是近代以来中西文明相遇,那些早期抵达的欧美传教士、探险家和旅行者们最先提出的。因为曾让他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众多族群,历经千年沧桑却未像古希腊、古埃及文明那样消失,也没有像欧洲人进入印度之初,看到的只是一个社会,而非统一的政治实体,更不像他们熟知的欧洲历史自神圣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出现的碎片化,分裂成众多封建邦国。④出于欧洲文化中心观的立场,那个时代的欧洲汉学家和思想家的普遍看法是中国长期封闭自锁、停滞不前,就像被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从不接触新鲜空气的木乃伊。⑤虽则,关于“中国”一词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广泛流行,历史上也早有六艺、经史、诸子百家,以及汉学、宋学、清代考据之学,但所谓“中国”只指中原华夏诸国的文化概念,讲述一家一姓、王朝兴亡更替的故事。1902年前后,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新史学》、《中国史叙论》等一系列文字,明确提出古代中国历史经历了“中国之中国”,前近代“亚洲之中国”,近代以来“世界之中国”,并称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所以,梁启超大力鼓吹书写国家、国民、社会、群体,即中国的历史,所谓:“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⑥
由于自视晚清思想界、言论界的陈涉,梁任公虽鼓动人心地提出“新史学”的响亮口号,并“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⑦,却因杂事牵累而终其一生无法平心静气写出一部能够作为学术典范的中国历史。此后1910-20年代的四分五裂和军阀分立的政治乱象,也没有为学者提供重新书写中国史的必要条件。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历史学者鼓吹:“吾国学者,尤切望其整理国史,更进以搜掘古物,补正前史,以应西洋学者之寻求,而与中国史以适当位置,史学成立四千余年之国民乎!当不辜负此重大之责任也。”⑧可是作为偏隅江南的地方性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风夙称保守、稳健,根本没有统领重写中国历史的文化和学术能力及信心。再至1922年,由胡适、顾颉刚等人领军的北京大学国学门,虽也曾力图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做成系统的中国文化史,并称“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但同样让他们难展宏图的是,北洋时期军阀割据的政治格局,不仅未能调查较多遗存中国古代民族语言的各地方言,且对于安特生发现的渑池石器时代之遗迹,中国学者也从未“身莅其境”。⑨再至1925年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吴宓聘请了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以及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回来的李济,尽管组成了当时国内最卓越的研究阵容,却也只是个人兴趣意义上的教学和研究,始终未能形成重新书写中国历史的团体之合力。时任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所助教的浦江清,在1928年1月14日日记中写道:清华主其事者均外交系中人,官派与洋派兼而有之,不知教育为何事,学术为何事也,研究院国学部“故三年来成绩一无可观”。⑩
1927年7月,国民政府定鼎南京,随即议决由蔡元培主持创办中央研究院。最初,中央研究院没有成立专门研究中国历史之机构的计划。由于傅斯年一再强调近代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科学性质,并认为重写中国历史学和语言学,更是中国人的责任,何况中国本有那么丰富的资料,遂使蔡元培同意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11)其时,傅斯年被聘心理所筹备委员,后任史语所负责人,又任广州中山大学国文、历史两学系主任,胡适戏称为“狡兔三窟”。不过,在致胡适的信中,傅斯年充满期待地说:“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业已筹备,决非先生戏谓狡兔三窟,实斯年等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必黾勉匍匐而赴之。现在不吹,我等自信两年之后,必有可观。”(12)果然,1928年10月22日,史语所正式对外宣告成立,即派遣了由董作宾带队的考古小组,赴河南安阳的殷墟进行发掘,并派助理员黎光明赴川边进行民俗调查。此后又派考古组长李济主持了殷墟第二次和以后多次发掘,并多次派出人员前往广东、广西、福建和河南等地进行民族、民俗、考古、人类学和方言学的考察和调研。作为一个划时代的重大学术突破,史语所诸君的中国古史已不只是拓片上文字的研究,而是对实物(甲与骨)的观察,再由实物注意到地层,并参证其他遗物和比较国外的材料,进而揭示中国文献关于商朝的记载并非向壁虚构,把中国的历史从周文王、周武王上溯到商汤以及其先王,保持了中国文明古国的地位。(13)傅斯年由此充满信心,称:“假以时日,使此研究所能为中国建立若干文史科学,则后之探河源者,必以为北辰韩愈,祭酒荀卿,昭然无他属也。”(14)
王汎森等研究者早已指出,傅斯年揭橥的史语所工作旨趣,深受德国兰克(Ranke)实证史学影响。然而,兰克对史料的开掘之所以如此坚定不移,义无反顾,恰在于他矢志于德意志统一民族国家的历史。1824年,兰克出版了第一部名为《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的历史专著,关注16世纪转折期近代国家体系的形成,此后一生研究重心几乎都围绕着主要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晚年更想写作一部以民族国家兴起的世界通史。伊格尔斯写道:兰克强调的新的历史科学中,看起来有一种悖论,学术的专业化一方面要求严格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要求历史学家起到政治的和文化的作用,因为“科学化的发展要求历史学家们深入到档案中去寻求证据,以便支持他们民族主义的阶级的成见并从而赋给它们以一种科学权威的气氛”。(15)此外,曾游学于德国的傅斯年还认为:“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语言学总是一个大题目,而直到现在的语言学的成就也很能副这一个大题目。”(16)如果考虑到不仅傅斯年,其时治中国史的主流学者,如陈寅恪、顾颉刚、李济等人也都将研究重心集中在语言和种族的议题。倘若追溯到拿破仑战争后德国思想学术界的发展,即面对其时政治上四分五裂,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德意志各邦,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格林兄弟(Jacob Grimm,1785-1862 Wilhelm Grimm,1786-1859)赫德(Johann Gotffried Herder,1744-1803)等一批德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强调从语言-种族意义上展开对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研究,以求由此推动政治上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17)
不同于傅斯年等人以语言-种族为中心的文化研究范式,此时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强调从社会经济生活的角度进行研究。作为其时这一学派的领军人物,一位是在1930年1月将自己在1928年至1929年期间发表的五篇关于中国古史讨论的文章,汇集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的郭沫若;另一位是积极参加193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史论战,并于1934年12月创办《食货》半月刊,也鼓吹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书写中国社会史的陶希圣。(18)尽管两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所不同,但都将自己定位于对以语言-种族为中心的文化研究范式的反叛和挑战者。郭沫若对傅斯年的老师胡适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称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支配了几年,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从新‘批判’的必要”。(19)陶希圣在晚年写道:“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六年,我在北平各大学讲课及演说,又往天津、济南、太原、南京、武昌讲课及演说,全是以社会史观为研究古来历史及考察现代问题之论点与方法。在正统历史学者心目中,我是旁门左道。正统历史学可以说是考据学,亦即由清代考据与美国实证主义之结晶。我所持社会史观可以说是社会观点、历史观点与唯物观点之合体。两者格格不入。”(20)
基于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郭沫若认为讨论中国历史的起源,先要弄明白中国的真正的历史时代究竟从哪儿开幕。通过对罗振玉收集的卜辞及殷墟考古挖掘报告,郭沫若具体考察了商代的渔猎、祭祀、婚姻制度、货币、贸易,以及奴隶名称、奴隶身分之升迁、奴隶来源、王的谥号,以及兵器、用器等,推定商代的经济生活方式主要是农业,并有繁盛的畜牧业和手工业,断定中国在殷周时期出现了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捩。殷代已到氏族社会之末期,一方面氏族制度饶有存在,另一方面则是阶级制度已逐渐抬头。对于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关于周人制度创新的著名论断,郭沫若评价道:“其说大抵近是,然此乃时会使然,即经济状况发展到另一阶段,自不能不有新兴之制度逐渐出现。于理非一人一时之所能为,于事亦实非一人一时之所能就。”(21)与郭沫若多少有些相同,陶希圣也曾认为中国古代经历与欧洲大致相似的历史发展阶段,并聚焦于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不过,至1932年前后,陶希圣开始强调细致和具体的研究,而非热衷于理论论战。用他的话说,经过四年的社会史论战,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见解已多,希望减少短篇论文,“多来几部大书,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下一个强固的根基。”(22)由他创办和主持的《食货》杂志,1934年12月至1937年7月共出版了61期,发表了300余篇大小论文,除少数外国社会经济史理论的翻译和作为社会史讨论之余绪的中国社会形态讨论外,绝大多数是具体社会史及经济史研究,迥异于作为当时主流学术期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较多刊载文化史论文的治学意向。(23)
二 “东方学之正统”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面对近代以来欧美/日本学术的巨大影响,1930年代这两个学派明确提出在中国史研究领域里的应对模式。正如傅斯年虽深受欧洲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影响,但在其游学德国的那段时间里,语言学似已不是欧洲历史学主流,不居显学地位。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的季羡林,在1950年代初撰文称:20世纪之前,欧洲学者认为语言学家的前途是有无限光明的,但是到了20世纪初年,不但人们盼望的光明没有到来,且还逐渐暗淡下去。大师一个个凋零了,Karl Varner死于1896年,Johannes Schmidt死于1901年,Henry Sweet死于1912年。后起的语言学家不但数目极少,且一代不如一代。季羡林说自己初到德国不久,本来想专门研究印欧语系的比较语言学,但了解到按照传统办法,想研究比较语言学最少要会三种语言,即梵文、希腊文、拉丁文,遂决意先念希腊文。不久,季羡林彷徨起来,请教在德国语言学界极有声望的老语言学家E.Horammnn,得到的答复是最好不要研究这门学问,因为它的前途已经很黯淡。Horammnn教授不无悲凉地告诉季羡林:大家熟知的材料都已经一遍又一遍地研究过了,“在这些嚼过的骨头里很难再嚼出什么油水,除非再有新材料发现,这门学问就不会有什么发展,但哪里有那样许多新材料给人发现呢?”(24)不过,季羡林指出Horammnn教授是一位有五十余年研究经历的老学者。统计数字也表明,自1850-1900年期间,德国大学总共141位历史讲座主讲人之中,87人有语言学(其中72个是古典语言学)训练或研究背景。(25)所以,或可认为傅斯年、陈寅恪关注的是其时欧美最为成熟、积累最厚,且逐渐沉寂的学科。
傅斯年没有追风于当时德国历史学主流,尤其是抽象玄虚的德国历史学理论。即使傅斯年终生服膺和倡导的兰克史学,按照王汎森教授的说法,他一生也只提过其名字二三次,“藏书中没有任何兰克的著作”。(26)或可再按照王汎森教授的解释,当傅斯年到达德国时,大学里已不再讲授兰克史学,而是作为德国史学的普遍性知识,“化作春泥更护花”。实际上,其时德国历史学发展态势,如果兰克复活,肯定也会目瞪口呆、摇头叹息。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史地系教授徐则陵撰文介绍当时西洋史学概况,将兰克译为“朗开氏”,称在他之后西洋史学家始有批评精神同考评方法,史学乃有发展之可言。不过,徐则陵指出,近四十年来,普鲁士国人民爱国思想而统一日耳曼,“德国史学受其影响,顿失朗开派精神,而变为鼓吹国家主义之文字,自成为普鲁士学派,国家超乎万物,为国而乱真不顾也,视国家为神圣,以爱国为宗教,灭个己之位置,增团体之骄气,其源盖出于海格(Hegel)世界精神(world Spirit)争觉悟求自由之史学哲学,乃尼采之强权学说”。或可证明徐则陵并未虚掷此言的是伊格尔斯在回顾20世纪德国史学发展时,也称在19-20世纪之交,德国历史学家在俾斯麦之下的德国统一进程中放弃自由主义信念,加强对国家中心地位及对国际事物的强调。这种狂热状态至少持续到魏玛共和国时代,也就是傅斯年游学德国期间。伊格尔斯说:那些1914年以前训练出来的历史学家们,几乎都抵制同一时期美国历史学转向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法国历史学在转向这些新生学科的同时,也在转向人文地理学和人类学的变化,“他们满怀憧憬地回顾霍亨索伦王朝的君主制,并且这一点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27)
面对欧美学术,尤其是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中亚西域史研究的领先地位,傅斯年主张从历史学和语言学两个方面确立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史的主体地位。即他所说的:“理宜发达我国所能,欧洲人所不能者(如文籍考订等),以归光荣于中央研究院,同时亦须竭力设法将欧洲所能,我国人今尚未能者而亦能之,然后国中之历史学及语言学与时俱进。”(28)在傅斯年看来,这两个方向在中国“发达甚早”,至少在顾炎武、阎若璩那个时代就已经使用最近代的手段,历史学和语言学都是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物的,中国学者似不难与欧美学术平起平坐。傅斯年认为西洋人治中国史没有太高的水准,即使他们之中最优秀的汉学家,注意的也只是汉籍中的中外关系,经几部成经典的旅行记,所发明者也多在这些“半汉”的事情上。傅斯年强调,尽管这些研究意义重大,可能会改动中国史的视影,但“中国史之重要问题更有些‘全汉’的,而这些问题更大更多,更是建造中国史学知识之骨架。”(29)实际上,认为欧美研究中国历史的水准不高,在那个时代不只是傅斯年一个人的看法。南京高等师范的缪凤林也写道:百年以来,西洋史发展,一日千里,一般史家,率有宇宙史之希冀,其努力于世界通史之编纂者,亦不乏其人。然彼等于欧美诸国史乘,综合分析,闻已日趋精细,而对于东方各国,则大半模糊,尤以中国为甚。缪凤林点名批评1870-97年期间曾在中国海关任职,1902年被聘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教授,并也是当年胡适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的夏德(Friedrich Hirth,Ph.D,1845-1927),所著《中国古代史》(Ancient History of China)“更属专论中国古代之书。然余读其书,既未能明了吾国文明之真价,而其错误,直非吾人所能想象。”(30)这也容易理解在那个普遍以为中国事事不如人的年代里,傅斯年何以会如此满怀信心地提出“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同样,对王国维、罗振玉等人著作有过精深研读的郭沫若,也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几乎等于零。郭沫若的解释是,外国学者对于东方情形不甚明了,那是情理中事。“中国的鼓睛暴眼的文字实在是比穿山甲、比猬毛还要难于接近的逆鳞,外国学者的不谈,那是他们的矜慎,谈者只是依据旧有的史料、旧有的解释,所以结果便可能与实际全不相符。”在他的心目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价值在于人类思维对自然观察上所获得的最高的成就,即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方法论、认识论,而非关于某一社会历史的具体知识。他说:“要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31)至于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郭沫若认为应该尽量让研究使得一般的,尤其有成见的中国人,感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外来的异物,而是泛应曲当的真理,并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已经有着它的根蒂,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循着那样的规律而来。作为具体实践,郭沫若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初时,每天从与东京附近的千叶县的市川,乘车前往东洋文库,除读完了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还读完了被他称为令人神往的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以及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河南考古时所做的彩陶遗迹的报告和北平地质研究所的关于北京人的报告。(32)用郭沫若的话说,要书写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33)
值得一提的是,在1930年代诸多历史唯物史学家中,被认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成功典范,并非是能熟练阅读德文原著的郭沫若,而是从考据训诂、诵习师说的经学系统走出来的范文澜。据说,范文澜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原著,还是在1938年河南沦陷之后,当时他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之中,一面深入山区,向群众作抗战宣传,一面阅读马列著作,“认真圈点,还写了许多札记”。(34)1940年8月至翌年4、5月完成上册的《中国通史简编》,最大特点是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文。范文澜承认自己当时只是“一个初学马列主义的人,一下子能够写出一本具有科学性的中国通史那真是怪事。只能像个初学走路的孩子,东倒西歪,连跌带爬,不成个样子。”(35)不同于郭沫若从《中国社会史研究》问世以来,就一直检讨研究中公式主义的倾向,范文澜在此后一系列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讲话中,重点似都在批判只会搬弄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教条主义的危害。1957年,范文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所做讲演中,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应得其神似,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也就是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具体问题密切结合,获得正确的解决;反对貌似,即“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灵丹妙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同样谈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范文澜认为恩格斯揭示的普遍规律来自印第安的原始社会,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西欧的封建社会,它们有各自的特殊规律,与“中国相比,就有很多很大的不同,只是学习观察问题的方法,并没有说可以搬来搬去套别国的历史”。(36)
三 对现实社会的激进批判与纯净学术之追求
如果仅就学术推动而言,傅斯年等史语所诸君强调主观的客观基础,重视考古学,将考古作为证据,无疑开启了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新时代。但如果就学术对社会的影响,即不但要研究、书写历史,同时也要创造历史的意义来看,傅斯年等史语所诸君把研究重点放在厚集史料,注重“窄而深”式的专题研究,只为高水平的同行专家写作,却又是自我放弃了模塑社会思想和引领时代精神之责任。作为一代学术领袖,傅斯年虽满怀重要的历史大问题,并也有将中国历史学推向世界、与欧美学者平起平坐的雄心壮志,但由于过于相信资料的搜集和考订,想等到资料收集齐全以后,全面撰写中国上古史,因而出版的学术论文不多。至于史语所的工作,事隔80年之后,台湾“中央研究院”出版的院史总结道:以李济为首的考古团队遵循考古学的专业方法挖掘遗址,过于看重详细记载科研资料,撰写的研究报告合乎欧美专业的最高标准,致使宣布殷商遗址的发现之后,始终没有出版品说明发掘这些古物的历史意义。相比之下,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顾立雅(Herlee Glessner Greel)听到安阳大发现的消息以后,远渡太平洋前来参观发掘,回到美国便立即写成专书,说明历史学研究可以从这一次考古发现和解决什么历史问题。当然,李济对顾立雅所为非常不满,却也无可奈何,“然而史语所在无意中也成为提供欧美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史资料的工具”。(37)至于其社会影响,与之关系密切的何炳棣认为,史语所的出版品虽考证精详,但是论点零细琐碎,缺乏综合,尤其没有西方社会科学的视野。(38)就此,一些台湾学者有所发挥地写道:由于史语所诸君不愿对中国当前处境提供历史解释,“反而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大行其道,垄断了历史解释”。(39)实际上,这种说法早见于1940年代的出版物,当年朱谦之就指责傅斯年等人反对历史哲学,“却不知即在这个地方,却给马克思派乘虚而入,以大大发展的余地”。(40)
作为一个普遍现象,1930年代那些深受马克思影响的历史学家,大都位处学术社会的边缘,生活境遇也都不宽裕。1922年北京大学毕业后,陶希圣就一直是在革命运动风口浪尖的弄潮儿。1928年至1930年,陶希圣再次栖居上海,撰写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一系列文字(后来辑成《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刊出),过的也是文人的刻苦生活,所谓“虽迁居数次,皆为一楼一底之房屋。每夜灯火如豆,夫妇两人同一书桌,各自做工。我写作之最高纪录为一个月十四万字”。(41)同样,范文澜1917年6月北京大学毕业之后,留校给蔡元培当私人秘书,不久因为缺乏社交经验和不会写白话文而辞职。直到投身革命之前,范文澜先后在沈阳高等学校、湖南省汲县中学、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任教,以及编写《文心雕龙讲疏》、《诸子讲义》等书,不论担任教职,抑或学术著述,均不在当时学术中心。再至1930年代中期,也曾受到马克思影响,且与郭沫若等左派学者多有交往的历史哲学研究者朱谦之,担任了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为了与置身学术主流的史语所、北京大学分庭抗礼,朱谦之提倡“民族的无产阶级文化”,高调反对以北平为代表的北方文化。朱谦之称北平老到好比一座“死城”,在死城中充满着安静寂然的乐趣,必然凝结成封建势力之无抵抗的策略和学术上的考古倾向,考古及考证派不谈思想,不顾将来,其心理特性完全表现着对于眼前社会之无关心,而只把眼光放在过去的圈套里面。朱谦之明确批评傅斯年等史语所学人视历史为破罐子,不认为历史进化法则之存在;这样以历史事实为特殊的孤立的东西,正是其个人主义特性之充分的表现,“是资产阶级社会之御用的史家”。(42)
不过,如果说傅斯年等史语所学人缺乏一种高瞻远瞩、总揽并包的识度与气魄,恐怕有失公允。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专制无胆,民主无量”的软弱行政体制,对知识分子只能拉拢利诱,而非打击改造。在傅斯年担任所长的史语所,抗战爆发之前专任研究员的薪资,月入200-500元不等。当时北平的生活水准是每个月花费20-30元,能租一个有二十几间房子的四合院,雇佣一个厨子、一个仆人和一个人力车夫,每天再花上1元菜钱(当时,10元一桌鱼唇席,8元一桌海参,12元一桌鱼翅席,酒水小费合起来近20元),就可以过很宽裕的生活。(43)正是有了这种衣食无虞、心无旁骛地进行高度专业化研究的生活环境和物质保障,傅斯年对史语所的定位是:“非袭北庭之旧,实在党国奠都南京之时,尤愿当建国之际会,树坚实之风气,藉洗往者叔世之浮华。”(44)傅斯年相信,他们正处在一个开代之际,如果能够坚持高贵的学术理想,为学术而学术,“十年之内,必成一风气,以召世人。”(45)需要说明的是,不像此后经历了无数次政治运动和高度市场化的冲击,士林文化浸染太多投机取巧、落井下石、随机应变和钻营求售之恶习,傅斯年那个时代所谓的学风不振,主要体现在相当一批学者自说自话,既不辨西土文化之美隆如彼,又不察中国学术之枯槁如此。(46)作为以一贯之的学术理想,傅斯年早在《新潮》发刊词中,号召中国学者应该知道本国学术在世界上地位之低下,如果自我孤立于世界思想潮流,“不啻自绝于人世”。后来《新潮》推出学术批评专版,傅斯年撰文批评当时中国的学术出版物,“有价值之作,能有几何?所累出不穷者,皆不堪寓目者耳。”(47)接着在留学英国期间,傅斯年又致函蔡元培,批评作为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北京大学,此刻之讲学风气,从严格上说,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即“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48)再当主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之时,傅斯年强调:“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与同伦。”(49)所以,如果就对中国学术发展的贡献和影响来看,即使最激烈的批评者朱谦之也承认:“胡适等人审定及整理的史料,还不过文字史料,历史方法不外乎校勘、考订、分类、训诂、批判,傅斯年则主张考古学,利用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的工具。”(50)
四 结语
针对当时欧洲主流学术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历史,外国学者在中国境内广为收集“学问的原料”,1930年代的这两个学术典范都强调中国历史的普世价值,反对将中国历史研究归类于偏重古代文献考订的国学。(51)的确,从黑格尔到兰克,欧美当时主流学术都认为印度和中国只有“自然史”而没有历史。“历史与自然相反,乃是由人的有目的行为所决定的,所以与所谓的自然人相反,只有文明的民族才有历史。”(52)1930年代前后,正值美国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张,日本帝国主义成为远东霸主,各方在经济、政治方面的争夺也转到对中国学术的控制和影响。其时,除日本东亚同文书院“从事于中国之经济社会调查,其精密皆非国人意想所及”,(53)在中国境内进行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考察,还有北平协和医学校的中国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及以北平作为活动中心的外国学术团体遣送的各种科学远征队。用李济的话说:这些外国人不是专凭着其政治优势,“他们更有一套学术上的理由说给中国人听,使听的人亦可感觉到他们持之有故言之成理”。(54)作为体制内主流学术领袖的傅斯年强调:“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55)同样,正在日本市川撰写《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郭沫若,也不满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派受法兰西学派影响,好作放诞不经的怪论,认为所有先秦古典,一律都是后人假造。(56)当然,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对中国历史知之甚少,郭沫若坚信清算中国的社会,不是外人的能力所容易辨别的,“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57)
正是将中国历史视为世界史,或全人类共同文化史,1930年的这两个学术典范又旨在建设一个开明、平衡而具国际性的中国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家自不待言,因为他们相信人类有共同发展规律,鼓吹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较多关注经济生活、社会结构、历史规律和阶级斗争,比较容易超越民族国家历史书写的狭窄框架。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序言中说得很明确:“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但这必要的条件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58)至于傅斯年史语所诸君关注的种族-语言,虽然较多关注文化精英阶层的文化感受,直接触及历史变迁中的种族识别和文化认同议题,但他们强调为学术而学术,也曾有效地防止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历史真实的曲解和遮蔽。王汎森的研究表明,陈寅恪研究唐代与外族关系史时,指出刻意吹嘘盛唐武功伟大,是忽略了客观事实。在他看来,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唐朝本身的武功,而是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陈寅恪还考证李唐先祖出于胡人,致使有些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深为不满,认为陈氏将中国历史最足以自豪的李唐归于胡种是自损民族信心。(59)正如王汎森教授曾发人深省地比照傅斯年与王国维对殷周文化变迁的不同看法,得到结论是王国维以强烈的道德动机,试图维护“周文化主义”;傅斯年认为所谓周公之盛德,“则非历史学矣”。(60)因为在傅斯年看来,“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61)
学术有多种发展面相,相关研究似也应有多个角度。作为中国一个源远流长的思想史研究传统,司马谈论及春秋战国以来的学术发展时,援引《易·大传》中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的六家,虽学术取向颇多歧异,但目的都是一致的,所谓“务为治也”。再至晚清道咸年间,阮元、曾国藩等人大力提倡宗宋学而不废汉学、宗汉学而兼采宋学,最终达到汉宋会通。无疑,司马谈,乃至此后的阮元、曾国藩等人,并非不知晓,或刻意回避学派间的对立和纷争。之所以认定大道并行而不悖,在于他们面临一个历史的大时代,需要兼综诸说、言会众端的文化和思想建设。就如司马谈论及六家要旨之时,正值统一的秦汉王朝兴起,中国第一次形成了多民族相互依存的文化共同体;再至阮元、曾国藩等人强调汉宋会通之时,又是西方文明东渐,中国文明面临三千年以来未有之最大变局,必须有学术和思想上的兼容并蓄,有容乃大。与之相应,如果仅从当时人、当事人的角度,一味强调“心同此心,情同此理”的现场理解,虽有可能在还原历史意义上有较为生动和细致的呈现,却不一定能够在思想史意义上有效展示那个时代与今天密切相关,或者说进一步拓展“使其在我”的历史精神。作为后来之人,我们的幸运在于能够用后见之明的批判性视野,不再背负前人的历史包袱,并超越前人的历史局限。尽管1930年代这两个学术典范有着语言-种族和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研究取向,与欧美学术又有着“东方学之正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应对,以及对现实社会激进批判和纯净学术之追求的不同考量,然而,从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来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二者的交融会通之处在于共同开创了一个关于“中国”、“中国历史”书写的新境界和新格局。
注释:
①②Eric Foner,"American Freedom in a Global Age," American History Review,February,2001,p.6.
③《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④Michael Ny-Quinn,"National Identity in Premodern China:Formation and Role Enactment,"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Kim ed.,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38.
⑤经典描述请参阅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⑥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48-449页。
⑦梁启超:《三十自述(1902年12月)》,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9页。
⑧陈训慈:《美人研究中国史之倡导——美国拉多黎教授著》,《史地学报》第1卷第3号,1921年。
⑨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⑩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
(11)(13)台湾中研院编《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简史》,台北中研院2008年,第16-29、29页。
(12)傅斯年:《致胡适(1928年4月2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14)傅斯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编辑人附识》,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483页。
(15)[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2页。
(16)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10月),第3页。
(17)Richard Bauman,Charles L.Briggs,Voices of Modernity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the Politics of Inequality,Cambridge,U.K: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pp.193-220.
(18)何兹全:《爱国—书生》,何兹全:《何兹全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717-2718页。
(19)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民国丛书》第1编第76辑(历史、地理类),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2页。
(20)陶希圣:《夏虫语冰录》,(台北)法令月刊社1980年版,第1637条,第344页(此资料的PDF文件,由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蒋宝麟同学提供,特此致谢)。
(21)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民国丛书》第1编第76辑(历史、地理类),第94页。
(22)陶希圣:《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原载1932年8月《读书杂志》第8页,《中国社会史论战》第3辑,《民国丛书》第2编第80辑(历史、地理类)。
(23)有学者统计1928年至1948年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刊发了文化史论文134篇,占236篇专题论文总数的57%。请参见孔祥成:《历史语言研究所学人的史料观——解读1928-194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东方论坛》2002年第5期。
(24)季羡林:《语言学家的新任务》,《新建设》第3卷第4期,1951年1月1日。
(25)[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续二)》,王燕生译、何兆武校,《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26)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页。
(27)[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75页。
(28)傅斯年:《致蔡元培、杨杏佛》(1928年5月5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61页。
(29)傅斯年:《〈城子崖〉序》,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235页。
(30)缪凤林:《中国史之宣传》,《史地学报》第1卷第2号,第1-2页。
(31)(32)郭沫若:《革命春秋》,《郭沫若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301-365页。
(33)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民国丛书》第1编第76辑(历史、地理类),第5页。
(34)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史研究室主编《新史学五大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
(35)潘汝暄:《范文澜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4辑,第216页。
(36)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4页。
(37)(39)台湾中研院编《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简史》,第136、31页。
(38)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2004年版,第329页。
(40)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现代史学》第2卷第1、2期合刊,1944年5月25日。
(41)陶希圣:《夏虫语冰录》,第1631条,第342页。
(42)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现代史学》第2卷第1、2期合刊。
(43)台湾中研院编《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简史》,第24页。
(44)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敬告河南人士及他地人士之关心文化学术事业者》,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96页。
(45)傅斯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编辑人附识》,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482-483页。
(46)傅斯年:《致胡适》(1934年4月19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128页。
(47)傅斯年:《出版界评》,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111页。
(48)傅斯年:《致蔡元培》,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16页。
(49)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9页。
(50)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现代史学》第2卷第1、2期合刊。
(51)关于这一代学人力求超越1920年代胡适、顾颉刚等人提供新国学的研究,请参见余英时:《“国学”与中国人文研究——提纲》(中研院第28次院士会议主题演讲,2008年7月1日)。
(52)[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王燕生译、何兆武校,《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这种观念体现到课程设置方面,是当时几乎没有一个欧美大学开设专门中国历史。以坐落在美国西海岸,与亚洲太平洋联系最密切,并也是开设东方课程最多的斯坦福大学为例,历史学课程130余种,其中属于远东史的九种,日本居其四,其余则是包括菲律宾、中国、交趾支那在内的远东史。Griffin(Oregon University),《美国人之东方观》(“Why Study Far Eastern History and How?”),张其昀译,《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2年。
(53)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43页。
(54)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李济:《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73页。
(55)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10月),第7页。
(56)郭沫若:《革命春秋》,《郭沫若全集》第13卷,第364页。
(57)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民国丛书》第1编第76辑(历史、地理类),第5页。
(58)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民国丛书》第1编第76辑(历史、地理类),第1页。
(59)王汎森:《新派史学的批评者》,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和社会·史学卷》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
(60)王汎森:《王国维与傅斯年——以〈殷周制度论〉与〈夷夏东西说〉为主的讨论》,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279页。
(61)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10月),第10页。
标签:中国历史论文; 郭沫若论文; 傅斯年论文; 1930年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陶希圣论文; 语言学论文; 范文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