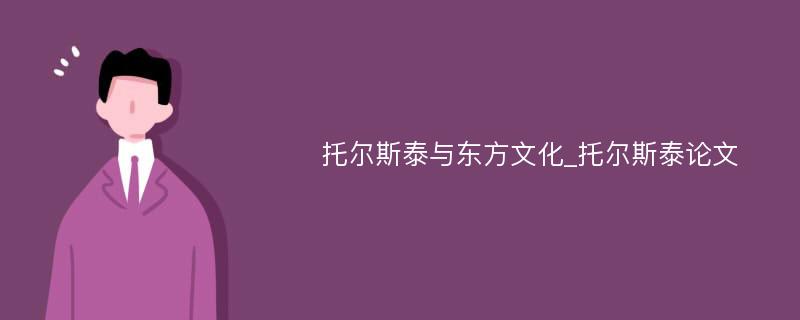
托尔斯泰与东方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尔斯泰论文,东方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托尔斯泰留给人类巨大的精神遗产——托尔斯泰主义,属于东方文化体系。
东方始终吸引着托尔斯泰。1844年在喀山大学开始读书时,他就选定研究阿拉伯土耳其的东方语言文学系;1847年在喀山医院住院期间,他从邻床的一位喇嘛身上,平生第一次受到“不抵抗主义”的启示,……在东方文化中,对托尔斯泰最具吸引力的是中国文化。他自1877年开始阅读研究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并且一直到暮年,兴趣有增无减。其间写过大量的评注和介绍,还曾一度从事过老子《道德经》的由法、德文到俄文的翻译工作,只因精力不及和语义上的障碍才未得完成。他曾经说过:“我被中国圣贤极大地吸引住了,……这些书给了我合乎道德的教益。”他认为:孔子和孟子对他的影响“非常深”,老子对他的影响“强烈”。〔1〕
在俄国上流社会对法国一片奴隶般的崇拜声中,托尔斯泰推崇俄罗斯灵魂。他在俄国农民身上发掘俄罗斯灵魂,也表现自己心爱的贵族身上的俄罗斯灵魂。他笔下贵族和人民之间和谐的纽带就在于俄罗斯灵魂。
在《战争与和平》中,劳斯托夫家族属于庄园贵族。托尔斯泰笔下的庄园贵族更多地保留着俄罗斯的传统习俗。娜达莎·劳斯托夫具有一颗俄罗斯灵魂。紧张而富有生趣的奥特拉德诺耶围猎过后,来到乡间的叔叔家做客。车夫米特加弹奏的三弦琴声令她着迷,正如她觉得叔叔家的腌蘑茹、蜂密和樱桃白兰地是世界上最好的食品一样,她认为这三弦曲是音乐魅力的顶峰。叔叔用六弦琴弹奏的《街上来了一个姑娘》引发了娜达莎心中的“朴素的乐趣”,她随着叔叔的琴声跳起了早已被法国披肩舞挤掉了的民间舞蹈。这位伯爵小姐,受的是一个亡命的法国女教师的教育,她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及怎么样地从她所呼吸的俄罗斯空气中吸取了这种精神?而这正是叔叔所期望于她的那种学不来、教不会的俄罗斯精神。叔叔的女管家安妮西娅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她有感于这个在黑天鹅绒中养大的、跟她自己很不相同的文雅的伯爵小姐,却能懂得她安妮西娅和她的父母、亲属以及每个俄罗斯男女的内心世界。
娜达莎以及整个劳斯托夫家族身上的俄罗斯灵魂表现为习俗和家风,包尔康斯基家族身上则表现为“报国至上”,〔2〕库图佐夫则把蕴藏在全体人民身上的俄罗斯灵魂升华为哲学。库图佐夫是全体俄国人民的精神领袖。
库图佐夫勉勉强强地充当军事会议的主席和议长。在军事会议上心怀不满地昏昏欲睡,甚至鼾声大作。他打着哈欠说“时间有的是”。他认为占有一个要塞并不难,难在赢得一个战役,因此需要的不是强袭和进攻,而是忍耐和时间。他的座右铭就是“忍耐和时间”。〔3〕他深知“欲速则不达”,〔4〕他要靠“忍耐和时间”让法国人吃马肉。〔5〕
对于俄国人来说,俄罗斯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他们在战场上,看见夜空星光明亮,便知道这是“丰年的兆头”。〔6〕农民出身的士兵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说:“俄国和夏季并非绑在一块儿。”库图佐夫和他的部下,懂得根据自然节气的更替去制服敌人。在一定意义上,是俄国的冬天打败了拿破仑。库图佐夫这位“拖延专家”,这个专门反对打硬仗的人,以无比的严肃为波罗金诺战役做了准备。从波罗金诺战役开始到结束,只有他一个人说波罗金诺战役是俄国人的胜利,只有他一个人说“失掉莫斯科,不等于失掉俄国”,〔7〕法国人退却时,也只有他一个人主张给敌人一条退路,并且认为挡住一头受伤的野兽的退路是办不到的。得知拿破仑撤离莫斯科的确切消息,库图佐夫合着手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俄国得救了……”,〔8〕
库图佐夫以全部的俄罗斯灵魂——感情、宗教、哲学——来理解这场战争,领导这场战争。他每时每刻地在领悟这场战争中的神秘主义。作为民族战争的统帅,他不是在他的宝座上用尽力量杀人,毁灭人,而是倾其全力来救人,同情人。他的行为毫无偏差地指向同一的三重目的:调动起全部力量跟法国人战斗;打败他们;把他们赶出俄国。同时尽可能减少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军队的痛苦。他认为,为了十个法国兵而牺牲一个俄国人也不值得。俄罗斯民族在1812年战争中所赢得的胜利,是以库图佐夫为代表的俄罗斯灵魂的胜利,是体现在库图佐夫身上的哲学的胜利。
体现在库图佐夫身上的托尔斯泰哲学,属于东方哲学体系,同主张“绝圣弃智”、“守柔曰强”,崇尚“无为”的老子哲学,和重视“天时地利人和”的儒家哲学一脉相承。中国古代神话《愚公移山》形象地表现了东方哲学的大局观。它肯定愚公对于事务发展趋势的把握,否定智叟将智力仅仅用于对数字的绝对计算。
通过库图佐夫形象表现的托尔斯泰哲学,也同当时流行于西欧的历史理论构成了鲜明的对垒。
这些历史理论认为重大事件的发生是由机会和天才的结合而造成的,认为主宰人类事务的权力操在“伟人”手里。《战争与和平》中的拿破仑则是这种理论的代表。托尔斯泰不仅描写拿破仑的暴躁和过失,更主要的是描写他的自信。托尔斯泰认为拿破仑身上侵略者的自欺欺人的特性使他产生了一种幻觉,使他自以为是在主宰事件的进程。“他早就形成一种信念:在世界任何地方,从非洲到莫斯科维亚草原,只要他在场,毫无例外地使人大大吃惊,舍己忘我地疯狂。”〔9〕波罗金诺战役前夜,拿破仑走到儿子的画像前,觉得自己的一言一行便是历史,伟大得足以让他的儿子玩耍地球。他盲目自恃,认为莫斯科一经占领,俄国就会屈服,夺取世界霸权的计划也就大功告成。可是波罗金诺会战一直持续到日落,也不曾给法国人带来胜利。
库图佐夫正因为不是英雄,才能够感受到最终打败拿破仑,使俄国恢复国土和光荣的“历史的潜流”。事件进行过程中,他所以能够做出一个又一个的正确判断,不是根据战争理论,而是依靠合于自然的天性,将个人意志服从天意,对最高法则大彻大悟。正如庄稼汉卡拉塔耶夫将“无为”哲学用于指导自己的全部人生。他整个形体,既显得“浑圆”、“柔软”,又让人感到“经久耐用”。〔10〕他嘴上挂着的一条重要的格言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11〕托尔斯泰对老子“无为”哲学做如下理解:人的一切灾难的产生,“不仅在于他们没有做完应当做的那些事,还因为他们做了那些不应当做的事。”他欣赏《道德经》第八章中“事善能,动善时”的见解。在他看来,“无为”并非不为,而是守道,“因此人们若遵循‘无为’,便能避免所有个人和社会性的灾难。”〔12〕
托尔斯泰青年时期适值1848年欧洲革命前后,西欧资产阶级新思潮“欧化东渐”,而出国考察却使他对西方文明所抱有的某些若明若昧的希望破灭。他第二次出国期间,得知俄国废除农奴制,他对此态度冷漠。他深知取而代之的不是他理想的制度,而是将会给俄国带来灾难的西欧道路。1861年以后,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面对由此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端,托尔斯泰更加致力于俄国社会道路的探索。
托尔斯泰探求的俄国道路属于东方社会形态。在所有的探索主人公中,《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列文是集大成者。列文同作家本人最为相近,他代表托尔斯泰在各个领域孜孜不倦地探索。对于俄国社会道路探索的重任,主要由他承担。列文比谁都更了解西欧,也比谁都更了解俄国。这同屠格涅夫以及他的小说人物身上单一的“西欧教养”形成鲜明的对照。
列文看到了资本主义对于俄国社会的冲击。“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下来”——对于1861年以后俄国的这一形象概括,就是出自列文之口。摆脱农奴制的束缚,列文是欢迎的,对于在俄国“刚刚安排下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却抱着强烈的批判态度。列文看到,从西欧移植来的雇工制度给俄国带来的是农民普遍的懒惰、怠工、酗酒、偷窃……,造成土地大片的荒废,社会普遍的贫穷,国家财富的减少,以及农民和地主的严重对立。在列文看来,这些制度即使在西欧是合理的——实际上当时西欧对于这些已经不满了——但它不适用于俄国,“正如三一节我们所插在地上的桦树枝,看上去好象是生长在欧洲的真正的桦木林一样,我却不能给这些桦树枝浇水,也不能相信这些树枝。”〔13〕因此,他反对照搬西欧的现成模式。这同屠洛涅夫的西欧派主张大相径庭。
列文体现了托尔斯泰的有关见解。在托尔斯泰看来,没有证据证明俄国必须遵循西欧文明的模式,西欧道路不是全体人类必须遵守的法则,东方各国可以不受它的影响。〔14〕托尔斯泰的社会改造思想首先是对于土地占有制度的改造。面对土地大量荒废和农民的日益贫困等等弊端,列文感到最重要的是调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使农民关心土地上的收成。去史惠兹斯奇家的路上,遇到了那个“蒸蒸日上”的农民家,给列文带来了启发、鼓舞。农业改造的热情占据了列文的心。这户农家致富的原因在于全家是在自己的——或者相对地说是自己的——土地上劳动,他们和土地,土地上的收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屠格涅夫“西欧派”的主张属于“改良”,托尔斯泰主义关于社会改造的见解则属于“改革”。为了调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列文主张“他和农民同样以股东资格参加农业经营”,〔15〕建立具有承包特点的“劳动组”〔16〕……这种旨在改变地主对土地的不合理的占有,改变现存生产关系的改革,对社会具有根本性变革的意义。列文的理想是:“以人人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利害的调和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一句话,是不流血的革命,但也是最伟大的革命,先从我们的小小的一县开始,然后及于一省,然后及于俄国,以致遍及全世界。”〔17〕列文的“改革”是对《死魂灵》第二部中开明地主康士坦夏格罗思想的承继。托尔斯泰探索的俄国道路和果戈理推荐给俄国的改造之路,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倡导的斯拉夫道路一样,都力图避免俄国实行西欧制度,也力图避免俄国发生革命民主主义者所主张的欧洲革命式的暴力革命。
托尔斯泰认为土地所有权是人民自由的保证。1901年5月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思索了人民的种种要求,觉得主要的是土地所有权。如果取消土地占有权,实行耕者有其田,这将是最可靠的自由保证。比‘人身不受侵犯’更可靠。因为‘人身不受侵犯’不是实际上的保证,而只是道义上的保证,即人们感觉自己有权保护他们的家。人们同样地,甚至更多地应该感到自己有权保护用来养活家口的土地。”〔18〕托尔斯泰缅怀十九世纪初叶俄国尚且存在的农耕生活,讴歌历史上农民安居乐业的“小康”社会。他让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在1812年间心满意足地述说:“我们那个田庄很富,田地很多,农民的日子过得不错,我们家也很好,谢天谢地。连老爹一家七口下地干活。好日子。……”〔19〕据那个年间在大俄罗斯梁赞省所做调查记载,那里实行的是按每家已婚男子的数目定期给农民分配公有土地。〔20〕
托尔斯泰也向往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他于1884年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比得过中国人那样善于耕种土地并靠土地养活自己。”〔21〕同年还在《日记》里将中华民族赞为“最富有,最古老,最幸福,最爱好和平的民族”。〔22〕托尔斯泰所向往的中国几千年绵延不断的“农耕文明”,其赖以形成的社会基础是“地主——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冯天瑜先生对此论述道:“这种体制比西欧中世纪的领主制经济给予农业劳动者以较多自由,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结合成男耕女织的生产单位——农户,在这些独立的农户中,农民可以支配自己一家的劳动时间,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因而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这显然比农业劳动者处于农奴、半农奴地位的领主制经济优越。中国在十六世纪以前一直保持着领先于西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此直接相关。”〔23〕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梁漱溟先生等通过长期、周密的社会调查,就已得出下述结论:“北方情形,就是大多数人都有土地。”〔24〕其中河北定县被调查的三个乡区“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家都有地。”〔25〕梁先生通过对中国文化的多年研究甚至认为“限田”、“均田”等一类运动,“不绝于历史”,〔26〕独立生产者大量存在,“阶级隔阂不深”,人与人关系和缓。〔27〕托尔斯泰则通过列文探索的以土地所有制改革为基础的理想社会,以及他不断讴歌的“小康”〔28〕生活,同中国历史上建立在“地主——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太平盛世一脉相承。
托尔斯泰一系列的探索主人公——从《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的聂赫留道夫到《复活》中的聂赫留道夫,都力图使自己在道德上不断完善。在托尔斯泰的道德观念中,为谁而活着是一个致命的问题。那些失掉了俄罗斯灵魂的人物,都是为自己活着。那些具有俄罗斯灵魂的人物,不断地围绕为谁而活着这一致命问题反省自己,领悟“为他人而活着”这一人生真谛。如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在奥斯特里齐战役中负伤,倒在普拉茨山上,高不可测的天空给他以启示,实现了一次顿悟,清洗了自己对拿破仑的盲目崇拜,以及追逐功名的虚荣心。后来又经和平生活的启示,他内心里开始了一种新生活。第二次参加军队时,他与奥斯特里齐战役时大大不同了。一生中的三大悲哀揉合在一起形成了对敌人的极大愤慨,并把自己作为人民中的一分子。此时,那些只知道追求虚荣心的人已成了他嘲笑的对象。又如彼尔同朵罗霍夫决斗之后,灵魂受到极大震动,不断地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我杀死了她的情人,是的,我杀死了自己的妻子的情人。是的,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呢?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呢?”他竭力想弄清自己的过错在哪里,进而提出善与恶,爱与恨,生与死这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问题。彼尔为自己活着的时候,结果毁了自己的生活,只有当他抛弃过去的生活,开始为别人——至少是努力为别人活着的时候,才觉得找到了人生的幸福。随着民族危机的发展,波罗金诺战役前,他深入士兵中间,焦急不安的同时,也体验到一种新鲜的喜悦,一种必须做点什么和牺牲点什么的感情。比起这种感情,舒适、财富,甚至生命都成了弃之为快的虚妄的东西,灵魂里燃起了卫国战争的烈火。
安德烈和彼尔道德上的自省是成长型的自省。两者各自的自省方式类似于南北禅宗的不同:前者通过顿悟,后者通过渐悟。两者又体现了两种归宿:安德烈似乎是看破红尘归于圆寂,彼尔则属于“吃饭穿衣皆是禅”。而列文的自省表现为转变型的自省。列文在探索俄国道路的同时,也在实现从“旧生活”向“新生活”的转变。列文的自省中,包含着作家本人的诸多体验、隐秘、自白,甚至对于某些行为的忏悔。而列文的自省又不同于后来《复活》中聂赫留道夫的赎罪型自省。聂赫留道夫对于自己过去的整个人生进行孤立、静止的忏悔,列文则在人生进程中探索理想的人生,并且这种探索与时代息息相关。
民粹派批评家米海伊洛夫斯基曾就这个时代说过:在七十年代的俄国,自杀者和“我们要面包和娱乐”的呼声使我感到,我们的时代与临近灭亡的罗马很相似。托尔斯泰通过奥布朗斯基家庭的混乱和卡列宁家庭的崩溃,反映西欧“文明”在精神、道德领域对于俄国的冲击,并且通过列文对理想的道德、婚姻、家庭进行探索,以抵御西欧“文明”的冲击,防止莫斯科以至整个俄国成为巴比伦。
列文始终觉得他自己的富裕和农民的贫困两相比较是不公平的,并且一直过着勤劳俭朴的生活。求婚失败,从莫斯科回到乡间开始一种“新生活”时,他下决心以后要更勤劳,更俭仆。他同农民一起割草,体会忘我状态下的幸福。他吃那个笃信宗教的老头儿的泡水面包,像老头儿那样在小树丛下枕着草睡午觉。他对这个老头儿比对自己哥哥还亲近。他吮吸农家出身的乳母的乳汁的同时,吸进了对农民近乎血统一般的感情。他把自己看成农民中的一分子。他为青年农民伊凡和妻子之间所流露的强烈的、青春的、刚刚觉醒的爱情而打动,感觉到这种生活的朴素、纯洁和正当。他向往这种“健康的快乐,同时也加强了自己追求纯洁、美好生活的信心,就像那户蒸蒸日上的农家加强了他探索俄国道路的信心一样。
托尔斯泰认为:“只有当一个人过着在各方面都很自然、都合乎人类固有的常规的生活时,他心里才可能产生感情。”〔29〕在托尔斯泰笔下,凡是自然的,便合于道德。他所偏爱的人物,无一不与大自然有着密切联系。他们心灵纯洁,天性高尚,健康质朴,遵循自然法则,探求一种和谐的生活。娜达莎吸引安德烈的,就是她身上独特的、新鲜的“非彼得堡的”东西。这种女性身上最自然的天性,治愈了安德烈的消沉,也照见了彼尔身上的“最好的一面”。
托尔斯泰主义中的道德观,属于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东方文化中的道德观,“天人合一”的一元价值观,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的天道观一脉相承。这种道德观念注重内心生活,使内心合于自然。托尔斯泰创造了一群内心生活丰富的贵族男女,他们“成长”的过程就是抛弃虚荣、归于内心生活的过程。
面对西欧“文明”在道德、婚姻方面对俄国的冲击,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里礼赞了“家庭的思想”。安娜情节和列文情节代表着社会的两种全然不同的形态和走向。安娜情节表现的是都市上流社会的病态生活,以及它在西欧“文明”冲击下日甚一日地腐化的现状。安娜同卡列宁组成的家庭,是没有爱情的家庭,冲破卡列宁的家庭,同渥沦斯基相爱,她希望重建有爱情的家庭。可是渥沦斯基声言自己是个“吉卜赛人”,过游荡的爱情生活,跟一个个女子调情而永远不结婚。安娜情节处处是“非家”。列文情节表现的则是以宗法制庄园为纽带的农村的健康生活,并到处呈现家庭的意象。他不但不能撇开结婚来设想对于女性的爱,甚至是先想象家庭,其次才想象能给予他家庭的女性。吉提是个“妻子型”——或者“母亲型”的妇女。她爱丈夫,爱孩子,像做了母亲的娜达莎那样,依照卢梭的学说,亲自给婴儿哺母乳,同婴儿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而安娜追求的则是虚幻的情感,违背了自然法则,因而等待她的只能是悲剧。
托尔斯泰礼赞的家庭以及家族文化,绵延于中国上下几千年。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起源于家族文化,“仁”发凡于孝悌,《孟子》这样写道:“仁之实,事亲是也。”(《离娄上》)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的成分,或者说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与家族文化水乳交融,休戚与共。”〔30〕同时,“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 ”〔31〕将发凡于家族关系的儒家学说推及于社会, 便建立起伦理本位社会秩序。伦理本位强调个人同他人、群体的关系,从而有别于个人本位。
俄罗斯历史上也大量存在过家族文化。据记载,十九世纪初梁赞省有65%的家庭有三代以上的人口,有的地区家庭共同体平均为10到11人。〔32〕托尔斯泰笔下的农民卡拉塔耶夫称颂“小康”生活的同时,也不断地抒发对于父母、兄弟、孩子的亲情,表现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意识。〔33〕《战争与和平》处处讴歌了父辈们的家庭生活,托尔斯泰认为这是“绝对愉快的缅怀”。〔34〕列文认为:“自古以来哲学的主要问题就是发见存在于个人和社会利益之间的不可缺少的联系。”〔35〕社会成员间的和谐、一致,是他的理想。托尔斯泰宣扬这种社会道德观,想以此抵制从西欧传入俄国的“个人主义”。托尔斯泰两度国外之行,使他对原先颇为欣赏的“社会自由”完全失去信心。《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自由主义贵族史惠兹斯奇,在自己的庄园里实行了雇工制度。结果“简直是糟透了”。〔36〕
托尔斯泰探索主人公道德自我完善的归宿是宗教。他们找到的“为他人而活着”的人生真谛,同时也就是“为上帝而活着”。托尔斯泰认为好的艺术是宣传人类爱的艺术。对宗教福音穷根究底地探讨,是托尔斯泰创作动机之一。他以宗教原则衡量一切。凡被认为属于亵读了神圣的原始基督教教义的事物,他都给以无情的抨击,而在他的理想人物身上,则倾注全部的宗教感情。有人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那》“好象是上帝拿起他的笔写下的”。〔37〕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笃信宗教的民族。托尔斯泰的艺术表现了作家自己以及俄罗斯民族笃厚的宗教感情。托尔斯泰的“宗教”是广义上的,上自严格的正教,下至个人的生活哲学。
《战争与和平》中1812年事件的双方,不仅表现为两种哲学的对峙,也表现为宗教上的冲突。拿破仑问沙皇的侍从武官巴拉舍夫莫斯科有多少教堂,听到有二百多座教堂的回答后,他说“要这么多教堂干吗”,接着还发表议论:“大量的修道院和教堂从来就是人民落后的特征”。〔38〕而库图佐夫作为俄国人民的代表, 上帝无时不在他的心中。1812年事件里,他和他的部下是在履行上帝的意志。听到拿破仑离开莫斯科的消息后,库图佐夫转向房间对面,转向被神像遮暗的角落,合起掌,声音颤抖地说:“主啊,我的造物主啊!您已经答应了我们的祈祷……俄国得救了。我感谢您,主啊!”〔39〕1812年战争俄国的胜利,是哲学的胜利,也是宗教感情的胜利。
一个意大利青年军官对彼尔说:“同您这样的人民打仗,简直是罪过。法国人使您受了那么多罪,您甚至不怀恨他们。”〔40〕彼尔的这种宗教感情来自于普拉东·卡拉塔耶夫。托尔斯泰的主人公在人民战争中经受的最深刻的洗礼是宗教的洗礼。卡拉塔耶夫笃信宗教。他对一切人——不是对某一个特定的人,而是对他眼前所有的人都爱,都处得情投意合。他爱同伴,爱法国人,爱邻人彼尔。他满口的俗语、格言。彼尔听到的除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还有“受苦一点钟,活上一世纪”,“以为是灾,其实是福”,“蛆咬卷心菜,还是蛆先死”……彼尔突然明白了好久以前他的老保姆告诉过他的那个道理:上帝在这里,在那里,无所不在。卡拉塔耶夫心中的上帝,比共济会所承认的造物主更伟大,更无限,更不可思议。因为彼尔有了信仰,可以经常感觉到上帝,所以他用一种新的眼光看人生,看世界,看每一个人。他不抱怨俄国,在贫穷、愚昧、落后的后边,在积雪的掩埋下,他看到俄国辽阔的大地上非常强大的生命力。
托尔斯泰和俄国广大民众笃信的宗教属于东正教范畴。在各种宗教中,托尔斯泰认为基督教是最理想的宗教。托尔斯泰只承认基督教的真正教义,而不容忍同真理相悖的任何权威。不容忍对于宗教的迷信。在托尔斯泰看来,“必须打破一切对于人,对于经典的盲目的信仰,单把教义中与一切人类的良心及理性相合的留下来方好。”〔41〕他宣称“基督教不是神学,而是对于生活的崭新理解”,“天国就在你们心里。”〔42〕
梁漱溟先生在论述中国文化特征时指出:“中国以道德代宗教”,〔43〕孔学作为两千多年中国风教文化的主体,“相信人都有理性”,“完全依赖人类自己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什么事该作,什么事不该作,从理性上原自明白。一时若不明白,试想一想看,终可明白。因此孔子没有独断的标准给人,而要人自己反省。”〔44〕梁漱溟先生甚而认为孔子“是走顺着调理本能路的先觉”,孔子的路“不单是予人以新观念并实予人以新生命的哲学”,〔45〕孔子“任直觉”,仁就是“直觉”。〔46〕东方文化充实了托尔斯泰对基督教义的理解,为他的“内心宗教”提供了哲学基础。他发觉只有《圣经》不够,到东方寻找,发现他所要探求的和中国数千年来圣哲的遗训一拍即合,便产生了一个理想:用东方的“教义”造福欧洲。他在1884年3月29 日《日记》中写道:“如果没有孔子和老子,《福音书》是不完整的,而没有《福音书》于孔子则无损。”〔47〕英国托尔斯泰研究家亨利·吉福德在他的《托尔斯泰》(1981年)一书中写道:“托尔斯泰追求教义的确定性。他最关心的是找到无懈可击的行为规范。他宣扬的教义在诸如儒家学说一类的各种宏大道德理论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很难说与宣扬三位一体的基督教各种体系有什么关系。”〔48〕
托尔斯泰主义的各个要素都属于东方文化体系,他还径直地将俄罗斯包括在东方民族之中。〔49〕
东方理所当然应该接受托尔斯泰。
注释:
〔1〕《给我留下印象的作品》,《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8页。
〔2〕《战争与和平》(一)刘辽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160页。
〔3〕〔4〕〔5〕《战争与和平》第十卷,第十六章。
〔6〕《战争与和平》(四)刘辽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222页。
〔7〕《战争与和平》(四)刘辽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211-212页。
〔8〕同上,第130页。
〔9〕《战争与和平》(三)刘辽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10页。莫斯科维亚原是西欧人对莫斯科大公国的称呼,这里泛指俄国(原注)。
〔10〕参见《战争与和平》,董秋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26页。
〔11〕《战争与和平》,董秋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23页。
〔12〕《托尔斯泰全集》第66卷,第326页。
〔13〕《安娜·卡列尼娜》,周杨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61-362页。
〔14〕见〔苏〕贝希科夫《托尔斯泰评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年版,第99页。
〔15〕〔16〕〔17〕《安娜·卡列尼娜》,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 社,1956年版,第493、494、499页。
〔18〕《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页。
〔19〕《战争与和平》(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
〔20〕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12页。
〔21〕《中国的贤哲》,《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1页。
〔22〕《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131页。
〔23〕《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页。
〔24〕《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147页。
〔25〕同上,第147页。
〔26〕同上,第173页。
〔27〕同上,第174页。
〔28〕《安娜·卡列尼娜》,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139页。
〔29〕《艺术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7页。
〔30〕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
〔31〕《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1页。
〔32〕同〔30〕,第12页。
〔33〕《战争与和平》(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第53页。
〔34〕转引自〔英〕吉福德《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第40页。
〔35〕〔36〕《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62、475页。
〔37〕见《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页。
〔38〕《战争与和平》(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
〔39〕《战争与和平》(四),人民文学出版社,董秋斯译,1958年版,第1719页;刘辽逸译,1988年版,第130页。
〔40〕《战争与和平》(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第239页。
〔41〕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与东方》、《东方杂志》1928年,第25卷第19号60页。
〔42〕《天国就在你们心里》,《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
〔43〕《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页。
〔44〕《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三),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页。
〔45〕《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一),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2-523页。
〔46〕同上,第452-453页。
〔47〕参见《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127页。
〔48〕《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82 -83页。
〔49〕见1906年2月6日《日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标签:托尔斯泰论文; 战争与和平论文; 安娜·卡列尼娜论文; 文化论文; 东方文化论文; 俄罗斯文学论文; 日记论文; 拿破仑·波拿巴论文; 宗教论文; 国学论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论文; 农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