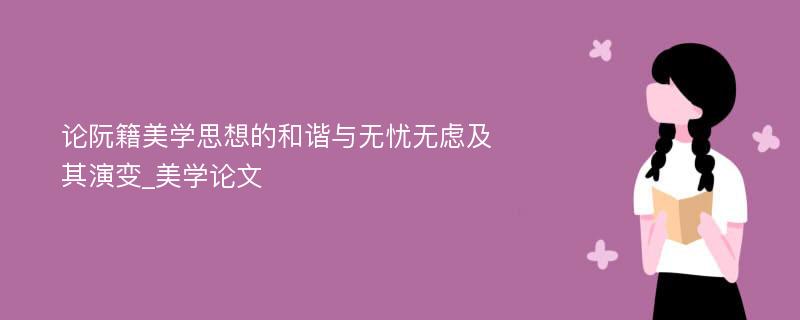
和与逍遥——论阮籍的美学思想及其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逍遥论文,思想论文,阮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从魏晋易代的历史背景和玄学思潮的演进中,全面考察阮籍的美学思想。认为:“和”与“逍遥”是阮籍美学思想的内核,阮籍引老入儒,以自然之道作为乐之和谐的终极依据,将乐的审美价值归结于实现个体心灵的和谐,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阮籍以庄学逍遥游放的自由精神铸就其具魏晋风度的人格理想与人格范型,扬弃沦为末流的儒家名教,由道德他律走向道德自律。从“和”到“逍遥”,反映了阮籍美学思想的嬗变。
关键词 阮籍;美学思想;和;逍遥;嬗变
阮籍美学思想的嬗变和玄学思潮的演进及魏晋易代之际的政治斗争,声息相通。正始以前,魏明帝“尊儒贵学”,老庄受到排抑。正始年间,玄学清谈、名士著述都以易老为主。在这种玄风煽扬,易老大盛的背景下,“妙达玄理”的阮籍撰《通老论》、《通易论》、《老子赞》、《孔子诔》和《乐论》诸篇与之呼应,是完全可能的。这一阶段,阮籍美学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和”。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诛曹爽 、何晏等,“天下名士减半”,曹氏同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日渐激烈,文人名士的个人生命常有不虞。于是曾经胸怀“济世志”的阮籍便逍遥浮世,“不与世事”而以“酣饮为常”〔1〕,思想上归于庄学。与这种人生态度相须发明的著述有《达庄论》、《大人先生传》、《答伏义书》等。这一阶段,阮籍美学思想的基本精神是逍遥。
从“和”到“逍遥”,反映了阮籍美学思想的嬗变。这一变化有其内在的联系和必然的逻辑走向,倘就其阶段性的主导理论的特质而言,以正始末年为限,大体上将阮籍美学思想的嬗变断为前后二期,或恐不远于事实。
一
阮籍前期的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乐论》之中。《乐论》的基本精神是“和”。“和”是阮籍前期美学思想的核心和政治伦理观的概括,也是阮籍“济世”的人生理想在审美观念上的反映。阮籍虽在理论上接受了儒家乐论的某些思想,将礼乐并举,重视乐的伦理教化功能,但《乐论》不是《乐论》的儒家礼乐观的重复,阮籍也不是“俗儒乐论”的拥戴者。〔2〕
阮籍论乐正值玄风大畅,《乐论》以自然之道释乐之本体,以老学思想释儒家正声雅乐,体现出鲜明的玄学精神,从而与《乐记》判然殊分。
《乐记》认为乐的本质属性是和谐,这种和谐由“法象天地”而来,表现了天地的和谐,所谓“乐者,天地之和”。阮籍则认为“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二者之于乐的和谐的看法立见岐异。《乐记》以天地作为乐的和谐的依据,尚未脱前人宇宙构成论的拘囿;《乐论》则从玄学本体论的层面追究乐的义理。乐与天地皆为形而下之“有”,所以乐不是“法象天地”,而是要“顺天地之体”,形而上的“天地之体”才是乐的本体。“天地之体”自非天地本身,它的实质是什么呢?《乐论》指出“自然之道”是“乐之所始”。始是发端的意思,玄学本体论认为,现象之万有发端于超验的本体,这一思想渗入阮籍美学,他认为乐始于“自然之道”,乐“顺天地之体”,所以天地的本体就是“自然之道”。
阮籍深契老子“道法自然”的旨趣,在《通老论》里援道入儒,将老子之“道”、《春秋》之“元”、《易》之“太极”视为同一层级概念的不同指称,体现了儒道兼综的玄学色彩。
其次,道无意志无目的,“法自然而为化”,其本质特征就是自然,因而阮籍称之为“自然之道”。社会生活中的人伦秩序也要取法自然。前期的阮籍肯定君臣上下的等级名分,“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3〕,但异于正统儒学的是,他以自然之道作为人伦规范的理论根基,调节社会等级的强制性,力求人伦秩序与自然秩序相协调。这种合乎自然的人伦规范可以使“上下和洽”,“万物得所”,“不为而成”,这种理想的至治状态既因循秩序,又充满活力,是秩序与活力的和谐统一,因而在阮籍看来或许就是社会美的极致。
再次,自然之道在其不可端倪的运作中有着终极和谐,它决定了乐的和谐,是乐的最高理则。乐虽然随时代发生变化,但这只是“改其名目,变造歌咏,至于乐声,平和自若”,乐的本体之和永不更易。乐是经验事实,自然之道则是超验的本体之“无”,“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4〕,阮籍“乐顺天地之体”的精义在于,乐的和谐感性地显现了自然之道的和谐,它将自然之道形式化、审美化了。这一美学思想包孕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它昭示着魏晋士人走出汉儒经学的樊篱,以全新的眼光审视宇宙与人生、艺术与自然。个性的自觉,主体意识的弘扬,使他们发现了自我致广大,尽精微,斑斓五彩的精神境域,从而超越形而下的现象世界,在玄远的本体中安顿自己的灵魂,体悟生命的真意。
阮籍还以老学思想重新认识正声雅乐,这一理论转型是阮籍美学异于儒家乐论的又一表征。阮籍虽然肯定正声雅乐之于社会人生的教化意义,但当《乐论》提出“正乐声希”,“雅乐不烦”,“五声无味”时,他则认为正声雅乐与自然之道有着精神同构的关系,这就不免“阴令道家夺儒家之席”。老学的道至大无外,兼纳万类却超越现象界的任何属性,倘从味觉而言,道是“无味”之“至味”;就听觉而论,道是“希声”之“大音”。阮籍在《清思赋》里把这一哲学思想落实到审美的层面,他认为“形之可见,非色之美;音之可闻,非声之善”,能够直接感知的经验世界的形色音声不是至美至善,只有“微妙无形,寂寞无听”的自然之道才是绝对的美。正声雅乐以无为本,契合道体,不粘滞于有限的音调,唯其如此,才能“总发众情”。这种平和的乐声感发平和的心境,丰富的乐感体验疏泻化解了郁结于心的“纵欲奢侈之意”,以及不同地域环境所引起的“风俗之偏”,审美的精神愉悦压倒了单纯的感官享受,滤却了“荣名”、“声色”等生理心理上的物欲私利,使人“恬淡无欲”,从而表现为“泰志适情”、“心气和洽”的美感形态。它是个体精神的“自适”,这种“自适”的怡然心态顺乎自然,是人生体验的最高境界。这显然是道家标举的人生境界,阮籍认为正声雅乐是实现这种境界的凭借。当主体以“冰心玉质”的虚静心胸,超越有限的形色音声而沉入无限的精神冥想,体悟到“微妙无形”的自然之道,观照到“窈窕而淑清”的美之极境时,这同时也是道德的极境。所谓“道德平淡”,“寂寞者德之主”,在“寂寞无听”的心灵谛视中,个体泯灭了善恶是非,情感与意志和谐运作,感性与理性充分展开,向着“万物齐一”,与道同体的境界飞升。
在这种美学思想的支配下,阮籍反对音乐表现与鉴赏中“以悲为美”、“以悲为乐”的审美趣味。“悲”与“乐”是调质相对的一组情感形式,音乐作为表情艺术,可以表现人类情感的各种调质,应该说,“以悲为美”的美感体验渗透了更深刻的理性精神,更能烛照人生社会的艰难困苦,和悲剧性密切相关。阮籍“精于音律”,自不会有昧于此。〔5〕阮籍的这一理论倾向,在其切近的层面上是对汉魏以来“以悲为快”的音乐审美趣味的反拨,它的现实针对性在于魏明帝、曹爽等耽于音声,忽略音乐的教化功能。〔6〕在理论意义上,阮籍主张音乐的审美价值是“人安其生,情意无哀”,“精神平和”,他的自然无为的思想,使他注重音乐唤起的“心澄气清”的宁静谐和的精神状态,而“以悲为乐”则背离这一本趣,让人“怀永日之娱,抱长夜之叹”,从而丧失了个体生命的真性情。
二
正始末年以后,曹魏集团与司马氏的政治斗争愈趋激烈,政坛风云变幻难测。这种历史环境决定了阮籍的“济世志”已无现实的可行性、先前所追求的和谐的人伦秩序归于幻灭,他陷入惶惑苦闷之中,感到了人生支点的失落。其《咏怀》之九云“良辰在何许?”辰,指个人的时运,在阮籍就是伸展抱负的机遇;“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世路险薄,良运不逢,他不得不调整处世原则和人生态度,“观时而行”(《通易论》)。处身人的自觉时代的魏晋之际,他深谙个人之于现实的无能为力,又自觉到生命价值高于一切,因此在“乱而不已”的现实里“思患而豫防之”,他辞曹爽参军,“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这正是阮籍汲汲于个体生命的存在,全生远祸,“观时而行”的写照。
阮籍究竟选择何种人生态度呢?《咏怀》其46以鸴鸠、海鸟象喻两种人生价值的取向:或如海鸟击水三千,扶摇九万;或如鸴鸠游于园圃,集于蓬艾。阮籍郁愤满怀,不得已放弃斡旋天地的高情远意,“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咏怀》其八)。在《答伏义书》里,他对伏义所规谏的干世务入的人生观弃之蔑如,将俗儒士子比作“瞽夫”、“琐虫”。既然“良运未协”,便只能退回自身,“邈世高超”,拓展自我的心灵空间,“从容与道化同,逍遥与日月并流”,追求精神的无限自由,用另一种方式肯定自我,在思想上接受庄学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归于庄学的逍遥。
就庄子而言,逍遥是全生远祸、傲世拔俗和委运乘化、安时处顺的统一,相形之下,阮籍则于前者心契神合,领会尤多。《大人先生传》中的大人先生“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他不与世俗争逐富贵,也不愿终身系累于“细物琐事”而销磨了生命的意义,更不取隐士那种“抗志显高”,“伏于岩穴”,如同“禽生而兽死”的生存方式。大人先生“不避物而处”,与物逶迤,“应变顺和”;“不以物为累”,也就是超然世表,不以世事撄心,驻足现实,却又寄情高远,形见而审藏,这恰是阮籍现实人生态度的绝好写照。阮籍之于曹马交争的政治倾向是一历史之谜,或以为阮氏两世皆为魏臣,自然心系魏室而“疾司马氏之僭越”;或以为阮籍“嗜酒荒放”,实则“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7〕,孰是孰非,阮籍著述中表露的心态应该最为雄辩。大人先生视王朝更迭为历史的循环,所谓“夏丧于商,周播之刘”,如此看来,曹丕代汉,司马氏觊觎魏室,世事转毂,就正是“至人未一顾而世代相酬,厥居未定,他人已有。”《咏怀》第20首委婉表达了阮籍对禅让的厌恶:“揖让长别离,飘摇难与期”;对时局动荡的茫然:“扬朱泣岐路,墨子悲染丝”。在血腥的政治角逐中,阮籍忧心忡忡,慨叹“何用自保持”。他不愿作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如何晏、夏侯玄等,某种意义上,嵇康也属一例),便超然于政治漩涡之外,“不系累于一时”,不把自己系于曹氏、司马氏的任何一方。正是这种心态决定他“口不论人过”,“未尝评论时事”〔8〕,酣醉辞婚,复又与司马文王周旋,草“劝进笺”,他的行事看似扑朔迷离,实则是“不避物而处”,“不以物为累”,在 艰险的环境里依违避就相机而作,从而远祸全生,而其精神却高蹈世表。他所关怀的是个人的存在,精神的自由。自东汉“党锢之祸”以后,士人心理上逐渐疏离了曾经汲汲关怀的王室,转而关注自我,阮籍的超尘拔俗正是这种心态的延续与发展。到了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9〕,阮籍傲世拔俗的愤激遂被陶渊明的平淡冲和取而代之。
阮籍张扬庄学,这典型地体现在其理想人格的建构上。魏晋之际,人物品题由先前注重伦理情操,转而重视才情气质,风度仪容,个体的人格理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而建构新的理想人格的问题则成为魏晋美学关于人的美的核心问题。刘劭《人物志》论人物材性,独拔“中庸至德”之人,以“平淡无味”,“其质无名”的“中和之质”作为理想人格。王弼则从本体论出发,认为“君德配天”,理想人格当以无为本,与道同体。对这一问题的探究,到了阮籍以及嵇康时才算全面展开。阮籍以外显的放达任诞返照内隐的精神自由,以自己的感性存在展示了新型的理想人格。
阮籍的人格理想首先表现在对情感价值的肯定。阮籍重情代表了新的感性要求在魏晋士人内心的觉醒,也是对儒家名教的反动。阮籍重情的理论依据是庄学的自然观。从《达庄论》的论述来看,“自然者无外”,自然这一概念具有绝对性、统一性和无分别性。“天地生于自然”,天地万象无不出于自然,无不是自然自由化育的结果,所以自然的精神实质就是自由。“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人秉自然的性分,得“自然之至真”,人应当是生来而自由的。人的道德生活也应当“循自然”,最高的道德境界体现了自由精神,具有绝对性和无分别性,所谓‘至德之要,无外而已”,它具体表现为“善恶莫之分,是非无所争”,因为“是非之辞著,则醇厚之情烁”,阮籍认为是非之分、善恶之别是相对的,它本身意味着至德的沦丧。至德之境的实现非但不以牺牲个体感性生命的丰富性为代价,相反,它使“万物返其所而得其情”,是人的本真性情的复归,所以至德之境就是实现了的人的伦理自由。名教作为伦理规范,调节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为感性与理性寻找恰当的结合部,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有其积极意义。历史发展到魏晋,人的自觉使个体向社会提出新的感性要求,个体、群体关系必须调整,而名教却滞后于这一社会现实,暴露出不合理性和虚伪性。名教之父子、君臣两伦远自东汉中叶即已动摇,孔融从纯生物意义上看待父子关系,阮籍缵承余绪,放谈“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在同禽兽的比较中看待“杀母”一事,认为“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10〕,这种惊骇之论的视角与传统的父权中心论相左。君臣关系方面,阮籍已不把个人视作王权的附庸。汉晋间的两次“禅让”,曹魏、司马氏二者不臣之心如出一辙,而曹魏以礼治天下,司马氏以孝治天下,名教徒具形式而已。阮籍《大人先生传》将君臣之设当作天下祸乱的渊薮,主张“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否定君臣名分,下开鲍敬宫“无君”论的先声。阮籍站在思想解放的前沿,敏锐地洞察到名教传统伦理体系的衰颓,其僵死的伦理形式一方面压抑人的正常情感需要,一方面异化为王权政治的工具和俗儒士子厕身庙堂的凭借。阮籍便由先前的笃信礼法转而否定名教,变俗归真,崇尚自然。他外显行为的放达任诞超越了旧有的伦理规范,在新旧价值观、伦理观交替之际所形成的道德真空之中,阮籍的放浪形骸是一种必然的历史现象。他的“礼岂为我设”的论调似乎给人以道德虚无主义的印象,但究其本意,却不是要破坏群体纲纪。他居丧饮酒,“不拘礼俗”,但“性至孝”,“举声一号,吐血数升”,“殆至灭性”。〔11〕何曾指责他“纵情背礼败俗”〔12〕,所谓“纵情”,无非是阮籍个性豪迈,纯任自然,任率真情,以“外坦荡而内淳至”〔13〕的心胸烛照“孝不任诚,慈不任亲”的伪善,他的行为切入伦理的实质而非其形式。所谓“背礼败俗”则是阮籍不甘随俗浮沉,他毁弃了为世俗所固守的僵死的伦理形式,让那些“外易其貌,内隐其情”,“出媚君上,入欺父母”的礼法之士(如何曾等人)感到作假的尴尬。他哭才色俱佳,“未嫁而卒”的“邻家处子”;还常常醉卧于“当垆沽酒”的“邻家美妇”之侧,虽然其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14〕这些表明,他既不掩饰对女性美的欣赏之情,又具有自律的道德意识,也就是以真率之情冲击没落的礼法,在情与理之间建构新的和谐,由名教的道德他律走向道德自律,现实主体的伦理自由。所以,阮籍的放诞是积之有素的内在精神的延伸,和后来元康名士“捐本循末”的放达有本质的不同。阮籍的放诞是他的理想人格极富魅力的一部分。他以磊落的心胸,天放的情怀把现实人生艺术化、审美化,他的行为映现了魏晋士人的审美追求和审美理想,铸就了魏晋风度的人格范型,其予后世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儒家强调以情从礼,以理节情,表现在美学思想上,便有“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传统。魏晋士人则突破礼教的限制,把个人情感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王弼在与何晏的论争中,力主“圣人有情”,王戎宣称“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阮籍则从理论和行为两方面肯定个体情感价值,追求“性命之真”,渗入到美学,便是以庄学自由精神为依托,畅情达性,突破“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为“文的自觉”提供新的人生体验。阮籍还以其《咏怀》诗美的创造,艺术地实践了他的审美追求,直至逗引出晋人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重要美学命题。
阮籍的人格精神是逍遥,这一心态与庄子极为相似。庄子的逍遥游是建立在发愤抒情的基础上的,成玄英《庄子疏》称庄子“叹苍生之业薄,伤道德之陵夷,乃慷慨发愤”,藉“心游”返求精神自由,遁入无所待的超越世界。阮籍“济世”理想的幻灭使他不得不放弃儒家的人生观。现实的颠倒混乱使他的个体生存时常受到威胁,俗儒的矫情伪饰给他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与其低首匍匐于下界,不如发愤神游于天下,于是阮籍把庄子的逍遥融入自己的人格理想,大人先生则是这种自由精神的象征。大人先生“与造物同体”,“不知姓字”,“莫知其生平年数”。造物即自然之道,与造物同体就是以自然之道为体,“不知姓字”是指大人先生“无名”。无名无形是道的特征。阮籍以自然之道为人格本体,正是倾心于主体精神的无限性和丰富性。大人先生“变化聚散,不常其形”,“精微妙而神丰”,这些玄妙的摹状昭示着人格精神的多采多姿,变幻莫测,折射出个性自觉的魏晋士人对自我才情神貌的愉悦陶醉。在他们看来,玄远超著的精神实践高于客观实践,内在精神的无限丰富性决定了丰富多样的现实性。大人先生的人生旨趣是“弃世务之众为,何细事之足赖”,他的价值取向是“不与尧舜齐德,不与汤武并功”,他有着独特的时空尺度,“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乃至泯灭了时空界限,“无后无先,莫究其极”。大人先生“吸浮雾”,“兴朝云,飏春风”,俨然是庄子笔底的藐姑射山之神人; 他“被发飞鬓,衣方离之衣,绕绂阳之带”,“养性延寿”,又兼有魏晋神仙家的风采,所不同的是,道教神仙旨在彼岸世界延长世俗的人间富贵,而大人先生则摈弃一切外在于生命的赘疣,追求人生的永恒意义。所以,阮籍吸庄生“至人”、“真人”、“神人”的精髓,酌道教神仙的意蕴,融自己的“胸怀间本趣”,塑造了大人先生这一形象,寄寓了超尘拔俗的人格理想。阮籍以大量篇幅极意渲染了大人先生的逍遥游,不难看出,这种逍遥的庄学境界高悬于现实之上,抚慰着阮籍苦闷悲怆的灵魂,在现实里,阮籍“终岁履薄冰”,举步维艰,而精神的逍遥游放把他解救出来,他那郁积于心的愤懑、欲求,种种莫名的冲动和情绪都得到渲泄。生活中的阮籍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为人至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15〕,但他通过大人先生抨击礼法,怀疑现存的人间物序,揭露俗儒的虚伪,君臣的罪恶,这种批判现实的精神正是阮籍理想人格乃至魏晋风度所蕴含的历史意义。
总的来看,阮籍的逍遥游放是慑于现实异已力量的威压而产生的,他既执着于人生,又痛感到个体渺小,个体生命无法在现实中展开,这才“逃避到主体本身的内心自由中去”。〔16〕它拓展了审美心理空间,展现了多采多姿的审美心态,为庄学注入了更为自觉的美学意义。由于这种人格理想仍停留于庄学的精神冥想里,不具有实践品格,而“济世”的思想依旧蛰伏于阮籍内心深处,所以作于晚岁的《东平赋》还恋念“政教”“美俗”。他向晋王举荐卢播,称赞卢播“耿道悦礼,仗义依仁,研精坟典”,这纯然是儒家的价值标准。所以,济世与逍遥构成强烈的心理张力,使阮籍徘徊容与,无所适从,陷入苦闷惶惑。作为名士、哲人和骚客的阮籍,大概因此才有穷途之恸,魏晋士人风神萧朗之下隐匿的命运悲剧也在这里。
注释:
〔1〕〔10〕〔11〕〔13〕〔15〕《晋书·阮籍传》。
〔2〕陈伯君先生认为,《乐论》“初未越出《礼记·乐论》之范围,虽间有所发挥,而其体统则归于一致”(《阮籍集校注》),似忽略《乐论》引老入儒的玄学精神。王德埙《中国音乐美学史举要》一文将《乐论》看作“俗儒乐论”的“旧调重弹”,实乃悖于《乐论》之本来面目。至于臆断嵇康《声无哀乐论》是阮藉与嵇康“论战的记录”,嵇、阮分别为文中之“东野主人”和“秦客”等等,毫无据实,更属不稽。
〔3〕〔9〕《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
〔1〕《王弼集校释》之《老子注》(楼宇烈校释)
〔5〕史称阮籍“善弹琴”,《咏怀》41云:“素琴凄我心”,其一云:“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以抚琴自写心胸,抒发悲情,足见其并非与“以悲为快”之审美趣味无涉。又,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上册称阮籍尝作琴曲《酒狂》,表现其遭受政治打击的苦痛以及“强烈的反抗之情”。
〔6〕魏明帝当天下三分,生民凋敝之际,“大治殿舍,西取长安大钟”,高堂隆引周景王铸大钟招致“周德以衰”之事,力谏明帝(《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阮籍《乐论》也引此例立论作说。《咏怀》三十一首借战国之魏以喻曹氏,陈沆《诗比兴笺》以为暗讽明帝“歌舞荒淫”。又,《三国志·魏书·曹爽传》称:曹爽惑溺,“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纵酒作乐。”
〔7〕叶梦得:《避署录话》。
〔8〕《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李康《家诫》。
〔12〕《晋书·何曾传》。
〔14〕《世说新语·任诞篇》。
〔1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