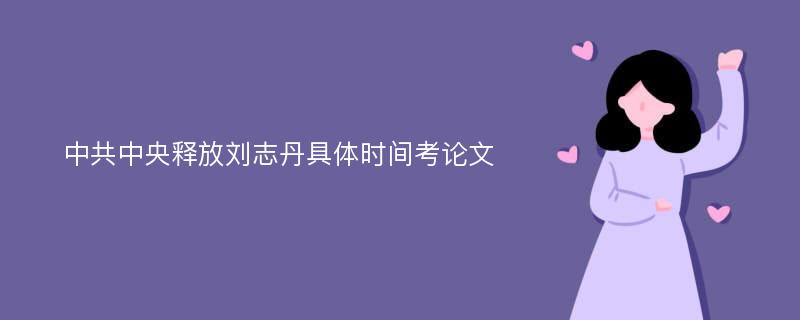
中共中央释放刘志丹具体时间考
魏德平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 中共中央制止“陕北肃反”释放刘志丹的具体时间长期存在不同说法。一种观点指出,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时立即释放了刘志丹。另一种观点认为,1935年12月13日毛泽东抵达瓦窑堡后才释放了刘志丹。上述两种说法都缺乏坚实历史依据难以成立。其他一些说法也需进一步考证。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即指派王首道等赶赴瓦窑堡接管陕甘晋省委保卫机关制止“陕北肃反”继续蔓延,抵达瓦窑堡后成立以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小组审查肃反问题。在张闻天领导下,经过五人小组工作,推翻了原中共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戴季英等以逼供信方式加在刘志丹等身上的各项“罪状”,并大致于1935年11月18日至20日之间释放了刘志丹等被关押在瓦窑堡的肃反受难幸存者。
【关键词】 陕北肃反;毛泽东;张闻天;刘志丹
中共中央抵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积极制止“陕北肃反”继续蔓延,并迅速释放了刘志丹等肃反受难幸存者。这对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转战,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部团结,在很短时间内摆脱被动局面,将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文献、档案资料较为缺乏,以及随后中共党内复杂政治斗争造成的肃反主要当事人、知情者命运沉浮等原因,当时一些历史事件仍存在需要澄清的遗留问题。中共中央释放刘志丹的具体日期就存在多种不同说法。这些说法和观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还存在互相抵牾的内容。有鉴于此,笔者利用当时发布的文件、部分档案资料以及新发现的史料,结合相关回忆录、著作、文章等对此问题作以辨析和考证。
一、中共中央释放刘志丹具体时间的主要观点
关于中共中央释放刘志丹的具体时间,当事人回忆、相关研究著作和文章存在不同说法。一种观点明确指出,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时立即释放了刘志丹。另一种观点认为,1935年12月13日毛泽东抵达瓦窑堡听取汇报后下令释放了刘志丹。还有其他一些中共中央释放刘志丹的不同观点,但是要么缺乏较为明确的时间,要么明显有违历史事实,尚需进一步考证。
当事人、知情人回忆和研究著作、文章比较集中认为中共中央释放刘志丹的具体时间是1935年11月7日。“陕北肃反”受难幸存者、原西北军委情报侦查科科长高朗亭回忆:“张闻天、李维汉、董必武、博古、王首道等同志于十月三十日到达瓦窑堡,撤销了中共陕甘晋省委保卫局,接收了所辖一切。经过党中央在瓦窑堡组成的五人小组(董必武负责、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洪涛组成)审查,于十一月七日下午,首批释放了受诬害被捕的刘志丹、习仲勋、杨森、杨祺、张秀山、刘景范、任浪花、孔令甫、高锦纯、赵启民、胡彦英、黄罗斌、郭宝珊、高朗亭、朱奎、王据德(应为王聚德——引者注)、王佳娃(刘志丹的警卫员)同志和高岗共十八人。”[1]98一些著作也认为中共中央释放刘志丹的具体时间为11月7日。《高岗传》记载:“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下午,中央党务委员会即下令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因西北错误‘肃反’而被关押的100多人。”[2]419《刘志丹年谱》也明确记载1935年11月7日,“经中共中央代表的审查,刘志丹等大批被诬陷而逮捕的同志获释”[3]117。上述观点,虽然在中共中央释放“陕北肃反”人数方面有很大差距,需进一步考证,但都强调释放刘志丹等人的时间为11月7日。
毛泽东1935年12月13日抵达瓦窑堡后下令释放刘志丹也是比较流行的说法。中共中央委派负责处理“陕北肃反”、时任中华苏维埃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王首道回忆:“直罗镇战役结束以后,毛主席来到了瓦窑堡,我们即将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汇报,毛主席、党中央肯定了我们的看法,并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4]170参与处理“陕北肃反”、时任中华苏维埃国家保卫局干部刘向三回忆:“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主席来到了瓦窑堡。当时中央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博古、王首道和我组成负责审理此案的五人专案组。五人专案组将审理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案件、重点是刘志丹的冤案向中央和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党中央肯定了专案组的看法,批准了专案组的意见,并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5]105-106“陕北肃反”受难幸存者、原陕甘边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回忆:“后来,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一到瓦窑堡,立即释放了刘志丹同志和其他被捕的人,恢复了我们的工作。”[6]568“陕北肃反”受难幸存者、原中共西北工委组织部长张秀山回忆:“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等从前线回到瓦窑堡。他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听取五人小组关于审查肃反案件的汇报。毛泽东再次严肃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立刻释放。’这样,我们这些遭受迫害的同志,才从‘左’倾的屠刀下被救了出来。”[7]90“陕北肃反”知情人、原红26军干部王世泰回忆:“经过王首道等一番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推翻了那些“左”倾机会主义推行者强加在志丹等人头上的罪名,如实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听了汇报,严肃地指出这次肃反完全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的狂热病,所有被冤枉的同志均应释放,恢复领导工作。于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关怀下,刘志丹、习仲勋等党、政、军的领导干部被救出狱。”“志丹出狱时,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亲自派人去接到驻地,作了两个多小时的亲切谈话。”[8]214有些著作也认为是毛泽东在瓦窑堡下令释放了毛泽东。《贾拓夫传》载:“毛泽东到了瓦窑堡后,党中央肯定了平反的意见,立即释放了所有被错捕的同志。”[9]41如果这种说法成立,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12月13日抵达瓦窑堡[10]495,那么刘志丹等获释则在12月13日或其后。
还有一些“陕北肃反”知情人、受难幸存者对中共中央释放刘志丹也有时间相对模糊的回忆。时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回忆:“1935年10月20日,也就是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的第二天,毛泽东听取当地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和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的汇报,了解到陕北错误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形势。许多共产党的干部被错误处理,刘志丹等陕北党政军高级干部被错误逮捕,关押在瓦窑堡,随时可能被杀害。”“毛泽东听完汇报,当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决定成立由董必武、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洪涛等五人组成的中央党务委员会,审查西北错误的肃反事件。11月初,王首道等到达瓦窑堡,代表中共中央释放了被关押的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苏区和红军领导一百余人。”[11]17-18“陕北肃反”知情人刘英回忆:“到瓦窑堡后,闻天领导纠错,组织了以董老(必武)为首,有王首道、罗迈、张云逸、郭洪涛参加的五人小组来调查处理。闻天抓得很紧,错误很快得到纠正。11月下旬就为刘志丹、习仲勋等彻底平反,被关起来的红二十六军干部也都放了出来,恢复了他们的工作。”[12]93“陕北肃反”受难幸存者、原陕甘边根据地干部张策回忆:“毛主席一到吴起镇,就发现了肃反是一严重错案,立即发出停止肃反等待处理的命令。这才给我们每人发了铺盖,虐待行为也告停止。随后,中央又派王首道、贾拓夫同志到瓦窑堡释放了我们,并逐步重新分配了工作。”[13]61-62“陕北肃反”受难幸存者、原陕甘边根据地军委主席刘景范回忆:“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第一批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杨森、杨琪、朱子休、郭宝山、黄罗斌、张策和我十几个人。”[14]89“陕北肃反”知情人、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回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开了一次平反会,洛甫、博古、刘少奇等出席,五人委员会也都参加了。记得这次会是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会上,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分配工作。”[15]372
王首道等代表中共中央提前赶到瓦窑堡重新对“陕北肃反”进行了调查和研究。王首道和刘向三等先期抵达瓦窑堡的中共中央先遣人员,对肃反问题作了大量工作。王首道回忆:“当时,直接审理刘志丹同志案件的是戴季英,他当时任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陕甘边区(应为陕甘晋省委——引者注)保卫局的局长。我们一到瓦窑堡,他就拿出很多案卷来,作为刘志丹等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的‘证据’。我们按照毛主席‘要慎重处理的方针’,并不轻信这些案卷,立即进行调查访问。”[25]167刘向三回忆:抵达瓦窑堡后,“王首道同志带领我和朱明同志等4人向朱理智(应为朱理治——引者注)、郭洪涛、戴季英等负责主管肃反工作的人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接管肃反工作的指示。互相交换意见后,我们提出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将肃反委员会的工作自今日起全面交接;第二,除工作组的人员外,其他任何人不准再插手这里的工作,如提审犯人、翻阅案卷材料、巡视牢房等;第三,请原主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和业务人员给予大力支持,主动提供情况和说明问题。负责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局长向我们介绍重要犯人的‘罪状’后,并拿出一堆案卷材料交给我们,作为‘右派’、‘反革命’的‘罪证’。从介绍中我们了解到,作为肃反工作负责人的戴季英同志没有找过刘志丹同志等所谓重要犯人谈过话。面对这么多的‘罪证’材料,我们需要一件一件地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最后才能证实它的真伪。”[5]96-97王首道、刘向三等所作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为中共中央抵达瓦窑堡进一步处理“陕北肃反”打下了基础。
二、中共中央释放刘志丹几种主要说法考辩
中共中央1935年11月7日释放刘志丹出狱值得商榷。关于中共中央1935年11月7日释放刘志丹的说法和中共中央抵达瓦窑堡的具体时间密切相关。中共中央抵达瓦窑堡具体时间到目前仍存在不同说法。现在一些回忆录、研究著作对中共中央抵达瓦窑堡的具体时间比较集中的认为是11月7日。随同中共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回忆:“洛甫、博古、刘少奇、邓发、董必武和我率中央机关从下寺湾直接去瓦窑堡(陕甘晋省委驻地,苏区的中心),于十一月七日到达瓦窑堡。”[15]371时任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回忆:自己“11月7日,跟随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16]18。另一位随同中共中央抵达瓦窑堡的历史见证人刘英则明确说:“我们中央机关于11月10日到达瓦窑堡。”[12]90迎接中共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时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回忆:“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率中央机关于13日到瓦窑堡。”[17]78《朱理治传》载: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18]136。中共官方权威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也认为:“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19]394当然,关于中共中央抵达瓦窑堡的具体时间,研究著作也有重要分歧。《张闻天传》、《张闻天年谱》则坚持认为中共中央抵达瓦窑堡的具体时间为11月10日。[20]264另一位随同中共中央抵达瓦窑堡的历史见证人刘英也明确说:“我们中央机关于11月10日到达瓦窑堡。”[12]90迎接中共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时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回忆:“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率中央机关于13日到瓦窑堡。”[17]78
根据文献资料和现有资料考证,现有关于中共中央1935年11月7日释放刘志丹出狱和毛泽东1935年12月13日抵达瓦窑堡下令释放刘志丹的说法都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局限。其他关于刘志丹获释时间的说法,要么存在明显违背史实之处,难以自圆其说;要么在关键时间点上语焉不详,需要进一步考证。
据当事人回忆,中共中央抵达瓦窑堡后刘志丹才获释。据刘向三回忆:“艰苦的工作刚开始不久,保卫局看守人员跑来向专案组秘密报告说:‘狱中很冷,刘志丹把棉大衣送给同狱的青年人了,饭吃的不好,也吃不饱。’接到报信后,我立即写了给刘志丹同志发棉大衣和提高伙食标准的报告,呈送王首道和张闻天同志。”[5]97刘英回忆:“到瓦窑堡后,闻天领导纠错,组织了以董老(必武)为首,有王首道、罗迈、张云逸、郭洪涛参加的五人小组来调查处理。”[12]93“五人小组”成员郭洪涛回忆:“中央到瓦窑堡后,决定由中央、地方、军队的代表组成五人委员会,由董必武同志负责处理错误肃反。”“五人委员会在听取了王首道同志的审查汇报后报告中央批准,决定对刘志丹等受冤同志平反,并立即释放。”[17]78-79上述当事人回忆都明确指出刘志丹获释在中共中央张闻天一行抵达瓦窑堡之后,因此,有必要对中共中央抵达瓦窑堡具体时间作以考察。
具有很好的防水性能,这是保障路面不会受到路表或外界环境中的水的影响而造成路面整体性、强度和刚度下降的主要因素。
据《张闻天年谱》记载:11月5日,中共中央机关在张闻天率领下向瓦窑堡进发。[21]273《刘少奇年谱》明确指出:11月5日,刘少奇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22]142《周恩来年谱》也记载:11月5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23]295刘少奇和张闻天是一起出发赶往瓦窑堡的,因此可以确定张闻天一行出发时间为11月5日。当时延安地区还被国民党东北军占领,张闻天一行不可能径直取道延安,需要绕道前往瓦窑堡。实际上,张闻天一行是从下寺湾出发,经过高桥、安塞、蟠龙,最后抵达瓦窑堡。[20]264这条路是从延安西南部出发,绕过延安,从延安西边行军,最后进抵瓦窑堡。张闻天一行所经历行程大致超过了400华里。张闻天一行包括身负重伤的王稼祥、女干部刘英、老干部董必武等,行进速度必然受限,11月7日不可能抵达瓦窑堡。郭洪涛所讲11月13日说法也需要商榷,如此说成立则相当于中共中央机关当时每天前行10余公里。现在亦没有材料说明张闻天一行路上遇到过意外事故,行军受阻,故此说也值得商榷。而11月10日之说似较为准确。[24]因此,11月7日,中共中央尚未抵达瓦窑堡也不可能直接负责处理“陕北肃反”问题,与当事人回忆张闻天亲自过问等历史情节不符。
毛泽东1935年12月13日抵达瓦窑堡释放刘志丹出狱也有违历史史实。根据现在刊布的当时刘志丹发出的电报记载:1935年11月25日,刘志丹已在后方发电报给前方的毛泽东、彭德怀:“关于动员新战士问题,动员武装[部]已正式成立,他们决定三边及陕北完尾,在瓦窑堡集中运送前方,陕甘省各地动员之新战士均在王家坪集中,直送前方。除动员加上负责领导动员外,希你们亦直接派员帮助及指导,如何?”[3]4012月9日,刘志丹再次致电博古、彭德怀和毛泽东:“一、北清涧南五里、宜川之各黄河渡口,均已责成请延水、延长县速派专人建立侦探,但并未用一切关系派探去山西侦察匪情。传达消息,由递发站担任。”“二、一切情报均经过延水、延长报告后方军委及我、周,佳县工作除黄河游击队担任外,并在各渡口用武装守备队,群众经常用土枪[将由]山西来[犯]敌击回。据探报,近日山西来[敌]并无变化,侦察及警戒工作已有[相]当建立,延安残敌亦困守不动,我开无线电,在这里无重要工作,架电任务[应向]何处行动,请示、复知。”[3]44电文与回忆材料相比更具有可靠性和客观性。由这两则电文时间和内容可知,毛泽东12月13日抵达瓦窑堡之前的11月25日前,刘志丹不但已经恢复了人身自由,而且还担任了一定的军事领导职务。
综上所述,中共中央1935年11月7日释放刘志丹和毛泽东12月13日抵达瓦窑堡释放刘志丹的说法都缺乏史实依据。根据上文分析,刘志丹获释时间大致应该在1935年11月10日至25日之间,故与之相违背的说法可以排除。其他各种中共中央释放刘志丹出狱的说法因时间比较模糊,还需要进一步推敲和考证。因此,刘志丹获释的准确时间还需深入考证。这是深化和拓展西北党史的需要,尤其是解决“陕北肃反”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
三、中共中央释放刘志丹具体时间考
中共中央在下寺湾期间,为控制“陕北肃反”继续恶化确保刘志丹等被捕人员人身安全,立即指派王首道等赶赴瓦窑堡接管陕甘晋省委保卫机关制止肃反继续发作。中共中央抵达瓦窑堡后积极处理“陕北肃反”遗留问题,成立以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小组审查肃反问题。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①的领导下,经过五人小组积极工作,推翻了原中共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戴季英等以逼供信方式加在刘志丹等身上的各项“罪状”,并于1935年11月18日至20日之间将刘志丹等肃反受难幸存者释放。
随后,中共中央经过积极审查及时对“陕北肃反”做出了处理,相继释放了刘志丹等肃反受难幸存者。中共中央成立五人“党务委员会”专门机构审查“陕北肃反”。刘英回忆:“到瓦窑堡后,闻天领导纠错,组织了以董老(必武)为首,有王首道、罗迈、张云逸、郭洪涛参加的五人小组来调查处理。闻天抓得很紧,错误很快得到纠正。”[12]93“经过5人专案组审理后,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高岗、杨森、杨琪、张秀山、刘景范、任浪花、孔令甫、高锦纯、赵启明、胡彦英、黄罗斌、郭宝珊、朱奎、王君德(应为王聚德——引者注)等30多人首批被平反释放,恢复了工作。”[5]100-101中共中央释放“陕北肃反”受难者时,也曾召集过专门会议进行了讨论。参与审查和释放刘志丹的郭洪涛在后来召开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的西北高干会和西北历史座谈会上多次谈释放刘志丹前中共中央对此问题的讨论情况。郭洪涛在西北高干会上讲:“中央到了瓦窑堡以后,宣布王首道同志为保卫局长。王首道同志找我谈(因我是本地方的干部)问我究竟反革命问题是怎么一回事?我就告诉他说,刘志丹、高岗、杨森这些老干部,不是反革命,顶多是封建结合。提出蔡子伟、张胖子(指当时担任西北军委副主席的张庆孚——引者注)等反革命(这情形王首道同志可以证明)。以后保卫局开会,参加会的有博古、洛甫、李德、王首道同志,也找了我去开会。我参加这个会,我又表明说:他们不是反革命,这由到会同志可以证明。这个会开完以后,就要放人”。“在放人的时候,王首道同志还征求我的意见:那些人要放?那些人不敢放?当时在名单上我给打过圈。”[26]1104“以后在保卫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参加会的人有李德、洛甫、博古、王首道和我;关于放人的事,他们问我,那个该放,那个不该放,那个先放,那个后放,这是我圈了圈的。”[27]1245郭洪涛在西北历史座谈会上讲:“中央来后在保卫局召集了会议决定放人。先放那批后放那批我就都圈了名字,放了之后我还认为这批干部是有错误的。”[28]1597可见,中共中央抵达瓦窑堡后并未立即释放刘志丹等人,而是经过了一系列较为严格的审查和甄别工作后才对被关押的刘志丹等“陕北肃反”受难幸存者分批进行释放。
上述关于中共中央释放刘志丹的说法和记载基本都源自“陕北肃反”受难幸存者、知情人和专门著作,有一定的可信性。但是如果细究其结论,则有的貌似言之凿凿,但似是而非;有的违背史实,缺乏根据;有的前后矛盾,违背常识;还有的时间模糊,需要进一步考证。总之,现在中共中央释放刘志丹具体时间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有待进一步考证史实,澄清问题,统一认识。这既是维护学术研究严肃性的应有之义,又是进一步澄清关于西北党史、尤其是“陕北肃反”问题当下争论的迫切需要。
王首道等人还访问了刘志丹。王首道回忆:“同干部本人谈话,是了解干部的重要途径之一。志丹同志被捕时,戴季英没有让他说一句话,就将他关押起来了。我们亲自访问了志丹同志,他是‘首犯’,带着手铐,还钉了脚镣。他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二十五军来到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25]170刘向三的回忆更为具体:“我们专案组在王首道同志带领下专门去访问了刘志丹同志。他是‘首犯’,看管很严,带着手铐,钉上脚镣。我看得出他表面上平静,可是心情沉重。他说:‘这么多干部被关押,我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我政治水平不高,远离中央不能及时请示汇报,给苏区工作造成损失,我是有责任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25军来到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又来陕北,我非常高兴,对我鼓舞很大,今后工作信心更足了。’”[5]104中共中央接管原中共西北政治保卫局后,被关押的刘志丹等人的生活待遇和管理环境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和提高。刘向三回忆:“艰苦的工作刚开始不久,保卫局看守人员跑来向专案组秘密报告说:‘狱中很冷,刘志丹把棉大衣送给同狱的青年人了,饭吃的不好,也吃不饱。’接到报信后,我立即写了给刘志丹同志发棉大衣和提高伙食标准的报告,呈送王首道和张闻天同志。这份报告很快被批准,我们马上派人送去棉大衣一件,同时向伙房交代按提高的标准给刘志丹同志供给伙食。从此,狱中同志能够吃饱,也注意了保暖。”[5]97刘向三回忆明确指出当时向张闻天汇报过刘志丹被关押的情况,可见张闻天一行抵达瓦窑堡之后刘志丹仍未被立即释放,还在继续接受审查。
在前方的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也非常关注在后方的张闻天、博古等对刘志丹等的处理情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于11月18日从前线发电报给在瓦窑堡的张闻天、博古等人,请他们详细考虑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指出:“错捕有一批,定系事实。”提出纠正肃反中的错误。[29]487笔者认为,虽然这是现在唯一公开的一份在前线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和在瓦窑堡后方领导人之间关于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的电报,但是可以推测,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与张闻天、博古等人在此前应该有过磋商,并达成了一定共识:极有可能是后方张闻天、博古等关于释放刘志丹等与前方交换意见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前方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该问题的集体答复。毛泽东在领导直罗镇战役期间仍然念念不忘刘志丹等人的安危,强调:“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越割越长;人可不一样,割下脑袋就再也长不出来了!”[30]19如果在此之前刘志丹等已经获释,则毛泽东等似无必要对此事仍如此关注和重视。因此,在没有新的权威史料公布前,刘志丹等获释应该在11月18日及以后。
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抵达瓦窑堡后随即正式接管了原西北代表团保卫局,任命王首道为保卫局局长,并指示成立由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王首道和郭洪涛组成五人“党务委员会”②负责调查审理“陕北肃反”问题。五人“党务委员会”成员王首道对中共中央审查“陕北肃反”过程有详细介绍:“在掌握了事实之后,我们就向戴季英提出: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那么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又怎能建立和巩固下来呢?对于这些问题他都答不上来。但他仍顽固的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我们仔细地翻阅了那些案卷,发觉其中所列举的志丹同志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捎山(应为“梢山”——引者注)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过程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同志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我们还陆续提问了几个所谓‘犯人’,当他们知道我们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时候,就敢讲真话了。经过再三审查,证明所谓‘口供’中,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意破坏外,其余都是逼、供、信所造成的结果。”[25]169-170
在返程之前,我们专门来到格罗布尼克汽车世界。这条赛道的设施自然是比不上那些国际级赛道,但赛道旁小吃店的意式浓缩咖啡的味道极佳。如果你也希望沿着我们的路线享受这样一段跨国之旅,那么这里非常值得一试。
在认知的初期,自动化加工过程的形成与重复有关。基础理论的练习做得越多对认知效率的提高越有益处,在后续提高性的学习中所需的认知资源就越少,有利于形成完成认知任务的自动化加工过程。通过大量练习来提高完成认知任务的效率,达到仅需要较少的注意就可以完成同样的认知过程,减少了注意能量的使用,最终用自动化加工过程来完成基础任务,把认知资源利用到复杂问题的解决上去。这些重复练习在学习的早期会占用大量时间来提高基础的技能,容易产生枯燥的感觉,通过设立目标,互助协作,增加竞争性,奖励等方式鼓励学生渡过打基础的阶段。
4.注水施肥。栽培前5~7天,注水0.3m左右(确保能刚好漫过水草),进水口用40目筛绢进行过滤。并根据虾田肥瘦情况,在需要种植水草的位置施用少量腐熟粪肥或复合肥等。
实验室安全是高等院校校教学和科研工作顺利完成的先决条件,也是国家财产和实验室活动人员安全的重要保证[1]。而医学院校因为其专业特点,实验室的安全管理显得更为重要,由于其管理不善所引发的都是损失惨重的大事件[2-4]。比如,在2009年,浙江某所医学高校误将实验室的一氧化碳气体接到了学习室,从而导致一位在读博士的无辜中毒死亡等事故。类似的众多事件告诉我们: 现在的医学院校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比较落后,操作过程中存在较大的漏洞,必须通过完善其安全管理评价体系,在宏观上减少管理上的疏漏,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和减少相关安全事故的发生。
根据相关资料也可以推测出刘志丹获释的时间下限。据有关研究记载:11月21日至24日,在直罗镇战役期间,刘志丹在延长地区指挥地方武装围攻延安等地,牵制和打击国民党东北军第129师等部,配合当时的直罗镇战役。这就是说刘志丹在11月21日前已经获释。这个时间根据当时张闻天给毛泽东的一则电报也可以得到佐证。张闻天1935年11月10日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后,即同当时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等不断有电报和书信往来。11月26日,张闻天致电毛泽东:“同高桂滋谈判已[有]初步成绩。协定草约已由双方代表同意后送上级批准。”[31]11这段电文的主要内容,是张闻天向毛泽东等通报北线统战情况。其时,中共中央已委派中央白区工作部北路工作处处长赵通儒负责这一工作,对分别驻扎在绥德的国民党84师高桂滋部和榆林的86师井岳秀部进行统战。赵通儒后来多次回忆自己第一次出发与84师谈判前在瓦窑堡见到刘志丹的情形:“走李银家沟刘给20响手枪,回来还刘。”[32]“刘任西北军委副主任(全称应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引者注),我一见,他一句不说,给我一支二十响手枪;我也一句不讲,就去搞北线统战工作。”[33]“中央要我去搞北线统战工作,志丹任西北军委副主任,以廿响手枪及骑马给我出发工作助行。”“中央恢复志丹职权后,我出外工作,志丹给马给20响手枪。”[34]赵通儒和国民党84师代表第二次谈判时间是11月25日,地点是在清涧县老君殿苗家沟(今属子洲县),签订了《八十四师、陕北临时省苏维埃政府代表第一种协约》,即张闻天11月26日致毛泽东电报中所讲“协定草约”。[35]
通过赵通儒的回忆,可以获知如下信息:第一,赵通儒见到刘志丹时,刘志丹已经获释,并且担任了相当高的军事领导职务;其二,赵通儒回忆中提到的“李银家沟”在今子洲县周家硷镇张家渠村,距瓦窑堡约一天多的路程。李银家沟在大理河川,苗家沟在淮宁河川,二者相距也有一天的路程。从第二次谈判协议签订日推算,赵通儒在瓦窑堡见到刘志丹的时间应该在11月20日左右。根据赵通儒的回忆和其他相关资料可以推测,在此之前刘志丹肯定已经获释,并且恢复了职务。综合上述史料记载,笔者认为刘志丹获释的时间基本可以确定为1935年11月18日至20日之间。这一时间段,在当事人的回忆中也能得到佐证。马文瑞回忆:“我抓得较迟。抓我的时候,中央红军已经到保安县吴起镇了。”“我被关押20多天后,就放出来了。”[36]89-90刘英回忆:“11月下旬就为刘志丹、习仲勋等彻底平反,被关起来的红二十六军干部也都放了出来,恢复了他们的工作。”[12]93
综上所述,此次个税的改革是为了能够更加合理的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尽可能缩短贫富差距,从而提高我国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但是,由于地区经济水平的差异,收入与支出都会存在差异,如果不划分档级,可能会因为个税基数的差异而引发矛盾。所以,个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还需我们进一步做出研究与探讨。
综上所述,超声能清楚显示乳腺叶状肿瘤的形态级血流动力学特征,可以作为乳腺叶状肿瘤良恶性病变的鉴别诊断参考资料,乳腺叶状肿瘤良恶性的超声表现在肿瘤边界是否清晰、内部回声是否均匀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肿瘤边界否清晰及内部回声是否均匀是乳腺叶状肿瘤良恶性鉴别的重要依据。
通过对中共中央审查和释放刘志丹等出狱一系列史实的具体考证,可以明显看出,当时中共中央虽然刚刚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内外形势,但是在处理“陕北肃反”问题过程中展现出了既坚持政治严肃性,又积极作为的特点。一方面,不轻信逼供信材料,严格审查肃反存在疑点的问题,最终推翻当时强加在刘志丹等肃反受难幸存者身上的不实罪状;另一方面,在认识到“陕北肃反”问题严重蔓延的千钧一发之际,果断接收保卫机关,制止肃反继续发作,一旦审查清楚后立即释放刘志丹等肃反受难幸存者。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的重视和积极介入,及时果断处理,不但制止了肃反的进一步发作和恶化,保全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一大批西北根据地党政军干部的性命,并为当时中共中央在西北地区迅速立足,获得补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关于张闻天在当时中共内部的职务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认为张当时是中共党内“总负责”,另一种说法即为“总书记”。本文在参考一些资料,尤其是张培森发表在《炎黄春秋》2006年第7期《为张闻天总书记正名》一文的观点,认为“总书记”说符合实际,故从此说。
②关于五人“党务委员会”具体组成成员,当事人也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这五人分别是董必武、李维汉、博古、王首道、刘向三。王首道回忆:“当时中央是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博古、刘向三我们五人负责审理此案的。”(王首道:《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70页);刘向三回忆:“当时中央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博古、王首道和我组成负责审理此案的五人专案组。”(刘向三:《往事的回忆》,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106页)。另一种观点认为五人分别是:董必武、王首道、罗迈、张云逸、郭洪涛。刘英回忆:“到瓦窑堡后,闻天领导纠错,组织了以董老(必武)为首,有王首道、罗迈、张云逸、郭洪涛参加的五人小组来调查处理。”(刘英:《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李维汉回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西北中央局指定组成在博古指导下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其成员为董必武(主任)、王首道(红军保卫局长)、张云逸(代表军委)、李维汉(中央组织部部长)、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72页);郭洪涛回忆:“中央到瓦窑堡后,决定由中央、地方、军队的代表组成五人委员会,由董必武同志负责处理错误肃反。五人委员会成员:董必武同志是中央纪律委员会负责人,李维汉同志是中央组织部长,王首道同志是国家保卫局局长,张云逸同志代表军委,我代表地方。”(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似更准确可信,理由有两点:一是以当事人当时在中共党政军中地位和代表性而言,刘向三不大可能位列“五人委员会”;二是相较于王首道、刘向三而言,当时李维汉、刘英和郭洪涛均更有条件接触中共中央领导层的决策,因此他们的说法也更为可信。
参考文献:
[1]高朗亭.西北红军的组建和党中央拯救西北革命根据地史事纪实[G]//陕西文史资料:第11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2]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M].西安: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3]刘志丹.刘志丹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王首道.王首道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5]刘向三.往事的回忆[M].北京: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
[6]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1979年10月16日)[M]//习仲勋文集:上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7]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修订版[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8]王世泰.王世泰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9]周维仁.贾拓夫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10]逄先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1]叶子龙.叶子龙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12]刘英.刘英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3]张策.我的历史回顾[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14]刘景范,口述,宋金寿,整理.关于陕北错误肃反问题访刘景范同志(1981年3月28日、5月8日)[C]//刘米拉,刘都都,编.刘景范纪念文集: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1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16]聂洪钧.半世略纪(1955年5月)[M]//聂洪钧回忆与文稿.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17]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18]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1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20]程中原.张闻天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21]张培森.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24]魏德平.中共中央长征抵达瓦窑堡具体时间考[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2).
[25]王首道.王首道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26]郭洪涛同志在高干会上的发言(1942年11月6日)[G]//周国祥辑著.“肃反”纪事:卷2.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23辑,2018.
[27]郭洪涛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2日)[G]//周国祥,辑著.“肃反”纪事:卷2.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23辑,2018.
[28]郭洪涛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摘要(1945年7月5日)[G]//周国祥,辑著.“肃反”纪事:卷3.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23辑,2018.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30]叶子龙.叶子龙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31]张闻天.为建议优待被俘东北军军官致毛泽东电(1935年11月26日)[M]//张闻天文集(1935—1938):2.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32]赵通儒遗稿.回延笔记——杂忆1949年3月14日[M].魏建国提供.
[33]赵通儒遗稿:致彭德怀信1949年12月26日[M].魏建国提供.
[34]赵通儒遗稿:致彭德怀信1950年3月18日[M].魏建国提供.
[35]赵通儒遗稿,魏建国提供.
[36]马文瑞.马文瑞回忆录[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An Examination on the Exact Time for Liu Zhidan’s Release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EI Deping
(School of Marx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disagreements over the exact time for Liu Zhidan’s release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mid the insiders,survivors of the movement as well as the relevant academic works.Some hold that Liu was set free on November 7th of 1935 upon the arriva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at Wayaobu.Others maintain that Mao set Liu free when he was briefed on the situation about the movement upon his arrival at Wayaobu on December 13th of 1935.However,both statements prove untenable as far as the existing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literature are concerned.There are other views which,however,either lack a definite time or obviously disagree with historical facts.Therefore,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During its station in Xia Siwan,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first sent Wang Shoudao and other leaders to Wayaobu to take ov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olitical Security Bureau for Shaanxi-Gansu-Shanxi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and stop the exacerbating situation there,to ensure the safety of Liu Zhidan and the others arrested.The Central Committee set to address the issues upon their arrival at Wayaobu.A five-member leading group headed by Dong Biwu was set up to examine and redress the cases.Under the leadership of Zhang Wentian,the group worked actively,overruled the“counts of crime”imposed on Liu and others by Dai Jiying and other former leaders of the Political Security Bureau through forced means,and set Liu Zhidan and the other survivors free roughly between November 18th to 20th of 1935.
Key Words: movement to eliminate counterrevolutionaries in Northern Shaanxi;Mao Zedong;Zhang Wentian;Liu Zhidan
【中图分类号】 D235;K26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码 号】 1674-0351(2019)04-0110-09
【收稿日期】 2019-05-04
【作者简介】 魏德平,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刘 滢】
标签:陕北肃反论文; 毛泽东论文; 张闻天论文; 刘志丹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