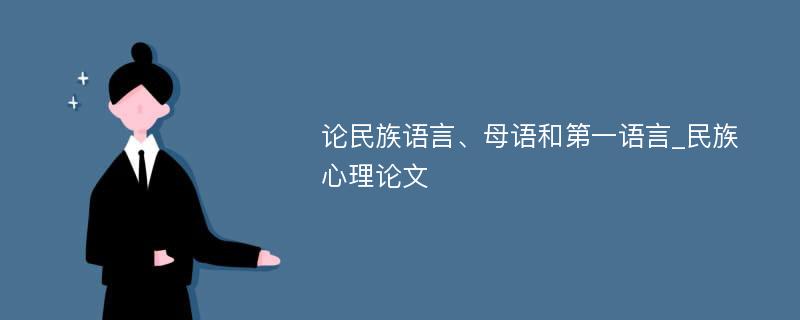
论民族语、母语和第一语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母语论文,民族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语言是人们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按人们集团的性质来区分语言,有氏族语、部族语、民族语等形式。广义的民族语是泛指所有这些形态的语言。在我国,识别民族也是指广义的民族,不管其历史发展处于何种形态。一般说来,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语言。但是,有的民族已转用了别的民族语言,如满族、回族转用了汉语。有的民族有一种以上语言,如瑶族有勉语、布努语和珞珈语(还有一部分瑶族使用汉语)。在我国,不采取民族和民族语完全一致的原则。民族学原则和语言学原则用于识别民族或识别语言时,两者有关联,但又不是一回事。一个民族可以分出一种以上语言,是坚持科学态度、实事求是、严格按照语言学原则作出的具有我国鲜明特点的科学主张,对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语言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1958年和“文革”期间出现的极“左”思想,不顾我国的实际情况,错误地认为一个民族不应该有一种以上的语言,否则不利于民族团结,甚至会分裂民族。这种错误的思想影响了正常的学术研究,如对景颇族的语言分景颇语和载瓦语的问题,长期以来不敢正视,认为在景颇族中推行了景颇文,似乎没有必要在载瓦语地区推行载瓦文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一些民族有一种以上语言(使用一种以上语言,也可以使用一种以上民族文字)的客观事实才得到了承认。一个民族有一种以上语言是历史形成的,是客观存在,与长期形成的民族心理和民族凝聚力并不矛盾,识别出其有一种以上语言这一固有的特征不会有不利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语言调查和补查,都按语言学原则识别和确定新的语言,不拘泥于一个民族一种语言,如彝族中有普标语、哈尼族中有桑孔语、拉祜族中有老缅(毕苏/米苏)语;又如瑶族中除上述三种语言外,又识别出巴哼语、炯奈语。我国有56个民族,但语言有80种以上。从语言使用的角度看,有的民族有一种以上语言,有的民族兼用别的民族语言,还有的民族转用了别的民族语言,形成了民族语、母语、第一语言之间相互交错的局面。
民族语和母语在一般情况下是一致的。民族语是对民族这个人们集团而言,母语主要是对个体使用的语言而言。在民族内部,其成员一般都以本民族语为母语。使用一种以上语言的民族,其成员一般以本族支系的各自语言为母语。但是,一种新的情况是:由于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上的密切关系,文化上的互相交流,住地的变迁,双语现象的出现,特别是那些不生活在本民族地区的人,其中有的人从小习得和使用的语言不是本民族语而是别的民族语言,如有的少数民族儿童在城镇长大,最先学会使用的是汉语而不是本民族语,虽然其父母的语言是本民族语;又如广西都安瑶族家庭有的儿童最先学会使用壮语,本族的布努语稍晚才学会使用。以上情况,属于母语中断现象,第一语言也与本民族语分离。
母语体现人们世代的语言关系。母语是祖祖辈辈沿用下来,至少是父母一辈使用的语言,后代加以继承。通俗的说法,母语是母亲的语言,是父辈的语言。不过,对母语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解释:1.母语是一个人最初学会的语言;2.本民族语是母语;3.母语、第一语言、民族语三位一体。这三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有局限性和偏颇之处。一个人从小学会的语言是第一语言,一般都是从父母一辈习得的,继承了前辈的语言——母语。这是最常见的情况,所以人们往往把第一语言和母语等同起来。父母一辈的语言在一般情况下是本民族语言,所以人们也往往把母语与民族语等同起来。应该说,在一般情况下,母语与第一语言和本民族语言是相一致的,但母语与第一语言的分离、母语与本民族语的分离及第一语言与本民族语言的分离,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在现实的语言生活中,民族语、母语、第一语言这三者是有区别的。
二
民族语、母语和第一语言三者可以是统一的。这三者不一致的情况值得讨论。
先从“第一语言”说起。应该把第一语言作为语言学的一个术语确定下来。它指的是一个人生下来最先习得的语言。第一语言的实现有三种基本情况:1.儿时从父母习得本民族语。这种情况,第一语言与母语一致,也与本民族语一致。2.儿时从当地社团习得外族语言,或者从父母第二语言习得外族语言。这种情况,第一语言与母语分离,也与本民族语分离。3.双语地区的儿童,从小掌握两种语言。如果有一辈人就已如此,下一辈沿袭下来,我们趋向于承认这新一代儿童的母语为“双语”。以两种语言为母语似乎是可能的,但有待进一步观察。我国的双语现象,一般说来其中一种为本民族语,另一种为外族语,多数地区表现为民族语—汉语。
母语,一般说来是民族语与第一语言连结的纽带:母语通常体现民族语的传统,第一语言通常是这种传统的现实。母语是父母以至多代以前一直沿用下来的语言。儿时从父母习得其语言这一事实,一般指的是使用和继承了母语。不过,父母的语言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本民族语,而是转用了别的民族语言。因此,母语有本民族语和非本民族语两种情形,并非都是本民族语。但是,任何人都有母语,如同必定有父母一样。然而,可能出现母语的中断和转移:一个人儿时从当地社团习得非父辈的语言,或虽从父母习得却是其第二语言。这意味着语言传统的改变。如果下一代加以继承,就逐渐形成了新的母语传统。
母语的转换,往往是受当地强势语言的影响。强势语言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以至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示出它的力量,往往在人们的第一语言中占优先地位,并有可能逐渐取代处于弱势的语言,从而形成新母语的传承关系。母语的继承性和连续性,有时表现得比较特殊:母语习得一般都通过第一语言来实现,但有时却是通过第二语言来实现。例如,有的少数民族在汉族地区长大,首先习得汉语(第一语言),然后又学习本民族语(第二语言)。这时,母语为本民族语的性质不变,但却是通过第二语言实现的。又如海外华人,有的儿时习得英语,后来又学习汉语。第一语言非母语也非本民族语的情况屡见不鲜。
民族语在本民族成员中体现为第一语言,是由于其强大的交际职能使民族成员在儿时就必须习得。民族语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世代相传,因此民族语作为民族成员的母语有长时期的稳固性。同样,第一语言、母语和民族语有着持久的一致性。民族语言的转用,是母语改变的一个前提。在转用了别的民族语言有了两代人的传承关系后,非本民族语作为新的母语,才算真正确立起来。不过,笔者不认为外族语成为自己的母语后,它也就成为“本族语”。例如,满族人转用汉语并形成了世代的传承关系,汉语是他们的母语,但满语仍是他们的民族语(只不过不是活的语言,但有大量文献)。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第一语言与母语,第一语言与民族语,母语与民族语,它们之间关系密切,但又是互相区别的。
三
母语有本族语和非本族语两种形式。对母语的确认,要不要考虑人们的心理因素呢?有人提出母语概念的两个标准:一是语言标准,一是心理标准。所谓“语言标准”,即“从语言的角度看,笔者同意母语就是一个人从小习得的第一语言的说法。”(注:戴庆厦、何俊芳:《论母语》,《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下文讨论的一些观点也出自该文,不再一一注明。)这个标准未能反映出母语的继承性、连续性。笔者以为应该补充一层意思,即从小习得的语言必须是父母的语言。第一语言不等于母语。不言而喻,第二语言也可以是母语,如儿时先习得汉语,后来才学会父母使用的本民族语。笔者有条件地同意“如果一个人从小习得两种语言,那么这两种语言就是他的母语”。不过,必须确认双语制已经形成继承性系统,承自父辈,这样“双语”才取得母语的地位。所谓“心理标准”,是“从心理的角度出发,就是一个人从感情上确认哪种语言是自己的母语”。例证是:“有些人从小习得汉语,后来才慢慢学习了一些本民族语”,“出于本族语的感情,认为母语还是本族语”;“另外一种情况是把非本族语认作母语”。笔者以为,不应把上述两种情况简单地看作“心理”或“感情”上的问题,应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在笔者看来,儿时习得的虽是汉语(第一语言),但只要其父母的语言为本民族语,那么其母语仍为本民族语,只不过其不用第一语言来继承,而用第二语言来实现,即“后来才慢慢学习”的。在此条件下,“认为母语还是本民族语”是合乎理性的,简单地归结为心理上的原因是不妥的。至于“把非本族语认作母语”,这也要有分析。如果父母的语言为本族语,即使儿时习得外族语,也不应把外族语当作母语,本族语仍为母语,但属“母语中断”状态。如果非本族语沿用了几代人(至少两代),非本族语也可以转换为自己的母语,如满族人不再使用满语,转用汉语并形成传承关系,汉语就成了他们的母语。在此情况下,“把非本族语认作母语”也是合乎理性的,不是什么感情上的问题。总而言之,给母语提出所谓“心理标准”是没有科学意义的。也就是说,没有必要把母语作语言上的和心理上的区分。
有学者对几十位大学生进行“有关语言知识水平”的问卷调查:“您认为哪种语言是您的母语?”选项有:1.本民族语;2.本民族语和汉语;3.汉语。调查者有意通过问卷的反馈,观察不以本民族语为母语的原因,观察以本民族语和汉语或以汉语为母语的原因。可是,调查者对母语的概念缺乏科学界定,较为含混:或把儿时习得的语言(第一语言)视为母语,或把本民族语视为母语,或认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他们(引者按:指不懂满语只会汉语的满族)的母语应该是那种他们掌握得好和广泛使用(的)语言,那种他们用来进行思维、进行创造的语言——汉语”。应该看到,调查者有如何正确解释“母语”和“母语转移”的问题,被调查者也确实有个“语言知识水平”问题,这两者在认识上不可能一致,必定会有错位的地方。调查者试图用心理因素来解释,把那些不合乎自己设想的“母语”的选择,说成是出于心理上的原因,实际上是把双方认识上的一些问题与心理因素混为一谈了。人们看不出母语“心理标准”的科学意义。
如果我们不把母语与民族语和第一语言(儿时最先习得的语言)纠缠在一起,提出“你的母语是哪种语言”的问题,回答的选项有明确的含义:1.本民族语(±父母的语言);2.本民族语和汉语(±父母的语言为此类型的双语制);3.汉语(±父母转用了汉语)。那么,被调查者的回答就不会产生歧义,并排除了所谓心理因素。被调查者肯定了选项中的一项,如果与其儿时习得的语言(第一语言)不相符,那就是母语的中断,新母语要从下一代的继承才显现出来。
母语的转移,作为一种语言现象由来已久,十分古老。自古以来有过各种形式的语言接触,母语的转换早就发生过,只是没有像现在这样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但笔者对母语的“心理标准”或“主观依据”不敢苟同。母语的“功能说”也不可取。有人说“母语应该是那种他们掌握得好和广泛使用(的)语言,那种他们用来进行思维、进行创造的语言”。笔者认为,这不是母语的真正意义。对母语的界定,应以客观为标准,取“心理标准”或“主观依据”是不可靠的。人们对母语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认识,但都要统一到客观真理上来。
从语言使用的角度看,民族语、母语和第一语言的关系,其基本模式有:
1.〔+民族语〕〔+母语〕〔+第一语言〕:三位一体。这是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使用的一般情况。
2.〔+民族语〕〔+母语〕〔-第一语言〕:第一语言与民族语、母语分离,儿时习得非本族语言。
3.〔+民族语〕〔-母语〕〔+第一语言〕:有自己的民族语,但母语与民族语分离(父母转用其他语言),第一语言继承。
4.〔-民族语〕〔+母语〕〔+第一语言〕:本族已不使用自己的语言;所转用的语言作为母语已经稳固;第一语言同母语。
现实的语言观要求人们把民族语、母语和第一语言区别开来。笔者以为,确立“第一语言”的观念,对认识语言生活的规律性和分辨语言使用情况有重要意义,但过去被忽视了。过去往往把民族语和母语完全等同起来,忽视了语言的转用,也忽视了母语的中断和转移。正确把握各族人民语言生活的规律性,正确对待民族语、母语和第一语言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正确贯彻党的民族语文政策。例如,我国民族地区的语言教育,可分第一语言教育、第二语言教育和双语教育三种不同的类型,各有特点和优势,人们要善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而这些都与如何看待民族语、母语和第一语言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