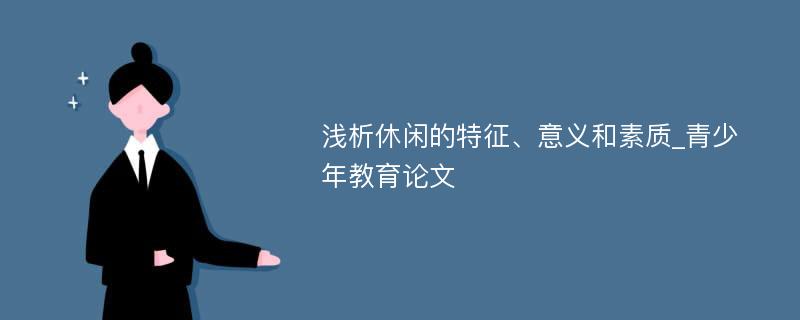
闲暇的特点、意义与质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闲暇论文,意义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闲暇”的界定
从一般的语义学上分析,闲暇是指人的空闲时间。《现代汉语词典》中,“闲暇”一词的释义即为“闲空”,而“闲空”的释义是“没有事的时候”。由此可见,闲暇标示了一段特殊的时间过程,即人们没有工作和事情要做、可以悠然消闲的时间过程。
但是,当我们对闲暇进行理论分析时,“闲暇”一词的语义学含义就远远不够用了。闲暇的确是人们没有“必须做的事情”的时间,但它并不是“不做事情”的时间。准确地说,闲暇是与社会分工规定的劳动和必须承担的家庭义务相对应的概念。因此,人们在参加或完成了社会规定的劳动和一定的家务劳动之外完全由个人自由支配的空闲时间,就是闲暇时间;而人们在闲暇时间中所从事的一切自由的活动,就是闲暇活动。
随着近几十年来人类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许多学者对闲暇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为闲暇下了自己的定义。其中,杜马泽德(J·Dumuzedier,1962)所下的定义是很著名的:
所谓闲暇,就是当个人从工作岗位、家庭、社会所赋予的义务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为了休息,为了散心,或者为了培养并无利害关系的知识和能力,自发地投身社会,发挥自由的创造力而完全随意进行的活动的总体。[1]
日本学者荫山庄司分析说,在这个定义中,闲暇是与“个人被工作岗位、家庭、社会所赋予的义务”相对而言的。我们可以把这种义务看作是劳动,闲暇的意义之一就是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杜马泽德的定义还涉及闲暇活动的功能,这与单纯把闲暇看作多余的闲工夫的观点不同,它赋予闲暇以“个人自觉地积极地花费的主体时间”的意义。我们在研究现代青年时可以看到,这个意义上的闲暇还没有在生活中占据足够的地位。这个问题应当作为教育问题加以考虑。[2]很显然,杜马泽德的定义和荫山庄司的分析,对于我们思考闲暇活动的特征、功能、意义等,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近年来,闲暇理论也已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有的研究者认为,“可以给闲暇下这样一个定义:所谓闲暇,就是指个人没有必须做的事情因而最感到自由和最能表现个性特点的时间。”[3]这个定义虽未涉及闲暇的具体功能,但对闲暇时间的基本涵义却作了高度概括的揭示。
因此,在闲暇理论的研究中,严格意义上的闲暇时间是指:按个人意愿自由支配的时间。
二、闲暇的特点
根据以上对闲暇含义的界定,我们可以发现闲暇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性。
自由性。闲暇是与人们所承担的社会规定劳动相对应的。社会规定劳动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它带有勿庸置辩的他律性、强制性,或者说是不自由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过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4]“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且把我们的打算化为乌有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5]这就是说,自发的社会分工所导致的人的社会活动的固定化,一方面反映了一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也使人类的社会规定劳动和工作成了“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力量,带有一定的“异化”性质。于是,闲暇时间就成为人类渴求自由、舒张身心的最重要的补偿通道。在闲暇时间里,人的自由意识得到了最自由的表现和满足。你愿意干些什么,你愿意想些什么,你愿意上哪儿去,你愿意与谁在一起,或者,你什么也不干,哪儿也不去,你就愿意一个人静静地呆上一会儿——一切都悉听尊便。很显然,自由性是闲暇的最基本最本质的特性。
由自由性,以导出了闲暇的另外两个特性:个人性、情感性。
个人性。分工从根本上说是劳动、工作社会化的结果。处于一定分工系统中的不同个人的劳动、工作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社会共同活动整体,因此,人的社会规定劳动必然是一种集体性的活动,一种社会性的行为。在这种集体性的劳动中,任何个体都必须遵循群体活动所形成和约定的纪律、程序和规则,而不可能拥有超出群体规范要求之外的纯私人性的愿望和要求;社会规定劳动要求于个体的是与群体规范的一致性、统一性,任何个人性的愿望及表现都只能被认为是非份的、犯规的。
与此相反,闲暇则为个体对社会规定劳动所要求的集体性、社会性规约的反叛和从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可能。作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自由支配的时间过程,闲暇具有鲜明的个体性和私人性的特点,也就是荫山庄司在分析杜马泽德的闲暇定义时所说的,闲暇具有“个人自觉地积极地花费的主体时间”的意义。在闲暇时间里,个人不但是自己闲暇活动的参与者,它的价值的承受者、消费者,而且是它的设计者和它的结果的评判者。因此,在闲暇时间里,人相对地脱离了集体和社会,成了不受约束的“自由人”,并因此而最充分自觉地体验到、认识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6]
当然,个人性不能理解为绝对没有伙伴的孤独的个性。事实上,闲暇伙伴的自由选择和组合,也构成了闲暇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所谓闲暇的个人性,是相对于社会劳动的集体性而言的。
情感性。人的社会规定劳动当然并非毫无情感性因素的介入和存在,有些分工甚至具有很强的职业情感色彩,但是,从总体上看,人的职业分工和规定劳动更主要地是蕴含和体现了一种客观的社会性的要求,它更多地涉及人的理性、义务和责任感,更多地具有一种他律性的、强迫性的色彩,而人的个性化的情感生活一般说来并不成为它所必须考虑和照顾的方面。于是,闲暇在填补和满足人的情感需求和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便突现了出来。在闲暇生活中,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和需要,脱下理性的厚靴,步入一片自由的情感的绿洲。在情感的世界里,精神是自由的、放松的,而被情感所唤醒的理性又可能具有一种新的生命活力和创造智慧。因此,闲暇生活对人的精神的健全发展,具有特殊的作用。
三、闲暇生活的意义与质量分析
1.闲暇生活的意义
从闲暇的特性中,我们不难看出闲暇在人的生存和发展中的特殊意义和价值。事实上,人们对此也早已有所论述。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就专门论及闲暇对人生发展的意义,认为闲暇是一个重要的,甚至高尚的概念,它的涵义并不是无所事事,纯粹玩乐,而是一种自由的、有意义的活动。在东方,中国古代著名的教育论著《学记》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提出了“藏、修、息、游”的教育思想,主张把敬德修业与休闲游乐结合起来,使受教育者在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到了近代,启蒙主义思想家洛克、斯宾塞等进一步发展了“闲暇教育论”。马克思对闲暇时间于人的发展意义的论述则更为深刻。他不仅重视劳动时间的节约,而且十分重视闲暇时间的价值。他指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在这里,马克思把自由时间的增加、人的充分发展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密切联系起来,揭示了闲暇时间对人和社会发展的意义。马克思还曾肯定“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一个“精彩的命题”,并断言“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很显然,闲暇作为一种财富,其价值正体现在它对个人的充分发展、进而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促进作用上。
从更深的意义上看,劳动与闲暇到底哪个是生活的核心,也是值得思考的。“劳动是神圣的,劳动就是生活”的观点曾长期统治着人类。这种观点认为“生活的中心是劳动”,而闲暇只是为了更好地劳动的一种手段。这一闲暇观如今已经受到了有力的挑战。在国外,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认为“劳动和闲暇并存”的观点和认为“生活的中心是闲暇”的观点正在增加。据日本总理府的调查,在70年代,持“工作闲暇并存型”观点的人占压倒多数,而分别把劳动和闲暇作为生活中心的两种观点却占少数。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年间,持“劳动为中心”观点的人减少了三分之二,而持“闲暇为中心”观点的人则处于渐增的趋势。尽管不同年龄的人的情况多少有些差异,但发展趋势基本一致。由此可以看出现代人们对闲暇的看法的特点。[7]其实,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把闲暇仅仅看作手段,即认为只有为了更好地工作、劳动才可以从事一下闲暇活动的人,他大概也不能说明工作、劳动又是为了什么。就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和传统的观念恰恰相反,人类无止境追求的目的正是为了增加闲暇时间和提高闲暇质量。[8]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描述,共产主义社会正是一个人们能够充分根据自己的意愿从事生产和工作的时代,一切活动都已成为那个“伟大的闲暇”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9]这也就是说,人的工作劳动与闲暇活动已经由相互分离趋于合一,劳动成了“乐生的要素”,成为闲暇活动的一个部分、一种形式。在这种情况下,闲暇就不仅是一种生活手段,而且成为生活的目的。
当然,在现代社会,闲暇仍然主要还只是人们生活中调剂精神、丰富生活内容的一种手段,特点是对青少年来说,他们处于人类发展中的准备期,系统的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文化传递本身的需要,而且也是他们开创未来生活的必然要求和前提。一般说来,青少年的以掌握知识为中心的学习任务主要是通过学校组织、监督和完成的,不过在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得到空前发展的现代社会中,青少年的闲暇生活内容和方式都随之大大地丰富起来,闲暇在青少年发展中的社会学习功能、发展个性功能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现代教育理论已经明确地把青少年学生的闲暇活动提到了与正规课堂教学同等重要的地位。现代课程理论认为:学生的文化学习,不但有正规课堂内有组织、有计划地传授知识、技能、行为规范的正规学习、正规课程,同时也存在着通过非正式方式和途径,借助生活环境中的各要素(习俗、风尚、文化氛围、游乐休闲、自发活动、人际交往)进行的潜在的、隐喻的、无意的潜隐学习、“潜隐课程”。潜隐课程填充着学生课堂以外的时间空间,对学生增加知识信息,学习社会生活技能,获得休闲愉悦,接受一定的思想和行为规范,促进个性特长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育人作用。[10]例如,在闲暇时间中,青少年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地阅读各种报刊书籍,收听广播、收看电视,或通过与社会实际和各种人们的广泛接触、了解,来多方位地、大量地获取各种信息和知识,培养自己的各种技能,发展自己的兴趣、个性,这些都可能是学校规定课程的学习中所难以获得和实现的。可以说,闲暇生活不仅为青少年学生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继续“学习”的过程,而且为他们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自由而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文化途径。
2.闲暇生活的质量分析
我们强调并肯定闲暇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同时我们也意识到,由于潜隐学习是人们在现代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整体经验环境中自发地、自由地进行的,因此,它不仅可以产生正向的诱导和影响,也可能产生负向的效应。所以,我们有必要对闲暇生活进行深入的质量分析,区分积极的闲暇和消极的闲暇,以便为分析、研究闲暇生活提供相应的价值尺度。
由于闲暇文化环境的复杂性,所以闲暇生活对人们的影响也是复杂的。例如,闲暇之于当代青少年就有两重性:它既可以是青少年的一笔财富,也可以是他们的一个负担;既可以成为他们自由活动、自我发展和完善的生命乐土,也可能成为虚掷光阴、消磨意志、放浪形骸的生命泥沼。因此,闲暇生活从其方式、后果、效益等方面看,可以区分为积极的闲暇和消极的闲暇。在这里,闲暇的效益不仅是就闲暇生活的个人主体而言的,同时也是就其对整个社会整体利益和发展的效果而言的。所谓积极的闲暇,其活动方式既是丰富多样的,又是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其效果对主体个人身心的全面发展和整个社会文化进步来说都是积极的、有益的。而消极的闲暇则与此相反,其活动形式和效果或低级庸俗,或无聊盲目,或愚昧落后,或惹事生非、危及社会。因此,闲暇生活尽管在具体形式和内容上千差万别,但就其功能和质量而言,可划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类。
首先,积极的闲暇有利于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开阔视野、健身益智、愉悦性情、发展个性。对青少年学生来说,作为学校生活的扩展和补充,积极的闲暇生活使他们有可能从社会整体经验环境中进行内容和形式都更丰富和自由的社会学习。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从这种学习中内化一定的价值体系,习得一定的生活技能,培养和完善自己的个性品质,并且反过来对课堂的专业学习产生有益的影响。报上曾载文介绍过一个19岁的女孩炜的例子。在中学时代,炜爱好文学和语文课。考大学时她选择了自己喜爱的理工科专业,同时又惦记着中学时代的语文课,盼望能有人和她谈文学。她将文学视为自己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她说:“一天到晚学数学、化学、制图,再也没有语文课。”“想想自己并不是不喜欢这个专业,也还算用功,可还是觉得空虚,真不知该怎么办?”她接受了咨询指导者的建议,在不影响学业的前提下,去建立起有益的闲暇生活,在闲暇的时间里满足自己对于文学的“饥渴”。后来,她在给指导者的一封信中这样叙述了自己的收获和感受:“以前我还真是不知道,闲暇生活对人有如此积极的意义。以前,当我感到空虚时,我真的很想去阅读那些文学作品,可心里又觉得自己‘不务正业’,不踏实。于是强迫自己整天扎在专业书中,试图从中去发掘生活的意义。可无济于事,仍感到空虚。心情上的压抑,令学习显得枯燥,而且效率低下。现在我听从你的建议,在课余时间,挤出一段时间,‘心安理得’地享受文学,我不仅阅读,有时还将心得写信与老同学交流,还参加了学校的书社,结识了一批文科学生。我还投过几次稿,尽管没被录用,可我不在乎,因为从中我愉悦了身心。做这许多事,不仅没耽误学习,反而提高了效率。我不再感到孤独,因为我不再是憋着股‘怨气’在学。”[11]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有益的闲暇生活之于主体的精神调剂、个性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其次,积极的闲暇对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是有益的。闲暇虽然具有个人性,但人却是具有社会性的人,闲暇文化说到底也总是特定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良好的闲暇生活状况对于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对于人类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都将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例如,许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正是在闲暇时间的自由探索和创造中,获得了宝贵的发展和发明,创作了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从而为人类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这里,闲暇生活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整个社会进步都具有积极的、肯定性的意义。
消极的闲暇则具有无聊、落后、愚昧甚至是腐朽堕落、危害社会的特点。例如,有的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于是闲得发腻,无事生非,所谓“吃饱了撑的”是也。尤其是青少年,在物质生活相对改善的今天,如果不能建立正常的、积极的闲暇生活,就更有可能干出危害社会的事情来。曾有论者谈到,就今天的青少年来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对他们中的多数人已文不对题,说是“吃饱了的孩子不当家”倒差不多。现在,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令人忧虑的社会问题。而据调查了解,青少年犯罪之始很多恰是因为“吃饱了撑的”。在农村城镇及附近的大道上,常见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成群结伙,你推我搡,嬉笑打闹,见有女郎经过,便打胡哨或怪声怪气地吼叫:“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有时候,三四人摇摇晃晃骑一辆自行车(夹在中间的一位故意穿上女性衣裳),嘴角叼着香烟,口吐污言秽语,从东头摇到西头,又从西头晃到东头。问这些自称“油皮得很”的哥儿们何故如此,回答是坦然的:“没事嘛!”再打听,他们身上几乎都有一把匕首,也差不多都有一些劣迹。《大地》月刊1992年第2期有报告文学载:湖南邵阳有一个流氓团体的首犯戴某,常砸保险柜,他自己解释说:“生活太没意思,就想寻点刺激。不玩点花样,心里就发痒。”有一次,他们一伙将一个14岁小孩的7根手指砍掉,原因不过是“酒醉饭饱,肚子里胀得难受”,拿这个两年前曾口角过一次的孩子“寻开心”。[12]可见,个人闲暇生活的无聊和愚昧,终将成为社会治安和文明的一个不稳定的破坏性因素。
看来,闲暇虽然属于个人性的生活领域,但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很显然,闲暇生活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如兴趣、爱好和人生观,也能反映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有人认为:“一种文化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自身的前途,检验这种能力的有效办法之一是看它如何处理闲暇问题”。[13]也有人认为:“改变了某个民族的闲暇品性就可以改变这个民族的整个个性和这个民族的效率。”[14]这些说法是有道理的。闲暇生活正是以它的广泛而突出的自由性、个人性、情感性特征,展现出闲暇个体的心灵状态和精神品位,也展示了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系统和文明水准。因此,提高闲暇生活质量和品位,无疑是当代生活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注释:
[1][2][7]转引自〔日〕荫山庄司:《现代青年心理学》,邵道生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6月版,第93—97,93—94页
[3][8]张国珍:《论闲暇》,《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2期
[4][5][9]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7、38页
[6][14]参见J·曼蒂等著:《闲暇教育理论与实践》,春秋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至18页
[10]参见董娅:《深化学生闲暇活动指导与管理刍议》,《教育管理研究》1992年第1期
[11]仲炜:《建立有益的闲暇生活》,《文汇报》1992年4月18日
[12]参见冯日乾:《“吃饱了撑的”》,1992年4月20日《文汇报》
[13]斯金纳:《超越自由与尊严》,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页
标签:青少年教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