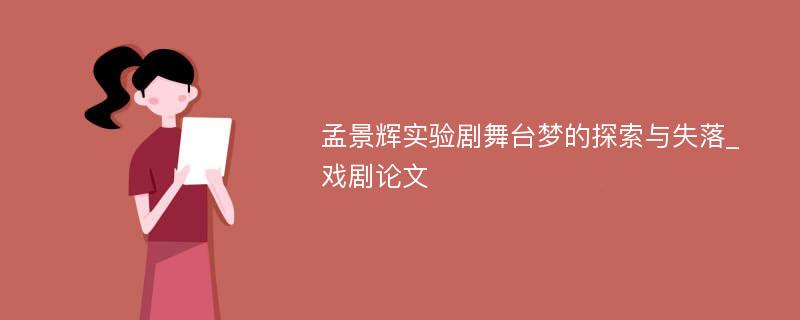
舞台梦寻者的探险与迷失——关于孟京辉的实验戏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剧论文,舞台论文,梦寻者论文,孟京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代年轻的艺术家,出于对话剧领域内观念陈腐僵化、传统保守的写实风格一统天下、观众大面积流失等状况的强烈不满,承80年代“探索戏剧”之余韵,以标新立异的先锋姿态和充沛的创造活力跃跃欲试。在与有志于革新的前辈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实验性戏剧已从开始的悄然兴起发展到今天的登堂入室,以致逐步改变了中国话剧的原有格局。
在实验戏剧为数有限而卓有成效的实践者中,孟京辉以其作品不拘一格的形式创造、鲜活奔涌的时代气息及与观众密切相投的亲和力,成为90年代实验戏剧中无可争议的代表人物,他的实验戏剧也因此成为话剧天地中的一个独特景观。
孟京辉顽强探索的脚印与中国实验戏剧近年来徘徊与前行的轨迹几乎是同步的。他的戏剧出现伊始,曾令人心动莫名,也曾令人惊诧咋舌;它领略过欢呼与喝彩,也经受过疑问与叱骂,但经历诸般艰辛和挫败、磨砺与考验,它终归别开洞天,渐入柳暗花明之境。这个过程本身就无可非议地证明:孟京辉的实验戏剧早已是种无法忽视的艺术现象。从孟京辉创作开始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等待戈多》算起,他已在国内外导演了十数部可回可点的实验剧目。在近10年的舞台实践中,孟京辉获得的成功与认同不是偶然的,他所遭遇的困境与迷失也不乏普遍意义。无论其成败得失,孟京辉的努力都为戏剧艺术未来的拓展与改革的深化提供了可资探讨与借鉴的有效资源。
(一)
舞台梦寻者的探险之途
1991年6月,《等待戈多》作为孟京辉导演硕士学位的结业作品在中央戏剧学院小礼堂上演,这部作品至今仍属孟京辉实验剧目中的力作,标志着孟京辉导 演艺术风格的成型乃至成熟。看过这场内部演出的为数不多的观众至今难忘当时那种突如其来的令人耳目 一新、亢奋不安的感觉。孟京辉似乎初出茅庐便出手不凡,其实这部别开生面的作品并非空穴来风,它是以孟京辉舞台梦寻生涯中的各种经历与尝试为铺垫的,其中包括他在首都师范大学期间戏剧天份的最初萌动,在“蛙实验剧团”与同仁们的艰辛创业,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后与志同道合者共同进行的一系列实践……《等待戈多》不是一个懵懂的开始,它已是相当积累的结晶。
《等待戈多》几乎显现了日后孟京辉实验戏剧的基本个性特征和所有审美旨趣:饱满炽热,激情充沛,机智诙谐,高潮迭起。贝克特的这部玄奥深谨的荒诞派戏剧经典,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在中国演起来,更容易有拖沓、冗长、乏味的危险,而孟京辉全力凝神于戏剧美感和舞台魅力的营造与挖掘,整台演出既刺激、热闹,又温馨、隽永,取得了不同凡响的突破。
小剧场实验戏剧《思凡》已成为中国小剧场戏剧诞生以来最为优秀、也最具原创价值的一部保留剧目,它脱胎于1992年12月“大雪”日首演于中央戏剧学院的行为艺术剧《思凡·双下山》,孟京辉参与原初策划并执导。媳凡》是孟京辉首部获正式公演的作品,它在’93中国小剧场戏剧展演暨国际研讨会上,得到了来自国内同行与国外友朋的衷心赞赏,并获“优秀导演奖”的政府鼓励。其后《思凡》远征东流、上海,无不载誉而归,迄今仍以雅俗共赏、妙趣横生的极佳演出效果,保持着其它小剧场戏剧难以堪比的久演不衰的纪录。
《思凡》的成功,为孟京辉赢得了最初的观众和声誉,也为他未来的实践探险提供了契机,拓展了道路。继此,孟京辉踌躇满志,才情勃发,先是在1993年秋隆重推出了首都颇具制作规模的法国作家让·日亲的荒诞派杰作一一《阳台》,又接二连三地在几年间创作、改编了一系列情态各异的实验剧目:自创的小剧场戏剧《我爱×××》(1994年末);中德合作的、根据中国街头剧与德 国作家毕希纳的经典名剧改编合成的《放下你的鞭子·沃伊采克(1995年夏);实验音乐剧《爱情蚂蚁(1997年春)等,其间还应邀前往香港、日本、韩国等地,排演剧目,举办讲座,广泛展开了与实验戏剧有关的社会活动。
1997年秋至1998年春,孟京辉赴日本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戏剧考察观摩,归来后即进入了新的一轮创作与演出的高峰。仅在1998年内,就有《坏话一条街》及《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两部大戏连续上演。后者是根据意大利当代戏剧家达里奥·福获诺贝尔文学奖原作改编的,上演后广受好评,掌声四起,尤其引起了社会文化界及舆论界前所未见的关注。
已渐成文化焦点人物的孟京辉,1999年度在公众的热切瞩目中执导了两部小剧场新创剧目:《恋爱的犀牛》与《盗版浮士德》,这两出新戏在市场运作和票房收入方面大获成功。观赏孟京辉的戏剧演出,甚至已经成为当今一些青年的高级流行时尚;但与此同时,媒体上也开始出现了对孟京辉作品的不同批评意见。
经过在实验道路上历经数年的孜孜以求,行走不息,孟京辉终于确立起一套个性鲜明的语言方式和独异于众的艺术风格。他的实验戏剧以充足的观赏魁力逐步吸引了以青年为主体的日渐众多的观众群体,使原本囿于小圈子的实验戏剧开始冲出孤芳自赏、曲高和寡的狭窄天地,同时也以跳出樊笼、力创新篇的叛逆的勇气与创新的精神,打破了话剧领域长久以来冷寂、僵滞的局面。
灵动多姿的诗化戏剧
孟京辉的戏剧作品大多灵动机智、撩人心怀,它们丰富而多元,感性而细腻,有贯穿如一的强烈个性化色彩。他的每一部戏,几乎都是狂放、温情、幽默、怪诞、不恭的混合体,兼备现代主义气质与古典主义趣味,其中粗狂的颠覆与唯美的意趣同现,深浓的诗情与谐谑的讥嘲互映,跌宕起伏的情感伴生着强烈的韵律节奏,突兀夸张的动作凸显著炽烈的表现性风格。
孟京辉以自己大胆的舞台实践展开若对空洞僵化戏剧模式的挑战与超越,他鄙视肤浅造作、循规蹈矩,标榜离经叛道、前卫革新,因此作品多有横逸斜出的新颖构思,舞台上不时出现妙想天开的神来之笔。在《等待戈多》中,随处爆发着令人猝不及防的突发奇想:自行车内圈到处滚动,窗户玻璃被突然击碎,演员们忽而谵言妄语、手舞足蹈,忽而愁绪满怀、深情脉脉……孟京辉不拘泥于原作的题旨,使理性的冷峻化为了可以触摸感知的丰富意象;《思凡》将昆曲《思凡·双下山》与薄迎丘《十日谈》中的两段故事巧妙无痕地嫁接在一起,中国戏曲的表现程式与意大利喜剧的夸张诙谐杂糅并用,看似信手拈来,却又浑然天成,演员们在舞台上的表演即兴挥栖,灵动舒展;《我爱×××》更是别出心裁,这部90分钟的小剧场戏剧无任何具体情节、故事、人物,以灯光暗转或纪录片间隔为若干段落,由750句“我爱……”贯穿始终,全剧用男声、女声、混声及呼喊至细语间的各种音质、音色乃至哑语、无声,传递着各种关于“我爱……”的长短句;在《放下你的鞭子·沃伊采克》中,孟京辉又进行了一种新奇的尝试:将《放下你的鞭子》与《沃伊采克》分别作为一出戏的两部分在室外和室内分别演出,室外进行的环境戏剧《放下你的鞭子》,将中国歌剧、外国民谣、流行歌曲、街头把式、西洋小丑、名片译配熔为一炉,活泼自如,意趣迭生,为观众提供了一次新鲜有趣的体验。
孟京辉的戏剧是一种新型的写意性的诗化戏剧,他在每部作品中都竭力摒弃对琐屑生活的写实性再现及对形而下日常化状态的平板描绘,而喜爱以变幻多姿的风格化渲染、诗意性的语言表述呈现一种提炼了的精神寓意、一种浓缩了的生命激情,而且他的戏剧大多呈现的是一种明媚绮丽、浓烈饱满的温暖色调。在充分体现让·日东美学思想的《阳台》中,孟京辉与原作取得了气质上的相通与化合,将其表现得极富仪式感和游戏性,它看似怪诞不经,却人骨地折射出人类灵魂的深刻真实及世间万象的离奇百态。这出多姿多彩得令人炫目的荒诞戏剧,诡异奇谲,激昂烂漫,恣意的挞伐与瑰丽的诗情交映,其乖张、暧昧、秾丽、炽烈,共同编织出了一幅亦真亦幻、光色迷离的人生图景。在室内小剧场演出的《沃伊采克》,是孟京辉唯一一部格调沉郁的作品,但它仍未偏离诗意弥漫的表现性风格,却因激情的更加浓稠、心绪的更加郁结而闪射出了一种凄怆而骇人的美丽,它集合了背叛、血腥、暴力的残酷,又糅入了伤感、酸涩、滑稽的笑闹,既炽热灼人,又愁肠百结,有一种紧紧攫住人心的力量。实验音乐剧《爱情蚂蚁》仍承继着一如《阳台》般的称丽与烂漫,只是褪去了些火气与喀噪,多了几分的隐幽与委婉,它妙语连珠,冷眼讥嘲,但已趋向合而不露,沉静内敛,因而更有种耐人寻味的细润微妙。
孟京辉力避对观念的直接传导和阐释,而喜爱任由艺术的想象恣肆驰骋,在他奔放不羁的创造狂想中产生了很多成功的实验成果。《思凡》对戏曲程式精髓的独到领悟与成功巧用,以及摹拟、戏仿、反讽、符号化等表现方式,不仅成为日后孟京辉创作的重要手段,且从它一开始出现,即引起他人纷纷仿效,迄今不绝。作为一部实验大戏,《阳台》在整体上虽非尽善,却以令人应接不暇、精彩纷呈的形式美感,带给了观众强烈的审美冲击。《我爱×××》完全可以看作是一次关于语言的纯粹的形式实验,戏中语言的层层声浪增成了强劲的旋律,释放出富有表现力的独特能量,如其中一句每个中国人都熟透了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全体合声朗诵达20遍,它在巧妙而特异的处理后,产生出了不可言说的丰富意味。《我爱×××》出奇制胜的形式突破,当即获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反馈,而它对形体语言、诗朗诵等形式的挖掘出新,都在孟京辉未来的戏剧中得到了更广泛灵活的应用。
对文学因素的重视和把握,是孟京辉的戏剧获得诗化效果的重要基础,而经由具有广博文学修养的沈林、黄纪苏处理与改编过的几部戏剧经典之作,尤其以缩丽的文词、机智的思辨,显出了不凡的品位与内蕴。
音乐始终是孟京辉钟爱的一种言说方式,较早的《思凡》、《阳台》人放下你的鞭子·沃伊采克》都有音乐在剧中适时穿插,它们常常能够烘托气氛,激荡情感。从《爱情蚂蚁》开始,由于与孟京辉艺术气质相投的优秀作曲家张广天在创作中的成功介入,孟京辉更将音乐作为一种有力的表现手段大量直接引入舞台,在《爱情蚂蚁》、《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等剧中,声情并茂的歌曲在营造诗意、撩拨激情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点化作用,同时也提供了某种可待继续完善的音乐戏剧的雏形。
一种独特的精神文本
孟京辉戏剧的意义不只限于一种新颖的形式创造,更在于他以戏剧的形式对特定时期内一代人的精神世界作出了独特而有意义的表达。作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的孟京辉这一代人,成长于充满启蒙色彩与理想主义的80年代,创作成熟于纷繁多元的90年代。而孟京辉在创作中往往服膺于激情与感受的导引,本能地植入了自己的个体生命的真实形态,因此其个性特征在很大程度决定了作品的艺术特征,作为一代人的某种心灵特征也明显铸造了其作品的人文特征,这使他的戏剧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自述性的精神文本,具有可供分析和解读的相当价值。这也是他的戏剧能够与为数众多的观众发生共鸣并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
孟克辉的戏剧中,往往有两种对峙的精神因素并行不悖地共存着:恣意放纵的嘲弄不恭与深怀难弃的理想梦幻;精致的优雅诗意与俚俗的平民色彩……但其貌似玩世不恭的内里,其实是对虚伪的鄙弃、对苟且的不甘,是对生命价值的执着与在意,而源于生命的激情,更为其作品带来了骨子里某些真正严肃的品性。
《我爱×××》就是一代人率性直陈的精神自白,它以“我爱……”这样一个鲜明的判断句式,连缀起了纵跨一个世纪、横跨东西世界的诸多事件与人物,从而涵盖了相当广阔的意识形态内容,明确展露了创作者多方面的价值取向:这是些怀疑和梦想的产儿,他们嘲弄道貌岸然、煞有介事、虚伪矫饰,颇有嬉皮气质,但又崇尚创造,张扬个性,富于理想情怀,具有难以氓灭的爱心和参与精神。自幼受到的”假大空”式教化的坍塌带给这一代人怀疑、叛逆、反思的自觉,而理想主义的启蒙埋下的先天基因,又养育出他们对道义与责任的几分格外敬重,因而他们在玩笑中有清醒的判断,嘲弄中有认真的坚守,这无疑是一种健康而有趣的人格构成。
反叛与悖逆有时又是通过对青春与激情的赞颂来表现的。可以说《思凡》就是一出青春生命的庆典,它灵动剔透,谐诸俏皮,闪耀着温馨的人性的光泽。在幽幽缈缈的梵音诵唱击罄摇铃中,小和尚本无与小尼姑色空春情萌动人性勃发,最终冲破羁绊走向凡尘;沐浴在人文主义阳光中的异国青年,尽享男欢女爱甜蜜浪漫,却也有恼人的困惑与无奈……这里没有刻意言说什么高深的理念,却在馆戏笑闹中蕴含了令人会意的人生况味,它对青春生命的赞美与自由人性的高歌,本身就是其价值与鬼力所在。《思凡》恩昂扬自信而机智通达,因激情充盈而意趣盎然。
即使是展露人生的虚空与绝望的荒诞派戏剧,在孟京辉的处理下,也往往衍生出了新的含义。《等待戈多》在呈现荒诞的同时,又在竭力打碎荒诞,在描述虚无的时候,又在竭力抵抗虚无;看似遥遥无期的“等待”中,有热切焦灼的希冀,有冲破黑暗的决心——要“站在最高处向人类心灵的最阴暗处宣战”(《等待戈多》说明书)。它最终带给我们的不是颓丧、压抑、绝望,而是憧憬、通达、宽释,这是一种试图去拥抱理想的积极“等待”,更是一种水不沉入黑暗谷底的中国式的坚韧”等待”。荒诞戏剧《阳台》原本就汇合了多种令孟京辉这一代人着迷与心仪的美感元素,经由孟京辉式的艺术处理,它更被涂抹得生机勃勃:法兰西文化的浪漫背景下,从革命与暴力中流淌出来的殷红的血色,对权威与禁忌冒犯亵渎的淋漓的快感;艺术与爱情的绮丽幻美,反叛与冒险的炽烈绚烂……它几乎没有灰色沮丧的调子,倒像在表现一场世俗的狂欢与盛典,太过华美堂皇的气息几乎遮掩了原作部分思辨的光辉,生命中无可掩抑的力与美的展现,甚至扭转了让·日东原作中某种颓靡沉溺的倾向。
心怀天下,志存高远,本是一代人不灭的理想情怀,当剥离了曾经与之相连的某些畸形的政治色彩,它便不再是矫情的作态与空洞的口号。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孟京辉恰逢其时地取到了与之最相通的人文精华,将此前他所提出的“人民戏剧”的观念渗透进去拉近了实验戏剧与当下社会及大众生活的关系。
多种精神特质的杂糅并陈与某种暧昧游移的情感倾向,使孟京辉的戏剧具有了丰富多元的个性,也正暗合了时代的某些典型特征。他的戏剧既是敏锐犀利的,又不失之于刻薄、狞厉,而是温情弥漫;既是富于独特见解的,又不失之于沉重枯涩,而且有充足的审美魁力;既是气势逼人的,又不失之于强词夺理,而是圆融通达的,这些品质互映互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张力与意味。
(二)
青春褪色 诗情难再
随着青春期的自然退隐,孟京辉的戏剧逐渐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激情勃发的冲击状态进入了相对宁静的沉潜冥恩的低徊状态。《爱情蚂蚁》显现了这种特征:原来狂须突进式的理想主义激情更多地被伤感无奈的低吟浅唱所代替,平和超然从容优雅消解了某些酷烈和偏执,您意的调侃嘲弄化作了冷眼旁观的窃笑,失重的细碎的无聊感也悄然浸入,正像剧中人所歌——“我的眼中有方向,可我为什么总想睡?”
这是一个很必然的变化过程,在步往生命的成熟期时,他的作品也应借此走向浑厚、走向深广。
但另外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却开始出现:当青春的热力退隐后,他的戏剧已不再那么激情饱满,而显得日益空洞苍白;形式上的花样翻新虽令人感到眼花缭乱,但每出新戏都像是集往日之大成者;诗意的渲染中出现了“做”的痕迹,原本就存在潜伏或隐而不显的问题逐渐突出出来。孟京辉的某些作品还突然不可思议地染上了些闹剧气息,从动作到语汇,流俗符号悄然介入,使其原来的谐谴俏皮趋向滑稽笑闹,逸趣优雅走向媚俗矫情,艺术境界与格调出现了明显的滑落。
普遍受到好评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无疑是孟京辉的一部出色作品,但仍露出了一些问题的端倪。它在形式上巧妙地汇集了既往各种成功的语言表达方式,睿智的妙语中思想的火花四溅,精彩的枝蔓四处伸展,观众一次次发出会心的笑声,剧场内掌声不断,但它呈现出的却是一种典型的精彩的“碎片”状,太多的地方出彩的噱头成为了戏剧本身,而孟京辉过去一直存在又始终未得解决的不足——逻辑关系的梳理,内涵的把握与提升,对通篇作品的整合与控制,对剧情的叙述与交待等等,都更明显地暴露出来。相对原作甚或改编本所提供的丰富深邃的空间而言,《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是并不让人十分满足的。
孟京辉虽已意识到,在“人民戏剧”的观念中蕴藏着一种真正的先锋精神,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道出的只是达里奥·福——一个人民游吟诗人的模糊影像;“人民戏剧”与“游吟诗人”的意象虽无限美好,却有些语焉不详,因而有隔靴搔痒之感,一些精彩的抨击性言辞只成为飘浮在作品上面的激进口号,其社会批判意义也就显得单摆浮搁。同样的症结也出现在《盗版浮士德》与《恋爱的犀牛》中。“浮士德”作为一个含义丰富的经典文化符号,其意义的产生有赖于与当下中国生存情境准确的衔接对位、对于所要坚守与批判对象的坚定认知,否则就会有种“强说愁”的味道;而由于魔鬼梅菲斯特的干瘪无力,浮士德也同步虚弱,对峙的精神因素的削减,使浮士德缺少了诱惑与沉沦、自省与拯救的心灵变化轨迹,只是一味地处于莫名其妙的神经质的痉挛状态里,使这个人物应具有的力量远远没有得到正常的释放。《恋爱的犀牛》中,创作者本着意表现物质主义时代一个不合时流的异类的可悲境遇,这本是一个大可言说的深刻题目,但由于对表现对象精神价值认同点上的模糊,创作者没有将人物所谓的“偏执”进行基本的准确解码,它展现的就不是一种当下所罕有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落寞英雄或美丽人性遭到毁灭的悲剧,而成为对一个不可理喻的智能不足者可笑性格、滑稽行为的讴歌。
有人认为孟京辉戏剧的实质下滑源于其艺术模式的形成和对其的固守,其实“模式”的定型还远不到令人忧虑的程度,而不幸的恰是在某种“模式”尚未获得充盈的支撑物而趋向完善时,便失去了必需的涌养或被过度不当地使用。形式重复的背后实际上是精神的迷茫、徘徊与停滞,当作品失落了精神的内核与生命的激情,即被抽掉了根基,这时所有刻意的形式雕琢与铺排渲染都只是一种纯技术性的操作,只显得言不及物,浮躁虚空,愈来愈趋向形式主义的极端。
孟京辉本是一个诗人气质浓郁的艺术家,他戏剧中真挚的诗情正是其戏剧之魂,正是其审美魅力产生的源头,而当“诗心”失落,作品即便依然沿用既往美丽、炫目的形式外壳,即或再加上种种新颖的时尚包装,却也只能徒有其表。当机智变异为油滑、激情变异为姿态、通达变异为玩世,他的戏剧便诗情不再。
突破困境继续求索
鉴于孟京辉实验戏剧目前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和影响,我们有理由充分苛责它所存在和出现的各种问题。
凭借青春的本能与生命的锐气,孟京辉曾使他的戏剧可喜地冲出了僵滞与羁绊,然而青春易老,这种处于自发状态中的激情相对脆弱易变。当曾经阻碍生命自由呼吸的东西已自生自灭,并在历史中逐渐尘埋;当伴随着成功的到来,反叛的对象已被瓦解击溃;当青春的苦闷多愁都成为了往昔。解构与冒犯都失去了针对性,精神就注定陷人平席自足、人文热情也必随之衰减吗?抵抗奴役却终被奴役,抵抗投降却在胜利来临之际自我缴械,这是艺术史中太多的发生在艺术家身上的故事。
要投入新的一轮更艰辛的战斗,仅仅停留在一种自发的创造状态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以理性的自觉担承起继续前行的使命。一个面对业已散架的风车仍挥剑不休的唐·吉诃德不仅是陈腐的,更关键的是正事也会被这样耽误掉;如果总在对抗颠覆一个已然萎顿的事物,挑战者本身也会随之衰弱——可能这时最致命的敌手已经就是自己。
如果像孟京辉所说过的那样——“实验本身就是一个标准”,那么“实验”的精髓就在于一种恒久的反叛与大胆的重建。实验艺术家作为永远的责无旁贷的艺术革新者,任何精神上的自足,都意味着实验精神的停滞,革命性的衰退,梦想的卑微,而注定有从青春激情滑向“老滑俏皮”(林语堂言)的危险。
新时期以来桶现的一代年轻艺术家在解构时往往痛快淋漓,进入建构时期,由于文化准备不足,常常显得难堪其重,普遍少有精彩完美的表现,致使反叛后只剩下精神的废墟,成为有人所说的那样,“最终闹剧代替了尖刀”。这似乎成为了一个普遍的困境。其实如今即便围绕着“人民戏剧”的观念,也还有太多的课题要做。作为一个当代的戏剧艺术家,为民而歌,决不是过时的调子,而恰是要急切呼唤的良知与激情。那么,如何真正确立自己的民间立场,如何真正置身于为民而取的广场?光有甘居“人民”一员的决心与姿态怕是远远不够的,更不可缺的是要对人类深广关怀下的清醒的批判、勇敢的坚守及忘我的担承。
孟京辉的实验戏剧当前正值品牌形成、观众盈门之际,这正是弘扬实验精神,对观众进行心灵引导的绝好时机。作品精神品质的完善,只会为观众提供更具观赏愉悦的艺术品,而不会吓退正处于审美兴奋期的观众的热情。目前孟京辉的作品在实验戏剧的市场中可谓一枝独秀,同行中也少有势均力敌的同龄对手,因而在创作环境方面缺少竞争与抗衡,这对其艺术的发展利弊兼有。自孟京辉的实验戏剧诞生以来,批评始终处于缺席状态,少有真正意义上的鼓励与匡正,舆论则一贯长于畸形的炒作,总是不脱“捧杀”、”骂杀”两套传统的家法,这都不利于中国年轻一代业已初具规模的实验艺术深入地发展。
孟京辉实验戏剧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提供了将实验深入进行下去的多种可能与萌芽。在由孟京辉一部一部戏剧构成的时空中,艺术迎来了变革,时代发生了变化,一代人在成长,而他创造的那些难忘的戏剧篇章,已注定成为留在很多人记忆中的一支深情欢快而美好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