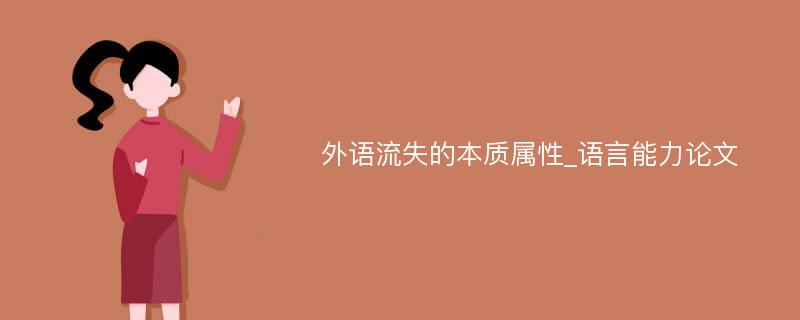
外语磨蚀的本质属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属性论文,本质论文,外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外语磨蚀是语言磨蚀按受蚀语种分类时,两个类别(另一类为母语磨蚀)中的一类[1:11]。语言磨蚀(language attrition;简称语蚀)是语言学习的逆过程,意指双语或多语使用者,由于某种语言使用的减少或停止,其运用该语言的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退的现象[2:3]。
在语蚀研究领域,与母语磨蚀相比,外语磨蚀因涉及对象广和成果应用价值大,而更受研究者青睐。在语蚀研究这门学科创立前,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语蚀的研究对象就集中在欧洲学习外语(德语、法语、拉丁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学生身上。在学科创立之际的20世纪80年代初,外语磨蚀仍不失为研究的热点。在标志学科成立的首届专题研讨会上(1980;美国),被大会收入论文集的12篇论文中,与外语磨蚀相关的就多达10篇[3]。在学科成立之后,外语磨蚀的研究仍一直保持着原有的势头,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造就了一批成绩卓著的学者,如:Lambert、de Bot和Hansen等;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外语磨蚀解释框架,如:激活阈值假设(Activation Threshold Hypothesis),干扰假设(Interference Theory)和处理资料减少假设(Reduced Processing Resources Hypothesis)等;出版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探明了外语磨蚀的一些影响因素;明确了受蚀语言要素的主要特点和完善了系列的外语磨蚀检测方法。
诚然,在外语磨蚀研究领域仍有一些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其中,外语磨蚀的本质属性界定就是尚未探明而亟待解决的遗留问题之一。目前,已探明的外语磨蚀本质属性仅有两项[4:22-37,5:60-73]:(1)外语磨蚀的生理性。外语磨蚀的语言能力减退属于自然的生理性而不是病理性现象。这使得外语磨蚀有别于失语症或老年痴呆所致的语言能力减退。(2)外语磨蚀的代内(intragenerational)特征。受蚀者语言能力的减退属于代内而不是代间(intergenerational)的变化。这使得外语磨蚀有别于方言研究中的语言迁移或消亡。其实,随着外语磨蚀研究的不断深入,外语磨蚀的本质属性已逐步显现出来,只是尚未得到及时分析和梳理。
分析、梳理和界定外语磨蚀的本质属性,无论是对于语蚀的本体研究还是外语教学研究,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对于语蚀的本体研究,界定语蚀的本质属性是开展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这是因为不明确语蚀的本质属性,就无法将语蚀现象从纷繁复杂的语言能力减退现象中独立出来,语蚀的专题研究则无从谈起。要分析语蚀的本质属性,理应首先明确语蚀各类型的属性。就语蚀的两大类型而言,外语磨蚀比母语磨蚀的研究历史更长,资料更多,其成果的应用面也更广。如能以此为突破口,通过对比分析,母语磨蚀的本质属性分析亦可迎刃而解。如进而将两者综合,语蚀的本质属性即可界定。对于外语教学研究,由于外语学习与磨蚀互为逆过程,其关系密不可分,如果外语教学研究者能从其逆过程——磨蚀的角度换位反思,重新审视目前外语教学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现有成果,定能有所创新。此外,明确界定外语磨蚀的本质属性对于促进国内语蚀研究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如火如荼的国际语蚀研究相比,国内的研究现状显得一片落寞。到了本世纪初,国内个别学者,如:钟书能[6:66-70]和蔡寒松[7:924-926],才开始简介国外的相关研究。然而,中国既是外语学习者也是受蚀者最多的国家,急需让学习者保持花费巨资学习来的外语能力,并让他们在最需要的时候运用自如。面对这一广阔的应用前景,国内的语蚀研究如能以外语磨蚀的本质属性界定为契机,定能逐步走向成熟。
为此,本文拟就外语磨蚀的“诱发因素的归一性”、“发生机制的生理性”、“受蚀个体的独立性”、“受蚀对象的选择性”、“磨蚀过程的回归性”、“磨蚀速度的非均衡性”、“表现形式的隐匿性”和“再学习的优越性”等八个方面,对其本质属性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梳理。
1.诱发因素的归一性
一般说,能够影响外语学习的因素,也可影响外语磨蚀。目前,有些因素的影响作用尚未探明,如:学习者的个体差异(认知风格、智力、学能等),已经探明的有磨蚀前外语水平、受蚀时间、与受蚀语的接触方式、年龄、外语学习方式、社会情感因素、读写能力和目的语语种等八种:(1)磨蚀前外语水平:是影响外语磨蚀的关键性因素,与磨蚀的量或/和速度成“倒置”关系[8:40]。(2)受蚀时间:是外语磨蚀的决定性因素。在外语磨蚀研究中,中短期跨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月和1~4年。为期3个月(欧洲的暑假时间)的研究对是否存在外语磨蚀尚无定论,有学者[9:132-146]支持,也有学者反对[10:127-138;11;12:400-405]。为期1~4年的研究均证实了外语磨蚀的存在。长期跨度(50年)的研究显示:外语磨蚀过程呈现一种“前快—中慢—后快”的发展趋势[13:1-31]。(3)与受蚀语的接触方式:对外语磨蚀速度和程度的影响至关重要。受蚀者与受蚀语的接触可分为两种类型:自然和人工干预状态。自然状态下的研究结论基本相似[14;15;16:519-540]:与受蚀语接触多的受蚀者,其语言技能的磨蚀程度明显低于接触少的。人工干预状态下的研究主要基于理论分析。这些学者[17:176-190;18:80-111]声称:人工干预的方式可有效防止外语能力的磨蚀。(4)年龄:研究者经过成人与儿童和儿童间的对比后发现,儿童的外语磨蚀比成年人快,年幼的比年长得快[14;19;20;21;22;23;24:175-188;25]。(5)外语学习方式:外语课堂教学方式[26:15]、侧重点[27:114-141]和强度[28:169-200]均对学习者尔后的外语磨蚀产生一定影响。(6)社会情感因素:有关社会情感因素对外磨蚀影响的研究[14;29:305-308;30]大多集中在态度和动机上,且所得结论相似:社会情感因素是影响外语磨蚀的间接原因之一。(7)读写能力:不少学者[5:60-73;31:187-204;32:151-165;33]均证实读写能力可有效地防止外语磨蚀。(8)目的语语种:Reetz-Kurashige[34:21-58]通过研究证实了Geoghegan[11]、Edwards[29:305-308;14]、Lowe[17:176-190]、Berman[35:222-234]、Clvne[36:23-36]和Olshtain[31:187-204;32:151-165]等学者的观点:母语与外语类型和语用上的相似性有助于外语能力的保持,而母语与外语的差异容易导致干扰和磨蚀。
外语磨蚀的影响因素除了类别多而杂外,因素间还存在交互作用。比如:年龄和读写能力,社会情感因素与接触方式等。尽管如此,外语磨蚀最原始或前提性的动因却只有一个:外语接触的减少或停止。没有这一诱因作为前提,其他因素将无法影响到受蚀者外语能力的磨蚀。这是外语磨蚀的本质属性之一,可称之为外语磨蚀诱发因素的归一性。
2.发生机制的生理性
虽然语蚀与失语症、老年痴呆和帕金森氏综合症一样,均表现为语言能力的下降,但是其发生机制却存在本质的差别。语言磨蚀属一个随着受蚀语使用的减少和停止,人脑认知的自然生理性过程。这与遗忘一样,均为大脑正常的认知机制。
目前,虽然在语蚀研究领域,对其发生机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框架,比如:检索失败假设(Retrieval Fail Hypothesis)、激活阈值假设(Activation Threshold Hypothesis)和处理资料减少假设(Reduced Processing Resources Hypothesis),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这些假设均基于人脑认知机制的生理性,而不是病理性特征。这正是语蚀有别于病理性语言能力减退的本质属性。
然而,纵观语蚀研究近70年历史,对语蚀发生机制生理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是在语言磨蚀的学科创立之际,语蚀研究与病理语言学仍属同一研究范畴。比如:在1980年首届语蚀研究的专题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既有病理语言学的,也有语蚀研究的[3]。到了1982年,在荷兰Nijmegen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会议上,仍没有学者指出语蚀发生的生理性特征[37:177-186]。只是到了1986年,在荷兰Kerkrade小镇召开的第三届会议上,才有学者[4:22-37]正式将语蚀的生理性属性作为语蚀本质属性确定下来。在此后的3~5年内,即:在外语磨蚀与母语磨蚀从语蚀研究中分化之时(注:有学者认为在1991年由Selige[38:227-240]撰写的“First Language Attrition”,标志着外语磨蚀与母语磨蚀研究的分离),病理性语言能力减退的研究才逐渐淡出语蚀研究范畴[33]。由此,鉴于外语磨蚀属于语蚀的一个重要类别,语蚀发生机制的生理性理应属于外语磨蚀的本质属性之一。
3.受蚀个体的独立性
任何一个外语学习者,在外语正式学习结束后,如果与外语的接触减少或停止,即可认为他已经进入外语的磨蚀阶段,他也随之成为外语磨蚀的受蚀者或受蚀个体。这些受蚀个体,在横纵两个纬度上均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横向上讲,受蚀个体的相对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个体的聚集不以独立的语言社团为标志。所谓语言社团(speech community)意指许多人形成的一个团体,如一个村子、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大家都使用同样的语言或语言变体[39:354]。外语受蚀个体,可能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社区,也可能使用外语(虽然很少)进行交流,但他们的聚集不构成独立的语言社团,相互间的影响方式与独立语言社团成员间的亦完全不同。另一方面,这些个体,如果基本情况相似,如:教育背景、学习过程、磨蚀前的外语水平等。如人数众多,仍可构成语蚀研究中的群体。其外语磨蚀的程度、速度等方式可能趋同。通过对这一群体的分析,可为具有相同背景的更大群体提供参考数据。这正是语蚀抽样研究的科学基础。
纵向上讲,受到外语磨蚀影响的个体,其语言能力的减退只发生在受蚀个体这一代。他不可能通过遗传或交际影响到下一代。换句话说,外语磨蚀所致的语言能力的减退属于代内(intragenerational)而不是代间(intergenerational)的改变。运用外语磨蚀不跨代的特点,(可将外语受蚀者的外语能力磨蚀与方言研究中语言迁移(language shift)或语言消亡(language death)时语言社团成员所表现出的语言能力减退区别开来[4:22-37],[5:60-73]。)因为语言迁移或方言消亡时的语言能力减退效果是依靠代间的积累来体现,特别是在语言消亡时,随着更年轻语言社团成员成为另外一种语言的主流,语言消亡才有可能发生。
4.受蚀对象的选择性
所谓受蚀对象的选择性(selectivity),意指外语语言体系中的受蚀对象是由规则控制的(rulecontrolled),并具有一定的选择性[38:227-240],即:语言体系中的不同对象对外语磨蚀的敏感性不同,其磨蚀的速度和程度也不尽相同。受蚀对象的选择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语言技能间的选择性。语言按技能可大致分为听说读写。其中,听和读属于接受性技能(receptive skills),而说和写属于产出性技能(productive skills)。在外语技能的磨蚀研究中,Tomiyama[40:59-79]通过调查证实:与接受性技能相比,产出性技能对磨蚀更为敏感,磨蚀的速度更快。这与Weltens[41]、Yoshitomi[42:293-318]和Reetz-Kurashige[34:21-58]的研究结论相似。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语言使用者在应用产出性技能时,在语言的计划和协调上需要动用更多的资源[18:80-111]。二是由于受蚀者掌握的语言信息不一定丢失,而可能是暂时通达困难。如果能提供正确的通达路径,仍可以检索到这些信息。研究者在测试受蚀者的接受性技能时,提供的测试材料本身就是一种检索线索[4:22-37]。
(2)语言层面间的选择性。按传统的语言磨蚀研究方法,语言体系可分为语音、词汇和语法(词法和句法)等不同层面(aspect)。在外语磨蚀研究领域,Tomiyama[40:59-79]曾对比过语音、语法和词汇的磨蚀程度。她的研究结果表明:磨蚀程度最明显的是词汇,其次是语法,语音的磨蚀最小。迄今为止,虽然尚未收集到词法和句法间的对比资料,但将词汇与词法和句法的磨蚀程度进行对比的实证资料不少。而且,这些资料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均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相比较而言,词汇最早受到磨蚀,其次才是词法和句法[24:175-188;27:114-141;40:59-79;42:293-318;43:138-154]。这主要是由于词汇知识是开放的体系,需要终身学习。而词法和句法知识,在外语学习结束后,即使处于磨蚀中,也不会再增添新的内容[44:53-78]。
(3)语言层面内各要素间的选择性。在语音层面上,各要素间的磨蚀程度对比虽未进行实证研究,但是Andersen[45:83-118]进行过理论分析。她认为:高功能负荷的音位比低负荷的耐磨蚀。在词汇层面上,有关不同类型词汇间磨蚀程度的对比研究,可能是外语磨蚀领域开展得最热门的课题。虽然词汇分类方法可能不同,比较的类别也可能不同,但通过实证的研究结果大多表明,不同类别的词汇,其磨蚀速度差别较大。比如:Hansen & Chent[46:90-110]曾用标记理论(Markedness Theory)研究过日语不同数量词间的磨蚀程度。他们发现:使用频度高和标记性小的数量词磨蚀程度小。又如:Gonzo[47]、de Bot[48:151-166]和Graham[49]等人均发现产出性词汇知识比接受性的磨蚀程度大。在词法层面上,由于语言类型不同,词法的应用手段亦不相同,故有关不同词法要素间的磨蚀程度的对比,与语音一样,也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Andersen[45:83-118]认为:在受蚀语中具有低功能负荷、低使用频度和高标记度的词法形式更容易磨蚀。在句法层面上,常用于研究的要素有词序、介词短语、(格、时态、主谓等)一致性、否定形式和从句等[38:227-240]。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要素也是句法中容易受到磨蚀的成分。其研究结果也因语种而异,比如:Hayashi[50:154-168]通过西太平洋群岛人日语否定用法的调查后发现:被试保留的属使用频度高的日语否定形式。由此,从语言层面内各要素间的选择性来看,虽然语言类型不同,研究层面内的要素也不相同,但是耐磨蚀成分的特征基本相似:功能负荷大、使用频度高和标记性小。
5.磨蚀过程的回归性
当受蚀者的外语能力出现磨蚀时,语言成分的磨蚀顺序与其掌握的顺序相反。这一属性称之为外语磨蚀的回归性,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基于历时的顺序。最先掌握的,最后磨蚀;二是基于训练强化程度的:在教学中强化训练多的先掌握,后磨蚀[33]。关于磨蚀过程的回归性,在语蚀研究领域已有专门的理论进行概括:“雅克布逊回归理论(Jakobson's Regression Theory)”。
其实,语言丢失或能力减退时的回归现象,并不是雅克布逊最先发现。早在1880年,Ribot就提出了“Ribot规则”(Rule of Ribot),意为最近学习的,最容易遗忘。该规则于1891年由弗洛伊德引入心理分析,并首次改用“Regression”一词。到了1941年,雅克布逊才引入失语症的研究。最后,由Freed于1980年引入语蚀研究,且命名为“雅克布逊回归现象”,意指:后学会的,先磨蚀,掌握好的,后磨蚀[51:13-23]。此后,验证雅克布逊现象的外语磨蚀研究才日益增多。目前,用于实证研究,且得到验证的语言成分有:德语格标记[52:159-176;53:179-204]的磨蚀、北印度乌尔都语否定形式的磨蚀[35:222-234;31;31:187-204;32:151-165]、日语否定形式与数量词的磨蚀[26;50:154-168]和词汇的磨蚀[54:143-158;55:135-150;43:138-154]。
诚然,也有文献[56;57]指出:不是所有的外语磨蚀过程均可用“回归性”加以解释。他们认为,除了回归性外,还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磨蚀的过程,如:外语的学习方式和环境[58:31-52]。此外,在语言体系各层面上记录语言学习和磨蚀的过程,其研究方式本身就存在问题。既跟踪学习又跟踪磨蚀的研究周期太长。而且,在试验条件下,具有普遍意义且可以预测学习和磨蚀顺序的理想研究模型,只有在为数不多的语言结构中才能建立起来。在检验雅克布逊回归现象时,理想的模型应该是:其结构的掌握是逐渐形成并按固定的顺序发展,而且是相对数量较小的语言成分[59:109]。
因此,正如Yoshitomi[42:295]所说,通过有限的几种语言成分归纳,就将结果推广到语言体系的其他层面上去,并认为其磨蚀也具有回归特性的做法,存在一定的风险。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可以明确这一点:外语磨蚀是朝着学习的逆方向发展,并且部分语言现象的磨蚀呈现出回归的趋势。
6.磨蚀速度的非均衡性
一般来说,在外语正规学习结束后,如果学习者不刻意维护,其外语能力的磨蚀会随之出现,其磨蚀速度并不是线性的递减,而是呈现出一定的非均衡性。这主要体现在横纵向两个方面。
横向上说,不同个体间的磨蚀速度因所处的环境不同,影响因素不一样,磨蚀的速度也会不同。如果其他因素均相似,只有外语学习的终极水平不同,那么其外语终极水平与磨蚀速度会呈现出一种“倒置”关系[60:189-203]。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关系并不是线性的负相关,而是在受蚀者的终极水平间存在一个“关键阈值”。在这一阈值上下的受蚀者,其外语磨蚀的速度存在非常大的差异[8:40]。
其实,早在1982年,Lowe[17:176-190]就发现这一阈值位于S2/B2和S3/R3之间(注:S和R分别代表说和读,这个系列是美国政府界定工作人员外语能力的标准,先称FSI量表,后改称ILR量表,共5等11级)。外语终极水平超过这一阈值的受蚀者,通过复习来弥补磨蚀的能力非常容易;如果低于,通过复习很难弥补。到了1984年,Clark[15]等采用大型调查后才进一步明确:这一阈值在FSI量表上的为3级。此后,Nagasawa[28:169-200]也确认这一阈值在ACTFL量表(该标准由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制定)上为优秀级(Superior)。
纵向上说,对于每一个受磨蚀个体,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外语磨蚀的速度也不相同。Bahrick[61:105-118]曾对773名把西班牙语作为外语学习的被试,进行过为期50年的研究。他发现:被试的磨蚀过程呈现一种“前快—中慢—后快”的发展趋势,即在停止使用外语后的前期(如前5年)磨蚀非常严重,中期(如其后20年)不明显或无磨蚀;后期(如其后25年)磨蚀又加快。他[13:105-118]的后续研究表明:大量的外语磨蚀(阅读能力、词汇、短语、语法和词序等)出现在培训结束后的头几年里。
7.表现形式的隐匿性
研究外语学习和磨蚀过程的理想化模型,可用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加以概括[16:519-540]:开始学习和接触外语的时间(T1)、学习结束或外语接触减少或停止的时间(T2)、进行磨蚀程度评定的时间(T3)。一般来说,在进入T2阶段后,受蚀者外语能力受蚀表现是:在实际交际时,受蚀者首先表现为单项语言技能的协调能力下降(可恢复,不积累),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磨蚀后,受蚀者单项语言技能会出现较多的磨蚀(不可恢复,积累)。外语受蚀的最终表现是受蚀者语言能力的整体水平下降[42:293-318]。然而,在T3时,这些表现不一定能够充分地展现出来,其表现的隐匿性主要体现在受蚀者和检测手段两个方面。
在受蚀者方面,他们为了达到最满意的交际效果,总是会采取一些补偿措施,想办法弥补他们受蚀的语言能力,让交际对方,甚至包括自己,感觉不到外语能力磨蚀的存在。比如:使用外延更大的词汇(用harness代替yoke、用artistic thing代替trellis)[62:31-52],在说话时,更多地使用感叹词、填充词和富有感情表达的句子等来延长思考时间[40:59-79]。这些补偿措施的应用肯定会从一定程度上掩盖外语磨蚀的表现。
在检测手段方面,目前能够用于T3检测外语磨蚀的手段虽然很多,有些也非常先进,如:词汇通达时间的测定、事件相关电位的测定等。但是,在检测手段方面,有几个关键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一是对比基线的确定。外语磨蚀的程度是一个相对量,是T2与T3的外语整体水平的差异量。由于磨蚀时间的跨度长,受蚀者在T2时的真实资料难以完善保存,故在T3时一般不易获取受蚀者的相对差异量。二是测量方法本身的信度和效度问题。三是语言磨蚀的检测手段间的差别问题,如:听磁带后讲故事比看图表讲故事发现的错误少[26:3-18]。四是检测手段提供的数据的代表性问题。就检测结果的代表性而言,即使是通过高信度和高效度方式获取的数据,也不一定能真正代表磨蚀整体状况。比如:词汇的通达时间就难以全面反映受蚀者外语整体水平的受蚀程度。由此看来,检测手段的局限性,也从一定程度上掩盖外语磨蚀实际状态的整体表现,从而增加外语磨蚀表现的隐匿性。
8.再学习的优越性
人一生中可能有机会多次学习外语。在第二次学习时,如果所学知识以前学过,即使对于学习者来说,有些知识可能已完全遗忘,但与新学的知识相比较,掌握这些知识要容易得多,而且学习速度也快得多。这就是外语学习过程中再学习(relearning)的优越性。
虽然de Bot & Weltens[48:151-166]早在1995年就发现了语言磨蚀中再学习的优越性,但到了1998,de Bot & Stoessel[63]才将认知心理学的保留范式理论(Savings Paradigm Theory)正式引入语蚀研究。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所谓保留(savings)意指重新学习以前学过的知识时,与学习新知识相比所具有的优越性[64:453-468]。认知心理学家认为,即使所学习的知识不能再认知或回忆,这些学过的知识仍然保留在大脑内,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来激活。相比较而言,回忆所需的激活水平高,而认知的激活水平低。如果某一知识的激活水平下降,就难以被大脑检索到。如果通过再学习,学过的知识就有可能又被激活到可以检索到的水准。对于新学习的知识,虽然同样经过简短的学习,但还是不如旧知识容易被激活。
在外语磨蚀研究领域,最早由de Bot & Stoessel[63;65]采用实证的方法来验证外语再学习的优越性。他们曾经开展过两项试验。一是分析成年人再学习童年时代学过而且早已完全遗忘的外语词汇;二是分析大学生在课堂中学过的外语词汇。这两项试验均证实:对于一些学过的词汇,即使被试不能回忆,或不能认出,但他们仍保留在记忆中。根据这一思路,Hansen[66]也进一步证实,成年人在自然环境中掌握的外语词汇,一些虽然已经遗忘,但在他们的记忆中仍然保留着这些词汇残留的知识。
综上所述,通过对外语磨蚀八大本质属性的系统分析和梳理,我们可对外语磨蚀进行明确的界定和描述:外语磨蚀是发生在外语学习结束后,由外语使用减少或停止所诱发的一种生理性的语言能力减退现象。这种语言能力的减退仅影响受蚀者本身,不会通过交际影响到其他受蚀者。此外,受蚀者的外语磨蚀表现虽然存在一定的隐匿性,磨蚀的速度也不均衡,但其外语语言体系的磨蚀却呈现出一定的选择性,而且有些语言成分的受蚀顺序还表现出明显的回归倾向。
标签:语言能力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