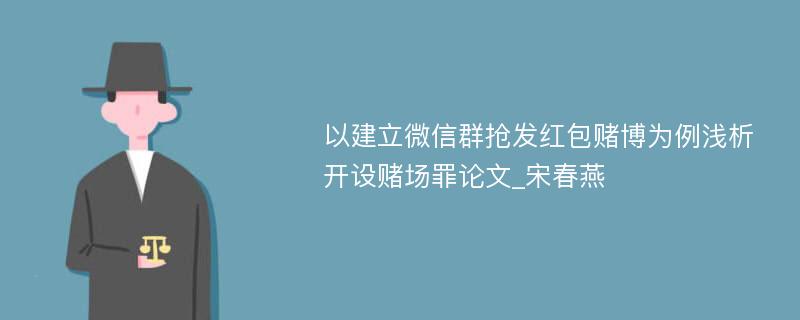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省 西安市 710000)
摘要:目前,微信红包作为网络兴起的新事物受到了越来越多用户的青睐,但是随之利用微信红包进行犯罪的行为也愈加猖狂,建立微信群抢发红包赌博就是其中之一,它被认定为是一种新型赌博犯罪,与此相关的法律问题也应运而生,这其中包括对微信平台抢发红包赌博的行为定性为开设赌场罪还是赌博罪等问题。根据历年判例,对于这几个问题在实践中认定的标准不统一,今年一月最高法新出台的指导案例,将微信红包赌博犯罪行为的组织者认定为开设赌场罪,是结合微信红包赌博犯罪的特殊行为,并通过区分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的不同犯罪特征来认定的,这为开设赌场罪的适用提供了指导。
关键词:微信群;赌博罪;开设赌场罪;抢红包
一、建立微信群抢发红包赌博定开设赌场罪的案例分析
随着科技的进步,微信聊天工具应运而生,并以其娱乐性,互动性和便捷性而受到越来越多微信用户的追捧,作为微信功能之一的微信红包也火了起来。但是,在微信红包受到追捧和热议的同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建立微信群,招募人员,制定严密的规则,抢发红包赌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
在一起微信红包赌博案件中,2015年7月,王某甲以营利为目的在微信上组建微信群抢发红包赌博。赌博规则是:“代包手”发一个人民币125元的红包由4名赌客抢,抢到红包金额尾数最小的人支付人民币138元给“代包手”,“代包手”抽取13元人民币后,再发一个人民币为125元的红包由赌客抢,开始新一轮的赌博,以此类推。为了增加发红包的数量,扩大赌博规模,王某甲雇佣王某乙、应某、王某丙等人拉人入群,并在该微信群内代发红包赌博并抽头营利,“代包手”每抽头13元可得好处费人民币2元。至案发时,该四人共发微信红包2977个,总金额人民币410826元。本案于2016年4月26日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四名被告人均被认定为开设赌场罪。
在上述案件中,王某甲团伙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建立微信群抢发红包的形式,分工负责,制定严密的运营规则组织赌博,法院将其认定为开设赌场罪。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赌博类型的犯罪包含了聚众赌博、以赌博为业、开设赌场三种行为方式,聚众赌博和开设赌场罪二者常常在适用方面存在异议,同时又由于微信红包赌博犯罪行为发生在微信这个网络平台,这个网络平台不同于以往的犯罪场所,其具有虚拟性的特点,这就导致了在实践中大家对其定性持有不同观点。《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赌博罪的最高法定刑为三年有期徒刑,开设赌场罪的最高法定刑为十年有期徒刑,最高法定刑相差七年之多,如果对组织微信红包赌博行为定性不清,不仅关乎司法统一性的问题,更加涉及行为人的人身自由等权利。从刑法立法目的和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上来说,组织微信红包赌博行为应当被认定为开设赌场罪更为妥当,这也印证了最高法发布的指导性案例认可的观点。
二、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
在我国司法实践过程中,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经常出现适用错误的情形,根据《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的相关规定,开设赌场罪和赌博罪在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和侵害的客体都是相同的。要想对两罪做出明确的区分,我们需要从两罪的客观方面入手,探讨其客观方面的区别。但是《刑法》条文对两种犯罪规定的过于简单,又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加以释明,在加上两者的客观犯罪行为具有相似性,如,两者都需要一个用于赌博的场地,都是由组织者召集组织多人赌博,都具有抽头渔利的行为等,这使得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对两罪进行准确的鉴别。鉴于此,笔者将通过对比开设赌场行为与聚众赌博行为的不同犯罪特征,理清开设赌场罪独特的客观犯罪行为,为后文将组织微信红包赌博犯罪行为认定为开设赌场罪提供理论支撑。
(一)对开设赌场罪中“赌场”的认定
开设赌场行为与聚众赌博行为均需要有供赌徒赌博的场所,但是,二者确实有明显的区别的。第一,一般来说,开设赌场罪中的“赌场”,必须具有较高的固定性,而聚众赌博罪对赌博场所的要求不需要包含此性质。[3]开设的赌场的地理位置不能轻易发生变化,开设赌场罪之所以具有比赌博罪更加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就是因为开设的赌场具有固定的场所,其会慢慢发展蔓延,为更多人所知悉,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赌博,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加剧犯罪率的提升。当然,设立赌场的位置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赌场的开设者为了更好的吸引赌客,或者为了逃避警方的侦查而变动的场所,在为大部分赌客所知悉的前提下,也应当被认定为开设赌场罪中的“赌场”。而在聚众赌博行为中,赌博的地点往往由召集者临时选定或者与参赌者协商确定,一般表现为为了方便赌博或者为了躲避警方的侦查随意选定赌博地点,其地点往往不固定。第二,开设赌场罪中的“赌场”具有较弱的隐蔽性。因为聚众赌博多为组织熟人小范围小规模的参赌,为了逃避警方的侦查,他们的赌博地点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流动性,往往在个人家中或者是在宾馆之中。而开设赌场却是要吸引大量的赌客前来赌博,其开设的赌场往往需要让一部分人知悉,所以其隐蔽性往往不及聚众赌博的赌博场所。
笔者认为,在互联网赌博案中认定开设赌场罪中的“赌场”应当明确两点:第一,赌场可以是实体意义的物理空间,也可以是虚拟的网络空间。随着社会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为赌博提供了一个新的场所,该场所确实是一个数字化的物理空间,任何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参与赌博,互联网中的赌场与现实的赌场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因此,对开设赌场罪中的“赌场”应作扩大解释,将互联网中的用于赌博的场所纳入其中,这并不违反立法目的和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因此是完全合理合法的。第二,互联网平台中的赌场不仅仅包含赌博网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5年颁布了《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规定在互联网上开办的赌博网站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的“开设赌场”。虽然司法解释只列举了赌博网站被认定为赌场,但这不是穷尽是的列举,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的网络元素层出,立法以及司法解释往往具有滞后性,我们应对开设赌场罪中的“赌场”做扩张解释,使之包含除赌博网站以外的其他网络空间,而最高法出台的指导案例将建立微信群抢发红包赌博行为定性为开设赌场罪也等于认可对赌场做扩大解释。
(二)开设赌场罪具有经营赌场的行为
在开设赌场行为与聚众赌博行为进行定性的过程中,认定确有“赌场”的存在是基础性的条件,仅凭这一点还不能将某一行为认定为开设赌场罪,还需要进一步认定是否存在经营赌场的行为。首先从字面含义理解,开设赌场中的“开设”体现了赌场从无到有的过程,似乎没有体现经营赌场的含义,但是我们应当结合开设这个动词的客体进行分析,开设餐厅除了有创设建立餐厅的意思外,还有经营餐厅的含义。所以,“开设赌场”一词中也包含了经营赌场的含义。而聚众赌博中的“聚众”所体现出来的是聚集召集的含义,并不包含经营赌场的含义。其次,在实践中,聚众赌博,因为行为多是临时组织的小规模的亲友之间的赌博活动,其具有临时组织的特征;而开设赌场罪中的“赌场”具有规模大,服务全等特征,其本质就在于经营赌场。因此,笔者认为开设赌场罪的犯罪客观方面的本质就是对赌场的经营。那么认定经营赌场需要我们从行为人对赌场的支配性,赌场的服务性等角度分析。
首先,开设赌场的行为类似于运营一家公司。第一,从人员组织来看,开设赌场者往往召集或者雇佣熟人参与赌场的经营和管理,他们内部有明确的工作分工和上下级关系,他们各司其事,使赌场得以生存和发展,例如:在企业里面有董事长、总经理、各部门经理、出纳、会计等职务;在开设的赌场内也会有赌场设立者、管账人员、发牌洗牌人员、保安、接送赌客的司机等。第二,从赌场的经营状态来看,赌场的经营需要连续性和稳定性,与经营公司的状态相同,而聚众赌博行为则是临时召集,临时商定,不具备这种连续性和稳定性。第三,从获利方式来看,开设赌场并经营类似与我们所说的第三产业,是通过提供服务获得利益,这与经营公司提供服务获利也是相类似的。第四,从开设程序来看,开设赌场与设立公司在设立程序上具有相似性,都具有明确的内部分工,具体的利润分配方案,完善的管理经营制度和早起的经营场所选定。而聚众赌博行为多为松散的赌客临时聚集赌博,并没有如此复杂的设立流程。德国《刑法典》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未经官方许可而公开举办赌博活动,经营赌场或者为此提供赌博工具的,处两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其中,也点名了开设赌场犯罪行为的经营性。
其次,开设赌场行为需具有服务性。赌场经营者正是通过经营这种服务获取收益,聚众赌博行为往往是由召集者临时通知组织赌博,其没有特定的人员从事服务行为,或者仅由参赌人员临时提供一种低层次的服务,召集者和参与者通过自我服务完成赌博活动。而在开设赌场行为中,因具有完整的人员分工,可以为前来赌博者提供一整套服务,赌博者在赌场开设者的组织,管理,服务,控制下参与赌博。赌场开设者也以提供服务的方式从每次的赌博行为中抽取一定比例或者数额的金钱作为报酬,赌场提供的服务越是周到,则参与赌博的人数就越多,则抽取的利润也就越大。
最后,赌场开设者对赌博活动需具有控制性。经营一个赌场必须对赌场内的一切都牢牢控制,否则赌场很难有序稳定的运营下去。对赌场的控制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有明确的赌场经营时间。此时间由赌场开设者加以规定,在赌场的经营时间内,任何人可以进入赌场参与赌博。第二,由赌场提供赌具,制定赌博规则。每位赌客只需携带一定的金钱或者其他财产进入赌场参与赌博即可,不需要准备赌博用具和选择场地,参赌的赌客只能按照赌场预先制定的规则参与赌博,不允许私下更改赌博方式,以维护赌场秩序的统一。第三,赌场获利方式固定。通常包含入场费、每局抽头渔利的费用,或者从赌客所赢取的金钱中抽取分红,这些收费方式都是由赌场开设者控制的。日本刑法学者将“开设赌场”解释为行为人本人成为主办者,在其支配下开设用于赌博的场所”[5]而将“聚集赌徒”的行为解释为召集结合赌徒的行为,也仅仅体现了行为人的召集功能,这其中体现了赌场开设者对赌博活动的支配控制性。
三、建立微信群组织他人抢发红包赌博认定为开设赌场罪的定性分析
作为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产物,在微信社交平台中建立聊天群,邀请好友进群,并招募人员,制定赌博规则抢发微信红包赌博行为在最高院发布指导性案例前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罪名定性分歧,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的《刑法》及其司法解释对赌博罪中的聚众赌博行为与开设赌场行为未做明确的界定。笔者认为在确定微信红包赌博行为组织者罪名时,应当将微信红包犯罪行为与上文中开设赌场的客观要件相联系,将其认定为开设赌场罪。
(一)用于赌博的微信群应当被认定为赌场。
为抢发红包赌博而建立的微信群被认定为赌场原因有其二。第一,从存在形式上分析,微信群是在微信社交平台上申请建立的专属聊天群,是一个数字化的物理空间,通过邀请的方式,人们可以进入该群参与群聊,当群主或者其他组织者在群内制定规则组织赌博活动时,微信群就成为了一个为赌博而存在的专属空间。微信红包群赌客是由群成员介绍进入且需要群主同意进入,这与为了躲避警方侦查,赌客首次进入赌场参与赌博时,往往会受到工作人员的层层盘查行为具有相似性。因此,微信红包群符合了赌场的流动性和开放性的特点,该群就成为了一个供赌客赌博的特定的网络空间。第二,从功能上分析,此种微信群具有实体赌场的功能。实体赌场可以容纳人数众多的赌客参与设立的赌局之中,微信群同样可以。实体赌场有筹码换现金服务,赌客们同样可以利用微信对赌资提现转账,犯罪组织者利用微信群红包的随机性制定赌博规则,在功能上与实体赌场毫无差别。微信群内同样有“代包手”等服务人员为整个赌博活动提供服务,与实体开设的赌场所具有的服务属性毫无差别。从以上两个角度分析,不能因微信群是新生事物在《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未提及其为开设赌场罪中的“赌场”就把它草率的定性为聚众赌博行为。
(二)微信红包赌博活动具有经营赌场的特征
通过上文对开设赌场罪客观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开设赌场罪与赌博罪中聚众赌博行为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开设赌场罪行为人需要具有经营赌场的特征,我们结合微信红包赌博犯罪组织者的行为特征来看,其是完全符合开始赌场罪中经营赌场特征的客观构成要件的,因此,其组织者应当被认定为开设赌场罪。
首先,其具有了类似公司的运营模式。由前文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群主雇佣多人参与到微信群的管理当中,他们分工负责,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有明确的内部分红方案,有特定的人员维持群内抢发红包的正常秩序,如:在群内的“代包手”,拉人入群者,计算营利分红者,等等。其像一个有着完整规章的企业一样,共同参与到微信赌博群的建设当中,使该群的规模不断发展壮大,使赌博违法活动长期稳定的开展下去,具备了经营赌场的类似经营公司的犯罪特征。
其次,该微信红包赌博活动具有服务性。赌博活动的组织者从建立微信群到制定赌博规则,拉人进群,到代发红包,甚至是当有人在赌输后拒不支付下轮红包金额时则也是由该群主补齐,这一系列行为都体现了该赌博活动具有极强的外部服务型,每轮赌博只需要由赌客们凭手速抢红包即可,无需自我服务。因此,该行为是完全符合经营赌场具有的服务性的特征的。
最后,赌博活动组织者对赌博活动具有控制性。微信红包赌博群的经营和管理都是由组织者牢牢掌握的,群内的赌博规则以及每局的抽头数额都是由组织者规定的。参赌人员进入该群必须经过好友的邀请且必须经过群主的同意方可进群,群主也可以将不遵守赌博规则的破坏赌博秩序的赌客踢出该群,每局赌博的发起时间也是由“代包手”掌握,这些都体现了组织者对整个赌场的经营和对整个赌博活动的掌控。并不像聚众赌博那样赌博规则由所有参赌者共同协商确定,召集者对整个赌博活动的掌控能力不强,仅仅起到一个召集作用。微信红包赌博的组织者完全符合了开设赌场罪经营赌场特征的行为人对赌博活动具有极强控制性的特点。
综上所述,如果行为人组建微信群,雇佣人员分工负责,制定赌博规则,对该群内的赌博活动进行管理和控制并具有显著的经营性特征的,都应当被定性为开设赌场罪。
四、结语
2006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第三百零三条做了修改,将开设赌场行为从赌博罪中分离出来,单独构成开设赌场罪,并将最高刑提高到十年有期徒刑,这正是因为开设赌场行为往往聚集的赌博人数众多,且一般赌博金额巨大,该类犯罪行为日益蔓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一般的聚众赌博或者多次赌博以赌博为业行为,在适用原刑法量刑则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6]在微信红包赌博犯罪行为中,组织者雇佣多人,拉人进群,聚众造势,共同推动赌博活动的进行,且不断扩大赌博规模。他们利用微信的时效性和便捷性的特点,几秒钟即可完成一次赌博活动,赌博次数极高,一个微信群最多可以容纳五百人,人数远远多余一般的赌场,涉案赌资数额巨大,抽头数额也相对更多,相比于一般的聚众赌博行为具有更强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应将此行为定性为开设赌场罪,已到达罪刑相适应,遏制此类犯罪案件的发生。
红包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亲朋好友的情感,寄托了长辈的殷切期望,但是目前由于科技的迅速发展催生出了新型微信红包,作为时代进步的产物,它应当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不过我们需要正确的审视和对待时代的新事物。一方面,正确认识和利用微信红包,朋友之间的小额互发行为可以给生活增添乐趣、促进感情、丰富生活,从法律层面分析发微信红包的行为视为赠与行为,一般情况下不会违反法律,但需要切忌不要走上红包赌博之路,不能让微信成为违法犯罪的新领域,要明白以营利为目的建立微信群组织他人抢发红包就会涉嫌犯罪,要知晓利用微信红包参与赌博的危害性;另一方面,正确区分建立微信群组织他人抢发红包的行为定性,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开设赌场罪做出正确的适用。国家也要及时出台司法解释或者刑法修正案对新兴的网络犯罪要素做更明确具体的规定,以保障司法统一,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参考文献
[1]张建,俞小海.建立微信群组织他人抢红包的行为应定为赌博罪[J].中国检察官,2016 (18):3.
[2]罗开卷,赵拥军.组织他人抢发微信红包并抽头营利的应以开设赌场罪论处[J].中国检察官,2016(18):11.
[3]彭磊.如何认定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J].法制与社会,2012(18):250.
[4]周立波.建立微信群组织他人抢红包赌博的定性分析[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20(03):110
[5][日]山口厚.刑法各论[M],王昭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606.
[6]林丹丹.从组织架构谈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的区别[J].中国检察官,2017(16):70.
[7]张明楷.网络时代的刑法理念——以刑法的谦抑性为中心[J].人民检察,2014(09):6-12.
论文作者:宋春燕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9月36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8/8
标签:赌场论文; 红包论文; 赌客论文; 刑法论文; 组织者论文; 发红包论文; 抽头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9月36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