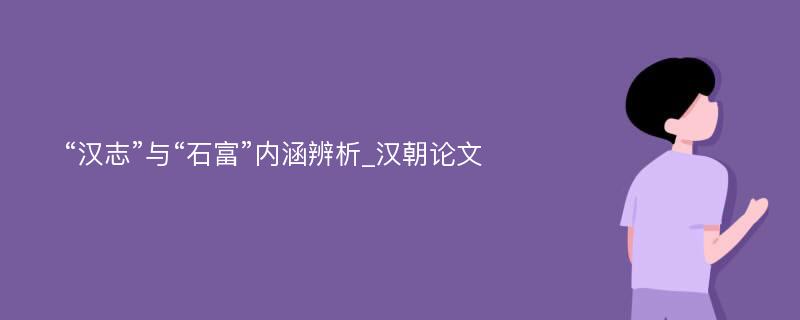
《汉志》“诗赋”内涵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赋论文,内涵论文,汉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1)02-0159-06
《汉书·艺文志》设《诗赋略》,以与《六艺略》、《诸子略》等相区别。因为《汉志》对“诗赋”内涵没有作出明确的界说,又没有标明略内诸种的分类依据,造成后人理解的歧义。
对于《汉书·艺文志》之“诗赋”一略,其分类依据与得失,前人已多所探讨,尤以清人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论列为详。章氏的很多观点,至今仍被治汉代文体学者视为定论。如章氏指出:
诗赋前三种之分家,不可考矣,其与后二种之别类,甚晓然也。三种之赋,人自为篇,后世别集之体也。杂赋一种,不列专名,而类叙为篇,后世总集之体也。歌诗一种,则诗之与赋,故当分体者也。就其例而论之,则第一种之《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及第三种之《秦时杂赋》九篇,当隶杂赋条下,而独厕专门之家,何所取耶?揆其所以附丽之故,则以《淮南王赋》列第一种,而以群臣之作附于其下,所谓以人次也。夫著录之例,先明家学,同列一家之中,或从人次,或从时次可也,岂有类例不通,源流迥异,概以意为出入者哉?[1]1065
这是目前所见《汉志·诗赋略》的现实情况。章氏既肯定《汉志》分歌诗、赋两大类的合理之处,又指出《汉志》在著录体例上略显混乱,并提出己见。对《汉志》的细部疏失,章氏亦有所摘掘,多有见之言。然《汉志》的上述疏略,并不等同于其以为著录根本的“诗赋”观念的混乱。以此为前提,本文重在探讨《汉志》“诗赋”的内涵,而对于作者细部分类与收录的得失,则不予评价。
首先需要指出,“诗赋”作为特定称谓,在汉代文献中较为常见:
文学曰:“《书》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贤之臣,导主志,承君惠,摅盛德而化洪,天下安澜,比屋可封。何必歌咏诗赋可以扬君哉?”
(《文选》王褒《四子讲德论》)[2]2250
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书·礼乐志》)[3]1045
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类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
(《汉书·扬雄传》)[3]3575
薛方尝为郡掾祭酒,尝征不至,及莽以安车迎方,方因使者辞谢曰:“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节也。”使者以闻,莽说其言,不强致。方居家以经教授,喜属文,著诗赋数十篇。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3]3095-3096
左右常荐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歆通达有异材。上(成帝)召见歆,诵读诗赋,甚说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
(《汉书·王莽传》)[3]4018-4019
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
(王符《潜夫论·务本》)[4]19
虽然我们今天无从将上述文献中“诗赋”的具体所指一一落实,但有一点可以明确:“诗赋”在汉代文化语境中作为一个成词,频频出现。《汉志》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下,设“诗赋”一略。
接下来需要探讨的是,《汉志·诗赋略》具体包含哪些文类?从字面及《诗赋略》总序来看,似乎只有两类:歌诗与赋①。然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歌诗,即乐府诗,是和乐的歌词,历来没有异议,而“赋”却颇费后人笔墨。翻开《汉志》,我们看到,赋类中赫然有“《孝景皇帝颂》十五篇”。章学诚对此即表示不满:
《孝景皇帝颂》十五篇,次于第三种赋内,其旨不可强为之解矣。按六艺流别,赋为最广,比兴之义,皆冒赋名。风诗无徵,存于谣谚,则雅颂之体,实与赋类同源异流者也。纵使篇第传流,多寡不敌,有如汉代而后,济水入河,不复别出;亦当叙入诗歌总部之后,别而次之,或与铭箴赞诔通为部录,抑亦可矣。何至杂入赋篇,漫无区别邪?[1]1066-1067
章氏此言,与其对“赋”的理解有关: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徵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1]1064
章氏的观点,基本上承刘勰而来②,虽然将赋的文体渊源溯至《诗经》,但尤其重视战国文化给予赋的温床般的实际影响。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刘勰、章学诚等人将赋、颂予以区别,视为两种不同风格的文体: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文心雕龙·诠赋》)[5]80
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风雅序人,事兼正变;颂主告神,义必纯美。
(《文心雕龙·颂赞》)[5]95
刘勰认为,赋这一文体,主要采用铺叙的手法,体察事物,表现情志;颂作为另一类文体,来源于《诗经》之“颂”,在内容上与风雅相区别,以正面颂扬为主。这种赋、颂两分的看法,在魏晋以后成为主流,如晋人挚虞讨论两汉之“颂”,即与刘、章等人观点相成:
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
(《全晋文》卷七十七)[6]1905
虞氏以语言风格为区分“赋”、“颂”的标准,肯定《安丰戴侯颂》、《出师颂》、《赵充国颂》等与《诗》颂风格接近者为“颂”,而对于《广成》等名“颂”则以为失。上述诸家都强调“颂”的文体渊源于《诗经》,将《汉志》之“颂”等同于雅颂之“颂”。没有考虑到“颂”的体制变迁。
上述看法在汉代也间或存在,然更多时候,汉人并不区分作为文体的赋、颂,而是赋颂连言,视为一类:
(刘安)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3]2145
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汉书·贾邹枚路传》)[3]2366
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杨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
(王充《论衡·定贤》)[7]1117
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戆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者也。(王符《潜夫论·务本》)[4]19-20
班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固数入读书禁中,每行巡狩,辄献赋颂。
(《东观汉记》)[8]675
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是以“赋”名篇之作,然其序文却以对“颂”的探讨为缘由,表明自己为文乃是有所传统:
诗人之兴,感物而作。故奚斯颂僖,歌其路寝。而功绩存乎辞,德音昭乎声。物以赋显,事以颂宣。匪赋匪颂,将何述焉。[2]509
受句法的限制,作者将赋、颂分言,并非以为两种不同的文体。
汉人视赋颂为一类,赋予其相同的语言风格。我们先看《汉志》对于“赋”的讨论: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列为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事,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3]1755-1756
班氏将“赋”分为两种:抒写情志类与铺写物事类,前者由屈原、荀子启其端绪,后者由宋玉、枚马等人定其标格。又根据扬雄的意见,以儒学经义(所谓“则”)为参照,分为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前者的立意与古诗(《诗经》)相接,后者多侈丽闳衍之词,超越经义限度。然无论何种分法,都肯定“赋”之“丽”。“丽”是汉“赋”最重要的文本特征。
丽,指辞采华美、铺张。汉人往往辞赋连言,所言之“辞”,非后世文体之谓,而是与“丽”同义,或以“丽”为其内在构成。《汉书·扬雄传》言扬雄著述之语可用为说明:“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此处之“辞”,正是就辞采而言。“辞”与“赋”在同一语境中出现,前者往往构成对后者的界定。扬雄《法言吾子》:“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正是在此意义上,扬雄区分“诗人”与“辞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史记·屈原列传》之“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亦当如是理解。好辞,即喜欢丽靡之辞,“以赋见称”是“好辞”的必然结果。
就创作而言,汉“颂”虽然立意与风格多样,但莫不以“丽”为归。两汉以“颂”名篇的作品,留存颇多,现将可以考见篇名者排列如下③:《孝景皇帝颂》十五篇、董仲舒《山川颂》,淮南王刘安《琴颂》④、《长安都国颂》⑤,东方朔《旱颂》,王褒《洞箫颂》、《甘泉宫颂》、《圣主得贤臣颂》、《碧鸡颂》,刘向《高祖颂》、《琴颂》,扬雄《甘泉颂》⑥、《赵充国颂》,东平王刘苍《光武受命中兴颂》⑦,黄香《天子冠颂》,崔琦《四皓颂》,傅毅《显宗颂》、《窦将军北征颂》、《西征颂》、《神雀颂》,崔骃《四巡颂》、《北征颂》、《杖颂》,崔瑗《南阳文学颂》,班固《安丰戴侯颂》、《神雀颂》、《窦车骑北征颂》、《东巡颂》、《南巡颂》,贾逵《神雀颂》,杨终《神雀颂》,侯讽《神雀颂》,史岑《出师颂》、《和熹邓后颂》,马融《东巡颂》、《广成颂》、《梁大将军西第颂》、《上林颂》,蔡邕《陈留太守行县颂》、《湖广黄琼颂》、《京兆樊惠渠颂》、《祖德颂》、《五灵颂》⑧,曹朔《汉颂》四篇⑨。我们抽取其中数例来看:
明灵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汉西疆。汉命虎臣,惟后军将。整我六师,是讨是震。既临其域,谕以威德,有守矜功,谓之弗克。请奋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从之鲜阳。营平守节,娄奏封章。料敌制胜,威谋靡亢。岁克西戎,还师于京。鬼方宾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诗》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汉中兴,充国作武,赳赳桓桓,亦绍厥后。
(扬雄《赵充国颂》)[9]224
车骑将军,应昭明之上德,该文武之妙姿,蹈佐历,握辅。翼肱圣上,作主光辉。资天心,谟神明,规卓远,图幽冥。亲率戎士,巡抚疆城。勒边御之永设,奋轒橹之远径,闵遐黎之骚狄,念荒服之不庭……师横骛而庶御,士怫以争先。回万里而风腾,刘残寇于沂垠。
(班固《窦车骑北征颂》)[10]90-91
若夫鸷兽虫,倨牙黔口,大匈哨后,緼巡欧纡,负隅依阻,莫敢婴御。乃使郑叔、晋妇之徒,睽孤刲刺,裸裎袒裼。冒柘,穷浚谷,底幽,暴斥虎,搏狂兕,狱熊,抾封狶。或轻訬趬悍,廋疏岭,犯历嵩峦,陵乔松,履修樠,踔攳枝,杪标端,尾苍蜼,掎玄猨,木产尽,寓属单。罕罔合部,罾弋同曲,类行并驱,星布丽属,曹伍相保,各有分局。矰碆飞流,纤罗络縸,游雉群惊,晨凫辈作,翚然云起,霅尔雹落。
(马融《广成颂》)[11]1962
辞采莫不铺张华丽。就文体而论,第一例颇近于马积高先生所论列之“诗体赋”,后二例造语风格乃至审美取向则与马氏所论列的“文赋”没有不同⑩。而王褒《洞箫颂》、扬雄《甘泉颂》更以赋名见称于当时及后世(11)。傅毅《雅琴赋》,马融亦称为“颂”:“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唯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赋》。”(《长笛赋序》)以前人之“颂”作为自己造作《长笛赋》的楷模。这是作家实践方面显示出赋颂风格的一致性。
汉人不分赋颂的更为切实的依据是,其论汉“颂”,亦以“丽”为言:
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颂文谲以奇,彰汉德于百代,使帝明如日月,孰与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论衡·须颂》)[7]854
谲奇,指语言与取物用事的奇谲瑰丽,亦即扬雄所谓的“丽以淫”。面对大量的汉代颂作,即便是主张区分“赋”、“颂”的刘勰也不能回避两者表现手法的相同:
原夫颂惟典懿,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虽纤巧细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
(《文心雕龙·颂赞》)[5]96
“敷写似赋”,亦即后文的“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都是对“颂”之“丽”的展开之语。李善注《文选》陆机《文赋》“颂优游以彬蔚”句也说:颂以褒述功美,以辞为主,故优游彬蔚。[2]766
“以辞为主”,即以追求文辞之丽为主。这都是基于以汉“颂”为主的实际创作得出的结论。
以“颂”为“赋”的归类方式,肇端于屈原,至汉代成为普遍认识。屈原《九章·橘颂》其实就是一篇咏物赋。虽然屈原并未以“赋”为称,汉人则以之为“赋”类。《汉志·诗赋略》列“屈原赋二十五篇”,顾实《讲疏》:“今《楚辞》,《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三篇,凡二十五篇。”[12]166其他诸说虽略有出入,但以《九章》此篇入此二十五篇之数则没有异议。王逸《楚辞章句》正是以此为基础,探讨屈作与后人仿作之旨:
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闇蔽,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九辩序》)[13]182
至刘向、王褒之徒,咸嘉其(指屈原)义,作赋骋辞,曰赞其志……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裨其辞。(《九思序》)[13]314
直称《九歌》、《九章》、《九思》等为“颂”。又说刘向、王褒等人嘉屈原之义,“作赋骋辞”,复言自己仿刘王等人之作为“颂”,在概念的使用上,看不到赋、颂之间的任何界限。
综上,可以说,就汉代作家的实际应用而论,“赋”、“颂”实无差别。班固的《两都赋序》以赋家身份总结西汉“赋”作的立意与功效:“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已将一般经学家所言的“美盛德”的“颂”包括在“赋”内。然需要指出,赋、颂浑言虽无别,析言则有异:“颂”以其古老的渊源,获得“美盛德之形容”的经学立意,而赋在经学视阈下,被视为“童子雕虫篆刻”(《法言·吾子》)、“淫靡不急”(《汉书·王褒传》)之事。这样的结果便是在经学极盛的东汉时期,出现大量的以“颂”为题之作。这或可看作是经学于文学构成影响之一迹。重视“辨章学术,考竟源流”的章学诚等人对于“赋”、“颂”的不同理解,从某种角度看,正是汉代以来经学态度的折射。
至此,我们可以明确:就汉人(尤其是汉代作家)的识见,“赋”、“颂”并无明显区别。既然如此,那么将以“颂”为题的作品置于“赋”下,就是顺理成章的事。继踵而生的问题是:《后汉书·文苑传》、《文心雕龙》所论列的“箴”、“铭”、“赞”、“论”等文体是否也应涵容于“诗赋”范畴之内呢?章学诚《校雠通义·内篇三》的一段文字即由此而发:
道家《黄帝铭》六篇,与杂家《荆轲论》五篇,其书今既不可见矣……《荆轲论》下注“司马相如等论之”,而《文心雕龙》则云:“相如属词,始赞荆轲”。是五篇之旨,大抵史赞之类也。铭箴颂赞,有韵之文,例当互见于诗赋。[1]1049
章氏注意到《汉志》“诗赋”范畴的内涵大于“歌诗”与“赋”两种文类的简单叠加,这自是章氏的卓识之处。然其认为应该于《诗赋略》的“歌诗”、“赋”两种之外,别列一种,以纳“铭”、“箴”、“颂”、“赞”等,则颇可商榷。近人章太炎先生的意见稍有不同:“其他有韵之文,汉世未具,亦容附于赋录。”[14]71章先生将“赋”视为有韵之文,故将“赞”、“铭”、“箴”等文类都归于其中,主要依据是《诗赋略》总序“不歌而诵谓之赋”之语。但《汉志》此语并不必然得出“凡不歌而诵者俱为赋”,换句话说,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有韵之文都应附于“赋”类。
二章的认识非《汉志》之意,这在《汉志》中可以找到内证。扬雄的箴类作品,《汉志》明确将之列为儒家。《汉书志》“诸子·儒家”有:“扬雄所序三十八篇。”班固自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箴》,即《后汉书·胡广传》所云之十二《州箴》与二十五《官箴》(12)。是《汉志》不以“箴”为“诗赋”(13)。
“铭”与“箴”略同。《文心雕龙·铭箴》总结前人之作说:“夫箴颂于官,铭题于器,明目虽异,而警戒实同。”这主要是基于汉代及汉代以前的铭、箴得出的结论(14),则铭、箴异名而同用的认识为汉人所固有。既然“箴”被斥在“诗赋”之外,“铭”亦应被如是看待。将蔡邕的《铭论》与《汉志》结合起来考察,尤能助成我们的结论:
春秋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昔肃慎纳贡,铭之楛矢,所谓“天子令德”者也。若黄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盘盂之诫,殷汤有甘誓之勒,毚鼎有丕显之铭……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在宗庙两阶之间。近世以来,咸铭之于碑。德非此族,不在铭典。
(《全后汉文》卷七十四)[6]875-876
据此,蔡邕将《孔甲盘盂》视为铭。《孔甲盤盂》,《汉志》则入“诸子·杂家”:“《孔甲盤盂》二十六篇。”《诸子》“道家”类又有“黄帝铭六篇”。是《汉志》亦不以“铭”为“诗赋”。
再有“赞”、“论”。《汉志》“诸子·杂家”有“荆轲论五篇”,班固自注:“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文心雕龙·颂赞》则曰:“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15),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刘勰此言,当是承前而来,则《荆轲论》即《荆轲赞》。这种等同下面有一潜在的认识,即“论”、“赞”无别,同属史论,列“杂家”,不当在“诗赋”之列。
《诗赋略》不录“箴”、“铭”、“赞”、“论”,这说明上述文类在《汉志》成书的时代,相较于“诗赋”而言,属于应用性论说性文体,以警戒教化等伦理政治功用为主,尚未流入“降及品物,炫辞作玩”(《文心雕龙·颂赞》)的逞才之域,而与丽辞之赋颂构成根本区别。与“箴”、“铭”、“赞”、“论”相类者,诸如“诔”、“碑”等亦应如是看待。
尚需讨论的是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见《汉书·韦贤传》)等不入乐的汉代文人诗,从其题名为“诗”来看,当入《诗赋略》,然《汉志》未收。仅凭《汉志》线索,我们无法得知《汉志》作者的态度。然从相关的资料入手,则可以为上述作品作一定位与归类。
在明确我们的观点之前,需要指出,先秦荀子在其《赋篇》中收入《佹诗》,说明先秦时,“赋(颂)”就有较广的指称区域。西汉或承此,将诗归于赋类。被《汉志》归入“赋”的楚辞体作品,汉人或以“诗”为称:
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属诗。(庄忌《哀时命》)[13]259
舒情陈诗,冀以自免兮。(刘向《九叹·远逝》)[13]295
既然不歌而诵的“赋(颂)”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涵盖了“诗”,上列韦氏作品自然可以归于“诗赋”之下。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知道,在《汉志》乃至《汉志》前后的时代,“诗赋”并非仅指两种狭义的文体,而是数种文类(歌诗、文人诗、赋颂等)的合称,有较为明确的内涵:在内容上以体物态写情志为主,文辞上有美丽夸饰之观,以游意娱情为目的,而具有较强现实伦理政治功用的作品如箴、铭、赞、论等则不在此列。
注释:
①此处之“赋”,取其狭义,即六朝以后人们所通常认为的某种特定文体,如刘勰所谓“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赐名号,与诗画境,六艺附庸,蔚成大国。述主客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文心雕龙·诠赋》)。现代学者马积高先生所论近之,而角度不同:“赋是一种不歌而诵的文体,它既不包括具有某种特定社会作用的不歌的诗体如箴、铭、颂等,也不包括具有某种特殊社会作用的韵文如诔,祭文(有韵者)等(但吊文多是赋),更不包括后起的五七言诗。”(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②《文心雕龙·诠赋》:“诗有六义,其二曰赋……班固称古诗之流也……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
③按,未标明出处者,俱见万光治《汉赋通论·附录:汉赋今存篇目叙录》,巴蜀书社1989年版。
④《汉志·六艺略》“乐”类小序“凡《乐》家,百六十五篇”下,班固自注:“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
⑤《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初,(淮南王刘)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祕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
⑥王充《论衡·谴告》:“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
⑦范晔《后汉书·光武十三王列传》:“(明)帝以所作《光武本纪》示(东平王)苍,苍因上《光武受命中兴颂》。”
⑧《全后汉文》卷七十四辑蔡邕五颂(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874-875页)。
⑨范晔《后汉书·苏顺传》:“又有曹朔,不知何许人,作《汉颂》四篇。”
⑩马积高先生根据赋形成的三种不同途径,将赋分为基本的三类:骚体赋、文赋、诗体赋(《赋史》,第4-6页)。
(11)王褒《洞箫颂》,《文选》作《洞箫赋》;扬雄《甘泉颂》,《汉书》本传称为《甘泉赋》:“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其辞曰。”
(12)《后汉书·胡广传》:“初,杨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
(13)今本《汉书·陈遵传》:“先是黄门侍郎扬雄作《酒箴》以讽谏成帝,其为文云云。”传文所云《酒箴》,后世多题为“赋”。严可均《全汉文》卷五十二:“案:《汉书》题作《酒箴》,《御览》引《汉书》作《酒赋》,各书作《酒赋》。《北堂书钞》作《都酒赋》。”(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408-409页)扬雄此文从形式上来看,为赋属,且与其它州、官诸《箴》全然不同。今本《汉书》名其为“箴”,或是传写之误。
(14)《文心雕龙·铭箴》所论列的铭箴作品,从上自黄帝刻舆几,下迄晋张载《剑阁铭》,共二十余篇,只有魏文帝《九宝》、张载《剑阁铭》二篇为汉代以后作品,其余均为汉代以前及汉代作品。
(15)所谓“纪传后评”,即《史记》、《汉书》纪传末尾的评语,其领起文字为“太史公曰”、“赞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