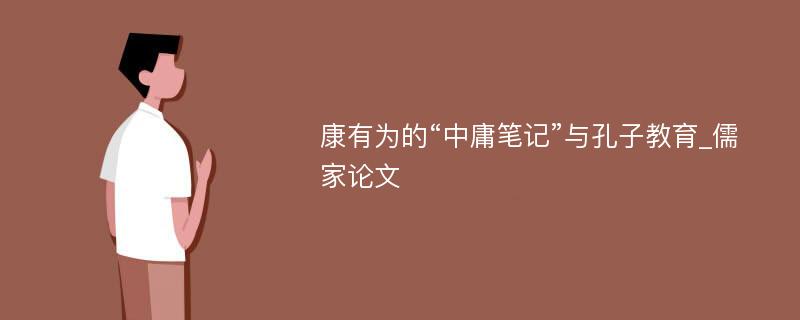
康有为的《中庸注》与孔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庸论文,康有为论文,孔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4)04-0108-08 康有为于流亡海外的1900—1902年间集中注解了一批儒学经典,“四书”就在其中①。康氏后来屡次提到这批注解,特别是在1912年致信陈焕章并鼓动他主持孔教会时说“吾注有《礼运》、《中庸》、‘四书’、《春秋》及《礼记》选,可以宣讲,发明升平、太平、大同之义,令人不以君臣道息而疑孔教之不可行”②,自信其注解可在君主制已废除的新形势下宣讲孔教。康氏的自信源于他对儒学的重建可使儒学获得新的生命力。萧公权也指出,这批注解是“康氏经由研治古经、佛学、西学以及改革与流亡之余而想重建儒学的一个结果”③。因此,深入研究康氏的这批注解,对于把握其孔教思想非常重要。 本文无意于全面考察这批注解,仅以《中庸注》为对象,从康氏的注解意图出发,分析康氏引进《中庸》的新内容及其目的,以此探讨康氏重建儒学的一些努力。 一、注解意图 对于康有为此期注解大批儒经的目的,有论者断定康氏是为了使“他的论点可以更加突出和可信”④,或者“乃是要缓解他与普通士林文化之间的紧张”等⑤。这些论断似乎忽略了一个史实:除了《孟子微》的部分篇章外,其他注解均在民国后出版。如果康氏仅是要使人相信其学说,按理来说应该尽快出版这批注解,但康氏有此条件却没有这样做。同时,这种理解偏于从消极面理解康氏。揆之撰注时的处境及其蓄意,康氏应含有积极的深意。《中庸注》就如此。 康有为注解《中庸》,自言始于“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一年”(1900),成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当时康氏流亡到槟榔屿,自言“蒙难艰贞”⑥。康氏此时处境确实不佳。据其女康同璧记载,“先君经戊戌、庚子之难,积忧多病”,身体不佳,因而她“闻讯特来槟侍膳”⑦,后来还因槟榔屿不适养病而陪赴印度。在这种情况下,康氏执意注《中庸》,如果没有强烈的动机支撑,恐难以想像。 而且,康氏自言在广州讲学期间曾注解《中庸》⑧。这是否确切,由于康氏戊戌前的注解未见,难以确证。从现存的广州讲学笔记来看,康氏曾专门论及《中庸》,内容与后来的《中庸注》有一致之处,如将《中庸》看作是孔子行状等,但相异之处甚多,如“三世”、“三统”、鬼神等问题⑨。两相比较,不管此前有否注解,后者远非简单的“润色夙昔所论思,写付于世”⑩,不妨将《中庸注》视为新作。 虽然康氏对《中庸》的看法前后有变,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传统的《中庸》注解不满已久。虽然如此,如果从经学立场来看,康氏不一定非注解《中庸》不可。康氏1890年后宗今文经学,在中学方面主要得益于以《春秋》和《易》为主的经学。《中庸》虽是《礼记》中的一篇,但由于理学的表彰,已脱离《礼记》单行,成为“四书”之一。尽管“四书”与今文经学不必河水不犯井水,康氏也不必急着非在此时注解《中庸》。对此,康氏提供的解释是:《中庸》是孔子学说的精华所在,是子思所作的“孔子之行状”(11),关系到“孔子之大道”、“生民之大泽”。尽管前人有注,但“恨大义未光,微言不著”,因此要用“孔子改制之盛德大仁”阐发《中庸》(12)。这一解释未必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中庸》固然重要,《五经》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康氏多次提到《易》,也认为《礼记》中的《王制》《儒行》非常重要,但都未作注(13)。如此看来,《中庸》的重要性仅是其中一个因素。如果联系其稍后注《孟子》《大学》《论语》,康氏以“四书”为目标的意图清晰可见。《中庸》是作为“四书”之一而被注解。显然,康氏的矛头直指朱子。 康氏早就对朱子有所不满:早期的《教学通义》就批评朱子“惟于孔子改制之学,未之深思,析义过微,而经世之业少,注解过多”(14),万木草堂讲学时批评朱子“不治《春秋》,而但言义理,于孔子之道,只得一半”、“少言制度”、“得经学尚少”等(15)。具体到《中庸》,康氏认为“宋儒发挥《中庸》最透,然于孔子之道无焉”、“宋儒言《大学》最有功。言《中庸》、《系辞》已入佛理”(16)等。这些都表明康氏认为以朱子为代表的宋儒并未深解“孔子之道”。《中庸注》沿袭了相关批评,指出“宋、明以来,言者虽多,则又皆向壁虚造,仅知存诚明善之一旨,而遂割弃孔子大统之地,僻陋偏安于一隅”(17)。以朱子为代表的心性义理之学只抓住了“存诚明善”,不明孔子改制,故而未能使孔子之道发扬光大。但“僻陋偏安”并非一无是处,“大统之地”当然包括宋明理学的“一隅”。这透露出康氏并不准备全盘反对朱子,故而注中沿用不少朱注,但其进路与朱子有很大差别。这突显出康氏要重建儒学的意图。 事实上,康氏很早就有重建儒学的想法,早年与朱一新论学时已提出一个卫教计划。计划分三步走,首先辟伪经,其次阐明孔子改制,再次发孔子微言大义,其中包括“七十子后学记”(18)。第一步对应于《新学伪经考》,第二步对应于《孔子改制考》,这两步在戊戌前已经完成;第三步则大致对应于注解其他儒家经典。康氏当时并未言及“四书”。而以“四书”为目标,主要是因为“四书”“元、明至今,立于学官”(19),属官定科举教材,已成为一般士人的必读书目,其影响非同一般。 康氏在民国后也一再申明重建儒学之意,如:与日本人的笔谈中,康氏说“吾所著发明孔教之书,有《孔子改制考》、《伪经考》、《论语注》、《中庸注》、《孟子微》,又《春秋微言大义考》,又《春秋董子学》”(20);在长安讲演中,康氏说:“然则虽知孔子之教,当知《春秋》三世之义,当知《礼运》大同之说……吾有《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论语注》、《中庸注》、《孟子微》,皆发此义。庶几孔教可兴,大同之治可睹,而诸君尊孔之心为之大慰。”(21)虽然这些撰述在前,但康氏自信其重建工作能超越形势的变化,故而在科举被废除、民国成立的形势下仍能发挥宣扬孔教的作用。当然,由于民国后经学失去了制度支撑,“四书”的作用也不如往昔(22),但作为孔教思想的阐发,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上可见,康氏此期注解儒经(包括《中庸》)的意图并不消极,而是要重建儒学,“复明”孔教的“大统之地”。这一强烈的动机支撑着康氏在策划庚子勤王失败后迅速投入到注解儒经的大业中。 康氏重建儒学,其理论支柱无疑是孔子改制。但这只是总宗旨,落实到具体文本,阐述重点并不相同。在《中庸注》中,康氏认为子思阐述了孔子的“盛德至道之全体”,也就是“原于天命,发为人道,本于至诚之性,发为大教之化,穷鬼神万物之微,著三世三统之变”(23)。康氏对《中庸》的概括,正是其在注解中特意要阐明的内容。其中,“人道”、鬼神、“三世三统之变”最能反映康氏孔教的理论特色,故而值得关注。 二、“人道” 康氏关于孔教是“人道”的阐述,主要集中在《中庸注》的前半部分,主旨是将孔教立基于“人道”之上。康氏所说的“人道”,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人道价值,而是指顺应自然人性的世俗生活。 对于开篇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句,朱子在《中庸章句》中用理来贯通天—性—道—教。在形式上,康氏也贯通四者,认为“孔子教之始于人道,孔子道之出于人性,而人性之本于天生,以明孔教之原于天,而宜于人也”(24)。但是,在性、道的理解上,康氏与朱子的心性进路差距甚远。 对于性,康氏认为是“生之质也,禀于天气以为神明,非传于父母以为体魄者,故本之于天”(25)。康氏持灵魂、形体二分的观念(26),性即指由“天气”构成的“神明”。此处的“天”不是道德修养的最终依据,没有道德意味,而只是指向人天生具有的相同本质,亦即相同的行为、欲求等。在此解释下,性是人的自然本质,没有善恶之分。性“未有善恶”是康氏一直坚守的立场(27)。这一立场从训诂看性,大体是受乾嘉汉学与西学自然人性论的影响,近于董仲舒,而远于宋明理学。 对于道,康氏注为“可行之谓,尚多粗而未精”,但在稍后的注中补充道:“犹路也,人身出入动作由之,无离乎路者”。这是从人的世俗生活需要遵循的角度来解说道,因而“非人所共由,不谓之道”。这是为随后的排斥外教作准备。由性、道出发,“人道”就成了“人性之有交接云为无离之者”(28)。“人道”基于人性,涵括人的活动范围,“无离”源于道的可行、必行。这是从人的自然本性来看,并非着眼于道德价值。 顺应着道是人性的交接,“人道”的具体内容就是:“自形上言之则为阴阳,自继成言之则为善性,自形下言之则为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皆人道之不可离也。”(29)形上的“阴阳”取自于《易》,不涉善恶问题;“自继成言之则为善性”,这是要导引人向善;形下内容则是儒家的五伦。为强调儒家伦常关系,康氏在注解中不惜采用变更经文顺序的办法来配齐五伦。经文“亦勿施于人”后原接“君子之道四”,但只讲了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四伦,缺少了人类生活最重要的夫妻伦常。而在康氏眼中,夫妻是人道之始,“孔子之道,造端乎男女饮食”(30),不可或缺。因此,康氏将“君子之道,辟如行远……父母其顺矣乎”提前,给出的理由是这章“在‘素位’章下,‘鬼神’章上,于义不伦”(31)。实际上,康氏看中的是经文中所引的《诗》提到夫妻关系,提前后就能凑足五伦,使儒家的“人道”圆满。这是康氏《中庸注》中变更经文的惟一一处。但是,康氏避开了“三纲”,这是因其持强烈的平等观念(32),但“三纲”毕竟是王朝的核心纲常,不宜公开抨击,故避而不谈。在后续的注文中,康氏所说的“人道”形下内容更宽,把饮食、日用都囊括其中,泛指一般的世俗生活(33)。尽管“人道”所指的范围宽窄不同,但都以儒学作为范本。由此,越出儒学伦常范围之外的就是“非人道”:“故舍阴阳、善性、父子、夫妇、君臣、兄弟、朋友,亦有以为教者矣。然或爱奇好癖之人,行之非人人所共由,即非人道也。”(34)这样处理的目的之一,就是确立儒学,排斥异教。 康氏用是否顺应人的世俗生活来判分教派的差别,可追溯至早年的《康子内外篇》。当时,康氏根据阴阳将世界各种不同的教分为阴教和阳教两种:阳教指“孔氏之教”,特点是“顺人之情”,与世俗生活紧密联系;阴教指“佛氏之教”及耶稣、马哈麻、一切杂教,特点是“逆人之情”,有戒肉、不娶、反对鬼神、崇拜教主的行为(35)。《中庸注》中的“人道”承接早期的“阳教”而来。 然而,何以孔教是“人道”并且独尊?康氏对此进行了解释。他将教的性质与创教者直接联系起来,认定创教者的性情决定了教是否偏失:“创制者喜怒哀乐之本性有偏,则喜怒哀乐之发情有戾。于是施行之而为道教,即不能无畸轻畸重、毗刚毗柔之失。”“故君子欲为道教之发施,先养性情之本原。”(36)这样,问题就转换为阐述创教者孔子的品性。 但是,《中庸》里有论述孔子的品性吗?按照通常理解,《中庸》讲修德问题,并非专述孔子的品性。但是,康氏认为《中庸》集中论述了孔子的品性,其理解借助于郑玄的注。郑注在解题时说,《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37)。依此,康氏将《中庸》看作是“孔子之行状”,将文本中的“君子”看作专指孔子(38),经文便变成了孔子品性的记述。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句,康氏注为“此孔子保合天生之性,洗藏于密,养成神明,以为发教之本也”(39)。通过这一定位,孔子就具有了《中庸》所说的“戒慎恐慎”、“慎独”、“中和”等品性,因而“惟孔子之性情能得中和之极,故孔子之道教亦得中和之极,而可配天地、本神明、育万物”(40)。这样,孔教就由于创始人孔子的品性而超拔于诸子所创的教派之上。 确立了孔教的地位后,康氏对诸子等外教进行了批评。如以“中庸”为据,批评外教有“偏邪”。但这些批评通过曲解经文来实现,如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的“君子”定位为“从儒教中人,履中庸之道者”,“小人”则为“背儒教之徒”;“民鲜能久矣”的“民”曲解为“当时诸子之徒”。由于教派很多,康氏提请要用智来“辨道教之美”,遵行中庸之道,不为异教所诱(41)。在另一处注解中,康氏注:“故孔子之道,因于人性有男女、饮食、伦常、日用而修治品节之。虽有高深之理、卓绝之行,如禁肉去妻,苦行练神,如婆罗门九十六道者,然远于人道,人情不堪,只可一二畸行为之,不能为人人共行者,即不可以为人人共行之道,孔子不以为教也。”(42)从中可见康氏借“人道”来排斥外教、独尊孔教之意。 康氏要判分孔教、诸子等外教,有其特有的问题背景。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氏以上古“茫昧无稽”为起点,让诸子和孔子一起托古创教改制,形成了教派竞争的局面。这与廖平等今文学者专断地认定只有孔子有创制立法的资质不同(43)。按照康氏的解释,孔子失去了创教立制的专权,这使独尊孔子成为问题。尽管《孔子改制考》对此曾有所解释,如诸子“各因其受天之质,生人之遇,树论语,聚徒众,改制立度,思易天下。惟其质毗于阴阳,故其说亦多偏蔽,各明一义,如耳、目、鼻、口不能相通”,而孔子“积诸子之盛,其尤神圣者,众人归之,集大一统,遂范万世”(44),也提及“然圣道至中,人所归往,偏蔽之道,入焉而败”(45),但并不集中。康氏在《中庸注》中要重新处理这一问题,一方面是企图借助《中庸》文本来完善他的理论,使人信服;另一方面则在于“四书”毕竟自成一系统,需要在此系统内阐明此意。这就使《中庸注》呈现出既正面肯定孔子的品性、又强烈排斥外教的特点。 康氏为了阐发孔教是“人道”,以致《中庸注》思路奇特。康氏何以要选择“人道”来提升孔教、排斥外教?儒学本身重视世俗生活是其中一个大原因。儒学的这一特点,易于将它与其他教区别开来。但是,仅据此来理解康氏,可能还不够。康氏要以“人道”作为基础,还涉及其“不忍之心”、去苦求乐的人性观以及对历史发展趋势的看法。“不忍之心”使康氏确立救助世人的宏大目标;而去苦求乐的人性观使康氏深悉普通人更乐于接受顺应自然人性的生活;从《公羊传》悟出的“三世”说,使康氏认定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向是顺应“人道”,亦即满足人的自然欲求。这些因素使康氏作出断定:“循人之性以为道,故人人所乐行而不可去。”(46)如果将孔教深植于“人道”,显然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使其在未来继续指导人们的现实生活。 三、鬼神 康氏将儒学立基于“人道”的同时,也从报应的角度突显了儒学的鬼神。 康氏的逻辑是借助于《中庸》的命引出“报”,由“报”再突显出鬼神。“君子素其位而行”章的注文就体现了这一逻辑。康氏从“君子素位而行”入手,得出富贵贫贱皆有命,而命有其造因。康氏引用《孝经纬》指出,命是出于善恶的报应。而报应可分为两类:“《京氏易说》有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归魂游魂,故宿世造善恶之因,而今世受报。此传于魂者也。《系辞》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祖宗善恶之因,而子孙受报。此传于气者。”(47)前者是通过魂报应于现世的个人,后者借助于气报应到子孙。在这两类报应中,康氏最重视前者。 由于“君子之道,辟如行远……父母其顺矣乎”章被提前,康氏便可以借紧接着的“鬼神之为德”章来说明魂的问题。康氏从文字学的角度说“鬼从人从脑,魂气上升之形”,再引用《礼记》为据,将魂分为神、鬼两类。大体而言,鬼是一般的魂气,而神则是其中的精气(48)。这样,《中庸》中的鬼神被突显出来。康氏进一步阐明鬼神、命、“报”之间的机制:一方面,受报、受禄的轻重有不同,这由天来决定;另一方面,又借用所获得的科学知识,认定鬼神、命、“报”之间是出于电的吸引作用而实现。前者是为了解决具有大德之人在当世何以有圣人、天子的不同受命;后者则是一般机制,借助于电的作用来说明“报”的真实性。不过,康氏本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清晰,只笼统地说:“其理虽玄冥,而电气魂知相引相感,其来极远,皆有所因。虽迟速有时,错综不同,而为善必报,大德必受命。不于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而报之,亦必于十、百、千、万世而受之。至于报时,前因尽发。故合而算之,大德亦无不受命,大恶无不受报者。”(49) 康氏在《中庸注》中对鬼神及报应的说法并不令人信服,只是借用了电的作用使报应机制带有一丝科学的味道。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十分牵强。在此不讨论其细节,但其动机值得探讨。 就文本而言,鬼神在《中庸》中与“报”、慎独等相联,带有较强的实存味道。宋明理学基本立足于哲理来解释鬼神,抹去了鬼神的存在及其报应作用。如朱子《中庸章句》就说:“愚谓以二气言,则鬼者阴之灵也,神者阳之灵也。以一气言,则至而伸者为神,反而归者为鬼,其实一物而已。”(50)鬼神主要被看成气的功能。但《中庸章句》未对“大德必受命”下断语。不过,在《朱子语类》中,朱子并不认为“大德必受命”具有必然性,而是以“常理”与“非常理”的区分来化解受命带有的偶然性,不需借助鬼神的报应作用(51)。从经文的脉络来看,朱子的解释不算圆融。康氏突显鬼神的报应作用,可能更符合经文的意思。但康氏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使解释更加圆融,在一段注文中康氏引用《礼记·祭义》透露了其用意: 孔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魂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孔子意也。佛氏专言鬼,耶氏专言神,孔子兼言鬼神,而盛称其德。惟程、朱以为天地之功用,张子以为二气之良能,由于阮瞻《无鬼论》来,于是鬼神道息,非孔子神道设教意也。太古多鬼,中古少神。人愈智,则鬼神愈少,固由造化,然其实终不可灭也。(引者按:此段的标点符号略有校改)(52) 康氏的用意有二: 第一,在康氏看来,圆满意义上的“教”,应该讲“鬼与神”。就此而言,佛、耶均有所偏蔽,只有孔子兼言两者,表明儒学高于二者。康氏无疑欲借鬼神问题压抑佛、耶,突显孔教的圆满。这种想法在其万木草堂讲学时期就已经提及(53)。 第二,重申“百众以畏,万民以服”这一神道设教的用意。康氏的注文说:“故人生世世,当慎其造因之微,而积其仁德之诚也。”(54)用鬼神来约束人的行为,贯穿于此期康氏的注解。如稍前的《礼运注》说:“至山川五祀,孔子何为不除去之?盖山川为怪物所聚,门、户、溜、灶、行,为人身所切,耸以鬼神,著其监司功过,而后动人知畏敬,不敢妄为,以迁善远罪。”(55)稍后的《论语注》也说:“如以神道设教,则民以畏服。若明言鬼神无灵,大破迷信,则民无所忌惮,惟有纵欲作恶而已。故可使民重祭祀,而鬼神之有无生死,不必使人人知之。”(56)基于此,康氏批评宋学从哲理上处理鬼神是不明孔子神道设教的用意。然而,康氏也知道迷信会带来害处,所以对此作了限制,提出以实据作为根据:“谶记之说,灾祥之论,卜相之事,窈异恍惚,不尽可信。而前知之理,盖实有之。经史传记,繁不胜征。”(57)这与早年《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以“实测”作为祸福是否可信的标准一致(58)。这一标准显得颇为奇特。而且,如果要让鬼神起作用,需要预设鬼神的存在。引文中说“人愈智,则鬼神愈少,固由造化,然其实终不可灭也”,这是偏于承认鬼神的实存,尽管随着人智力的提高而变少。但稍后的《论语注》却一反此调,说“盖怪、力、乱、神者,皆乱世之事,至太平之世,则不独怪、力、乱无,即神亦不神也”(59),又偏向于鬼神的不存在。这种暧昧不清的说法,反映出康氏的理性与鬼神迷信的矛盾心态。 除了“迁善远罪”等劝善作用外,康氏突显儒学的鬼神还有一层考虑,就是儒学的传播问题。《孔子改制考》曾说:“角祖张道陵者也,为老学一变。有跪拜,有符咒,有疗病,变老子之虚而为实,遂大盛于晋世……盖言术而不言道,故不光大,否则为中国之天主矣。张角于老学化精为粗,而老学强;慧能于佛学撇粗归精,而佛学衰。何哉?盖人为血气之躯,本不能与于精绝之道,故诸教之大行者,莫不精粗并举,而粗者乃最盛行,亦可推其故矣。”(60)康氏观察到普通民众对鬼神等具有实际功用的“粗者”更在心。这一观察无疑有事实依据,哲理化的解读更多的是引起精英分子的兴趣,但普通民众更加在意“效验”与“灵验”问题(61)。康氏的目的是希望借助突显鬼神,让儒学对普通民众更具号召力,使它能对抗基督宗教。这并非康氏的独创,至迟晚明时已有人作过这种尝试(62)。康氏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作尝试。 四、“三世三统之变” “三世三统”说是康氏颇为自得的创见,《中庸注》对此着力颇多。叙中说“后进承流守旧,画地自甘,不知孔子三重之道通变因时、并行不悖之妙”,他本人要阐明“三重之圣德”(63)。康氏此处用“三重”而不用“三世三统”,不只是用词的变化,而是受经文启发所作的理论深化。 “三重”来自于《中庸》“王天下有三重焉”,康氏对这段经文的注解别出心裁: 孔子世,为天下所归往者,有三重之道焉。重,复也……三重者,三世之统也。有拨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拨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时,内外远近大小若一。每世之中,又有三世焉。则据乱亦有乱世之升平、太平焉,太平世之始亦有其据乱、升平之别。每小三世中,又有三世焉;于大三世中,又有三世焉:故三世而三重之,为九世;九世而三重之,为八十一世。展[辗]转三重,可至无量数,以待世运之变,而为进化之法。此孔子制作所以大也。盖世运既变,则旧法皆弊而生过矣,故必进化而后寡过也。(64) 在传统注解中,“三重”主要有两种解释:第一,以郑玄、孔颖达为代表,指三王之礼(65);第二,以朱子为代表,指议礼、制度、考文(66)。康氏对“三重”的注解,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继承之处是采纳了第一种注释,将“三重”看作三统,这与其万木草堂讲学时期盛赞郑注相同(67);创新之处是在此基础上,借助于“重”的多义,将它释为“复”。而“复”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时间的纵向重叠,亦即每一世下再不断地用三世来重叠划分,这样可以形成“无量数”的世态;二是空间的横向重叠,即同一时间内,可以有不同的世态并存。经过两种重叠之后,“三世”说就从原来三阶段的机械系统变成一个开放的系统,具有了更强的解释力:纵向重叠形成不同的更小世态,可以更加细化地说明各国发展程度的具体差别,这在原来简单的“三世”说里无法做到;横向重叠使得不同的世态可以并存,可以说明各国及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如注文中用以说明苗、猺、黎、狪等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的文明程度不同但在中国并存。“三世”说深化为“三世三重”后,更易于解释世界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但“三统”的作用也被削弱了。尽管注文仍强调“三统”的作用,但就理论而言,“三统”已属多余。因此,康氏后来的重心就偏向单言“三世”说(68)。伴随“三世三重”的出现,社会进化的进程被减缓,康氏可以随心所欲运用这一历史观对现实加以说明。这也成为后来康氏既反对革命派又反对保守派的理论武器。 由此看来,康氏将“三世三统”说发展为“三世三重”,是在自觉地完善其历史观。 “三世”说作为康氏的自得之学,用来重建孔教实属必然。但仅仅如此理解,实未能体会其用心。康氏深明世界不断进化,如果孔教没法跟上发展,就不能指导现实生活,衰微将不可避免。这是康氏不想看到的局面。因此,康氏要使孔教能跟上历史发展过程,就必须要使孔教笼罩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这样,孔教就需要包容“三世”说并以此为框架进行重建,因为“三世”说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基于此,就可以明白何以后来康氏一直强调“三世”说是孔教命脉之所在:如1913年底致信廖平说“仆……既信史公而知古文之伪,即信今文之为真,于是推得《春秋》由董、何而大明三世之旨,于是孔子之道四通六辟焉”(69);1920年与日本人的笔谈中,康氏说“今所最要明者,是三世之义”(70)。只有容纳了“三世”说的孔教,才可以做到“四通六辟”,不用担忧其衰微。到了太平世:“至于是时,孔子三世之说已尽行,惟《易》言阴阳消息,可传而不显矣。盖病已除矣,无所用药,岸已登矣,筏亦当舍。故大同之世,惟神仙与佛学二者大行。盖大同者,世间法之极,而仙学者长生不死,尤世间法之极也。”(71)人类社会政制到了大同就已经到了终点,孔教需让位给仙、佛学及所谓的天游之学。从中可以看出,康氏将儒学定位为“世间法”,偏重于儒学维系社会政治秩序的功能。从终极意义上看,康氏似乎很难说是一位虔诚的儒学信徒,在其内心深处更信奉仙、佛之类学说。 康氏经常引用《庄子·天下》“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72)来描述孔教。对康氏而言,这不是语词修饰,而是真实地描述了孔教的“大统”状态。康氏的儒学重建,就朝着这个目标进行。这个目标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横向要弥纶整个人类社会,纵向则要涵括当下与未来。从这两个维度看《中庸注》,可以发现:将孔教植根于人性,强调其“人道”意义,是使孔教能面向人智渐开的当下及未来;突显鬼神,要表明孔教优于耶、佛,同时提升儒学的号召力,使普通民众信奉与敬畏;阐发“三世三重”则在于让孔教能笼罩整个人类历史,避免儒学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而衰微。 康氏的苦心孤诣体现了其思索儒学如何应对近代生活的焦灼。不过,要建构一个无所不包的孔教,这一目标过于庞大,也不现实。儒家经典有自身的限制,不可能容纳康氏的庞杂想法。为此,康氏不惜歪曲经文,过度诠释。《中庸注》就体现了康氏的这些特点。这一做法显然难以让人接受。同时,康氏所要阐明的孔教内容也颇值得商榷。但是,从康氏对儒学的重建中,可以看到其目的是要走出宋明儒学心性修养的限制,让儒学积极介入社会政治,并持续地指导现实社会生活。这一思考方向无疑有其意义。从当下的儒学发展来看,儒学只是固守心性修养似乎还不足以焕发其生命力,毕竟心性修养多限于精英分子,难以推广到普通民众中。儒学要保持活力,应该进入到普通民众的日用生活中,并在心性修养以外的领域发挥它的作用。 *收稿日期:2014—01—26 注释: ①除《大学注》现仅存序外,其他三部均已出版。 ②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9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7页。引用时标点有改动。此信将《中庸》与“四书”并列,应属笔误。 ③萧公权著、汪荣祖译:《康有为思想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53页。 ④萧公权著、汪荣祖译:《康有为思想研究》,第55页。 ⑤吴义雄:《理学与戊戌前后康有为的思想体系》,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33页。 ⑥⑧⑩(12)(17)康有为:《中庸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369,369,369,369,369页。 ⑦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85页。 ⑨参见《康有为全集》第2集《万木草堂口说》及《万木草堂讲义》等。另可参阅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11)这与孔子作“六经”的今文经学立场不一致。《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如果孔子作“六经”,《中庸》应为孔子所作。 (13)“能传孔子之学者,《戴记》:《中庸》、《大学》、《王制》、《礼运》、《儒行》。”(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93页) (14)康有为:《教学通义》,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46页。 (15)(16)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36、146、288,166、245页。 (18)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25页。 (19)康有为:《中庸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369页。 (20)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118页。 (21)康有为:《长安讲演录》,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285页。 (22)康氏1910年致梁启超的信中,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用《儒行》《大学》《礼运》《中庸》“四记”代替“四书”等方案(参见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166页)。 (23)(24)(25)康有为:《中庸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369,369—370,369页。 (26)早期的《实理公法全书》已经体现出这一想法。 (27)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66页。 (28)(29)(30)(31)(33)(34)(36)(39)康有为:《中庸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369—370,370,373,374,373,370、371,370页。 (32)在早年的《实理公法全书》,康氏即持强烈的平等观。 (35)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03页。 (3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61页。 (38)《万木草堂口说》等述及《中庸》时说:“君子,指孔子,非泛指后贤。”(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66页)这些讲义记载得比较简单,难以断定康氏此时是否认定经文中所有的“君子”都特指孔子。《中庸注》则基本上认定“君子”特指孔子。 (40)(41)(42)(46)(47)康有为:《中庸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371,371,373,374,375页。 (43)廖平《知圣篇》对此曾有批评:“或云:自孔子后,诸贤各思改制立教。最为谬妄!制度之事,惟孔子一人可言之,非诸贤所得言也。”(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上册,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183页)廖平此言直指康有为。 (44)(45)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8,164页。 (48)(49)(52)(54)康有为:《中庸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376,377,376,376页。 (50)[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页。 (51)[南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84页。 (53)“佛言鬼不言神,耶稣言神不言鬼,惟孔子兼言鬼神。”(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75页)然而在早期的《康子内外篇》中,康氏说佛教是“去鬼神之治”,与此处不同。 (55)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565页。 (56)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439页。 (57)(63)(64)康有为:《中庸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383,369,387页。 (58)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43页。 (59)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430页。 (60)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80页。 (61)黄进兴:《从理学到伦理学: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241页。 (62)参见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65)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701—1702页。 (66)[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6—37页。 (67)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72、174页。 (68)参见马永康:《从“三统”、“三世”到“三世三重”——论康有为的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69)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0集,第19页。 (70)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118页。 (71)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188页。 (72)康氏有时将“六通四辟”写作“四通六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