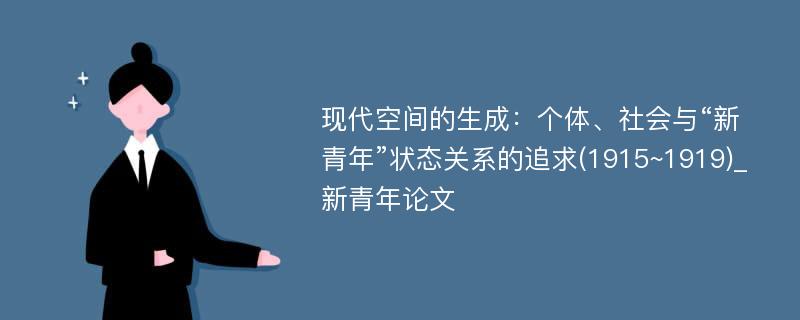
现代性空间的生成:《新青年》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寻踪(1915—1919),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新青年论文,关系论文,社会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06)02—0151—05
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基本学术命题。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开始就将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纳入到最为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议论位置。审视作为新文化元典同时也是现代性重镇的《新青年》杂志,我们会发现,当西方文明的价值资源被其顶礼膜拜的同时,她也就不能不面对一个具有焦点、重点同时也是难点的思想命题: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在中西文化之间如此不同,在两种文化直接冲突之际,究竟如何整合性质不同之思想谱系并令其适合中国土壤构成了一代关心国事民瘼先驱的历史担当。笔者以为,在这一意义上探讨本文立意的学术命题则是一个具有现实性和当代性的思想史诠释。
一、《新青年》同仁思想谱系的哲学透视
《新青年》是一个由有共同旨趣的知识分子自由结合而成的松散的、“联邦”式团体。关于这一点,我们从鲁迅那段回忆“同一战壕里战友”的故事中可窥见一斑。鲁迅承认自己在《新青年》上与同仁采取了一致的步调,同时他还将那些“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自命为“遵命文学”,但他却在这种“一致”后特别提出了个性独立、思想自由“同盟”的运作方式:“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1](p455—456) 既然是一个提倡个人本位主义的同仁团体,既然以自由主义思想相标榜,那么就必然有“同气相契”的气质或说气度在。不然,这样的松散而又“脆弱的”团体不可能在一个很长的时段里互为呐喊、相与助威。尽管个人内在的教育背景、思想资源不尽相同,具体到个人思想的“微言大义”也有一定的龃龉或说紧张,但他们毕竟在同一个阵地上吟唱过“同一首歌”,并在近现代思想史上形成了大的气候。说到这里,我们不妨首先回望一下《新青年》同仁在个人(本位)主义原则上的“上下一盘棋”开局。
论及《新青年》及其同仁,除却上面重点考察的主编、主笔兼主导的陈独秀,第一个涌入我们脑际的就该数胡适了。而论及胡适,其思想火花的最耀眼处还在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他看来,“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是一个基本常识,但他在两者之间却有着个人优先原则:“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Individuality),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单独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2] 他曾借挪威作家易卜生之口表达了自己的人生信仰,“我所最期望于你的一种真闪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进而认为“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2]。同是在该文里,他把家庭、社会、国家对个人的摧折、腐败、黑暗一一加以分析,从而得出了如下结论。
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所以易卜生的一生目的只是要社会极力容忍,极力鼓励斯铎曼医生一流的人物,社会上生出无数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敢说老实话攻击社会腐败情形的“国民公敌”;要想社会上有许多人都能像斯铎曼医生那样宣言道:“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
胡适将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的关系置于一个对峙的层面上,其意思极为浅显透明:反对它们“借着‘公益’的名义去骗人钱财,害人生命,做种种无法无天的行为”[2]。在《新青年》同仁中,除却来自安庆的陈独秀和徽州的两位安徽同乡名声大振外,还有一位安徽人士高一涵也是活跃于《新青年》上的自由主义者。应该说,高是《新青年》杂志上论述国家与个人关系最为深刻有力的一位。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这篇在《新青年》上连篇累牍连载的长文中,高一涵旁征博引,力述“国家”与“人民”的干系,在“各流、各系、各党、各派”与“小己”(个人)的关系中,“即以小己主义为之基,而与牺牲主义及慈惠主义至相反背者也”[3]。于是,弥尔论述自由著作中的个人主义成为高一涵启蒙思想的主要依据。在传统社会里,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是一种独立的存在。所谓个性,所谓自由,皆被一种依附性关系“伦理”所取代。而在现代社会,个人的独立自由与平等必须建立在“契约”伦理关系之上。因此,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就要一改传统的伦理关系。高一涵在另文中这样讲述古今国家与人民之间手段与目的的反复:“往古政治思想,以人民为国家而生;近世政治思想,以国家为人民而设。”[4] 除却“人民”与“个人”在政治学意义上的等质,不难发现其将个人置于与国家观念密不可分的地位。他另一篇论述国家观念的文章开篇便说:“今吾国之主张国家主义者,多宗数千年前之古义,而以损己利国为主。以为苟利于国,虽尽损其权利以至于零而不惜。推厥旨归,盖以国家为人生之蕲向,人生为国家之凭借。易词言之,即人为国家而生,人生之归宿,即在国家是也,人生离外国家,绝无毫黍之价值。国家行为茫然无限制之标准。小己对于国家,绝无并立之资格。而国家万能主义,实为此种思想所酿成。吾是篇之作,欲明正国家蕲向之所在。”[5]
再说周作人。他一加入《新青年》队伍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文学天才能力和敏锐的思想洞察力。在我看来,与其说他以译作和创作著称,毋宁说他的“人的文学”文小鬼大,将新文学的“新”抬了出来。周作人的“改良人类的关系”,也是说要置换个人与类群、国家以及社会的关系。对此,他说得较为透彻:“但现在还须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去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6]
质而言之,周作人“人间本位主义诉求”的立意还在张扬人性,排斥家、国与族、类的暴力。在这一点上,他和1922年8月的郭沫若同气相求:“我们是最厌恶团体之组织的:因为一个团体便是一种暴力,依恃人多势众可以无怪不作。”[7] 1922年4月发生在已经成为党魁的陈独秀与周作人之间的名为“非基督教非宗教”大同盟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思想公案。当陈独秀以“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向周作人等五教授发出公开信后[8],周作人的回答是:“我们承认这些对于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所以要反对这个似乎杞忧的恐慌。”[9] 时至《语丝》时期的周作人,为了突显“自由思想,独立判断”,该刊与非个性化的文学刊物针锋相对,连“社”、“团”、“会”之类的词汇都不提及。
也许这些属于《新青年》的余音,有游离本论之嫌,但作为思想史光谱上的“一束”却不能忽略。
二、《新青年》个人与国家关系思想的集束与辐射
所谓“集束”,是说社会转型期的思想特征在一个特点上不约而同的集体兴奋,所有的思想光束都聚焦于一个点上,具有非常浓缩的思想穿透力。所谓辐射,是说思想史上的主流趋势会在某一个时期占据优势和主导,但由于其主潮的形成是同声共求的结果,因此也难免在高潮之后在不同的哲学基础和教育背景下走向不同的思想归途。《新青年》杂志同仁由“同一首歌”到各种“唱法”的浮出水面就是一个由“集束”到“辐射”的过程。我们之所以将《新青年》与20世纪中国的走向联系起来,并认为它影响了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思想文化和政治选择,实在是因为它强烈的集束穿透力和惊人的辐射力。
在述说过个人在国家、社会的中心地位后,笔者顺便引出与这一命题息息相关的话语:《新青年》集束特征的另一面则是,两端砝码之间的互补与平衡。尽管当时思想家们以“大我”与“小我”、“小己”与“国家”、“个人”与“社会”、“我”与“世界”的不同名目表达出来。笔者之所以拉出这样一个命题作为后续,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有的能够守成,有的则放弃守成,还有的不能守成(自一开始就决定其不能守成)。我以为,从个人与社会的平衡到两者关系倾斜(不再互补的失衡)的视角观照《新青年》的思想的变迁是一个较为得力的论证设计。
还是先看看主编在个人优先性之后是怎样强调个人有限性的。在此,我们不妨先开出陈独秀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平衡等式:“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10] 那意思是说,即使得是个人优先,也不能让“个人及社会、国家者”相互“为害”。尽管陈独秀“内图”与“外图”的对等公式早于1918年得出,但笔者以为真正在心理达到平衡还在1918年以后。在该年2月写的文章中,他才切实把“个人”与“社会”的互助互补关系作出合理合情的诠释。陈独秀一改在此之前抑“孔孟”扬尼采的言行,认为双方都不够全面。陈独秀认为,“自利利他”价值趋向才是完整的:“总而言之,人生在世,究竟为的什么?究竟应该怎样?我敢说道: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接受,以至无穷。”[11]
“千呼万唤始出来”。作为编委的李大钊进入《新青年》之初就有着很强的平衡意识。为此,他开出的“国家与个人”处方则是:“个性的自由与共性的互助。”他在《新青年》的新生儿《新潮》上撰文指出:“方今世界大通,生活关系一天复杂似一天,那个性自由与大同团结,都是新生活上、新秩序上所不可少的。”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看来,“生活关系”和“组织”关系的复杂乃是需要调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本因。在“个性自由与大同团结”价值趣向的引导下,一种理想化的“联治主义”范式出现了:“因为地方、国家、民族,都和个人一样有他们的个性,这联治主义,能够保持他们的个性自由,不受地方的侵犯;各个地方、国家、民族间又和各个人间一样,有他们的共性,这联治主义又能够完成他们的共性,结成一种平等的组织,达他们互助的目的。这个性的自由与共性的互助的界限,都是以适应他们生活的必要为标准。”[12]
按照李大钊与陈独秀的思想逻辑,他们就是要以“个人”与“社会”平衡互补为价值准则,建立“联合自治”的政治模式。这构成了陈、李从个人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过程中“独标异见”的思想火花。我们看到个人与社会的平衡不止是表现在陈独秀、李大钊身上,同样是胡适、高一涵、周作人等的思想症候。胡适的说法是: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理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13]
鉴于《易卜生主义》中有将“各人自己充分发展”的个人主义归为“人类功业顶高的一层”的表述,自此学术界将两文置于根本的对峙中。笔者以为,胡适固然有个人本位主义与社会本位主义的两极砝码的平衡,但这并非唯一。事实上,“大我主义”的出现并非那么突兀。无独有偶,高一涵的平衡观是一以贯之的,他始终坚守“小己”与国家和社会的和谐同一、并立,坚信它们不应相互为害。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民约与邦本》、《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等论述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系列文章中,他一直守恒着:“故欲定国家之蕲向,必先问国家何为而生存;又须知国家之资格,与人民之资格相对立,损其一以利其一,皆为无当。”所以“小己人格与国家资格,在法律上互相平等,逾限妄侵,显违法纪”[5]。个人优先,但社会马上跟上。应该说,高一涵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位稳健的自由主义者。与以上同仁对应,周作人在爱人先爱己之后也不敢怠慢,立刻抛出了下面的话语:“墨子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便是最透彻的话。上文所谓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6] “自利利他”正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相互寻求平衡的又一翻版。
综上,《新青年》在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曾一度出现过一个相对平稳的“平衡过渡带”。但毋庸讳言,这个平衡是短命的昙花一现式的“闪断”。由此,我们可以理解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自由(理想)模式是多么短暂稀缺。值得说明的是,那知识群体思想的摇摆如同家常便饭。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更为关键的是: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或倾向。
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平衡”是短暂的。他们应该说是《新青年》团队中从先前的个人主义(极端)走向社会主义(完全)的典型。李大钊1919年7月那篇《我与世界》的全文录制如下:“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园、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14] 这和陈独秀将宗教、君主、国家都斥为“无用的东西”、“都应该破坏”的观点联系起来看,他们浸润的无政府主义“营养”还是非常充足的。
胡适,一个人们习惯于以自由主义称呼的人士,在他的“易卜生主义”背后潜存着深沉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恰恰是这个“主义”,正是前期易卜生中的思想核心。以后的易卜生主义乃是它完备的发展与延伸。胡适对此也非常认同:“易卜生起初完全是一个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人。当普法之战(一八七○至一八七一年)时,他的无政府主义最为激烈。”后来易卜生“进到世界主义的地步”也正乃无政府主义的合理发展[2]。20世纪20年代中期,胡适对“集团主义”、“新俄”理想以及国民革命的态度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位“健全个人主义”者无政府“大同”倾向的隐隐作痛。关于这一点,在陈独秀、李大钊思想谱系的演变中线索非常分明。照常规思路,高一涵的相对纯粹的自由主义应该与无政府主义无缘,但就是他的《老子的政治哲学》一文构成了他整个《新青年》时期自由思想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老庄那消极革命、“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等带有乌托邦意义的思想资源构成了他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思想衔接的利器。等到1919年5月将自己的家底和盘托出,他在之前的现代性追求也就让我们明白了大半。他说:“无论是人、是地、是天、是道,总要受自然支配的。顺着自然法则,便‘无为而无不为’;背着自然法则,‘虽欲为之而无以为’。他把‘自然法’的功用,康德这样森严,所以才主张放任主义。不过老子的放任主义。”[15]
这和《天义报》时期刘师培论学论政中借助老子哲学大谈特谈无政府主义如出一辙。
在《新青年》杂志同仁中,周作人的温和、中庸、谦逊是众所周知的,但就是这样一位人间本位主义者有着极其唯我的个人主义特质。他将“人道”、说自由、论个性,可在“自利”与“利他”的设计中还走向了极端为我的无政府主义老路。那经典之文《人的文学》在散发着个性启蒙光彩的同时,也夹杂着一头雾水般的思想菜单。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混杂在一起进行着文化启蒙。在他说过自利利他的“个人主义”之后就有了这样情不自禁的表述:“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人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饿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6] 其实,极端的个人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哲学基础,完全处于一个意识形态之下。如果说这里的引述还不足以证明周作人也有无政府主义的影子,那么在其之后发表的《日本的新村》等文章无疑为6卷4号的“劳工问题讨论”(以王光祈的《工作与人生》为标志)和5号的“马克思专号”(这个专号包括高一涵的《老子的政治哲学》和克水的《巴枯宁传略》两篇论述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开了先河。他介绍日本的新村实况说:“近年日本的新村运动,是世界上一件很可注意的事。从来梦想Utokia的人,虽然不少,但未尝着手实行;英国诗人Coleridge等所发起的‘大同社会’(Pantisocracy)也因为没有资本,无形中消失了。俄国Tolstoj的躬耕,是实行泛劳动主义了。但他专重‘手的工作’,排斥‘脑的工作’,又提倡极端的利他,没杀了对于自己的责任,所以不能说是十分圆满。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个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通的人生的福音。一九一0年,武者小路实笃(一八八五年生)纠合了一班同志,在东京发刊《白桦》杂志,那时文学上自然主义盛行,他们的理想主义的自由,一时没人理会,到了近三四年,影响渐渐盛大,造成一种新思潮,新村的计划,便是这理想的一种实现。去年冬初,先发队十几个人,已在日向选定地方,立起新村,(Atarashiki Mura)实行‘人的生活’。”[ 16]周作人不但有了《日本的新村》,而且日后还有《新村的精神》的宣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但有“新村的理想”的鼓吹,而且还有新村精神的实践。《新青年》7卷2号上的一则启事就足以让读者刮目相看:“新村北京支部启事:本支部已于本年二月成立,由周作人君主持一切,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手续,支部会址及会面日期如下:北京西道门内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宅。每星期五及星期日下午一时至五时。”[17] 我们虽然不能说周作人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但从他的思想流变以及精神诉求来看,在他个人的思想谱系中,并不能完全排除他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亲和与缠绵。事实上,他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流思想总是与具有“工读互助”的乌托邦精神谱系藕断丝连。
的确,20世纪初年无政府主义思潮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种思潮流派。它也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日后在中国的生成。1918年到1919年,《新青年》上“劳工神圣”的宣传一浪高过一浪。时至1920年,如果是思想集体曝光,那么的确是同仁集体上阵。《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的“发起人”中除了鲁迅,主体作者几乎全部到位:李大钊、陈溥贤、李辛白、陈独秀、王星拱、孟寿春、蔡元培、高一涵、徐彦之、胡适、张崧年、罗家伦、周作人、程演生、王光祁、顾兆熊、陶履恭[18]。“同仁”中除却陈溥贤、李辛白、孟寿春三位少有出头露脸,其他人都是已经在《新青年》上频频出场并已经混到脸熟程度的多产作者。由此不难发现,从初期的个人(本位)主义到中期的“互助”倾向,再到“一发而不可收”的社会(本位)主义,尽管中间有歧路上的分离,但用“大风起兮云飞扬”来概括一个同仁杂志对中国20世纪近一百年走势的震动和影响并不为过。的确,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团队舆论力量以及打造的思想走势就是这样不可小觑。
论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三者之间在《新青年》的交织、转换以及“合力”也许有游离本论之嫌。但笔者以为,在思想史意义上探讨他们如何在个人思想主流与他者思想“排列组合”中生成“合力”并发生转向则是具有问题意识的选择。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文化元典与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演进”(2004DZX005)
收稿日期:2005—11—21
标签:新青年论文; 个人主义论文; 陈独秀论文; 周作人论文; 社会论文; 读书论文; 李大钊论文; 胡适论文; 现代性论文; 无政府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