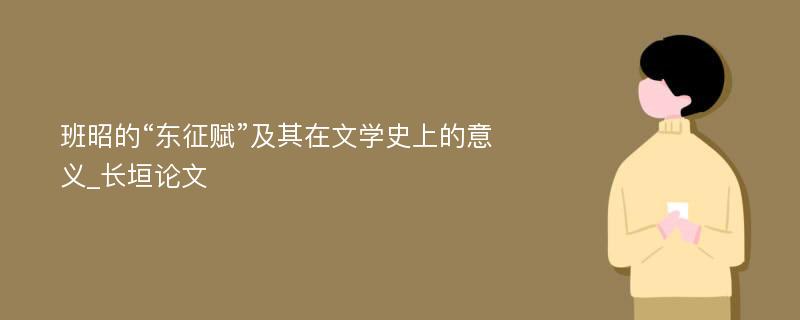
班昭《东征赋》及其文学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意义论文,班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06-0150-05
班昭《东征赋》是汉代述行赋的代表作之一。关于它的作年,尚存有分歧;关于它的主旨,迄今鲜有深入探讨。而考订这篇赋的作年和主旨,对理清班昭的为政思想和文学成就,进而把握《东征赋》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很有必要。
一、《东征赋》作于永元七年考
关于班昭《东征赋》的创作时间,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看法,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作于安帝永初七年(113)。研究者大多依据班昭《东征赋》的开篇所言“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随子乎东征”[1](P962),而把班昭随子东征的时间确定为“永初七年”。认同此说者较多,如刘汝霖指出:“永初……七年癸丑,昭子榖为陈留长,昭随至官,发洛至陈留,述所经历,作《东征赋》。”[2](P36)陆侃如指出:“永初七年,班昭随子至陈留,作《东征赋》。”[3](P138)此外,石观海《中国文学编年史·汉魏卷》[4](P253)、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5](P465)也都持此观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作于和帝永元七年(95)。如清代学者阮元指出:“昭之东征,因子榖长垣长而出京师。考昭本传言昭卒年七十余。昭卒在邓太后之前。故邓太后素服使护丧事。又考安帝永初元年,昭谏邓骘之事,是昭在京师为太后所敬听,故其子称谓中散大夫,必和帝永元七年为长垣长以后事。盖班固卒于永元四年,班固死,始召昭入宫续编《汉书》,亦当在子觳为长垣长之后。当时昭已年将六十矣。以此推之,则赋首‘永初’亦为‘永元’之误。若是‘永初’则当作安帝矣。”[6](P301-302)朱维铮在其《班昭考》一文中也赞同此说。[7]
以上两种观点,究竟哪一种符合事实呢?笔者认为,既然班昭的《东征赋》写于她跟随儿子曹成东征之时,那么,要弄清此赋作年,必先弄清曹成东征的准确时间。解决了这个问题,《东征赋》的作年问题也就随之而解了。
那么,曹成究竟是在哪一年东征的呢?是否真的如《东征赋》中所言是在“惟永初之有七兮”呢?且看相关文献记载。
第一,据《三辅决录》记载:
齐相子榖,颇随时俗。曹成,寿之子也。司徒掾察孝廉,为长垣长。母为太后师。征拜中散大夫。子榖即成之字也。[8](P26)
由此可知,曹成东征担任长垣长是因察孝廉。但考察《后汉书·孝安帝纪》和《后汉书·皇后纪》,在安帝永初七年,却没有察举孝廉的任何记载。那么曹成究竟于何时因举孝廉而东征赴任呢?据《后汉书@孝和帝纪》:
(永元七年)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帝引见公卿问得失,令将、大夫、御史、谒者、博士、议郎、郎官会廷中,各言封事。诏曰:“元首不明,化流无良,政失于民,谪见于天。深惟庶事,五教在宽,是以旧典因孝廉之举,以求其人。有司详选郎官宽博有谋、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选郎出补长、相。[9](P180)
永元七年,汉朝发生日食。在这个讲究天人感应的朝代里,人们认为,这种天文异常现象乃是上天对统治者过失的警告,王充《论衡》所云“人君失政,天为异;不改,灾其人民;不改,乃灾其身也。先异后灾,灾为已至,异为方来”[10](P634),就生动阐释了这种灾异谴告思想。正因如此,日食的出现引起了汉和帝的极大重视,他立即采取多项措施加以弥补,以禳除灾难。其中之一便是选举贤良,并把所选孝廉郎中宽博有谋的三十人全部出任县长、侯相。曹成被派往陈留郡担任长垣长一职,正缘于此。而这也与曹成“司徒掾察孝廉,为长垣长”的历史记载相吻合。因此,笔者认为“永初七年”当为“永元七年”之误,阮元提出“赋首永初为永元之误”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
第二,就曹成任职情况看。曹成任职履历,文献有较详记载,兹列如下:
《三辅决录》:“曹成,寿之子也。司徒掾察孝廉,为长垣长。母为太后师。徵拜中散大夫。”[8](P26)
《后汉书·列女传》:“(班昭)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关内侯,官至齐相。”[9](P2785)
据此可知,曹成曾担任司徒掾,察孝廉为长垣长,又因母亲班昭为太后师的缘故,徵拜为中散大夫,特封为关内侯,官至齐相。另据《后汉书·皇后纪》记载:
元兴元年,(和)帝崩,长子平原王有疾,而诸皇子夭没,前后十数,后生者辄隐秘养于人间。殇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及殇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犹临朝。[9](P423)
从这一记载可知,和帝皇后邓后被尊为太后并临朝称政,始于元兴元年(105)和帝驾崩、殇帝即位之后。因此,班昭为邓太后师,亦当在元兴元年之后;曹成因母为太后师而担任中散大夫,也当最早始于殇帝延平元年(106)。
又据《后汉书·孝安帝纪》,延光三年(124),发生废除太子一事,“九月丁酉,废皇太子保为济阴王”[9](P240),为证明太子清白,曹成等人诉说太子之冤:
(太仆来历)乃要结光禄勋祋讽,宗正刘玮,将作大匠薛皓,侍中闾丘弘、陈光、赵代、施延,太中大夫朱伥、第五颉,中散大夫曹成,谏议大夫李尤,符节令张敬,持书侍御史龚调,羽林右监孔显,城门司马徐崇,卫尉守丞乐闱,长乐、未央厩令郑安世等十余人,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9](P591)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曹成从延平元年到延光三年一直担任中散大夫一职。
假如曹成在永元七年担任长垣长一职成立的话,那么根据汉代的职官制度可知,长垣长是陈留郡的属官,职位较低,其官俸仅为三四百石而已。如《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11](P742)另据《后汉书·百官五》记载:“属官,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9](P3622)
关内侯为级别较高的军职,相当于诸侯,根据《后汉书·百官五》记载:“关内侯,承秦赐爵十九等,为关内侯,无土,寄食在所县,民租多少,各有户数为限。”[9](P3631)从《后汉书·百官二》的记载可知:“中散大夫,六百石。”[9](P3577)此时曹成的官俸为六百石,虽然关内侯一职无土,但在寄食的县却可以分得民租。两相对比,官俸的从少到多也正好印证了曹成“子以母贵”的事实。
第三,从邓太后永初年间面临的政治形势看。邓太后临朝称政的时间,先后经历殇、安二帝。殇帝于“元兴元年十二月辛未夜,即皇帝位,时诞育百余日。尊皇后日皇太后,太后临朝”[9](P195)。而于延平元年“八月辛亥,帝崩。……年二岁”[9](P199)。殇帝作为和帝的小儿子,从即位到驾崩都处于婴幼儿时期,不存在与邓太后之间权力相争的问题。而安帝刘祜则不同,他在延平元年八月即位时已经十三岁,翌年改元为“永初”。而“太后犹临朝”[9](P204),此举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不满。
据《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记载:“时和熹邓后临朝,权在外戚。(杜)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乃与同时郎上书直谏。太后大怒,收执根等,令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9](P1839)又,“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谏太后归政,坐抵罪”[9](P1840)。杜根和成翊世都认为安帝已长大成人,谏议邓太后归政于安帝。此举极大地触怒了邓太后,杜根和成翊世也因此遭到了沉重的打击。邓太后不肯让权,不仅遭到了朝中大臣的反对,而且连邓氏家族的人也谏议她应归政于安帝。“永初六年……(邓)康以太后久临朝政,宗门盛满,数上书长乐宫谏争,宜崇公室,自损私权,言甚切至。太后不从。”[9](P606)邓康屡劝太后隐退深宫,邓太后不从,将邓康罢免官职。此外,“自太后临朝,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9](P425)
由此可见,永初年间,正值汉帝国内忧外患、天灾人祸较为严重之时,也正是邓太后需要亲近之人为其出谋划策的紧迫之时。据《后汉书·列女传》记载,班昭“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以出入之勤”[9](P2785),可见班昭在邓太后临朝后,“与闻政事”,“出入勤”,实际承担着幕后智囊的角色。因此,假如认为班昭在此时随子东征,不仅有悖情理,而且更与史实相左。所以,班昭随子东征的时间不应在永初七年,而应在永元七年。
第四,从班昭自身的情况来看。曹成此次东征担任陈留郡长垣长一职。据《后汉书·郡国志三》记载:
陈留郡武帝置。洛阳东五百三十里。十七城,户十七万七千五百二十九,口八十六万九千四百三十三。
长垣侯国。有匡城。有蒲城。有祭城。[12](P3447-3448)
陈留郡的设置始于武帝时期,位于京都洛阳东五百三十里。长垣是陈留郡的一个侯国,包括有匡城、蒲城和祭城等地。从京师洛阳出发,途径偃师、巩县、成皋、荥阳、原武、阳武、封丘、匡郭,最后到达长垣县,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行程艰险无比,恰如《东征赋》中所言:“历七邑而观览兮,遭巩县之多艰。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门。既免脱于峻崄兮,历荥阳而过卷。”[1](962)
根据笔者推论,班昭约在建武二十五年(49)出生。如果班昭随子东征的时间是永元七年(95),那么班昭此时是46岁。在这样的年龄出行,她完全可以承受路途遥远带来的种种不适,并能把途中所见所感记录下来,以寄托自己对儿子曹成的厚望。但如果班昭是永初七年(113)随子东征,她就需要以64岁的高龄经历几百里的长途艰难跋涉,在此情况下,我们也很难想象她会有足够的精力用一篇极费心力的赋去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当然,这只是笔者在史料匮乏的情况下进行的大胆揣测,虽然缺乏直接的证据,但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第五,从班昭作品的流传情况来看。在班昭去世之后,她的作品被其媳妇丁氏加以整理,编纂成集。丁氏为曹成之妻,对班昭和曹成的行踪理应都了如指掌,因此,班昭的这篇赋在《大家集》中应当不会出现文字上的错误,而当属在流传的过程中,传抄时出现了错误。如班昭的《东征赋》在《昭明文选》中完整地保存下来,而李善在为《东征赋》作注时却说:“和帝年号永初。”但是,和帝年号乃是“永元”,而非“永初”。也就是说,这样的传抄错误在今存李善《文选》注中已经出现。但至于“永初”为“永元”之误是否首次出现在《文选》之中,因文献资料的不足,已不得而知。
综上,在对各种线索进行整理、分析之后,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即“永初七年”当为“永元七年”之误,也即班昭的《东征赋》作于永元七年。
二、《东征赋》主旨考论
由于班昭《东征赋》是东汉述行赋的代表作之一,后世研究者往往认为,它的主旨就是班昭随子东征经历的记述。如《文选》卷九《东征赋》李善注曰:“《大家集》曰:子榖为陈留长,大家随至官,作《东征赋》。《流别论》曰:发洛至陈留,述所经历也。”[13](P184)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2](P36)等也持此观点。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主要是受体例限制,只是简单解题,并未深入《东征赋》的文本来把握其深刻寓意,因此不够全面。笔者拟从三个方面对其主旨进行辨析。
第一,从《东征赋》文本表现的内容来分析。赋中,班昭指出:“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1](P963)班昭的父亲班彪曾作《北征赋》记载其流亡经历。班昭以父亲为榜样,把东征路上的所见所感记载下来,虽形式上有模仿,但她对自己所记之事有意剪裁,却使主题别具新意,继承中有创新。
曹成此次东征,从京都洛阳出发,一路向东,途经多地。集史学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于一身的班昭,随着空间位置的移动,都会结合当地的历史故事来抒发自己的看法,尤其在历史人物的选择上,班昭更是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可以说,对材料剪裁的详略不同,不仅彰显了班昭扎实的文学功底,更突出了她的匠心独具。这是因为“汉代纪实性的《述行赋》是把古代典故作为现实的借鉴加以陈述,但是,究竟选择哪些历史掌故来和现实沟通,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作主体的心境、志向、兴趣,以及对相关历史事实的掌握程度,还和创作主体的生存环境,亦即和时局形势密切相关”[14]。
班昭在《东征赋》中,首先记录了偃师,这里是古代贤君帝喾曾经建都的地方。接着她又先后记录了以下行程:
涉封丘而践路兮,慕京师而窃叹。……入匡郭而追远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乱之无道兮,乃困畏乎圣人。[1](P962)
封丘县,曾是殷商时期纣王烹醢九侯的地方。经历此处,班昭不由得想起纣王的暴虐无道,由此生发感慨,希望曹成能够成为一位道德高尚的君子,而不是尸位素餐、为害百姓的无耻之徒。匡城,是孔子当年因被匡人误认为是鲁国的阳虎而遭受围困的地方。班昭在此也想让曹成认识到:做地方官,只有体恤民情、关心百姓疾苦,才能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拥护。
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惕觉悟而顾问兮,想子路之威神。卫人嘉其勇义兮,讫于今而称云。[1](P963)
蒲城为春秋时卫国所辖,经过此地,班昭不由得联想到曾任蒲城大夫的孔子弟子子路。子路在此讲义施仁,政绩卓著,深受卫国人敬爱,他们不仅称颂其勇敢、义气,而且还为其立下祠堂,令其声名流播后世。因此,班昭告诫曹成要汲取历史教训,顺应潮流,修身正己:
勉仰高而蹈景兮,尽忠恕而与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诚通于明神。庶灵祗之鉴照兮,祐贞良而辅信。[1](P963)
总之,在赋中,班昭使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告诫曹成就任要做好思想上的准备和行动上的严格要求,起到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完美结合。由此可见,这篇赋并不是一篇单纯的述行之作,而是欲通过此赋教育孩子为官做人,可谓一箭双雕。
第二,从班昭此时的心理背景因素上看。永元四年(92),窦宪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自杀,班固因加入窦宪幕府,“及窦氏宾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9](P1386)。班固可以说是班氏家族中死于政治争端的第一人,他的死也为整个班氏家族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所幸永元五年(93)正月和帝“大赦天下”,窦宪党人也得以大赦。永元六年(94),和帝“幸洛阳寺,录囚徒,举冤狱。收洛阳令下狱抵罪,司隶校尉、河南尹皆左降”[9](P179)。同年,“西域都护班超打破焉耆、尉犁,斩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纳质者五十余国”[9](P179)。班超在西域取得巨大成就,则为班氏家族增添了光彩。由班固、班超等家族成员的经历,班昭深深知晓官场的凶险,不免有出世心理,但维护家族荣誉的强烈责任感,又使班昭在儿子曹成被朝廷举用之时抱着积极入世的心态来面对。她的这一选择也延续了班氏家族历久不衰的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传统。另据作者考证,班昭于永平五年(62)嫁于曹世叔为妻,之后方生曹成,由此可以推知,曹成东征时年龄当不超过30岁。再加上他初入官场,涉世未深,因此班昭就担负着指导曹成如何为官、如何为民的职责。
第三,从曹成此次东征的政治背景来看。由上文考证可知,曹成被派东征,是因日食出现、汉和帝为弥补政治失误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受此影响,曹成的东征任职本身就具有不平凡的政治意义。他不仅肩负着安抚百姓、改善统治者在百姓心目中形象的神圣使命,而且更要公正廉明、取信于民,以维护汉帝国的稳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班昭《东征赋》的主旨是通过一系列的史实来告诫儿子曹成为官时应具之德、应做之事,以不辜负朝廷的重托。
三、《东征赋》的文学史意义
班昭《东征赋》作为汉代述行赋的代表,在继承前代述行赋的基础上,融述行、写景和抒情于一体,推动了述行赋的进一步发展,在汉代文学史上别具特色,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第一,创作题材的拓展。综观班昭前后的汉代女性作品,很多女性由于自身生活的坎坷不幸,往往会选择以写作来抒发个人情感,作品几乎全是笼罩在哀怨伤感的氛围之中,基本上都是抒发一己的情怀,如乌孙公主的《悲愁歌》、班婕妤的《怨歌行》、蔡琰的《悲愤诗》,都是如此。
由于个人经历的特殊性,班昭的文学创作开始在更广阔的领域进行摸索和尝试。她的《东征赋》就从汉代女性文学狭小的闺阁走向了广袤的现实世界,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汉代女性作品相思愁怨的单一创作模式。这篇赋,开始以广阔的视角去审视社会人生,颂赞明君圣主,关注百姓的生活与社会的矛盾,此赋融抒情、写景、思亲、咏史于一炉,极大丰富了汉代女性文学的表现空间。可以说,她的作品不但继承了情感真挚这一女性文学的创作传统,而且开始注重文学的社会价值,借作品阐发了她对个人和国家的独特看法,体现了强烈的用世精神。
第二,丰富了文学的表达样式。汉代的女性文人在抒发个人哀怨时,往往仅仅借助于诗歌这一文学样式。如胡应麟所言:“汉妇人为三言者,苏伯玉妻;四言者,王明君;五言者,卓文君、班婕妤、徐淑;七言者,赵飞燕;八、九言者,乌孙公主、蔡文姬。皆工致合体,文士不能过也。”[15](P134)虽然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诗歌的发展,但也约束了女性文学的全面发展,导致不少女性文人“缺乏对文学的文体自觉,缺乏在艺术形式上有所建树的信心”[16](P165)。
班昭的《东征赋》在作品的体裁选择上,将表情达意的笔触扩展到了辞赋。辞赋不仅句式长短不受限制,而且字数增多,也使其意义容量加大,从而利于班昭自由而恰切地表现自己丰富而复杂的情感。
同时班昭也打破了男性文人独统赋坛的传统,以自己不俗的才华获得了男权社会的认可,堪与男性文人比肩,在中国文学史上为女性文人书下了浓重的一笔。她的辞赋创作,在继承的同时也有创新,并融入了自己的个性色彩,以女性文人特有的细腻感情立足于赋坛。其《东征赋》描写她随儿子曹成从洛阳前往陈留的经历。虽然这篇述行赋在形式上模仿了其父班彪的《北征赋》,但是在感情抒发上更为细腻真挚,因此赢得了何沛雄的大加赏誉:“曹大家《东征赋》,韬笔排宕,名理曾出。巾帼不让须眉,可垂不朽矣。”[17](P131)
第三,文学风格的新变。在文学风格上,班昭的《东征赋》一改汉代女性文学忧伤凄美的格调、婉约柔美的风格,把女性的柔弱美,文人的理想美和温柔敦厚、充满理性之光的个性美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柔美中见刚直,即文笔庄雅,感情平和的文学风格。因此清人王士禄《宫闺氏籍艺文考略》引《神释堂脞语》评价班昭的作品为:“二班奕奕,流耀东京,大家如白发青裙,婕妤殆藐姑冰雪矣!”[18](P2)王士禄用“白发青裙”四字来一针见血地概括班昭的作品风格,这个评价非常精当、妥贴。阅读班昭的《东征赋》,宛如听一位饱经岁月风霜的老人,一切过往在她的娓娓讲述之中,显得那么亲切、温和,却又不失深沉、典雅和凝重。
班昭学识渊博,基于对儒家典籍和历史史实的熟稔,她在《东征赋》中可以应用自如、自然得当地连续使用多个典故。这样文章不仅显得典雅、富丽,而且气势恢宏,增强了说服力和感召力。如:
惟经典之所美兮,贵道德与仁贤。吴札称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后衰微而遭患兮,遂陵迟而不兴。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兮,尽忠恕而与人。[1](P963)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班昭的《东征赋》在题材内容、文学样式以及文学风格上皆有重大突破,并取得了一定的文学成就,因此,其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