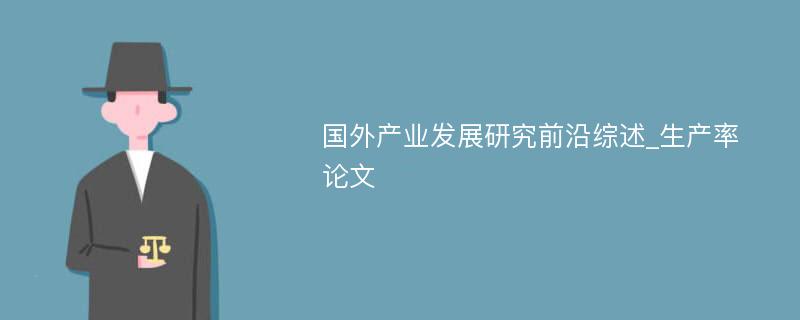
国外产业发展研究前沿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发展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工业发展与工业化
1.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
刘易斯增长模型的标志是经济的二元结构(现代-传统部门)假设,其前提有两个,传统部门有丰富的劳动力(发展中国家的过剩劳动力);存在一些正式的或非正式的限制阻碍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自由流动。Ranis and Fei(1961)扩展了刘易斯模型,强调刘易斯经济不仅以组织的二元性(organizational dualism)为特征,而且存在产品的二元性(product dual-ism),后者使得两部门间的贸易成为产出的重要决定因素,因为现代部门的工资主要花费于传统部门的产出。南亮进(Minami,1973)将刘易斯模型全面应用于日本,提出5种识别拐点的标准:(1)维持生计部门(subsistence sector)工资和劳动边际产出的比较;(2)维持生计部门工资和劳动边际产出的相互关系;(3)维持生计部门实际工资的变动;(4)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工资差异的变化;(5)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部门的劳动供给弹性。标准(1)提供了对拐点的最严格的检验,并且决定了其他标准。Islam and Yokota(2008)利用Minami标准(1)检验中国工资曲线拐点的存在。研究结果显示,农业工资随时间而增长,显示传统部门的工资曲线不是保持完全平坦;传统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品的增长速率超过工资;尽管劳动的边际产品曲线的增长比工资陡峭,以致二者的差距在缩小,但平均工资曲线作为一个整体仍然保持在劳动边际产品曲线之上。总之,中国正逐步向刘易斯拐点趋近,尽管还没有越过这一拐点。该文还表明,与假设完全流动和产业间要素回报均等的新古典模型相比,假设二元结构的刘易斯模型更符合中国这样的劳动力丰富国家的现实。
Abegaz(2008)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结构向稳定状态的收敛问题。如果制造业在经济范围内份额的相似性伴随着产出或要素使用的产业构成的相似性提高,那么两个国家的制造业领域就可以说是结构收敛的。收敛的终点是长期占优的稳定状态的产出份额,对于失败者是份额地板(share floor),对于成功者就是份额天花板(share ceiling)。他的研究发现,生产效率是产业间(inter-branch)产出份额调整的主要决定因素。收敛速度与成本效率指标(例如毛利和单位劳动成本)正相关。如果向稳定状态份额天花板移动,具有较好成本效率指标的产业会经历快速的份额增加;反之,如果向稳定状态份额地板移动,则经历较慢的份额损失。他认为,后发国家以重塑比较优势为目标的幼稚产业保护的普适性是工业化的少数法则。产业调整的速度会被产业中性的政策立场所加强,包括基础性服务的投资、信贷获得、关键技能供给、加强竞争的贸易和规制环境。
2.贸易与工业化
Christiaans(2008)利用两部门非规模增长模型(two-sector non-scale growth model)分析了国际贸易、增长和工业化的关系。在非规模增长模型中,长期人均增长率不直接依赖于人口(或其他规模指标),但是依赖于人口增长率。由于非规模增长模型中的长期增长率通常独立于政策工具,他们也被称为半内生增长(semi-endogenous growth)模型。他的模型显示,人口增长率是内生比较优势、结构变化和长期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国际贸易导致国内经济的工业化或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iton)过程,这反过来解释了长期增长率以及人口增长对人均收入增长影响的国家间差异。具有较高人口增长率的国家,如果它在制造业具有初始比较优势,就会获得正向的增长-贸易联系;如果劣势导致去工业化的过程,负的增长-贸易联系是可能的。具有较低的人口增长率的国家甚至会失去制造业的初始比较优势,并且长期来看是去工业化的。然而,因为自由贸易下的贸易条件比自给自足下提高得更快,它会从国际贸易中获利。他的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最好的发展政策(外向或进口替代)没有简单的答案。如果对国际贸易开放过早,具有较高增长潜力的国家(以人口增长率衡量)会承受与去工业化过程相关的负的增长-贸易联系,但是如果它能够以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起步,就会在自由贸易下获得高增长率。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以保护幼稚产业为目标的暂时性政策措施给予结构变化一个有利的方向就是合理的。
根据经济学理论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外向型特别是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其他低收入经济拥有巨大潜力,是一种合适它们的发展战略。但是Kaplinsky and Morris(2008)的研究对这一共识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由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以制成品重要出口国的身份进入全球市场,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和纺织领域(通常被认为是出口导向制造业增长的第一步)与亚洲生产者相比不具有持续的贸易优势,从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服装和纺织产业被排除于国际市场之外,它的国内市场也面临严重的进口威胁。除非在高度限制的贸易环境中(但是与WTO和其他机构推动的自由贸易的全球经济相悖),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才能奏效。
3.集群与工业化
一般认为,发育良好的金融体系是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然而中国过去30年快速的工业化却对此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大量的民营中小企业基本被排除于国有银行的正式信贷体系之外,但是在信贷约束的环境下,中国的中小企业大量涌现并快速成长。Long and Zhang(2011)利用两次工业普查的数据,从集群的视角对此给出了解释,提出了“以集群为基础的工业化”(cluster-based industrialization)的概念。他们认为,在产业集群中,一体化的生产过程分解为许多细小的环节,这就降低了进入该环节生产的资金门槛;同时集群内企业间的接近与激烈竞争也会降低不诚实行为的诱惑,使集群内部企业间经常的贸易信贷(trade credit)成为可能,减轻了非国有企业对外部融资的依赖。由于生产的投资门槛很低,财富不多的企业家能够开始他们的事业,从而吸引了大批企业家参与到非农生产中,促进新企业的涌现。该文发现,某个区位国内非公有企业的出现与当地产业集群的程度相关。集群也推动了集约增长——通过增加相似企业间的竞争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在集群程度高的地区,国内非公有企业有更高的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而集群与国有企业的绩效几乎没有关系。他们认为,以集群为基础的工业化模式也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大部分集群建立在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的基础上,该商业模式使用较多的企业家能力和劳动以及较少的资本,这是与中国的比较优势一致的。政府在不能够利用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中推进集群为基础的发展时要非常当心。第二,即使具有相似禀赋的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意识到制度会影响以集群为基础的发展。由于财政分权,中国的地方政府积极推进以集群为基础的发展,然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政府在促进产业政策方面是相当消极的。Huang et al.(2008)发现,发展中国家中小农村企业面对的一个主要障碍是他们常常在获得合适的技术方面有困难。而集群依赖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分工,将生产过程分解为很小的阶段和步骤,这就降低了产业进入的技术和资本门槛,小型创新企业能够通过一个很窄的生产阶段而进入产业,有利于发挥企业家的才能。
4.政府在工业化中的作用
对于政府在工业化中的作用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从许多富裕国家(包括美国、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发展经验看,支持者认为大量的政府干预是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关键,而反对者则认为由于政府失灵(无法选择合适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以及有效地实施政策),挑选胜者(picking-winner)战略很可能会失败,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但是政府失灵的潜在危害并不意味着较少的干预总是最优的选择,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之间存在着权衡,特别是对于那些无效市场主导的最贫困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需要大推动从而助其脱离低收入陷阱(low-income trap)。Bjorvatn and Coniglio(2011)从20世纪80、90年代81个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和人均GDP增长的描述分析指出,减少产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并不一定经历更快的竞争增长。该文的理论模型表明,雄心勃勃的政府支持投资的政策对于刺激工业化是需要的,这些政策在最不发达的国家可能更为成功。然而在发达国家,产业政策的害处会大于好处。因此工业化政策是否会导致大推动或大失败(big failure)依赖于所处的环境。贫穷国家在实施放松管制和私有化政策时要三思而后行。
5.其他有关工业化的研究
信息不对称和协调的失败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例如,林毅夫(2007)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重复建设时提出了“潮涌现象”,认为由于有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发展中国家众多企业可能同时看好某一个相同产业,企业的投资会像浪潮般涌向这个产业,从而造成重复建设。他的研究只强调了信息不对称的一种可能,然而还有另一种均衡存在。针对为什么起点相似国家的工业化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结果,Rosenstein-Rodan(1943)提出,企业推动某产业工业化的投资对于推动其他产业工业化进行投资的企业的利润具有正向影响,也就是说投资者的决定是战略互补的,一个投资者预期收益的增长在于其他投资者的投资决定。这就会导致多重均衡存在:如果没有人投资,不投资就是最优的;如果有其他人投资,那么也进行投资就是最优的。因此,一些国家没能成功工业化的现象可以解释为协调的失败。Englmaier and Reisinger(2008)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国家投资环境这一变量——企业投资的收益率不仅依赖于其他企业投资的数量,也依赖于一国的投资环境,并利用全球博弈方法(global games approach)解决了多重均衡问题。他们的模型显示,正确的信号提供也就是更准确的私人信号能够提高效率,补贴等公共支出作为昂贵的信号(costly signals)能够克服信息提供时的信用问题,吸引投资者进入不具吸引力的国家。
产业崩溃(industry collapse)已经成为中国近来经济发展波动中的重要现象。所谓产业崩溃,是指在相对短的时期内,产出和就业突然和大规模的下降。Lai(2010)的模型聚焦于外部需求下降导致的产业崩溃。其模型揭示,外部需求的大规模下降和水平国内供给曲线的组合导致国内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经历短期内的产出急剧下降,这进一步导致就业的急剧下降。然而,传统的宏观稳定政策在应对突然的产业崩溃时效果不佳。中国政府需要形成合适的产业结构稳定政策应对产业崩溃,特别是实施对产业崩溃造成的失业工人(特别是来自农村地区的低技能劳动力)进行直接的就业援助。
Tang and Chyi(2008)将企业创业(business entrepreneurship)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他们识别了台湾地区产业TFP增长的三个显著来源:研发活动、通过出口的外部知识扩散、通过建立风险资本(venture capital,VC)的内部知识扩散。技术创新和企业创业能够互相加强从而提高TFP,而风险资本不仅在财务上支持了企业的创办,而且提供给他们管理和营销等方面的指导和专门技能。风险资本的发展能够作为衡量管理和营销知识增长的一个合适的代理。该文建立了能够阐明过去20年间风险资本发展和台湾地区产业TFP增长关系的法律环境指标,包括:资金来源、税收激励和IPO促进。他们发现,风险资本对于台湾制造业及电子和电子设备产业的TFP增长有显著影响,更高的国内R&D增长和通过出口的外部知识扩散也引致更高的TFP增长。
Desmet and Rossi-Hansberg(2009)发现,1970-2000年间,美国县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展现出非常不同的模式。制造业的就业在小的县比大的县增长的快,表明制造业的就业在空间上分散化;服务业呈现出S型模式:对于小县来说,1970-2000年服务业就业的增长和1970年服务业的就业是负相关的,对于中等县正相关,对于大县又是负相关(1900-1920年的制造业展现出与服务业相同的S型模式)。该文从产业的年龄——用从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影响该产业开始所经历的时间衡量——解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差异。影响制造业的GPT是电力,20世纪中期该技术已普遍用于制造业,制造业已经成熟;开始于1970年代中期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对于服务业具有巨大的影响,因此服务业比较年轻。技术变化过程与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一起产生三种力量:技术扩散导致分散;知识溢出有利于集中;土地拥挤意味着分散。在年轻产业,技术扩散在低就业地区占统治地位,知识溢出在中等就业地区占统治地位,土地拥挤在高就业地区占统治地位。这就解释了在年轻产业所观察到的S型增长模式。相比之下,成熟产业的知识溢出弱,从而分散占统治地位,这解释了成熟产业向下倾斜的模式。该文的数据也显示生产率具有相似的规模依赖模式。
二、产业生产率
1.创新、技术与生产率
Ngai and Samaniego(2011)发展了一个跨产业的内生增长一般均衡模型,发现产业的生产率增长和R&D强度的长期差异主要反映在技术机会(technological opportunities)的差异上,技术机会可以解释为知识生产参数,包括R&D的资本强度(capital intensity)、知识溢出和R&D的收益递减(diminishing return)。产业间生产率增长差异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R&D活动的收益递减。尽管其他两个机会因素——新知识建立在既有知识之上的程度以及研究活动的资本比例——在数量上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但理论上也是重要的。Chun and Nadiri(2008)将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分解为过程创新、产品创新和规模经济的贡献。他们发现,产品创新、过程创新和规模效应分别解释了计算机产业TFP增长的30%、40%和30%,表明1990年代后期美国计算机产业的快速TFP增长主要由技术的快速提高引起。计算机产业对整体TFP(aggregate TFP)增长的贡献平均为0.22,解释了几乎1/3的整体TFP增长。该研究与常规的TFP解释有两方面区别:明确地考虑了产品需求和规模经济两方面效应,识别了计算机产业的产品创新对整个经济TFP增长的贡献。Yang et al.(2010)利用2005-2007年5696家电子企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了R&D和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电子产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R&D、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在职培训和雇员、健康保险和退休金)对全要素生产率(TFP)有积极的贡献。R&D对生产率的影响随所有权差异而变化,外资企业的R&D效率高于国有和私人企业。该文的结论表明,为了促进中国的产业转型和升级,政府应该加大对公共R&D的投资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IT技术和产品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但是IT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却有非常不同的看法。例如,索洛就提出“计算机生产率悖论(computer productivity paradox)”,“你能在处处看到计算机时代,除了生产率统计”。Ketteni(2009)利用1984-2001年间42个美国私人产业的数据(包括总产出、中间投入、劳动、IT和非IT资本),检验了IT资本是否有助于生产率(用TFP指数衡量)的提高以及调整成本的角色。调整成本角色的研究认为,新技术的引入会涉及很大的调整成本,因为它们涉及新技能的采用、新组织形式的实施以及互补性投资的发展。IT也依赖于与新的IT设备安装有关的调整成本。该文的研究发现,调整成本是重要的,IT对样本中所有产业的产出增长都有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对于IT密集型产业,此外,IT资本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Dimelis and Papaioannou(2011)利用产业层面的数据估计了1980-2000年间信息技术对美国和欧盟产业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1990年代,信息技术对美国和欧盟的增长都表现出显著的影响,但是ICT的生产率影响主要存在于生产ICT或者大量使用ICT的产业。
2.贸易、外资与生产率
Melitz(2003)的研究显示,企业异质性的存在——企业间资本和技术密集度、规模和生产率差异,会提高产业的平均生产率,导致产业内资源的重新配置。Ramondo(2009)利用智利制造业国内和外国企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了Melitz类型的预言。产业生产率提高是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1)生产率更高的外国企业的进入;(2)低生产率的国内企业退出;(3)更具生产率的国内企业的进入。同一产业中的外国企业进入对国内在位者存在积极的溢出,国内在位企业的生产率也会因此提高,但是它们的市场份额会由于竞争加剧而降低。
国际贸易被认为是国家间技术性知识(technological knowledge)溢出的重要渠道,发展中国家被认为是贸易促进型(trade-facilitated)技术溢出的主要受益者。通过促进技术溢出,贸易能够引起国家间的收入收敛,而收入收敛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国家间的收入差异主要归因于生产率的差异,而生产率的关键决定因素是技术(Prescott,1998)。R&D溢出不是消极的过程,而是积极的过程,企业需要主动的努力以全面吸收。之所以需要这些努力是因为知识的默会和复杂特性,需要特定的能力吸收知识,企业可以通过投资于R&D、工厂和设备以及雇佣有技能的工人来建立起这些能力。Parameswaran(2009)利用印度制造业企业的微观层面数据,检验了贸易促进型R&D溢出对生产率的影响。贸易相关的R&D溢出可分为两种:租溢出(rent spillover)和知识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Griliches,1979)。租溢出通过购买内含更好技术的资本产品时发生,但是仅当购买的R&D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低于能反映出全部质量时产生(full‘quality price’)。知识溢出则发生于一个企业的思想被另一家企业所利用时。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知识溢出并不依赖于投入的购买价格低估了它的质量。有几个渠道可以促进知识溢出:个人交往、熟悉技术优异的产品、关于专利的信息、科学杂志的出版以及参与学术会议。贸易能够促进贸易参与国之间的这两种溢出。从研究密集型国家进口资本商品能够将R&D受益转移到进口国家。贸易还能够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与发达国家的制造商、购买者和产品的交互作用,促进知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溢出。该文的研究表明,R&D溢出对于生产率有显著的影响,并且在技术密集型产业更大;对工厂和机器的投资(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生产的)都提高了知识溢出对生产率的影响。
Liao et al.(2009)利用随机前沿方法检验了工业化国家R&D通过贸易作为技术溢出渠道对东亚经济体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他们发现内涵于贸易中的国外技术溢出是生产率增长的推动力之一。样本国家关于国外R&D的产出弹性在2.5%~19%之间,越是发达的国家,国外R&D对其生产前沿的影响越小。外国R&D的平均回报率在3%~21%之间,它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年均2%,显示样本经济体TFP的提高利用了更发达国家的技术积累。由于TFP增长率比较明显,表明TFP增长解释了产出增长的很大一部分。Ruan and Gopinath(2008)利用1993-2004年间34个国家(11个高收入、23个低收入)5个食品产业的数据,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食品加工业生产率和空间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自由化的贸易制度能够提高产业的平均生产率,产业内市场份额和资源的重新配置非常依赖于国家的相对生产率增长。比全球平均水平拥有更快生产率增长的国家通过获得更大的全球市场份额和资源而受益于贸易自由化。国家边界通常会降低边界两侧经济变量(variables)的移动,这被称为边界效应(border effect)。Vigfusson(2008)研究了边界效应是否影响产业层面的生产率波动。对于美国和加拿大来说,跨境的生产率波动的相关性要比以往报告的要高,但是仍小于一国之内相似产业之间的相关性,即存在边界效应。投入使用的相似性有助于解释跨国界的生产率波动的联动。
3.产业和竞争结构变化与生产率
总体生产率(aggregate productivity)的增长一方面来源于构成该产业的企业内部的生产率增长或者产业内部细分行业的生产率增长,另一方面,即使在缺乏内部生产率增长的情况下,总体生产率的增长也可能受结构变化效应的影响,即市场份额从缺乏生产率的实体到更具生产率实体的重新配置。Krüger(2008)利用分解方程对美国制造业领域1958-1996年间的总体生产率增长进行研究,该分解方程考虑了区分4位数水平的450个制造业行业的内源生产率增长以及与结构变化相伴的外源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结构变化用某一产业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或就业的比重衡量。该文的结果显示,即使单一产业的内部生产率增长对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长有主要贡献,以增加值或就业向具有高生产率水平产业的重新配置为形式的结构变化对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长也有可观的贡献。结构变化也是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当结构变化以增加值比重而不是就业比重变化衡量时,结构变化的影响更为突出。从产业间增加值重新配置的角度看,结构变化比就业的重新配置更剧烈,尤其是在高技术和耐用品生产等细分产业组。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仅来自于投入和技术的变化,市场竞争甚至潜在竞争状况的变化也会对它产生影响。Bridgman et al.(2011)对巴西国有石油公司Petrobras的研究发现,Petrobras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它失去法定垄断地位后急剧提高,6年间翻了一番。1995年之前,Petrobras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资本积累和原材料的使用,而TFP几乎没有增长。从1995年开始,TFP快速增长,解释了几乎所有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改革没有立即影响到Petrobras的市场和所有权变化,几乎没有其他企业进入石油开采市场,也几乎没有竞争性的进口,Petrobras仍然在巴西石油市场占据统治地位。这表明,竞争的威胁——甚至没有实际的竞争也会提高生产率。这一发现表明,改变竞争环境对于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是一种有力的途径。
4.对劳动生产率的研究
对经济效率的研究一般关注于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labor productivity)的变化则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规模报酬不变(CRTS)的假设下,劳动生产率变化可以分解为效率变化、技术变化和工人人均资本积累的影响,其中前二者的乘积是TFP的变化(Kumar and Russell,2002)。以他们的非参数前沿方法为基础,López-Pueyo and Mancebón(2010)将6个发达国家20世纪最后20年的ICT生产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OECD(2003)认为技术通过三条主要渠道影响增长:(1)ICT制造业快速的生产率增长以及这些产业规模的增长;(2)设备投资的密集化,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从而改进了劳动生产率;(3)产生于这些技术的对生产率的溢出效应。而López-Pueyo and Mancebón(2010)的研究结果显示,ICT产业劳动生产率的高增长率主要来自于本地化的创新转换到世界前沿的高端技术领域,在较小程度上来自于资本的密集化(积累),同时技术溢出速度的差异不足以缩小与新的前沿的距离。资本的密集化(技术升级)是能够受益于国际技术溢出的先决条件,但是溢出的吸收也需要时间以及国家缩小与前沿距离的能力。研究结论意味着要加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需要投资于物质资本、建立新的知识以及有利于采取变革意愿的政策。
三、创新、技术与产业发展
1.政府研发投资的作用
政府的研究支出与私人领域的相互作用非常复杂。在知识生产中,公共和私人领域会为重要的投入而产生竞争(David and Hall,2000)。当投入的供给缺乏弹性时,公共部门R&D的增加会提高研究投入的价格从而阻碍私人投资的刺激,但是如果缺乏资金,即使最好的投资机会私人部门也难以利用。另一方面,公共研究为私人企业提供了新的技术机会,提高了它们的生产率,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反过来导致更高的私人R&D强度。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共资金通常比私人资金更昂贵、更缺乏效率。公共R&D对私人R&D的最终影响取决于正的溢出效应和负的投入价格效应的相对大小。生命科学是美国公共投资最集中的领域,尽管生命科学领域的R&D投资从以公共投资为主转向以私人投资为主(从1980年的98%下降到2003年的29%),但联邦R&D基金仍有53.7%投向生命科学。在生命科学这一投资密集型且企业主导地位不断提升的产业中,公共机构是否还应该保持如此高的投资水平?Wang,Xia and Buccola(2009)检验了公共资金支持的生物、农业和医药研究对产业研究努力和绩效的影响。需求的拉力和技术的推力都是在解释技术变革如何发生时需要充分考虑的因素。他们发现,总体上,通过公共研究创造的技术机会已经压倒市场需求的影响,成为私人研究投资的推动力量。公共资金形成技术机会,该机会进而为私人企业所利用,这已经成为公共研究刺激产业研究的主要途径。虽然溢出部分由于政府对稀缺研究投入的竞争而抵消,但是剔除竞争因素,公共投资仍然是私人投资的重要补充。Eom and Lee(2011)对韩国产业-大学和产业-政府研究机构(IUG)的合作及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也发现,在IUG合作的决定因素中,规模、R&D强度等传统的企业特征变量不显著,而国家R&D项目的参与在两种合作模式中都是最显著和稳健的,反映出后发经济中政府政策对促进IUG合作的重要性。IUG合作不能保证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成功,但是对企业研究项目的选择或方向产生影响。
2.大学在创新中的作用
Furman and MacGarvie(2009)同样研究美国医药产业,但他们关注的重点是美国医药产业内部研发能力形成的原因。通过对1920-1949年间美国大学-产业相互作用的定性和定量检验,他们发现,1920年代到1940年代间美国医药领导企业从主要从事药剂制造向研究密集型制度的转型,是通过大学的积极参与实现的,特别是通过获得大学培训过的科学和技术员工,以及通过与大学教员间的合作与合同研究。将培训过的R&D员工吸收进私人企业的能力与从领先的大学科学家获得指导的能力的结合,对于企业发展内部的R&D能力以及创造新的制度——私人R&D实验室(专用于创造医疗上有效的新产品)是非常关键的。具有较弱R&D能力的企业主要局限于与本地合作者的工作,而具有较强内部R&D能力的企业主要与本地合作者开展需要一般化技能的小规模项目,与远处的合作者开展大规模项目和特别的项目。与大学开展合作的医药企业在此期间实现了更快速度的专利和实验室增长。Furman and MacGarvie(2007)另一篇同样主题的文章得到类似的结论。他们调查了1927-1946年间美国医药产业中产业研究实验室的兴起,发现大学在企业内部的产业研究实验室中扮演者重要角色。产业和学术研究共同布局(co-located),接近大学研究意味着企业采用产业研究设施以及与科学机构的科学家合作的更大可能。
大学作为以生产和扩散知识为职能的机构,是本地化知识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对于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science-based industries)尤其重要。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由Pavitt(1984)提出,他根据创新的来源和创新过程的特征对产业进行分类。这类产业中的企业也会相对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研发活动上以及与学术机构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大学有多种知识溢出机制:第一,副产品构成了学术知识商业化的重要机制。副产品一般分布于接近母组织(parent organization)的地方,导致企业围绕大学和研究所进行空间集中。第二,劳动力的移动可以被看做另一种重要的知识溢出机制。可移动的雇员从一个组织移动到另一个组织时会转移他们所携带的知识。第三,非正式的知识交换也是知识溢出的重要机制,经常发生于本地化的社会网络中。除了非正式社会网络外,研究合作的正式网络也是一种重要的知识溢出机制,在科学为基础的产业尤其如此。尽管研究合作被看做知识的共同生产,但是知识溢出会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副产品产生。此外,合作研究会带来任何距离内的研究者间的持久的社会关系。例如,以前合作过的研究者会非正式地持续交换知识,研究合作会通过这种方式引起未来的溢出。Ponds et al.(2010)发现,尽管微观层面的经验研究发现劳动力的移动或副产品等溢出机制是本地化的,但并不适用于研究合作,学术型知识溢出既产生于地理上的本地化机制,也发生于长距离的合作研究中,且大部分发生于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地理的接近性既不是组织间知识溢出发生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在以科学为基础产业中,合作更像是建立在潜在合作者的特定知识存在之上,而不是地理的接近。该文的结果加强了既有研究关于大学研究本地化知识溢出的结论,另一方面也显示,对于本地化知识溢出的既有研究忽略了长距离溢出的存在,过度估计了地理对于学术知识溢出的重要性。
3.创新的内外部来源
内部R&D努力和外部引进技术(技术购买、技术转移)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Chesbrough(2003)在他的开放式创新模式(open source model)中指出了外部思想对创新过程的重要性,甚至提出内部研发不再是战略资产(strategic asset)。Freel(2003)等人认为企业内部资源才是创新绩效的主要决定因素,外部网络的创新仅具有有限的影响,也有人认为外部和内部知识的获取对于企业的创新战略是互补的。Tseng(2008)将两个传统的生产要素(物质资本和劳动)和两个创新要素(内部R&D努力和外部引进技术)看作4种最重要的企业投入。企业的绩效用销售和经济增加值(EVA)这两个评价指标来衡量。基于演化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用台湾地区1990-2003年间219个电子企业的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他发现,物质资本和劳动都对企业的销售有积极影响,但是对EVA没有显著影响;内部R&D努力对企业的销售和EVA有积极影响,相反,引进的技术对销售和EVA没有显著影响;尽管物质资本和劳动都比内部R&D和外部引进技术更影响企业的销售,但内部R&D努力对企业EVA的贡献超过引进技术、物质资本和劳动的影响;外部引进技术对内部R&D既不是互补也不是替代关系。Cohen and Levinthal(1989,1990)提出的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概念特别强调了在识别、吸收、利用外部知识之前存在的知识(pre-existing knowledge),创造新知识的企业内部努力不仅有利于外部知识来源的利用,而且也提高了有效利用它们发展新产品和过程的企业能力。因此企业内部能力越大,不同外部知识获取战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越大。Vega-Jurado et al.(2009)以从西班牙2004年技术创新调查提取的1329家在创新活动中活跃的制造业企业为基础,对外部知识来源战略对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发展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他们发现,产业的技术强度越高,与外部机构(特别是与大学和研究中心这样的科学机构)的合作越频繁,这一结论部分地与吸收能力的概念一致,即有能力实施内部R&D的企业能够更好的识别和获得外部知识。然而该文也有一些不同于既有研究的发现:产品和过程创新是相互独立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与不同的知识来源战略相关。过程创新主要受内化于机械设备的知识的活动所推动,与外部机构的合作没有明显的效应;相反,合作看起来对发展新产品是重要的战略,尽管相关性随合作者的状态以及企业运营的领域而变化。没有发现R&D的外包对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作用。
成本的增加、技术的不确定性以及创新商业化的复杂性推动了R&D合作现象。然而大部分R&D合作的研究中均质企业的假设不符合现实。Mukherjee and Ramani(2011)区分了R&D合作的三种形式:仅仅共享信息、仅仅共享固定成本、同时共享信息和固定成本。他们建立一个二阶段博弈模型证明,企业是参与R&D竞争还是在三种联盟形式间选择依赖于三个因素:企业联盟合作者之间创新能力不对称的程度、事后的市场竞争以及R&D固定成本的大小。创新能力接近的企业比不对称的企业具有更大的建立R&D联盟的倾向;最常见的合作形式是仅仅成本共担,这是因为成本共担联盟比其他形式的合作能容忍更高程度的不对称。虽然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任何形式的联盟都优于R&D竞争(成本连带信息共享联盟是最优的),但是如果企业能力不对称、垄断收益很高,没有R&D联盟能够形成。因此,在面临社会选择和私人选择冲突的时候,对促进R&D合作的技术园区的公共投资就是合理的。
4.技术转移和溢出
技术创新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赶超的关键要素。Fu et al.(2011)探讨了新兴经济体的本土和国外的创新努力在技术变革、赶超中的角色及其相互作用。由于创新是高成本、高风险和路径依赖的,因此获得发达国家创造的知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有效。技术能够通过几种传输机制在企业间以及跨越地区和国家扩散:通过国际贸易的商品流动;通过FDI和OFDI(outward/outfolw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资本流动;通过移民、旅游、学生和工人国外教育的人员流动;非体现形式的知识(disembodied knowledge)通过媒体和因特网的扩散;集成入全球价值链从而受益于国外技术的供应链内转移(Pietrobelli,1996)。但是技术扩散和采用既不是无成本的也不是无条件的,它们与技术能力的构建依赖于企业的吸收能力和互补性资产。只有当地创新能力存在时,跨国公司才会采用与当地经济有深入联系的更加一体化的创新活动,从而产生更多的知识转移机会。但是FDI能够提供基本经营能力的发展,对深化性的能力则不那么有效,大量本土的创新努力才是本土技术变革的主要推动力。
技术系统(technological system)(Leoncini and Montresor,2000)由四个部分构成:技术-科学知识(techno-scientific knowledge);用于生产的工艺系统;市场环境;制度界面。伴随着经济交往的知识和技术流动,例如中间品和资本品的交易,构成了技术系统的技术-经济关系。技术系统的参与者要提高他们的技术存量和面对激烈竞争的环境的适应能力,可以从内部创新或者吸收来自其他参与者的技术以获得技术。有两种类型的技术扩散:非体现形式的扩散(disembodied diffusion)和物化的扩散(product-embodied diffusion)。Guan and Chen(2009)检查了1997年和2002年中国制造业技术系统的特征,综合利用投入产出方法和网络分析来描述系统结构和每个领域的绩效。1997年和2002年,中国制造业产业间的创新扩散模式既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又有显著的差异。第一,2002年表现出低得多的每单位产出的技术强度以及下降的扩散效率。第二,在系统层面,扩散的技术提供方要比扩散的技术获得方更加集中。这就意味着少数产业作为主要的技术扩散源而大多数领域是技术扩散的获得者。第三,化学产业是扩散的最重要技术提供者,其次为金属冶炼和压延产业。普通和特殊机械产业、电力设备产业是最大的技术获得者,前者也是重要的提供者。ICT产业虽然R&D投资比重远高于平均水平,但并不是突出的技术提供者。中国制造业领域的R&D的内涵流动(embodied flow)仍然高度依赖于几个传统产业。
Park et al.(2008)以韩国TFT-LED产业为例,研究了跨产业的技术能力溢出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他们将技术能力分为三类:技术、人力资源和组织、网络。研究显示了韩国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产业向TFT-LED产业的技术能力扩散路线。DRAM的技术能力以投资基金、TFT-LED所需的半导体技术积累、技术的适时投资、DRAM的生产和质量管理系统、关键员工的流动以及组织生产劳动的能力等方式转移到TFT-LED,但从全球和供应商网络转移的技术很少。这对于赶超企业在多元化其业务时具有启发意义,也即有效地利用与新业务在技术上相关的既有业务的人力资源、组织系统和网络,非常有助于实现快速的增长。大量技术适用(technology adaption)的理论模型显示,当企业转向新生产技术时,它们的生产率会先降后升。先降是因为从旧技术运营中获得的经验不能完全适用于新技术,后升是因为新技术使用之后的干中学。Nakamura and Ohashi(2008)对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日本钢铁企业的精炼炉技术从平炉(OHF)转向氧气顶吹转炉(BOF)过程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企业采用BOF技术后,过时的平炉使用的特定经验导致了超过9%的生产率下降。尽管平炉特定经验的丧失,日本钢铁产业依然保持了氧气顶吹转炉技术的快速扩散。在这一过程中,日本通产省(MITI)压低了氧气顶吹转炉技术的许可费,降低了日本钢铁制造商接近更先进技术的壁垒,加快推动了新技术的扩散速度,最终使日本实现了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钢铁奇迹。这与Parente and Prescott(2000)关于技术前沿壁垒的移除能够加强经济增长的观点是一致的。
Deng(2008)在知识溢出的经济价值数量化方面进行了努力。该文将企业专利的引用(后向引用)作为企业获得的知识溢出的代理,这被认为是除直接R&D投入外的另外一种创新投入,在Tobin's Q框架下,估计了一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美国半导体企业的市场价格方程,发现内涵于每条专利引用中的知识溢出平均价值为0.6~1.2百万美元的R&D等量(R&D-equivalent)。这一估计意味着企业获得知识溢出的全部价值占到它在同一时期实际R&D支出的一半。这就提供了对相关基础创新的社会回报或外部性的经济价值的一个直接测量。该文发现,随着企业专利总量的增加,后向引用(知识溢出)的价值下降,引用对新企业的价值更大。自引比外部引用明显更有价值,表明在企业内部发生着巨大数量的默会知识或know-how的溢出。
5.R&D的布局
R&D国际化的文献认为,传统的海外R&D的实施是为了使国内发展的技术适应外国市场,而现在海外R&D活动则成为获得国外的本地技术经验和创造新的技术的更加重要的手段。Belderbos et al.(2008)建立了一个扩展的两国家、两企业的战略R&D区位决定模型,并利用1996-1997年间22个ISIC产业的102家最大欧洲制造业企业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检验。企业在决定R&D的国际化时,一方面要考虑来自本地市场竞争对手的R&D溢出以及更高的利用东道国的通用知识池(general knowledge pools)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企业要面对他们自己海外R&D中的know-how消散到竞争对手的风险,这有利于增加对从总部到东道国的企业内国际技术转移的依赖。在国外实施R&D的最优比例依赖于企业内国际技术转移的效率、企业间R&D溢出的程度、产品市场竞争的强度以及通用知识池的重要性。高效的企业内海外技术转移会导致技术落后者增加海外R&D,因为它们母国的市场经营能够从更有效的外国技术采购中获益;技术领先者对转移效率的反应较弱,因为他们的东道国市场经营活动能够更加有效地依赖于在母国开发并转移到海外去的技术。东道国相对于母国更有效的知识保护形成的较弱程度的R&D溢出,会增加技术领先者和落后者的国外R&D比例,但是技术领先者对该因素更敏感。这些发现表明R&D有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大的国家集聚的趋势。东道国相对于母国较弱的产品市场竞争鼓励落后企业的国外R&D,但是对于技术领先者的国外R&D有负面影响。更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鼓励领先企业从事防御性的国外R&D以利用他们的技术优势以及占领更大份额的本地市场。相比之下,落后者更愿意将R&D集中于母国以保障他们母国的市场地位。无论是领先者还是落后者都会被吸引到具有更大的通用知识池(与产业相关的许多关键技术活动)的国家,以及在他们经营更大制造工厂的国家开展更多的国外R&D。
Ibrahim et al.(2009)发展了一种基于专利分布的结构化方法用以识别特定产业的技术集群。他们将发明者分成两组:集群内的发明者和集群外的发明者。根据知识的形式(默会的和明示的)和发明者搜索特定的本地来源的知识的能力(个体的或集体的),将本地化的知识区分为四类:本地个人的默会知识、本地非解码的明示知识、本地解码的明示知识、本地集体知识。他们测度了不同类型的本地化知识对于两种不同发明者的影响。就本地化知识的溢出来说,技术集群中的本地知识来源对于集群内的创新者确有影响,但不同的本地化知识的重要性不同,其中本地化的集体知识最为重要,而本地化非解码的明示知识以及本地化解码的明示知识的作用并不明显。
6.其他创新研究
Mudambi(2008)指出,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中,除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与技术有关的经验外,企业也可以通过控制多个价值链活动以利用联系经济(linkage economies)。联系经济产生于与不同活动相连的生产功能之间的联系。如果企业具有进行不同活动间的协调、学习和创新的高水平能力,它就具有了联系经济。高水平的联系经济意味着控制价值链的多个活动以提高每一个的效率和效力。联系经济建立在企业专有的惯例(routines)和程序之上,产生于知识从企业内部的一个活动向另一个活动的转移。联系经济是解释产业内不同水平的垂直一体化的一种重要的知识为基础的方法。从价值链控制的角度,可以区分两种基本的战略:一体化战略强调控制多个价值链活动以利用联系经济的优势;相反,专业化战略聚焦于识别和控制价值链的创造核心并外包其他活动。由于后者不能利用联系经济的好处,因此他们必须通过开发全新的价值主张(架构创新)以超越既有市场的预期。在布局维度上,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利用不同区位比较优势的战略,导致企业活动展现出共同的地理分散模式。
需求和供给因素对创新和技术的生命周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对二者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在技术生命周期不同阶段角色的研究却很缺乏。Kim and Lee(2009)建立了一个要素和需求引致的创新模型,用以分析技术生命周期中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的创新来源之间的动态平衡活动,并通过用于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的DRAM经验地支持了一种技术创新的演化理论。其研究显示,技术创新的两种驱动力是高度地相互关联的,对于创新过程的整体二者缺一不可。产品的边际价格是决定技术创新主要力量(技术推动还是需求拉动)的主要因素。从全球DRAM市场的经验研究得到L曲线(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对于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可以用L型曲线来描述),在技术周期的早期,技术推动比需求拉动重要,但随着生命周期的演化重要性下降,需求拉动变得越来越重要。
四、国际化与产业发展
1.国际贸易与产业发展
Grossman and Helpman(1991)提出“出口中学”(learning by exporting)的概念,有形商品的交换能够促进无形知识的交换,因此贸易使一个国家能够接近其贸易伙伴所拥有的不同知识,知识通过贸易的溢出有助于母国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有助于降低国家间的技术和收入差异。Salomon and Jin(2008)则利用西班牙制造业1990-1997年的样本,检验了出口如何差异化地影响技术领先和落后产业中企业的创新产出。实证研究表明,出口提供给母国企业获得目标市场中更先进知识的机会,出口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在出口后提高,但是技术落后产业(technologically lagging industries)中的企业从出口学到的要比技术领先产业(technologically leading industries)中的企业要多。这一结论表明,增加贸易壁垒以保护技术落后产业的政策可能难以提高预期的增长和发展效果,相反,消除贸易壁垒、实施出口导向的增长政策对于技术落后产业的发展可能更有效。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技术性知识(technological knowledge)的不同是各国产业间生产率差异的主要来源。商品贸易能够直接和间接地传递知识。企业可以直接学习并模仿新技术;间接地,企业可以使用新的中间商品,这些商品中内涵有最终商品生产所需的先进技术。Unel(2008)提出一个经验模型,中间商品的贸易是产业和国家间R&D溢出的渠道。特别是该模型将生产率增长与商品贸易中的R&D密度联系起来。他区分了四种R&D:仅在特定产业中进行的R&D;在其他国家的同一产业进行的R&D;在其他国内产业进行的R&D;在其他国外产业进行的R&D。该文利用1973-1994年10个OECD国家12个产业的面板数据,检测了每一种R&D来源对生产率增长的显著性。研究发现,对生产率增长贡献最大的是国内R&D努力,本国的R&D无论对国内创新还是对生产率赶超过程都很重要。尽管国际R&D溢出对生产率增长有积极影响,但是影响并不显著。分析也显示,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直接影响生产率。
2.国际投资与产业发展
对于外国直接投资(FDI)对贸易保护的影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FDI的流入能够消除本地企业从保护壁垒(protectionist barrier)获得的保护租(protectionist rent),因此会降低他们寻求贸易保护的激励,支持自由贸易会产生更大的利益;另一种观点将FDI看作不同主权国家间企业的战略竞争,因而FDI的增长会引起更多的对贸易保护的产业需求。Zeng and Sherman(2009)利用美国反倾销调查的数据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由于反倾销申请通常是由私人产业参与者而不是政府提出的,因此能够比非关税壁垒覆盖率等指标更好地反应对贸易保护的国内政治需求。他们的研究显示,FDI对东道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生存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FDI并没有缓和美国的保护压力,相反,FDI增加而不是减轻了产业对反倾销保护的倾向,即增加了对贸易保护的产业需求。
FDI有两个方向的流动:FDI流入和FDI流出。大部分经验研究关注FDI流入对东道国的影响,对于FDI流出对母国的影响则存在很大争议。批评者认为,投资流出会导致国内经济就业的减少而降低了国内产出;支持者认为,FDI流出能使企业获得国外新的市场或便宜的投入,这会增加他们的国内和国际竞争力,长远上对母国产生积极的产出、就业和生产率效应。Bitzer(2009)利用1973-2001年间17个OECD国家的10个制造业领域的数据,对生产率和FDI直接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证明。结果表明,平均来看,FDI流入与产业层面的国内生产率正相关,而与FDI流出负相关,但是该效应在国家间有相当大的差异。
Fillat and Woerz(2011)利用1987-2002年间OECD、亚洲、东欧35个国家产业层面的可比较数据,检测了FDI在东道国生产率增长中的作用。该文强调了产业结构的异质效应,FDI的潜在积极溢出不仅依赖于一国整体的吸收能力,而且依赖于该经济体接收FDI的具体产业或领域(如该产业是规模效应递增还是不变,技术和人力资本密度、接受FDI的领域与该经济体向上游和下游的国内连接程度)。因此,就生产率进而效率增加而言,FDI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随国家具体的吸收能力、发展阶段以及产业结构和FDI的配置等而不同。FDI的作用在赶超经济中更强,虽然它不能产生经济奇迹,但是它能够在赶超过程的特定阶段发挥催化剂的作用。FDI在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在赶超的早期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赶超国家来说,如果与高投资或出口相结合,FDI通常能对东道国增长产生重要推动。Todo et al.(2011)利用2000-2003年中关村科技园的企业层面数据,检测了从跨国公司到欠发达地区的本国企业这种特殊的技术扩散渠道。该文发现,外资企业的R&D存量对同一产业国内企业的生产率有正面影响,而外资企业的资本存量没有影响。这表明,外资企业产业内的溢出是通过R&D活动,而不是通过他们的生产活动实现的。
过去10年的重要趋势之一是发展中国家FDI流出(OFDI)的出现。工业化国家跨国公司的出现建立在来自于创新活动的所有权优势基础之上,但是对发展中国家企业优势的来源从而使他们能够进行OFDI的研究却很少。Kumar(2008)认为,印度企业优势的主要来源是它们开发具有成本效率(cost effective)的过程和产品的能力,而这种节约的工程化能力又来自于印度企业所处的低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消费者对价格高度敏感,企业需要致力于开发消费者能够付得起但功能上高效的产品的创新。Kumar and Chadha(2009)对印度和中国企业在钢铁产业跨境国际直接投资(OFDI)的案例研究发现,印度和中国OFDI的动机和特征都有不同。印度企业在西方国家的绿地投资和并购主要是为了实现全球化,而中国企业的外向投资主要集中于原材料寻求活动。这一区别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所有权的不同,中国是国有企业并受国家的指导以保障长期的资源安全,而印度企业是私有企业,主要受经理人发展为全球企业的抱负的推动。
3.汇率与产业发展
Zhang and Wang(2010)利用中国纺织产业的三个子产业1999-2006年的数据,检测了成本结构、利润率和生产率,并对人民币升值对利润率的影响进行了估计。他们发现,原材料成本占到整个成本结构的绝大部分(80%左右),劳动成本和资本成本在10%左右或低于10%。这样的成本结构意味着该产业对成本几乎没有控制力,研究时期纺织业的盈利状况(边际利润和资本回报)非常差,特别是2003年后原材料成本的持续上涨使该产业的盈利面临非常大的困难。然而,中国的纺织产业实现了持续的生产率增长,大部分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都要超过劳动投入价格的增长。由于该产业非常依赖于出口,因此人民币升值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基于2006年的数据,他们估计该产业能够承受的最大升值率为每年5%。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于该行业的长期盈利性和最终竞争力非常重要。
五、新兴产业发展
Athreye and Godley(2009)研究了医药产业中国际化与技术蛙跳(leapfrogging)的关系。成功的蛙跳战略需要一些先决条件:发展对技术的吸收能力;获得与新技术相关的know-how和设备;互补性的能力(例如ICT产业中的系统集成和模块化界面,电信和医药产业中采纳产品和质量标准);实现向下一体化能力,例如产品设计、营销能力和创造自由品牌的能力(Steinmueller,2001)。一般来说,在讨论技术蛙跳和赶超时,贸易和内向国际直接投资(inward FDI)的开放是技术转移的主要手段,但是该文的研究显示外向国际直接投资(OFDI)在这一过程中也能够发挥作用,企业特有的优势对于国际化来说既不是必要也不是充分条件。医药产业经历了两个关键的技术不连续时期——抗生素革命和当前生物技术在新药发现中正展现出的潜力。1930-1940年代的美国企业和1999-2005年的印度企业都是在没有多少关键的企业特有资产或优势的情况下走出国门。技术落后企业尝试通过进入增长的市场以克服最初的劣势、发展知识能力,通过国际化战略建立持续的竞争优势。国际化战略可以依赖的三种因素是:技术差距的程度、IPR制度的状态以及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专利数据分析被广泛看作理解技术起源、形成过程和演化作用的一种可靠和客观的指标。Hu and Phillips(2011)使用欧洲专利办公室(European Patent Office,EPO)的世界专利数据库,采用两阶段交互数据收集方法识别了9246个中国申请的生物燃料相关专利,进行了专利族谱分析(patent family analysis)。该文得到以下几个经验结论:第一,中国生物燃料领域的技术发展在2000年前依赖于人类必需品技术领域(human necessity technology field,即食物或非酒精饮料的准备和处理),2000年之后转向依靠国家强大的化学相关领域。这表现出在建立国家创新能力时的演化的锁定效应、技术相互作用的重要性以及知识扩散。第二,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以前向工程(forward engineering)的模式演化,由中国的大学领导而不是由公共研究机构发起。第三,中国的生物燃料技术是应用导向的(application-oriented),2000年以来主要集中于利用发酵和催化技术发展生物产品。Cotti and Skidmore(2010)研究政府扶持政策对美国乙醇生产的影响。美国大部分州和地方政府采用三种基本的财政激励:(1)财务激励,包括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直接补贴和信贷担保;(2)税收减免,包括税款扣除、减税、减征和专门税率;(3)对商品和服务的直接补贴,包括土地、劳动培训和基础设施(Fisher,2007,p.647)。与Edwards(2007)认为政府激励造成市场扭曲和无效率的产出不同,Hahn and Cecot(2007)认为联邦、州以及地方政府的补贴和规制是乙醇产业的推动力量。Cotti and Skidmore(2010)研究了1980-2007年间美国乙醇产能和各州补贴/税收减免的数据,发现指向乙醇生产的一些激励对工厂布局和生产能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剑桥区域、经济与社会杂志》的社论对汽车产业面临的变革进行了分析(Bailey et al.,2010)。包括从大规模生产和消费、流水线为标志的福特主义向以柔性专业化、利基生产和服务(niche production and services)为特征的后福特主义的转变,以独立汽车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为特征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化模式下的区域化——OEMS靠近消费者、以本地化方式组装和设计汽车;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要求整个价值链的创新能力,通过模块化形成供应完整模块的能力,OEM的模块化外包使得主要供应商在地域上聚集到OEM工厂周围;成本压力(cost recovery)、市场竞争、规制压力和消费者需求促使汽车制造商通过标准化的内部(under-skin)平台提供多种式样的车身(产业的规模经济更多的与基础平台、共享模块和部件联系起来);世界范围内的产能过剩(根植于无法将供应与需求匹配起来)。汽车产业将要发生的变化主要是走向绿色及作为其结果的新的消费模式——受转向低碳系统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需求以及与供应限制及新兴经济增长需求相联系的高能源价格驱动的转型,其连锁反应就是为分担成本、分享技能而形成的合资企业和联盟的浪潮。
六、企业成长
在产业演化模型中,知识被看做形成产业周期模式的主要驱动力量。这些模型区分了知识的三种构成:于进入前获得的知识(进入前经验);进入后获得的知识(进入后经验);在创新活动的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创新的经验)。Cantner et al.(2009)利用1886-1939年德国汽车产业生命周期中知识的角色,研究了进入前经验、进入后经验和创新活动对德国汽车产业生存的影响。研究表明,三种知识构成对于企业的生存具有独立的和显著的正面影响。此外,与熊彼特创造性破坏一致,创新活动能够补偿进入后经验。
每年都会有大量的企业从一个产业退出,但是这些企业并非全部死亡。Greenaway et al.(2009)区分了三种企业退出方式:关闭所有经营活动退出、将生产活动转移到新产业、被其他企业并购。该文利用瑞典1980-1996年间3004家雇员数在50人以上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分析了产业退出的不同选择。该文发现,与没有退出的企业相比,关闭的企业平均来说更小,生产率和资本密集度更低,更少出口,多是中间产品的生产者。与继续在产业内经营的企业相比,通过并购退出的企业可能具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但是更低的资本密集度和出口。与退出的选择相比,企业变更产业的决定更加不依赖于企业层面的特征。成功的产品创新是位于或接近市场技术前沿的提升。产品创新对企业的生存率(survival rate)有两个方面的影响:成功产品创新的主要影响是提高了企业的生存率,但另一方面,成功的产品创新也会给竞争者提供收购创新者的激励(或者是因为创新者对在位者是一个威胁,或者是因为创新者提供了快速吸收技术能力的机会)。第二种影响会最终缩短企业的存在时间。局域网(LAN)交换机设备产业在1990年代的快速增长引起大量的进入和退出。在121家进入该产业的企业中,到2005年仅有38家存在,15家通过停业退出,68家被第三方收购。Fontana and Nesta(2009)的研究发现,企业质量(以距技术前沿的位置衡量)、创新资本、进入前的经验、年龄、规模都是决定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企业的R&D努力以及成功的创新对企业存活的可能性有正的影响。然而,如果成功的创新者(位置接近或位于技术前沿的企业)退出市场,它更可能是被收购而不是关闭。这一结果显示,并购是形成企业边界、决定市场竞争以及最终塑造产业动态(dynamics of industry)的关键。
受Gibrat的“比例效应定律”(law of proportionate effect)启发的许多研究发现,小的、年轻的企业要比以雇员数和销售额衡量的更大、更老的企业增长得快。1980年代以来,企业和政策制定者都很关注产业网络对创新和增长的影响。Park et al.(2010)利用1994-2003年间7889家韩国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以前较少被关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中产业网络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他们发现,企业的规模和年龄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对企业生存具有显著的正效应。R&D和出口活动都与企业的成长和生存正相关,分包对企业成长和在位者生存没有显著的影响,集群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成长和生存。
作为企业进入的工作创造、在位企业的工作破坏以及进入和退出企业影响的交互工作创造和工作破坏结果,企业形成(企业进入)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动态关系。Fritsch and Mueller(2004)强调了新企业产生对经济发展的两种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新企业形成对就业的第一个影响是工作的创造。随后,市场开始了企业选择的过程。因此,净工作形成可能为正或负并依赖于新的进入者如何发展。一方面,由于缺少竞争力,一些新企业会在一定时间后不得不退出市场;另一方面,一些在位者会因新的进入被迫退出市场。间接的供应侧效应产生于新企业的进入和更激烈的竞争的形成,这有助于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刺激经济的增长。Arauzo-Carod et al.(2008)的研究发现,新企业形成的短期影响为正,中期影响为负,长期影响为正,这就确定了类似研究中发现的间接供应侧效应的存在。因此,评价进入促进政策的效果以及新企业对就业增长贡献要根据是长期还是短期。如果为了增加就业,促进企业进入的政策应该调整为保证市场选择的质量和促进增加值的增长和创新,而避免阻止企业离开市场的补贴政策。
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在许多小企业的价格竞争后继之以淘汰,之后几家存活下来的企业主要进行成本竞争,重点从根本性的产品创新(radical product innovation)转向增量的产品变化(incremental product changes)和过程发展。但是有些成熟产业在增量技术变化和以成本为基础的竞争之后,进入技术的非连续(technological discontinuities)和后淘汰(late shakeouts)阶段,这一新的技术竞争阶段以在位者而不是新进入者新一代产品和技术的快速发布为特点。Bergek et al.(2008)针对重型电力工程产业的发电细分市场这一成熟、重要、古老、复杂以及技术领先的资本产品产业的四家企业(GE、Westinghouse、ABB、Siemens),从复杂系统的视角对成熟资本品产业的淘汰进行了研究,揭示了技术能力在其中的作用。所谓淘汰(shakeout),是指短时期内大量竞争性企业退出产业,留下少数的产业领导者。复杂产品系统(complex product system,CoPS)是具有高单位成本和客户定制程度、几种可替代结构以及深层系统(deep systems)的产品。一般来说,在复杂产品系统产业,连续性的创新在产业演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CoPS的总体结构或主导设计确定下来,通过系统部件或子系统中变化的持续引入,几代新的产品会在结构之下发生。与一般的模型相比,主导设计或标准的出现并不是技术发展速度下降的信号。例如,电力技术等CoPS产业通常表现出相对稳定的企业结构——很少退出和进入,部分是由于高进入壁垒,如安装基础、网络外部性以及技术相互依赖。该文解释了在发电设备市场,四家企业中的两家(ABB和Westinghouse)在淘汰后退出他们主要业务领域的原因。第一,具有由R&D活动建立起来的相关能力基础是复杂技术领域的产品发展基础。特别是为了发展新的子系统,从不同技术领域集成知识非常重要。尽管很难说是内包还是外包更好,但是从该案例研究中有以下观察:内包要求相关领域的内部能力;外包需要在战略和运营层面有效地管理联盟。第二,将技术战略聚焦于细分市场层面与绩效正相关,这意味着技术深度比技术广度更好。第三,开发和推出新产品不像大多数能力文献设想的那么重要,解决交付后的问题和保障高运行可靠性是复杂机械领域的关键。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