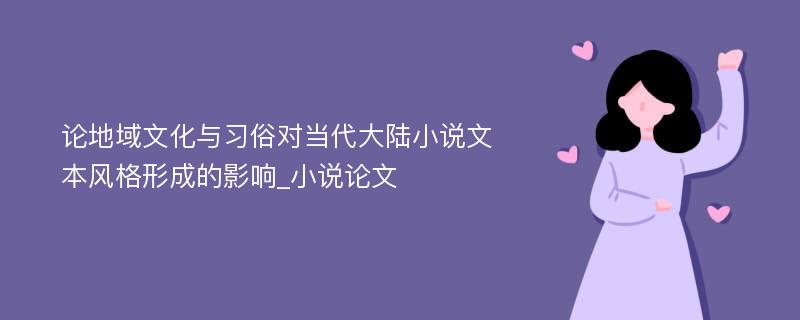
论区域文化风俗对当代大陆小说文本风格形成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俗论文,当代论文,文本论文,区域论文,风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区域文化风俗对当代大陆小说文本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区域文化风俗使创作主体本身成了某种区域文化的载体。二、当带着区域文化色彩的“人”进入小说文本时,小说文本将产生个性化品格。三、风俗习惯作为生活材料直接进入小说文本,会带来个性化品格。四、从小说文本的艺术形式、手法,如风俗、民歌、风物意象、魔幻与轰毁、方言俗语,可看出区域文化风俗对小说文本风格的影响。
区域文化风俗对当代大陆小说文本风格的形成施以重要的影响,这是我国当代小说发展中的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小说家要进行创作,就必须占有一块他十分熟悉的、并置身其中的生活的土地,没有这样一块土地,小说家们的创作就会无所凭依。在文学史上,那些卓有成就的小说家们,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文学的永恒正取决于作家对这块土地独特的文化风俗和生活底蕴的审视和表现。美国现代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就是以写“家乡”的小说闻名于世的,他说:“打从写《沙里多斯》开始,我发现我家乡的那块邮票般小小的地方倒也值得写一写,只怕我一辈子也写它不完,我只要化实为虚,就可以放手充分发挥我那点小小的才华。”①在我国现代小说家中,沈从文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总是以“乡下人”自居,他的“乡下人”有着特定的区域文化内涵,即湘西这块封闭、朴实而又神秘的土地上生存着的人们,他真情地歌咏这块土地上田园牧歌式的淡泊生活和真纯和谐的人际关系,他尽力描写他们“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②。在当代,赵树理保持了他在解放区创作的一贯风格:地方色彩、乡土风味浓郁,康濯曾说过,赵树理的《登记》“仅仅是他家乡的《登记》”,他说有些地方的剧团改编了这个作品,就已经不是赵树理的《登记》了,因为失去了《登记》的地方特色③。到新时期,许多大陆小说家都自觉地发掘“故乡”的生活宝藏,邓友梅之于北京,陆文夫之于苏州,贾平凹之于商州,韩少功之于湘西,等等,他们根系魂绕于此,他们的艺术生命是这一块块土地赐给他们的。看来,区域文化风俗对于小说文本风格的形成有着普遍意义。正是由这些进入小说创作审美表现世界的不同区域的文化风俗和现实生活,给小说文本带来不同的区域文化色彩,形成小说文本的风格,当代大陆小说文本风格的形成,也同样如此。
区域文化风格对当代大陆小说文本风格的影响,首先通过对创作主体的影响体现出来。特定的区域文化孕育着小说家,塑造着小说家的主观世界。尤其是区域文化中的群体思维模式和心理因素,影响着小说家的包括直觉或感受方向在内的主观世界,诸如精神气质,情感内涵,表情达意的方式,乃至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等等。因此他本身就成为某种区域文化的载体和体现者,以至于形成了与这种区域文化同质同构的心理定势。由此,他的小说创作就必然会体现该文化区域的独特风采。如赵树理小说创作中体现出来的线性的艺术思维就脱胎于山西民间说唱文学。新时期大陆小说家“土生土长”的似乎更多,陆文夫、邓友梅、汪曾祺、刘心武、何士光、贾平凹、韩少功、路遥、李杭育、张炜、池莉、方方等等,他们的“人”和“文”都带着一地的风采,以至于如陆文夫被称之为“陆苏州”,他的小说艺术被台湾作家施叔青称之为“心中园林”④。其次从表现主体的角度来看,区域的“人”也影响着当代大陆小说的文本风格。卡西尔在《人论》中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⑤,作为生活在特定区域的“人”,他的行为模式及其符号化就必然打着深刻的区域的烙印,区域文化对他的影响就必然如遗传基因一样深植在他的意识和潜意识深处,他由此而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的区域色彩的人。小说以写“人”为中心任务,当带着区域文化色彩的“人”进入小说文本时,就给小说文本带来个性化的品格。在当代头二十七年的大陆小说创作中,个性最为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马多寿、朱老忠、梁三老汉、盛佑亭等,都是“土生土长”的人,他们和小说的环境构成一种内在同构的性质,形成一种互动的和谐关系。在新时期小说中,邓友梅、刘心武笔下的“北京人”,陆文夫笔下的苏州“小巷人物”,李杭育笔下的“渔佬儿”、“画屋师爹”,莫言笔下的“我爷爷”、“我奶奶”,邵振国笔下的高原“麦客”,李锐笔下的吕梁山人,张贤亮、路遥等作家笔下的西部妇女形象,等等,都是浸润着区域文化神韵、有着区域文化内蕴的人物形象。不少作家把刻划带着区域文化特色的人物性格作为自觉的审美追求。再次,风俗习惯作为生活材料直接进入小说文本,也带来一种个性化的品格。这里试以池莉的《太阳出世》和刘心武的《钟鼓楼》所刻意渲染描写的迎亲习俗为例。这两个作品描写的迎亲场面都发生在80年代,一在武汉,一在北京,两场婚礼的男女双方都属小市民阶层。《太阳出世》中的新郎赵胜天结婚得到大哥赵胜才的全力资助,其原因是赵胜才原是屠宰工,找对象碰过许多钉子,当个体户发了大财后,为“他的荣誉问题”,要把弟弟的婚礼“按武汉市第一流的水平办”,于是他为弟弟精心策划了迎亲的过程和方式。武汉是商业都市,“喜欢显”是这里市民的文化心理特点,既是阿Q式的“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了”心理的另一面的反映,又有着武汉小市民心理特有的表现形式。武汉小市民“喜欢显”是显钱,显财,他们的“显”是赤裸裸的、大张旗鼓的,又是琐屑的、卑微的、荒唐可笑的。为了“显”,赵胜才才耗巨资把弟弟的婚礼办成“武汉市第一流的水平”;为了“显”,迎亲才雇用“麻木的士”;为了“显”,才出现“一支竹竿高高地挑着煤气户口卡”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细节;为了“显”,才撇下十分钟就能走完的直道不走,而要绕上许多倍的路程去大张旗鼓地“游行”。池莉的《太阳出世》对武汉小市民这种风俗习惯和产生这种风俗习惯的文化土壤、文化氛围、文化心理的生动传神的描写,使文本形成反讽的叙述风格。《钟鼓楼》的迎亲场面则另有特点。新郎薛纪跃和新娘潘秀娅都是售货员,可谓门当户对。但正因为门当户对,潘家就特别注重迎亲礼节,并要潘家七姑担当“送亲姑妈”的重要角色,专挑薛家的不是。首先是要求小轿车迎亲(和武汉小市民迎亲雇“麻木的士”形成鲜明对比),尽管潘家住在一条窄小的胡同里,但还是要求把车开到门口,由此,七姑和潘家的人获得一种莫大的精神满足。这种习俗表现了北京这座文化古都重礼的文化特色,和武汉这座商业都市重金的文化特色形成鲜明的对比。北京市民重礼的文化风俗与正宗的儒家文化最为贴近,更具历史蕴涵。《钟鼓楼》通过对这种文化风俗的描写,把邈远的历史和活生生的现实联接起来,形成一种庄重深沉的叙述风格。
最后,区域文化风俗对当代大陆小说文本风格的影响,还通过对其艺术形式和手法的影响体现出来。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直接。因为风俗既是历史的沉积,又是现实的存在,既具物质性,又具精神性,既具共时性,又具历时性,故风俗常常成为情节发展的主要契机,结构安排的中心纽结,由此形成不同风格的艺术结构,就象各种建筑结构具有殊异风格一样。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商州》每一单元的三节中用第一节集中写商州地区的文化风俗,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追溯现实存在与历史文化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形成一种互补互应的结构章法。邓友梅《烟壶》中的烟壶则成为关连小说整体的纽结,把晚清的时代矛盾、各色人物都拴结一体。他的《索七的后人》也是以商朝的五羊尊和战国的双耳铜盘作为情节的契机和结构的纽结,两件历史文物连结了索七和他儿子两代人的命运。邓友梅的文化风俗小说大都是用风物意象作榫结的。刘心武的《钟鼓楼》则被称为“花瓣式”或名“剥桔式”的结构形态。作者以北京钟鼓楼下一个四合院里九户人家为中心,反映了近40个颇具社会代表性的人物的经历、命运、心态和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多层次、全方位地再现了“当代北京市民生活的社会生态群落图”。对于这样一部30万字的长篇来说;要表现40来个人物为主组成的“生态群落”,要把现实情节限制在“1982年12月12日这天上午5点到下午5点12个小时里”来表现,并且还要有很强的历史纵深感,情节结构的安排规整是一个大难题。而四合院充当了“大主角”,它既成为结构的纽结又成为结构的框架,它把各个人物横向地组合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严整的结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处置得有条有理,尊卑分明,主次清晰,真可谓“巧夺天工”。同时,四合院是封建文化意识物化的表现,它很自然地把历史和现实纽结在一体,把今天的“生态景观”和古老民族的文明史接合起来。张承志的小说文本则擅长由某一富有魅力的民间传说作为中心纽结,这种民间传说反映了深刻的草原民俗心理,给作品带来理想化和富有深沉广博的情感内蕴的特色。长篇《金牧场》的结构中心纽结是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人们传说中的“金牧场”,它成为理想的象征,围绕它,小说展开了对历史和人生的描写。短篇《九座宫殿》也类似这种结构形态。“九座宫殿”那片“干净的乐土”只存活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以它为中心纽结,作品写出了理想与现实之间深刻的矛盾。中篇《黑骏马》则以一首古老的民歌作为小说的依托和结构框架,古歌歌咏的是草原上一个美丽而悲壮的传说,它给小说文本带来一种深沉的旋律,造成一种超越具体时空的广远博大的意境。
区域文化风俗对当代大陆小说文本艺术形式和技巧的影响还表现在诸多方面,它们都指向小说文本风格个性化这一终极目标。一种常见的形式表现为带着浓郁的区域文化色彩的民歌进入小说文本,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民俗氛围的烘托,叙述节奏的调整,抒情意味的加浓,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而体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如《芙蓉镇》中胡玉音和秦书田同居以后,在不敢点灯的晚上,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和着民歌《喜歌堂》,表达了这对苦命夫妻的酸甜苦辣,深广的忧愤,表现出深沉细腻的特点。而《最后一个匈奴》把陕北信天游民歌穿插其中,白日里想你饭不吃,/到夜晚想你偷偷哭。//白日里想你认不上针,/到夜晚想你吹不谢灯。//前半夜想你不吹灯,/后半夜想你翻不转身。//想你想成病人人,/抽签打卦问神神。//……给小说文本带来的是回肠荡气的热烈粗犷,刻划了陕北高原人民的整体性格。
风物意象成为象征意象,增大文本的“张力”,使文本既具多重暗示的意义,又具明晰的外延,也是常见的表现形式。如《老井》中“井”的意象象征着我们民族坎坷艰难的命运,愚昧保守的心态和艰苦卓绝的抗争精神。陆文夫《井》中的“井”的意象,则使我们想到封建的文化遗毒,传统的习惯势力和极左路线流毒的祸患无穷。李锐的《眼石》中的“眼石”成为女人命运的象征。莫言小说更善用象征意象,他说,“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汤寡水。空灵美、朦胧美都难离象征而存在”。⑥他的“《红高粱》系列”中那一望无际的红高粱是“笼盖全篇的象征”,“它不是肤浅的‘兴’和‘喻’,不是为‘比附’而设的可有可无的装饰,它本身也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生灵,与小说的人物平行,就象‘神话模式’之运用于小说,作为民族精神的异质同构对应。红高粱与小说人物意合为巨大意象,共同奔赴揭示民族性格底蕴的目的地”⑦。
魔幻、轰毁等技法的运用也受到区域文化风俗的影响。新时期大陆小说家们借鉴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技法,但这种借鉴必须有根植它的文化土壤。新时期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较深的作家,如莫言、陈忠实、韩少功、彭见明、扎西达娃等,他们所占有的那块土地都有着魔幻神奇的文化风俗。莫言的山东“高密东北乡”、陈忠实的“白鹿原”、韩少功的“湘西”、彭见明的“洞庭湖”、扎西达娃的“青藏高原”都是如此。如彭见明的《大泽》对神奇的巫术作了许多描写,这种神奇的描写当然和洞庭湖巫术盛行及人们对它虔诚信仰的风俗密切相关。而尹林垸最后“两千余生灵,不到几年功夫,全部死绝”的“轰毁”结局,也是湖区血吸虫病肆虐和人们的愚昧落后所致。同样,韩少功的《爸爸爸》中描写的鸡头寨寨毁人亡的“轰毁”结局,也是由鸡头寨文化环境的愚昧落后造成的。我们不能把这些手法的运用仅仅看作是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简单移植。
方言俗语对当代大陆小说文本风格的影响就更为显明。方言俗语是区域文化风俗的承传载体,是区域文化风俗赖以留存、承传的媒体之一,它本身又成为区域文化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方言俗语的形成和某一区域人们的文化心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方式以及自然生态、地理背景等等因素密切相关。用方言写作很容易形成小说文本的地域风格,也较易凸现人物的个性。《山乡巨变》和《创业史》这两部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力作所表现出来的地域特色,很大程度上就得力于方言的运用。《山乡巨变》写邓秀梅在“入乡”路上碰上农民盛佑亭,邓秀梅问他多大了,他说:“痴长五十二,命好的,抱孙子了。我大崽一死,剩下来的大家伙,都是赔钱货。”仅仅几句话,就传神地写出了这个湖南老农民幽默风趣的性格,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痴长”、“大崽”、“大家伙”、“赔钱货”都是很有文化内涵、很有表现力的方言词汇。《创业史》中的落后农民王二直杠一直抱着“天官赐福”的观念,他用这种观念解释土改分地时说:“这也是天官赐福喀!我的天!要不是天意,杨家和吕家大片的稻地,一块一块弄到手的,平地一声雷就完了吗?要不是官家派工作人来分地,庄稼人敢动吗?甭吹!还是天官赐福喀!”特有的方言语气词,“天官赐福”、“官家”、“工作人”这些方言俗语也将这位关中平原农民的落后顽固的性格形神毕肖地刻划出来了。方言俗语对当代大陆小说文本风格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注释:
①见《福克纳评论集》。
②《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45页。
③《忆赵树理同志》,《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辑。
④《陆文夫的心中园林》,《人民文学》1988年第3期。
⑤《人论》第34页。
⑥《天马行空》,《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2期。
⑦雷达《评〈红高粱〉》,《文艺学习》1986年创刊号。
标签:小说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风俗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 钟鼓楼论文; 读书论文; 太阳出世论文; 陆文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