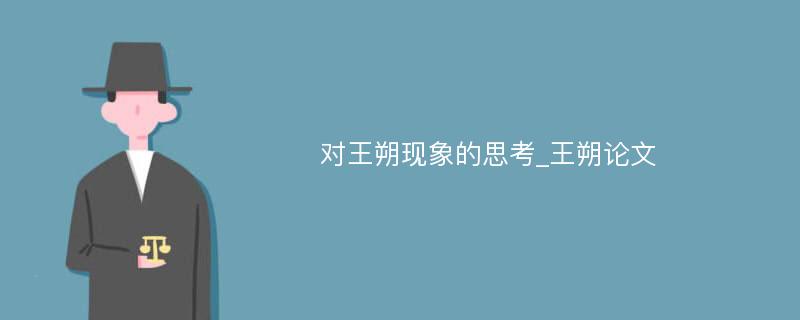
王朔现象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朔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王朔现象的实质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这种大众文化是商品经济社会的特有产物。
关键词 王朔现象 思考 文学理想主义
一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王朔的诞生并非偶然。与其说是他选择了这个时代,倒不如说是时代选择了他。因此,考察王朔的位置是必要的,只有找到了王朔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位置——坐标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王朔,才能比较直观地认识王朔产生的必然趋势。
王朔的第一篇有影响的作品是发表于1984年的《空中小姐》。这是一篇非常纯情的爱情故事,现在重新阅读,仍感余香满口。然而这种过分的纯净似乎使它显得与王朔的真正风格不相谐调。只有到了1985年,先是《浮出海面》,继而《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玩得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编辑部的故事》等小说与影视剧的批量问世,才使王朔真正成为王朔自己。所以我们说,作家王朔的诞生,应在1985年。
那么,1985年意味着什么?1985年意味着中国新时期文学开始发生明显的变革与转折,这种变革与转折的标志是多方面的,评论界已有诸多论述。但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标志便是文学理想主义的充盈到失落的变化。因此,以1985年为界可把新时期文学分为前后两大阶段。进而以此为依据,我们还可把迄今为止的新时期作家约略分为三个代别:早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诸作家为第一代,寻根作家为第二代,寻根后新潮作家为第三代。三代作家各以自身的文学行为清晰可鉴地昭示出文学理想主义由充盈到失落的历史轨迹。
第一代作家所开创的文学活动是真正的理想主义的,其主要作家以王蒙、刘心武、张贤亮、蒋子龙等人为代表。他们的作品所讲述的本质上是一个“愿望”的故事,在经历了文革十年(抑或更久远)的大断裂之后,他们试图接续、修复和重建50年代那个天真而温馨的乌托邦旧梦,诚然对于他们而言,这一切努力也许是有意识的,也许是无意识的,但无论如何不能摆脱那个昔日的巨影。正象王蒙笔下所反复出现的那些“钟亦成”们,为了那一神圣的“布礼”而甘愿受苦受难,上下求索,虽九死犹未悔。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他们潜意识深处所固有的50年代所受教育的积淀,已化作一种无以化解的内在“情结”,在左右其行为,使他们在看取世界时,价值参照系只能是过去的,因而无论他们怎样求变,这种理想主义的内在因子,都始终积极地起着作用。
寻根文学从1984年打出旗号,1985、1986年达到高潮并很快衰微下来。它横跨1985年而承上启下属于从充盈到失落的过渡阶段,因而便具有了过渡阶段的诸多特征,例如尴尬。这一代作家基本上都是知青,他们世界观形成阶段正处于文革时期,大起大落的现实处境造就了他们矛盾的痛苦心态:虽然文革铭刻在心头的痛苦记忆使他们对旧有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怀疑,但他们又不可能以一种新的姿态彻底摧毁之,残存的理想主义信念支持着他们试图寻找一种永恒的超越性价值,他们面对着民族现代化的艰难困窘的局面,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企图在民族文化层面中挖掘民族生存,民族心理的恒定结构,他们的视点是古典的人道主义。这一基本立场使他们同80年代前期的文学理想主义脐带不能断绝,但现实的困境与观念(文化、哲学)的挑战,使他们的处境异常尴尬,他们在“现代性”与“历史性”的夹缝中求生存(陈晓明语)。正如一位论者所指出的:寻根作家是一批裸露于荒野上的弃儿,①他们无家可归,找不到“父亲”,(“父亲”一词在雅志·拉康那里是法、权和秩序的象征),这种“根”的缺失,“家”的缺失,“父”的缺失,就使他们永难在“家庭”的坐标系中获得命名和位置,也即永远不能从想象界进入象征界。于是寻找的焦虑、皈依的渴望,便必然造成他们强烈的内在矛盾性:一方面他们对民族文化表现出难于抑郁的依恋(恋祖),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它的无情批判(审父),依恋/批判,张扬/背离的二项对立,使得他们在构筑理想大厦时似乎也在准备着它的轰然崩塌。莫言的情况也许很能说明问题,他是寻根的最后一位作家,他虽不是知青,但他的经历和基本思路同其他寻根作家有相似之处。1986年莫言《红高粱》的发表,可以看作是寻根文学的新发展和必然归宿,他把走上困境的寻根文学从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历史沉思中解放出来,改变为对生命强力的自由渲泄,在主观臆造的乌托邦情境中,人的理想得到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想象性满足。从表象上看,莫言似乎轻而易举地超越了那种令人尴尬的处境,但仔细究之,则会发现,莫言的尴尬更不堪言说。他实质上在逃离现实,而且更为彻底地逃进了幻想之域,幻想忍受了他的“利必多”蛮力,成为走投无路的莫言的一个栖息之地。但梦不会长久,幻想终归要破灭,大写的人不可避免地要颓然倒地,正如一位颇有才气的青年论者所说:“80年代关于人的想象力已挥霍干净,英雄主义的主角怀抱昨天的太阳灿烂死去,理想在时代的终结倒也干脆利落。”②
事实上,理想主义与非理想主义的界限并非黑白分明,它是一种镍币的正反两面,当这一面黯然失色之后,另一面便开始浮出历史地表。1985年《人民文学》第3期推出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成为理想主义失落之后的第一声叹息。之后,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王朔的《浮出海面》及其他作品,陈建功的《鬈毛》、刘毅然的《摇滚青年》等小说的发表,在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现代派”与“伪现代派”之争。在这场争论中,有人赞扬,有人拒斥,有人恐慌,显示了它对文坛的震撼力,它似乎正是一个宣言,宣告了文学理想化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非理想化时代的开端。如果说,寻根文学的着眼点是民族整体生存状态的批判,而这一批判往往从古老蛮荒的过去寻找题材,从而显露出某种程度的对现实的逃避的话,那么,“现代派”文学则将视点转向现实,从个体生存的角度,演示人的当下困境。随着《你别无选择》的获奖,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到来了。
毫无疑问,王朔应该属于这个时代,他不仅诞生于这样的文学背景之中,而且也诞生于产生这一文学时代的意识形态氛围。众所周知,1985年以后,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由利益分配不均而引起的各种矛盾空前尖锐,新旧交替中体制的不完善,使诸如官倒、腐败等阴暗面日益暴露,旧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也日益显出虚伪和过时。同时,西方第一世界的各种价值观念也蜂涌而入,成为左右人们生活趣味的重要参照系。在各种因素的促使下,一种讲求实用,追逐实利的风气迅速在国民中滋生,价值失落了,理想主义成为滑稽可笑的代名词。所有这些都成为刘索拉、王朔诸人诞生的原发性情境。
文学反映生活,文学总是投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说法好象已不时髦,但细究起来又十分真实,世界上绝不会有纯而又纯的文学。美国学者杰姆逊教授说:“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立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里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③从刘索拉、王朔甚至一向被评论界称为形式主义的先锋作家们(马原、余华、苏童、格非等)身上不是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吗?
于是适应现实与文学发展的潮流,王朔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是一个异端的位置。王朔似乎是一匹不祥的黑马,当他以卓尔不群的彻底反叛姿态踏足文坛,就给正统的文学圈内一种非我族类的异样感,于是拒斥、争议,一会儿推给通俗,一会儿又判给新潮,他在通俗与新潮之间,难于确切地加以界说。当1988年电影界被称为“王朔年”之后,评论界仍显得相当冷淡,甚至轻蔑地称其为“痞子写,痞子演,痞子看”的“痞子文学”。
那么实际是否如此?王朔的文化意味何在?这个答案还须从王朔的本文系列中去寻找。
二
在通读了四卷本《王朔文集》之后,我愈来愈清楚地感觉到了王朔的整个本文系列尤其是前中期作品,所努力进行的是一种文化解构运动,这种解构的文化功能指向是对某种价值禁忌的反抗。不过这种反抗是盲目的,由于盲目又多少透露出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喜剧的悲凉,由于盲目则又使作品笼罩着一种浓郁的流浪情调,进而使这种情调成为王朔人物的最内在气质。
王朔塑造了这样一批人物,要么是孤儿或者半孤儿,要么是有家也不归,他们是真正的“无父的一代”。他们浪迹社会,放浪形骸,纵情酒色,违法乱纪,蔑视伦理纲常,成为地地道道的“小痞子”、新型的流浪汉。当然,他们并非是走南闯北地去流浪,而是一种精神性的流浪意识。现实社会的丑恶、价值观念的动摇,理想的幻灭,使得他们以彻底的决绝态度同过去告别,但同时又找不到新的理想,不能确立新的价值。如果说寻根作家还曾有过家园的记忆的话,那么他们则根本就没有家园,没有家园对现代人来说则意味着无尽的精神痛苦,加上无力正面抗争的弱小意识,使他们不可能以崇高的严肃来扮演英雄的角色,于是便只有以恶抗恶,以佯装颠狂的洒脱、玩世不恭、看破红尘来故意“犯规”。如果仔细考究,这些人物同魏晋文人的人生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倒是有一定的相似性——表面上的无所谓难掩内在的深刻苦痛。《玩得就是心跳》中那群“京油子”,整天无所事事,玩世不恭,当小打小闹一切都玩腻了的时候,他们竟别出心裁出玩杀人游戏来寻找刺激,并把不知底里的哥们儿方言牵连进来、把他做成杀人犯,静观警察的追捕与反追捕,“玩就玩他个心跳”。这种游戏人生的作为不正透露出他们的无聊与空虚,痛苦与难堪吗?正如主人公方言向李江云倾吐心迹时所说的:“我其实心里特苦,这点苦水不倒给你倒给谁?我,唉,活活一个苦儿流浪记中国版。”
《橡皮人》的主题其实是写一个异化为非人的“人”(兽)渴望向人回归的痛苦的内心独白。橡皮人在与那群群奸群宿的哥们儿相处过程中,他其实是身不由己的,当遇到纯情姑娘张璐时,他内心残存的一丝人性的光辉又熠熠闪光,在黑夜独处时,他回想着自己童年的纯真,实质上是对今日非人处境的检点。然而,“身不由己做人的尴尬和不做人的不可能”使他处于“二难”而不能自拔。
由此可见,并非象有人说的那样,王朔笔下的人物丢开了一切道德伦理包袱而活得洒脱、轻松、自在。这是不确切的,至少是一种表面文章。王朔说过,他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不是并不等于没有过。王朔说:“我认识到理想主义的问题。但咱们这一代人,说实话,哪儿能没有理想啊!我对真正的理想是珍视的……人类有时需要激情,为某种理想献身是很大的东西,我并不缺少这种东西。但这种东西必须出自内心。我看到的却是这些美好的东西被种种学说……和别有用心的人给毁得差不多了。”④从王朔的这些自白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向非理想主义者的过渡,这种蜕变过程难道是轻松的吗?同时我们看到所谓理想与非理想是相对的。人在本质上都是理想主义者。德国当代哲人海德格尔就认为世界是由短暂者、神圣者、天空和大地这四维统一的结果,缺少了任何一维都不成其为世界,海德格尔称之为“四元”。⑤短暂者是人类存在,神圣者是神性召唤的信使。这里在也可理解为理想与信念。诸神的隐退,神恩的坍塌,是当今世界不完满的标志。短暂者在这种不完满中受到煎熬。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理想主义是用一种统一的价值尺度来衡量的。理想主义指的是对某种固有的价值观及体系的尊崇和执著,而非理想主义则是对它的动摇甚至抛弃,这种动摇和抛弃本身便是对一种更新的真正的理想和价值的向往。但由于这种新的理想和价值具有某种超前性,往往不可把握,因而造成痛苦,我认为王朔笔下人物的痛苦当属这种情况。比如《浮出海面》(电影《轮回》)中的石岜的痛苦,他对舞蹈演员于晶的追求,可以看作是一个象征,象征他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理想的寻找,但一旦结婚,石岜似乎感到于晶并非自己理想中的真正所求,于是便痛苦、自杀。这一处理也许过分理念化了,这样的人物或许不会自杀,但他的痛苦是真实的。似乎告诉我们,所谓理想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它就象潘多拉盒子里那个希望一样。电影《轮回》中石岜的自杀,使这一人物具有了悲剧的特质,这有违于王朔的初衷,也有悖于生活的逻辑。王朔笔下人物内心痛苦的渲泄运作方式往往是喜剧式的。喜剧构成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物行为范式,丑角成为这些人物的最恰切的角色。王朔是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的。我始终认为王朔的人物虽然以“小痞子”,流浪汉的姿态出现,但在他们身上却多少包含了某种未来趋向的进步因素,甚至可以说在他们身上已经显露出新价值的微弱曙色,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就是这些人物之所以并不引起读者的反感,反倒被同情、赞赏甚至于认同的缘故。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人物的力量还太弱小,而且并不是新价值本身,所以使得他们反传统反价值的行为成为盲目的,滑稽可笑的。相比之下,旧价值还十分强大,它所附着的上层建筑仍充满生命力,成为全社会认同的固有秩序。同时旧价值的某些不合理性并非是它本身的错误,而是历史性的。因而它的失落往往具有悲剧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然产生的理想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廖误。因而旧制度的死亡也是悲剧性的。”⑥可见新旧事物的悲喜剧形式是一个辩证的相互转换过程,当旧事物是悲剧,新事物的萌芽必然以喜剧形式开始。马克思说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喜剧的,我们同样可以说,世界历史新阶段的最初萌芽也是喜剧的。
对于王朔而言,他的喜剧形式的最基本手段是调侃。调侃不仅成为叙述话语的叙述方式,而且成为作品人物的一种人生态度,说话腔调。这种腔调并非只是塞林格的简单翻版,而主要的仍是中国社会“泛文化”背景下的原生情境。调侃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反讽和否定,解构与毁灭。在调侃面前,所有的严肃、神圣、道德,理性乃至人自身都无一幸免地遭受了灭顶之灾。当德育教授赵尧舜滔滔不绝、以无与伦比的严肃和神圣来扮演青年导师的角色的时候,一个漂亮的小妞便可以摧毁一切。小说评奖本是十分严肃的事,但菜坛子作奖杯的闹剧又是何等的滑稽!
调侃自身,解构自身,否定自身,这是接近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问题。现代主义认为世界需要修补,而后现代主义则认为世界无法修补。19世纪的尼采说:“上帝死了”,而20世纪的福柯说“人死了”。人的命运由“万物灵长”(莎士比亚语)到“一半是兽一半天使”(托尔斯泰语)再到“人死了”,它一步一步走进了深渊,走进了痛苦,走进无望。这是人类在迄今为止的历史进程中,经受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三次发现的沉重打击之后,对自身丧失信心的表征。由于对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因而更无力追问世界的本源,在他们看来,世界是无意义的,荒谬的,人的局限性是先天决定的。米兰·昆德拉说,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也就是这个意思。可见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大潮流。在王朔的作品中,人物对自身不乏自嘲,在一种近乎绝望的幽默中,显现了对自己无能为力的超脱。
调侃人人,也调侃自身,仿佛成为王朔的一种策略,一种向现存秩序挑战的策略。在他的人物看来,世界上本没有正经与不正经之分,只有不正经与假正经之别,他们毫不隐讳自己的不正经,并且通过这种不正经与假正经的对比,戳穿假正经的画皮,使其显出虚伪、丑恶的原形。这样,王朔的人物便要付出代价:不惜以自身的毁灭,同一切假正经假道学同归于尽。
三
王朔的本人系列所反复演绎的就是以上这一基本主题。但是后期的王朔似乎又在有意识地开拓新路,而这条路子却带有明显的皈依感,给人一种“浪子回头”的改邪归正味道。例如《刘慧芳》、《过把瘾就死》等,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它不仅丰富了王朔现象的内涵,而且还为我们进一步思考王朔现象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成功与失落,升温与降温,异端与皈依,王朔现象成为我们这一奇特时代的晴雨表。
王朔现象的实质,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大众文化不是赵理式的,赵树理的文化指向是民间的或农民的。我们所说的大众文化是商品经济社会的特有产物,指的就是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如电视、广播、报刊、广告等手段形成的一种通俗时髦的流行性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具有从城市向农村蔓延的特点。王朔的本文具有大众文化的诸多特征。
(1)“可读的文本”:通俗化与平面感
前面谈到王朔的位置,他属于中国的“现代派”,这里关键词语是“中国”。同西方现代派相比,王朔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并不颓废,而是十分严肃的,其作家如卡夫卡、加缪、萨特,艾略特,里尔克等,既是文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的作品不仅反抗和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态,而且更重要的是思考人类存在的终极命题,因而是深刻博大的。当你面对着西绪福斯的徒劳与无奈,当你不断谛听着“今天不来明天来”的戈多的宣谕,你对人类存在的尴尬与无助能不有所感悟吗?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所反复思考的“轻”与“重”的哲学命题,是一个怎样困惑着人类的难解的谜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就是人生缺乏实质,人生的实质太轻飘,所以使人不能承受。昆德拉在文论《小说的艺术》中说:“如果上帝已经走了,人不再是主人,谁是主人呢?地球上没有任何主人,在空无中前进。这就是存在的不可承受之轻”。可见其义与尼采的“上帝死了”的命题一脉相承,即指人生根本价值的失落。⑦因此,现代派文学对人生存在的终极价值的思考,显然已超出了狭隘的阶级分析框框,而成为人类性的永恒命题。
相比之下,王朔则显得浮浅,小家子气。而且从根本上讲,王朔对待文学和人生的态度又显得不够严肃,因而透出一定的痞子气来。不仅如此,即使与同时跻身文坛的先锋小说相比(余华、苏童、格非等),无论是从那个形而上的抽象深度还是叙述技巧来看,王朔都相形见绌。王朔的震憾力是观念上的,而这一观念又是作者靠直觉朦朦胧胧得来的,因而不具备超时空的立体深度。王朔似乎不屑于那个深度,这从他对米兰·昆德拉的贬斥上可以见出。⑧但据我看来,王朔并非不想获得那个深度,而是他根本无法达到而已。
然而历史仿佛总是恶作剧。王朔的浅薄反倒成为“芝麻开门”的秘咒。我们不应否认王朔的才华,他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有时甚至相当出色。时代成全了王朔,在这一讲求实用的年代里,精神生活也变得实用起来。对于我们这一文化水准普遍不高的接受群来说,阅读王朔仿佛成为一种比较高雅的时髦举措,从中既可得到某种官能刺激和消遣,同时又可获得一些观念上的满足。
王朔的本文是可读的本文。根据罗兰·巴特的分类,“可读的本文”与“可写的本文”是两种绝然不同的本文。前者按照读者熟悉的密码写成,因而读起来比较省力,但这种本文只供消费不能再生产,一般读者习惯于如此;后者则不同,由于未与读者达成“默契”,因而使他们一时读不懂,但这种文本却给读者进一步发挥主观想象力,进行再创造提供了新天地,读者从不懂到读懂的过程中,阅读思维习惯经受了挑战,从而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可读的本文往往具有时间性,事过境迁,它的意义渐趋于无;而可写的本文则具有较长的生命力。试想一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某些价值禁忌的渐趋放开,王朔的这种通俗而平面化的本文还会有多久的生命活力?
(2)商品化:媚俗、矫情及其他
大众文化的最重要特征是商品化。这一特征也是时代的特征。
我们的时代是商品经济刚刚起步的时代,由于它面对的是世界性的宏大背景,因而起步蹒跚而迅猛,新旧交替、泥沙俱下;时空错置、万象竞生。人类面对商品经济的选择实质上已处于“二难”之中;没有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和历史进步、物质生活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但历史的发展往往以诸多美好事物的沦丧为代价。商品经济一方面带来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却助长了见利忘义,金钱万能恶习的滋生,从而加速了人的异化。金钱成为社会发展的杠杆,同时也成为主宰一切的神奇力量。由于兴奋点单一,使社会更趋平面、机械,缺乏深度,丧失诗意,成为浮躁、浅薄而又矫情夸饰的社会。对于这样一个一切都商品化(或正在商品化)了的时代,米兰·昆德拉则直呼为“缩减”。对此,我国一位青年学者曾作过进一步的引伸,他说:“缩减仿佛是一种宿命,我们刚刚告别生活一切领域缩减为政治的时代,一个新的缩减旋涡更加有力地罩住了我们。在这个旋涡中,爱情缩减为性,友谊缩减为交际和公共关系,读书和思考缩减为看电视,大自然缩减为豪华宾馆里的室内风景,对土地的依恋缩减为旅游业,真正的精神冒险缩减为假冒险的游乐设施。要之,一切精神价值都缩减成了实用价值,永恒的怀念和追求缩减成了当下的官能享受。”⑩问题的可怕不在于这种既成事实的缩减,而在于人们对这种缩减的麻木不仁,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贫乏的时代甚至不能再体验自己的贫乏”。(11)因此,致人于死地的,并不是威力无比的原子弹,而是人性本身:“在人的本性中威胁人的是这种观念;技术的制造使世界有秩序,其实正好是这种秩序,把任何秩序都拉平为制造的千篇一律。”(12)
那么处于这一贫乏时代的文化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这一使世界有秩序化的机械制造中,文艺创作者不复为创造者而成为作坊里的匠人。(比如王朔的电视剧是几个哥们儿躲在豪华宾馆里神吹胡侃地弄出来的)。制造的目的是金钱,这样文化成为商品,文人成为商人、倒爷,而促销活动必然以顾客为转移,因而必然会出现昆德拉所抨击过的“媚俗”。这就是王朔为什么看好电视与影视联姻的原因。电视是最重要的大众传媒,在电视普及千家万户的今天,统治电视的仍然是金钱,没有赞助单位,一部电视剧就不能播映,而赞助单位则趁机抖售自己的广告,广告成为左右人们生活的重要方式,这是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被拉平为千篇一律的生活,失掉个性与创造,成为大众传媒的俘虏。那则尽人皆知的关于农药的广告:“我们是害虫……”竞成为小学生们唱的歌儿。广告造成了全民的失语症,极大地助长了千篇一律和商品化倾向。(13)
在这样的“泛文化”背景下,王朔却如鱼得水,在我看来,王朔本质上是一个商人,不过他所经销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产品。王朔经商不成,被逼成作家,他说:“虽然我经商没成功;但经商的经历给我留下一个经验,使我养成了一种商人的眼光,我知道了什么好卖”。(14)他甚至把作家比作妓女,“除了出售的东西不同,就纯感受而言,甚至行为本身都和妓女无异。”(15)
这种商业化的功利性特强的文学观念,既给王朔以文换钱帮了大忙,但同时又使王朔的作品缺乏必要的历史深度,成为一次性的消费型产品。
然而文学毕竟是文学,真正的文学艺术创作是一种生命活动,即不把逐名与谋利作为第一需要。最近王蒙曾谈到文人下“海”时有一番十分精辟的见解,颇引人深思,他说:文学从来不是一个很好的发财的办法,也不是一个非常威风的事情,威风还是要掌权。……从事文学活动的选择是精神的选择,超功利的选择,如果都是百分之百的功利化,百分之百的市场化,就没有意思了。(16)
事实也是如此,许多艺术大师在从事文学活动时,并非是冲着金钱去,屈原、司马迁、曹雪芹、卡夫卡……有哪一位是以卖文为生的呢?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可谓呕心呖血。作者之所以如此投入,既不为名也非为利,而是在历过一番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梦幻之后的生命感慨。所以题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因此,作家才能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狼狈境况下,坚持把《红楼梦》这一千古绝唱写下去。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生前有许多作品并未发表,他写小说完全是述怀明志式的,并非只为稻粱谋。
王朔自言要写一部《残酷青春》,并无限自信地说:至少要弄成中国的《飘》,一不留神就弄成《红楼梦》了。(17)根据王朔商人性质,我觉得这很可能又是在作广告,因为从王朔的气质而言,他的魅力主要在“一不留神”弄出的具有某些先锋性质的观念上,他既缺乏深度(哲学、文化的),又没有历过一番梦幻后的大彻大悟,充其量也不过是些个人化的艳遇恋情,在这样的时代,人们的兴奋点不一定专注于其中(《爱你没商量》的失败就是明证),因此,只凭这些就想跻身大家行列,恐怕只是一种梦呓。《红楼梦》不仅是言情,它的博大精深是无与伦比的,鲁迅说的从《红楼梦》中道学家看见淫,经学家看见易,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诽谤就是这个意思。自《红楼梦》面世以来,“红学”研究便无有穷尽。而王朔的作品只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看起来他是不屑于深刻的,拒绝深刻,也只能是“一不留神”弄出些皮毛而已。
当然,王朔是一匹黑马,“一不留神”暴出冷门也未可知。因此,我们还是不敢过早下结论,我们将拭目以待。
注释:
①参看孟悦《历史与叙述》,第101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版
②陈晓明《最后的仪式》,《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第128页
③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载《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第48页
④⑧(14)(15)(17)《我是王朔》,第80、94、20、65、94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6月版
⑤参看海德格尔《诗·语言·思》,第135页,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
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⑦⑨⑩周国平《探究存在之谜》,《读书》1993年第2期
(11)(12)海德格尔《诗·语言·思》,第83、10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
(13)参看《王朔自省:我们该有个教训!》,载《中华工商时报》或天津《家庭报》1993年5月31日
(16)刘健民《文学从来不是发财的好方法——王蒙谈下“海”》,《工人日报》1993年2月24日
标签:王朔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红楼梦论文; 读书论文; 理想主义论文; 浮出海面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