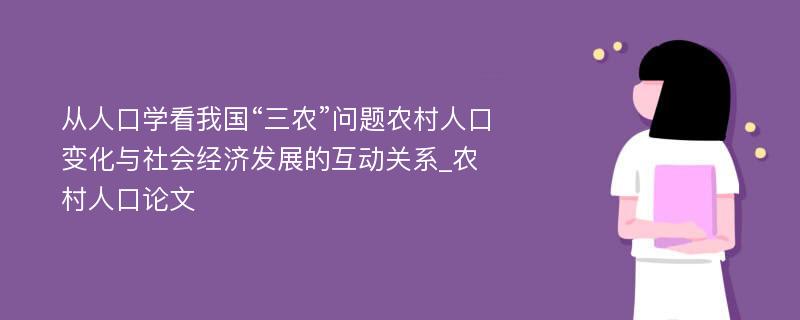
从人口学的视角看中国“三农”问题——试论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交互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学论文,三农论文,视角论文,试论论文,中国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之同时,国家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取得卓越成效,基本实现了人口从高生育水平向低生育水平的转变。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们曾拥有占总人口80%之多的农村人口。在20多年的经济发展与人口转变过程中,中国人口在人口数量、人口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其中农村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的“三农”问题产生了连锁性的效应与影响。
一般的认识是: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低,出生人口少,少儿人口所占比例低,因此,城市的人口老龄化会比农村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更快,程度会更高一些。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计划生育水平低,因此,农村人口众多,青壮年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会高一些。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人口受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的双重影响,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不断下降,迁移流动又造成人口的不断流失,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远比城市发展得快,且老龄化程度远比城市要高。由此带来农村人口自然结构、地域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全面变化,这些变化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一种“互动”,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一、中国农村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化及其相关数据比较
本文主要引用资料为全国自1982年以来的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我们还将全国的三次普查数据与浙江省的三次普查数据做了对比。浙江省位处中国东南沿海较发达地区,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之一。改革开放带来浙江省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区域内人口流动频繁,外出、外来人口十分活跃,人口流动量很大。同时,浙江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引起人口社会结构的快速变动。浙江省又是中国的计划生育先进省份之一,人口控制工作做得较好,其人口的发展进程快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因此,我们认为,浙江的人口发展现状对中国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将全国与浙江的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放到一起来分析,并认为:从人口学的视角分析中国的“三农”问题,这样做不仅具有典型意义,并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通过中国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从1982年到2000年,全国的总人口与城镇人口,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所占比例都一直在增加,而与此同时,农村的人口数量与所占比例一直在下降。在此期间,全国总人口增加了2.39亿,其中城镇人口增加了2.52亿;农村人口减少了1376万,城乡人口的所占比例同期各增长和下降了16.37个百分点。从浙江省的数据看,其城镇与乡村的人口反向比例变化得更快,同期分别增长了和下降了22.96个百分点,其人口变动的态势显得更为清晰。
除了总人口的变化之外,从数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少儿人口的数量不断下降。1982年至2000年,全国总人口中,0~14岁的少儿人口所占比例下降了10.70个百分点,浙江下降了11.24个百分点;而同期,全国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上升了2.05个百分点,浙江上升了3.16个百分点。浙江的人口变动速度明显快于全国的人口变动速度。其实,早在1991年,浙江省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就已经超过7%,差不多早于全国10年提前进入老年型人口。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浙江全省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省人口的8.92%,其人口老龄化程度仅次于上海,位于全国第二,在全国省、自治区中位于第一。
如果我们分城乡来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全国还是浙江,农村0~14岁的少儿人口其下降趋势都快于城市。2000年与1982年相比,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全国城市少儿人口的比例下降了8.27个百分点,而农村少儿人口的比例下降了9.86个百分点;浙江城市少儿人口下降了8.16个百分点,而农村少儿人口的比例下降了11.16个百分点。实际上,中国目前的生育政策实行城市与农村的双轨制,城市普遍推行独生子女生育政策,许多夫妇终生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的生育政策相对宽松,许多省市规定,在农村,夫妇双方都是农民的一个女孩家庭可以再生育第二个孩子。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22,其中的市总和生育率为0.86;镇总和生育率为1.08;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为1.43,显然农村妇女的生育率要高于市镇妇女的生育率。为什么在生育率更高的农村,其少儿人口所占的比例的下降速度却要快于生育率更低的市镇?很显然,这是人口流动所造成的结果。80年代以来,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的20年,从1982年到2000年,全国农村人口所占比例下降了16.37个百分点,农村总人口的下降主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是人口迁移流动的结果。由于人口迁移流动的年龄选择特征,农村流失的人口主要是青壮年,处于生育期的青壮年的人口的外迁流失,是形成农村少儿人口比例下降速度快于城市的主要原因。
在少儿人口比例下降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全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所占比例正在上升,尤其是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要比城市快。从全国的数据看,目前中国市镇人口大于65岁的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为6.42%,而农村这一比例则已达到7.50%。因此可以说,中国城市人口目前还尚未进入老年型人口,而农村人口已先于城市进入老年型人口,中国的老龄化首先是农村人口的老龄化。从浙江的数据看,浙江农村和城市大于65岁的老年人口均已超过7%,城市与农村均已进入老年型人口,但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更引人注目。从三普到四普,浙江农村的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从5.66%上升到6.94%,8年间只上升了1.28个百分点;而从四普到五普,这个比例从6.94%跃升到10.59%,10年间跃升了3.65个百分点,其老年化程度之高,发展速度之快是惊人的。
我们将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与“三普”和“四普”的相关数据进行比较,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中国农村人口数量以及所占比例不断下降的同时,全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口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例迅速降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各有所提高。数据表明,从1982年到2000年,全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比例从73.7%下降到64.4%,下降了9.3个百分点。而同期在浙江,这个比例从62.4%下降到33.5%,整整下降了28.9个百分点,下降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1倍以上。普查表明:在浙江,目前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比例已经下降到总就业人口的约1/3。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全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例都在上升,其中第二产业上升了0.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上升了8.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快于第二产业。这种发展趋势,从浙江的数据表现得更清楚,同期,浙江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上升12.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上升了16个百分点。浙江的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全国亦由此可见一斑。
二、中国农村人口变动的相关因素分析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村人口在近20多年的发展中,人口数量无论从绝对值还是所占比例都在快速下降,与此同时,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速度要快于城市。中国农村人口的这种数量与结构的变化,其成因来自多个方面,它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我们认为其主要因素如下:
1、人口自然变动的因素。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性的人口控制对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具有明显的意义与作用。纵观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在刚建国后的50年代,全国城市人口的出生率历年都高于当时的农村人口。1954~1958年,全国市人口的平均出生率为39.80‰,自然增长率为31.30‰;县人口的出生率为32.34‰,自然增长率为20‰,当年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农村。60年代是文化大革命特殊时期,许多历史数据缺失不论。70年代初,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中国的计划生育首先是在城市取得显著成果。1971年~1979年,全国市人口的平均出生率为16.22‰,自然增长率为10.63‰;县人口的出生率为24.52‰,自然增长率为17.27‰。虽然70年代农村人口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出现高于当时城市的情况,但数据表明,与50年代相比,农村人口已随着全国人口的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而逐年下降。整个80年代是中国计划生育大力推进的时期。四普数据表明,从1982年到1990年的8年间,全国年平均增长率为14.8‰。在这期间,全国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为2.10,其中市、镇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为1.67和1.73;县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为2.27,农村妇女的生育率已开始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乡村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43,虽然还是高于同期城市的生育率,但已远低于人口的更替水平。中国农村人口的生育率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计划生育功不可没。[1]
2、人口迁移流动的因素。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影响作用下,城市的劳动力需求不断扩大,人口出现区域间大量的迁移流动,造成了农村人口的外迁流失,也有效地抑压了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五普数据显示,2000年,按户籍人口统计,全国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有6710万人;按外来人口户口登记地状况统计,全国外来人口总数达到1亿4439万人,其中在省内跨县市流动的有3634万人,到省外跨省际流动的有4242万人,两者相加,流动的外来人口达到7876万人。在浙江,全省外出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有768.52万人,外来人口总数为859.87万人,其中省内跨县市流动的有173.74万人,外省来浙江流动的有368.89万人,两者相加,流动的外来人口有542.63万人。根据我们的有关流动人口问题的专题调查,在流动人口中,占总数79%以上来自农村。[2] 目前,有许多对我国流动人口总量的估计,但由于流动人口的可变性与统计难度,不能有一个统一的具体的结论数据,但大部分学者都接受全国流动人口总量超亿的观点。可以推测,1亿多的流动人口,其中的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农村,这对农村人口的影响是巨大的。
3、人口社会经济结构变动的因素。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的提升,工业、服务业就业人口不断增多,农业就业人口不断减少,推动了人口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变。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就业结构是产业结构的具体表现。以浙江人口为例,从1982年到2000年,全省就业人口的绝对值增加了567.34万人,其中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减少了415.67万人,在全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了28.9个百分点。而同期,第二、第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口共增加了982.95万人,其中第二产业增加了500.79万人,第三产业增加了482.16万人,分别增加了12.9和16个百分点。全国的三次产业就业人口结构变动幅度虽然小于浙江,但是其变动趋势相同。即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比例稳步下降,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例稳步上升,这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展轨迹相一致,符合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不断提升的发展规律。
4、农村生育文化变迁的影响因素。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促进新人口文化思想的嬗变,农民的生育观念向少生优生优育转变。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思想意识的改变,在21世纪的现代农村,传统生育观念的转变是不容置疑的。笔者曾经对浙江临安农村5561对女孩已满6周岁、至今未申请生育二孩、夫妇双方均为农民的农村独女户家庭进行了调查。调查采用了专题座谈、走访调研和调查问卷等多种调查方法,期望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对现代农村生育文化的变迁进行专题性的研究与探讨。其结果表明,临安农村农民的生育观念确实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育动机的变化。原来农民生孩子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现在生孩子主要是维系夫妻感情和生命的延续。二是生育意愿的变化。原来农民认为多子多福,现在认为孩子不在于多而在于好,而且是愿意生就生,不愿意生可以不生。三是生育性别选择的变化。以前,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非常严重,现在普遍认为,顺其自然,生男生女一样好。四是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的变化。以前农村是“早婚早育”,“早生贵子早得福”,现在是追求最佳婚育年龄。五是生育质量观的变化。原来认为把孩子养大了就算完成任务,现在是不但要把孩子养大,而且还要养好。表现在实际行为上,农民们开始重视优生优育,对孕期保健和检查的重视,和对孩子教育的重视与投入。六是生育自主性的变化。以前农村里什么时候生孩子,生几个孩子,往往是由长辈们决定,现在则主要由年轻夫妇自己拿主意。七是对计划生育工作看法的转变。以前在农村是计划生育干部上门要求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现在是群众自己找计划生育干部要求实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在临安农村正在从他律向自律转变。[3] 临安是浙江的一个经济处于中等水平的县市,其农村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浙江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三、对中国农村人口变化所带来的部分人口问题与社会问题的思考
从宏观上看,中国农村人口数量的减少,占总人口比例的下降,有利于缓解农村人口过多的压力,有利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在人口领域的反映,它揭示了现代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方面,这种人口变动也给当代农村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主要影响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对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影响。由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的减少,人口外迁的流失,在中国农村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劳动力结构老化,农村人口的“机会窗口”几乎没有出现。具体表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其一,农村劳动力人数的绝对值呈下降趋势。在全国,2000年与1982年相比,虽然城镇与农村劳动力的所占比例都略有上升,但全国城镇劳动力的绝对值增加了2亿零293万人,而同期农村劳动力的绝对值只增加了4949万人,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显然比城市要低得多。在浙江,2000年与1982年相比,城镇劳动力增加了1018万人以上,而同期农村劳动力却减少了189万人,其一正一反,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要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从所占比例来看,浙江农村劳动力的增加速度比城市慢,从1982年到2000年,浙江市镇劳动力占市镇劳动力总量的比例提高了7.04个百分点,而同期乡村只提高了6.24个百分点。
其二,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多为青壮劳动力。以浙江人口为例,“五普”期间,浙江全省共有外出人口6957103人,其中15~44岁的青壮劳动力人口外出数为4973334人,占到外出总人数的71.49%。
其三,农村劳动力的老化速度快于城市。由于人口迁移流动的年龄选择特征,乡村流失的主要人口是青壮年,因此,乡村人口的劳动力的老化现象十分明显。浙江2000年的五普数据表明,农村15-29岁组的低龄劳动力,乡村比全省平均水平低4.20个百分点;30岁到44岁组的中龄劳动力,乡村比全省平均水平高0.18个百分点,但到了45岁到54岁组和55岁到64岁组的中老龄劳动力,乡村分别要高出全省平均水平2.32和1.70个百分点,如果把乡村各年龄组的劳动力与市、镇两地的同年龄组劳动力相比,这个反差会拉得更大。
第二个方面是对农村老龄化进程的影响。农村青壮劳动力的大量外出与流失,造成了农村人口自然结构的失衡,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
2000年与1982年相比,全国市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4.54%提高到6.42%,提高了1.88个百分点,同期乡村人口的这一比例从5.00%提高到7.50%,提高了2.50个百分点,乡村的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的发展速度快于市镇。而在浙江,同期全省市镇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6.04%提高到7.17%,只提高了1.13个百分点,而乡村人口的这一比例则从5.66%提高到10.59%,提高了4.93个百分点。近10年来,浙江在进入老年型人口后,其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是十分惊人的,这预示着我国人口在全面进入老年型人口后,人口老龄化将会有一个加速度的快速发展过程,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从人口学的视角看中国的“三农”问题,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流失,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是其最主要的两个突出问题,其主要结果是导致农村经济发展缺失相应的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从劳动力结构看,对于目前农业劳动尚处于传统生产方式下的农村,劳动力数量还是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劳动力的缺乏与老化,直接影响农业经济生产。农业经济发展受阻,农村面貌就难以有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依然留在农村的真正农民的生活也就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很大的提高。从老龄化角度看,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城市地区来说相对要低许多,而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尚未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大部分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障还是一个空白。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速度比城市要快,众多的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地、及时地解决好农村这一社会养老保障问题,就难以真正地、彻底地解决好“三农”中的农民问题。
因此,中国农村人口数量与结构的这种变化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互动性,它们交互发生着或正或负的影响与作用。一方面,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农村人口转变的主要动力,也是农村人口数量问题与结构问题的主要成因之一,反映了农村社会的进步与文明。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的数量现状与结构现状是不利于农业经济发展的,它给农村带来了一些难以解决的人口问题与社会问题,对农村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民生活的改善产生一定的负面的影响。本文关于从人口学的视角分析中国的“三农”问题有助于我们认识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其唯一的出路还是要快速发展和全面发展社会经济,只有全面提高社会的经济水平与经济能力,中国的“三农”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得到彻底的解决。对城乡人口比例、年龄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动进行客观地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有的放矢、未雨绸缪地解决好这一难题。
标签:农村人口论文; 中国的人口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农村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老年人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