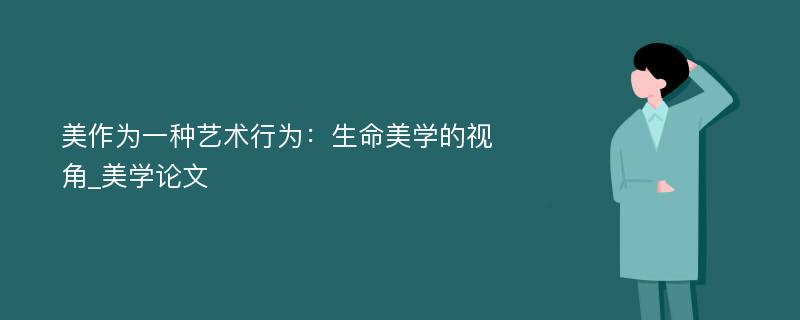
作为艺术行动的美———种生活美学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视角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段时间,王峰和刘旭光二君有一场争论,焦点是美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王峰的意思很明白:美学不合法,是因为美作为一个“超级概念”,是先行设定或者说是假定出来的,没有、也不可能有那么一个“超级事实”和它对应,它犯的是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错误(“美学”87-89)。在这一点上,刘旭光的回应要复杂些。一方面,他认为“自唯实论失败之后,自新柏拉图主义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没有谁把‘美’作为一个实体来对待。”也就是没有人把美当作“直观的对象”来看,从而由王峰的消解视野脱身而出,或者说是间接消解了王峰的消解目标;另一方面,又站在康德自律美学的立场,坚守美学“形而上学”的阵地,用康德的“合目的性”,将形而上学同审美的“理想与价值”嫁接,认为对美的每一次“设定”都不是追求“统一性”,而是“合目的性”。由于这是“美学自近代成熟以来”的真正问题,前者的日常语义分析没有关注于此,反而还是追问“‘美’这个超级概念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自然就“没有进入到真正的美学问题中去”(刘旭光8)。这是直接的消解。 如果我的归纳没有错,王、刘二君的分歧就远没有像字面上那么大,准确说,二人的想法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交锋。王峰以维特根斯坦的方式敲打着形而上学的城堡,虔诚而执拗;但我不认为刘旭光住在这个城堡中,只不过是他将手里的形而上学这面旗探到城堡内,人却在城堡外。他并未反对王峰所反对的“实在论”,二人并不在一个“问题域”。王峰也非常清楚,刘旭光所理解的“形而上学”是“现代改良版”,是“把康德海德格尔化,并进而通过实践概念达成马克思化”(“盟约”14-16)。这很难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至少不是王峰原初所要消解的那种形而上学(尽管王峰仍在努力嗅察其中形而上学的因子)。因此,说二人的观点没有分歧肯定不对,但至少在反对实体论形而上学这一焦点问题上,分歧并不存在。相反,他们对美还有着相同的理解,都把美看作为某种“艺术行动”,①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两个人都没有展开,而我以为,这才该是争论的基本“问题域”。无论形而上美学对美的合目的性“定义”,还是取消主义美学对“审美规则”的“解释”,都须在此获得各自理据,也只有在此层面,才好将各自的道理讲清楚。 美不是实体,是艺术行动、审美活动,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这也是本人非常赞同的。问题是,这究竟是怎样一种艺术行动?首先,如果像刘旭光所言,它同道德、认知、官能满足等“人类其他活动”有别,是“自律的”审美活动,那么,这种自律的活动和“其他活动”有无连通的内在渠道?如果没有,它的“教化”、“陶冶”等等价值功能恐怕就无从谈起。其次,审美活动肯定有其他活动不具备的特殊地方,这一点王峰在自己的两篇文章中没有谈到,刘旭光说它是一种“理性的超越性”,某种精神性的理想价值,那么,这种超越是否一定要出离“日常”、表面和短暂的感性“肉身”,才能赢得自身的“崇高地位”和特殊性呢?如果是这样,审美活动就依然是向某种“最高范畴”(不管它是人的主观“目的”,还是人设定的客观实体)的回归和对应,美的“生成性”和“建构性”也随之沦为纸面游戏。最后,王峰对“超级概念”和“普遍性机制”形而上学性质的“清理”,肯定有价值,可是在审美活动中,它们只有“遮蔽”作用,就不可能有“合理”的积极功能吗?如果有,且不问取消主义美学的“清碍”工作有无“告一段落”的时间,即便这种工作本身就要给自己划个限度。这三个问题涉及艺术行动的性质、价值及其与语言实践的关系,就此我也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自律美学的自闭性 我很同意把美理解为“艺术行动”的提法,但在其性质问题上,我和旭光君有个不同的意见。他的看法来自康德,认为审美和认知、道德与官能满足等人类其他活动有很大的差异,是种“自律”的活动,换言之,是一种非认知、非功利性的活动(刘旭光8)。康德这种看法在西方有很大影响,席勒的审美游戏说、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美学等,大多以此为理论源头。中国近些年来的文艺观念也自觉不自觉体现出这种影响,很注意强调文艺的自律性,甚至用这种自律性作为文学史编写的理论基础。这当然是件好事情,好就好在它让我们多关注一下文艺自身的特殊性。特别是对中国,对一个历史上让文艺承担了太多认知、功利性责任的国度而言,提文艺的自律,有很强的针对性,甚或有着知识分子深层的“自保”意图。如果审美活动果真成为一块自由的“领地”,无疑就有了某种话语赦免权,历史上的许多悲剧就可以避免重演。这种意图不难体谅。 问题是,如果承认马克思“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01)的这个判断,审美活动就不可能同认知、道德、官能满足等生活活动彻底撇清关系。人活在人群中,人的审美活动尽管特殊(每一种活动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却也必然会同其他生活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隔断,那只是一种愿望和想象。想象毕竟不是现实,如非得把它当作现实,这样的现实即马克思所讲的“抽象物”。就像巴台农神庙(Parthenon Temple)的美,绝不仅仅意味着大理石柱廊多立克式(Doric Order)的古朴、静穆,黄金分割的优雅、恰当,而是意味着当时走在街道上的雅典公民,意味着他们战胜波斯后的骄傲,他们的信仰,他们对勇敢的确认。美体现在他们的生活体验当中,里面有认知,即便不同于哲学的玄思;里面有道德,哪怕勇敢只表现为散步时挺起的胸膛;里面也有感官的享受,只需看看他们望向神庙时肃穆或惬意的表情。如果抽去这些,我不知道巴台农神庙的美,是否会只剩下一些形式上的数据。我想,康德自律美学不现实的地方就该在这里。抽象可以划分存在,却不能替代存在。马克思在后半生,非常忌讳唯美主义的诗人参加到工人运动中来,称这些“职业文人”“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②根据恐怕也在这里。 马克思为什么用“灾难”这个词?在我想来,大概是将抽象理解为现实存在,会看不清审美,也看不清现实,在有些时候,指其后果为“灾难”并非危言耸听。想想为我们某些教科书推重的“文学自觉时代”的魏晋时代,想想嵇康、阮籍、陶渊明等人潇洒文字内里的煎熬和不潇洒,甚或想想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时期,毛泽东让知识分子向群众学习的苦衷,该不难体察这点。看不清,意味着蒙昧;蒙昧有很多种,自律美学当居其一。人存世间,审美活动很重要,但不意味着其他活动不重要,比如经济、政治、宗教等,甚至比审美更重要。由此就不难理解,柏拉图指责荷马时,为什么理直气壮地采用“真实”这一认知标准;③亚里士多德为诗人辩护,说“诗比历史更真实”(81)时,为何也沿同一个尺度。不是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话没有问题,但否认审美活动中有其他活动的因子,肯定会有问题。 如果查勘一下审美活动的历史和今生,会发现没有哪一个活动真正能摆脱其他活动的纠缠。这不是审美活动的错,错的只是我们的观念,说明自律美学的观念并非出自审美活动的实际“语境”,而是来于他处。对此,杜威曾说过这么一段话:“有些理论将艺术及其鉴赏归入到某一独立领域,同其他经验方式隔离开,这样的理论并非从艺术题材本身推导出来,而是明显出自那些外部条件的影响。”这些“外部条件”包括:1.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掠夺艺术品,修建美术馆,以炫耀自身武力;2.资本主义制度下,暴发户(nouveaux riches)、收藏家包括国家社群显示自己文化品位的心理;3.商业全球化趋势下,艺术品批量生产后“土生土长地方性的流失”;4.艺术家拒绝迎合经济潮流所采取的审美“个人主义”姿态(Dewey Art as Experience 8-10)。杜威的概括周详与否姑且不论,但它对博物馆艺术、艺术商品化、审美精英化的批判,既可以让我们看到不同审美现象背后相同的自律美学观念,又可以令我们明白,这种观念的产生就脱离开了审美活动本身的语境,是其他人类活动,特别是资本经济刺激下的产物。 杜威没有看到,或者他没有说,自律美学其实也是近代自然科学观念的伴生物。邓晓芒先生把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思想看作是文艺复兴的延续(邓晓芒6),在反对神学蒙昧的意义上,这有道理,但不全对。我一直以为,英国经验主义、法国启蒙运动等,在继承文艺复兴人学思想的同时,更有反拨;反拨的是后者向古希腊罗马复归的理想化倾向,它来自1527年查理五世对罗马的劫掠,几乎一夜间扑灭了理想的燥热,迫使人们面对严酷的现实。在这种背景下,弗·培根开始压制形而上学的冲动,从认识论的角度确认知识在经验“实验”中的合法性,从而为自然科学提供了哲学的依据。这样做的时候,培根也颠覆了古希腊以来的美学传统,不再把审美活动当作真善美的统一,后三者各成方圆,自行其是。哲学(包括自然科学)“切不可给我们的认识装上翅膀,反应挂上铅锤,以免跳跃和飞翔”(Bacon The New Organon 83)。“飞行”是审美活动的特权,是想象,是虚构。“想象不受物质规律的约束,它随心所欲[……]它提供的只是虚构的历史[……]这种虚构的历史可以给人心提供虚幻的满足”(Bacon “Advancement” 89)。这样,就不能用真,也不能用善来要求审美活动,它只是一种闲情逸致,是一种“纯净的趣味”。我们常说自律美学从康德开始,实际上应该是培根。④培根的美论“虚构”审美活动的同时,也“虚构”了自律美学本身。因此,尽管我不完全同意邓晓芒先生的某些意见,却很赞同他对康德道德学说的判断(同样适用于康德美学),即它是“非历史的”,是“脱离尘世和客观世界一切可以把握的对象,只是对超验而不可知的彼岸世界的一种主观假设”(邓晓芒11)。 自律美学的自闭性,非但不符事实,在理论上也封闭了审美活动进入日常生活实践领域的可能性。 二、拒绝肉身的超越 就像我并不否认审美活动的特殊性,也并不是完全否认自律美学一样,我很理解,也完全赞同刘旭光在文中表达的忧虑。在我们的时代,的确有太多的人群沉湎于感官和肉体享乐,也有太多的理论竭力为这种享乐辩护,说这是“精神生活”的危机,一点儿都不过分。而且,我也完全赞同审美活动要有精神超越性的提法,包括理想和价值方面形而上学冲动的合理性。我只是有两点担心,一是自律美学的自律性本身就封闭了这种超越和引导的价值功能,坚持这种理论基础,非但在观念上难以自洽周延,在事实上也会否定超越和启蒙的可能性;二是超越究竟要不要携带肉身?如果不携带,审美活动可以是认知,可以是道德行为,却很难再说是审美活动。 自古希腊以降,精神超越性一直被看作是审美活动的基本属性,这本身没有问题。所谓超越,无非是人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品格,是人对实践中自身优越性的肯定,对自身有限性的反省。特别是后一方面,我愿意理解为审美活动超越性的基本维度,如果审美活动丧失了这个对现实有限性的批判维度,其存在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不能接受它还是审美,还是艺术。毕达哥拉斯说赛场上“观看者”的欣赏是最好的,要优于运动员和赛场里的小商贩(Tatarkiewicz 310),这是审美活动“静观”(contemplation)说的滥觞,是对精神反省的肯定。柏拉图受他的影响很深,他基于迷狂和灵魂回忆的“静观”说依然是理智反省,是对感性、短暂、欲望、肉体的超越,从而获得某种“特有的快感”,“和搔痒所产生的那种快感所产生的那种快感是毫不相同的”(柏拉图298)。这种静观或直觉的精神性超越,经奥古斯丁、康德、叔本华等,贯穿各个不同派系,一直是西方美学的主流声音之一。不管超越的理想不恰当地放在某个实体身上,还是超越了它不该超越的目标,审美活动的精神超越性维度的确不该否定。旭光君如果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取消主义美学”没有进入美学“问题域”,我还是基本赞同的。在王峰君的两篇文章中,除了要“在行动中展现出真正的艺术趣味”这个表述(“美学”89),还没见到他对审美活动价值层面的意见,更多则是对形而上学美学“超级概念”和“大词”(如“理想”)的消解,这难免让人怀疑,取消主义美学对审美活动的超越性,也持有相同做法。 尽管我很愿意接受审美活动超越性的看法,更同意其教化和指引功能,但我不相信这种观念可以引导审美活动做到这点。从理论本身这方面来讲,审美活动既然是非认知、非功利性的活动,又要让它发挥出后者的功能,这在逻辑上就很难讲得通。阿多诺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艺术固然是一种很好的实践方式,“本身也是对实践的批评”,然而,“艺术作品一旦以否定现实的姿态展示着自身,对现实持有否定的立场,无利害感的观念就必须要做出调整。”否则其观念就会“自相矛盾”,成为“没有欲望的欲望学说”。这是他不满意康德美学的地方,所以他的否定美学尽管承认审美活动的自律性,却坚持认为“如果里面没有异质的(heterogeneous)东西,艺术的自律性也就无从产生。”又说,“艺术具有自律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性是艺术自律领域固有的特征”(5-12)。很明显,阿多诺是想用自己的否定辩证法,为艺术进入社会搭建一座桥梁。不管他对康德自律美学的这种“调整”是否成功,至少他看到了,审美活动只靠自律性,就无法行使自己的“批评”功能。 再从审美实践的实际情况来看,据自律观念生成的艺术非但堵塞了教化的通道,实际起到的作用恐怕也适得其反。杜威说:“那些有教养的人所认可的美的艺术由于高高在上,在老百姓的眼里未免苍白无力,这时,他们对美的渴望很有可能转移到那些低级、庸俗的趣味上去”(Dewey Art as Experience 6)。并不是老百姓觉得精神生活不好,更不是他们不想得到艺术的教化,他们也想活得有精神、有品位,问题是自律艺术太过高远,高攀不上的结果,下落的趋势只会愈加迅疾,对审美的冲动转移到日常感官刺激当中,也就不难理解。在此情形下,自律艺术实施教化,陶冶出的却是自己的对立面。 这当然不是老百姓的错,错的是艺术脱离肉身的高翔。肉身是感性,是遍布感性与功利诉求的日常生活,是阿多诺所讲的“异质”、“社会性”,是杜威想把审美归还给的领域,甚至也是马克思所讲的实践。不论把美学学科的创立荣光放在康德身上有多少理由,但毕竟是鲍姆加登第一次限定了这门学科的研究领域。“感性学”,如果离开了感性,感性学又何以立足?如果审美活动自律到只剩下精神理性,我看美学倒真是“取消”来得好。这种抛却肉身的观念并不新鲜,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经中世纪、康德甚至一直到今天,感性的普通生活始终是备受贬损的对象。这有道理没有?当然有,因为后者的确混乱不居、动荡易逝乃至浅薄鄙俗,它的确需要精神理性的调理导引,所以猿成了人,有了哲学、伦理学,也有了美学。然而,因精神成人,人就和感性肉身就此隔绝了吗?若真如此,人只需进化为一丝脑电波就已足够。道理简单到俗气,但只要人脱离不开吃穿住行,谁都不能免俗。正如审美活动,可以有精神超越的义务,却并没有脱俗的特权;审美必须要“从感性提高到精神”,这没错,可它却没有权力“让感性享受让位于精神愉悦”(刘旭光10)。我的意思不是说单纯的感官享受是美的,也不是说纯粹的理智活动不可以是美的,而是说,彻底与感性肉身隔绝开的美是不存在的。 1928年鲁迅批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时曾说过:“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社会停滞着,文艺绝不能独自飞跃”(42)。自律美学的问题,就在于为审美活动圈地之后的“独自飞越”,在拒绝感性生活的肉身之后,又怎可奢望肉身非得接受你的教化?展开双翅无归程,这是精神超越的不可承受之轻。审美活动和它的生活肉身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就像山峰与大地,无论它怎样特殊,总是和生活大地血脉相连。隔断这种血脉,漂浮于云端的山峰只是一个神话。 三、取消主义美学的自我取消 旭光君有个思路我很赞赏,他把对美的定义融进审美活动当中,作为“合目的性”的理想,一方面避开了向实体还原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又以此来重新解释美学史,认为“每一次新的定义,都是给出一种审美的契机”(刘旭光10)。对此,王峰的把握非常敏锐,说这种看法明显离开了康德,“因为先验的形而上学美学本身就拒绝历史流转的维度[……]走上了实践主体论美学与先验美学杂糅的道路”(“盟约”15)。如果说此思路有问题,王峰指出的这点该是最基本的,这也是自律美学自闭性造成的结果。但抛去理论内在的断裂不论,此思路本身的价值却不该忽视。美的定义固然意味着“独断”,没有避开实体论形而上学的嫌疑,可将其置放于某一具体的审美活动语境之下,作为一种目的性的价值理想来理解,不但可以讲得通,事实也必然如此。王峰君一概否定下定义,反对“美的理想”之类的大词,诚然击中了它们实体化的形而上学倾向,但在他所坚守的理论基础、对语言本身的看法等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这些问题会让人看不清“下定义”或“大词”在审美活动中的积极作用。 在消解“超级概念”和一些“大词”时,王峰的理论根据取自维特根斯坦,认为它们“内涵不稳定”,缺少现实的所指。必须要承认,将语言和对象对应起来,说语言指称着对象的本质,这的确是实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一个人吃到可口的食物、闻到可口的味道,会和听到一首曲子一样,“做出相同的表情”(Wittgenstein “Lectures” 11-12)。这个“相同的表情”(可以称之为“快乐”)究竟指向食物还是音乐呢?不确定,它不能对应一个明确的对象,所以是大词。可是当我们反过来问:是不是语词、概念一旦有明确的内涵和所指,就不是大词,不是超级概念了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于是问题随之出现:维特根斯坦恰恰是站在实体论的立场来指责实体论,他指责的是实体论的结果(语词在指称对象本质方面的乏力),而不是实体论本身。在前期的《逻辑哲学论》中,维氏一方面反对实体论形而上学,指出命题不能说出对象的本质,另一方面,又时不时暴露出自己实体论的立场,说“命题记号的要素与思想的客体相对应[……]名字表示客体。客体是它的意义”(维特根斯坦30)。或许,正是这种逻辑原子主义的立场后来不能令其满意,说这本书有“严重的错误”。但在后期的《哲学研究》中,尽管他反驳了奥古斯丁的意见,说语词无关乎对象,只关乎“如何使用”,其“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2-3,20)但“家族相似”理论却仍没有抛弃掉对“相同”的渴求。奎因说他仍在坚持一种“语言拷贝理论”(Quine 27),原因正在于此。 取消主义美学反对实体论的不彻底性,也令它错认了语言的性质,让自己的“清障工作”陷入原子主义的泥沼。我这里说的不彻底性,指的是这种美学潜在的实体论立场。由于这种立场必然要求语言与对象本质的对应,而对象作为事实又没办法要求,所以只能要求语言,要求清理掉一切名实不符的语词、概念和判断。悖谬就在这时出现了。按索绪尔的理论,语言和言语不同,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意味着共性;言语涉及语言实践,表现为个性。二者在事实上并不可分,是一种“体用不二”的关系(30-37)。换言之,语言的本命就是抽象,它离不开共性,是“逻各斯”,是将混乱世界条理化、将易逝对象固定化的一种手段,更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标志,它本身就该泯灭个别、留存共性。语言没有了共性,人与人就无法交流,也就没有了个性化的言语,即语言实践。问题是,共性是对个性的抽象,本就不是对应对象。实体论的真正错误,正是要求它对应对象。“那是一匹马”,“马”这个语词只是一种抽象,它并没有也本不是要讲出眼前那匹马的“本质”。按王峰的逻辑,这就是个“大词”,因为它的“内涵不稳定”,没有告诉我们那匹马是白马还是黑马,是蒙古马还是大宛马,如此等等。如果这个推断成立,结果就是,凡是有语言的地方,到处都是大词。所以,我不相信王峰的“清碍工作”会有“告一段落”的一天,果真有了,这个世界也就没有了语言。这就是悖谬,悖谬在于用个性化的言语要求语言,用共性的语言来对应言语。 这种悖谬也注定取消主义美学是一种自我取消,它本身也避不开“超级概念”的纠缠,除非它不再使用语言。设想自己的“新美学”时,王峰说美学应该只提供解释,从审美活动“实践出发寻找到一些稳定的规则,这些艺术规则或审美规则都是带着语境的,而不是超语境的,有适用范围或作用方式,不具有抽象的本质性特征”(“盟约”17)。从规则本身来讲,无论是否出自语境,它必然反映着共性,否则就不成其为规则;再从语境的具体性和个性方面来看,由于每个人、每次审美活动都独一无二,带着这种独一无二语境的“解释”或“规则”必然也是无穷尽的。那么,新美学必然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它或者是无数人、无数次审美活动规则的集合,其实根本集合不起来,这是个无法统计的工作,果真这样做了,结果也只能是向无尽处繁衍的原子美学;⑤或者可以统计,是“经典”艺术行动规则的统计,但经典的界定标准在哪里呢?为什么选择这个而不是他者?这仍然涉及进一步的共性规则。所以不论如何强调规则的语境性,规则就是规则;是规则,就避不开语言的共性,避不开超级概念的嫌疑。 “大词”的错误不在语词本身,它不得不大,也不能不大,正因其大,我们的审美活动才能像山峰般,耸立在大地之上,让我们的生活有所期盼。杜威将我们的世界看作是“稳定”与“动荡”因素的混杂状态,语言包括理智、知识都是人们求得稳定的一种手段,其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从属一致性的规律”,“排除个性”。但这不是语言的目的和意义,它的意义是“使得什么成为可能”(Dewey Experience and Nature 122,108)。在生活活动,特别是在审美活动中,表现为“假设”或“意图”。这种意图也就是亚里士多德那里“可然或必然的原则”,据此诗人才可以“描述可能发生的事”(81)。这种引导者的身份由此让审美活动染上了超越性的理想价值色彩,具有了“某种仪式般的尊严”(139)。当然,共性语言所把握到的可能性也只是可能性,不是实体论的教条,在审美活动中都是可调整的。就像托尔斯泰创作《安娜·卡列尼娜》,他本想让自己深为同情的安娜活下来,但创作过程中终究还是让她死去,小说更强的审美魅力也由此产生。 把美理解为艺术行动或审美活动,是20世纪以来西方美学的重要贡献,但这只是思想的起点。接下来必然还要追问这种审美活动的范围、性质、价值等问题,在我看来,这是王峰和刘旭光二君文中所做的工作,也是我自己感兴趣的工作。遗憾的是,我虽然在副题中加了一个“生活美学的视角”,但除了表明审美活动不能和普通生活隔离,审美超越要携带肉身,不该反对大词等几条纲目性的意见外,对这个视角本身没更多说些什么,遗憾也只能日后弥补了。 ①在刘旭光那里,美作为实践,是生成性或者建构性的“反思判断”;在王峰那里,则是和语言概念结合起来的“艺术实践”,是审美规则得以产生的“语境”。 ②见马克思:“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77年10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421。1864年12月10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也对“职业文人”表达过同样的警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41。 ③“从荷马开始,所有的诗人无论是模仿德行,还是模仿任何其他东西,所得到的不过是影像,而没有抓住真理。”见柏拉图:《理想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352。 ④参见拙文“审美经验范畴的流变”,《哲学动态》9(2011):100-04。 ⑤维特根斯坦的传记作者巴特利证明,的确有很多人在“错误”地这样做,认为这些追随者以为“每个活动——法律、历史、科学、逻辑、伦理、政治、宗教等——都有自己特殊的语法或逻辑;混淆这类语法与那类语法将导致哲学错误。”见巴特利:《维特根斯坦传》,杜丽燕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129。标签:美学论文; 艺术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文化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康德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