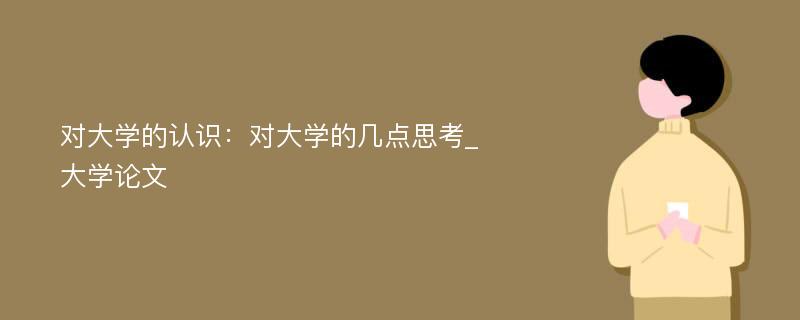
理解大学——关于大学的几点断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论文,断想论文,几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实之中人们对于大学的理解也并非无共识可言,譬如,从职能角度,如今基本上无人否认,所谓大学就是承担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机构。然而,这种共识充其量是建立在对大学作为分工明晰的现代社会中一种实体性机构的理解基础之上,至于大学到底意味着什么,人们要么不把它作为一个问题而弃置一边、不予理睬,要么只是根据自己的感受或想像做纯粹个人式的理解与阐释。而在笔者看来,这一问题恰恰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基所在,对此问题的漠视或过于个人化的理解,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人们逐渐放弃对大学之本义予以更深层次的文化追问,进而一步步淡漠对共同核心价值和精神的体认,其在制度层面的表现就是,一点点地丧失自己独立的立场,让外部势力来侵蚀或接管退却之后所留下的空间,因而在成为依附性机构的同时大学也在渐渐地丧失了自身。现代大学发展的逻辑轨迹,可以说已经清晰地昭示了这一点。所以,带着这一问题意识,笔者试图从几个角度来理解和阐释大学的本质。
一、大学的象征及其现实意义
如今人们对大学作为象牙之塔的象征性称谓似乎惟恐避之而犹不及,因为它几近于守旧、封闭和脱离现实的代名词。在为生产和消费文化所垄断了的21世纪,一个带着后现代主义标识的时代,再提大学的象牙塔精神,即使不为人所斥责,也难免因为不识时务、思想僵化、荒诞滑稽而成为人们百般嘲弄、挖苦和讥笑的对象。但是,在经过一番对现代大学组织文化深切的体认、悟解和冷静的分析之后,笔者不能不为象牙塔精神在现代大学中所依然展现的魅力而略有所动。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人文主义关怀等至今依旧为传统大学所倡导的精神理念,无一不散发着旧式的象牙塔精神气息。拒斥现实诱惑,不为权势所左右,全心沉醉于繁琐的词章考据、严密的学理推演、客观的分析求证(证实或证伪),不惟为学术界所认同的研究规范,而且也是为整个大学共同体所共同体认的学者风骨、品格和精神风范。而这种学者独立人格的塑就,其底色的铺就无不来自大学的象牙塔精神。
客观而言,从中世纪到今天,大学也从来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象牙之塔,完全脱离现实环境的大学过去未曾有过、将来更不可能出现,正因为此,象牙之塔才只不过具有其象征意蕴,或者用带有褒义的言说方式——它不过是大学史中的“神话”而已。象牙塔的神话魅力就在于它是大学作为追求理想、追求真理、追求知识的圣地的象征。它以知识的拥有和真理的标准来塑造知识权威,而扬弃俗世的门第、官阶作为个人身份高低的标志。对知识、真理的推崇,不仅构成了大学成员不断探索、获取新知识的精神动力,而且也使象牙之塔作为城堡的隐喻具有了新的意蕴,即它的相对封闭和自我清高,尽管多少地隔绝了现实生活的鲜活和生气,但也为外界功利诱惑和强权的长驱直入设置了障碍,维护了知识的尊严和真理的崇高。尤其是这种精神在整个共同体的珍视与呵护下,渐渐地以制度化的形式缓慢地存续下来,并孵育成为惟有大学所独有的组织性征。如大学管理的学者自治、组织构成的松散结合、维护思想言论自由的宽容和保障机制、与外部环境间不即不离的公共关系策略等等,这些都无不是象牙塔精神的制度性外化表征。
或许是为了避讳,或许是要告别过去,20世纪的人们赋予了大学以许多崭新的象征意谓。克拉克·克尔把现代的“多元化巨型大学”称之为一座“城市”,一个充满无穷变化、混乱、各种人群斑驳相杂、人们的生活样式千姿百态的“城市”(注: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29.);而阿米泰奇则称现代大学为“社区服务站”(注: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43.);与之相仿的还有社会的“加油站”、“核电站”等等。显然,与象牙塔的喻义迥然不同,如今,人们所赋予大学的象征意蕴,不仅仅是大学作为一个世俗化的机构,而且还是一个能向社会辐射能量的动力枢纽。这一象征一扫往日大学精神贵族的孤傲和清高,而使之具有了些平实、生活化了的平民味道,甚至还时时带有些舍我其谁的入世霸气和雄心。
的确,如果说象牙塔的隐喻是透现着大学虽然还远离现实,但对俗世的芸芸众生还抱以一种终极性的关怀,那么,上述有关现代大学的象征则喻示着象牙塔的坍塌,就如同古巴比伦通天塔的命运一样,在现代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主宰的世界中,它要么只会成为历史上的精神废墟,仅具偶或还有供人凭吊的意义而已;要么就是洗却身上浓厚的贵族气息,垂身入世,成为不仅要食人间烟火,而且还要为稻粱谋的俗民。如此,大学就再也回复不了它超脱现实的不朽之身,而不过是一个要适应、依附和寄身于社会的凡胎俗夫。
然而,问题在于,如果真的完全丧失了象牙塔精神,大学求真、求知精神以及俯视众生的终极情怀为俗世的名利、权势所湮没,大学就不过仅仅是一个抽离了精神的躯壳而已;当然,如果没有务实的入世求存策略,大学也会丧失自身。这就是现代大学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一个择其两端都无出路的两难抉择。当然,寻求两者的结合与平衡也不是不可能,从西方大多至今依然声名显赫的大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启发。以美国哈佛大学为例,在哈佛人心目中,除教育学院外,实在无人会恭维哈佛商学院的学术地位,尽管它的MBA证书被称作是通向金钱王国的通行证。因为,大多哈佛人从来就自奉自己的大学为一般人所无法企及的象牙之塔,它是学术界的桂冠和社会的精神领袖。然而,众多哈佛人的鄙夷目光,并未妨碍哈佛商学院成为美国大学中赚钱的金字招牌。(注:舸昕.从哈佛到斯坦福——美国著名大学今昔纵横谈[C].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68-69.)这真可谓象牙塔的精神慧光与黄金之灿烂,传统的崇高与现代的俗气,交相辉映、相映成趣。
遗憾的是,现实中的人们似乎越来越不满于大学之内求自我完善的象牙塔精神,倒是对其外适功用情有独钟,恨不能一夜间就把大学推向经济的主战场。这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和浅薄只会把大学导向惟有经世之“术”,而无象牙塔精神所关照之“学”的知识与技术“加工厂”。无“学”之玄奥高深、深明大义和超凡脱俗,我们也很难想像会有“术”之持之有效、取之有度和远功近利。易言之,大学不能无象牙塔精神的恪守者,也不能缺乏经世致用之术之专攻者。正如葛兆光先生所指出,老清华之所以有其精神和学风,合乎大学的本义,就在于它不仅有工科的实干、农科之贴近中国,还在于它有理科之冷静、文科之敏锐和法科之严谨,其实没有了许多似乎“无大用”的文科和理科,大学再大,“也只是跛足的巨人,因为那种广博的视野、自由的精神和活跃的风气,在仅仅充满实用与实干的气氛中难以建立”。(注:葛兆光.走近清华[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0-11.)而这种所谓的“务实”最终会因缺少精神之根基而流于浮泛和庸俗。
由是观之,即使是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那些诸如大学的独立自主、自治,学术自由等传统资源缺乏的国度中,今天的大学还是需要有一种象牙塔精神。当然,我们认可象牙塔精神未必就是贬抑大学外求功用的入世态度,而是为了多少地克服一些心性的浮躁、视野的狭隘和行为的短视,多一份冷静和矜持,对名利的淡泊,对思想和精神的守望。也惟有如此,大学之谓才名副其实,它一方面是智慧、思想、精神、知识和真理的城堡,将功名利禄的诱惑、权势的凌人盛气多多少少地拒之于城堡之外;另一方面,它又是开敞的思想和知识源头,以其源源不断的活水泽被人类的生活世界。
二、大学的科学与人文之维
自19世纪初始,在近两个世纪的时代变迁中,伴随着科学主义逐渐从其母体——近代人文主义思想传统中分离出来,甚至对其母体的僭越,大学也渐渐地为科学话语所垄断,诸如科学的思想、方法和规范,越来越为人们所推崇,人们甚至尊奉科学为人类探求所有未知领域的基本范式。
作为对西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传统思想精华的嫡传与合法继承者,科学主义甫才露出水面,便彰显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勃勃的扩张雄心。它赋予人类以求知过程的逻辑严密、精确,经验上的可证实原则和可检验性,因而不仅全面拓展了人类的认识视野和认识领域,推动了知识的增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人类摆脱自然的约束和威胁、改善物质生活环境创造了条件,进而将其外显的实用工具理性价值展现无余,并鼓舞了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社会的勇气。
就科学主义内蕴的精神价值而言,它的价值内核便是现代人的真理观。以真理为客观的价值评判标准不仅是人们在求知活动中所凭依的惟一价值尺度,甚至也是人们在面对社会现实时所保持的基本价值评判依据。可以说,尊重科学、崇尚真理、倡导民主和公正是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社会所尊奉的主导价值取向。在这一主导思潮的冲击之下,整个人类世界的确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人的精神面貌也为之焕然一新,为捍卫真理而不屈不挠便展现了现代人基本的精神和价值诉求。这一价值诉求在大学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学者的独立人格、批判精神和价值中立的学术态度。
然而,科学主义在一步步占据垄断地位的同时,它自身也逐渐完成了与其母体——传统人文主义间由疏离、隔阂到对峙的过程。尤为意味深长的是,恰恰是在科学取得巨大成功、步入其巅峰期之时,人们对科学主义却给予了无情的抨击。进入20世纪后,现象学、存在主义、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目前的后现代主义等等诸多流派,尽管各自的哲学立场不同、批判的角度也不同,但它们无一例外地把攻击的目标指向科学主义,如科学主义的理性传统和真理观,科学主义的外显工具价值即技术功利主义倾向、科层化秩序和效率观等等,它们或者指责科学主义遮蔽了真实的生活世界,或者批判其作为维护社会不平等秩序的统治工具,或者认为它忽视了人的存在、抑制和扼杀了人的创造活力。总之,各哲学流派的基本主张都以人为核心,旨在通过价值的重建将人从科学主义的樊篱解放出来。
不可否认,上述诸流派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和指责未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但它们对现代人的精神状态所表示的关注和对科学主义非人化倾向的批判又的确不乏深刻之处,它揭示了科学主义所存在的固有缺陷。而这些缺陷在现代大学教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在科学话语宰治下,大学内部出现了严格的学科划分、越来越细的专业化倾向,如此不仅导致知识的四分五裂,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学科间的彼此轻视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诸如人文与科学、直觉体验与逻辑推演、重实用与重理论建构等相互间的对峙和彼此轻视,都反映了现代大学内在的矛盾与冲突,而其实质则是肢解了传统人文主义所倡导的人的精神的统一性。此外,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双面神形象雅努斯(注:在古希腊神话中,雅努斯(Janus)是一位专司进入、转折和出去的罗马神,他的形象特征是具有双重面孔,可以同时看到前后相反的两个方向.),科学主义在恪守真理标准并塑就了现代大学精神理念的同时,它的另一面技术功利主义也在大学中颇为盛行,现实中的许多高等教育机构虽然以大学自居,但实际上它们不过是一些高级技术、管理人才培训和技术成果推广的基地。只重理工而淡漠人文学科的建设,姑且不论人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结合在人的培养中所产生的互动效应,仅就其存在状态而言,它已偏离了大学的本义。因为,缺少了人文学科的建设,如此之大学就不可能形成深厚的文化底蕴,人的批判精神、学者的独立人格、精神和思想的自由之形成以及创造活力的迸发等等,也都无从谈起,甚至它也会将科学的求真精神淹没于功利主义的欲海横流之中。
可以说,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在经历了它分娩的阵痛,并艰难地产下科学主义这样一个并不健全的胎儿之后,它又必然面临着一个对现时代精神进行反省、痛定思痛的新的精神孕育过程。新的时代精神核心还需回复到已然为科学主义所疏离的人自身上来,这就需要新的人文主义精神还应续接其传统的“祛魅”法宝——对人的存在状态和人生意义的深切关怀,来对科学主义所营造的笃信再次祛魅。这一精神历程显然不是弃旧从新,不是对科学主义的颠覆、消解和破坏,而是一种对已经被分割、肢解后的现存价值的统合。哈贝马斯提出,人类的认识兴趣分为三种:1.技术的兴趣,即“人们试图通过技术占有或支配外部世界的兴趣”,他认为,技术兴趣内含于自然科学之中,为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2.实践的兴趣,即“维护人际间的相互理解以及确保人的共同性的兴趣,实践兴趣是精神科学研究的原动力,指导精神科学的发展”;3.解放的兴趣,即“人类对自由、独立和主体性的兴趣”,哈氏认为,“一切批判性的科学就是在解放的兴趣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注:郭官义.认识与兴趣.译者前言[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12-13.)显然,在此哈贝马斯所作出的努力并非是要全盘推翻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主义渐成社会文化与理论建设、人的精神信念主流的整个发展轨迹,而是期望以他所谓的沟通理性,来对时代精神和价值进行批判性的重建。这一价值重建的前提是在认可作为传统科学主义的典范——自然科学话语的合法性同时,也不否认传统人文学科和批判的社会科学话语的合法性,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它们都可统摄于科学话语之下。
从哈贝马斯的知识和价值重建主张中,我们不难悟解到科学与人文精神在现代大学中的重要性,它们可谓构成或支撑现代大学精神的两维,缺一不可。任何一维的缺失或弱化,都偏离了大学之谓的本义。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大学的普遍教育改革、我国90年代高等教育领域的人文教育、大学素质教育的吁求等,都可以认为是人们对科学主义主导所引起的大学人文精神失落的回应。当然,尽管在科学主义依旧强大的声势之下,这种回应还显得相对苍白无力,尤其是对于在现时语境中如何给予大学传统人文精神以新的阐释,目前还根本谈不上有共识可言,所以,大学的人文之维的重建还依旧步履维艰。然而我们深信,走向21世纪的大学,尽管它的功能会更趋于多元化,但它所关注的核心必将重新定位和聚焦于“人”的位置上,一个作为类概念的大写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生命的冲动和激情、有着丰富现实需要的个体的人。
三、现代大学精神的自我放逐和制度重建
大学是一个更倾向于情感型的社团性机构,尽管就组织的功用与文化个性而言,它有别于其他组织,但一般组织所具有的结构化、制度化特征也同样适用于大学。然而,大学组织结构化、制度化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维持组织的平稳运作和内部活动的秩序化,相反,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营造组织内部良性冲突频发氛围的激发机制,也是使组织免于为环境所控制,进而完全沦为环境附庸的保障。
一所不能容忍学术观点的冲突、学科间的争端和分歧、后生之辈对学术权威的冒犯的大学,不可能有学术创新的活力;同样,一所完全为外部力量所牵制并成为权力和利益仆从的大学,也不可能为其内部成员的大胆探索、勇于求知和求真提供精神庇护和精神动力。大学的制度框架和组织的半科层化性质存在的原初意义理应在此。管理制度作为一种带有行政性的强制力量,如果持之有度,对学术权威的学阀式统治也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牵制。现实之中,因学术权威力量过于强大,以至于遏制了学术创新的例子并不鲜见。例如在20世纪初,在欧洲大陆国家出现了一批社会学学科的缔造者和大师级人物,如迪尔凯姆、齐美尔等,但他们的具有开创意义的社会学思想和理论并不能为当时的学术权威们所认同,甚至他们在大学中的职位都不能得到正常的晋升,尤其是齐美尔一生郁郁不得志。至于学阀性的统治对一些极有天分的年轻学者个人所造成的戕害,在现实的大学中也可谓触目皆是,个别的甚至是令人震惊的恶性事件。
故而,就此意义而言,大学需要建立起一种开明的行政管理制度,它在倡导学术创新、各种价值取向共存、容纳各种相冲突的学术观点、尊重学术权威并把它们作为大学学术管理主体的同时,又应注意从制度建设层面上来预防和检视有可能出现的学术霸气,特别是个人不良人格、好恶、学术偏见因素与权力混合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为新的学术思想的孕育和形成、为学术新人的发展和成长营造宽松的环境。然而,树立适当的行政权威,其目的在于对学术权威可能出现的权力过分膨胀加以抑制,进而形成一个良好的校园学术风气,而不是以行政权威来压制学术权威,如若至此,则完全背离了大学组织制度的宏旨,即尊重知识、崇尚真理和倡导学术自由的大学精神理念,其后果更为可怕。
现代大学越来越突出的科层化倾向表明:学者自治传统正日渐淡化,而行政力量却日益膨胀,并全面渗透到学术领域。尤为令人担忧的是,在环境所施与的越来越强大的各种压力面前,大学的行政力量往往是作为环境的代言人出现,在缺少来自学术权威的力量牵制情形之下,大学丧失的不仅是自身的独立立场,更令人不安的是学者的淡泊名利、无私求真和求知的精神也逐渐为浮躁的情绪和功利思想所取代,在被动地适当环境需求过程之中,大学在近期内或许确实获得了丰厚的物质回报,但它所付出的代价却是精神的失落、思想的不自由和视野的偏狭。
稍微感受一下如今大学的现实,我们会发现,与一个世纪之前相比,大学城内所独有的那份典雅、宁静以及人们心态的平和与恬淡,委实消淡了许多。或许还值得欣慰的是,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未受到降损,相反倒是有所提升。因为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越来越不敢小视大学的作为知识之城堡、思想文化之源头对现代人类社会所具有的独特功用。这对大学的发展来说是重要的条件。但是另一方面,面对各种内外压力,一些学校行政部门的“科学、客观”的指标体系考核,以及倡导高强度竞争和物质激励政策倾斜,大学越来越难以坚守其严谨和冷静的学术态度。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对功利的追逐也极大地损害了大学的人文精神氛围。
或许放弃了对精神与思想的执着追求,大学同样可以履行它自身的社会职能,但它充其量只是一所事业性的科研院所或人才培训机构,通过提供优质的社会服务它可以换取丰厚的物质回报,却无法内求自我完善和追求完美。这也意味着大学自身所应具备的文化底蕴的缺失,人文精神的淡漠。其结果是不仅最终会导致大学学术创新活力的枯竭、造成人的精神缺憾,而且,最为可怕的是作为组织特质的体现——大学的文化属性也会日渐为物欲所湮没,甚至面临着被替代的威胁。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在利益的驱动之下,现代大学的制度安排也呈现出与其他组织日益趋同的特点,刻板的科层化程序、频繁的考核与评价、高强度的物质奖励机制等等似乎是很有助于提高大学内部活动的绩效的,但是,也不可否认,它也多少地扭曲了大学存在的本质。稍稍留意一下周围,在那些来自于大学、并不断膨胀的可谓汗牛充栋的研究文献之中,我们会发现又有多少是真正令人欣喜的创新之作?其中相互复制、穿凿附会的低劣之作的数量令人触目惊心。至于各种以获利为目的而开展的各类低水平、重复性的研究项目,也不在少数。甚至,一些人为了达到一己目的而不择手段,伪造实验数据,剽袭他人成果。无怪乎,近年来人们对学术界的学术腐败现象也越来越表示其不满,大学自身所具有的神圣意蕴也日渐淡化。
其实,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固然不能排除学术人员的职业素养因素,但其症结所在主要归咎于现行的大学制度安排。行政权力过多地介入学术活动、周期过短频繁的考核评优、刚性的量化评价指标体系等把大学内部的利益竞争和冲突推向了白热化程度,加上捉襟见肘的物质待遇造成的生存压力,使人们很少能够按捺住来自利益需要的冲动,保持一份平和的心态,扎扎实实地潜心于周期较长、工作量大、回报率低,但其意义却非同寻常、影响极为深远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科塞针对美国大学的现状就深有感触地说:“当代大学年轻一代学者在发表作品方面有一种内在的压力,换句话说,大学已经把教师前进的等级系统机构化和制度化了。在这种体系中,只有发表了令人满意的著作才能得到晋升,这样,有抱负的学院人也许不得不抛开那些花费数年才能完成的大规模知识计划,而去追求发表对职务晋升有直接作用的范围狭窄的作品,就像洛根·威尔逊所说:‘无功利的活动和成熟期缓慢的长期计划,在要求短期效益的制度压力下化为泡影。’”(注: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10.)的确,在大学中建立适当、合理的竞争机制是必要的,但如果人们所争相竞逐的是利益目标,这种功利性的竞争和冲突越剧烈,有可能所付出的运作成本和代价越惨重,大学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的长远利益所受到的损害也越严重。
制度安排是特定组织内在精神与理念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反过来,制度安排又培育和营造了组织内部所特有的文化氛围,进而内化为组织中个体的精神人格、价值诉求、信念和行动取向。现代大学的制度安排之所以越来越呈现出与其他组织相趋同的特点,就在于它们逐渐放弃了自己的精神价值追求和对作为组织特性体现的自身场域逻辑的认同,而倾向于以时间和金钱可量度的效率和效益来监控和调节组织运作状态。对效率的追求催发了人的务实精神、竞争意识和时间经济等现代观念的形成,但与此同时也加剧了大学传统精神与现代观念间的疏离、断裂乃至对峙。在有形产出不断增殖的同时,大学的精神、价值和信念等无形的传统资源却日渐枯竭,由此而引起的广泛性、长期性的不良影响不言而喻。如果说在传统资源原本就相对丰厚的国度中,效率观的冲击还未尝不是一种损益的话,那么,对于一些本来传统资源就先天不足的大学,多一分对理想的追求、精神的执着和功利的淡泊则不惟必不可少,而且在目前物质条件有所改善的情况下也适逢其时。否则,欲以跻身世界名校行列恐怕永远都只是一种殷殷期待与想望。当然,至于如何能塑造大学之真精神,只能从制度安排着手,对外,将学术自由精神具体体现在制度层面上,适当强化独立意识;对内,建立一种行政与学术权威两相牵制的体制,少一些对个体过多的无关学术的限制约束和功利化的侵扰,多一些对思想的宽容和对学生独立人格的尊重,建立以质为本而非以数量取胜、以长期的而非频繁的短期性的考核与评价体系,如此,大学才能为真正意义的学术创新、多学科领域的全面渗透和学术新人的成长,预留下弥足的时间和精神空间。自然,这一制度安排的实际效果在于营造一种大学所独具的组织文化氛围,着意于人的精神与物质需要、大学近期目标与长远发展、其对内的自我完善与对外的社会奉献等的和谐统一。
总之,大学不仅仅是一个承担其特定社会职能的物理空间场所,它的存在意义更在于它自身所应具备的文化个性与精神品格,以及由此而焕发出的旺盛创造活力。失去了大学之精神的本义,人力资源的培训、研究的开展、成果的开发应用,也未必一定由大学来承担,大学完全可以由其他社会机构来取而代之,甚至由非人化的现代信息技术来替代。怀特海认为,大学存在的目的在于培养人富有想像力的学习和研究能力,而不是单一的知识积累和技能培训。(注:阿尔弗莱德·怀特海.思想方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32.)在此,对怀特海关于大学本义的理解姑且不议,但从中我们可以领会到,他倡导发展人的想像力教育思想,显然与大学对智慧、思想、精神和价值追求的理想联系更为密切,而现实社会职能的履行只是第二位的。故而,我们把大学作为学术性组织其应具的文化底蕴和精神视为它的灵魂所在并不为过,无论在任何时代的社会背景之下,任何技术环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