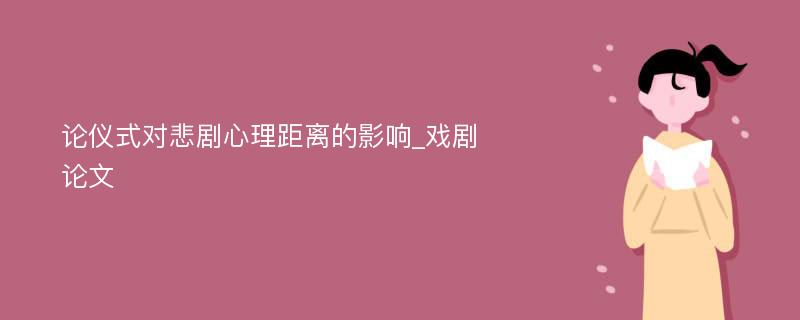
试论仪式对悲剧心理距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仪式论文,悲剧论文,距离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仪式指“按一定文化传统将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集中起来的安排或程序。由此言之,大多数宗教和巫术行为都具有仪式意义。但仪式这一概念并不限于宗教和巫术,任何具有象征意义的人为安排或程序,均可称之为仪式。”[1] 正如英国社会学家邓肯·米切尔所指出的:仪式的意义在于通过隐喻或转喻来陈述心灵体验[1]。仪式的种类很多,本文所探讨的仪式仅限于宗教仪式和巫术仪式。
仪式有两种存在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发展成戏剧。随着原始仪式的发展,仪式中原有的戏的因素慢慢成熟了,再加上新的戏剧因素,仪式也就发展成具有演员、观众、剧场的戏剧。第二种方式是仪式被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保留在戏剧里,这时的仪式或者以巫术仪式和宗教仪式的形态保留在戏剧里,或者以巫术或宗教的仪式感存在于戏剧中。
从仪式到戏剧,有一个精神流变的过程。一方面,仪式中包含了大量的戏剧因子,或者说戏剧继承了仪式中的许多因素。对于这一点,研究者已有颇多论述。在探索戏剧起源的问题上,很多学者主张“仪式说”。他们认为,戏剧起源于原始祭祀仪式,原始祭仪中已含有戏剧因素。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云:远古之巫觋“或偃蹇以像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2] 这段话说明祭仪中已含有装扮和歌舞的因素了。《中国古今戏剧史》认为“宗教仪式是戏剧的孕体,歌舞、游戏、杂技、格斗借宗教仪式之胎而综合形成戏剧。”“百兽之舞,象舞、鹤舞、猴舞等都模仿动物的动作或作类似动作的装扮……”[3] 胡志毅也认为,中国戏剧起源于巫术仪式,尧舜时期的“百兽率舞”,是众多的以动物为图腾的氏族,分别装扮成各种动物,并模仿该动物的动作进行生动的拟态性表演[4]。吴双则认为,中国戏曲的基本要素在上古时代的祭祀性仪式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原始宗教祭祀仪式极其富于戏剧性,仪式中种种构成因素,如以歌舞娱神,以祝词表达心愿,独特的装扮,与假想中的鬼神进行表现式的、超越时空的、形象的、具体的交流等等,都已具有戏剧的成份。他还举了上古祭礼中的颂、蜡祭、傩祭和社祭为例进行说明[5]。不难看出,这些学者认为原始宗教祭祀仪式中包括后来戏剧中所含的歌舞、故事、交流等因素,尤其重要的是,它包含了模仿的因素。这就是后来戏剧中“编”与“演”的成份。
如果说,戏剧起源于仪式揭示了仪式和戏剧之间的源流关系,那么,从仪式到戏剧,则还存在着质的变化。首先,就“模仿性”看,仪式中的“模仿”更大程度上与人们内心的欲望相联系,而不是为了演给人看。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仪式的意义在于陈述心灵体验,是内心欲望的直接投射。在傩祭中扮演野兽是为了驱鬼,在社祭中扮演社神是为了丰收,仪式成为人们内心被压抑的欲望的宣泄处。而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的“模仿”目的在于表演,而不在于陈述心灵体验。戏剧主要是为了演给观众看的,同时也是角色内心欲望的直接投射,戏剧的观赏功能大于它的宣泄功能。
再者,从仪式到戏剧,神性精神弱化了,世俗性增强了。无论是宗教仪式还是巫术仪式,其表现的都是人与神等超自然力量之间的交流,它更多地与宗教、神灵联系在一起。因此,仪式本质上具备神圣性。但是,仪式又往往借助神等超自然的力量来达到世俗的目的。人们以歌舞娱神,以祝词表达心愿,不仅表达了对神的虔诚的信仰,而且渴求着神替他们解决人类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一点就体现了仪式的世俗性。尽管这样,在人们的内心,世俗的目的毕竟要通过神的力量来实现,因此,仪式中的神圣精神最终超乎世俗性之上。而戏剧却不然,戏剧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戏剧中,神与巫的影子不再频繁出现或已不复出现,现实世界中的世俗功利目的占据了戏剧的舞台。在马丁·埃斯林看来,一切戏剧都是政治活动:它或是重申或是强调某个社会的行为准则[6]。罗念生认为,古希腊戏剧表现英雄人物的斗争,通过神话和英雄传说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剧场成为政治讲坛,诗人是人民的教师[7]。夏庭芝在《青楼集志》中曰,杂剧在“群臣、母子、兄弟、朋友”关系上“皆可以厚人伦,美风化”。由此看来,戏剧的整体空间已从仪式的神圣空间蜕变为世俗空间,戏剧比仪式更直接更强烈地流淌着世俗的精神。正是由于戏剧中的主导气氛是世俗的,所以,一旦在世俗气氛中出现神圣的空间,这个神圣的空间就会与世俗空间产生距离,并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因素。
经过上述分析后,再来对戏剧进行整体审度,就会发现戏剧实际上是一个被扩大了的仪式,这个仪式是原始巫术或宗教仪式的嬗变,内中承继着原始仪式的精神,但某些精神被强化了,某些精神被弱化了。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是世俗精神被强化了,神性精神被弱化了。这也是戏剧同仪式的最大区别。
仪式的第二种存在方式就是在神性精神被弱化了或消解了的戏剧的世俗空间里,保留着具有神性精神的仪式的某种形态或因素,或者保留着神性的仪式感。仪式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于戏剧中,对戏剧尤其是悲剧的心理距离产生了深刻影响。
“心理距离”这个概念是由瑞士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在他的论文《作为一个艺术中的因素与美学原理的心理距离》中首次提出的。他认为美感的产生是由于与对象保持了距离,这个距离不是时间或空间的距离,而是心理距离。“距离是通过把客体及其吸引力与人的本身分离开来而获得的,也是通过使客体摆脱了人本身的实际需要与目的而取得的。”[8] 朱光潜认为“戏剧艺术由于是通过真正的人来表现人的行动或感情,所以有丧失距离的危险。”“它必须讲述人世间的故事,而这类故事很容易产生习惯性的概念联想,唤起一种多少是实际的态度。”[9] (P46)但是,他接着指出了“这些不利条件一般都被戏剧艺术的各种手法弥补起来了。”他着重论述了悲剧中使生活“距离化”的几种较重要的手法:空间和时间的遥远性;人物、情境与情节的非常性质;艺术技巧与程式;抒情成分;超自然的气氛;舞台技巧和布景效果[9] (P49~58)。尽管朱光潜先生未从戏剧发生学的角度审度仪式在创造“距离化”方面的作用,但笔者认为古代或现代戏剧中所留存的仪式形态(因素)中的神性精神以及与神性精神相联系的浓郁的抒情性都为悲剧心理距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戏剧中的仪式不仅以一种艺术形式存在着,并且以神圣空间的形式独立于戏剧这一世俗空间里。它的神圣的仪式感自然拉开了同戏剧的世俗精神及其现实色彩之间的距离,而这种距离的存在帮助悲剧形成与现实生活的心理距离。如果把戏剧比作暗夜,那么仪式就好比这暗夜里的灯光,它使观众的眼睛为之一亮,使欣赏者的心灵从悲剧的狂潮中走出来,得以栖息与平静。
《长生殿》中有一系列关于祭祀仪式的描写:“密誓”、“哭像”、“私祭”等。“密誓”写乞巧节李隆基与杨贵妃在长生殿里以银汉桥边双星为证,密誓共为夫妇,永不相离。“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10] 祷词悄然传达出李杨二人对于他们在世俗世界里的爱情的担忧,而双星为证的神性的光芒保佑他们的爱情得以在天上继续以至永存。这一仪式场面既是李杨两人心中虔诚的祈祷,也是沟通地与天、人间和神界的精神纽带,为全剧现实与虚幻两境界的融合埋下了伏笔,是将全剧由世俗空间引向神圣空间的先兆之音。“哭像”一出则写唐明皇祭奠杨贵妃的奠灵筵礼。其时,唐明皇对亡妃的深深忏悔与留恋溢满字里行间,也折射了人在世俗空间里的无力与无助。从“密誓”到“哭像”,一祈祷一忏悔,表现的都是人与神灵之间的交流。人物因为对世俗的担忧或者在世俗空间里的受挫而转向对神灵的祈祷或哭诉,这正是仪式能够使人陈述心灵体验的表现。这时候,仪式也成了沟通世俗空间与神圣空间的桥梁,它使剧中人物在与神的集中而专注的交流中,宣泄内心的悲凄与欲望,获得了一个在世俗空间中无法找寻到的独立和宁静的陈述空间,给人的心灵带来慰抚与平静。在这个意义上,戏剧中的仪式拉开了与悲剧中的世俗空间之间的距离,同时也拉开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成为产生悲剧心理距离的手法之一。
再如《汉宫秋》中灞桥送别后,王昭君到了边境遂投河自杀。剧中淡淡地描写了昭君投河前祭酒辞汉的场景,这也是一个简短的祭祀仪式。奠酒地点设于江边,苍凉之味弥漫其中。昭君辞汉寥寥数语,却已道出心中的冤屈与无助:“大王,借一杯酒,望南浇奠,辞了汉家,长行去罢。”(做奠酒科,云)“汉朝皇帝,妾身今生已矣,尚待来生也”(做跳江科)。从奠酒到跳江,昭君完成了一个虔诚的祭祀礼仪。她将回归汉朝故里的心愿寄托于来生,是对世俗空间的决绝辞别,也是对神圣空间的寄托。这时,神圣的仪式感也产生了悲剧的心理距离。
《原野》是中国现代话剧中一部具有强烈巫术仪式感的剧作。其仪式精神主要体现在第三幕焦母为了唤回小黑子的亡魂,请了老神仙来招魂的仪式中。鼓声、歌声、招魂声等各种声音同时也幻化成仇虎心理上的幻觉,为全剧罩上了神秘、恐怖的色彩。这个仪式的场景不仅将剧中人物尤其是焦母和仇虎从世俗的现实的世界引入虚幻的鬼神的世界,而且也以浓厚的神秘与恐怖气氛区别于日常生活的现实色彩。
希腊悲剧可谓将仪式的神性精神保留得最为完善的剧种之一,而悲剧中合唱队的歌词则是原始仪式的神性精神体现得最为强烈的地方。在欧里庇得斯之前的悲剧作品中,对神的虔诚和不容置疑几乎成了悲剧中的主导精神,合唱队的歌词充满了大量祭神的祈祷语。如《俄狄浦斯》中的进场歌:“这无数的死亡毁了我们的城邦……祈求天神消除这悲惨的灾难。求生的哀歌是这般响亮,还夹杂着悲惨的哭声;为了解除这灾难,宙斯的金色女儿啊,请给我们美好的帮助。”这段具有浓厚神性意味的祷词正是城邦人民对神的召唤,并以其集中强烈的神圣精神感染着整部悲剧。尽管到了欧里庇得斯的作品里,悲剧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对神的公正性、权威性的怀疑,但对神的呼唤,与神的交流仍然充满于许多悲剧中,可以说,歌队的合唱便是存留于希腊悲剧中的神圣仪式的因素,是席勒所说的“隔断与现实世界接触”的“理想领域”[11]。它对神的召唤强烈地将人引入与神与宇宙的交流中,在某种程度上拉开了与正在进行中的悲剧之间的距离。
从西方悲剧发展史看,近代西方悲剧已不像希腊悲剧那样充满着强烈的宿命论色彩,而是世俗的力量增强了。正如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所言:“近代西方悲剧在基本精神上来源于欧里庇得斯,而不是埃斯库罗斯或索福克勒斯,它从探索宇宙间的大问题转而探索人的内心。”[9] (P141)爱情、嫉妒、野心、荣誉、愤怒、复仇、内心冲突和社会问题成为近代西方悲剧的主题。莎士比亚悲剧表现的正是近代西方悲剧的世俗主题。因此,如果说希腊悲剧中的合唱是对剧中已有的神性精神的强化,那么,在莎氏的悲剧作品中,祭礼的味道却是对世俗悲剧中缺失了的神性精神的拟补。威尔逊·奈特在《莎士比亚与宗教仪式》一文中说,莎剧的结尾总带有祭献的味道[12] (P419)……基督教精神自始至终贯串着莎氏的作品[12] (P422)。的确,在莎氏的悲剧里,原始仪式感虽未得到像古希腊悲剧那样集中的体现,但它的神性精神却散落在戏剧的诸多场景中,让人不时地体验到与神交流时的庄严肃穆的气氛,拉开了与正在进行中的世俗悲剧之间的距离。威尔逊·奈特说:“《奥瑟罗》的结尾更是一场崇高的祭礼。床就是祭坛,铺着结婚的被褥,旁边一盏蜡烛,像祭神的蜡烛,室外天空挂着贞洁的月儿和群星。”[12] (P417)这不是一场真正的祭礼,然而,却充满了祭礼的仪式感。当一个无辜的生命行将走尽,或已经离开人间时,这承载着死亡的躯体的床霎时间成了一座祭坛。蜡烛、月儿和群星都在默默地为这屈死的亡灵洒着光辉,为她祈祷。这里,“祭礼”把人从世俗的世界带到神圣的世界里,一个远离了寻常生活中卑微污秽与无休止争斗的世界。虽然它只是戏剧中的一种艺术形式,但神性精神的存在悄然淡化了悲剧中的恐怖、彷徨与无着,代之以崇高与悲壮感,从美学上看,悲剧的心理距离产生了。再看《哈姆雷特》最后一幕简短的葬礼,《理查三世》中一系列哀悼死者的场面,这些零散的祭祀的场面或意象为剧作罩上了神性的色彩,拉开了与世俗生活的距离。
抒情性是仪式的另一个特征,甚至是很根本的特征。这是因为仪式本身就是宣泄人的内心情感、欲望的空间。但仪式并非一个一般的抒情空间,而是“一个想通过模仿行为来表达主体情感或意愿的强烈要求的空间”[13]。它来源于“举世都有的深切的愿望,但愿那看来是死的自然能复活起来。”[13] 卢卡契曾说:“巫术,从最广义上说,始终有激发情感的目的。不仅因为激发到狂热程度的效果对于氏族集体是必要的……而且因为那种扎根于巫术观念中的与自然的关系也产生出一种激发的意图。”[14]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仪式的抒情性具有不同于一般抒情的两个特征:一是仪式中的抒情是十分强烈的,与深切的愿望联系在一起,参与仪式中的人身心处于迷狂状态,正如尼采所说的,悲剧起源于希腊的酒神仪式,“在酒神状态中,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既是情绪的总爆发,又是情绪的总释放。”[15] (P313)这是阐明仪式抒情的迷狂性特征的一个范例。二是仪式中的抒情始终源于与自然生灵、自然力的联系,呈现出鲜明的神圣性。仪式的上述两种抒情特征在进入悲剧时,虽不无嬗变或换形,却自然地成为悲剧审美的独特的抒情手段,成为产生悲剧心理距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最容易从仪式的语言中感受到它的抒情性。诗意的、诗歌式的语言是仪式的重要抒情成份。按照朱光潜先生的看法,悲剧的抒情性主要来源于诗一样的语言,诗的语言同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相区别,诗的成分构成了重要的距离化因素。“它那庄重的华美的辞藻,和谐悦耳的节奏和旋律、丰富的意象和辉煌的色彩——这一切都使悲剧情节大大高于平凡的人生,而且减弱我们可能感到的悲剧的恐怖。情境越可怖,就越需要抒情的宽慰。”[9] (P53)当仪式被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保留在悲剧中时,它并未失却诗的成分。诗一样的祈祷语被较完整地保留在素有“诗剧”之称的希腊悲剧和中国戏曲中。其间,诗的语言,诗的音调都以整体性的姿态笼罩着整部悲剧作品,而留存于其中的仪式的语言自然也带上浓郁的诗的气息。诗的气息缓和着悲剧紧张的节奏,使痛苦的写照减免了现实性。除了希腊悲剧和中国戏曲外,近代悲剧作品中的仪式也留有诗歌的言语,但这种保留是相当有限的。朱光潜以为,“在近代欧洲的悲剧中,纯抒情的成分似乎大大减少了。我们只是偶尔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一支歌……”[9] (P53)而在中国话剧作品里,留有诗语的仪式也是极少的。《桑树坪纪事》保留了古老的歌队形式,但歌队的唱词也仅是一首被反复吟咏的带有传说色彩的诗。然而,无论如何,仪式中诗一样的祈祷语毕竟构成了悲剧中抒情语系的一部分,对悲剧的审美距离产生着影响。
仪式的抒情性不仅仅靠诗的语言来传达,它还以一种“有秩序”的“感性形式和结构”阐述着人的内心感受。当仪式进入悲剧中时,它已不可能完整地保留原有仪式的形式,它的整段的诗样的祈祷语有可能丧失,而仅留下些许仪式的因素和一种仪式感。这些仪式的因素是“有秩序”的“感性形式和结构”,仍然具有很强的抒情力量。《汉宫秋》中,王昭君奠酒辞汉,虽只有寥寥数语,但奠酒、跳江两个动作却显示了祭祀和牺牲仪式的某种特定的秩序,表达人物对故土的眷恋,对生命无望的弃绝。在《茶馆》剧终之前,三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撒下纸钱,提前为自己举行了告别生命的仪式。我们听不到长长的祈祷语,然而纸钱纷飞的场面却构成了浓郁的抒情氛围,表达了老人们对于一个时代,对于人生的绝望。《哈姆雷特》最后的牺牲仪式虽只有军乐响起和那默默的抬尸动作,却以静穆的氛围深深地传达出庄严和敬重感。撒钱、奠酒、跳江、抬尸……仪式中的这些动作以及其他相关的因素,共同显示出仪式的某种既定的程序,这是易于让人接受,按照一定的文化传统形成的“有秩序”的“感性形式和结构”,具有传达人的内心感受的潜在性和合理性。王良范认为“有秩序”的“感性形式和结构”把“混乱和不可表达的种种实际经验表达了出来”[16]。林克欢也以为:“仪式操作永远是复制着一系列程序、结构固定不变的动作,以便再唤起、再创造某种特定情感。”[17] 仪式中的特定的动作和程序长久地被延续下来,与人们内心深度的渴望和信仰联系在一起,这使它在抒情的意义和强度上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的抒情,从而产生了悲剧的心理距离。
仪式中诗意的抒情语言,“有秩序”的“感性形式和结构”,共同构成了悲剧中一个独立的抒情领域,并以其浓郁的诗的气息,强烈和独特的抒情色彩,区别于日常生活空间,对悲剧的心理距离产生着重要影响。但是,让我们无法回避的是,这个独立的抒情领域始终体现为一种与神性精神相联系的抒情境界。席勒在《论悲剧中合唱队的运用》中认为,希腊剧中的合唱是“一堵活生生的墙,这堵墙使悲剧围绕着自身进行,完全与现实世界隔绝,并且保持它的理想的基础,维护它的诗的自由”[11]。尼采说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见解”,并且指出席勒所说的“理想领域”不仅来自“诗意的自由”,还源于“虚构的自然生灵”[15] (P26),强调了神性的超自然的因素赋予希腊悲剧合唱的理想色彩。的确,无论席勒所讲的“理想”指何种理想,都无法与神性精神割裂开。因为正是神性精神的存在,赋予存在于悲剧中的仪式抒情以超乎平凡的意义,也为剧中人物内心情感的倾吐创造了和谐的、超然的、与现实的世俗的世界相隔离的抒情境界。当原始仪式以一种艺术形式存在于中国戏曲、曹禺戏剧或者莎士比亚戏剧等作品中时,它同样也是以其浓郁的抒情色彩及与神性相联系的抒情境界表达着悲剧与日常生活的距离。朱光潜说,抒情给人以宽慰,笔者认为,存在于悲剧中的仪式或仪式感不仅以强烈的抒情性给人以宽慰,而且因其与神性精神的内在联系创造了崇高的抒情境界,而崇高感不正是悲剧区别于日常生活的最本质的特征吗?
与希腊剧中的合唱相似,仪式在悲剧中也是作为一个“理想领域”而存在的。这个独立的领域内含多种产生悲剧心理距离的因素,它们互相融合,构成一个审美空间,以整体的方式影响着悲剧的心理距离。仪式在美学上的这层意义渊源于它在文化人类学上的内涵与表现方式:作为宗教仪式和巫术仪式精神内核的神性精神,是仪式在悲剧中构成距离化因素的本质;而满足仪式参与者内心欲望与信仰的文化功能则被置换成美学意义上的抒情功能;仪式长期以来形成的一套感性的动作和程序,也成为美学上独特的抒情方式。这一切都证明了悲剧中的仪式在对悲剧的心理距离产生影响的同时,其自身的文化功能也被转化成美学功能。仪式借此十分自然地沟通了文化人类学和美学两个领域,为悲剧甚至是艺术的整个审美领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观照视野。
仪式产生悲剧心理距离的手法——神性的精神和独特的抒情方式,对悲剧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西方的现代派、后现代派剧作,还是中国当代探索剧和先锋剧,对于生命感的强调,对于神性精神的崇拜与信仰,早已成为剧作家远离世俗的方式,而借鉴仪式中那一套不断重复的程序来表达某种特定情感的创作思维,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剧作家艺术运作的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