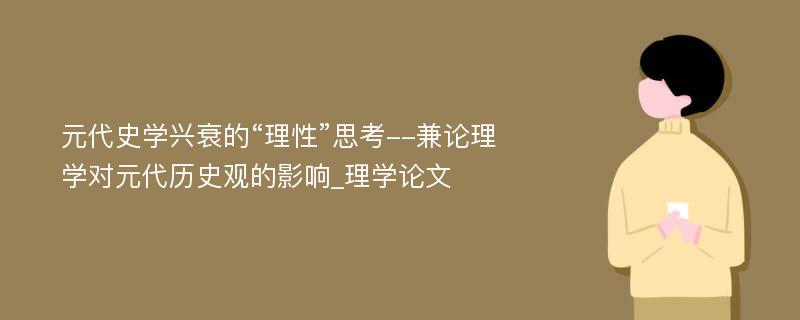
元代关于历史盛衰之“理”的思考——论理学思潮对元代历史观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论理学论文,历史观论文,盛衰论文,思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往今来对于历史的认识,总是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比如,历史是如何运动的,历史为什么是这样或那样地运动,是什么在其中起了决定的作用?这是历史观的问题,由于一个时代史学思想中的历史观与当时哲学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此,考察元代历史观,必须特别注意元代理学思潮对于当时史学思想的影响。
在宋代兴起,并于元代成为官学的理学是由赵复北传和“北许南吴”的推动而发展起来的。元代理学继承了宋代理学思想的基本原则,通过天道观、心性观、知行论等理学范畴的阐述,对封建秩序符合“天道”的合理性,以及人们如何遵守伦理纲常、加强自我修养的方法进一步加以发挥和论证。元代理学思想中对于自然与社会中“天理”的探讨,影响了元代社会对于历史过程中盛衰原因与治乱标准的理性思考。
一、“物盛而衰,固其理也”
理学的核心是理,以理或天理作为宇宙本体是宋代程朱理学最基本的命题,不仅程朱如此,陆氏心学也有大致相同的认识。陆九渊说:“塞宇宙,一理耳。”(注:《象山全集》卷十二《与赵咏道之四》。)程朱与心学重要的区别是求理于物或求理于心的不同。尽管宋代理学各派学说各有特色,但都无一例外地承认存在某种超乎天地万物的宇宙本体,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均由这一本体产生、派生或外化。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理学家们系统地回答了社会、政治、人性、道德等一系列问题。元代理学继承了宋代理学思想原则,同样以理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只是有时所用的术语不大相同而已。比如,理学大儒许衡(1209—1282)就说:“太极之前,此道独立。道生太极,函三为一,一气既分,天地定位。”(注:《鲁斋遗书》卷九《稽古千文》。)道是最先存在的本体,道生太极,太极包含天、地、人三才,故太极又可生天地万物。“道”也就是“理”,“只有一个理,到中间却散为万事,如达道达德九经三重之类,无所不备。”(注:《鲁斋遗书》卷二《语录下》。)理作为绝对的本体,它决定了事物产生的所以然和发展的所当然,“其所以然与所当然,此说个理”(注:《鲁斋遗书》卷一《语录上》。),“所以然”是指事物发生的本原和根据,“所当然”是指事物发展的规律和法则。许衡正是从理出发,探求万事万物的“所以然”和“所当然”,并依据所处时代的客观条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历史观。
首先,许衡看到历史过程运动变化的必然性,他说:“尝谓天下古今一治一乱,治无常治,乱无常乱,乱中有治焉,治中有乱焉。乱极而入于治,治极而入于乱。乱之终治之始也,治之终乱之始也。”(注:《鲁斋遗书》卷九《与窦先生》。)这种一治一乱,治极而乱,乱极而治的历史观包含了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辩证法因素,而这样的辩证法因素又与他论阴阳消长,“消之中复有长焉,长之中复有消焉”(注:《鲁斋遗书》卷六《阴阳消长》。)的思想密切相关。因此,许衡观察社会历史运动时,就能注意到治乱双方是对立统一、相互依存,“乱中有治,治中有乱”的关系。它们的相互转化,是一个渐进转换,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世谓之治,治非一日之为也,其来有素焉”;“世谓之乱,乱非一日之为也,其来有素焉”。许衡看待历史过程运动变化的眼光是辩证的,但是他未能说明社会历史一治一乱的运动结果,究竟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因此他像古代许多具有辩证思想的思想家一样,没有跳出历史循环论的窠臼。
社会历史总是由治而乱、由乱而治不断交替的,然而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变化呢?其中的“所以然”和“所当然”是什么呢?许衡曾尝试对此进行解释,他说:
治乱相寻,天人交胜。天之胜,质掩文也;人之胜,文胜质也。天胜不已则复而至于平,平则文著而行矣……人胜不已则积而至于偏,偏则文没不用矣……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时也,时之所向势也。势不可为,时不可犯,顺而处之则进退出处、穷达得失莫非义也。古之所谓聪明睿智者,唯能识此也。所谓神武而不杀者,唯能体此也。(注:《鲁斋遗书》卷九《与窦先生》。)
在这里,许衡以一套“天人相胜”的道理来解释治乱相寻之“所当然”,他继承司马迁“一质一文,终始之变”的说法,把尚质、尚文作为不同的社会特征。他认为,天是尚质的,人是尚文的;天胜则质掩文,乱世渐“平”而转为治世;治世尚文,于是文胜质、人胜天,治世渐“偏”而转为乱世,这便是一治一乱的变化规律。应该说,许衡对于治乱相因的分析是具有辩证因素的;但是他将治世乱世“所以然”的探究归结为“莫非命也”,认为人们只要尚质无为、顺从于“天”,就可达于治世,从而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看成无用甚至有害,则是明显的缺陷。在这一段文字中,他用了天、人、文、质、命、时、势等许多概念,显得比较混乱。其实,所谓的天、命、时、势,他这里说的是表里相关的一回事,总的意思是要说明“天命”对于历史治乱的决定意义。这是宋元理学唯心社会史观不可避免的错误结论。
应该指出,许衡的天命史观又与以往空洞虚诞,依靠天命神意、五行灾祥进行说教的天命观不同,他的天命观重在强调封建纲常秩序的合理性,是以理学王道德治的政治目标来衡量治世或乱世的;王道德治要靠人来实现,因此许衡的天命史观其实也不完全排斥人事,这一点在下边的相关问题中将有详细分析。这里可以看出,许衡虽将治乱成因归于“天命”,但他毕竟联系到社会变动中的“时”与“势”,他主张人之所为要顺应时势、合乎时宜的思想是合理的。尤为重要的是,他能论史而求理,注意探索历史运动的法则和历史变化的成因,尽管其结论终归错误,但这种哲学思考对于元代历史观的纵深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在元代理学思想认识的影响下,元代史家在史学研究中多能注意透过纷繁杂呈的史事,探求历史兴衰治乱之理。比如稍后于许衡的史学家胡三省(1230—1302)在一生心血凝聚的史学巨作《通鉴音注》中,就没有把《通鉴》注释仅仅看作是文字训释或名物考证的工作,而是通过对史事的分析,在注释文字中融入了他对历史运动过程的深刻思考。他说:“物盛而衰,固其理也。”(注:《通鉴》卷一四九,梁武帝天监十八年注文。)指出历史盛衰变化受“理”的支配,理存于史事之中,因此考察历史要善于求理。如何观史以求理呢?胡三省认为看待历史变动时,必须抓住影响盛衰的“大致”,“善觇国者,不观一时之强弱,而观其治乱之大致。”(注:《通鉴》卷二八六,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注文。)他在分析一些朝代兴衰变化、鼎祚迁移时,特别注意从人心向背以观历史大势,便是他抓历史“大致”的具体体现。元代中期主持大型典志体史书《经世大典》编撰工作的虞集,也强调了从历史兴废存亡处,思考变通之理的重要性,他说:“夫古今治乱之迹不考,则无以极事理之变通,又史学之不可不讲也。”(注:《道园学古录》卷三一《送饶则民序》。)从“考史以极事理”的思想出发,虞集总裁《经世大典》修撰时,不仅议立篇目,网罗文献,而且在全书各门各类之前设立序录,交待立目旨意,勾勒元初以后各项典章制度的演变原委,总结历史经验。现存于《元文类》的《经世大典》146篇大小序录, 反映了虞集等史臣对元代中期以前历史进程及典制沿革深层“事理”的探讨。
总之,元代史学思想的历史观在经历理学思想的洗礼之后,史学的思想境界和思辨能力提高了,它不仅仅局限于连缀、考证由时间、地点、人物、经过组合的历史事件,而注意在“理”的层次上认识历史,这就大大地增强了这一时期史学的价值和意义。
二、通“变”而达于“数”
通变以合理的思想也是元代历史观中值得人们注意的内容。通变思想是中国史学家和思想家对于思想界的一个突出贡献,通是连接、联系和因依,变是运动和变化;通与变两者结合起来成为一个范畴,说明了事物不断变化的基本原则,以及事物从一个方面向另一方面转化时对立双方互相联系,可以因势利导的条件。通变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说明了历史过程运动变化的必然趋势,以及人们在变化过程中因势而行,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可能性。《周易》最早提出了中国古代的通变思想,它说:“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注:《周易·系辞下》。)它强调变的普遍性和通的必要性。《周易》的通变思想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得到贯彻和发展,元代思想家和史学家在理学认识的基础上,从求理与合理的要求出发,提出了通变以合理的思想,这是对通变史观的发展。
许衡的历史观中就有通变以合理的思想。他在循治乱之迹以求理时,虽然表现出明显的天命史观色彩,但从总的思想认识来看,他并不认为人在历史运动过程中是完全被动和无所作为的,而以为,在合理的前提下,人们只要以通变精神行事,是可以发挥历史作用的。许衡说:
五帝之禅,三代之继,皆数然也。其间有如尧舜有子之不肖,变也。尧舜能通之以楫逊,而不能使己之不丹朱、商均。汤武遇君之无道,变也。汤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无桀纣。圣人遇变而通之,亦惟达于自然之数,一毫之己私无与也。(注:《鲁斋遗书》卷一《语录上》。)
他认为社会历史过程具有规律性和必然性,这便是“数”,所谓“数”其实就是决定事物发展“所以然”和“所当然”之“理”。“变”是变异,历史的变动发展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如尧舜不能避免不肖之子,汤武不能避免无道之君一样。但是在历史变动转化的大势下,人又不是完全束手无策的,他们可以顺应社会变动的趋势,“遇变而通之”,推动社会向着有利的方向转化。尧舜通过禅让,保证了五帝时期盛世的延续;汤武发动对桀纣的讨伐,分别建立了强大商朝和周朝。许衡在列举历史上遇变而通的事实时,特别强调了通变的依据在“达于自然之数”,也就是说,通变不能杂以“一毫之己私”、不是在个人意愿驱使下的盲目行动,而是顺应发展大势的合“理”变革。许衡通变以合理的思想指出了社会历史变化的绝对意义,同时也说明了人们在“理”的规范下,顺应潮流,及时变革的重要作用。他的历史观不仅是观察历史的思想,又是思考时代变革的观点,特别是在元朝这样一个民族新组合,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这种思想显得尤其可贵。
元代思想家还利用“通变”史观作为他们政治理论的依据,在这一方面,应属郝经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他在《上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注:《陵川文集》卷三九。)这篇洋洋12000字的政论文中, 调动上起三代,下至南北宋的大量史事,用以说服宋主放弃南北争战,以实现“撤天下之藩蓠,破天下之畦町,旷然一德”的政治局面。贯穿于《上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全文的核心思想便是审势求理的“通变”史观,郝经说:
夫天下有定理而无定势。圣人驭天下之大柄,本夫理而审夫势,不执于一,不失于一,而惟理是适。是以举而措之,成天下之事业。以天下之至静,御天下之至动;以天下之至常,御天下之至变;以天下之至无为,而为天下之至有为。势莫能定,而理无不定。推理而行,握符持要,以应夫势,天下无不定也。贾谊有言: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审者何?审夫势也;定者何?定夫理也;取舍者何?理势之间也。见夫势必求夫理,轻重可否,不相违戾,而后权得而处之。
在这里,郝经提出了“天下有定理而无定势”的命题。理与势的概念早在先秦就出现了,郝经对于“天下有定理而无定势”命题的分析,首先说明了历史过程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因此天下无定势而有动势。其次,他指出“势莫能定,而理无不定”,天下大势虽然变动不羁,分分合合,但是它的运动方向是有内在规定的,这个规定就是理。第三,郝经认为能成就天下大业者,要“本夫理而审夫势”,在本理、审势的前提下,善于“取舍”。取舍即通变,“取舍者何?理势之间也”,这就是说要把握理所规定的势,善于通变,去顺应这个发展的趋势。他列举了汤武、秦王的史实进行比较,说明虽然他们都是以征伐得天下,但是汤武善通变而能治,秦王不善通变,照行暴政,因此运祚不长。郝经用通变以合理的史观说服宋主顺应历史发展大势,不仅从理、势的角度发展了通变史观,他所表达的政治思想也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的。
刘因也曾从理势关系上谈到事物发展的规律,他说:“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而已矣。”“成毁也,代谢也,理势相因而然也。”(注:《静修文集》卷二《游高氏园记》。)他强调了天地万物新陈代谢、不断变化的必然规律,并把这种生生不息、存亡成毁归结为“理势相因”的结果。
刘因虽然没有从史学的角度详细论述理势关系及其在历史运动过程中的作用,但是他在讨论一些具体历史事件时,则反映出他主张通变,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反对逆势而动的思想。比如,刘因咏荆轲的三篇诗文,就通过怀古咏史,表达了他这方面的历史观。以《吊荆轲文》(注:《静修文集》卷五。)一篇为例,刘因在序文中先是对荆轲“豪饮燕市,烈气动天,白虹贯日”的英烈之气深为赞叹,称荆轲“亦一时之奇人也”。然而,在吊辞正文中,他对荆轲刺秦王这一事件本身却是持否定态度的。吊辞曰:“呜乎吾子,将何为哉?此时何时兮,不匿影而逃形。”“逞匹夫之暴勇兮,激万乘之雄兵。挟尺八之匕首兮,排九鼎之威灵。死而伤勇兮,虽死何成!呜乎吾子,何其愚也!”“子亦何人兮,敢与天仇?”荆轲重然诺,不惧强暴,慷慨赴死,这种气概实在令人钦佩,也为刘因所惋叹;但是如果将荆轲刺秦一事放在历史长河中来衡量,则不难看出荆轲的行动确实违时逆势,面对战国末年统一大势的滚滚潮流,不管荆轲刺秦是否得手,对于挽救燕国的灭亡都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刘因批评荆轲不识时务,“此时何时兮”;他认为荆轲所为是“逞匹夫之勇”,“何其愚也”。愚在何处呢?刘因说愚在“敢与天仇”,真是一语中的。这个“天”,正是战国末年历史发展的大势,荆轲等人孤注一掷,逆势而动,其结局虽然悲壮,但终究是一场悲剧,这在元代思想家的理性思维中是不能认同的。
元代思想家、史家从合理、求理的角度发展了通变史观,这自然与理学的影响密切相关,但同时也要看到,元初激烈动荡的社会巨变,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代潮流对于理学和史学的共同滋养。
三、王道德治的盛衰标准
元代历史观所折射出来的理学色彩还有很突出的一面,就是以是否实行王道德治,作为治乱盛衰的历史标准。
王道和德治是儒学古老的命题,早在孔子时就提出“为政以德”(注:《论语·为政》。)的政治构想,主张以道德标准作为政治统治的指导方针。从德治的要求出发,孔孟提倡推行“王道”,以德治国,以仁义治理天下。与王道相反,先秦法家提出了“霸道”的政治模式,即凭借威势,利用权术、刑法来达到统治的目的。王道、霸道的对立又与历史上的义、利之争互相联系。王霸和义利问题,在宋代有过激烈争论。北宋二程首先从理的角度上说明历史上王道、霸道的分别,南宋朱熹继承二程观点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三代以理与道治天下,人心合于仁义,因而是盛世;三代以后以法术治天下,人心为利欲所蔽,因而是衰世。当时的陈亮驳斥了朱熹的说法,他指出古今异道,今世不必法古,汉唐并非不如三代,并主张王霸兼用,义利并举。元代学者基本继承了朱熹的王道德治学说,在宋代史学总结“德政”治国、“礼义”兴邦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王道德治为标准考察历史的盛衰治乱,更为系统地阐述了王道德治对于治世兴邦的实质意义和重要作用。应该看到,元代史学思想的王道德治理论并不是对程朱理学的简单继承,它的思考与发展是元代特定的社会环境有紧密联系的,一方面,它是元初儒臣劝导元朝统治者改变蒙古时期多事武功、残酷杀掠政治方针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元代王道德治理论在理学领域和史学领域的总结发展,也适应了元朝中期统治者重视“文治”的需要。
元代王道德治的历史盛衰观包含若干内容。首先是从历史考察的角度誉“王”毁“霸”。强调王道德治为治世之坦途,霸道是乱世的祸端。元初大儒许衡就是主张王道,极力批评排斥霸道的。他曾纵论春秋五霸相争历史,极言王道式微、霸道横行之弊端,然后他总结说:
世之诋霸者,犹以尚功利为言,殊不知霸者之所为,横斜曲直莫非祸端。先儒谓王道之外无坦途,举皆荆棘;仁义之外无功利,举皆祸殃。(注:《鲁斋遗书》卷八《子玉请复曹卫》。)
只有王道德治才是达到盛世的唯一坦途。除此之外,“举皆荆棘”、“举皆祸端”。由此看出,他誉王毁霸、以王道为治世标准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还认为,霸道这种政治模式的问题不仅仅是追求功利,而是存在于国家政治中的方方面面,触处皆成祸端,因此单从功利角度去批评霸道是远远不够的。他一面深责霸道,另一面则将王道德治抬高到至理至善的地位,他说:“唯仁者宜在高位,为政必以德,仁者心之德,谓此理得之于心也。”(注:《鲁斋遗书》卷二《语录下》。)“诚敬之德是以感人,不用偿赐人而人自然相劝为善,亦不用嗔怒人而人自然畏惧不敢为恶。”(注:《鲁斋遗书》卷五《中庸直解》。)按照他的说法,王道德治从感化入手,自可人心咸服,无往不胜了。许衡的这些思想成为元代史学从王道德治出发,总结历史盛衰经验的基调。
元中期虞集主持编撰《经世大典》,他秉承朱学的王道思想,从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为元朝统治者总结“德治”的历史经验;同时,他也尽力排斥霸道的政治影响,甚至认为:“霸代王而淳朴散,利胜义而诈伪生,其由来亦久矣。”(注:《经世大典·宪典·诈伪篇序录》。)把历史上民风世俗的败坏都归结于霸道政治模式的侵蚀。元末编修宋、辽、金三史,总裁官欧阳玄在《进宋史表》中也明确表示了“先理崇德”的修史宗旨,在评价王安石变法时,《宋史》甚至不顾王安石新政为社会经济带来生机的历史事实,而全以朱熹崇道德、黜功利的观点来否定王安石变法的成绩,谴责王安石富国强兵之法只图功利,“躁迫强戾”,“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不合于三代“正其谊不谋其利”之王道(注:《宋史·王安石传》。)。
元代后期著名的史学家苏天爵曾进一步阐述了王道德治的基本要求。他说;“有国家者,欲图安宁长久之治,必崇礼义廉耻之风,敷求硕儒,阐明正学,彰示好恶之公,作新观听之几,使人人知有礼义廉耻之实,不为奔竞侥幸之习,则风俗淳而善类兴,朝廷正而天下治。”(注:《滋溪文稿》卷八《静修先生刘公墓表》。)他承袭朱熹的观点,认为三代行王道,“故其政教行于天下,莫不身修而家齐,礼明而乐备”(注:《滋溪文稿》卷五《深源刘氏传家集序》。);三代以后,治非正儒,王道渐微,汉唐数百年间,尽管也有名臣辅弼,但迷于“权谋功利之说”,因此“虽治弗善也”(注:《滋溪文稿》卷五《伊洛渊源录序》。)。元代史学根据当时社会崇儒重礼的需要,结合对前期几次失误的理财活动进行反省,从王道德治角度总结历史经验,因而具有某些独立的思想认识。但总的来说仍未摆脱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走出所谓“汉唐不如三代”这种历史退化论的误区。
第二,突出“仁政”这一王道德治的核心。元代史臣、儒士针对蒙古统治者在长期征战中对社会生产造成破坏,给人民带来灾难等问题,为了帮助元朝统治者从征战杀掠的武功转移到施行德治、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轨道上来,在提出王道德治的治乱标准时,突出了以“仁政”为核心的思想。元初大儒许衡首先借用《易大传》的内容,提出了“元”即“仁”的观点。《周易·乾卦·文言》在解释卦辞“元亨利贞”四字时有这么一段话: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这段文字的主要意思是说“元亨利贞”代表着“仁礼义正”四德,君子能行四德便可大吉。许衡巧妙地抓住了“元”与“仁”相配并称的关节点,用以阐述行仁政便得治世的思想。他说:
仁为四德之长,元者善之长。前人训元为广大,直是有理。心胸不广大,安能爱敬?安能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仁与元俱包四德,而俱列并称,所谓合之不浑,离之不散。元者四德之长,故兼亨、利、贞;仁者五常之长,故兼义、礼、智、信。(注:《鲁斋遗书》卷一《语录上》。)
应该看到,许衡煞费苦心地寻绎经典,反反复复强调“仁”与“元”的密切关系,绝非一般的解经说义,而是意在暗喻:元朝仁政,是早在圣贤经典中就有了定数的。当然,许衡没有停留在引经据典的说教,他又从历史总结的角度,多方阐明了为君治国推行“仁政”的重要。他说:“孔子道:‘一家仁,一国仁。’如尧帝、舜帝行仁,天下皆行仁;桀王、纣王不行仁德,政事暴虐,待教天下行仁,百姓每怎生行得仁?”(注:《鲁斋遗书》卷三《大学要略》。)不仅五帝三代时如此,秦汉的历史亦然,“秦楚残暴,故天下叛之;汉政宽仁,故天下归之”(注:《鲁斋遗书》卷七《时务五事》。)。许衡提倡以“仁政”为王道德治之本,对于元朝稳定统治秩序,推动多民族统一国家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苏天爵说:“昔我世祖皇帝既定天下,淳崇文化……而文正(许衡)之有功于圣世,盖有所不可及焉。”(注:《滋溪文稿》卷五《伊洛渊源录序》。)
继许衡之后,元代又有史臣不断从历史经验中总结“仁政”治世的作用,比如虞集在他主编的《经世大典》各篇序录中就突出表达了他的仁政思想,尤其在《宪典》各篇序录(注:见《元文类》卷四二。)中有比较集中的体现。《大恶篇序录》就说:
天地之道,至仁而已。国以仁固,家以仁和。故国不仁则君臣疑,家不仁则父子离。父子离,无所不至矣;君臣疑,亦无所不至矣。
他把“仁”作为天地之道,治家治国之本,并指出不守仁义之道可能产生的恶果。守仁义之道就是实行王道,因而它的政治措施与霸道有根本的区别。《宪典》各篇序录特别重视这种区别,指出在德治国家里,刑法只是仁政之余一种不得已的辅助手段,“夫圣人以礼防民,制刑以辅其不足”(注:《奸非篇序录》。);“教化不足,然后制以刑,而非得以也”(注:《户婚篇序录》。)。《宪典》虽然也记诉讼刑狱等制度,但他们真正期望的是以王道仁政达到“无讼”、“无刑”、“空狱”的局面。元修三史也常常通过史事和论赞强调仁政在治世中的重要作用,比如《辽史》就用最多的篇幅来记述圣宗朝的仁政,《圣宗本纪》概括了辽圣宗在位49年,“理冤滞,举才行,察贪残,抑奢僭”,勤政勉力的业绩,说明了施行仁政是圣宗能为辽国“维持二百余年之基”的根本原因。《金史》记载金世宗的“大定之治”,关键在于“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注:《金史·世宗纪》。)。《宋史》中,也对宋仁宗“恭俭仁恕”,审定死狱,“岁常活千余”的仁政大加褒扬,赞曰:“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注:《宋史·仁宗纪》。)由此观之,三史以仁政为治、暴政为乱的价值标准是很明确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三史中有不少内容能够结合历史事实,总结仁政与暴政的成败之因,具有较强说服力,这是与那些泛泛而论、脱离实际的王道德治说教绝不相同的。
第三,强调伦理纲常是决定历史盛衰的基础。儒家的纲常名分思想是王道德治理论的根基,宋元理学把这种纲常名分的等级秩序上升为天定的自然秩序,是“不易之理”。许衡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贵贱位矣。在上者必尊之,然后事可得而理。为君长,敬天地、祖宗、鬼神;为百执事,敬事君长;此不易之理也。舍此便逆,便不顺。”(注:《鲁斋遗书》卷二《语录下》。)他强调上尊下卑的关系是一种不可改变的理的规定,违反这种规定就会出现逆乱。为了更详尽地说明纲常名分对历史盛衰的决定作用,他还说:
自古及今,天下国家惟有三纲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则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则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妇知妇道,则夫妇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则他事皆可为之。此或未正,则其变故有不可测知者,又奚暇他为也。(注:《鲁斋遗书》卷一《语录上》。)
许衡总括古今历史,论证只有三纲五常正才可为国为政,否则“其变故有不可测知者”,更何谈有治世安邦了。许衡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元中期的虞集对此也有类似的阐释,他归纳《春秋》经传所述史实说:“《春秋》道名分,实尽性之书也。分上下不辨,则民志不定,乱之所由生也。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分定,则王道行矣。”(注:《道园学古录》卷三一《送饶则民序》。)他把维护三纲五常的名分等级看成是推行王道的基本保证,只有尊卑上下之位分辨清楚,各行其常,王道才能实行,天下才能得治,否则民志不定,便会生乱。元末三史的编撰思想中也特别注意突出纲常名分在历史盛衰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贵贱为而后君臣之分定,君臣之分定而后天地和,天地和而后万化成”(注:《辽史·逆臣传》。)。因而纲常名分之立为“天地圣贤之心,国家安危之机,治乱之原也”(注:《辽史·奸臣传》。)。为了“扶纲常,遏乱略”(注:《宋史·叛臣传》。),三史分别用大量的篇幅设立《忠义传》、《逆臣传》、《叛臣传》和《奸臣传》,强调“天尊地卑”、“贵贱位矣”、“君臣之分定”,以纲常伦理、君臣大义等道德价值为标准,褒贬善恶,以为治乱兴衰之戒。他们判断历史盛衰的标准是看王道是否实行,而王道之行关键又在于纲常能否确立,于是这便形成了天理纲常支配历史盛衰的逻辑关系。
元代史学在总结王道德治盛衰标准时,一方面通过强调“仁政”,肯定了历史上施行仁政的一些积极措施,揭露了封建制度一些不仁的弊端,这不仅有助于从历史观上逐步认识社会盛衰治乱的原因,也为元朝政治向好的方面转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在强调王道德治历史意义的同时,依然未能走出理学社会观中“三代胜于汉唐”的思想误区;在强调德治仁政和人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却又常常偏离历史实际,陷入理学以道德评判标准衡量一切社会问题的错误逻辑关系,最终得出天理纲常支配历史盛衰的唯心结论。
总的来说,理学的思想认识水平,为元代史家对历史的理性思辨提供了哲学依据,使之在考察以往历史过程时,能够在一个较高的价值层面展开思考和分析,探求历史盛衰的原因。当然,理学的“天命论”、三纲五常思想和后世不如“三代”的观念对史学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但是元代史学毕竟有自己的客观认识对象和内在的发展规律,因而理学对史学的渗透没有使元代史学成为理学的附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