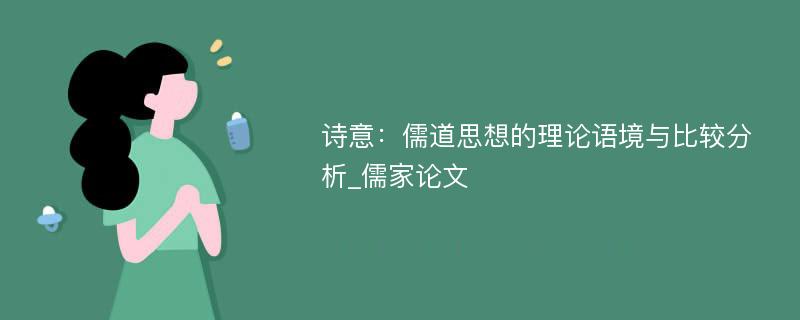
诗言志:儒道两家的理论脉络及其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道论文,两家论文,脉络论文,理论论文,诗言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定的文学本体论总不免在一定的哲学本体论的笼罩之中;任何概念都有其不可推移的定性。我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莫过于儒道两家,二者尖锐对立,却都认可诗言志说,然而儒家之志与道家之志大相径庭,这又是最明显的事实,究其要源,则不得不上溯到各自的哲学本体论去。
儒家之志是一种入世之志。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以孔子代表的儒家痛心疾首又执着于人生,以改造社会为已任,积极进取。不信天命,只靠人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挽狂澜于既倒的勇气,非道德高尚者不能有,因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以儒家之志又是一种君子之志,所谓“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杀身以成红”“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种志从道德修养而来,涵养的是一种伟大的人格,仰慕的是一种君子之风,目的却不是为的洁身自好,而是通过修身来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儒家之志又是一种治世之志。世何以治?关键在治人,由此孔子编织了严密而精巧的以治人为中心的治国治家方略、道德规范之网: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礼(等级)定秩序,“非礼勿视,非视勿听,非礼勿动”,“君子臣臣文文子子”,当这些外在的道德规范就成了人的自觉的内心需求的时候,就实现了“仁”,就是最大的“善”。既然儒家之志是如此这般的志,它就不可能不重视文学,因为文学正有这治世治人的妙用:“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术之名。”而文学要想起到这样的作用,又非得“言志”不可,“志”在文学作品中就成了浸染着儒家道德意识的理性内容。与之相呼应的是“文以载道”,这里的道和志一脉相连,只不过在意义的表述上比志更显豁,更单纯,也更观念化罢了。
道家也讲“诗言志”;《庄子·天下》篇云“诗以道志”,其言可证,但儒家之志与道家之志一在此一在彼,有着绝大的不同。儒家讲礼义,重秩序,倡人为,这在道家看来大可不必,甚至有害无益。老庄认为,正是礼义搞坏了道德,人为造成了虚伪,秩序造成了混乱,使天下汹汹,而救之之道,便是反其道而行之,倡导“无为无不为”。无为即天所作为,一切顺应自然,正因为顺应了自然的规律,放弃了狭小的急切的功利,才能得到不可限量的功利,这叫“无不为”。“无为无不为”的哲学原则同时又是老庄的美学原则,征之于文学的作用,就是“无用无不用”,这正与儒家的“有用”针锋相对。而这“无用”并非是真的无用,却说的是文学本无具体的有限的小用,而有无形的无限的大用,即使身心与宇宙同一,臻于自由和超越的境地。这样的“用”固然是“有”。但同时因其无限的大,就又是“无”。拈出文学“无用”两个字,真使儒家的“有用”黯然失色:“兴观群怨”太小巧了,“事文事君”太迂阔了。由此道家反对有限有形的文艺,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最好的文艺不在形而下,而在形而上:“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得鱼忘筌”;唯有神化的境界才是美的境界:庄周梦蝶,不知是蝶论庄周还是庄周化蝶,陶潜抚琴,琴无一弦而出神入化,这正是道家之志的形象体现。有无之辩,旨在自由;道家之志是自由之志。
不同的志与道进入具体的创作过程,依然是大相径庭,儒家之志是一种观念化的东西,它是由儒家精神所规定的一种人格和怀抱,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这么说:儒家之志与道在具体的创作过程开始之前,就已经观念性地存在于诗人和作家心中了。这是儒家创作论的一个可取处。它在文艺创作上非常清醒地强调目的,强调理性,与创作的不可知无意识绝缘;但同时这里面也隐藏着严重的缺憾,最终导致了它的创作论的危机。因为无论诗之志或文之道,都是观念性的东西,在诗文创作中是第一位的东西,作诗是为了言志,作文是为了载道,譬如车之载物,船渡人,这未免太有些实用主义了,与文艺本身的存在不相容。更关键的是儒家创作论中的志与道仅仅是儒家之志儒家之道,它把一家的理性社会化乃至人性化,描绘成万世不变的理性,而在这社会化人性化的途路中,具体活动着的个人的感性生命便被榨干。须知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于它是个人的一种精神流程,须以独特的艺术情感铸造独特的艺术形象,其中自有理性在,但这理性只能属于感性的生命,在无数个感性生命中蕴藏,在人类的历史进步中积淀。儒家无视这些,把理性一律化,必须重道轻文,反映到诗文创作中,不能不造成文道脱节,主题先行的倾向。虽然孔子早就有这样精巧的辩证的文道关系理论:“质胜文明野,文胜质则史”但由其整个思想体系以及文艺思想体系的决定,到底难逃唯理和致用的偏向。果然,待到儒家思想成了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我们就看到了两汉儒生和文人的“依经立论”,降及唐代的“文以载道”,甚至恶性发展为宋明理学“作文害道”。虽然,儒家之道经二千余年发展,以道家思想作补充,又援佛入儒,丰富或拓展了自己,甚或在历史的进步之中,产生相应的异变。溶入了劳动人民群众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智慧、道德、希求等等,但儒家思想的根本性质并未改变,它对文艺的本质及作用的规定并未改变,“文以载道”贯穿历史,一脉相承。只要看看清末的梁启超怎样把小说当作载其变法维新之道的利器,把小说的社会作用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就知道为儒家文艺观所决定的文以载道说是怎样要深蒂固。当文艺为儒家之志与道所凌驾的时候,文艺自身便不得不异化:文艺家主体性的丧失以及文艺作品的主体性的丧失。文艺作品文章化。文艺成为一种工具。文艺学也就成了文章学。
文艺自身异化的另一方面是创作过程的文章化、程式化。儒家以善为文艺的本质,以经世济用为文艺的社会作用,这就引出文艺自身的一对矛盾:文与质的关系。把整一的文艺作品在理论上分离出去,文与质即内容与形式两大组成部分,这就把立体的动态的创作过程纳入平面的静态的研究,极容易导致对这一过程进行程式化的描述。后来的陆机在《文赋》中把文艺创作描绘成“物一意一文”的过程,就在理论上更进了一步。维之刘勰在《文心雕龙·熔裁》中提出“三准”说:“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在立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写作步骤,了了分明,更趋于程式化。
陆机、刘勰的文章理论经唐宋明代古文家的发展,到了清代桐城派那里,更加精巧了,完全成熟了,桐城派古文家讲究“义法”,讲究“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总结出“义理、考据,文章”的写作路数,这是彻底的理性化,也是彻底的规范化的程式化,与文学学几乎不搭界了。
对比之下,道家之志进入具体的文学创作,却没有这样的危机。
如前所述,道家之志是一种自由之志,这种志并非观念化的东西,也不是某种理论体系所规定的人格和怀抱。它的产生全然依靠人与自然的巧妙遇合,和谐统一。它在过程中产生,并且只有在过程中才能显示出来。道家开山老庄其人或许并不自知,这种过程不仅是人的自由的活动,同时也是美的创造过程,道志也就具有纯粹的美学意义了。因为道家追求“化”的境界,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之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在这一境界中,物即我,我即物,神与物游,天人合一,在这里,本无须问文艺是什么,我们只见到人与自然如两个亲密的灵魂的和谐与默契,它是文艺,也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身;在这里也无须问文艺之用是什么,它根本不是工具,也不担负着训诫的任务。从生命中生发出来的,又原原本本还给生命,把人从喧嚣的尘世中提出,在自由的螺旋上升高一步,如此而已。
既然道家是在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中产生,而这统一的过程本身又是美的创造过程,那么道家之志与具体的创作过程就谈不上分离,二者本是浑然一体的。集中到“意境”的创造上,那创造必然是一立体的,运动的过程,也分离不得。当然,老庄不可能做这样的描述,但这样的描述完全合乎老庄的初衷。使诗人怦然心动,诗兴勃发的不是理念,而是诗的意象,这是诗的受孕,意境创造的开始。在理论上,我们可以给意象以尽可能清晰的解释,其实它在诗人头脑中的存在,是很朦胧的。首先这“意”不等于理,理如酒精,意如醇酒;理可以明晃晃地先存在于胸中,意只能从人与自然的撞击中而来;由此理明确而单纯,意却模糊而多义。其次,这“象”也不等于物;物是纯自然的,而象是心灵化了的物,一被灵魂的眼睛看见,它就不再属于自然。所以与理相对应的物和与意相对应的象进入创作过程,那是很不相同的。理与事可分可合,因为理从事来。原本是对事的提升和抽象,二者就有了距离,主体客体分得清而儒家之理往往从心中来,这就与事的距离更大,以此指导创作,理在事先,以理为帅。搜寻于物,合则留不合则去,在创作过程中,理就始终凌驾于物之上。创作之始,是理的切入;创作之中,是理的发挥;创作完结,是理的完成。整个创作过程,竟是理对物的指挥,物对理的认同,它留给文艺作品的标记是或开篇明志或卒章显志。理之于事,正如油之于水,即便竭力搅拌,还是分得清。这样的创作过程,必定在一平面上展开,或可做定量分析了。而与之相对的意象却是不可分的,它是诗人与自然的一次极巧妙的遇合,诗人凭直觉知道,它是诗,极有意味,但却知其然不知所以然,诗人当然也可以就此停步,对其中的含义穷追不舍,一直抽象出其中的理来,但这显然是科学思维而不是艺术思维,诗人一旦作此尝试,他就不是诗人。事实上,诗人在发现意象的惊喜中,绝不会也不可能做理论上的停留,此时他的整个注意都为艺术形象所吸摄,整个思维都为艺术想象所占领,而支配那艺术想象合情合理和艺术形象体系丝丝入扣的,便是原本存在于诗人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的意象中的艺术逻辑的延深和发展,其指向是意境的形成。这样的创作是“无目的的合目的”;说它无目的,是因为引起诗人创作冲动的,不是明确的理念,而是很有些朦胧的诗之意象;推动艺术构思的行程的,也不是明确的理念,而是由这意象所激发的蓬勃的艺术想象创作主体所感知的,只是艺术形象的逻辑运动,仍然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这并不意味着创作的无意识或非理性。因为艺术构思虽无直接的目的,但却必须符合艺术逻辑,这就使思维具有了不可置疑的理性。凡是合逻辑的,必定是合情合理的;艺术逻辑只管想象的是否合理,却不说明一个单纯的目的,虽然这目的最终是要显示出来的,却完全由运动中的形象来显示,不是创作者予先决定,强加上的,所以说创作是无目的的合目的。这样,就决定了整个创作过程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是一个立体的运动过程。理论家面对静态的文艺作品所做的一切分解研究,在艺术构思创作过程中都是整体地发展,整体地落成,无论是诗之意境,还是它的性格、情节和主题。严格地说,艺术创作中不允许有“单独”存在。这就是老庄的文艺思想在创作上给我们的启示,毫无疑问,它非常符合创作规律。
但是,道家之志中缺少一种正确的理性。因为它的自由与实践无缘,与必然无缘,它是种绝对的自由,逃遁和出世的自由,其实不自由。这反映在创作的方式上,就使创作虽暗合规律却过于神秘化,反映到文艺作品中,就使其理性内容日益空灵,淡泊,不见人间烟火,不见生命的血色,这不能不是文艺的一种失落,文艺是自由的,这固然是一种理性,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才是文艺所须臾不可离的正确的理性。于是,面对道家文艺思想的遗憾,我们不得不把目光再移向儒家了。儒家的急功近利,使它探索起文艺的规律很是隔膜,但惟其如此,它才成为一种地道的入世哲学。它把人世的一切都纳入到家国的规范之中,耳提面命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强大的道德规范深入尘世与人心,渗入于文艺,就变成脚踏实地的强大的理性内容,如地网天罗,牵掣着文艺思想也未可轩轾,两家互补——把儒家的理性内容和道家的创作规律统一起来,倒是满写意的。
可是这么一来,又出现了新的疑问,那就是,上述的理性内容和创作规律能否完美地结合?古代的有才能有成就的文艺家是否在不知觉中暗合了这规律,循此创作?
作为一种处世哲学,儒道互补在封建社会必定存在。虽然它只给知识分子以表面的心理平衡,更多的依然是惶惑与痛苦;作为一种创作理论,儒道文艺思想却很难结合,理由很简单,因为创作理论需要一体化,排斥二重性。对立的互补可以在此为人处世,对立的“结合”却无法以此著诗作文。处世哲学并不等于创作论。概言之,二者原本不在一层次上,不可对比和以此类推。并且儒学和道学之中都没有人的真正的自由,都不能真正实现人的价值,因之,它们都不能成为文艺的富有生命力的理性内容。文艺虽受思想的影响但不能在思想中寄生,从思想中取材,它必须植根于生活,而生活的中心和焦点是人,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就在于要表现这人的思想情感,性格命运,所以“文学是人学”。从另一面看,文艺创作的主体也不得不是有着独特思想情感、性格命运的人,而不是某种思想,即便是权威思想的化身,虽然他难逃这思想的影响。这样,思想的权威性总想使文从属于已,文艺的自立性却使它终于走自己的路去了,一部古代文学史只能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历史,而不是儒道思想的形象注脚,可是我们往往忘情于传统思想的深邃与玄妙之中,却不免忘却了构成古代文艺的理性内容的源头活水,那最富有生命力的具体活动中的人的因素,而正是这人的生命内容,才构成文艺的理性内容。
古代文人并非是暗合了儒道文艺思想互补结合的“规律”,并循此创作的,征之于那些千古流传的古代文学杰作,但见字里行间活泼泼生命的跳跃和闪烁,使人想起活的人生;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离人之梦,羁旅之思……灵魂的喧嚣与骚动,人生的欢乐与酸辛,幻化成最美的诗行,令人惊赞不已。遥想那些大诗人的创作,大概绝不会如汉大赋的创作那样费时三年、穷搜海内、吐血几升的拼凑吧,反倒一定是脱口而出,不暇布置的。情之所衷,如骨在喉,一吐为快。老庄那令人击节赞赏的美的创造过程他们一蹴而就,孔孟所耳提而命的道德规范却未成为他们诗作的理性内容。他们抒发的是一已之情,暗合的是全人类的情感。他们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却不屑于把它交给一种统治思想去掌握。虽然,统治阶级的思想从来都是占统治的思想,但是任何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从来也不可能统一思想,否则诗早绝灭了,因为驯化了的思想之中没有诗分子。当然,他们的思想总不免受儒道思想的影响,但他们的思想也同时对后者做出泼辣的反博,这才有独立的人格在。正是这人与社会的矛盾运动,人对自由的追求显示的生命活动的本身,才构成他们诗作的理性内容。“天意君知否,人间要好诗”,而“好诗不过尽人情“,真是一语中的。这也正是”诗言志“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