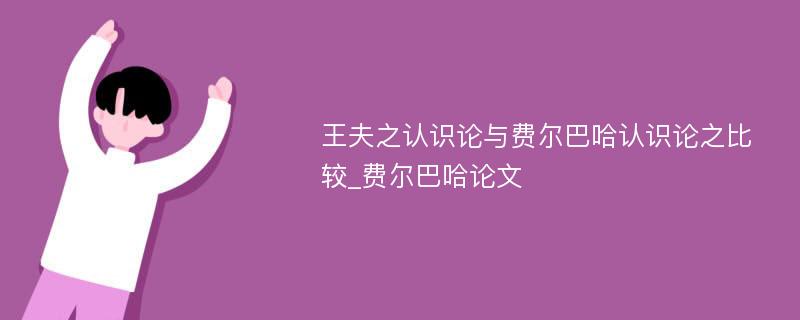
王夫之与费尔巴哈的认识论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费尔巴哈论文,认识论论文,王夫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王夫之和费尔巴哈是中西哲学史上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在认识论上有相似的看法,也有不同的见解。本文通过对他们的认识论进行分析比较,旨在说明我们中华民族不仅有灿烂的科学文化,而且有丰富的优秀的哲学思想。
关键词 认识论 思维 存在 理性认识 感性认识 实践
王夫之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在认识论方面,王夫之提出了许多别具一格的卓越见解,深入发展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是西方旧唯物主义发展的高峰,在认识论上也有独特的见解,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创立提供了理论前提。王夫之生活于十七世纪中国的封建社会,费尔巴哈生活于十九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时期,他们虽然生活于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形态,但这两位哲学家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却有不少相似之处,本文试对他们的认识论进行分析比较。
一、认识来源于客观存在
王夫之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则,强调人的认识来源于客观存在,否认人类有先天固有的知识。他说:“知见之所自生,非固有。”〔1〕王夫之认为, 认识不是单纯由主体的感觉器官及其能动性引起的,也不是单纯由客体的存在及其作用引起的。而是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发生的,他说:“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2〕“形”是指感觉器官,“神”是指思维能力,二者都属于认识的主体;“物”是指客观对象,是认识的客体,主体与客体相结合,才有知觉的发生,才能产生认识。王夫之认为,客观事物是天下固有的,不依赖于人的主观认识而独立存在,也不以人的主观认识为转移,相反,主观认识倒是以客观事物为源泉。他说:“色、声、味之在天下,天下之故也(自注:故谓已然之迹)。色、声、味之显于天下,耳、目、口之所察也。……若其为五色、五声、五味之固然者,天下诚然而有之,吾心诚然而喻之;天下诚然而授之,吾心诚然而受之。”〔3〕五色、 五声、五味是天下固有的客观存在,人们通过自己的五官去辨、去审,再经过大脑的思维,就可以获得认识,认识来源于客观存在,这是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观点。
费尔巴哈认为,思维是人的大脑的活动,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人的认识内容的来源。他说:“我的感觉是主观的,但它的基础或原因是客观的。”〔4〕人正是在和万事万物的接触中形成各种感觉和概念, 从而产生认识。因此,他指出:“思维和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5〕费尔巴哈认为,思维存在于肉体,是人脑的属性, 思维离不开人而存在,思维的内容是反映外在客观世界,思维也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他说:“我把我的思想建筑在只有借感官活动才能经常不断地获得的材料上面,我并不是由思想产生对象,正相反,是由对象产生出思想;只是,这里的对象,专指在人脑以外存在着的东西。”〔6〕
可以看出,王夫之和费尔巴哈都坚持了唯物论的反映论,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客观世界,思维是存在的反映,只有借助人的感官,才能产生认识。
二、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我们知道,认识是思维对存在、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反映关系。王夫之利用、改造佛教哲学的“能”、“所”范畴,对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和客体、主观认识能力和客观认识对象,给予了正确的规定和区分。他说:“立一界以为‘所”,前未之闻,自释氏也,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能’、‘所’之分,夫固有之,释氏为分授之名,亦非诬也。”〔7〕在这里, 王夫之明确认为,“能”、“所”之分是认识论中有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能”与“所”。他认为,“所”是接受主体能动作用的客观对象,是认识的客体;“能”是主体作用于客观对象而有其实际功效的能力,是认识的主体,“能”和“所”相互区分,“所”不在内,“能”不在外,认识的对象与认识的活动是有区别的,认识只是主体的活动,它不能代替客观的对象;认识对象则是不依赖于主体的客观存在。他指出:“‘所”著于人伦物理之中,‘能’取诸耳目心思之用,‘所’不在内,故心如太虚,有感而皆应;‘能’不在外,故为仁由己,反己而必诚,”〔8 〕认识的对象“所”表现于自然物体和社会关系之中,因而不在主体之内“能”即主观认识能力,则表现人的耳目等感官和脑的思维活动,它是在主体之内,而不在客体之中。
至于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王夫之认为,客观对象虽然是“俟用者”;但主观认识毕竟是由客观对象的引发而产生的,这叫“因‘所’以发‘能’”〔9〕,必须依靠客观存在着的真实对象, 才能引起认识作用,客观“所”是第一性的。“‘能’必副其‘所’”,〔10〕主观认识虽然可以作用于客观对象,但主观认识必须与客观对象相符合,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费尔巴哈是以人为基础来解决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的。他认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在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有真理。”〔11〕精神、思维不过是人脑的属性。他说:“没有脑的活动,我便不能思维,不能分辨。”〔12〕思维“对我来说,即主观上说来,是纯精神的、非物质的、非感性的活动,那么,就其本身说来,即从客观上说来,是物质的、感性的活动。”〔13〕这就是说,在主观上,思维是非物质的;在客观上,思维又是物质身体的活动。“人”相对于自然界而言是主体,但相对于自己的精神而言是客体。因而,费尔巴哈认为,精神和肉体、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以肉体为基础不可分割地统一于物质身体之中。
王夫之利用、改造佛教哲学的“能”、“所”的范畴,从而论述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费尔巴哈是以人为基础解决思维与存在,主体和客体的统一问题的。王夫之和费尔巴哈都认为,客体不依赖于主体而独立存在,主体能够反映客体,认识就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但是,费尔巴哈没有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王夫之认识到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性,王夫之提出了“善动化物”、’以人造天”的思想,他认为“天无为”,“人有为”,人能够“相天”、“胜天”、乃至“造天”。“相天”,意即治天;而要“相天”,就必须努力“竭天”,尽力地去了解天。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够从事改造自然、治理社会的“相天之大业”,〔14〕创造出社会所需要的一切。
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
王夫之沿用传统哲学中“格物”和“致知”范畴来说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并对这一范畴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赋予了新意,增添了新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认识运动的辩证法。他说:“夫知之方有二,二者相济也,而抑各有所从。博取之象数,远证之古今,以求尽乎理,所谓格物也,虚以生其明,思以穷其隐,所谓致知也。非致知则物无所裁,而玩物以丧志;非格物则知非所用,而荡智以入邪。二者相济,则不容不各致焉。”〔15〕“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惟在心官,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辨之疑。致知在格物,以耳目资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非耳目全操心之权而心可废也。”〔16〕王夫之把人的认识区分为格物、致知两个阶段,其内容相当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里所说的“格物”,即认识的感性阶段,是通过考察自然现象,研究历史过程,以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所说的“致知”即认识的理性阶段,通过心官的理性思维,根据已有的原理加以分析,进行推理,以穷尽其中的隐微,王夫之认为,“格物”主要是通过感官与外界发生联系,但也离不开心官的思辨作用。“致知”主要靠心官的思辨作用,但也不能脱离“格物”阶段的耳目之实。耳目闻见的感性材料是“资心之用,而使有所循”的基础,又是“决思辨之疑”的根据。“格物”得到的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它有很大的局限性,容易“为物所蔽”,而“致知’则是“心之独用”的专有领域,它离开了具体的物象,可以突破“耳目但得其表”的局限性,使人们的认识由“但得其表”上升到“表里之俱悉”,从而深入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因此,王夫之强调认识的两个阶段都是不可缺少的,二者“相济”,不可偏废。只讲“格物”,没有“致知”,感性认识如果没有理性认识的指导,就会迷惑于现象“而玩物以丧志”,达不到真正认识事物的目的;反之,只讲“致知”没有“格物”理性认识如果不以感性认识为基础,就会流于空想“而荡智以入邪”。所以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又必须以感性认识为基础。
费尔巴哈主张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他认为,感性是认识的起点,是理性的基础,是沟通主体和客体和桥梁。人们只有通过感官才能同客观世界打交道,也只有在感性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思维。他说:“没有感性的东西或在感性的东西以外,精神的东西便什么也不是;精神不过是感官的英华、感官的精粹罢了。……理性是以感官为前提的,感官却不是以理性为前提。”〔17〕感性先于理性,理性只有通过感官才能找到通向客体的道路,达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大树感性的权威,是费尔巴哈认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他把自己的哲学即所谓新哲学叫作“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18〕他非常强调感性认识的确实性、可靠性。他说:我与那自绝于感官的哲学相反,把感性的东西确定为直接具有确实性的。”〔19〕费尔巴哈之所以强调感性认识的的确实性,可靠性,是因为他认为只有感性认识才是直接认识,而理性认识是间接认识,费尔巴哈在强调感性认识的同时,并不否认或贬低理性认识的作用。他认为,感性认识虽然是认识的起点和基础,但它只能提供个别的、分散的感觉材料。“没有思想的感性止于个别现象”。〔20〕单靠感觉是不能真正认识事物和现象的,要深刻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从感官提供的各种现象的特征连结在一起,进行分析,而“联系起来读感官的福音就是思维”。〔21〕因此,他说:“我们读自然的书用感官,但要了解它却不能用感官”,〔22〕而要用思维。只有思维,才能从感性事物中“分解、寻找、抽出统一的、同一的、一般的规律”。〔23〕所以,人的认识不能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必须提高到理性认识阶段,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费尔哈认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虽有区别,但两者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他说:“感性若无思想便等于零,思想,即理性,若无感性也同样地等于零。”〔24〕不可能有无思想的感觉,即使是纯粹的视觉也需要思想,也不可能有无感觉的纯思维。
可见,王夫之和费尔巴哈都认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阶段,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但感性认识只能提供个别的、分散的感觉材料,而理性认识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感性认识必须发展到理性认识。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又有不同的错误认识。王夫之有时严重地割裂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贬低耳闻目睹的感性认识,否定它作为认识的基础,片面地推崇离开感性认识的理性思维。费尔巴哈没有脱离旧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框框,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上,有些看法是矛盾的,混乱的,他同王夫之一样,有时也割裂了两者的关系。在费尔巴哈看来,理性无非“是诸感官之作用的总和”。〔25〕按照费尔巴哈的这种观点,感性和理性的差别只是局部和整体的差别,只有数量上的差别,而无质的差别,与王夫之有时推崇理性认识相反,费尔巴哈夸大了感性认识的作用。费尔巴哈认为,理性、思维并不比感觉说明更多的东西。他说:“思维、精神、理性,按其内容,除了说明感觉所说明的东西而外,并未说明什么其他的东西。”〔26〕这样一来,费尔巴哈实际上把理性降低为或归结为感性的东西了。这表明费尔巴哈并不懂得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其原因是他不懂得人的认识过程是一个能动的过程,而把人的认识看成是一个静止的、被动的、照相似的反映。
四、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关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王夫之是通过知行这一哲学范畴来论述的。知行问题,也就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王夫之认为,知行始终不相离;知行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它们既对立,又相互依存,在全部认识过程中各有功效,“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27〕行是知的基础,对知的发展有决定作用。他说:“且夫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28〕王夫之认为,知是依靠行来完成的,而行不是依靠知来完成的;知只有通过行才能取和成功。行可以得到知的效果,而知不能得到行的效果,而且行是鉴别认识的真正效验的标准,行是知的基础,行优越于知。他说:“闻见之知,不如心之所喻;心之所喻,不如身之所亲行焉。”〔29〕“身之所亲行”的实践活动,不但比“闻见之知”的感性认识重要,甚至比“心之所喻”的理性认识重要,王夫之如此重视行并不意味着贬损知。王夫之认为,知行相资以为用,知对行也具有反作用。他说,行和知“可立先后之序,而先后又互相为成,则由知而知所行,由行而行则知之,亦可云并进而有功。”〔30〕王夫之在肯定由行而得知的基础上,又肯定“由知而知所行”,即肯定了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实践产生认识,认识也指导实践。人们通过行由不知到知,由浅知到深知,“日进于高明而不穷”,〔31〕不断开拓人类认识的广度和深度。
费尔巴哈在他的著作中,企图从理论上解决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费尔巴哈认为,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人是可以认识世界的,虽然个人的知识和才能是有限的,但人类的知识和才能是无限的。他说:“有无数的东西,我们的祖先不能做的,也不知道的,现在我们能做了,也知道了。”〔32〕“我们没有认识的东西,将为我们的后人所认识。”〔33〕费尔巴哈关于个人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以及整个人类认识能力的无限性和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的见解是正确的,是他的认识论的精华。
费尔巴哈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生活实践比引证更为重要,“比渊博的征引更加有用到无量数倍的,却是实践,却是生活。”〔34〕“从理想到实在的过渡,只有在实践哲学中才有它的地位。”〔35〕费尔巴哈还认为,在认识过程中,实践比理论重要。他说:“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36〕
由于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的本质,不懂得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对实践的理解是片面的,只是把实践局限于人们眼前生活的范围之中,把实践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感性直观,即人的感官对外界的直接的、被动的、照相似的反映活动。他还认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乃是直观。”〔37〕费尔巴哈不懂得感性直观仍属于主体认识的范围,而把它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表明他并没有摆脱主观主义。费尔巴哈还把实践看作是人与人的交往等生活实践,他说:“一般说来,实践的观点也就是生活的观点。”〔38〕费尔巴哈还把实践理解为一种利己主义的活动。他说:“站在实践观点上,人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用场,去同一切事物打交道。”〔39〕因而,人们之间的交往,乃是利己主义活动。“直到今天,犹太人还不变其特性。他们的原则,他们的上帝,乃是最实践的处世原则,是利己主义。”〔40〕
王夫之和费尔巴哈分别在不同程度上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他们都正确地认识到了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但是,他们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一样,不懂得实践的社会性,因而对实践(行)的理解,其含义比较狭隘。他们所说的行或者实践,都不是社会实践。王夫之心目中的“行”的主体还主要囿于圣人贤智的范围,主要是指日常活动和道德行为。但我们应该看到,王夫之的“行”也涉及到了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活动。费尔巴哈把“实践”理解为感性直观、生活实践和人们之间的利己主义活动。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费尔巴哈“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尽管费尔巴哈不懂得“实践”这一概念的科学含义,但费尔巴哈所说的实践,不是脱离现象的实践。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
应该指出的是,在知行(认识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王夫之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对知有决定作用,知对行也具有反作用,二者“相资以为用”,“互相为成”,“并进而有功”。〔41〕王夫之的知行统一学说,符合列宁所说的“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认识路线。在当时能达到这种水平,是相当卓绝的。王夫之离开了社会实践,当然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解决知行(认识和实践)关系问题;但王夫之在论述二者关系问题的时候,显然要比费尔巴哈深刻一些。
综上所述,王夫之和费尔巴哈在认识的来源、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等问题上,有相似的正确看法,也有不同的错误认识。王夫之的认识论,达到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为我国封建社会过渡到近代社会的发展作了思想上的启蒙,对于十九世纪末的爱国主义维新运动和二十世纪初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产生过积极的广东的影响,费尔巴哈在反对唯心主义和神学的斗争中,使唯物主义恢复了它应有的权威,用清醒的哲学代替了沉醉的思辨,这是他的伟大功绩。费尔巴哈的认识论有着划时代的历史地位,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创立提供了理论前提。生活在十七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王夫之和生活在十九世纪德国资本主义时期的费尔巴哈,行为人类认识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注释:
〔1〕〔31〕《思问录内篇》。
〔2〕《张子正蒙注·大和篇》。
〔3〕〔7〕—〔10〕〔15〕〔27〕〔28〕《尚书引义》卷三。
〔4〕〔5〕〔11〕〔12〕〔13〕〔18〕—〔26〕〔35〕〔36〕〔37〕《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30、115、181、195、169、251、254、219、253、252、216、252、108、248 、179页。
〔6〕〔17〕〔32〕〔33〕〔34〕〔39〕〔40〕《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2、587、781、635、554、511、146页。
〔14〕《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
〔29〕《周易内传》卷五。
〔39〕〔41〕《续四书大全说》。
〔38〕《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1页。
标签:费尔巴哈论文; 认识论论文; 王夫之论文; 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客观与主观论文; 感性认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