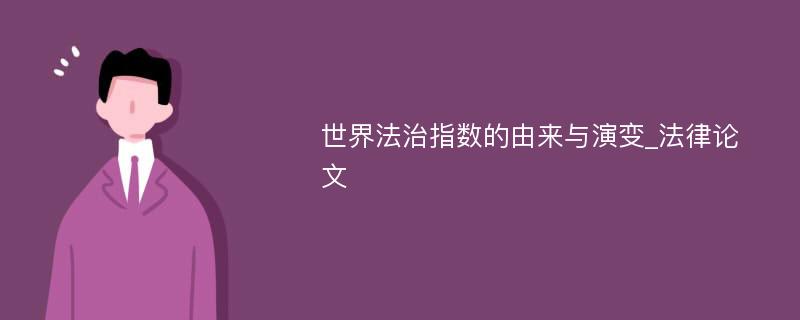
世界法治指数的缘起与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缘起论文,法治论文,指数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0年以来,一种名为“法治指数”(Rule of Law Index)的新现象出现在中国,引起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①并在我国一些地区形成了富有成果的实践。这种“法治指数”被很多学者视为新颖、客观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衡量与评估法治发展状况的技术手段,反映了跨学科研究的新趋势。而与此同时,它也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怀疑和批评。“法治指数”的构想从何而来?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建立在何种认识论基础上?其效果如何,缺陷在哪里?都是值得研究与思考的问题。 本文试图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法治指数”的理念与实践产生、发展、传播和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回答前面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在笔者看来,对中国来说,与现代法治的理念与实践一样,“法治指数”也是一种“舶来品”,是在法律全球化背景下一种全新的世界法律地图,是法律散播(diffusion of law)的一种新形式。它所传播的是特定的法治理念,有特殊的原始样本,自然难以避免地产生一系列扭曲作用,成为葡萄牙学者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所说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过程的组成部分。如果中国试图引入乃至创造自己的法治指数,就首先要对其“母体”保持批判反思的能力。 一 世界法治指数的演进 所谓法治指数,是用一套由诸多指标所构成的评估体系,以量化的形式判断和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法治状况的技术手段。这种法治指数依托于一套科学、完整的评估指标系统,表现为一系列的量化数据以及围绕这些数据形成的分析、评价和排名。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表现法治状况的形式具有科学主义的外观,它部分来自于经济学界对经济发展进行数据跟踪和评估的实践,②受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指标运动的影响,③希望在法治领域找到化约种种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公约数”,乃至绘制出一幅数字化的世界法律地图。 但应当看到的是,法治指数既不同于GDP等经济指标,也与其它类型的社会指标有所不同。它所凝聚的是某种特定的法治理念,因而是以特定的视角去截取高度复杂社会的一个断片进行观察。因此,法治指数是否能像致力于这一事业的学者所声称的那样,具有绝对的客观性、中立性,要取决于我们对这些学者所采纳的法治理念和标准的观察和反思。从这一点来看,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法律与发展运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 (一)世界法治指数的早期实践 从一开始,法治指数便与著名的“法律与发展运动”结下不解之缘,④而这一运动的实质恰恰是美国向拉美和北非等发展中国家进行法律输出的活动。⑤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美国律师协会、美国国际法学会以及国际法律中心等机构,和来自哈佛、耶鲁、斯坦福和威斯康星等大学的学者奔赴拉美和北非进行法律援助和输出美式法律教育。这些学者的专业背景是比较法学者、第三世界法专家和法人类学家以及部分来自于政治学、历史学等其它学科的专业人士,数量不过50人。⑥尽管这场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却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其中有些部分至今仍发挥着作用。⑦ 197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得到国际开发署的专项拨款,从事“法律与发展”问题研究,他们将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欧洲大陆和拉丁美洲国家,历经5年时间,完成了这一项目。1979年,梅里曼、克拉克与弗里德曼等人出版了《大陆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法律与社会变化》一书。⑧在这本书中,他们首次采取了对法律制度进行定量描述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倡导“定量比较法”。⑨ 所谓定量比较法,是与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法相对的一个概念。梅里曼等人认为,传统比较法一向是定性研究,是“对法律规范的实体内容、法律学说和法律概念的比较”,⑩而定量比较法则是在对法律制度进行定量描述的基础上,对不同法域的法律制度以及同一法域不同时期的法律制度进行比较。因此,这种定量比较兼具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的内容。为此,他们选取了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意大利、秘鲁和西班牙这六个国家作为观察样本,并建立了一套法律制度分析结构。这一结构由立法、行政、司法、私法行为、法律执行、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六个范畴组成,在每个范畴中围绕机构、工作人员、程序和消耗资源四个维度进行评估。通过这种评估机制,梅里曼等学者希望检验他们所提出的四点假设:(1)社会变化时时发生,社会变化可用社会指标加以测量;(2)外部法律文化调整社会变化释放出的力量,导致它们趋近或远离法律制度;(3)内部法律文化影响着法律制度接受社会变化带来影响的方式;(4)由法律文化所认同的社会变化将导致法律制度的变化。(11) 然而,尽管几位学者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从事数据的搜集整理以及指标体系的建构,并运用内部法律文化与外部法律文化的互动(12)来阐释搜集到的大量数据,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并未如预期的那样产生广泛的社会反响,这一法治评估的早期实践很快随着“法律与发展”运动的式微而偃旗息鼓,(13)主导该研究的几位学者也陆续将兴趣转移到了其它方面。 (二)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数(WGI) 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第二轮法律与发展运动的兴起,(14)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将视野投入到了“法治”上面,以至于这场全新的法律与发展浪潮又被称为法治运动。(15)1998年,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托马斯·卡罗特斯(Thomas Carothers)在《外交》杂志发表文章指出,在国际政策领域,一股重视并加强法治的趋势正在世界各国兴起。(16)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与民主、人权乃至发展这些词汇相比,法治显得更加吸引人,更能够化解分歧,取得共识,也相对容易嵌入各种迥然不同的社会语境。于是一时之间,法治成为西方政策制定者为转型国家开具的“仙丹妙药”。(17)据卡罗特斯观察,这场法治运动沿着三个方向的改革展开:第一种改革集中于法律本身,包括改革法律或整个法典,祛除特定内容的条款,包括金融、税务、知识产权等经济层面的法律和刑法、诉讼法等保障人权方面的法律;第二种改革旨在加强与法律相关的制度,使其更加有竞争力、有效性和可归责性,包括对法官,警察、检察官等法律职业进行培训等;第三种改革则以强化政府守法作为深层目标,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推动司法独立。(18)为了寻找将法治嵌入各国政治、经济决策的最佳途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世界贸易组织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法治”政策向世界各国输出的中介和中心。(19)而在这一背景下,一种全新的法治指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世界银行逐渐开始关注“治理”(governance)问题,从1996年开始,来自世界银行的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mann)等三位学者提出,应当在整合来自国际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各种指标的基础上,发展一套能够有效评估世界各国治理状况的综合指数。(20)这一综合指数最初由三个基本方面构成,即法治、政府效能与贪污。随着研究深入,它很快变得复杂起来,形成了6个指标序列,分别为(1)“言论与可问责性”,(2)“政治不稳与暴力”,(3)“政府效能”,(4)“规制负担”,(5)“法治”与(6)“腐败”。其中前两个指标用于衡量“政府选举、运行和轮替的过程”,第三、四个指标用于衡量“政府有效制定和执行合理政策的能力”,最后两个指标用于衡量“政府是否尊重公民以及建立管理经济社会活动制度的情况”。考夫曼等人将之概括为“一个国家的政府权威运行所需的传统和制度”,即治理。(21)值得注意的是,与世界银行的职能相匹配,这套指数赋予商业组织的经济需要以相对较高的权重,尤其注意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国进行投资与经营的外部环境问题,其经济色彩显得较为浓厚,与此同时,也成为世界银行发展援助贷款的一种参考指标。 到目前为止,这一世界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ex,WGI)已经取得巨大进展,其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根据较晚近的一份报告表明,(22)该指数已经涵盖并整合了来自于由33个组织所建立的35个数据来源中的441个变量,自1996-2008年几乎连续不断地针对212个国家和地区积累数据,并对它们的治理状况进行评估,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治理“大数据”,而法治始终成为这一指数当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善治这一理念紧紧地绑定在一起,成为世界银行和诸多国际机构对各个转型国家的改革所提出的共同期待。 (三)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WJP) 如果说梅里曼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的“法律制度分析结构”反映了第一次法律发展运动时期的总体面貌,那么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发展出的“世界治理指数”恰恰是第二次法律发展运动思想与实践的结晶。虽然两次法律与发展运动以及它们所催生的两套法治指标(或指数)不论在规模、影响、复杂性等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理念、学术与实践层面的内在联系。更值得注意的是,两次法律与发展运动都不同程度地显露出新自由主义法律全球化的某些基本面相,(23)他们将法治计划与市场、民主计划结合起来,在与市场计划的结合上,突出对私人财产权利、缔约自由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强调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去规制化、贸易自由化和开放资本监管等内容;在与民主计划的结合上,突出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和违宪审查等要求。这些基本面相不仅贯彻到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数和其它政策中,而且在世贸组织的法律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中都得到了明确体现。(24) 然而,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并未取得胜利,其市场计划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分化和引人注目的经济危机,其民主计划给很多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秩序解体。到2000年以后,第二次法律发展运动及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都开始遭遇批评和反思,随着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的到来,这种批评的声浪达到了顶峰,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等经济学家所主张的“能力进路”(25)和提高人的“实质性自由”(26)的经济思想开始逐步占据了国际政策界的主流,按照森的观点,法治不仅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外部工具,更是发展乃至实现全球正义的内在组成部分。(27) 在这一背景下,2006年美国律师协会前主席威廉·纽康姆(William H.Neukom)创立了一个名为世界正义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在微软、通用、福特等跨国公司的基金会提供大笔经济支持的前提下,于2008年发布了一套独立的法治指数。最初这套法治指数设计简单,覆盖国家只有6个,但随着时间推移,其指标复杂程度和覆盖国家数量都有了惊人的增长,由2009年的4大板块,16项因素,覆盖35个国家,扩展到2014年的4个普遍原则,9大主因素,47项子因素,覆盖国家达到99个。(28) 这份法治指数的制定者认为,“法治”包含四个方面的“普遍原则”,它们分别是:(1)政府机构以及个人与私人组织是否依法问责;(2)法律是否明确、公开、稳定与公平;平等适用于所有人,并保护基本权利,包括人身与财产安全;(3)法律制定、执行与司法的过程是否具有可接近性、公正而且高效;(4)司法是否由胜任、独立而遵守伦理的法官、律师或代理人提供,司法工作人员是否人员齐备、资源充足,并反映其所服务的共同体的情况。围绕这四个普遍原则,该指数细化成9个方面的指标,分别为(1)限制政府权力;(2)根除腐败;(3)开放政府;(4)基本权利;(5)秩序与安全;(6)监管执法;(7)民事司法;(8)刑事司法;(9)非正式司法。(29) 与20世纪70年代的“法律制度分析结构”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银行治理指数”相比,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存在着六个方面的突出特点。第一,“法治指数”是由非政府组织独立完成;第二,“法治指数”是第一个完整、明确地以法治为内容的指数;第三,“法治指数”建立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第四,“法治指数”以认知性指标为基础,着重考察的是专家与社会公众对法治运行状况的感知,并将其称为“普通人的视角”,(30)“影响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法治”。(31)第五,“法治指数”试图在彼此冲突的法治观之间寻找中间项。“法治指数”巧妙地将弱法治与强法治的需要交叠、混合,既满足了在策略上推广法治的现实需要,也满足了发达国家民主与人权爱好者的热切愿望;第六,“法治指数”最终绘制出了一幅世界法律地图。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正义工程在2014年发布的“法治指数”报告完全呈现为世界法律地图,而这是桑托斯、推宁等著名比较法学家所热切讨论的一种设想,(32)也是梅里曼等人当年所谓“定量比较法”的一种全新展示。 从这六个突出特点中,我们不难发现,历时40多年的发展演变,法治指数的事业不论在知识、技术还是在权力、心理等层面都取得了大幅的进展和惊人的成就,它正在成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象,对世界各国的法治进程产生影响。 二 对世界法治指数的比较法分析 (一)对法治指数的评价 随着法治指数的知识与技术日趋成熟,它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心和研究。应当如何看待法治指数,以什么样的视角和标准来衡量它,这是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形成了两组针锋相对的意见,而这两种意见又与人们对法律与发展运动的整体看法密切相关。(33) 一种意见继承了梅里曼等人的早期看法,对定量研究抱有乐观态度,认为法治指数是一种促进世界法治发展的有益尝试,反映了对法律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新趋势。(34)法治指数科学、客观、直观且具有可追踪性、可比较性与可分析性,是对传统定性研究的有效补充,特别有利于政策制定者作为决策的参考和依据。而且作为一种比较法的新尝试,虽然与以文化传统为核心的比较法范式有所不同,(35)但它不失为比较法上的一种突破。这一观点一方面得益于政策分析与法经济学在美国法学界的崛起,(36)另一方面也有着更为深远的社会理论基础。(37)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主张,具有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更加有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而他心目中的这种法律类型便是法律科学主义时代的产物,在其背后暗藏着一种特定形式的法律进化观,(38)而韦伯或许未曾料到的是,一种完全以指数形式呈现的法治恰恰是形式合理性法的某种隐喻式表达,在这种数字矩阵背后,能够透露出历次法律与发展运动始终加以贯彻的一些根本信念,包括(1)现代主义的法律进化观;(2)工具主义的法律作用观与(3)发展主义的法律目的观。(39) 但即使在乐观主义者阵营内部,也存在质疑声音。(40)有人认为,包括世界正义工程在内的所有法治指数,在数据的搜集上都很难说具有代表性,这影响了指数的准确度,如世界正义工程仅从目标国家的3个主要城市中进行抽样调查,不可避免地造成扭曲,我们很难想象,仅从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超大城市选取1000名公众,调查他们的意见就足以反映整个中国的法治面貌。类似问题也存在于世行的治理指数当中,将来自各个渠道,统计口径截然不同的数据整合进同一个指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避免扭曲作用,这本身就是问题。(41)也有的学者指出,随着法治指标逐步由客观指标向认知性指标过渡,法治指数越来越忽视法律制度在法治中的作用,而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反映的“民意”又具有流动性,这使法治指数很难确保客观。还有一种批评意见是,多数赞成并使用法治指数的人都将其视为一项制成品,而并不十分在意“产品”的制作流程,对其中观点的分歧与妥协、利益的角逐与博弈更缺乏了解,毕竟任何炮制法治指数的组织都是由不同想法和观念的人所组成,以世界银行为例,有研究表明,世行不同部门所采纳的法治理念与标准存在很大差异。(42)更值得重视的批评意见是,与其它类型的法学研究相比,法治指数与政策制定关系密切,而政策恰恰是容易直接卷入权力与利益纷争的领域,当法治指数成为政策制定的一种参考或工具时,难免会为政策制定者的观念、利益所左右,难以维持客观。 而悲观主义者的意见来自于另外一个阵营,他们对法治指数的批评更加激进。一种意见认为,像世行治理指数这样的指数充分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主张,其对法治的要求更多体现了跨国公司的商业利益,(43)尽管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标准在此基础上有所调整,但并未从根本上扭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方向。另外一种意见则指出,法治指数的技术与理念大多源自美国,与法律与发展运动一样具有鲜明的美国风格,(44)因而成为美国法全球化的组成部分。而从现代世界体系的视角来看,法治指数是核心区国家向半边缘与边缘区国家输出“标准”,继而固化既有世界格局的一种技术手段,当核心区国家认为开放市场、去除金融管制、提高知识产权标准对核心区更为有利时,就更愿意将它“加密”成为一套看似科学、中立的指标,继而向广大边缘区国家推销。(45)而如果按照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观点,(46)认为全球化所形成的是一种帝国体系的话,那么包括法治指数在内的各种指数,都不过是帝国内部的一种数目字管理。以上批评虽然有些危言耸听,甚至有阴谋论之嫌,但恐怕并非空穴来风。 (二)法治指数是一幅世界法律地图 在此,笔者既不准备卷入关于法治指数的方法之争,也不准备陷入意识形态分歧,而是试图从比较法来重新审视和定位法治指数。比较法关于世界法律地图的设想和反思以及对法律移植现象持续不断的研究,为我们分析和评价法治指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角度。在笔者看来,法治指数是全球化时代绘制世界法律地图的一种新构想,也是全球法律散播的一种新形式。 法治指数是全球化时代绘制世界法律地图的一种新构想。葡萄牙著名法学家桑托斯认为,“法律是地图”,(47)而绘制一幅完美的世界法律地图几乎是所有比较法学家的梦想,也是其工作的重心。(48)迄今为止,比较法学界大体形成了三种绘制世界法律地图的思路,分别是法系地图、国别地图与数字地图。法系地图是按照历史传统与源流关系,将世界法律分为若干大的“样式”,如英美法、大陆法等;(49)国别地图则按照民族国家来区分。第三种模式是依照特定标准,将汇集的数据、指数转化成为关于治安、腐败、权利保障等方面的世界法律地图。前两种法律地图是传统比较法范式的常用方式,而数字法律地图则是世界正义工程等法治指数的发布和研究者所采取的新方式。与前两种法律地图相比,数字法律地图显得更加直观、动态,具有更强烈的诱导性。 但不论何种法律地图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简化、歪曲、引导、暗示和传播五个特性。 第一,法律地图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化,而绝非事实本身,再完美的地图都不足以展现所描绘对象的全貌,而是要受制于绘图者所采取的标准、视角和方法,其所要实现的功能是特定的。以数字法律地图为例,其绘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绘图者所采取的法治标准以及他预期使用地图的人所需要达到的目的,根据世行治理指数所绘制的法治地图,与正义工程的指数所绘制的法治地图肯定会有所不同。 第二,法律地图是对现实的一种歪曲。正如桑托斯所说:“地图是对现实规则化的歪曲,是对地区的有组织的歪曲解读,该解读创造对应物的可信虚像”, (50)而在他看来,法律地图通过三种机制来歪曲现实:比例尺、投影法和象征符号。(51)一种地图如何展现,一方面取决于比例尺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按照何种投影法将错综复杂的事实“拉平”,更重要的是,任何法律地图都会以特定的象征符号展现出关于法律的隐喻。从这个视角看来,法系地图运用的是小比例尺,采取的是法系为核心的投影法,最后以文化的象征符号展示西方压倒东方的隐喻;国别地图运用的是中比例尺,采取的是国家为核心的投影法,最后以政治和经济为符号展示强国优于弱国的隐喻;那么,数字法律地图则是大比例尺,采取的是以法治效果为核心的投影法,最后以数据等象征符号展示善治与恶治、良法与恶法的隐喻。而不论采取哪种比例尺、投影法或象征符号,都不可避免地排斥、拉平与遮盖其它可能类型的法律地图。 第三,法律地图具有引导功能。地图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需要它来指引道路,法系地图可以提供特定法域中法律样式的粗略描绘,国别地图可以提供民族国家法律主要内容的索引,而数字法律地图及其背后的指标与数据也发挥着类似的引导作用,例如世行的治理指数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将引导发展援助的资金流向,跨国公司的投资方向,乃至对很多国家法治改革的趋向也将产生影响。 第四,法律地图兼具权力和心理的双重意义,具有心理暗示作用。从权力层面来看,它形成一种影响力模式,为地图使用者提供指引,而从心理层面来看,地图则是“关于事物排列的心理构想”,(52)当建立在认知性指标的基础上时,世界法律地图尤其展现出一种心理主义面貌。从人类学的调查经验来看,任何所谓的调查本身都是一种参与,是调查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心理互相作用,这种“心理构想”会进一步衍生出不易察觉的心理暗示,进而影响人们的主观判断。 第五,法律地图本身就是一种传播。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克卢汉曾经说:“媒介即讯息”,(53)而讯息本身就是传播。毫无疑问的是,地图也是诸多媒介中的一种,是数字化了的讯息传播形式,一旦一幅数字法律地图出现,它所承载的信息,如阿富汗的混乱、俄罗斯的腐败、中国的权力集中,会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远非大学教科书所能比拟,它会强烈地将某种固定的法治印象打入人的思维,形成人们对遥远国度法治状况的理解(或曲解)。更值得一提的是,数字法律地图制作技术本身也会转化成为讯息,从而在传播中得到复制。人们会模仿这种技术,应用到各个方面,从而实现指数的再生。(54) (三)世界法治指数是一种法律散播 我们还可以从比较法的动力学部分,即法律移植理论出发,来进一步分析世界法治指数。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梅里曼等学者从事法律与发展运动的时期,便有学者指出,这种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法律援助活动,会因建立在对法律移植理论粗浅的理解上而导致失败。(55)当时,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将美式的法律和法律教育输送到拉美国家,就自然能够收获民主改革、经济进步与社会发展,殊不知法律与社会发展之间远非线性的关系,其中暗藏着极其复杂的动力机制,(56)单纯地将某种样式的法律制度输入目标国家,只能接连不断地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例如,在第一次法律与发展运动中,很多项目试图通过美式法律教育来培育发展中国家本土的法律精英,却发现受教育的本土精英以此作为符号资本,转而以本土化的游戏规则继续攫取利益,并从事本土政治的“宫廷斗争”。(57)在这些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法律移植理论取得了长足进步。(58)但令人深感惊讶的是,法律移植理论的洞见并未给第二次法律与发展运动中的法律传教士们带来启示,旧的观念以新的计划继续推行,而法治指数成为新计划中新颖的组成部分。 推宁认为,在法律全球化时代,已经不能用简单的法律移植模式来解释复杂的法律传播现象,一种更具多样性的“法律散播”模式或许更有解释力。他主张,“法律散播”在12个方面与传统法律移植模式不同,(59)其中有5项内容尤其具有启发意义:(1)法律散播来源的多样性;(2)法律散播的跨层次性;(3)散播路径的多样性;(4)对法律散播解释的多角度性;(5)法律散播效果的长期性。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世界法治指数都是一种新的法律散播形式。 第一,从法律进口的来源来讲,法律散播是多样的,它不仅包括法律的规则和制度,而且包括思想观念、技术标准、通行做法,乃至于包括与法律并不直接相关,但携带有法律因素的其它形式,如影视作品、网络信息等。世界法治指数虽然并不是一种法律规则或制度,却是一套法律技术标准,是一种在国际组织中被广泛使用的通行做法,其背后暗含着法治的思想观念,且作用于不确定的国家和地区,因此毫无疑问的是,它是法律散播的一种形式。与传统意义上的法律移植不同,它并不寻求直接或强制性地向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输出法律,而是依靠影响力来发挥类似的作用,一旦目标国家感受到法治指数及其排名所带来的压力,便难免出于国际声誉、招商引资的需要、改善本国法治状况等各种考虑接受法治指数中的法治标准。高鸿钧教授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法律移植存在经济、政治和人类共同价值范式并存的现象,(60)而法治指数则横跨这三种范式,既有经济考量,也有政治内涵,而且以人类共同价值来自我期许。更值得注意的是,法治指数暗含着超越这三种范式之外的其它范式,即科学范式,它以科学技术的方式实现全球散播。 第二,从法律散播的层次来讲,法治指数不仅在国家这一层面进行散播,而是在全球的、国际的、区域性的、跨国的、社区间的多重法律空间(61)中进行传播。传统意义上的法律移植理论认为,法律在以国家为中心的法律空间中迁移,是一场法律由输出国到输入国的单向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现实。从法治指数的散播来看,它在以上提及的所有法律空间中穿行,既有全球或国际层面的世界法治指数,也有国家层面的法治指数,而且还有各种纷繁复杂的地方性法治指数。地方性法治指数不必通过国家中介,可直接从世界法治指数中寻找榜样,世界法治指数可从各种地方性的或国际性的商业团体、非政府组织中寻找数据和智力支持,多重法律空间对法治指数有各种利用和解读,彼此嵌套,形成“居间法治”(62)的复杂图景。桑托斯认为,目前的法律全球化过程表现为“全球化的地方主义”与“地方化的全球主义”之间的互动,(63)世界法治指数的散播也体现了这一点。世界法治指数最初来自于美国的地方性实践,其后通过两次法律与发展运动,借助世界银行、世界正义工程等全球层面的行动者上升成为全球性的法律实践,继而进入世界各个国家及其地方的各种法治指数,印证了这一法律散播过程。但另一方面,桑托斯仍批评这一过程是体现霸权共识(64)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正如法治指数那样,是从核心区国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广的变相手段。 第三,从法律散播的路径来讲,法治指数的散播路径是多样的。它体现在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民族国家政府的法治评估活动中,国际公民社会的宣言和调查中,跨国公司的投资分析和风险测评中,国际移民和旅行者的交流和行动中,地方政府和团体促进法治和改善本地经济社会环境的各种政策中,也体现在学术共同体对法治指数的制作、利用、研究乃至批评中。当然,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日益丰富和全球联通,法治指数会以种种形式跃入公众的视野,正如全球大学排名已经成为全世界公众所熟悉和讨论的议题一样,它会成为弗里德曼所说的外部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对法律职业群体中的内部法律文化带来冲击和影响。(65) 第四,从对法律散播的解释来讲,对法治指数的解释必然是多角度的,推宁认为,在法律散播过程中,会形成技术视角、语境型/表达型视角与意识形态视角三种解释类型。(66)从技术视角来看,法律大体是彼此不相关联的技术产品,作为法律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工具可被进口,法治指数完全是一种中性的、技术性的法律分析工具,既可以成为评估世界法治发展状况的手段,也可以被任何一个国家拿来,成为掌握本国或各个地区法治发展的技术标准。从语境/表达型视角来看,法治指数是刺激、影响特定法律系统的一种因素,而法律系统如何认识和改变,并不取决于法治指数,而是取决于法律系统本身。例如,2014年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在安全方面给予中国很高评价,对权利保障方面却评价极低,但这并不能直接使中国的法律改革沿着法治指数制定者所预期的方向发展,而是取决于中国法律系统自身的特点和对相关信息的理解。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跨国公司对法治指数的解读上,作为法治指数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腐败指数一直因为能够标识出境外投资者所需支付的额外成本而备受商业人士关心。但从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看,事实未必是政府越清廉,反腐败指数越高就越有利于投资。相反在某种条件下,满足少数腐败官员的利益换取投资便利所需支付的成本可能要小于在一个廉洁政府治下所需支付的成本。而从意识形态视角来看,尽管我们不必在意各种情绪化的批判,但从两次法律与发展运动及其所孕育的三套法治指数(或指标)来看,它们都与发展、全球治理、全球正义这些充满意识形态内涵的概念纠缠在一起,而这些概念都不约而同地有着特定的来源和特定的内容。例如,据楚贝克的研究,在第一次法律与发展运动中,各种法律援助项目的背后都暗含着“自由法条主义”的意识形态,(67)根据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的研究,在第二次法律与发展运动中方兴未艾的“全球治理”也有着美国源头;(68)而如果深入分析晚近逐步引起国际政策界关注的新宠——全球正义问题,我们不难发现阿玛蒂亚·森对罗尔斯和内格尔理论的改造,使其以非制度主义的和渐进改良的形式与国际发展政策兼容。(69)在这些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下,我们很难断定法治指数是一场全球法治的盛宴。 第五,从法律散播的效果来讲,法治指数的效果具有长期性。总体来讲,任何一种法律散播皆非轻而易举,其效果都是逐步显露的,其效果的发挥不仅取决于法律散播对象自身的特质,也取决于散播者、散播渠道和散播方式的选择。有的时候,一种法律散播看似失败,但很可能为将来的成功埋下伏笔,法治指数或许也属于这种情况。20世纪70年代梅里曼等人的定量实践在当时几乎没有取得什么引人注目的成果,却在二三十年后以世界法治指数的方式异军突起,这不能不说超出了梅里曼等人的预期。正像当年第一次法律与发展运动那样,早期的参与者们很难设想,日后法律与发展运动会改头换面,以更大的规模,更猛烈的方式向全球推行。美国法学家邓肯·肯尼迪(Duncan Kennedy)指出,自1850—2000年这150年中,先后有以德国法为代表的古典法律形式,法国法为代表的社会法形式与以美国法为代表的新公法形式主义结合政策分析,主宰着法律与法律思想全球化的进程,(70)其中美国法的优势地位于20世纪1970年代奠定,到1990年代达到顶峰,我们可以看到,法治指数及其法律思想折射出美国的法律政策分析的影子,而这种政策分析又是远源于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思想。可以想见,随着法治指数的全球散播,一种偏向于政策分析的法律研究模式会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辟出法律市场,而在这一法律市场当中,会有越来越多的法律专家进入政策领域,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政策界人士进入法律空间,双方会按照各自的设想为法治发展设定新议程,从而为法治带来更多可能性。 三 法治指数在中国 (一)中国的法治指数实践 任何一个重视法律的国家都会采取各种方式评估本国的法治发展状况,而采取何种方式,既要考虑到本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做法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已经成为我国的治国方略,而对立法、执法与司法的情况进行总体把握和评估成为重要任务。 在这一背景下,法治评估与法治指数作为一种有益实践被引入中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加入WTO,中国政府仅用两、三年的时间,就在中央层面清理法规多达2000多件,废除了500多件不合WTO规则的法律法规,加上地方政府清理的法律文件,共清理法律文件多达90000多件。(71)这种法律法规的清理活动无疑与法治评估相伴随。自加入WTO之后,WTO的贸易政策评审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法治评估的发展。近年来,在官方层面,立法评估、司法评估以及其它相关评估活动陆续展开,(72)而平安指数、法治指数等相关指数也开始陆续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一些地区陆续开展了法治指数的探索,其中香港法治指数与余杭法治指数引起了社会反响。(73)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全国性的法治评估活动也已经启动,其中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法学会以发布年度报告的方式,将法治评估的事业推向了新的层面。(74)迄今为止,尽管尚未出现一套覆盖全国的综合法治指数,但相关的学术研究和争论早已在法学界展开。总体而言,近十年的法治评估与法治指数的实践与研究呈现出五个特点和趋势。第一,从零散的法治评估向系统的法治评估转变;第二,从客观数据的搜集和整理向围绕认知性指标的调查转变;第三,法治评估日益向法治指数转变;第四,从地方性法治指数向全国性法治指数转变;第五,从政府主导的法治评估向学术界主导的法治评估转变。 在这一过程中,不论是梅里曼等人的早期实践,还是世行治理指数与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在中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借鉴,这种借鉴不仅包括形式和框架的引入,还包括理念与意识的吸收。以人民大学2007年的《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为例,这套指标体系建立的初衷,搜集的数据与设计的指标体系都与梅里曼等人的法律制度分析结构相似,暗含以发展为理念的法律进化观,具有功能导向的特点,注重制度结构,以客观数据为主体内容。(75)而余杭指数、法治广东以及法治湖南等地方性实践也受到了世行治理指数与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的影响,(76)这些指数往往与“社会综合治理”的理念结合起来,将法治视为地方政府治理社会诸多手段的组成部分。近两年,制定一套全国性法治指数的构想开始成为学术热点,吸引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法律专家,并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各种学术资助,而世界法治指数因其新颖性和完整性成为了设计中国法治指数的原始样板,其理念与技术潜移默化地进入了中国的相关法律实践。 但值得一提的是,世界法治指数在美国学术界所产生的影响似乎并不如它在中国的反响那么热烈,而考虑到各种世界法治指数都不同程度地有着美国渊源,这种反差就显得尤其引人注目。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有以下三点原因。首先,两国的国情和法治状况不同,在美国,司法审查客观上起到了评估法治状况的功能,而在中国,对于法治发展状况的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意愿,在两种不同的制度结构中,法治的定位和功能显露出差异;其次,在美国,法治与民主、权利等价值理念充分结合,是公民自治的组成部分,故此将法治视为社会治理工具的观点并不居主流,而在中国,法治的工具观仍占有相当市场,为法治指数的兴盛提供了空间;最后,这种反差也说明,在法治指数全球散播的过程中,散播的法律现象未必总是原产地中最好的或者最成功的事物,而往往是特定群体最“需要”的事物——例如,对很多法治指数的积极推动者来说,与其说其理想在于推进法治,不如说是为各种治理机构提供一套新的数目字管理工具,而这一事业尤其受到智库型学者的青睐。 (二)对中国法治指数的思考 2014年5月2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以“法治评估:普遍性与特殊性”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上,很多中外学者都表达出推动建立中国法治指数的愿望。(77)与此同时,一些反思的声音也开始出现。 苏力教授认为,法治指数希望实现的目标虽然十分美好,但方法论存在问题。他指出,法治指数的数据搜集将是对事实的简化甚至歪曲,而获得的信息往往面临着彼此冲突的解释空间,“天堂虽美,但道路不通”。而钱弘道、蒋立山等教授不约而同地提醒法治指数的实践者,要对其理论基础进行深度反思。(78)此外,更多学者对法治指数的独立性与科学性表达了关切。围绕这些反思,结合本文对世界法治指数和法律与发展运动的分析,笔者从比较法的角度,略陈管见如下。 种种事实表明,法治指数是一种舶来品,是全球法律散播中的一种现象,它所携带的法治理念有着特殊的来源,它所采取的方法和技术有着特殊的导向,而这些来源与导向不可避免与世界体系的格局和现状联系在一起。从这一角度看来,目前在中国逐步升温的法治指数热潮也是全球法律散播的组成部分,这一散播过程对中国来说既有好的方面,也可能存在坏的作用。好的方面是,它将有助于中国了解自身的法治状况,尤其是了解存在的缺陷,以利于未来的法治改革。而坏的作用是,法治指数方法暗含的缺陷乃至偏见可能会被不加分别地被引入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全面、公允甚至带有批判眼光地审视法治指数,显得非常必要。必须指出的是,法治指数往往将经济、社会条件完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拉到同一个水平面进行比较,衡量其优劣,其潜在问题绝非不值一提。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瓦利斯与温格斯特便指出,在当今世界只有不到24个国家进入开放准入秩序的阶段,而绝大多数国家仍停留在限制准入秩序的时期,(79)其背后的原因绝非进步与落后可以道尽,而对于这些至关重要的原因进行挖掘和理解是法治指数无法办到的,它只能显示出一幅不由分说且无法解释的排名与图表。可以想见,当法治指数被用于衡量中国各个地区的法治状况时,也会出现类似的抹除效果,从而产生误导作用。 从两次法律与发展运动和三套世界法治指数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法治指数与政策分析关系密切,而政策分析由往往牵涉到官僚系统对全社会施加的数目字管理。因此,法治指数的制作、分析与研究并非单纯的学术活动,它介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是学术与政治的混血儿。这便不可避免地使法治指数受到政治运作的影响,以至于带来独立性不足、公信力缺失,甚至是结果先行的种种病象。而随着法治指数实践引入中国,考虑到我国政府在社会各个方面扮演的积极角色,相关问题不仅不会缩小,反而会放大。由于政府掌握着外界所无法比拟的巨量信息,这使中国的法治指数会比世界法治指数更加依赖于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在这一背景下,确保法治指数的独立性和学术性殊非易事。 正如很多对世界法治指数保持冷静观察的比较法学家们所指出的那样,法律散播绝非一项利益无涉的事情,与此相反,它涉及国内外“法律企业家”们的利益和前途。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指数也可能是一门生意,从事每个领域的法律实践者,都希望在世界法治指数的“菜单”中找到符合自己口味的东西。以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为例,在其指标体系中,“非正式司法”尤其引人注目,这项指标被认为是考虑非西方国家法治特殊性的一个标志。但根据比较法学者德兹莱和加思的研究,与“非正式司法”相关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恰恰是美国律师在抢占欧洲仲裁市场时的发明创造,它在美国法律市场经历了出口转内销,进而包装再出口的戏剧性过程。与其说法治指数的这项指标体现了对非西方国家法治特殊性的关照,不如说体现了以“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为生的世界法律专家们的利益偏好。(80) 尽管面临着以上提及的各种批评和反思,法治指数的事业在中国已经上路,并且如火如荼地展开。对于苏力教授所表达的那种忧虑,法治指数的实践者们可能会用鲁迅的名言来做出回应:“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81)但随着这一事业的深入,或许另外一个问题会困扰我们——道路总是有的,但我们期许的天堂却并非同一个。但愿笔者的担忧纯属多余。 ①占红沣、李蕾:《初论构建中国的民主、法治指数》,《法律科学》2010年第2期;钱弘道等:《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李蕾:《法治的量化分析——法治指数衡量体系全球经验与中国应用》,《时代法学》2012年第2期。 ②秦麟征:《关于美国的社会指标运动》,《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③屈茂辉、匡凯:《社会指标运动中法治评价的演进》,《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3期。 ④法律与发展运动具有注重实证研究与调查的知识风格,参见姚建宗著:《美国法律与发展研究运动述评》,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3-64页。 ⑤参见[美]戴维·杜鲁贝克:《论当代美国的法律与发展运动》(上、下),王力威译,《比较法研究》1990年第2、3期。杜鲁贝克今天一般被译为楚贝克——作者注。 ⑥高鸿钧:《美国法全球化:典型例证与法理反思》,《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姚建宗:《美国法律与发展研究运动述评》,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⑦B.Tamanaha,"The Lessons of Law-and-Development Studies",89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483-485(1995). ⑧J.H.Merryman,D.S.Clark and L.M.Friedman,Law and Social Change in Mediterranea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A Handbook of Legal and Social Indicators for Comparative Study (Stanford:Stanford Law School,1979). ⑨[美]J.H.梅里曼等:《“法律与发展研究”的特性》,俗僧译,《比较法研究》1990年第2期。 ⑩[美]J.H.梅里曼等:《“法律与发展研究”的特性》,俗僧译,《比较法研究》1990年第2期,第58页。 (11)[美]J.H.梅里曼等:《“法律与发展研究”的特性》,俗僧译,《比较法研究》1990年第2期,第59页。 (12)所谓外部法律文化,是指在特定社会法律制度的外部担任职务的人对法律采取的观念;而内部法律文化是指由律师、法官等法律制度的“局内人”对法律采取的观念。参见[美]J.H.梅里曼等:《“法律与发展研究”的特性》,俗僧译,《比较法研究》1990年第2期,第60页。 (13)戴维·楚贝克认为,第一次法律与发展运动的失败归因于其“四大支柱”的崩解,这四个支柱分别是:(1)文化改革和移植战略;(2)基于简单理论预设的改革措施;(3)对通过经济实现民主和人权的信念;(4)强调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参见David M.Trubek:"The ‘Rule of Law'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Past,Present and Future",in D.M.Trubek,A.Santos(eds.),The New Law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Critical Appraisa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78. (14)关于第二次法律与发展运动,参见高鸿钧:《美国法全球化:典型例证与法理反思》,《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第6-9页。 (15)鲁楠:《法律全球化视野下的法治运动》,《文化纵横》2011年第3期。 (16)Thomas Carothers,"The Rule of Law Revival",77 Foreign Affairs.95-106(1998). (17)Ibid,p.98. (18)Thomas Carothers,"The Rule of Law Revival",99-100.更具体的情况参见高鸿钧:《美国法全球化:典型例证与法理反思》,《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第7-9页。 (19)David M.Trubek,"The ‘Rule of Law'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Past,Present and Future",p.82. (20)D.Kaufmann,A.Kraay and P.Zoido-Lobaton,"Aggregating Governance Indicators",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195,1-4(1999). (21)D.Kaufmann,A.Kraay and P.Zoido-Lobaton,"Governance Matters",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196,1(1999). (22)D.Kaufmann,A.Kraay and M.Mastruzzi,"Governance Matters VIII:Aggregate and Individual Governance Indicators,1996-2008",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4978,7(2009). (23)朱景文:《法律全球化:法理基础与社会内容》,《法制现代化研究》2000年第1期;於兴中:《自由主义法律价值与法律全球化》,《清华法学》2002年第1期。 (24)鲁楠:《全球化时代重新理解WTO》,载高鸿钧、鲁楠编:《清华法治论衡》(第20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余盛峰:《从GATT到WTO:全球化与法律秩序变革》,载高鸿钧、鲁楠编:《清华法治论衡》(第20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6页;[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全球化及其不满》,夏业良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 (25)P.Boettke ahd J.R.Subrick,"Rule of Law,Development and Human Capabilities",10 Supreme Court Economic Review,109-126(2003). (26)参见[印]阿玛蒂亚·森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7)[印]阿玛蒂亚·森:《全球正义》,高鸿钧译,载[美]詹姆斯·赫克曼等编:《全球视野下的法治》,高鸿钧、鲁楠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6-73页。 (28)WJP: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Rule of Law Index 2014,http://worldjusticeproject.org/rule-of-law-index,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6月10日。 (29)WJP: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Rule of Law Index 2014,p.8. (30)WJP: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Rule of Law Index 2014,p.5. (31)WJP: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Rule of Law Index 2010,http://worldjusticeproject.org/publication/rule-law-index-reports/rule-law-index-2010-report,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6月12日。 (32)[葡]博文托·迪·苏萨·桑托斯著:《迈向新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2-538页;[英]威廉·退宁著:《全球化和法律理论》,钱向阳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221页。 (33)K.A.Davis and M.J.Trebilcock,"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Development:Optimists versus Skeptics",56/4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895-946(2008). (34)钱弘道等:《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第141-143页。 (35)高鸿钧:《比较法研究的反思:当代挑战与范式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鲁楠:《全球化时代比较法的优势与缺陷》,《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 (36)沈明:《法律经济学——英美法系的理论、实践与影响》,载高鸿钧等主编:《英美法原论》(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3-1329页。 (37)L.Friedman,"Legal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4 Law & Society Review,29(1969); D.Trubek,"Toward a Social Theory of Law:An Essay on the Study of Law and Development",82 Yale Law Journal,1(1972);D.Trubek,"Max Weber on Law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Wisconsin Law Review,720(1972). (38)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9)J.H.Merryman,"Law and Social Change:On the Origins,Style,Decline & Revival of the Law and Development",25/3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457-491(1977). (40)D.Kaufmann,A.Kray and M.Mastruzzi,"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Answering the Critics",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149,3-26(2007). (41)M.J.Kurtz and A.Schrank,"Growth and Governance:Models,Measures and Mechanisms",538-554. (42)A.Santos,"The World Bank Uses of the 'Rule of Law' Promis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in D.M.Trubek and A.Santos(eds).The New Law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Critical Appraisal,pp.256-266. (43)Tor Krever,"Quantifying Rule of Law:Legal Indicator Project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Neoliberal Common Sense",34/1 The Third World Quarterly,131-150(2013). (44)T.M.Frank:"The New Development:Can American Law and Legal Institutions Help Developing Countries?",Wisconsin Law Review,767-801(1972). (45)鲁楠:《匿名的商人法——全球化时代法律移植的新动向》,载高鸿钧编:《清华法治论衡》(第14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176页。 (46)参见[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著:《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7)[葡]博文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5页。 (48)[英]威廉·退宁:《全球化和法律理论》,钱向阳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 (49)[德]K.茨威格特、H.克茨著:《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 (50)[葡]博文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5页; (51)[葡]博文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7页。 (52)[英]威廉·退宁:《全球化和法律理论》,钱向阳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53)[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3页。 (54)受到指数的影响,从事比较法研究的范例,参见[美]刘岱伟、米拉·沃斯蒂戈:《全球宪政主义:意识形态与演变》,徐宵飞译,载高鸿钧编:《清华法治论衡》(第17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3-370页;[美]丹尼尔·伯克维茨等:《全球视野下的法律移植效应》,魏磊杰、武雨佳译,载高鸿钧、鲁楠编:《清华法治论衡》(第20辑),第385-431页;[美]卡塔琳娜·皮斯托等:《社会规范、法治和性别现实:论支配性法治范式的限度》,张文龙译,载[美]詹姆斯·赫克曼等编:《全球视野下的法治》,第257-296页。 (55)[美]戴维·杜鲁贝克:《论当代美国的法律与发展运动(上)》,第48-49页。 (56)Scott Newton,"The Dialects of Law and Development",in D.M.Trubek and A.Santos(eds).The New Law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Critical Appraisal,74-202. (57)[美]Y.得兹莱,B.加思:《法律与法律制度的输入与输出:国家“宫廷斗争”中的国际战略》,鲁楠译,载[意]D.奈尔肯,J.菲斯特:《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高鸿钧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7-324页。 (58)高鸿钧:《法律移植:隐喻、范式与全球化时代的新趋向》,《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59)[美]威廉·特文宁:《法律播散:一个全球的视角》,魏磊杰译,载高鸿钧编:《清华法治论衡》(第14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60)高鸿钧:《法律移植:隐喻、范式与全球化时代的新趋向》,第128-129页。 (61)[英]威廉·推宁:《全球化与比较法》,吴大伟译,载[英]埃辛·奥赫绪、[意]戴维·奈尔肯:《比较法新论》,马剑银、鲁楠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 (62)[葡]博文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63)[葡]博文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1-222页。 (64)[葡]博文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7页。桑托斯认为,当今世界存在四个霸权共识,分别是(1)新自由主义经济共识;(2)弱国家共识;(3)新自由主义民主共识;(4)法治与司法改革共识。 (65)[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论法律发展》,陈鲁宁、甘德怀译,《法制现代化研究》1997年第3卷,第26-28页。 (66)[美]威廉·特文宁:《法律播散:一个全球的视角》,魏磊杰译,载高鸿钧编:《清华法治论衡》(第14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8-52页。 (67)D.M.Trubek and M.Galanter,"Scholars in Self-estrangement:Some Reflections on the Crisis in Law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4 Wisconsin Law Review,1062-1102(1974). (68)[美]戴维·肯尼迪:《全球治理之谜(上)》,刘洋译,载高鸿钧编:《清华法治论衡》(第14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页;David Kennedy:"The Myth of Global Governance",34 Ohio North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827-860(2008). (69)Amartya Sen,The Idea of Justice,(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2009),pp.52-74. (70)[美]邓肯·肯尼迪:《法律与法律思想的三次全球化:1850-2000》,高鸿钧译,载高鸿钧编:《清华法治论衡》(第1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17页。 (71)鲁楠、高鸿钧:《中国与WTO:全球化视野的回顾与展望》,《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7页。 (72)钱弘道等:《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第145-149页。 (73)参见戴耀庭:《香港的法治指数》,《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6期;钱弘道著:《中国法治指数报告(2007-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74)参见朱景文编:《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目前《中国法律发展报告》已发布到2013年;李林、田禾编:《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这一系列法治发展报告从2004年开始,也已追踪到2013年;中国法学会编:《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2010)》,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 (75)朱景文编:《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6)一些地方性法治指数对世界法治指数的借鉴,参见钱弘道等:《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戢浩飞:《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李蕾:《法治的量化分析——法治指数衡量体系全球经验与中国应用》,《时代法学》2012年第2期;廖奕:《法治如何评估?——以中国地方法治指数为例》,《兰州学刊》2012年第12期。 (77)其它与此相关的呼吁参见季卫东:《以法治指数为鉴》,《财经》2007年第21期。 (78)蒋立山:《中国法治指数的理论设计问题》,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x?id=40858,访问时间:2014年6月10日。 (79)参见[美]道格拉新·C.诺斯等:《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杭行、王亮译,格致出版社2013年版。 (80)Y.Dezalay and B.G.Garth,Dealing in Virtue: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Transnational Legal Ord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pp.33-62. (81)《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0页。标签:法律论文; 比较法论文; 经济指数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政府工程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政府治理论文; 全球化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