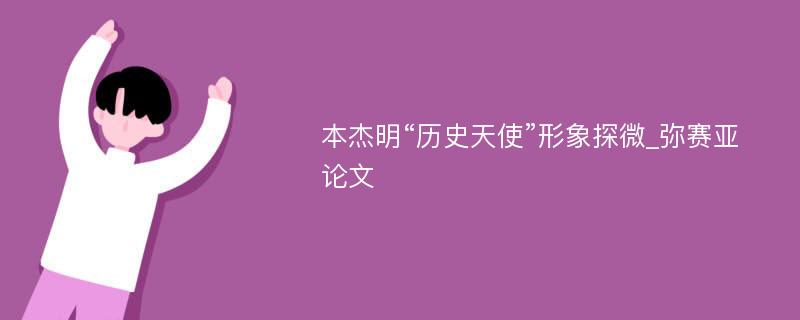
本雅明“历史天使”意象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象论文,天使论文,探微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5)05-0072-08 美国学者沃林在《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一书中认为,“历史天使”“或许是他全部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喻象”[1](P4)。其实,“历史天使”这个意象(喻象)蕴藏着本雅明历史观的全部秘密,诚如他的好友朔勒姆所言:“瓦尔特·本雅明的天才全都集中在这个天使身上。”[2](P261)若继续探问,我们就会发现,本雅明阐说“历史天使”的底据乃是其自出机杼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进而言之,若不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在本雅明那里的独特意味,也就无法解开笼罩在“历史天使”这个辩证意象上的种种谜团。 一、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 本雅明是一位以“历史唯物主义者”自居的思想家,他在生前写就的最后一篇文字《历史哲学论纲》中格外强调了“当下”这一概念,并有意与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区别开来:“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没有“当下”的概念。所谓‘当下’,不是一种过渡,而是时间的停顿和静止。正是这样一个‘当下’的定义,历史唯物者得以书写自己的历史。历史主义给予过去的是一个‘永恒的’形象;而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则是对过去的独特体验。”[3](P48) “历史主义”试图将充满诸多可能性的人类历史抽空成由无数因果联系、前后相续的事件组构的线性发展的历史,这种线性发展的历史观营造了一个无限进步的“历史幻境”,进而将鲜活的“过去”以及转瞬即成“过去”的“当下”风干成通向“历史幻境”途中的某个注定了的环节。这样一来,“过去”与“当下”就变成了自动流淌的物理时间中的某个不能自主的动点,那些为无限进步的“历史幻境”所魅惑的人们也就变成了被注定了的因果链条拖着走的行尸走肉。强调“对过去的独特体验”的本雅明显然不同意这种“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在他看来,“当下”是为个体主动介入与抉择着的某个时刻,个体在这个时刻挣脱了“时间”的裹挟,嵌入了属己的“独特体验”,因而“当下”不再是毫无人文意义的“过渡”环节,那似乎自动流淌的物理时间也在这个时刻出现了“停顿和静止”,并因此而被主动介入与抉择的个体赋予了历史意义。当个体带着这样的“当下观”回溯曾经作为属己的“当下”而存在的“过去”时,那“过去”不再是某个死掉了的“‘永恒的’形象”,毋宁说,它就是嵌入了属己的“独特体验”的活生生的“当下”,正是这样一个个活生生的“当下”,谱成了“历史唯物者”所书写的属己的历史。这种属己的历史,自然不再是“历史主义”者那里被某种所谓的“因果联系”所注定了的历史了。本雅明就此指出:“历史主义为在不同时刻之间建立起了因果联系而自得。然而,没有哪个具有因果关系的事件是因此而具有历史意义的。它后来之所以成为历史事件,恰恰是因为它在以后的千百年间,经历了诸多和它毫不相干的事件。一个以此为出发点的历史学家……便建立了一个当下的概念,在这个作为‘现在’的当下概念中,充满了弥赛亚时间的碎片。”[3](P50)可以说,将富有历史意义与拯救潜能的“当下”从那似乎注定了的因果之链中解脱出来,乃是本雅明所持守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底蕴所在。 事实上,本雅明所强调的“当下经验”乃是他毕生精神求索的辐辏点。1918年,年仅26岁的本雅明在《未来哲学论纲》一文中表达了自己关注“当下经验”的心愿:“和一切伟大的认识论一样,康德认识论所面临的问题具有两面性,而康德只是成功地对其中的一个方面给予了有效的解释。所谓两面性,首先是恒久知识的确定性问题,其次是短暂经验的完整性问题。……就其总体结构而言,当下经验还从来不曾作为某种具有独立的时间意义的事物,展现在哲学家面前。对康德来说也是如此。”[3](P19-20)本雅明的运思是以解决康德认识论所面临的难题为契机的。在本雅明看来,康德认识论所面临的问题具有两面性,他从其先验人学的视域只能解决“恒久知识的确定性问题”,至于“短暂经验的完整性问题”在他那里便成为一个无解的难题,而这个难题恰恰是关注“当下经验”的本雅明所萦怀于心的。可以说,将“作为某种具有独立的时间意义的事物”的“当下经验”完整地“展现在哲学家面前”,是本雅明从踏上思想之旅的那一刻起就为自己确立的一项有别于先哲的任务。他在《未来哲学论纲》的开篇颇为自信地写道:“未来哲学的核心任务是:对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我们对伟大未来的预期给予最深刻的提示,并通过与康德学说的融通将其转化为知识。”[3](P19)所谓“与康德学说的融通”,乃意指主动将自己置于“当下经验”与先验之维所构成的巨大张力间的本雅明,试图以“当下经验”为纽结点来解开康德认识论的难题,并试图通过建构起“经验连续体”[3](P26)来解开困扰“我们这个时代”的形而上学难题。在本雅明的期待中,“伴随着知识概念的改变,不仅是经验概念,就连自由概念也将经历一场决定性的变革”[3](P26)。我们看到,本雅明对“未来哲学”的这一构想,自始至终贯穿于其精神探求的各个时期,并为其充满时代感的文字奠定了一层悲郁的底色。 本雅明所强调的“经验”并非那种机械化、数量化的“经历”(“伪经验”),而是一种刻骨铭心且带有质感的“真经验”。在本雅明那里,这种“真经验”的核心意蕴说到底是一种“废墟”意识。1925年,他在申请教授职位的资格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篇长文在当时却遭到了拒绝,1928年才得以正式出版)里,首次以“寓言”这一“解释现代艺术的钥匙”(卢卡奇语)揭示了盛行于17世纪德国的巴罗克悲悼剧的碎片化特征,指出这种悲悼剧“从一开始就是以寓言的精神作为废墟、作为碎片而构思的”[4](P196),并就此阐发了这种巴罗克艺术之所以崇拜废墟的缘由:“悲悼剧舞台上自然——历史的寓言式面相在现实中是以废墟的形式出现的。在废墟中,历史物质地融入了背景之中。……寓言在思想领域里就如同物质领域里的废墟。这说明了巴罗克艺术何以崇拜废墟的原因。……作为废墟而展现在这里的,具有高度意指功能的碎片,那片残余,事实上,是巴罗克创造的最精美的材料。”[5](P146-147)在本雅明看来,“废墟”指的是思想世界与物质世界在“灵光”(Aura,也译为“灵韵”、“灵晕”、“光晕”、“光辉”)消失之后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碎片化的征候,而“寓言”就是对隶属于思想世界的巴罗克艺术因着其“光辉的缺场”而呈现出来的碎片化征候的一种命名。本雅明就此指出:“以前几乎从来没有这样一种文学以其幻觉般的精湛技巧把那种光辉从其作品中如此彻底地清除出去,那种光辉具有一种超验的效果,曾一度被正确地用来界定艺术的本质。可以把这种光辉的缺场说成是巴罗克抒情诗最鲜明的特点之一。”[4](P148) 如果说《德国悲剧的起源》的旨趣在于以“寓言”来揭示本雅明所“经验”到的思想领域里的“废墟”,那么从1927年至其自杀(1940年)之前一直盘桓于本雅明脑际的“巴黎拱廊街研究计划”的旨趣就在于揭示物质领域里的“废墟”了。1935年,他拟定了一份题为《巴黎,19世纪的首都》(起初拟订的标题是《巴黎拱廊:一个辩证的意象》;1939年,他应霍克海默的要求对这份提纲作了进一步的修订)的研究计划。在这项以巴黎拱廊为中心而展开的研究计划中,本雅明借着充斥商品拜物教气息的巴黎拱廊、世界博览会等景观揭示了“市场幻境”的秘密,借着“居室”对新技术与新经济的抗拒以及“青春艺术派”装饰对“居室”的消灭述说了“居室幻境”的命运,借着奥斯曼对巴黎的改建以及巴黎公社时期的街垒战和巴黎焚城等新行为分析了“文明本身的幻境”,指出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形形色色的物质世界到头来却只是一片支离破碎的“废墟”。本雅明就此写道:“在19世纪,生产力的发展促成种种创作形式从艺术中解放出来……在这个时代产生了拱廊和私人居室、展览大厅和全景画。它们是梦幻世界的残存遗迹。……随着市场经济的大动荡,甚至在资产阶级的纪念碑倒塌之前,我们就开始把这些纪念碑看作废墟了。”[5](P29-30)本雅明是一位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识的思想家,他从一开始就对资产阶级营构出来的诸种“幻境”作着“残酷的思考”(布莱希特语),并一语道破了资产阶级文明的“废墟”性。在这一点上,他同持守“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马克思一样,从未对看似辉煌的资产阶级文明史抱有任何幻想。本雅明敢于直面历史“废墟”的立场和勇气,在《历史哲学论纲》的这样一段话中得到了颇为集中的阐释:“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是一份野蛮残暴的实录。正如任何文明的记录都不可能免于野蛮残暴,文明从一只手向另一只手转移,传递的方式同样被野蛮和残暴玷污了。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者避之唯恐不及。历史唯物主义者视与历史保持一种格格不入的关系为己任。”[3](P42)在资本主义社会时代,由资本的疯狂扩张与贪婪掠夺所带来的那种野蛮残暴的面相显得尤为狰狞可憎。其实,马克思早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就道出了资本家靠剥削剩余价值来压榨无产者的秘密,并指出了资本在从原始积累到殖民剥夺再到战争掠夺的嬗演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贪婪本性:“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6](P839)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那里汲取过运思智慧的本雅明虽然并未以资本为辐辏来揭示资本主义文明的内部矛盾及其嬗演轨迹,但他以其诗人的气质从“野蛮残暴的实录”中同样敏锐地嗅到了一股难闻的“废墟”气味。可以说,“废墟”意识既是命运多舛的本雅明刻骨铭心的“当下经验”的内核,又是他借着这一“当下经验”书写“历史唯物主义者”自己的历史的枢机之所在。 当然,确认历史是由立于“当下”而经验到的一个个“碎片化”的“废墟”层累叠积起来的“幻境”,并非意味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必然导致绝望。不过,本雅明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将每一个“当下”都视为个体直面“废墟”的“危险关头”,正是在这样的“危险关头”,个体才为自己赢得了立于“废墟”之上吁求“救赎”的契机。在本雅明看来,“当下”并不是缠缚于因果链条之上的“事件”,而是“充满了弥赛亚时间的碎片”。由这种“当下观”来反观人类的历史,拯救“当下”同时意味着拯救“过去”,因为从因果链条之上挣脱出来的“过去”同样是曾经充满着“救赎”潜能与具有历史意义的“当下”:“对过去的看法同样和救赎的观念牢不可破地联系在一起,而这正是历史最为关切的。过去携带着一份秘密清单,并据此指向救赎。”[3](P39)若想把“过去”转换为指向“救赎”的“当下”,自然不能像“历史主义”所许诺的按照所谓“实际所是的那样”去认识它,这种烙有“科学主义”胎痕的历史观剥夺了人选择属己的历史的权利,最终也抹去了曾经的“当下”所赋有的历史意义。本雅明所希望的显然是另外一种“过去观”:“历史唯物主义希望当过去的图像在危险关头不期然地显现在历史主体面前时将其牢牢把握。……能够在过去(的灰烬)之中煽起希望之火花的唯有这样一种历史学家,他坚信,假使敌人获胜,连死者也不得安宁。而敌人从来不曾服输。”[3](P41)在本雅明看来,“过去的图像”是在“危险关头”向“历史主体”不期然地显现并被历史主体牢牢把握的,也正是在这一时刻,“过去”以其“废墟”的面目燃起了“希望之火”。透过上述这些言语,我们显然从中觉察到了那发自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的末世论、启示论的消息。所谓“危险关头”,指的就是那末日审判的时刻。在这一迎接“救赎”的时刻,“过去的每时每刻都将变成‘今日法庭上的证词’。那一天便是最后审判日”[3](P39)。关于本雅明由立于“当下”这一“危险关头”而迎接“救赎”所透示出来的末世论、启示论的消息,沃林的一个说法颇值得参考:“从最早的理论活动开始,末世论主题就在本雅明的思想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这又有什么值得困惑的呢?实际上,从青年时代到成熟时期,他的著作始终贯穿着一种深沉而急迫的启示论精神。”[1](P2-3) 二、“历史天使”的意蕴及其“辩证”性征 我们看到,从“弥赛亚主义”那里汲取“救赎”灵感的犹太思想家本雅明,在咀嚼人生与历史的种种痛楚之后,最终将“救赎”的希望与使命赋予了这样一位“历史主体”——“历史天使”。他写道: 克利有一幅画作,叫作《新天使》。画的是一个天使似乎正要从他所凝视之物转身离去。天使双眼圆睁,张着嘴,翅膀已展开。这正是历史天使的模样。他的脸扭向过去。在我们看来是一连串事件发生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不断把新的废墟堆积到旧的废墟上,并将它们抛弃到他的脚下。天使本想留下来,唤醒死者,弥合破碎。然而一阵飓风从天堂吹来,击打着他的翅膀;大风如此猛烈,以至于天使无法将翅膀收拢。大风势不可挡,将其裹挟至他背对着的未来,与此同时,他面前的残骸废墟却层累叠积,直逼云天。我们所谓的进步正是这样一场风暴[3](P43-44)。 本雅明心中的“历史天使”是背对“未来”而面朝“过去”的。这位姿态特异的“历史天使”之所以背对“未来”,乃是因为他并不相信“历史主义”所允诺的无限进步的历史幻境;之所以面朝“过去”,乃是因为在他看来“过去”携带着一份指向“救赎”的“秘密清单”。这份“秘密清单”的题旨只有两个字——“灾难”。这种清醒的“灾难”意识,正出自于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美国学者蒂德曼在《历史唯物主义还是政治弥赛亚主义》一文中曾指出:“本雅明从隐喻的角度所提到的天使……代表着真正的历史学家,代表着对人类历史不抱有任何幻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为了‘像我们以前的每一代人那样’使用所赋予我们的‘微弱的弥赛亚力量’,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身份看待历史——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而是本雅明第九论纲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是一场废墟‘越堆越高,直向天空’的大灾难。”[2](P353)一个接着一个的“废墟”被抛到“历史天使”的脚下,脚下越积越多的这些支离破碎的“废墟”其实就是“历史天使”正置身于其中的“当下”。直面脚下的“废墟”,“历史天使”想停留下来,肩负起“弥赛亚”交付的“唤醒死者、弥合破碎”的历史使命,于是“当下”便成为“充满了弥赛亚时间的碎片”。但是,他最终却未能完成这项使命,其中的原委在于,从“天堂”吹来的飓风太猛烈了,他的翅膀被势不可挡的飓风吹得无法收拢,值此“危险关头”,脚下的“废墟”也层累叠积地直逼云天,无法立足容身的“历史天使”只得一步步地退向“未来”。也正是在这个“危险关头”,“历史天使”意识到所谓的“进步”只是在层累叠积的“废墟”的威逼下不断地退向“未来”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天使”从未转身离去,他的双脚始终是立于“当下”、目光始终是投向“过去”的,我们正是从这里真切地觉察到了流淌于“历史天使”心中的那份永不熄灭的“救赎”冲动。这样一来,“历史天使”就成为一个坚忍地立于由“过去”与“未来”所构成的巨大张力的“当下”不断地凝视“过去”又不断地退向“未来”的“历史主体”。这个“历史主体”始终立于充斥着废墟的“当下”,却也从未放弃过救赎历史的乌托邦冲动。蒂德曼就此指出:“本雅明的天使完全是人性化的,却似乎在面对历史的非人性化时表达了超人性的绝望。尽管他无能为力,他也无法把他的目光从扔在他脚下的废墟上移开。然而这就是人类体验自己的历史之可怕的方式。如果还有什么在推动着人类前进,那是对失去的天堂的记忆。这股乌托邦的力量是一股还没有熄灭的冲动。”[2](P351)人类因着自身的原罪被抛入了历史,从此失去了“天堂”,然而介入历史且负荷着救赎历史使命的“历史主体”却并未失去对“天堂”的记忆。正是凭着这点儿温馨的记忆,作为“历史主体”之化身的“历史天使”才从“天堂”那里为自己觅得了一股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乌托邦力量。 本雅明笔下的“历史天使”是一个既令人着迷又令人困惑的辩证意象。同本雅明持守的那种韵致独异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倘若不理解他述说的那种似乎诡异难辨的“辩证思维”的意趣,同样无法理解他运用其辩证思维所构拟的“历史天使”这个意象。早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本雅明就借着阐发“寓言”这个尚带有思辨性痕迹的概念透示出了一种独特的“辩证思维”的消息:“把寓言这个新概念描写成思辨的仍然是合理的,因为它事实上已被用来提供一个漆黑的背景,这样,象征的光明世界才能被衬托出来。”[4](P131)“寓言”揭示的是思想领域里呈现出来的那种碎片化的“废墟”景观,其旨趣在于为彼在的“光明世界”提供一个“漆黑的背景”;这种“背景”愈“漆黑”,挣扎于其中的个体就愈为强烈地渴慕那个“光明世界”:“在寓言中,观察者所面对的是历史弥留之际的面容,是僵死的原始的大地景象。关于历史的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不适时宜的、悲哀的、不成功的一切,都在那面容上——或在骷髅头上表现出来。”[4](P136)这里所谓“历史弥留之际的面容”,其实指的就是《历史哲学论纲》中的那位“历史天使”从历史中觉察到的“层累叠积,直逼云天”的“废墟”面相。直面“僵死”的“废墟”面相,觉醒了的个体终于把目光投向了那个眺望中的“光明世界”。 本雅明通过这种启示了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辩证思维”,不仅创造性地发明了用以指称流行于17世纪的德国悲悼剧所呈现的那种碎片化特征以及废墟化面相的“寓言”这一概念,而且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1935年提纲)》中明确地道出了“在17世纪寓言变成辩证意象的规范”[5](P22-23)这一谜底,并就此分析了展呈于19世纪巴黎的物质领域里的“废墟”景观:“生产力的发展使上个世纪的愿望象征变得支离破碎了,这甚至发生在代表它们的纪念碑倒塌之前。……在苏醒的过程中让梦幻因素变成现实,这是辩证思维的范式。因此,辩证思维是历史觉醒的关键。实际上,每一个时代不仅梦想着下一个时代,而且也在梦幻中催促着它的觉醒。每个时代自身就包含着自己的最终目的(终结),而且正如黑格尔早已注意到的,用狡计来展现它。”[5](P29-30)本雅明在这里虽然将他所称的“辩证思维”的源头追溯到了黑格尔那里,但他在根底处并不是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家,而且其著述中也没有诸如“世界精神”之类的“总体性”的概念,难怪具有哲学家气质的阿多诺不无抱怨地指出“本雅明的著作无法达到任何完整性,而是成碎片状”[2](P115),并将这种“成碎片状”的思维称为“一种对历史的运动在那里停顿并分解为形象的最细小的事物的全神贯注而逃避了永恒和历史之间的对立”的“凝固的辩证法”[2](P124)。事实上,本雅明并未逃避“永恒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在他那里,“永恒”属于先验的领域,“历史”则属于经验的领域,二者之间永远保持着一种既亲切却又无法弥合的紧张关系。正是为了喻说这种紧张的关系,以完整的“当下经验”作为运思枢机的本雅明才别具匠心地构拟了一个立于“当下”、面朝“过去”、退向“未来”的“历史天使”意象。对于这个包蕴本雅明历史观全部秘密的“辩证的意象”,阿多诺却未曾理解它的幽趣。与此相比,阿伦特则看到了本雅明这位从“唯物主义”运动中产生出来的“最奇特的马克思主义者”[7](P152)的“最奇特”之处。她认为,本雅明是以一种诗人的气质来进行哲学思考的,当他以这种“诗意地思考”对并非随意撷取来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弥赛亚主义、超现实主义、德国浪漫主义等)进行吸纳时,同时也对它们作了一种富有个性的“隐喻性”转换。阿伦特颇为中肯地写道: 隐喻是一种途径,通过它,世界的统一性(oneness)被诗意地表达出来。理解本雅明之所以如此困难,就在于尽管他不是诗人,但他诗意地思考,由此必然会把隐喻当成语言对我们的伟大馈赠[7](P156)。 所谓“隐喻性”的思想,就是给无形的思想赋予一种具体可感的形式,这种“诗意地思考”善于将真切的生命体验转换为富有思想内涵的意象;这种意象看似是“非辩证”的乃至“暧昧”的,事实上却以另外一种形态演述了“辩证思维”的韵致。本雅明指出:“暧昧是辩证法的意象表现,是停顿时刻的辩证法法则。这种停顿是乌托邦,是辩证的意象,因此是梦幻意象。”[5](P22)事实上,正如本雅明阐发的整个“巴黎幻境”就是一个启人深思的“辩证的意象”,他寄予厚望的“历史天使”同样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辩证的意象”。 在本雅明笔下,“历史天使”既面向“过去”,又不完全属于过去;既退向“未来”,又不完全属于未来。他断然立于富有救赎潜能的“当下”这个交叉点上,同时向“过去”与“未来”保持着开放。“历史天使”所采取这种“暧昧”的姿态,恰恰是本雅明所致力的那种充满巨大张力的“辩证法”的“隐喻性”呈现形式。正是在这种呈现形式里,本雅明既保存了完整的“当下经验”,又为这个作为“危险关头”的“当下”赋予了“救赎”的维度。 三、“历史天使”是一位“忧郁”的“寓言家” “历史天使”同时向“过去”与“未来”保持着开放,这意味着他同时被“过去”与“未来”不断地撕扯着。他已从“弥赛亚”的注视中醒来,并且已从这位终局救赎者那里领受了“唤醒死者、弥合破碎”的天职,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委顺于废墟化了的历史;与此同时,他毕竟仍是历史中的个体,终究无法让自己作为“永恒形象”的“弥赛亚”完全摆脱历史之维的制约,“如本雅明在这里所看到的,历史的天使未能完成任务,而这个任务只能由弥赛亚来完成”[2](P260)。“历史天使”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上正负荷着救赎历史的任务,他也颇为清楚地晓得仅凭自身的力量最终无法完成这一须得由他倾尽生命予以践行的使命,于是,这位挣扎于历史与永恒之间的“救赎者”与“失败者”便成为一位带有忧郁气质的人物。朔勒姆就此指出: 历史的天使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忧郁人物。他毁于历史的内在性,因为只能通过跳跃才能克服这种内在性,但这种跳跃并不能以“永恒形象”拯救历史的过去,而只能从历史连续中跳入“当下的时间”,不管这个时间是革命的还是救赎的[2](P260)。 所谓“革命的”,指的是将“当下的时间”转化为现世解放的世俗形式,这是马克思所采取的途径;所谓“救赎的”,指的是为“当下的时间”赋予犹太教神学意味上的救赎潜能,这是本雅明所采取的途径。或许有人会把这两种救赎形式完全对立起来,事实上大可不必,因为它们在本雅明这里是并行不悖的。关于这一点,蒂德曼已明确指了出来:“借助救赎这一神学概念,本雅明的确超越了马克思,马克思只是涉及了救赎的世俗形式——解放;但这并没有损害他与马克思的并行不悖。他并没有把救赎的任务指派给一个从外部介入历史的救赎者,这是‘我们’的任务,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本雅明似乎要对此加以补充说明,人类因此首先使过去的历史具有完整性。”[2](P357-358)确实,“历史天使”并不是人类之外或之上的某种存在,说到底,他就是已经觉醒到历史的“废墟”性并断然承担起救赎历史的重任的“我们”的代表,尽管他自知作为历史中的人物不可能完成终局救赎的任务,但也从未消泯过涌动于心中的那份救赎的冲动,这就是以其西西弗式的坚忍意志在历史中救赎历史的“历史天使”的真实生命。也正因为这一点,他的生命中便透出了一种厚重的忧郁基调。 若追溯“历史天使”在本雅明思想中的最初萌动,可以说他就是《德国悲剧的起源》中的那位“寓言家”。本雅明认为,“寓言”具有一层阴郁的色调,因为它只适合于表现因着“光辉的缺场”而呈现出来的废墟化了的意象。如果这种废墟化了的意象在阴郁的眼光的注视下变成了“寓言”,那么它就把自己暴露给“寓言家”了。本雅明借着对意识到了废墟化的历史面相的“寓言家”的述说,阐述了“忧郁沉思”的本质: 在上帝的世界里寓言家醒了过来。“是的,当上帝从坟墓里带来了收获的时候,那么,我,一具象征死亡的骷髅,也将成为天使的面容”。这解开了最破碎的、最过时的、最分散的谜。……寓言的沉思必须清除对客观世界的最后幻觉,完全用自己的手法,不是在世俗物质世界上嬉戏地、而是在天堂的注视之下严肃地重新发现自身。而这就是忧郁沉思的本质:它的终极客体,即它认为完全能够使自身确保的那种邪恶,变成了寓言,这些寓言填充和否定了它们所代表的那个空隙,正如其意图最终并非在于忠实地思考那些尸骨,而背信弃义飞跃到复活的观念一样[4](P193-194)。 “寓言家”是在“当下”眺望到“上帝”之光的那个瞬间醒过来的,他一旦醒过来进而“在天堂的注视之下严肃地重新发现自身”,那谜一般“最破碎的、最过时的、最分散的”历史景观随之呈现出了它的底色——废墟。这种“寓言的沉思”不再耽迷于线性发展的历史观念,而是消除了“对客观世界的最后幻觉”,从而让“寓言在瞬间性与永恒性短兵相接的地方确立自身最永久的地位”[4](P185-186)。可以说,“寓言的沉思”的本质就是“忧郁沉思”的本质,它将充斥“骷髅”与邪恶的“终极客体”转化为间接肯认“上帝”之光的“寓言”。因此,“忧郁沉思”的旨趣“最终并非在于忠实地思考那些尸骨”,而是要“飞跃到复活的观念”,也就是说,要把堆满废墟的历史转化为当下“救赎”的历史。由此可见,《德国悲剧的起源》已包蕴了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所构拟的那位带有忧郁气质的“历史天使”的全部秘密,尤为显豁的是,他借用鲁亨斯汀所创作的一首题为《花》的诗中的句子——“是的,当上帝从坟墓里带来了收获的时候,那么,我,一具象征死亡的骷髅,也将成为天使的面容”——来阐说“寓言家”以及“忧郁沉思”的意趣,其中已明确提到了“天使”这个“辩证”且“忧郁”的意象。 本雅明是一位带着切己的生命体验探问人类历史及其命运的思想家,他所构拟的那位带有忧郁气质的“历史天使”其实正是他的生命气象的直观写照。可以说,正如敢于直面“废墟”而吁求“救赎”的“历史天使”,本雅明的心中自始至终都怀有一份不至于彻底绝望的希望:“同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一样,我们也被赋予了些微的弥赛亚式的力量。”[3](P39)尽管被赋予的“弥赛亚式的力量”只是“些微”的,不过就是这点儿“些微”的力量已足可让本雅明洞察到历史的真相进而断然负荷起最终无法由他自身独立完成的“救赎”的重任。这样的生命样态无疑是充满着巨大的张力的,正是这种充满着巨大张力的生命样态,使得本雅明最终把自己成全为一位从忧郁中汲取创造源泉的思想家。桑塔格就此写道: 他自认为是忧郁者,但对现代心理学标签不屑一顾,而是援引了一个传统的星象学观念:“我是在土星之兆下来到世间的,那颗星球运转得最缓慢,是颗绕来晃去并拖拉延宕的行星……”如果人们没有认识到他在多大程度上倚重一种有关忧郁的理论,恐怕就很难充分理解他的主要著述[8](P120)。 用以揭示本雅明生命底色的“忧郁”并不是一个现代心理学的观念,而是一个与传统星象学的“土星性情”相类似的观念。这颗行星运转得“最缓慢”,也最有耐力;它在多种力量的撕扯下“绕来晃去”地行走,却也从未偏离过自己的轨道;它的运行样态诚然显得“拖拉延宕”,不过其生命的内核则蓄积着无穷的能量。正如这颗在多种力量的撕扯下蓄积起无穷的能量且“绕来晃去并拖拉延宕”地缓慢运行的土星,本雅明同样在多种“立场”所形成的巨大张力下,以其“忧郁”的性情将这些张力内化为一种如原子核般看似静止不动的创造性力量,正是这种创造性的力量,缓缓地外化为一篇又一篇带有其生命热度与强度的文字。依着桑塔格的一个说法,即“具有土星性情的人……很适合做艺术家和殉道者”[8](P125)。本雅明不是一位艺术家,但他却是一位颇具艺术家气质的“殉道者”。身为犹太人,他继承了“弥赛亚主义”这笔精神遗产,并在苦苦觅寻历史救赎的路途中将波德莱尔式的忧郁诗人视为自己的同道。 在本雅明看来,“波德莱尔的天才是寓言家的天才;他从忧郁中汲取营养。在波德莱尔笔下,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这种诗歌不是家园赞歌。当这位寓言家的目光落到这座城市时,这是一种疏离者的目光”[5](P20)。波德莱尔之所以让本雅明着迷,其实正在于他那敏锐地道破巴黎废墟真相的“寓言家的天才”和那“从忧郁中汲取营养”的精神气质。诗人脚下的“巴黎”并不是他的“家园”;属于他的“家园”早已失去,他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立在这个废墟化的荒原上唱着一曲曲忧伤的挽歌。本雅明写道: 《忧郁与理想》是《恶之花》的第一组。理想提供了回忆的霸权;忧郁则调集了无数的分分秒秒来与之对抗。……忧郁组诗之一《虚无的滋味》表示:“可爱的春天,它的香味已归于乌有!”在这句诗里,波德莱尔极其谨慎地表达了某种极端的东西;这使它绝对无误地成为他特有的东西。“归于乌有”这个说法承认了他曾经拥有的经验现已崩溃。香味是“不由自主的记忆”的隐身处。……如果对一种香味的辨认比其他任何回忆更有可能给予人以安慰的话,这可能是由于它深度地麻醉了人的时间意识。一种香味可能把岁月淹没在它让人回想起的滋味里。这就使波德莱尔的诗句具有了一种无限感伤的意味[6](P220-221)。 所谓“不由自主的记忆”,指的是未经理智过滤与算计的记忆,这种普鲁斯特“意识流”意味上的记忆建立起了诗人与曾经经验过的那种“香味”的联系。这里所谓的“香味”,相当于《德国悲剧的起源》中提及的“上帝的光辉”、《摄影小史》与《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提及的“灵韵”、《历史哲学论纲》中提及的“弥赛亚”,在本雅明那里,它是彼在的理想之维。这种彼在的理想之维给人提供了“回忆”的权利,也能让人在“不由自主的记忆”中感到一丝“安慰”。然而,“忧郁”的诗人同时意识到那回忆中的“香味”在现世中毕竟已经“归于乌有”了。于是,波德莱尔的诗句便令人体验到了一种“无限感伤的意味”。对波德莱尔来说,这显然是一种无法自解的“感伤”,其中的原委在于,他始终以其忧郁的目光打量着这座“陷落到海底”的巴黎城: 把女人意象和死亡意象混合在第三种意象即巴黎的意象中,这是波德莱尔诗歌的独特之处。他诗中的巴黎是一座陆沉的城市,不是陷落到地下,而是陷落到海底。这座城市的冥府因素——地貌结构、被遗弃的旧塞纳河床——在他笔下明显地表现为一种模式。但对于波德莱尔来说,在这个城市的“充溢死亡的田园诗”中,最关键的是现代的社会下层。现代性是他诗中最主要的关切。由于忧郁,它(现代性)打碎了理想。但是,恰恰是现代性总在呼唤悠远的古代性[5](P21)。 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描摹“巴黎意象”的诗就是“充溢死亡的田园诗”。诗中的主人公,不再是那些与田园风光融为一体的牧羊人与耕作者,而是徘徊于“陆沉的城市”中的妓女、赌徒、闲逛者、拾垃圾者,他们与这座“陷落到海底”的城市一起,都带有“冥府因素”。本雅明从这些散发着死亡气息的意象中,颇为敏锐地看到了波德莱尔诗歌中的“现代性”因素。依着波德莱尔的一个说法,“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9](P485)。应该说,这一说法与本雅明将每一个“当下”都视为“弥赛亚侧身步入的那道窄门”在运思方式上是完全一致的。这一半是地狱与魔鬼,那一半是天堂与上帝;这一半是此在的瞬息万变的历史废墟,那一半是彼在的永恒不变的理想之维,而立于这夹缝之间的,正是那位与本雅明笔下的“历史天使”一样怀着一颗无比忧郁的心灵吟咏着“充溢死亡的田园诗”的诗者与思者。尤为深刻的是,本雅明就此提出了一个似乎诡异的辩证命题——“恰恰是现代性总在呼唤悠远的古代性”;依着本雅明的“辩证思维”,这个命题完全可以被进一步推演为——恰恰是此在的碎片化、偶然化、废墟化的“当下”总在呼唤那彼在的整一性、不变性、永恒性的“理想”。这其间的张力是可想而知的,正是这种巨大且无以自解的张力,成为波德莱尔乃至本雅明及其“历史天使”忧郁气质的最后肇因。就此而言,本雅明所持守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从一开始就带有忧郁的基调,他运用其辩证思维所构拟的所有“辩证的意象”其实都是忧郁的意象,这其中既包括“历史天使”,也包括波德莱尔之类堪称“历史主体”的诗者与思者,更包括怀着同样的“救赎”愿望却终究未能完成这一任务的本雅明自己。 追根究底,本雅明乃问题中人。例如,他始终“让自己置身于十字路口”[8](P135),在多重立场的叠加与撕扯所形成的巨大张力间左冲右突;他通过描摹那位屡遭厄运捉弄的“驼背小人”[10](P157-160),诉说着自己以及现代人不堪的命运,并用自己的生命化成文字以与这不堪的命运作毫无妥协的抗争;他透过“巴黎幻境”与“历史幻境”洞察到了西方现代历史的废墟本相,并试图借助他所期许的“历史天使”来拯救这场灾难深重的文化危机。然而,对于这位站在废墟化了的“当下”祈望“救赎”的思想家来说,本雅明自始至终都面临着一个无法自解的死结,那就是:他并没有也不愿意为作为“历史主体”的“历史天使”赋予善的根性。既然如此,“我们也被赋予了些微的弥赛亚式的力量”的根据究竟何在呢?也就是说,失去了善的根性的“我们”(“历史天使”说到底乃是作为“历史主体”的“我们”的代表)凭什么能得到“弥赛亚”的青睐进而从他那里获得“些微”的“救赎”历史的力量呢?要知道,“上帝”在下决心毁掉罪恶甚重的所多玛与蛾摩拉城之前,亚伯拉罕还是因着相信现世尚存少数几位“义士”而代人类向“上帝”祈求宽恕的;在两位“天使”奉行“上帝”之命用硫黄及火烧掉难以饶恕的所多玛与蛾摩拉城之前,他们尚因着罗得的善举而大施慈爱,指引仅存的这位“义士”带领他的家人逃到安全的琐珥城,进而给人类的自我救赎留下了一线的希望。 作为一位犹太思想家,本雅明肯定是熟知《圣经·旧约·创世纪》第18-19章所讲述的这个故事的,但他终究未能像亚伯拉罕那样相信人类中尚有“义士”存在,在他所有的著述中也找不到哪怕一位像罗得这样的“义士”来。由此看来,本雅明所期许的那位失去善根的“历史天使”最终无法完成人类历史自我救赎的任务从一开始就已是注定了的事,他的那份无以排遣的忧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甚至他运用其享有的否定的自由权利为自己选择的自杀这一告别现世的方式,也从另一个侧面为其激赏的现代艺术家及其构拟的“历史天使”的悲郁命运作了一个直观的注脚。可以说,这既是本雅明自身的悲剧,也是本雅明式的思者与诗者共同的悲剧。 [收稿日期]2015-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