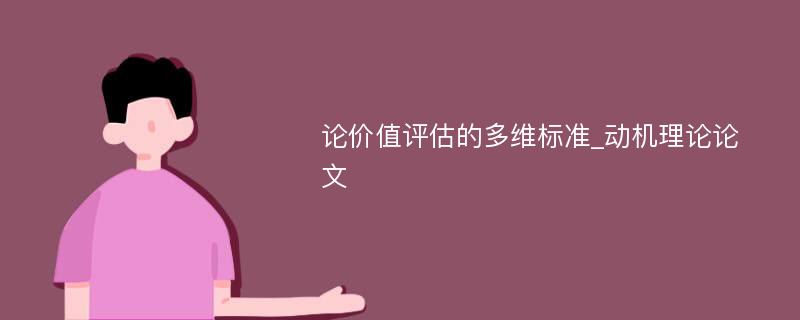
论价值评价的多维标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评价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4)09-0021-07 评价是人类生活的一大特征,构成人们活动的必要前提,贯穿于活动的始终。人们通过评价来揭示和把握价值,从而给自己提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务。然而,评价是一种具有强烈主观性的价值判断活动,既可能同客观的价值关系相一致,也可能与之相背离,这其中的关键是能否科学确立和正确运用评价标准。价值的本质规定决定了人的需要是最根本的评价标准。而人的需要是多维的,多维的需要之间可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要进行科学评价,就要正确地把握评价的多维标准,处理好多维评价标准中的矛盾,特别是个体标准与社会标准的关系、历史标准与道德标准的关系、动机标准与效果标准的关系。 一、个体标准与社会标准 评价标准是主体评价客体有无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的尺度。人的评价标准有很多,但归根到底是人的需要,也即人的利益。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意义关系,包含着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价值概念的这一基本规定中已经内含着价值评价标准于其中了。在现实社会中,每个人、每个群体、每个社会,无不自觉不自觉地以其自身的需要、利益来评价事物。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的评价会直接受到偏好、规范、理想等因素的影响,把符合自己的偏好、规范和理想的事物判断为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没有价值的。但无论是偏好,还是规范、理想,最终都根源于人的需要,是主体不同层次需要的反映。它们分别反映了主体的个体化需要、群体需要和长远需要,人的需要作为一种根本的尺度以间接的、潜在的形式存在于偏好、规范和理想之中。 主体有个体、群体、社会等不同形式,主体的需要也具体包括个人需要、群体需要、社会需要等不同形式。作为评价标准的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则表现为评价的个体标准和社会标准。毫无疑问,个体需要和社会需要固然有着相同或者一致的方面,但它们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其差别是十分明显的。马克思说:“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1](P536)符合个人需要的并不一定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对个人有价值的不一定对社会有价值。比如,袁世凯复辟帝制,实现了他的个人帝王梦,却出卖了国家民族利益,违背了民主共和的时代潮流。因此,依据个体标准和社会标准,来评价同一事物或者现象,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是冲突的结论。究竟该如何处理个体标准和社会标准的关系呢? 个体标准和社会标准的关系问题,在更大范围内,实际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无论是思想史上,还是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总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立场:社会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社会整体主义认为只有社会整体才是真实的存在,社会整体对个人具有优先性,它作为一个整体决定和支配着任何个人的行为和动机。因此,在价值论上,它主张社会整体本位。与此相联系,作为评价标准,它往往只承认社会需要这一标准尺度,而否认个人需要的尺度。个体原子主义则认为只有个人才是真实存在的,社会不过是抽象的个人集合体,是个人的相加,个体的属性先于和高于整体的属性。因此,在价值论上,它主张个体本位。与此相联系,它往往只承认个人需要作为评价的尺度,否认社会需要这一尺度,甚至否认或者消解社会需要、社会利益的存在,如边沁所说:“共同体是个虚构体,由那些被认为可以说构成其成员的个人组成。那么,共同体的利益是什么呢?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2](P58) 社会整体主义和个体原子主义是两种对立的立场,却分享着同一种思维方式:将社会和个人看作是两种既成的、相互分立的东西,把其中一方归约为另一方的抽象的、实体性的、静态的思维方式,导致了这两种立场的共同缺陷,即在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解上的先验性、非真实性和非历史性。事实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是实践,作为一种关系性的存在,个人与社会处在不可分割的关系之中,互为前提、互相依赖、互相创造。因此,对于价值评价来说,在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个体标准与社会标准的关系上,我们既不能用社会需要、社会标准取代和否定个人需要、个体标准,也不能用个人需要、个体标准取代和否认社会需要、社会标准。这里的关键是要区分评价事物对于某个个体的价值还是对于社会的价值。 凡是价值,都是具体的,是某事物对某主体的价值。主体的需要不同,客体的价值也就不同,价值表现出主体的个体性特征。价值的这一特征客观上决定了,当我们判断某一客体有无价值时,必须首先明确是“对谁的价值”、“以谁的需要”为标准。当判断某客体对某个人的价值时,其标准只能是某个人的需要,凡是符合这个人需要的就是对他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在生活中,有人会认为,如果以个人需要作为尺度来评价事物,就会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从而“天下无公理”。这种看法表面上似乎具有合理性,细究起来,实则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个体之为个体,就在于他的特殊性。每个个体的需要都是具体的、多样的,除了一般需要和共同需要外,还有自己的特殊需要。“公”之所需,未必是“婆”之所欲。因此,对“公”有价值的,对“婆”未必有意义。由此产生对同一客体的不同的乃至相反的价值评价,这完全是必然的、正常的现象。对某个个体来说,判断客体对其自身的价值只能是他的个人需要,而不能是其他人的需要或者社会需要。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反映的是个体追求的不同取向。“因材施教”、“对症下药”、“量体裁衣”等等,都是表示个人需要的独特性和它作为价值标准的不可取代性。倘若用别人的需要来判断客体对某个个体的价值,或者评价主体无论判断事物对谁的价值,都用自己的需要作为尺度,这无疑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的。 主体除了个体形式之外,还有社会形式。价值评价不仅要判断事物对个人的意义,更要认识事物对社会的意义。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和发展。每一个人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置身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生活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的需要的产生、发展和满足,都要通过社会得到实现。因此,社会对现实的个人来说,具有先在性。把握客体的社会价值,是价值评价的重要任务。 评价客体的社会价值的尺度是什么呢?不是个人的需要,也不是某个群体的需要,而是社会的需要。只有符合社会需要的事物,才是具有社会价值的事物;也只有从社会需要出发,才能正确地评价其社会价值。至于个人的需要、群体的需要,如果它们同社会需要是一致的,它们对于事物的社会价值而言,无疑具有客观评价标准的意义,因为它符合社会需要,是作为社会需要而起作用的。一旦个人需要、群体需要与社会需要相冲突,它便失去了正当性和合理性。以此为尺度评价事物的社会价值,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混乱和错误。 所谓社会需要,就是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符合社会发展趋势、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需要。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也就是符合社会进步需要的,就是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提出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3](P466)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4](P209)毛泽东说得更明确:“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5](P1079) 任何时代的历史活动都是群众的事业。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根本需要和利益同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以社会需要、生产力发展为尺度,实质上就是以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为尺度。毛泽东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5](P864-865)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系统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这一评价事物的社会价值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6](P372)在这里,发展生产力是基础,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目的,综合国力是生产力水平的表现和发展生产力的保障,也是人民富裕的前提。以此为标准,通过实践证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就是好的有意义的,反之则是不好的、没有意义的、有害的。 二、历史标准与道德标准 作为评价标准的主体需要,不仅有个体需要、群体需要、社会需要等多种形式,而且每一种形式的主体需要还有着多方面的内容,如功利的、认知的、道德的、审美的等方面的需要。在主体的不同需要、不同评价标准中,历史需要和道德需要、历史标准和道德标准特别值得分析。这是因为,对同一事物、同一社会现象,依据历史标准和道德标准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大不相同,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由此带来人们常说的所谓历史标准和道德标准、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某种“二律背反”现象:社会进步伴随着所谓道德退步。比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社会快速走向现代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道德失范、道德失序、道德缺失的现象。对这一现象,有人从历史的视角予以肯定,有人从道德的视角予以否定,这就产生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应该如何看待评价中的历史标准和道德标准的关系? 无论是思想史上,还是实际生活中,始终存在评价的道德主义与历史事功主义之争。道德主义仅仅强调以道德为标准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不知或者否认历史事功评价。中国传统儒家学者,大都属于道德主义传统。如朱熹认为“道”是超乎自然与社会之上的一种先验的道德,是为天理。他以义理为标准,秉承二程,把三代与汉唐作了严格区别: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故三代为王道时代,汉唐为霸道时代。他推崇三代,贬抑汉唐,认为“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7](P1583)历史事功主义者则强调历史事功标准,乃至用历史事功标准充当道德标准,所谓“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如与朱熹相对,陈亮则以历史事功为出发点,认为王、霸非截然之判分,王道只有落实为事功才不至于是一句空话,才有实质的意义。历史上诸多君王藉霸道取其位,因其位而有仁之功。“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8](P1850)孔孟虽贤却无位,“卒不得行其道以拯民于涂炭者”。[9](P34)在当代历史研究中,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人以历史事功标准为依据,针对以往根据道德标准对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所进行的评价进行翻案。道德主义与历史事功主义在争论中表现出来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二者都没有正确理解历史标准与道德标准的关系,他们用一种标准取代另一种标准,陷入绝对的一元论。 所谓道德标准就是一定的道德规范、道德观念。历史标准是个多义的概念,与道德标准相对应意义上的历史标准,指的是事功标准。这里的事功不是个人之私利,而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恩格斯认为,归根到底,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汲取自己的伦理观念的。因此,道德标准和历史标准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道德标准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它既有着历史的传承性,也有着对现实、社会历史的某种超越性和理想性。正因为如此,道德标准不能被简单归结为历史标准,更不能为历史标准所取代。反之亦然。由此,历史标准和道德标准就成了我们评价事物和社会历史现象的两个重要的尺度。我们既要遵循历史标准,将事物和社会历史现象放进历史进程中去,以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判断其是非得失;也要遵循道德标准,根据一定的道德体系判断其是非善恶。 由于道德标准和历史标准有着不同的视角和内容,因此,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结果必然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恩格斯曾经以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为例:一方面,这是社会巨大的进步,文化巨大的发展,人类文明的开始;另一方面,完成这一更替的手段和过程却是卑鄙的、恶劣的。“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10](P113)在这里,道德的不合理性和历史的合理性并存,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道德上应该加以谴责的事,在历史的发展中却是必然的。 对此,马克思反对用“道德化的批判”来对待历史,而是强调要变革产生不道德现象的生产关系。因为,道德现象相对于生产关系来说,是第二位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人们在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改变自己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意识观念,包括道德观念。他在论述不列颠对印度的统治、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时候,明确写道:“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总之,无论一个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11](P683)这清楚地表明,面对这种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中的矛盾,我们应该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上来观察问题,把历史评价放在第一位,坚持历史标准优先于道德标准。 然而,当我们说坚持历史标准和历史评价的优先性时,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甚至取消道德标准和道德评价。事实上,正是道德标准、道德评价与历史标准、历史评价的差异甚至矛盾,表明了道德评价、道德标准的独立价值和不可替代性。如果说历史评价反映的是必然性,客观规律性;道德评价反映的是人的主体性,价值选择性。人们通过对事物和历史现象作出道德评价、善恶判断,表达自己的价值立场,要求人对自己的活动承担责任。通过道德标准和道德评价所指出的恶,指出了社会现实发展的限度,指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可能的方向。基于此,马克思一方面从历史的视角,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1](P36)同时,又鲜明地从道德和价值的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取得的这些伟大成就并没有能够使人获得实际的解放,反而使人处于深刻的异化状态。“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1](P580)通过异化劳动理论和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理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以及由这种劳动体系所带来的全社会的非正义性和反人道的性质。这种道德和价值批判,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价值缺陷,也指出了未来社会的理想目标:异化的消除,无产阶级乃至整个人类的解放,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P185) 所以,这里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坚持道德标准和道德评价,而是站在何种道德立场上,以何种道德标准进行道德评价,形成与历史评价的矛盾。因为,任何社会存在的道德都有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种形态。站在代表过去的旧道德立场上,对事物和社会现实进行评价、揭示其中的价值缺陷所表现出来的高度,不仅没有超越历史的水平,甚至没有达到历史水平。犹如马克思当年讽刺站在封建主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11](P54、55)我们只有站在代表未来的新道德的立场上,对事物和社会现象进行道德评价,揭示其中的缺陷,才具有积极的意义,才能为社会历史发展指明可能的方向。 三、动机标准和效果标准 价值评价中最为复杂的是对人的评价。苏东坡说:“人之难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险,浮云不足以比其变。”其难不仅在于人的行为本身的复杂性,更在于人的行为是一个从动机到效果的过程。动机和效果之间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好的动机产生好的效果,却也可能好心办成坏事;坏的动机产生坏效果,却亦有好的效果的情况。一个行为是善是恶,如何评价呢?在这个问题上,功利论与道义论的争论由来已久。功利论强调效果标准,道义论强调动机标准。 功利论根据行为的结果来判断该行为是对还是错,预先比较该行为带来的好处和害处(快乐和痛苦),然后选择带来最多快乐的做法。为什么要根据行为的效果来确定行为的善恶?“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功利原理承认这一被支配地位,把它当作旨在依靠理性和法律之手建造福乐大厦的制度的基础。”[2](P57)边沁认为,凡是企图对这一点提出疑问的伦理学体系,都是空谈,不究义理,只凭臆想,不顾理性,只在暗中摸索,不从明处探求。如果把快乐和痛苦的因素去掉,幸福将变得无意义,道德也成为无意义的了。所以,行为的道德价值存在于行为的结果之中,一个行为是善是恶,只须考虑它的结果如何而定。其所以是善,是因为它能够引起愉快或排除痛苦;其所以是恶,是因为它能够引起痛苦或排除愉快。他们否认动机本身的道德评价,认为从同一个动机,以至任何动机都可以产生善的、恶的,乃至无善无恶的行为。 道义论的代表人物当是康德,他认为应该根据行为的动机而非结果来判断它是否正确。人的行为道德与否,不是行为的结果,而是行为本身或者行为所依据的原则,即行为的动机正确与否。凡行为本身或者行为所依据的原则是正确的,不论结果如何,都是道德的。为什么呢?道德行为的善完全出自善良意志,善良意志之所以善,不在于行为所达到的效果和利益,而在于它遵循普遍必然的道德法则即“绝对命令”。“如果它在尽了最大的努力之后依然一事无成,所剩下的只是善的意志,它也像一颗宝石那样,作为在自身就具有其全部价值的东西,独自就闪耀光芒。有用还是无效果,既不能给这价值增添什么,也不能对它有所减损。有用性仿佛只是镶嵌,为的是能够在通常的交易中更好地运用这颗宝石,或者吸引还不够是行家的人们的注意,但不是为了向行家们推荐它,并规定它的价值。”[12](P401)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说:“事情在这里仅仅取决于意志的规定和意愿作为一个自由意志的准则的规定根据,而不取决于后果。”[13](P49) 马克思主义反对单纯以动机作为价值评价的根据。动机是隐藏着的,看不见的,它只有通过活动才能发挥和表现出来。在这一点上,功利主义对道义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只有很好的动机,没有相应的行动,动机意志就不过是一句空话。同样的动机,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指导的不同,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后果。所以,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只有从属的意义。恩格斯说:“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11](P438)列宁也说:“我们有些人在评价某一党派的口号、策略和它的总方针时,经常错误地拿这个党派自己提出的愿望或动机来作根据。这样的评价实在要不得。俗话说得好,地狱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14](P349) 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反对只是以效果作为评价行为的根据。单纯的动机不能作为评价的根据,并不意味着动机在评价中毫无意义。正因为动机和效果之间可能并不一致,因此,动机在价值评价中就不能被忽视。事实上,出于希望获得报酬而救起溺水的小孩,人们对此行为并不给予很高评价;也没有人把正当防卫与故意伤人简单等同起来。尤其是对于道德价值来说,行为所遵循的动机和意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讲动机的效果论对许多复杂的道德现象,无法作出公正的评价,尤其是它会把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歪打正着的阴谋家、别有用心论者,看作是有道德的人,而这恰恰是人们的道德感所不能容许的。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是目的对对象的感性批判活动,是追求一定目的并产生实效的活动。“‘善’被理解为人的实践=要求(1)和外部现实(2)”。[15](P183)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主张联系动机看效果,透过效果看动机,把效果与动机结合起来评价人的行为。“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5](P866)这种动机与效果结合论,实即实践论。 在动机与效果统一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更侧重于效果,强调以效果为核心。马克思早就指出,“共产主义的博爱则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16](P121)动机与效果相对比,效果更为根本。动机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在实践中表现的,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尽管好心也可能办坏事,但真正的好心除了其本身的内容外,必须顾及效果。在这里,回顾毛泽东的话是极为必要的:“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5](P873-874) [收稿日期]2013-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