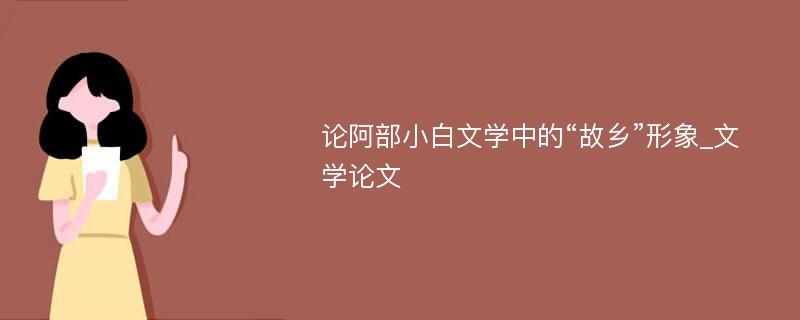
论“故乡”在安部公房文学中的意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房论文,意象论文,故乡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969/j.issn.1673-1646.2010.06.010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46(2010)06-0038-06
“无国籍思想”在安部公房的文学中可谓俯首皆是。它不仅指出了安部公房文学的国际性,也指出了其文学中“故乡”的问题。故乡通常指一个人的出生地,而安部公房的出生地和成长地是不同的。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侵略和掠夺令许多人背井离乡,这些人的身上都会看到像安部公房这样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说,安部公房运用在作品中重新建构现实的写作方法来描写“故乡”的存在状态是成功的。而安部公房文学中“故乡”的意象是这些问题交织在他文学中的一个谜阵。为了探究这个谜阵,本文拟以他主要作品中所出现的“故乡”为线索来进行分析。
1 失去故乡
如果要探寻个人或民族精神的根源,除了要了解其固有的时间和空间要素,还要证明两者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其中只有故乡才能反映出个人或民族所独有的风俗、思维、历史等现象。虽然人人皆有故乡,但却不能忽视世界近代史上所谓“失去故乡”这个哲学反题。下面分析安部公房在伪满洲的经历和“失去故乡”的关系。
1.1 伪满洲的生活经历
“我生在东京,长在旧满洲。但原籍是北海道,并且在那里还生活过几年。我的出生地、成长地、原籍都不是一个地方。……可以说本质上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或许,在我感情深处涌动着的对故乡的憎恶感竟是源于这种背景。一切有着固定价值的东西都会伤害到我。[1]”从引文可知他是典型的“失去故乡”者。没有故乡的失落感会让人不断憧憬故乡,最终促使其下意识地不断追求自己的归宿。“当谈到为何不能说沈阳就是我出身地时,简单讲,因为我们日本人是作为殖民地的统治民族生活在那里的……说到统治民族的特点,比方说现在在日本的美国人,他们只是把当地人看做是风景的一部分。虽然我在那里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也同时迷失了自己,这让人很是烦恼。绝不可能把殖民地称作故乡……我想去探访一次。但我不是归乡之人,仍不过是来自远方的旅行者罢了。尽管如此,我三分之一的梦依然是以沈阳为舞台的。[2]”如果说所谓“故乡”既代表人的出生地同时又代表人汲取精神养分的根源地的话,那么可以说伪满洲是安部精神上的故乡——这与在全球化时代交错的文化背景之下长大的年轻一代是不同的。从存在主义的角度上讲,伪满洲是安部存在论上的“故乡”,它具有既排斥故乡又包含故乡的双重性质。
1945年底到1946年战后,日本文学开始复苏,一系列文学刊物纷纷复刊或创刊。战后初期开始创作活动的是永井荷风、正宗白鸟等老一辈作家,随之石川淳、织田作之助、太宰治、坂口安吾等“无赖派(新戏作派)”的文学也开始受人瞩目;之后是中村真一郎、加藤周一、福永武彦等在战争中汲取了西欧文化的养分并于战后组成“诗朗诵会”;野间宏、椎名麟三、埴谷雄高、武田泰淳、梅崎春生组成所谓“第一次战后派”登上文学舞台;继其之后,大冈升平、岛尾敏雄、三岛由纪夫、堀田善卫等崭露头角被称之为“第二次战后派”,而安部就属于这一团体。安部于1946年末回到日本后便开始文学创作。和有从军经历的其他战后派作家不同的是,安部没有让情感陷入感伤的现实主义中而是以战争为媒介开创了文学的新起点。虽然战争中安部抱有对现实的内在抵触感,但是他依然坚持彻底了解现实的态度,并且这种态度成为促使他去创作的契机。1948年10月,安部的处女作《终道标》作为战后新人的创作系列丛书获得出版发行。自此安部成为“夜之会”的成员,和花田清辉也开始有了交流。
“正当‘日本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我在殖民地长大,故而形成一个习惯,就是从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观察日本。[3]”当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成为当时日本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时,安部则在伪满洲近距离地面对战争。正如他所言,当时日本国内“日本主义”受到狂热的追捧并且“故乡”或者“乡土”的字眼充斥着人们的视听。安部当时远离“故乡”,日本和伪满洲地理上的距离最终成为安部心理上的距离。通过伪满洲来观察日本,他的文学成为其直面自身孤独的世界。“如果我是在自己的故乡长大,那么我大概会生活在贴近大地的日本式感官和日本式的美中。但是,因为我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成长的缘故,所有日本人都是令人厌恶的印象逐渐烙印在我心里……在那时,对于日本式的东西有一种本能的、天生的、原始的厌恶开始在我内心生根。[4]”这是日本“战后派”文学中先锋派作品《死灵》的作家埴谷雄高在和秋山骏、森川达也的交谈中讲述自己殖民地经历的部分。事实上,埴谷雄高的作品刻画了一个比安部更难解的世界。埴谷雄高和荒正人等一起创办了《近代文学》,确保了“战后派”文学的阵地。他们重新认识了人的存在,这是对非人道战争的人性的自我觉醒。因而他们的文学在创作思想上和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本质的不同,它反映了反现实主义的抽象世界,这毫无疑问是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西欧文学的影响,当然也和他们的殖民地经历不无关系。
1.2 经历日本战败和回国
安部公房初期小说隐含着两个深层的主题——逃避战争和从伪满洲回国。1944年10月,安部讲到:“不断传着战败将近的风声,我伪造了因肺结核需要休学的诊断书,逃过宪兵的监视去了旧满洲。[5]”安部当时作为“弃民”艰难生活直到日本战败投降。当时的混乱和太多的生活磨砺既成就了《野兽们向往故乡》,又成就了《内面的边境》。可以说伪满洲深深影响了安部公房的文学。
“混蛋!这些家伙竟然说日本就在对面!……但是,我真的想过要来这里吗?……真想去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啊!……况且,居然还和高在一起!……或许这一切都是在做梦吧……混蛋!就好像是在同一个地方绕来绕去似的……无论怎么走,却一步也不曾离开过这片荒野……或许,根本就没有日本这个地方!……只要我一走荒野也跟着我一起走。日本变得离我越来越远了……[6]”《野兽们向往故乡》这部作品是以殖民地解放而撤离回国的经历为背景的,它深刻地描写了主人公从荒野(伪满洲)到故国(日本)的苦难之旅。主人公久三虽然乘坐走私船回到了日本领海,但是却因一个叫高石塔的中国青年携带鸦片而两人被封在船舱中无法登陆日本。上面引文描写的是主人公的绝望的内心状态,同时也是当国家崩溃时个人的国籍、民族、意识形态被剥掉并惨遭抛弃的久三的内心写照。安部从伪满洲的灭亡中经历了“国家”的解体,体验了他一向奉若神明的权威、价值观念的崩溃,这和他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一起奠定了他文学表现的根基。吉田凞生曾经谈到,“久三明确代表了在旧满洲长大不知道日本就是自己‘故乡’的一个少年的典型形象,高石塔则代表了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人的命运”[7],“战争中我是存在主义者,故而创作了《终道标》。‘存在先于本质’的思想带有相当程度的自我否定。……存在主义开始瓦解是战后的体验。我在沈阳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目睹了社会根基的彻底崩溃,完全失去了对恒常事物的信任,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8]”从安部经历日本投降的体验来看,其“失去故乡”的问题愈发变得深刻化,而《野兽们向往故乡》正是将其全面形象化的作品。
“从终点开始的旅程没有尽头。必须讲述墓中的诞生。人为何必须如此存在?……啊,无名的人们啊,我要将这放浪捧给你们![9]”实际上《终道标》这部小说的标题处附有给当时一同前去的亡友金山时夫的献词。对此磯田光一指出:“对祖国一直怀有憎恶,出于对逝去朋友的怀念,旧满洲也可不能成为故乡。[10]”历史上的伪满洲国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建立的傀儡政权,当时居住在伪满洲的日本人也是所谓“满洲国”的国民,日本投降后这种双重性便不复存在。但是,对像安部这样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期的一代人来说,确实很难感受到日本作为“故乡”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日本反倒是异国他乡。日本投降、伪满洲的灭亡以及之后的撤离回国,这些从未经历过的历史事件在他们内心引起了巨大的混乱。“8月14日我得了霍乱,部队把我丢在马厩里就出发了。到了傍晚,同样是从北方溃败下来的另外一支部队经过这里。[11]”在安部的文学中,伪满洲与其说是小说素材,不如说是为了接近深层本质而被使用的方法。比方说,众所周知的变身、颠沛流离、逃走等主题都源于“伪满洲国”中动荡的生活状态。正如在《变形记录》中,日本投降前的八月十四日主人公因身患霍乱而被丢弃在荒野中,其处境和当时的“伪满洲国”是一样的。我认为这是和安部公房从日本与“伪满洲国”故乡意象的双重性中苦寻身份的“追寻故乡”的问题直接相关的。这种“失去故乡”所象征的身份危机不只是安部文学确立的契机,对于现代文学也具有更为复杂和重要的意义。
2 《沙女》中的“故乡”
2.1 迷惘彷徨——出发的前提
如前所述,安部公房的“故乡”问题意指“具有固定价值的一切事物”的概念。比方说,在《墙壁——S·卡尔玛氏的犯罪》中的“名字”,《他人的脸》中的“脸”,《红茧》中的“家”,都可以理解为“故乡”的概念。而描写逃离故乡、为寻找自己心灵故乡而苦闷彷徨的人就成为安部公房文学的一个主题。实际上那是寻找主人公失去的东西即“名字”、“脸”、“家”——“故乡”意象过程的隐喻。如果《野兽们向往故乡》是表现此类主题的典型作品,那么《沙女》可以说是这类作品的一个顶峰。《沙女》的开头部分讲到,主人公仁木顺平来到沙丘后发现所有的房子都建在沙丘斜面的洞穴里面。“沙丘的线条变得缓长,一部分延伸到与海相反的一侧,他在发现猎物的感觉驱使下,从平缓的斜面滑了下去,……视野一下子中断了,他发现自己站在可以俯视深深洞穴的悬崖边。[12]”
安部在《红茧》中描写了空茧中停止流逝的时间。红色在小说中暗示了黄昏时分回家的时间。主人公无家可归为了寻找栖身的房子在街头徘徊,按照意识中的逻辑最终找到了“家”。而这个“家”是通过主人公“我”的消失而得到的一只茧。茧壳外虽然已经夜幕降临,茧壳内却始终是黄昏,火烧云的霞光笼罩其中。时间在茧壳内停止流逝被定格在一点上,而现实中的“我”原地不动始终孤零零一个人在里面。这和《沙女》的结尾部分是相似的。如前所述,随着日本投降和“伪满洲国”的消亡,安部也经历了流离失所。因此,在以伪满洲为背景的初期作品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其中期以后作品中所描写的都市或沙漠中的彷徨者形象。《变形记录》和《野兽们向往故乡》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可以说,“故乡、故国”存在与否的存在论本质上是和“失去故乡”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他梦见自己骑在旧筷子上飞翔在陌生的街道中……街道的颜色近观呈砖红色,远观则呈现绿色。其颜色的搭配中有种令人莫名不安的东西。[12]264”在“失去故乡”的意识里,对于伪满洲的记忆和由此产生的迷途彷徨的情绪以空中飘浮的形式出现在梦中。安部公房曾经受过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也为无意识的自我表达如何能成为艺术的问题而苦恼过。因为“似乎患上精神衰弱的现实变成了社会实实在在的现实”[13],所以意识的深层作用便具有了重要的寓意。如果把安部作品中使用的“日暮”、“黄昏”这样的时间轴和“螺穴”、“蜂巢”这样的空间轴连接起来的话,就会得到一个呈多层延展的螺旋结构,加之处于上面的沙丘,整个结构便成为一个没有出入口的迷宫。而这个迷宫在作品中是有生命力的。
2.2 迷宫般的沙丘和封闭的共同体
沙漠是一个干燥荒凉、毫无生气的世界,为了生存那里的人们都必须绝对服从部族的命令并团结在一起。所以,作品《沙女》中的“女人”也必须同村民合作来应付沙丘的流动。为了得到水和食物,她每晚必须去挖沙。“这些洞穴围绕着部落的中心排成好几层,乍望去就像是一个要朽塌的蜂巢。村子和沙丘互相重叠在一起。呈现出一副让人无比焦躁的景象。[12]”对仁木来说,沙穴不只是逃避现实的地方,还是一个比现实更加严酷的地方。部落是典型的村落共同体,而且和共同体的祭物——“女人”是共生的。可以说沙丘是“个人与共同体”、“城市与村落”、“孤立与连带”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迷宫。
“女人为何必须如此执着于这枯燥乏味的挖沙呢?我一点也不明白。……虽然说出于‘爱乡精神’或者义理,可是在丢弃它的同时也会有与之一起失去的东西,不是吗?……究竟,她要失去的东西是什么呢?[12]270”首先来看“女人”和村民之间的关系,村民们把“女人”挖下的沙子用土筐拉到洞穴的上面运走。当仁木感叹于他们之间的协调配合时,“女人”答曰:“在这个部落中爱乡精神无处不在”。所谓“爱乡精神”顾名思义就是热爱家乡之心。但是,沙穴并不是“女人”的故乡。她口口声声称“爱乡精神”是因为对她来说,那沙丘不是故乡而不过是生存的地方。沙丘于她不是出生成长之地,却是关乎生存于其中的人的现实。
“意外的是,她在没有受到任何强制的情况下自愿去合作。……自愿去合作是所谓的人情吗?这种做法果真是合作吗?……我很怀疑……难道就没有更合适的其他合作方式了吗?……”[12]286“女人”不能离开沙丘部落实际上是因为以前刮台风时随牲口棚一起被掩埋的丈夫和孩子,和“爱乡精神”没有关系。即便如此,她还是和部落进行合作。从她这种奇怪的生存状态可以发现一个线索。那就是在表象背后隐藏着一个由部落土著势力强制构建的伪共同体,它建立在把寻找“女人”的丈夫和孩子尸骨作为口实的人情和义理之上。这个伪共同体就像食肉植物一样有着很强的粘性,其他生物一旦被它挂住便很难脱身。也就是说“女人”和部落的关系只是表面上的自发合作关系。主人公仁木随着对“女人”所处状况的深入了解,其不安感也越来越强烈。因为每晚“女人”的工作,就像“在黄泉路上垒石塔”一样,永远也不可能完成。随着不断适应沙穴中的生活,梦魇般的气氛也变得浓厚起来。“女人的这种举动和沉默让人觉得异常可怕。心底的不安最终得到了证实,虽然我觉得这并不可能。绳梯是在女人知晓的情况下撤走的,说明她对此是首肯过的。女人无疑就是同谋。当然这并非是羞耻之类难以辨明的东西,而是心甘情愿去接受任何刑罚的罪人或者是祭物才会有的举动。我彻底落入了陷阱,被囚禁在这犹如蚁地狱的沙穴中。和稀里糊涂地受到斑蝥的引诱被带进无处可逃的沙漠中去的饥饿小白鼠一样……”[12]295
主人公脱离了工作和家庭,让自己慢慢习惯沙穴中的生活,和“女人”的关系也融洽起来。他不断要逃出沙穴,但是却在逃跑途中发现了水,其内心因此发生了很大转变。
2.3 逃离与定居
“记得十几年前的那个废墟时代,所有人都在为追求不用奔波的自由而狂奔。那么,是否可以断言现在果真不用奔波便可自由地吃到厌腻?现在,你被臆想的对手折腾的疲惫不堪才被引诱到这沙丘来的,不是吗?……沙子……无限的流动……”[12]302如果把文中“现在”作为创作《沙女》的时间,那么就会发现所谓“十几年前的那个废墟的时代”正好就是日本投降前后那个贫困和混乱的年代。通过这种假设不难想象以安部为首的许多人都在为寻找“不用奔波的自由”而艰难前行。高桥和巳曾说过:“有人抱一种把世界的荒芜作为自己的荒芜的态度,因此其意义不在于叙述荒芜而在于得到了大众的共鸣。[14]”作为战争留下的遗产大部分人都不得不把现实的废墟作为自己的命运去接受。问题是“现在”即处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人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前行呢?20世纪60年代在日本历史上是经济高速增长引起社会结构变化和大众社会化的重大转折时期。它不仅体现为国民生产总值飞跃式的增长,也体现为社会政治文化等一切领域的巨大变化。1960年,反安保斗争后,在以学生和青年为核心的时代状况的虚脱和混乱中只有通过对现实的认识才能透视未来。而安部始终和现实保持着张力,他从根本上去思考像脆弱的战后民主主义和经济至上主义那样涌动在社会底部的现实的反面。那么,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对《沙女》解读会是怎样的呢?
主人公仁木来到沙丘后便被囚禁在沙穴中。虽然经济的高速增长带给废墟时代的人们“不用奔波的自由”,但人们最终还是厌腻了这种自由。如果把废墟时代的“自由”假定为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富裕生活的话,接下来(1960年代)便是继续前行追求与身份认同、思想、精神相关的自由了。那就是仁木继续前行的意义所在。也就是说,通过被囚禁在无意识中来到的沙丘,他看到了“不用奔波的自由”的可怖之处。
如前安部公房谈到自己在战争中是存在主义者,而伪满洲的经历使自己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另外,除了当时世界上流行的超现实主义对他的影响之外,还不能忽视把成为其理论背景的法国前卫派艺术理论介绍到日本的花田清辉的影响。当时,花田在《复兴期的精神》中把日本战后的社会转型期和欧洲的文艺复兴重合在一起提出转型期的生存方式这一主题。“拥有人类的面容和动物身体的斯芬克斯处于灵魂和肉体对立统一的状态,它并没有把两者的对立作为形式逻辑上二者择一的问题提出来,不管是灵魂支配肉体还是肉体支配灵魂,一律作为感伤的态度来回避排斥。同时它把这种状态看作是事物的本质,不纠结于无用的烦闷而是怡然自得地横卧在沙子上面。令人叹服的是它的这种样子真切地讲述着沙漠的精神——‘干燥的炽烈’。[15]”在上面的引文中他通过把完全不同性质的事物连接在一起的诗性直观展现给人们开拓未知现实的方法。《沙女》中的“沙”是主人公身处的内在现实和外在现实之间错位的隐喻。从花田对沙漠精神的叙述——“干燥的炽烈”中可以看到沙子内在的意象即一种硬质精神,越是接近这种意象,主人公内在的现实也就越充实。也就是说,主人公身处沙穴并逐渐发现了沙子的本质,最后水从沙子的底部渗了出来。“沙的不毛,并非像平常臆想的那样单单是因为干燥的缘故,而是因为其不断的流动并拒绝接纳一切生物。和一年到头只是不断强要他物的现实郁闷相比,是多么的不同啊。[12]”沙子原本是流动之物,《沙女》中的“沙”施加影响给生活在其中的人类,要他们都必须随它流动。“沙”让主人公扪心自问自己存在的根源,是促使其寻找“故乡”的原动力。从干燥之极的沙中喷出水来的描述暗指超越了物质科学范畴的人类内在精神的问题。
“整个沙就是一个泵。完全就像是坐在了一个抽水泵上。男人为了平静自己内心的悸动,暂时屏住了呼吸一动不动地弯腰蹲着。[12]312”在安部的作品中沙丘作为思索的场所出现的例子还有《墙壁——S·卡尔玛氏的犯罪》。“墙壁不断地成长着,就像是被大地的压力顶出来似的又像是因为周围的空虚而被抽取上来一样。……不久,在一望无际的荒野中墙壁作为一个纵轴像塔一样矗立起来。[16]”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同样坐在沙上思索着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的问题。他思索之后发现那只是“墙壁”而已。如同《沙女》的主人公仁木发现了从沙底吸上来的“水”一样,卡尔玛氏发现了从无边的沙丘地平线上矗立起来的“墙壁”。这两部作品中“沙”是将动力输入主人公意识的泵。通过从沙底发现水从而带给自己可以忍受现实的有别于之前的意识变化。那不是简单的回归日常生活,而是恢复了日常生活。既没有悲剧的个人主义也没有人性的丧失,只有完完全全的一个“我”存在在那里。所以,“沙”的本质状态与其说在于其所具有的干燥性质中,不如说应该在其包含的湿气中寻找其原本的意象。“沙”的意象是对死的有机物变化扩大到活的无机物的隐喻。在作品中暗指从安于现状的日常自我变化到超越现实的实践能动的自我。在《墙壁——S·卡尔玛氏的犯罪》中,相对于之前的“名片”代表逃避的有限的自我而之后的“墙壁”则代表一个本质的无限的自我。
“虽然身处沙穴,可感觉像是已经在沙穴外面,沙穴中的全景一览无余。如果不隔开一定距离看,那么马赛克图案是很难辨识的东西。而凑近认真观察的话,反而会迷失在断片之中。……大概之前他所看到的不是沙,而只是沙粒而已。[12]”相对于“土”是生物创造的有机物,“沙”则是石头或矿物在风化作用下形成的无机物。这两者对人类生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在生活中只有那些能够触动心弦的最本质的感动之类的东西才是重要的。
“现在他手里有一张往返车票,目的地和返回地都空着,任凭本人自由填写。可是,他一心想要把集水装置的事告诉别人。要是想告诉谁的话,这个部落的人是最合适不过的对象了。想必他打算不是今天便是明天就告诉别人吧!……第二天考虑如何逃走也来得及。[12]347”如上,在安部的作品中主人公想逃离却一直没有付诸实施。那是因为对主人公来说,“逃离与定居”最终就像是莫比乌斯环一样,虽然被扭着但却始终连在一起。虽然主人公为了能够从日常让人心烦的义务和无为中解脱出来而来到沙丘,但是最终却再也没有回到日常中去。对于他来说,再回到日常已经失去了意义。在他看来沙丘带有积极的动机,他对于沙丘是消极的存在(悲剧的个人主义和人性的丧失)。这种消极方面通过沙和昆虫作用于积极的动机,最终沙丘和他相互抵消。
3 结束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安部文学作品的根基中深藏着“失去故乡”和“追寻故乡”两个相反的潜意识。“失去故乡”和“追寻故乡”都是缘自他“没有故乡”。这其中还包含着和沙漠中的昆虫以及游牧民族一样,不得不靠单程票生存下去的严酷恐惧。通过安部公房“失去故乡”可以解读出日本人或者现代人的另外一种“失去故乡”的现实——在经济高速增长之下日本式感性的丧失。日本在二战后十年左右迎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许多人都经历过离开战前的村落共同体所象征的农村前往都市谋生的社会自身的变化。
出现在《沙女》这部作品表面背景中的沙丘,其背后隐藏着都市的日常状况。它是安部公房站在与日本战后完全不同的角度上来截取现实并构想出的产物。安部以“失去故乡”这个具有负面印象的现实作为文学创作题材,创造出正面的相乘效果。可以说这在日本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正如安部公房在其处女作《终道标》中所指出的,以“人为何必须如此存在”——对于自身存在的疑惑为基础,继而提出“人为何必须要如此定居在一个地方”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意识导致他之后创作出以“都市”为主题的作品。所谓城市是人群聚集的地方,但是人们越是对它趋之若鹜,对于“定居”的疑惑就越发的强烈,直到失踪人们不禁要问“人为什么必须要失踪?”,于是乎问题就这样不断地扩展下去。这就是安部公房式的辩证法,是构成安部公房文学的核心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