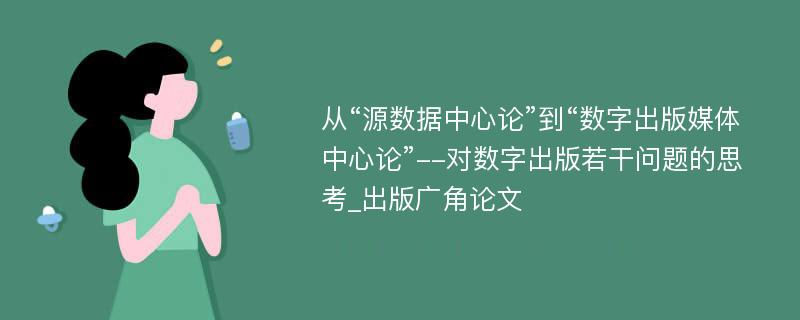
从“源数据中心论”到“数字出版介质中心论”——关于数字出版若干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数字论文,介质论文,数据中心论文,若干问题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数字出版是出版和IT相结合的出版方式,其基础是出版社所拥有的源数据和计算机技术。数字出版的形态包括电子书、博客、播客、数字期刊、电子词典、按需印刷、双语在线翻译平台、工具书在线、网络学习平台、手持阅读器以及手机出版等等,具有可移动的非纸质的海量存储的特征。目前在我国,数字出版市场空间广阔,前景看好,大量空白领域有待填补。
基于这样的形势,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在《我国将大力实施数字出版战略》一文中指出:“在‘十一五’期间,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及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三网合一’的逐步推进,我国将迎来比目前传输速度快千倍的第二代互联网的大规模应用,3G通信技术在传输音视频数据速度上的大幅提升,为出版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空间。未来几年,国家将大力实施数字出版战略,以推动传统出版业的产业升级和革新。”①由此可见,国家对数字出版给予了高度重视,今后在这一领域将有比较大的投入。但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的人发出了路在何方的疑问,有的人表现了徘徊歧路的彷徨,更有的人按兵不动,任凭数字出版之发展风云变幻,潮涨潮落……有鉴于此,当代出版界许多杰出之士对数字出版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他们纷纷著文立说,发表真知灼见,令人耳目一新。在此,笔者仅以“源数据中心论”为切入点,对有关数字出版的若干问题加以讨论。
所谓源数据,就是源头性质的数据,具体说来,就是那些以纸质书籍为蓝本,借助数字化技术处理之后生成的数字文件。这样的数字文件在内容上与作为蓝本的纸质书籍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存储的介质不同而已。任何一个出版社从事数字出版,源数据都是最为重要的基础。因此,目前出版界有关数字出版的讨论,也大都是以源数据为中心的。如蒋海鸥说:“源数据是出版社资源的沉淀和积累,尤其是专业出版社,多年的出版资源不仅使自己立于专家和权威的角色,也是今后赖以生存的食粮……没有细致完整的源数据,一切关于数字出版的项目、合作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②他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又产生另外的三种说法:一是“延伸说”。在第二届数博会上,商务印书馆副总经理江远宣布,在数字出版的产业链中,商务印书馆不仅要做内容提供商,而且要做数字出版商,争取并且掌握数字出版的主导权。他说,商务印书馆将把在传统出版领域多年建立起来的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努力延伸到数字出版领域,力争在数字出版领域打造强势品牌。③而商务印书馆数字出版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刘成勇在《主动介入、掌握数字出版的主导权》一文中也指出:“目前,商务印书馆数字出版的主要工作有四个方面:一是商务印书馆工具书内容系统……二是网络学习平台……三是电子书……四是按需印刷。”“通过这四大平台,商务力争将原有的品牌优势延伸到数字出版中来,并做出自己的特色。”④“延伸”的另外一种代语是“依托”,如尹翔宇所说:“真正的数字出版是依托传统的资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立体化传播的方式。”“只有根据资源的特点,设计数字化出版的流程,打造数字出版产品,完成资源的数字化、建立数据库体系和共享资源的管理信息系统,才能完成对内容资源的深度开发,使出版社变成真正意义的出版商。”⑤二是“书号决定论”。如谢寿光在《专业出版社的数字化生存》一文中说:“中国传统书业的成熟度较低,发展畸形,图书出版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始终是有限供给的书号和教材教辅这两根救命稻草,使得中国书业自觉利用信息技术、发展数字出版缺少现实动力。尽管各出版机构都承认传统书业已经受到了新技术的巨大挑战,但是,书号的有限供给决定了书号的价值所在,因此,即使是一家很小的出版机构,也可以凭借书号生存下去。”⑥在他看来,依靠书号的有限供给开发的精品图书才是出版社的核心资源。所以他又说:“要坚持对核心资源的自主开发。在发展数字产品上,出版社普遍采取的模式是和技术发展商合作,把资源卖给对方由对方开发,出版社只能分到点零头小利。如此一来,出版社就会始终受制于人,丧失了主动权,还影响了经济收益。因此,出版社必须把核心的内容资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自主经营开发;如果不坚持自主开发,就无法建立起自己的营销队伍,就掌握不了终端客户资源。”⑦而书号的供给,直接制约着源数据的开发。在这种意义上,在数字出版方面,我们由“源数据中心论”自然就会推导出“书号决定论”。三是“转型论”。“源数据中心论”和“转型论”说是密切相关的。在人们看来,既然当前我国数字出版的前景如此美好,既然出版社不能不涉足数字出版领域,既然出版社的源数据是数字出版的关键,那么,出版社就必须转型。转型的过程就是由传统的以纸质书籍为主的出版,变为以电子文本为主的数字出版。于是,人们提出了“传统出版业向数字化产业转型”的理念。⑧而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正是“第二届数字出版博览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数字出版的迅猛之势对传统出版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同时,纸质出版物的空间受到了挤压,数字出版的低成本效应极大地削减了传统出版的赢利水平。如谢寿光所言:“诸多现实都迫使传统出版人不得不考虑,传统出版如何向数字出版转型,如何实现数字化生存。”⑨我国的传统出版真的要向数字出版转型吗?出版社只有实现转型才能生存么?怎样来实现这种转型呢?实现转型后的结果又是怎样呢?我们看到,西方的数字出版高度发达,但人们并未放弃阅读纸质书籍,那么,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关系究竟如何呢?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冷静思考。因为从事任何事业,做任何事情,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面对数字出版的滚滚浪潮,在人们对出版转型的震天呼唤中,我们首先要选择,要抉择。还是让我们回到“源数据中心论”。源数据是纸质图书和数字出版的连接点。但是,以源数据为中心,所谓数字出版,实际就是纸质图书的数字化,而这一点正是我国出版界业内人士对数字出版的普遍看法。目前,大多数出版社所开展的数字出版业务就是如此。就此种意义上的数字出版而言,一个出版社所拥有的出版资源,编辑队伍的实力以及在读者群体中的知名度,对其数字出版肯定是有决定性影响的。谢寿光说:“数字产品对出版者和消费者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增值服务,出版数字产品是内容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和最优化。”⑩这种增值服务无论对出版企业,还是对广大读者,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伐木者无论如何不能自伤手足,拓荒者无论如何也不能忍饥挨饿,作为专业出版社,一旦开始数字出版的艰难旅程,痛苦便会随之而来,那就是数字出版物对纸质图书的销售必然产生负面的影响:一方面,正版数字出版物的廉价,读者自然对其钟爱有加;另一方面,正规的数字出版物经常遭到盗版,而这些盗版的数字出版物的价格更为低廉。因此,当人们怀抱着丰富的源数据做着数字出版的美梦时,暗夜里的众多魔鬼也在窥伺着夺宝、掠美的良机。数字出版需要绝对的法律保障,而这种法律的保障来自纯粹法制的社会环境和人们普遍遵守、尊重法律的文化自觉以及购买正版数字出版物的基本经济能力。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因跌止步。数字出版的道路究竟怎样走,如何来开展具体的实践,这些问题人们是应该谨慎对待的。依笔者之见,在目前的情况下,从事数字出版必须慎重,至于向数字出版转型,既然转型不容易,就不妨稍安勿躁。笔者之所以作如是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数字出版无论如何发展,其数字读物永远取代不了纸质读物,正如电脑永远取代不了人脑一样。电子读物适合浏览、检索、拷贝、传播,但并不适合欣赏性质的阅读,真正的读书的快乐恐怕永远与数字化无缘。因此,传统出版不仅不可废,而且还要大力发展;在发展传统出版的同时,也要发展数字出版。对出版社而言,此二者不可偏废。而事实上,从“源数据中心论”的角度看,此二者之间同消同长的共生关系,也决定了我们必须对它们兼容并包。
如前所述,“源数据中心论”是出版界关于数字出版的流行理论,这种理论的核心是源数据,而基础则是纸质图书。这种理论的具体实践表现于数字出版的生产流程,那就是:“纸本图书→源数据→数字出版物”。数字出版物的出版介质当然是电子的形式。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换一种模式,以数字出版介质为中心,则无疑能够扩大、拓展出版社数字出版的功能。这就是本文提出并要特别强调的“数字出版介质中心论”。这种数字出版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以数字出版介质为中心展开数字出版工作;第二,在实现数字出版的过程中,出版社所使用的数据,可以是在其原来拥有的图书资源的基础上产生的源数据,但是,这种源数据必须适合数字出版介质的特点;第三,独立开发适合某种数字出版介质的数据,即不生产纸质图书,直接为某种数字出版介质独立地开发选题;第四,以传统的编辑作业所培养的功底为基础,以数字化的形式执行编辑部门的功能,以切实保证为数字出版介质所提供的数据的质量。
我们试以手机出版为例对此加以说明。手机出版的主要形式有手机短信、手机小说、手机新闻、手机报纸、手机音乐、手机游戏、手机视频等等,它们已经开始广泛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按照我们关于“数字出版介质中心论”的思想,针对手机出版单独开发源数据,为读者提供时尚、美好、适用的手机读物。如从年龄划分,可以开发:(1)青年手机读物系列;(2)中年手机读物系列;(3)老年手机读物系列。从身份划分,可以开发:(1)中学生手机读物系列;(2)高中生手机读物系列;(3)大学生手机读物系列等等。我们可以根据手机用户人群的不同特点进行相应的选题开发。全国的手机用户已经将近5亿人,所以手机出版的市场空间是相当巨大的。当然,如果出版社原有的出版资源适合手机出版之用,也可以直接拿来;如果不完全合用,可以做适当的改造,使之适合手机出版的需要。无论如何,手机出版必须以手机这一特殊的数字出版介质为中心,从而形成手机出版的个性与风格。所以,在手机出版方面,“源数据中心论”不一定完全适用,也不一定完全不适用。当然,按照“数字出版介质中心论”的思想,“书号决定论”已经完全不适用于手机出版了,为什么?因为手机出版根本不需要书号,尽管它非常需要出版社的品牌。就此而言,手机出版的空间是无限大的。面对这无限大的出版空间,现代的出版者是手足无措,还是马上行动?当然,手机出版如何通过在管理部门的注册保证自己的权益与合法性,这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2007年7月17日《中国新闻出版报》。
②《传统出版社:数字出版的困境与思索》,《出版广角》2007年第7期。
③参见郝峥嵘《数字出版回归本源出版社借内容握主导权》,2007年8月6日《中国计算机报》。
④《出版广角》2007年第7期。
⑤《数字出版与业务流程管理》,《出版广角》2007年第5期。
⑥见http://xieshouguang.blog.china.com.cn。
⑦同上。
⑧蒋海鸥《传统出版社:数字出版的困境与思索》,《出版广角》2007年第7期。
⑨《专业出版社的数字化生存》,见http://xieshouguang.blog.china.com.cn。
⑩《专业出版社是发展数字出版最佳突破点》,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17日《新浪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