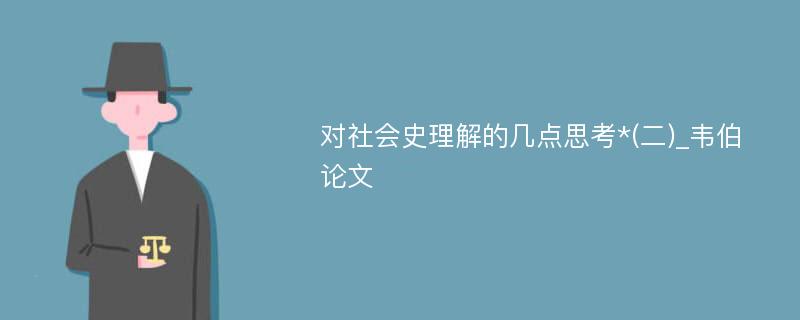
关于社会历史认识的若干思考*(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社会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历史的认识能否“价值中立”?
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的历史。由单数的人变为复数的人群的集合,不祗是量的累积。复数的人群不可能简单地还原为单数的人。“社会”作为一种“整合”人群的“突生现实”的出现,意味着人的境遇因此而迥然不同于生物界。自然科学(包括生物学、生理学)的方法不能不在这里受到严峻的挑战。
无论是对自然界还是对社会历史的深层思考,都存在着有关“一与多”的“哥德巴赫猜想”试解。莱布尼茨或许是受周易的启发,他创造了“单子”概念,说单子既不是单纯的一,也不是纯粹的多,而是“统一性中的多样性的表现”,是一个动力学的整体,只能在无限丰富的结果中表现自身。这虽然仍不脱“概念游戏”的技法,还是顽强地再现了不满足于“多样性”而欲寻求“统一性”的人的思维天性。同样,百年来关于中西社会及其文化的比较研究,多专注于殊相的抉发,也忽略了一个实在不应该忽略的思考,这就是:“从本质上来看,不同的国家的人民为同样的难题所困,为同样的疑团所惑。”(许思园先生语)从自然中脱胎出来的人,既是一个理智的存在物,又是一个社会的存在物。当他(这里指复数的人)脱离幼年的混沌状态开始获得“自我”意识起,命运注定了下述难题必将伴随着始终:个体与群体的矛盾,自然赐惠与人为索取的矛盾,物质享受与精神需求的矛盾,自由与秩序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稳定与变异的矛盾等等。除此而外,对个体而言,还有情感与理智的矛盾,生与死的矛盾等。中国古代关于群己之辨、理欲之辨乃至心物之辨、生死之辨,说明我列祖列宗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思索决不逊于世界任何别的民族,也再次证明人类面对的难题都是相通的。
社会,乃是人群合分聚散无定的“驿站”,天地悠悠,过客匆匆。个体的人既天赋有独立自由发展的要求(因为他是理智的存在物),又无以单个生存而必须合群,始于男女,成于家庭,外化为民族和国家(因为他是社会的存在物)。社会历史上所呈现的种种戏剧性的变化,无不基于人内在的本能要求(本我)与外在群体整合的要求(超我)的张力,其余一切矛盾都是由此而派生的。本我与超我、个体与群体的对立统一,是社会内在的结构性矛盾的“根”,是其它一切变化的最终的“深层原因”。当我们的视线转到“社会”,就必然首先地要指向个体与群体的整合。群体总是以利益的游戏法则组合的,人与人之间是以有形的或无形的“协议”(或曰:契约)互相联结,求同存异。每个个体必须出让部分权利以获取可能得到的权利,“利益最大化原则”只能在边际效率的函数集上才能得到确认。“正义”、“公正”、“合理”等等都是以特定的“协议”认可为前提的。最好的“平等”也只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每个个人权利的平等。克尔凯戈尔不无深情地说:“在一切痛苦中最为痛苦的是,既要完成精神任务(他指的是“精神自由”),同时又要生活在人群中。”这是个体精神至上者想摆脱“协议”的痛苦。卢梭是属于激进的一派,“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着眼的是政治或国家形式对人“约束”的夸张。道德理想主义者,恰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为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提供充分条件的社会。然而迄今为止,个体与社会的匹配契合,始终为一些最基本的难题所困惑,由此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人类先知圣贤们所渴求的那种完善,就成了社会发展中驱之不去、挥之不就的永恒“情结”。
人文学者,包括历史学家,通观古今中外已有的社会演进,不能不感慨万千,面临着评判上的尴尬。犹如人生诸多烦恼,叹道“人生就是过程”,社会的历史何尝不是如此,“过程”本身即是它的真义所在。我们找不到无可挑剔的完美,看到的只是对完美不懈的追求。转而不能不修正我们的期望,说道:“寻求的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不是成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卡西尔《人论》)“上帝”给我们的是一杆永远找不到合适平衡的、处于摆复中的“天平”。前述的种种两难,如阴阳两极相济,此重彼轻,过份倾斜到哪一头,而冷落另一端,社会都难得安宁,人们也不会感到满足。重则轻之,轻则重之,矫枉而过正,过正则再矫之,无穷的摆复调整,这就是社会动态的运行,这就是全部社会历史的真义。从这一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是不断“试错”(借用科技术语)的历史。那些为众人不满意、不合理的旧事物虽随变革潮流而淘汰,新的不满意、不合理又接踵而来,不舍昼夜。变革,将是无穷无尽,如危崖转石不达其地而不止。试看古往今来,转折之际变革热情高涨,人们基于对现状的不满,在先贤圣哲的理想之光的照耀下,一往无前。对未来期望值之高,必会鼓动出那种以身殉道、义无反顾的勇气,造作出种种可歌可泣的事件和人物。可是,一旦峰回路转,进入新的坦地,失望的情绪便会慢慢爬上心头,愈积愈重,社会现实并没有像期望的那样完美,还平添出原先想不到的许多讨嫌,于是就有了新的不满意,又有了所谓“超越”之类的新的追求。即以现代市场经济所引发的社会变革而言,无疑是对传统社会“群体”窒息“个体”极端倾斜的校正。现在又对个性的过份肆虐感到威胁,试图压抑之,故而西哲又忽然对东方群体主义格外垂青。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透露的便是这样一种信息。作如是观,方不至误读了汤因比中国将充当“世界大同的领导者”之类的预言。
我很欣赏卡西尔富有哲理的阐释:“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正是矛盾……人是存在与非存在的奇怪的混合物,他的位置是在这对立的两极之间”“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因此,数学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学说、一个哲学人类学的工具。”(《人论》)人是如此,社会则更是如此。传统的逻辑和形而上学本身由于同一律(不矛盾律)而不能理解和解释人与社会那种“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永处于创造和流变中的谜。社会的不和谐就是它自身的相和谐。前述永恒性的两难,对立面并不是彼此排斥,而是互相依存。社会正是在这些不同的力量之间的吸引中获取张力,在对立、磨擦和冲突中展示顽强的生命活力。历史的长链上每一环,好与坏都是相对而言的,无绝对的好,也无绝对的坏。
自从赫胥黎、达尔文发现并确证生物进化的历史以后,社会进化的概念也就深入人心。社会进化既与时间的尺度“同一”,演进的价值似乎也就变得可以用算术级数甚至几何级数来计量,一切都会由低级到高级那样有序的向前“逻辑发展”。中国古代哲人本不是如此看的(他们将历史运行的轨迹看作为圆),到了近世,我们也就相信了进化论,数典忘祖,追踪流行。细究起来,实在也很难判定究竟哪种说话法更逼真地还原了社会演进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多面性。前面我曾经提到过英国白德库克的《文化的精神分析》一书,他是采取倒过来的说法,声称农业社会是采集经济的“回归”,而资本主义却是畜牧经济的“回归”。我并不认为此种说法就一定成立,但应该承认它在触及社会心理乃至时代精神(前者驯顺内敛,后者野性外溢)方面是不可多得的传神之笔。最激烈的要数卢梭,他曾“忽如狼嚎般狂吼”道:“文明是道德的沦丧,理性是感性的压抑,进步是人与自然的分离,历史的正线上升,必伴有负线的倒退,负线的堕落……”(转引自朱学勤《启蒙三题》)。也许人们可以将这种激愤斥之为“道德”情绪化,想不到一向被认为“理性”的经济领域也存在着进与退的悖论。前面多次提到布罗代尔的三卷本《15~18世纪……》,洋洋150万言,只在读到他本人多次演讲、 答辩后,对该书的微言大义,才开始有某种感通。布氏认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由前者发展为后者,原先任何人都不占优势的、完全凭运气决定输赢的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被破坏,变成可以由“少数人串通交换纸牌”来“作弊”,造成了交换方面更大的不平等。布氏说道:“当有一种权力主宰市场时,那就是资本主义,因为在市场上进行的是不平等的交换。”对此,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罗代尔研究中心主任沃勒斯坦,作为朋友和该著作的研究专家,替布氏的“作弊”说下了更直白的注解:“没有政治作后台,谁也不可能独揽经济,更不可能有驾驭市场的能力。为了对经济活动设置非经济的栅栏,为了让桀骜不驯的价格唯命是从,或为了保障非优先项目的采购,必须由某一政治权威施行强制。所谓没有国家为后盾或与国家作对的资本主义,纯属无稽之谈……某种意义上说,近500年的历史是市场节节败退的历史。 ”实际上,布氏反对的是经济的“垄断”趋势和国家及国际政治的“寡头统治”,他认为这不是缩小了不平等而是扩大了不平等。关于这些判断的正确与否绝非本文所能说清的,这里无非是想说明,单线的、绝对的“进化”,把“进化”等同于“进步”,并非毋庸置疑、不可反驳的。
这种情形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时,中国人遭遇到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交战中,也反映得十分明显。再次证明对社会历史的动态运行,我先哲前贤的认识也远非清晰透明的。
无论是严复、章太炎、梁启超,还是王国维、陈寅恪,作为本世纪的一代学问大家,国学根底深厚,多兼通西学,也接受过进化论,严氏更是这方面的播火者。然而,真的面对社会转型种种“色相”,诸贤似乎就顿然失态,对西方现代化的负面特别敏感,担心中国步其后尘,重罹“物质富裕,道德沦丧”,以及弱肉强食、残酷斗争,人被严重异化的灾难。他们以“人心”或“国民性”为题旨,对当时社会演进的不满、激愤,形诸于色。章、严晚年更趋悲观,颇眷恋中国往昔的辉煌,不堪直面未来。由此在中国近世界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景象。首先,我们的先哲前贤睁眼看世界时,感觉到的不仅仅是现代化耀眼的荣光。这是因为,带血腥味的资本,西来殖民者对中国横蛮的掠夺,在中国人面前尽情裸露出了西方现代化的另一个侧面——丑陋阴暗的一面;与此不无关联,欧风美雨下中国社会特殊的变形,表明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完全排斥,权力之恶与金钱之恶可以交互为用,人性中原有的恶很可能会被新的诱惑教唆得更恶、更放肆。对此,民族的文化基因作出的回应又是西人所没有想象到的:原始儒学开创的理想人格与伦理至上的文化传统,使中国的人文学者特别注重人性向善的追求。老庄反社会、非难理性的哲学思维,特别是周易的变易哲学,又为中国人考察西方现代化提供了一种东方式的敏感和非线性的变易观,使中国人有可能摆脱西人那种昏昏然浸染于单线进化和满足于物质成果之中的自得,藉助交易的观念预感到肯定与否定、进步与退步必将负阴抱阳兼容并蓄,由此陷入极度困惑之中。
多年前,我还不能读懂前贤的苦恼,现在却有点开悟了:其实,既有的现代化模式,都是有利有弊、有善有恶,进步中包含着某种退化乃至退步。利益也不可能一体均沾。它不仅是利益的再分配,更为难堪的是,必然要从魔瓶中放出“欲鬼”,来个“孙行者大闹天空”,野性发作,使原有的秩序和平衡不复存在。西方先行者因为是自然演进,很像是摸着石子过河,顾前不顾后,见不到为净。后随者则大为不然,前辙清晰可辨,泥沙俱下,心态就复杂尴尬,进退取舍颇费踌躇在情理之中。严复是以翻译《天演论》而名震遐迩的,可晚年却对他一度钟情的进化论有非常刻薄的批评,说:“不佞垂老亲见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我以为,进化论自有其思想史的价值,但对进化论的诘难,更有它独特深刻的意蕴,不可忽视(这话题太大。有一点可以指出,即使在生物学界,达尔文进化论也已经修正,出现了不少新的学说。就说进化,它也不是绝对的。例如人为万物之灵,是生物进化迄今为止的最高成就。但是人的视力不及猫头鹰,听觉不如鸟类,行走还比不上兔子敏捷。当然这只是就个体生理功能而言。人类、即复数的人之高明,在于能创造出许多替代物,以弥补生理的退化)。1920年春,梁启超由欧洲考察回国,一改常态,竭力渲染欧洲的混乱和悲观主义,申言科学虽在欧洲赢得了绝对的胜利,但现在在凋谢干枯的、机械唯物论的西方,人被赋予了无人格、不安全感、忧虑、疲劳、闲暇的消失以及扩张欲凝聚的恐惧和丧失自由等特征,这是一种典型的精神贫乏症,故必用“以精神为出发点”的东方文化“救治”之。不期然,相隔不到半个世纪,却成了西人的“文化情结”,历史就是这样值得玩味!如果今天还把前贤对我们生存困境的普遍忧虑,祈求、警戒中国近世切莫重踏人性异化的歧路,看作为一种文化保守,那实在是对上述人类的生存困境和社会演进的矛盾性缺乏必要的哲学感悟了。
近代中国的哲人基于对本民族的人文终极关怀,不期然地与西方本世纪“物质——精神”的“世纪难题”发生耦合,早熟或超前地对资本主义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作了许多深刻有价值的批判,其精彩决不逊于本世纪批判“理性主义”的西哲,并显示出东方特有的人文主义的德性智慧。近来陈寅恪研究成了一个新的“热点”,我很不同意有些学者把先生看作“文化遗民”或什么“文化亡灵的守护人”。恰恰相反,基于前述的理由,在我看,与其把先生比作过去,毋宁将先生视作代表着未来,更切近对先生学术思想普遍价值的理解。先生虽激愤地说过,文化无法迁就实用,道德尤不济饥寒,但先生发自内心的祈愿,是他相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迟早会觉悟到文化与道德是他们永恒存在的“根”。哲人说得好:“无用之用乃为大用”。这里的“无用”,就是那种属于最高的、永恒性的东西。此时人们看来无用,说不定彼时突破会感到大大的有用。无论是陈寅恪,还是章太炎、严复,今天读来就要比一、二十年前亲切可解得多:我相信,下一世纪的人会更清晰、更强烈地意识地他们的价值所在。前辈的道德关怀和道德感召力,将使后辈获得一种张力,不至随着“资本”的诱惑而盲目狂奔,失去人类应有的自制力,沦为另一种动物——物质和金钱的动物。
相信科学客观主义的人,很可能会站出来大声叱责: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不容许择入主观的价值判断。学界朋友都熟悉,正是马克斯·韦伯主张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应该持“价值中立”的立场。然而,当我把他的名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读了好多遍,有一天突然发现,韦伯自己也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因此,我写下了一篇读书札记,题名为《悼念韦伯的精神分裂》,兹转录于下:
知识分子是人,是人就理应具有情感趋向和精神寄托。韦伯是一位著作颇丰,多方位有成就的学者。但,他首先是一个德国人,一个大日耳曼人。无论是他的经济学,还是他的社会学著作,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德意志这个国家和民族深挚的爱和热切的期望,期望她能在整个世界中扮演主角。唯因其爱之深沉,故而恨又显得特别激烈。他哀怨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该落后于英美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特别不满意那些“一心只想吃得舒服的有名无实的”德国新教徒。精神分裂病症发作后,他去美国旅行考察,更加深了这种刺激。
韦伯是以提出西欧资本主义发生独特的论证而享誉全球的。但即使在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义精神》这部核心论著时,他对当时欧美资本义现状也并不完全满意。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种内在的心理矛盾。在该书的最后几页,他竟诅咒起资本主义文明。他要比他的同胞施宾格勒和英国的汤因比都更早敏感到资本主义的机械理性正在吞噬着人性,文明的发展将要以文化的堕落作为代价,招致人心腐息,道德论丧。他说深受机器生产技术和经济条件制约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已经把“财富”这一昔日圣徒们随时可以抛掉的轻飘“斗篷”变成了一只禁锢人性、污染灵魂的“铁的牢笼”。他接着发表了一段略带怨尤凄楚和无可奈何的独白:
“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我不知道最后引号内的那段警世之语出自何处(原作者和后来的译者均未加注),够尖刻的。整段话连语言的风格,都活现出哈姆雷特式精神分裂的特征:不是一个具有精神分裂“异常”的人(或许这就是福柯所说的“癫狂”),是写不出这样深刻的话来的。至今读来,痛彻肺腑,又那么真切。
出人意料,强烈的激愤,没有使韦伯变成尼采,发展成尼采笔下呼叫“上帝死了”的疯子,相反他却从“上帝”那里找到了自认为可以慰藉破碎心灵的一块“净土”。那就是新教伦理。正是靠着这一直觉加细密的论证,发现了前人从未发现过的资本主义的“发生学”秘密。其实,这也并没有医治好韦伯心理的创伤,填平他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更没有使他的情绪稍为乐观、开朗些。他内心的精神分裂因此变得更深沉,更难熨灭:越是觉得“斗篷”的珍贵,就越难忍受“铁笼”的煎熬,恐怕只有在他全身心地投入时,才短暂地忘却了痛苦和焦虑。唯其如此,越是要奋笔写作。这就是他最后10余年创作速度、数量惊人,以及56岁英年早逝深层的心理背景。
新教伦理是不是西欧之所以率先产生资本主义独特性的关键原因,在东西方都有争论,不想在此多置一词。众所周知,韦伯在历史因果模式上是持多元、相对的立场的,即使是以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发生史上的地位而论,韦伯在其著作中也从未有过肯定性的明确单一的界说,而且非常反感别人由此引出简单化的“决定论”色彩的公式。正是新教伦理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要归功于他母亲的身教)促成了韦伯精神性的创造,他分裂而不疯,愤激中始终保持着穿透历史迷雾的冷静,依然不失学者慎密思辨的风格。
韦伯自己从不承认信教。但在我看来,在他的静脉里流淌的正是新教徒的血液。或者也可能是犹太血统的缘故,天赋中就有一份宗教的精神。新教精神救了他,也成全了他的学术伟业。是新教的敬业严谨,促使他崇尚科学精神和“价值中立”。他一再告诫自己,也对别人宣传,科学不容许将主观价值和信仰判断引入学术研究领域,为此,他决心走进历史王国,以冷峻的历史感审视全部资本主义发生史,暂时将个人的情感趋向和精神寄托抛在一旁,如实地发掘资本主义产生内在复杂多样的原因。正因为这样,多少人误以为是韦伯为资本主义作了最善最美的辩护,以至列宁不无反感地称他为博学、胆小的“资本阶级教授”。为了澄清对韦伯的误解,我想在这里引一段他最富哲理性的话:
今天,我们再一次认到,一事物之所以为神圣,不但不为其不美所妨碍,而且唯其为不美,方成其为神圣……
一事物之所以为美,不但不因其有不善之处所妨碍,而且唯其不美,不神圣,不善,方可成其为真。
韦伯的内心无疑最虔诚的皈依真善美,有神圣的理念追求,但在他将历史倒过去、翻过来认真严肃地审视之后,出语惊人:抛掉幻想,世上本无真善美集于一身的神圣。近乎阿Q式的解嘲, 生动凸现出摒弃一切感情色彩的历史学家的冷峻。在历史的法庭上,道德的辩护是不被接受的。人们只看,今天是不是比昨天、前天多提供些什么。这里,只有加法受到欢迎,至于减法却只能深埋进心底。由此推论,正宗的历史学家,内心恐怕很少不是精神分裂的,一定要换成学术性的表达,也叫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紧张和焦虑。
我敢说,韦伯从骨子里痛恨对财富贪欲的追逐。然而,他亲眼目睹了积聚财富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以及支撑这种经济秩序的工具理性,这正是他期望德国强大所需要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道德与效率,韦伯深知在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发生着严重倾斜,后者还有可能将前者撕成破布。他不平衡(因为他深知人类舍此没有别的更好选择),却必须找到平衡。我从韦伯的学术实践中,失却了对他“价值中立”的信念。到头来,韦伯还是唱出自己心中的歌。这又非凭空从“子虚”中捏制出个“乌有”来。韦伯的办法,犹如整理一团“历史发生学”的乱丝,果断地撕断舍弃他认为对他无用的丝线,将有价值、有意义的串起来,编织出一个美的境界——他告诉人们,不是那些贪得无厌、纵情声色的政治暴发户、奸商、海盗,而是刻苦、勤奋、吝啬的新教徒在“天职”的信念下开创出近代工业文明。无疑,这是大可争议的。其实,社会转型并不是一首田园诗,倒像是一场乱哄哄的闹剧,生、旦、净、丑,各色俱全,鱼龙虾鳖均有杰出的表现。然最终成功者,还是韦伯所断言的那样,必是正正经经的人,而非七歪八扭、靠不正当手段致富者。那种人成不了大气候,匆匆过客,兴也勃其败也速,下场、结局未必好;即使老子侥幸保住,儿子挥霍,一样输得精光……这是很值得正朝着“工具理性”路上狂奔的所有人三思的。
从社会历史评判的源头出发,流出的却是两条河床。一条是实证的、逻辑的,它以其严谨、科学的态度讲求重事实、重证据。在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说“存在即是合理”,某一主观价值判断都不容许去改变证据或论断的客观性。一条是价值的、体验的,它是以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或普遍的人道主义来审视一切历史,更正确地说,它是以批判的态度从对历史的审视中展示人的最高理想境界。我们对此很难舍割任何一方,鱼与熊掌都欲兼得。正因为如此,我宁愿用“精神分裂”这一可能难以被人接受的形容来指称历史学家的学术境况。一切富有价值的创造可能正是源于这种内在的紧张。不过,在我看来,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应用性的社会学科,都应该有两者的心思,但侧重点或主旨是不同的。社会学科往往更多地关注当下社会发展的难题和操作路线,具有明显的社会功利性。可行不可行,有利与无利,是他们所关注的重点。作为人文学科,历史学家应具有超越功利和特定时空的气度,尽管他们的研究对象具有时代性和暂驻意义,但透过对特定“存在”对象的意义阐释,表达的则是超时空的真、善、美最高准则的追求。当有人以经济学理论(即市场会促使成本和利润趋向均衡化)责难布罗代尔前述的资本主义“更大不平等”说时,布氏十分含蓄地回击道:“您已为我证明,一位经济史家不可能同是经济学家。同样,经济学家又兼顾历史的实属罕见。因为这很不容易……”。此处省略号是会议记录中原有的,言犹未尽,然一切都在不言之中——对学者而言,其间的微妙都是不言而喻的。
不能了结的“情结”
中国这个民族天份极高,智慧多来之于直觉,即使是对民族历史的认知也离不了心灵的感悟。太史公写完《(汉)高祖本纪》,突发一段“古今之变”的通论,值得诵读:“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薄。故救薄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教学的需要,《史记》是读过多遍,唯有这段觉得最深奥,最难读懂,也最耐读(恕我孤陋寡闻,今人治史学史,也少有对此段作解释的)。读船山先生的《读通鉴论》,也随处皆有这种西人无以理解的特别的感悟。试举一则:汉平帝时,陵阳严诩任颖川守,以孝行为官,“谓掾吏为师友,有过不责,郡事大乱”(略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地方胥吏的贪黩向为人不耻。放纵这类人物,没有不坏事的)。王莽却“慧眼识人”,将他推举为全国“美俗使者”另有重用。史载“诩去郡时,据地而哭,谓己以柔徵,必代以刚吏,哀颖川之士类必罹于法”。船山先生说:“乃思其(指严诩)泣也,涕泪何从而陨?诘之以伪,而诩不服;欲谓之非伪,而诩其能自信乎?”由此引出一长段议论:“呜呼!伪以迹,而公论自伸于迹露之日;伪以诚,而举天下以如狂,莫有能自信其哀乐喜怒者,于是而天理、民彝澌灭矣。故天下数万蚩蚩之众,奔走以讼莽称莽而翕然不异,夫岂尽无其情而俱为利诱威胁哉?伪中于心肾肺肠,则且有前刀锯、后鼎镬而不恤者。”识者皆知,这是针对王莽特定的时代现象而发的,回答了一个为人疑惑不解的问题:王莽何能以“伪”而获誉当时?以“伪以诚”三字立论,在我看到的今人王莽研究中几乎未见,假如到了西人手里恐怕可以做成一篇大的历史心理分析的文章,但也未必能尽达船山先生的意境。联想上面太史公的引文,我朦朦胧胧觉得,它简直就是“文之弊小人以薄”绝好的注脚。千年之间,互通感应若此契符,这是因为我先哲思维深处都有一部《周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这也就是我近年来对寅恪先生“神游冥想”说由衷服膺,而以为它应该成为史学仰之弥高境界的缘故。
有诗云:“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探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我在想,反正谁也不可能亲到“历史”的“长安”,画出的秦川景是由画者的心灵托出的,尽可以责之“非真”,也应无怨无悔。至少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拙著,一定是这样。也许,过不了多少时候,连我自己都会讨嫌它。我倒觉得福柯的话很合吾意:“不要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一成不变”——当然,朋友们大可不必担心,我没有能力成为福柯,别说才智,最大的障碍还在我毕竟理性过剩。是为导论。
标签:韦伯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读书论文; 道德论文;
